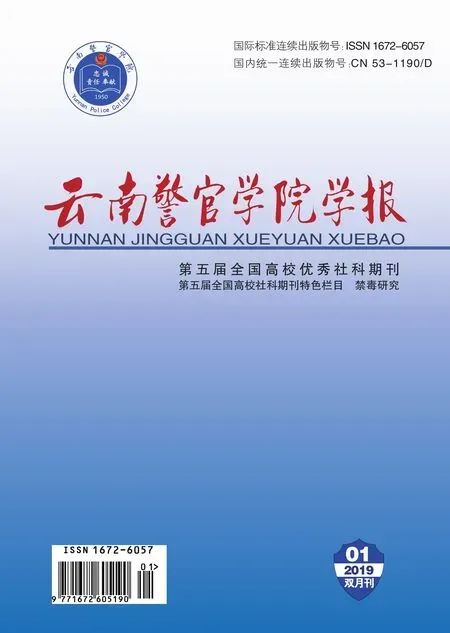警枪使用的法律要件研究
2019-03-04邵奇聪
邵奇聪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 102623)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以下简称《人民警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以下简称《警械和武器条例》)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注具体包括《监狱法》第46条、《反恐怖主义法》第62条、《戒严法》第28条、《看守所条例》第18条、《海关工作人员使用武器和警械的规定》第4条、《人民检察院枪支管理规定》第14条、《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条例》第12条、《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条例》第14条、《公安机关公务用枪管理使用规定》第22条、《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现场制止违法犯罪行为操作规程》第33条等。共同确立了我国警枪使用的法律要件,对警察使用警枪的法定情形作出了具体规定。然而,由于我国警枪使用的法律要件极不完善,在具体适用中存在诸多问题,致使公民的人身权利受到极大侵害,甚至还导致开枪的警察被追究法律责任。即便警察开枪情形符合法律规定,也会引起社会的质疑。例如,在“庆安枪击案”中,醉酒男子抢夺警棍袭警并意图夺枪,警察情急之下开枪将其击毙,虽然公安机关、检察院的调查结论都表明该案中警枪使用合法,但公众对警察“开枪是否合法”“击毙是否合理”等依然存在怀疑,致使警民关系陷入危机。为了解决我国警枪使用法律要件存在的问题,本文在比较考察美、日立法的基础上,对警枪使用的法律要件进行详细、深入地研究,以期对我国警枪使用的法律要件进行完善。
一、我国警枪使用法律要件存在的问题
我国警枪使用的法律要件主要规定于立法层级较低的法规和部门规章中,立法层级较高的法律层面规定过于简化,使得法律要件的合法性不足。而且,由于不同的法律、法规存在立法先后及立法主体的不同,使得有些法律规定的内容存在冲突。此外,我国警枪使用法律要件还存在立法内容不明确、情形过于烦琐以及法律要件不健全等问题。
(一)警枪使用法律要件缺乏充分的合法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第5条注该条规定:“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监狱、劳动教养机关的人民警察,人民法院的司法警察,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警察和担负案件侦查任务的检察人员,海关的缉私人员,在依法履行职责时确有必要使用枪支的,可以配备公务用枪。”赋予了人民警察依法配置警枪的权力,但未对使用警枪的问题作出任何规定,所以原则上使用警枪应当由其他法律单独作出规定。1957年颁布的《人民警察条例》(现已废止)第6条第4项规定警察执行职务遇有法定情形时可以使用警枪,因此该法明确赋予了警察使用警枪的权力。此后《监狱法》《看守所条例》《海关工作人员使用武器和警械的规定》(以下简称《海关规定》)等分别对各自警种的警察使用警枪的情形作出了规定。然而,现行的《人民警察法》第10条仅仅对公安机关的警察使用枪支的情况作出了规定,并未提及其他警种,导致目前海关缉私警察、检察院的司法警察、法院的司法警察在使用警枪时缺少《人民警察法》的授权,只能依据国务院制定的《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和海关总署、公安部、最高法、最高检制定的部门规章使用警枪。此外,《人民警察法》对公安机关警察使用警枪的情形仅仅作了授权性规定,并未详细规定具体的使用条件,公安机关警察使用警枪的具体条件主要由《警械和武器条例》予以规定。但根据法律保留原则,剥夺或限制公民人身权利的措施只能由法律进行规定,警枪使用的条件涉及对公民生命权的剥夺,由《警械和武器条例》这一行政法规对其进行具体规定,违背了《立法法》的基本精神。[注]高文英.警察使用枪支的若干法律思考[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因此,警枪使用的法律要件就总体而言,不具备充分的合法性。
(二)警枪使用的法律要件缺乏操作性
1.法条规定的内容极不明确
首先,《警械和武器条例》第9条第1款所规定的“判明”极不明确。该款只规定警察判明有法定暴力犯罪行为时可以使用警枪,但并未规定何为“判明”,也未提出相应的判断标准。[注]武西锋.论我国警察枪支使用法律制度的完善[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然而警察的判断是沟通法定情形与现场情形的唯一“桥梁”,一旦缺少明确的判断标准,两者将不再有必然的对应关系,法律规定便会因不可操作而失去意义。其次,《警械和武器条例》第9条第1款规定的“严重”标准极不明确。该条所列允许使用警枪的情形中,有五种均要求犯罪或造成的危险达到“严重”程度,[注]参见《警械和武器条例》第9条第1款第1项、第3项、第5项、第9项、第13项。但该条未对“严重”的标准作出界定。由于不同人对“严重”的理解不同,导致警察在实践中缺乏判断依据,使得这一规定缺乏操作性。
2.法条规定的情形过于烦琐
《警械和武器条例》第9条第1款规定的允许使用警枪的情形中,第1项至第8项所列举的危害公共安全、危及公民生命安全等情形以及第11项规定的在押人犯、罪犯行凶的情形,均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21条规定的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而已采取的紧急避险行为。该类紧急避险的情形原本可以一言以蔽之,立法却对此进行列举,导致法条数目无意义地增加。这种列举是不必要也是不可取的,一方面,列举法条无法穷尽所有情形;另一方面,烦琐的法条必将加重警察在理解和记忆上的负担,不利于现场快速反应。认知负荷理论认为:如果学习材料过于复杂,就会加大工作记忆负荷,加重内在认知负荷。[注]宋艳玲,孟昭鹏,闫雅娟.从认知负荷视角探究翻转课堂——兼及翻转课堂的典型模式分析[J].远程教育杂志,2014,(1).烦琐的法条会阻碍警察对法律要件进行认知,不利于警察在现场极短的时间内作出准确判断。
3.警枪使用的法律要件存在冲突
《警械和武器条例》第10条第2项与《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现场制止违法犯罪行为操作规程》(以下简称《操作规程》)第33条第1款第4项均规定了当犯罪行为人处于群众聚集的场所或者存放大量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等危险物品的场所时不得使用警枪,并都将不使用警枪可能发生更严重后果作为该项的例外。然而,《公安机关公务用枪管理使用规定》(以下简称《使用规定》)第22条第2项只规定在人群聚集的繁华地段、集贸市场、公共娱乐及易燃易爆场所不得使用警枪,并没有规定例外情形,导致该条规定与上述两部法律规范存在矛盾。此外,根据《操作规程》第31条关于警枪使用程序的规定,警枪的“使用”包括出枪、鸣枪警告、射击、持枪戒备等。基于此种解释,《警械和武器条例》第11条规定,当犯罪分子停止实施犯罪且服从人民警察命令或者犯罪分子失去继续实施犯罪能力时,警察应当立即停止使用警枪,此时不得持枪戒备。而《操作规程》第31条第6项针对同一情形却要求警察立即停止射击,并持枪戒备。由此可见,《警械和武器条例》与《操作规程》针对同一情形分别作出了停止使用警枪与继续使用警枪(持枪戒备)的相反规定。另有《警械和武器条例》第9条第1款针对在押人犯、罪犯暴乱、行凶、脱逃等情形允许“使用警枪”,而《看守所条例》第18条对上述相同情形却直接规定“开枪射击”,两者意义相差悬殊。
(三)警枪使用的法律要件不健全
《警械和武器条例》第2条规定只有在使用警械不能制止或者不使用警枪可能发生严重后果时才允许使用警枪,第4条则规定使用警枪应当在制止违法犯罪行为的同时尽量减少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可见使用警枪不仅要符合法定情形,即前提要件,还必须满足一定的限制性条件,即个案正当化要件。《警械和武器条例》第9条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较为详细的规定了警枪使用的前提要件,但对于个案正当化要件,立法并未作出全面系统的规定,仅以列举的方式规定了部分应当停止或禁止使用警枪的情形。如《警械和武器条例》第10条、第11条规定不得对怀孕妇女、儿童以及处于人群聚集或危险物品存放处的犯罪行为人使用警枪,当犯罪行为人停止或不能实施犯罪时,应当立即停止使用警枪。此外,《看守所条例》第18条、《使用规定》第22条以及《操作规程》第33条也列举了一些停止或禁止使用警枪的情形。然而,这些列举仅仅涵盖了部分应当停止或禁止使用警枪的情形,并没有穷尽所有情形,使得该要件的内容极不健全,导致其他应当停止或禁止使用警枪的情形被遗漏,如能否对青少年、精神病人、残疾人使用警枪等。如果警察仅依据《警械和武器条例》第4条的规定来判断是否停止或禁止使用警枪,由于该条的规定过于原则化,又会导致警察享有过大的自由裁量权,不利于有效约束警察权力。此外,如此多的列举情形,也不利于警察在现场短暂的时间内及时作出判断,影响了警察的反应速度。
二、国外警枪使用法律要件的比较考察
美国是自由持枪国家,其法律主要以允许使用要件与禁止使用要件划定警枪使用的边界。日本是禁枪国家,其法律是以使用容许要件圈定出允许初步使用警枪的范围,再以危害容许要件在其内部划出一个更小的范围,允许进一步使用警枪。在自由持枪国家中,以美国的法律较具有代表性,而在禁枪国家中,则以日本的法律较具有代表性。本文选择美、日作为研究对象,考察其警枪使用要件的设置、构成及内涵,为完善我国法律提供借鉴。
(一)美国警枪使用的法律要件
美国是英美法系的联邦制国家,因此其警枪使用要件的许可部分是以判例形式确立,并以州法律和政策性文件进一步细化的,而其禁止部分则是因1985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定原先的“重罪脱逃法则”[注]McDonald. Use of Force by Police to Effect Lawful Arrest,9 Crim. L.Q.435-437.违宪,随后各州对禁止使用警枪的情形作出完善后确立的。各州的法律与政策性文件互不相同,本文将其中涉及许可使用的部分称为“允许使用要件”,将涉及到禁止使用的部分称为“禁止使用要件”。
1.允许使用要件。美国允许公民自由持枪,所以警察在执法过程中面临的危险也较大,因此法律对允许使用要件的规定趋于原则化,以此赋予警察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应对风险。1985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田纳西州诉加纳案(Tennessee v. Garner et al)[注]See Tennessee v. Garner et al, 471 U.S. 1 (1985).中以判例的形式规定,警察有合理理由相信犯罪嫌疑人对警察或他人的身体及生命已经造成伤害或构成即时威胁时,才可以开枪。大部分州的法律都先后对此予以规定,或是在其政策性文件中直接体现,如《圣保罗警察局手册》《洛杉矶港务警察手册》、新泽西州《总检察长使用武力政策》等,当然也有少数州至今没有确立此规则。[注]Chad Flanders, Joseph C. Welling. Police Use of Deadly Force: State Statutes 30 Years after Garner, St. Louis University Public Law Review, 2016:17.除了防卫自己或他人,警察还负有打击、预防犯罪的职责,因此美国警察在逮捕严重暴力犯罪的犯罪嫌疑人时被允许使用警枪,基本各州都有这样的规定。例如,《圣保罗警察局手册》中规定,对于犯有使用致命武力或以致命武力相威胁的重罪的人,或者犯有重罪如果迟延逮捕可能会造成他人死亡或重伤的人,为逮捕该人或防止其脱逃,警察可以使用致命武力。[注]See Saint Paul Police Department Manual, Rule 246.00 (VII)(C).另有,《洛杉矶港务警察手册》、新泽西州《总检察长使用武力政策》等也对此做了相似规定。因此,美国主流警枪使用的允许使用要件是:(1)警察或他人的身体、生命受到伤害或威胁。(2)阻止危险嫌犯脱逃。从要件的内容来看,美国警察武器使用总体采取的是一种防卫性政策,重视保护警察与他人的生命安全,授予警察在防卫性用枪方面较大的裁量权,可以适当作为我国的参考。至于为防止严重暴力犯罪嫌疑脱逃的用枪规定,美国在原则层面较为合理,但本文认为在“阻止危险嫌犯脱逃”方面不宜照搬美国的规定,而应当根据国情考虑对原则作出具体化规定,以限制警察过大的裁量权。
2.禁止使用要件。美国法律在禁止使用要件方面规定带有较强的文化特色。由于特殊的政治体制,各州关于禁止性内容的规定不尽相同,新泽西州的《总检察长使用武力政策》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尤其是对致命武力使用的限制表现出相当的谨慎,而依据该州现行法律,从枪支中射出的任何弹丸都属于致命武力,包括致命性较小的豆袋弹药或橡皮子弹。依据该政策文件的规定,执法人员在使用替代措施能够避免人身伤亡且可以实现执法目的时便不应使用致命武力;对于破坏财产的行为人不得使用致命武力;对自伤人员不得使用致命武力;执法人员只有在保护自己或他人免受死亡或重伤的即时危险时才可以使用致命武力;执法人员不得开枪发求救信号或开枪警告;执法人员不能够从行驶的车辆上开枪或向行驶车辆的司机或乘客开枪,除非他认为对自己或他人存在死亡或重伤的即时危险且无其他方法消除时;执法人员不能仅为了使车辆停止而开枪。[注]See Use of Force: Attorney General’s Use of Force Policy, Part I (C).再如,洛杉矶《警察手册》规定警察不得向最危险的青少年违法者开枪,除非警察本人或第三人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注]域外警察枪支使用法律制度的启示[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该政策性文件对警枪使用的对象也提出了具体要求,与我国《警械和武器条例》第11条在结构、目的上都具有极高的相似性。从本质上看,这些文件是最后手段性原则以及必要性原则、合理性原则的具体化,是对美国赋予警察过多自由裁量权的一种制衡。但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制衡力量过于弱小,这也是美国警察暴力执法颇受诟病的地方。有研究显示,2015年至2017年,美国有近500名非洲裔美国人被警方枪杀,2017年美国有987人被警察枪击致死,甚至还有警察在执行逮捕令的过程中走错地址,枪杀了一名无辜者,且受害人并无任何犯罪记录。[注]参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2018年4月24日发布的《2017年美国的人权纪录》。值得警惕的是,我国在警枪使用禁止性方面的规定不如美国完善,亟待立法作出调整。
(二)日本警枪使用的法律要件
日本《警察法》[注]日本《警察法》,颁布于1954年,最新修订于2004年。赋予了警察使用警枪的权力,[注]参见『警察法』第六七条(小型武器の所持)。但未对具体使用的情形作出规定,日本《警察官职务执行法》[注]日本《警察官职务执行法》颁布于1948年,最新修订于2006年。(以下简称《警职法》)对警枪使用的前提条件以及允许对相对人造成伤害的条件作出了具体规定。依此,本文将日本的警枪使用要件划分为使用容许要件与危害容许要件,对其展开研究讨论。
1.使用容许要件。使用容许要件是指允许以通常不会对相对人造成危害的方法使用警枪的前提条件。《警职法》第7条上段规定:“警察官为逮捕犯人或防止其脱逃,防护自己或他人,或抑制对公务执行之抵抗,于有相当理由认为必要之情形下,得依其事态经合理判断为必要限度内使用武器。”[注]『警察官職務執行法』第七条(武器の使用)。可知,日本警枪使用容许要件为:(1)逮捕犯人或防止其脱逃;(2)防护自己或他人;(3)压制对公务执行的抵抗。当满足上述三种情形时,允许警察以不对相对人造成危害的方法使用警枪,即可以持枪瞄准相对人、鸣枪警告等,但是不可以朝相对人的方向射击。这样规定的好处在于:一方面以较为概括性的情形设定许可警枪较广的使用范围;另一方面严格限定了不可对相对人造成危害的使用方法,在利用警枪强大威慑力的同时,又能防止其被滥用。此外,日本《警用手枪使用和管理规则》[注]《警用手枪使用和管理规则》由日本国家公安委员会于1962年制定,最新修订于2017年。第7条第4项规定:“根据对事态的判断,只要认为合理而有必要,就可以向狂犬等动物或其他物品开枪”,[注]『警察官等けん銃使用及び取扱い規範』第7条(威かく射撃等をすることができる場合)。由于此项是与《警职法》共同设定的,所以该种情形也要满足使用容许要件,可见日本立法对警枪使用的对象范围也考虑得较为周到。由于对动物和物品等射击并不是对人构成危害,所以只要满足使用容许要件便可开枪,这样的规定既合理借用了容许要件的情形设定,又与对人使用的情形进行了区分,对我国立法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2.危害容许要件。危害容许要件是指允许以可能对相对人造成危害的方法使用警枪的前提条件。《警职法》第7条下段规定:“但除该当于刑法第三十六条(正当防卫)或同法第三十七条(紧急避险)或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外,不得对人造成危害:一是有充分理由足以怀疑现正触犯或业已触犯该当于死刑、无期徒刑或长期三年以上惩役或禁锢之凶恶犯罪之人,于警察官对其为职务执行时抵抗或欲脱逃时,或第三人欲助其脱逃而抵抗警察官时,为防止或逮捕之,警察官有相当理由足以相信别无其他手段时。二是执逮捕状为逮捕时,或执行勾引状、勾留状时,其本人于警察官对其为职务执行时抵抗或欲脱逃时,或第三人欲助其脱逃而抵抗警察官时,为防止或逮捕之,警察官有相当理由足以相信别无其他手段时。”可知日本警枪使用的危害容许要件为:(1)正当防卫;(2)紧急避险;(3)逮捕“凶恶犯罪”之人;(4)持逮捕令状进行逮捕。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是日本刑法赋予其公民的基本权利,因此将其作为使用容许要件具有充分的正当性。“凶恶犯罪”要求不仅依据犯罪在刑法中的罪行轻重,还需要考量犯罪的形式、手段、侵害的法益、危险性等,因此只有极少部分犯罪属于“凶恶犯罪”,满足危害容许要件。[注]札幌地方裁判所昭和48.1.30判決(1973年)『判例時報』709号69頁。此外,依据日本《刑事诉讼法》,逮捕令状只有检察官与一定职级的警察有权申请,只有法官有权签发,极为慎重。[注]青昭隆之.日本的警检关系[A].樊崇义.刑事审前程序改革与展望[C].北京:人民公安出版社,2005年。所以,日本警察仅在上述四种情形下才可以使用警枪对相对人造成危害,即可以对相对人(或相对人所在方向)射击致使其受伤或死亡,否则将被追究法律责任。相比于具有一定弹性范围的使用容许要件,日本立法在设定危害容许要件时就显得十分谨慎,允许使用警枪造成危害的相对人范围受到相当严格的限制,与使用容许要件在限定使用对象上宽严相济,值得我国立法时加以借鉴。
三、我国警枪使用法律要件的完善
通过对美国、日本警枪使用法律要件的比较考察,结合我国法律中存在的问题,本文认为应从警枪的前提要件与个案正当化要件两个层面,对警枪使用的法律要件进行完善,并将其上升到《人民警察法》中,以提高立法位阶,加强立法的合法性。警察在现场处置过程中,只有同时满足前提要件与个案正当化要件的双重要求,使用警枪才被认定为合法。
(一)完善警枪使用的前提要件
前提要件是指可能允许使用警枪的前提条件,若不符合则绝对禁止。因此立法中允许使用警枪的情形都属于前提要件,目前我国这一要件初具雏形但仍不完善。通过总结归纳我国法律规定的相关内容,并结合国外的立法例,警枪使用的前提要件应当包括防护自己或他人、逮捕犯人或防止其逃脱、压制持械滋事者、压制抵抗公务执行者四个方面。
1.防护自己或他人。我国法律列举了大量因危害公共安全、扰乱社会秩序与危及公民(包括警察)生命安全而允许使用警枪的情形。如《人民警察法》第10条规定抢夺枪支的紧急情形,《警械和武器条例》第9条第1款第1至8项规定的危害公共安全、危及公民生命安全等暴力犯罪情形,第10项后段规定的暴力袭击警察危及其生命安全的情形,第11项规定的在押人犯、罪犯行凶的情形,以及《监狱法》第46条第1款第3项、第5项规定的罪犯持凶器或危险物行凶、破坏危及他人生命、财产安全,以及抢夺武器的情形等。然而由于列举法不能穷尽所有可能情形,导致大量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的情形被遗漏,不利于保护国家、社会、公民的合法权益,如警察或群众被猛兽袭击的情形就没有与之相对应的法条允许使用警枪,因此立法宜对上述情形作概括性规定。此外,上述法条的机械列举极为烦琐,严重增加了警察掌握与应用的负担,不具有操作性,立法应当作出总括性的规定。另有部分法条对相对人身份做出了限制,如“人犯”“罪犯”等,但警察使用警枪行使防卫权与相对人的身份无关,只与其侵害行为本身有关,故建议在设定要件时取消身份限定。因此,本文认为既然《刑法》第20条和第21条已明确赋予公民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的权利,则不妨借鉴美国、日本的规定,确立“防护自己或他人”作为警枪使用的前提要件之一,将所有警察有合理理由相信犯罪嫌疑人对公共安全、他人及本人的人身安全造成严重伤害或即时威胁的情形,全部纳入该要件并规定于《人民警察法》中。
2.逮捕犯人或防止其逃脱。我国法律允许对拒捕、脱逃的犯罪嫌疑人、罪犯,以及试图劫夺在押人员者使用警枪,如对于《人民警察法》第10条规定的拒捕、越狱的紧急情况,《警械和武器条例》第9条第1款第11项至第14项规定的在押人犯、罪犯脱逃,劫夺在押人犯、罪犯,实施严重暴力犯罪行为后拒捕、逃跑,以及犯罪行为人携带危险物品拒捕、逃跑的情形,允许警察使用警枪。由于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拘捕、脱逃属于较常发生的情形,警察在逮捕过程中遭遇的抵抗往往最频繁和强烈,而在押人犯、罪犯越狱、脱逃的性质更是极为恶劣。为了维护刑事司法秩序,防止犯罪嫌疑人、罪犯逃脱刑事司法程序与刑事处罚,有必要将“逮捕犯人或防止其逃脱”单独作为一种情形列出,并制定单独的用枪政策。其中,对拒捕者使用警枪需要考量相对人拒捕的手段与涉嫌(或已经)所犯的罪名,若手段不具有暴力性则不得使用警枪,若涉嫌所犯罪名非暴力犯罪也不得使用警枪。而对逃脱者使用警枪则主要考量涉嫌(或已经)所犯的罪名和逃脱后的危险性,只有涉嫌致人死亡、重伤或试图导致上述结果发生的暴力犯罪,以及在脱逃后可能继续实施暴力犯罪或是在脱逃时就携带了枪支等危险性较大的犯人,才可以使用警枪。此外,在实践中脱逃者一旦进入警察实力控制的范围内则可能暴力抵抗,那么此时就应当使用针对拒捕情形的手段。对于上述针对实施暴力犯罪后拒捕或是逃脱会对他人生命、身体构成紧迫威胁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使用警枪的情形,本文认为应当归纳为“逮捕犯人或防止其逃脱”,并作为警枪使用的前提要件之一规定于《人民警察法》中。
3.压制持械滋事者。持械骚乱、聚众械斗、暴乱等往往会对社会造成极大危害,因此警察遇有《人民警察法》第10条规定的暴乱或者其他暴力行为的紧急情况,《警械和武器条例》第9条第1款第9项规定的聚众械斗、暴乱等严重破坏社会治安秩序的情形,第11项规定的在押人犯、罪犯聚众骚乱、暴乱的情形时,允许使用警枪。由于实施上述犯罪大多是通过打、砸、抢、烧等暴力手段,所以一定程度上与“防护自己或他人”的情形存在交叉。但考虑到在此类情形中并不是针对所有的参与者使用警枪,而是意在通过对少数犯罪行为恶劣的持械者使用警枪来压制整个犯罪群体,实现维护社会秩序,保护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财产安全等目的,与一般意义上的“防护自己或他人”不同,有必要单独进行明确。所以在上述犯罪中,只有持械者才有必要对其使用警枪,而盲目跟风、徒手打砸等危害性较小的人应当被排除。并且实施此类犯罪与相对人是否为罪犯、人犯等无直接联系,宜删除身份限定。此外,持械的个人有时能造成比群体更严重的危害,如持枪械、爆炸物等滋事,故立法应当删除人数限制而增加对持械并拒绝丢弃的人使用警枪的情形。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应当以“压制持械滋事者”代指警察针对持枪支、弹药、管制刀具、危险物品等实施暴力犯罪或滋扰社会的犯罪行为人使用警枪的情形,将其作为警枪使用的前提要件之一在《人民警察法》中予以确立。
4.压制抵抗公务执行者。警察依法履职时不乏遭到抵抗,但抵抗并非都只针对警察个人,也有针对职务本身的。为此,对于《警械和武器条例》第9条第1款第10项规定的以暴力方法抗拒或者阻碍人民警察依法履行职责,危及人民警察生命安全的情形;以及《海关规定》第4条第2项和第3项规定的走私分子或者走私嫌疑人以暴力抗拒检查,或者以暴力劫夺查扣的走私货物、物品和其他证据的情形,允许警察使用警枪。抵抗公务执行是对公权力的蔑视与侵犯,警察为保障公务正常执行而使用警枪予以压制具有正当性。实践中并非所有抵抗职务的行为都需使用警枪予以压制,如《使用规定》第22条和《操作规程》第33条第1款第1项、第2项以列举的方式规定,对非刑事执法活动的抵抗以及巡逻、盘查可疑人员未遇暴力抗拒和暴力袭击时,就不应当使用警枪。但此种规定也欠缺合理,使用警枪的必要性并不完全取决于执法活动的性质,更多的是考量是否有强制力参与实施。此外,警察在盘查中发现被盘查人可能携带凶器并有可能袭击警察时,为确保警察的生命、身体安全并顺利履行职务,警察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命令被盘查人停止行为、高举双手接受检查,若嫌疑人抗拒执行并有使警察遭遇突然袭击的危险时,使用警枪就具有合理性。[注]陈景发.论使用警枪之要件[J].法学新论,2009,(10).因此,本文认为应当将“压制抵抗公务执行者”作为警枪使用的前提要件之一规定于《人民警察法》中,当警察依法履行依靠强制力执行的职务而遭相对人暴力抵抗,或者在盘查时遭被盘查人抗拒而使警察有受到突袭之虞时,可以允许警察使用警枪。
(二)完善个案正当化要件
个案正当化要件是指使警枪使用行为在个案中取得正当性的条件。目前我国对该要件的规定较为欠缺,仅以若干禁止、停止使用警枪的情形作为对用枪的指导与约束,亟待完善。本文提出的个案正当化要件要求警察根据案件具体情形,考虑在客观上是否具有使用警枪的必要性,以及针对现场具体情况判断使用警枪较合理的程度,即在客观上具备使用警枪的必要性与使用手段具有社会通念上的相当性。
1.客观上具备使用警枪的必要性。我国《警械和武器条例》第10条、《使用规定》第22条以及《操作规程》第33条等出于对用枪必要性的考虑,将通常情况下不需要使用警枪便可处置的情形予以列举,规定不得使用警枪。但这样的立法模式局限性较大,一方面未能将不适合使用警枪的情形全部排除,另一方面未能对必要性的考察标准进行明确。对此,可借鉴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提出的判断标准,从以下三个方面对用枪必要性进行考察:一是相对人方面,例如犯罪的种类、性质,犯罪嫌疑人的数量[注]東京地方裁判所八王子支部平成4.4.30決定(1992年)『判例タイムズ』809号229頁。、年龄、身体条件等,抵抗的有无、方法及程度[注]広島高等裁判所平成6.10.31判決(1994年)『判例時報』1545号143-144頁。,凶器的有无及种类[注]最高裁判所平成11.2.17決定(1999年)刑集53巻2号174頁。,所侵害法益的种类、内容等;二是警察方面,例如警察的人数[注]福岡地方裁判所昭和4412.25判決(1969年)『判例時報』6号86頁。、防护能力[注]広島地方裁判所昭和62.6.12判決(1987年)『判例タイムズ』655号259頁。,有无支援及其可能性[注]福岡高等裁判所平成73.23判決(1995年)『判例タイムズ』896号252頁。,所遇危险的急迫程度[注]東京地方裁判所昭和45.1.28判決(1970年)『判例時報』582号49頁。,与相对人的距离,双方实力差异等;三是现场方面,例如楼房密集程度,人群聚集程度,现场危险物品的有无或引发危害的可能性,光线充足度,双方状态等。[注]陈景发.论使用警枪之要件[J].法学新论,2009,(10).然而,该标准需要考察的客观条件过多,警察难以在短时间内进行如此周密的分析,因此宜结合我国《警械和武器条例》第2条进一步规定警察只有在穷尽所有可行手段(包括口头警告、使用警械等)均无效果,或显然不可能期待取得效果时,才有使用警枪的必要性,并仅在同时满足以不对相对人射击的方法使用警枪仍未取得效果时,才有对相对人使用警枪的必要性。
2.使用手段具有社会通念上的相当性。实践中警察开枪后受到质疑,往往是因为导致了不必要的伤亡,逾越了人们普遍认为的必要限度。但到底何为必要限度,我国仅以《警械和武器条例》第11条、《看守所条例》第18条以及《操作规程》第31条第6项依相对人状态(如服从警察命令、失去继续犯罪能力等)对停止使用警枪的时机作了简单规定,未能从比例原则的角度对使用手段进行系统规定。使用手段的相当性取决于用枪所保护的利益,与因用枪而造成的法益侵害能否达成合理的平衡,即是否符合比例原则。至于使用手段是否符合比例原则,则应当依据社会上一般人的普遍观念进行判断,即依据社会通念判断。因此,较为合理的判断方法是站在警察的角度,依据社会通念考量案发时相对人、警察、现场方面的客观条件,在满足必要性的前提下,判断是否需要使用警枪,以及以该种方式、在该情形下使用警枪是否逾越必要程度。值得注意的是,社会通念虽然会随社会发展而变化,拥有较长的生命力,并赋予公民对自身行为的预测可能;但另一方面,社会通念却难以被捕捉和确定,反而不利于对自由裁量权的限制。鉴于限制警察裁量权,严格保护公民权利,指导警察快速、准确判断等目的,本文认为立法时不妨以行政法规的形式对使用警枪的程序予以合理规定,以确保警察尽到了观察、判断、警告、开枪后查看等义务,防止裁量权被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