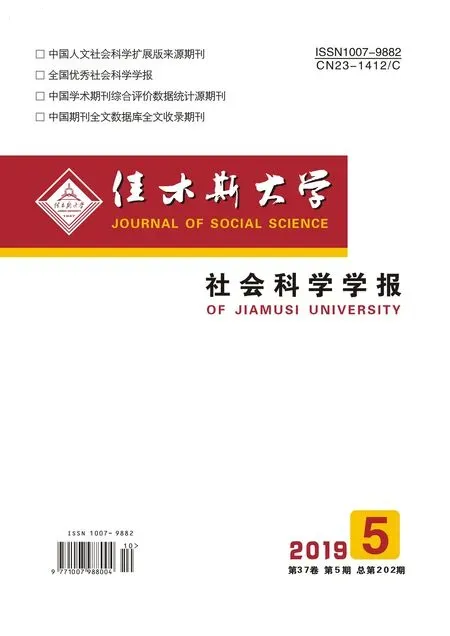叶燮《原诗》对苏轼诗歌的评点
2019-03-04李倩
李 倩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唐宋时期是中国诗歌创作的辉煌时期,在此之后的学诗者不出于唐即归于宋,很难突破这两座高峰。明代前后七子力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主张,以唐诗为典范,对宋诗则弃之如敝屣,多有诋毁,影响力之大波及整个明代诗坛。虽然明代诗学发展到嘉靖后期,公安三袁、竞陵派钟惺、谭元春等相继起而掊之,欲革除明诗积弊,同时为宋诗辩护,且于宋代诗人中极力推崇苏轼,却最终矫枉过正,有失公允,但也使得尊唐风气稍有逆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记载:“诗自太仓、历下,以雄浑、博丽为主,其失也肤;公安、竟陵,以清新、幽渺为宗,其失也诡。学者两途并穷,不得不折而入宋”[1]5205,使得清代诗坛的诗学宗尚逐渐转向宋诗。清初诗论家吸取明代七子派学诗独尊盛唐以至走向极端的教训,在诗学主张上不再分唐界宋,而是唐宋兼宗,既肯定唐诗的价值,也不贬斥宋诗。叶燮作为清代前期重要的诗学批评家,论诗主张唐宋兼宗,在其诗学理论专著《原诗》中对明代称诗者只谈唐诗,耻言宋诗的现象进行了批判,以“变”为核心,从诗史演进的角度论述了宋诗在唐诗基础上的继承与发展,能事益精,将宋诗置于诗歌发展的顶点,极力推崇宋诗,尤其推尊苏轼,在苏诗上着墨较多,对其给予极高评价,为我们研究苏轼在清代前期的接受情况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文献,以下详而述之。
一、苏诗创变之功
宋初,诗歌发展与晚唐五代一脉相承,仍袭唐音;到梅尧臣、苏舜钦出现,旨在廓清晚唐弊端,主张诗体革新,诗歌面貌才有所变化,逐渐更为宋调;发展到苏、黄主导诗坛时期,宋诗面貌基本定型,呈现出以意为主,重议论,尚理趣的风格特征。在这一宋诗区别于唐诗,最终能够在中国诗歌史上与唐诗平分秋色的过程中,苏轼对宋诗的创变有着关键性作用。然而,对于苏诗创变之功的评价,历代诗学批评家多持否定意见。
南宋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将历代诗歌分为五等:“国朝诸人诗为一等,唐人诗为一等,六朝诗为一等,陶、阮、建安七子、两汉为一等,《风》、《骚》为一等。学者须以次参究,盈科而后进,可也。”[2]451其中将宋诗置于最末的位置,同时对诗歌发展中几个关键人物予以评价,认为“自汉、魏以来,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2]57,对曹植、李白、杜甫给予高度赞扬,对苏轼则是给予严厉批判,其原因在于张氏认为苏轼作诗喜欢使事用典,讲究押韵,而将诗歌从《诗经》发端到唐诗以来力主咏物、言志的传统遗弃,本末倒置,致使诗歌的风雅精神荡然无存。明代胡应麟在《诗薮》中云:“永叔、介父,始欲汛扫前流,自开堂奥,至坡老、涪翁,乃大坏不复可理。”[3]209认为宋代诗歌在欧阳修,王安石时扫除晚唐诗歌积弊,开宋诗一代风气,而到了苏、黄主导诗坛时期却走向下坡路,对二人进行严厉批评。
叶燮对于历代诗人的评价,完全是以他们在诗歌史上的创变程度为衡量尺度的,因此,对苏轼于宋诗发展中的创变予以高度肯定,并将其与杜甫、韩愈并称,为古今一大变。可以说,宋代诗歌真正区别于唐诗的独特风貌,到苏轼才真正形成。在《原诗·内篇》上称“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而适如其意之所欲出,此韩愈后之一大变也,而盛极矣”[4]9,苏诗境界之大,盛极一时。又在《原诗·外篇》上中对苏轼诗歌的独特面貌进行概括,认为“举苏轼之一篇一句,无处不可见其凌空如天马,游戏如飞仙,风流儒雅,无入不得,好善而乐與,嬉笑怒骂,四时之气皆备:此苏轼之面目也。”[4]50苏轼作诗无所不有,森罗万象,世间万物经其陶铸,皆为上乘之作,是庸夫俗子无法领悟的。以才学为诗,擅长使事用典,并且能够恰到好处。叶燮从苏轼作诗擅长使事用典的渊源入手,指出其来源于杜甫,而又有所创造。然后对其具体的使事用典习惯进行说明。与韩愈用事习惯于根据自己的意愿将旧事更换一二字以出新意不同,苏轼用事经常是一句中用两事或三事,这并不是卖弄文墨,炫耀才学,而是其“力大”所致,广泛涉猎,博观而约取后无不可入的诗歌创造能力使然。而一句只用一事,并非不可,但是不能以之为准绳,要求诗歌创作必须遵循此规则,要灵活变通,否则不是在作诗而是在记事。而那些坚持一句只能用一事者,如井底之蛙,是没有见过韩愈、苏轼与杜甫如何使事用典的人,由此可见叶燮对苏诗的使事用典不止于一事的行为是颇为赞同的。
二、苏轼“自然”论文艺观
文学理论中强调“自然”的美学风范早已有之,其渊源于先秦时期老庄的“自然”论哲学,强调万事万物的本来状态,非外物使然。到魏晋时期玄学盛行,人们围绕“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展开论辩,“自然”观逐渐为时人所接受,开始运用到文艺领域。南北朝时期的刘勰在其批判理论巨著《文心雕龙》中多次将“自然”一词引入其文学理论体系中探讨文学的起源,如《明诗》中云:“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5]65,指出文学作品是人们有感于物,抒发自我情感的载体,刘勰在文学批评时对文学起源论——“自然”观的阐发逐渐演变为一种文艺观念,至此以后,许多文学批评著作在谈及文学时,时常以“自然”准则为论诗衡文的审美风尚。与刘勰同一时期的钟嵘在《诗品》中更是提出诗歌 “吟咏情性”的本质属性和“自然英旨”说,主张诗歌创作以“自然”为最高美学原则,很明显是从刘勰处发展借鉴而来。唐代皎然《诗式》中言“律家之流,拘而多忌,失于自然,吾常所病也”[6]204,对律诗严格讲究声病,而丧失自然本质的特点多加指责。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专列“自然”一品,足可见其重要性。
苏轼论诗同样崇尚“自然”,叶燮在《内篇》下卷中提到苏轼有言:“我文如万斛源泉,随地而出。”[4]23与自己的诗学理论相互参证,同时霍松林先生对此则诗论进行校注时又提到苏轼的其他言论来与叶燮的理论相发明,摘录如下:
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4]38
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4]38
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山川之有云雾,草木之有华实,充实勃郁而见于外。夫虽欲无有,其可得耶?[4]38
从以上几句我们可以洞察出苏轼论诗追求自然,这种“自然”在这里主要体现在创作缘起和创作法度两个方面。从创作缘起来看,苏轼主张“无意为文”,与刘勰提倡的“为情而造文”如出一辙,“能为之”与“不能不为之”的区别就在于作者是否带有功利目的,苏轼拿自然万物作比,山川之所以有云雾缭绕,草木之所以会开花结果,是因为它们充实蓬勃不得不发的结果,非外力强制。作文亦如此,情志充实于内心到了不得不抒发的紧要关头,这种情况下创作出来的诗文自然工巧雅致。从创作法度来看,苏轼主张为诗为文要顺应事物的自然规律及内在秉性,不要被法度所限制,要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这样创作出来的诗文自然是符合事物的本来特征而生动形象的。
叶燮在这里援引苏轼的观点是为了阐发自己诗学理论“理事情”三要素中“情”这一要素。“情”指的是客观事物的感性情状,不仅具有客体意义,同时经过审美主体的感性处理融入了主体之情,因此在叶燮这里,作为诗歌反映对象的“情”既表现为客体之情,也表现为主体之情,将主客体有机地联系起来,通过以泰山云彩变化作比,意在表明诗歌创作必须随物赋形,为表现客观事物的不同情状而形态各异。既然作为表现客体的事物变幻万千,那么创作也必须遵循自然之法,以表天地万物之情状。由此可见,叶燮这一理论是对苏轼诗论观点的继承和发展,二者可以互相参证发明。
三、苏轼其人之学识与道德修养
文学作品作为主客观结合的产物,其品质的高下优劣与作家主体学识修养的高低密切相关。这种学识修养由作家在阅读实践过程中积累而成,并在潜意识中作用于文学创作的全过程,集中表现为才、学、识等方面,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中多有提及。东汉品评人物的风气风靡一时,逐渐影响到文学批评中对作家的要求,魏晋时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即提出“文以气为主”[7]158,“气”指的是人的气质个性,表现在文学创作上就是人的才能本性,并且指出只有“通才”才能诸体兼备,创作起来游刃有余。陆机《文赋》中云:“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7]170,窥见作品中用心之处,对才识之士欣赏有加。严羽在《沧浪诗话》开篇即指出“夫学诗者以识为主”[8]1,强调了作家学识修养的重要性。如此种种,不胜枚举。唐代史学家刘知己在《史通》中论述史学家的学识修养时说道“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才少”[9]75,理想的史学家应是“才”“学”“识”三者兼备,三者缺一不可,然而很少能有人达到如此程度,因此真正优秀的史学人才很少,这一看法得到后代批评家的普遍认可。叶燮在此基础上发挥创造,迁移应用到文学创作理论上来进行详细说明,提出了“才、胆、识、力”四要素,从而对创作主体的主观条件进行系统性理论性阐述。“大凡人无才,则心思不出;无胆,则笔墨畏缩;无识,则不能取舍;无力,则不能自成一家”[4]16,四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叶燮论诗人于唐代最推崇杜甫和韩愈,于宋代最尊崇苏轼。在叶燮的批评中,对苏轼的才力予以高度赞扬,将其与左丘明、司马迁、贾谊、李白、杜甫和韩愈等古之才人并举,其共同点在于这些人都是集“才、胆、力、识”于一身。叶燮认为苏轼作诗作文,以才学为诗,运天地万物于笔端,无所不入,全在于其“力大而才能坚”[4]27,因此他的作品才能历经百代而流传千古。
考察文人品德修养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同样是文学批评家关注的重点之一。《论语·宪问》中言:“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10]144,孔子已然强调德行的重要性。《左传》提出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说法,并且将立德放在首位,足可见其重要性。刘熙载更是以“诗品出于人品”的论断为准则进行其文学批评,叶燮诗学批评中亦有涉及。在《外篇》上中称“每诗以人见,人又以诗见”[4]52,诗歌是诗人内心的写照。韩愈、苏轼、欧阳修等人都是文、诗和人品相统一的,意在表明人如其诗,诗如其人,接着又提出了“古人之诗,必有古人之品量。其诗百代者,品量亦百代”[4]52,一个人的诗作能够流传百代,那么他的人品同样传承下去。苏轼对其门人黄庭坚、秦观、张耒等人都爱之如己,非常赏识有才学的人,因此到其门下求学的人门庭若市。叶燮对于苏轼这一人格魅力是高度赞扬的,由此可以看出其对诗品与人品相一致的提倡。
四、对苏轼评诗话语的引录
苏轼作为宋代最具影响力的文人之一,其成就是多方面的,不仅在诗、词、文等文学创作与绘画、书法等艺术领域造诣极高,在文学评论方面也成就颇丰。这些有关诗词文的批评散见于他的记、序跋、书信等实用性文体中,都体现了作者自己的独特见解。叶燮在进行具体的批评实践时亦有提及,主要表现在叶燮评孟浩然和白居易二人时,引述苏轼的评语,并通过苏轼的评语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首先体现在叶燮评孟浩然诗的实践过程中。中国诗歌史上自王维孟浩然开创山水田园诗派伊始,后世诗人和批评家便时常对二人进行比较,尤其发展到北宋时期,这种比较愈演愈烈,走向极端,出现了明显的“王孟优劣论”划分,或扬王抑孟,或扬孟抑王,而苏轼可以说是发起此议论的第一人。苏轼坚持“孟不及王”,对王维诗进行高度赞扬,而对孟浩然之诗则多加贬斥。陈师道在《后山诗话》中记载了苏轼评价孟浩然的一段话,其云:“子瞻谓孟浩然之诗,韵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无材料尔。”[11]308成为后代评诗者评价孟诗时的一个重要参照,或认同而在此基础上继续展开议论,或反对而加以指责。叶燮在对孟诗进行具体的批评时,也引用了这一评语,说道:“孟浩然诸体,似乎澹远,然无缥缈幽深思致,如画家写意,墨气都无。苏轼谓‘浩然韵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无材料’,诚为知言。后人胸无才思,易于冲口而出,孟开其端也。”[4]65叶燮认为孟浩然的各体诗歌作品,看似恬淡广远,实则缺乏深意,原因在于孟浩然心中无才,作诗时易脱口而出,不假思索,给其后学诗作诗者作了不好的示范。叶燮对苏轼评孟诗这一话语予以了肯定,由此可见叶燮诗学思想中诗人之“才”对创作主体的重要性。
其次是叶燮评白居易诗。白居易作诗多通俗易懂,这一特点常被后人讥讽,在清初以王士祯为代表的神韵派主导诗坛时,追求典雅与神韵,对元、白诗派尚俚俗的诗风多有诟病,从叶燮开始,这一情况才稍有好转。叶燮在批评白居易诗时,指出历代文人称白诗“老妪可晓”,并且引述了苏轼的一句评语“局于浅切,又不能变风操,故读之易厌”[4]66作例进行他的分析批评,从中我们可以同时看出苏轼和叶燮两人的诗论观。苏轼论诗崇尚“枯淡”美,他在《评韩柳诗》一文中对“枯淡”一词做了详细说明:“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边皆枯淡,亦何足道!”[12]2109-2110苏轼论“枯淡”时,将“枯”与“膏”并置,枯淡之诗在外在形式上给人一种了无生趣之感,然而内在却是十分丰满,暗含精华的,枯以实为前提,实是枯的升华,二者相生相成,辩证统一,看似平淡,实则精美。如果整首诗都给人一种平淡的感觉,那么这种诗是不值得被人称道的。由此观之,苏轼对白居易诗的这一评价是源于其一味追求俚俗而无变化而发出的,可谓直中要害,与其追求“枯淡”的审美风格是相统一的。叶燮认为苏轼的这一评价有一定的道理,但这只是针对白诗中那些失口而出之作,白诗中还有一部分寄托深远,耐人寻味的作品,并且通过《重赋》《不致仕》《伤友》《伤宅》等作品来举例论证,言浅而理深,于俗处见雅,具有强烈的讽谕效果,因此苏轼这一看法有失偏颇,应该对白诗进行全面观照。叶燮对白居易的这一评价扭转了时人贬斥白诗的风气,为白诗在清中叶诗评家中重新定位其诗史价值开风气之先。
叶燮诗学思想扫除明代诗坛“诗必盛唐”积弊,论诗唐宋兼宗,将宋诗放在与唐诗齐平的位置,为宋诗张目,且于宋诗中最推崇苏轼,不仅在于其与苏轼有着相似的思想基础,深受释道两家影响,追求自由淡泊,更在于其诗学思想上的共鸣。叶燮对苏轼诗歌诗论的评点,既有对其诗歌成就的高度赞扬,也有对其缺陷的补充完善。对苏轼于宋诗发展中的创变予以高度肯定,以才学为诗,擅长使事用典,使得宋诗真正区别于唐诗,并呈现出与唐诗不同的独特风貌;援引苏轼崇尚“自然”的诗论主张,与自己诗学思想互相参证,表明其对苏轼诗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推崇苏轼其人的学识修养与道德修养,充实自己“才胆识力”的诗学理论;在评价孟浩然诗歌中引录苏轼对孟浩然的评价,并对其予以肯定,表明诗人之“才”的重要性,而在对白居易诗评价时,能够指出苏轼评白诗只看到了其缺点,而忽视了价值较高的那一类作品,在此基础上对白诗进行全面评价,尽显批评家的公正态度。综观叶燮对苏轼诗歌的批评,对我们重新认识苏轼于宋诗的价值,以及了解其在清代的接受有很大的帮助,意义非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