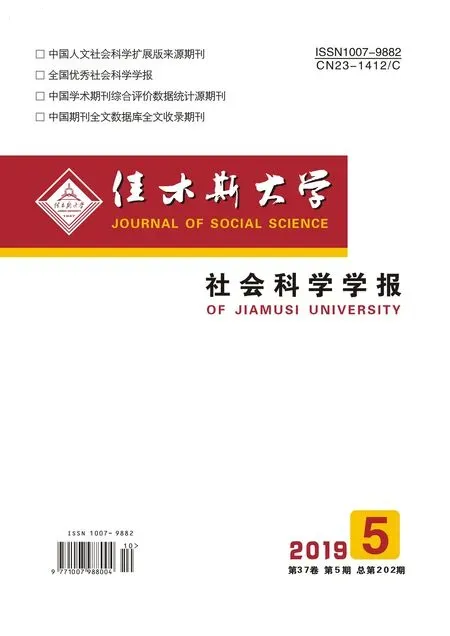辽宁沦陷后的社会控制
——以伪辽宁地方维持会为中心
2019-11-18卢仕豪
卢仕豪
(东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在抗日战争期间的沦陷区,日军多采用利用地方头面人物成立维持会的方式,以协助日本当局从政治、经济等方面入手建构殖民统治秩序、控制占领区的地方社会。伪辽宁地方维持会作为辽宁沦陷后日本当局扶持的重要傀儡组织,其发挥的社会控制作用具有鲜明的代表性,对于探究日本在辽宁沦陷后的社会控制工作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目前,学界对于伪辽宁地方维持会的基本发展过程、人员构成有了一定的研究成果。①但这些研究对于伪辽宁地方维持会的社会控制工作都未详细探究。因此,论文拟以伪辽宁地方维持会为中心,考察这一组织的社会控制工作,以期探究这一组织在建构伪政权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一、辽宁沦陷与伪辽宁地方维持会的成立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自行炸毁柳条湖附近的铁轨,并以此为借口发动了对辽吉两省全面进攻,由于东北军奉行不抵抗政策,日军于19日凌晨5时30分即占领了北大营。第二路兵分三支占据沈城内的北市场、南市场和大小西边门。至19日早上6时30分城内的边防司令长官公署、东北政务委员会、辽宁省政府、东三省官银号、沈阳市工会等重要设施也均被日军占领,沈阳城即告陷落。在沈阳的战事爆发后,19日凌晨日军又按预定计划先后向安东(今丹东)、营口、凤凰城等地发动进攻,这些地区也很快陷入日军之手。至9月23日,日军于一周时间内攻占城辽吉地区三十余座,控制铁路十二条,并由陆军中央部内定了三条逐步扩大的军事占领地的范围:第一道为最小限度满铁两侧警戒线,西以辽河为界,东以吉林海龙为界。第二道为可向外扩展的满铁两侧警戒线,西至洮南—大虎山一线,东至敦化为线。第三道为当时尚未占领的哈尔滨及延吉地区。[1]150-152至此辽宁省沦陷,形成了日军占据下的沦陷区。
辽宁沦陷后,省会沈阳市在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授意下迅速建立了以土肥原贤二为市长的市级伪政权。但在省一级的政权机构上日本的殖民统治仍是空白。是故日本为实现社会控制就迫切地需要一个新的省级行政组织发挥作用。然而,受制于当时的舆论压力,日本不能直接由自己出面组织省级政权。同时,作为奉系军阀统治核心地区的辽宁地区支持奉系的潜在力量仍然十分强大,仅凭日本的力量难以排除地方上的阻力。因此,日本方面希望利用亲日合作者成立维持会掩盖日本直接干预东北沦陷区的真相。受此局势影响,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向关东军司令本庄繁提出建议:“市政机关必须由中国人出面组成,即使由日本在背后加以实际指导,形式上也必须由中国人出面组成,否则将有诸多不便,所费过多而无实效,这将成为日本人干涉的结果而表现出来。”[2]287因此日本需要扶持代理人成立伪政权,并于9月22日在沈阳召开了商讨统治东北的方案会。这一会议综合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及日本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的建议,制定了《满蒙问题解决方案》。提出了“建立受日本支持的,领土包括东北四省及蒙古,以宣统皇帝为元首的中国政权”[2]282的东北统治计划。基于辽宁旧日的地方政权特征,日本需要借助原张氏政权在辽宁地区的影响力稳定局势,故日本选择扶持有奉系军阀政权背景的袁金铠。
作为一名知名士绅,袁金铠曾在地方创办乡团警察与办理地方自治,故在处理地方事务上很有经验。袁金铠也与日本人早有地方治安维持方面的合作。1904年日俄战争时,袁金铠即受命于辽阳东路吕方寺村日本军政分署署长渡边贤太郎创办地方警察维持受影响的地方秩序。[3]438作为奉系内文治派的代表,袁金铠在当时的东北地区一直有较大的影响力。更特别的是,袁金铠与日方欲扶植的清废帝溥仪也有比较亲密的关系。如1917年他在军民两署秘书长任内时曾提议向清室进献十余万元以解决清皇室的财政危机、1928年袁金铠参编刊印《清史稿》成功时,袁金铠亦受溥仪之特殊礼节招待。故鉴于袁金铠的地方维持方面的经验、在东北地区的影响力和与溥仪的关系,袁金铠对于日方有很高的利用价值,日方选择与之合作。除却日方的考量外,袁金铠也希望借助日方的力量实现自己“保境安民”主义的政治理想。因此,基于日本人与袁金铠等勾结者们之间相互利用中的共同利益诉求,双方合作的产物——“奉天地方维持自治维持委员会”诞生了。
1931年9月24日,在日本的授意和奉天各机关法团的推举下,伪奉天地方维持自治维持委员会成立,次日,该组织改名“辽宁地方维持会”并颁布了基本章程。从组织章程来看,伪辽宁地方维持会的主要任务是维持地方秩序及稳定金融,性质是临时机关,委员为地方士绅,任名誉职。[4]29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其委员人选都有于晚清或奉系政权统治时期任要职的经历。其中也不乏亲日派。这或许与旧时奉系军阀政府为了维持自己在东北的统治,任用过大量亲日份子有关。因此日军在选用人选时可选择更有亲日倾向而不是纯粹的在地方上有充分影响力的人,这样便有利于日本更好地实现对地方的社会控制。另外,从中我们还可以看出袁金铠个人和日方都试图将自己的力量注入这一组织,以期未来该组织完全为自己所用。其成员出身统计如下表所示:

表1 伪辽宁地方维持会初期委员出身统计[3]20-21
二、伪辽宁地方维持会的社会控制工作
如前所述,袁金铠个人和日方都试图将自己的力量注入这一组织,以期伪辽宁地方维持会为自己所用。因此,日方为了实现其社会控制工作,首要前提就是让这一组织成为完全化傀儡组织,同时在事实上承担省级伪政权的职权。在此基础上,辽宁地方维持会在日军的指使下从调整经济秩序、管控社会治安、开展“自治”活动等方面入手,开展了社会控制工作。
1.制造傀儡化准省级政权
伪辽宁地方维持会在成立后发生了显著的傀儡化与政权化变异。这种变异带动了伪辽宁地方维持会这一组织性质的变化。先是日方的渗透使得地方维持会傀儡化,使它完全沦为对日军言听计从、为日军开展社会控制的工具。后是日方在傀儡化的基础上让这一组织逐步政权化,最终成为省级准伪政权。
1931年9月25日,奉天地方维持自治维持委员会正式开始运行。次日,该组织更名为辽宁省地方维持委员会。成立之初,伪辽宁地方维持会的性质还只是秩序维持组织。由于袁金铠个人的合作追求并不完全同于日本,又忧心于贸然接受日方要求未来或许会被张氏政权清算,且日本缺乏对伪辽宁地方维持会的直接控制,因此在袁金铠领导下的伪辽宁地方维持会并不完全听命于日本。甚至对于日方将市政交由地方维持会接办的示意,亦以“维持会无此行政权力”之名加以谢绝,并多次见报发表否认组织自治政府的主张。[5-6]而这与日方的成立动机大相违背,因此日方决定指派满铁地方部卫生课长、满州青年联盟理事长金井章次出任伪辽宁地方维持会的最高顾问,后又增添野口多内、石田武亥、川东静夫、镰田弥助等人出任伪辽宁地方维持会顾问,以增加日本对于伪辽宁地方维持会的控制力。在这一系列渗透行动下,袁金铠在伪辽宁地方维持会的权力受到了限制并被逐渐架空,沦为关东军上传下达指令的中间人,因此伪辽宁地方维持会实际成为了日本控制下的完全化傀儡组织。而伪辽宁地方维持会的傀儡性主要表现在如下三方面:
其一,伪辽宁地方维持会的施政受日军监控。如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致维持会关于东三省官银号、边业银行开业指示中第三条规定:“日本军为达到前项(即东三省官银号业务执行应确保日本军之利益及尽一切手段确保公共秩序及生活)之目的,须派数名监理官前往监督……且日军中不时亦可派遣官吏前往监察东三省官银号业务。”
其二,关东军掌握地方维持委员会重大事项决定权。如本庄繁开业指示第五条规定:“地方维持会如欲造东三省官银号业务执行候补人员簿时,须受日本军之认可。”第七条规定:“关于东三省官银号之业务执行,如地方维持委员会与业务担当者指示时,须预先受日本军之认可。”[7]277
其三,任用日本顾问于地方维持会及所属机关,行使谘议权。如伪辽宁地方维持会下属实业厅临时办法规定:“为使实业厅行政完全计,地方维持委员会应聘请日本顾问及谘议若干名。”并且日本顾问在其中地位极为重要,主导着事务决策。如辽宁地方维持委员会财政厅临时办法第四条规定:“地方维持委员会谋取财务行政之完善,延聘日本顾问主事若干名,财政厅关于财务行政之运用,应尊重其意见。”[4]32
同时,张学良在锦州重新设立了东北边防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相比张氏政权的影响力,日本在东北的统治根基是相对薄弱的。因此日本需要断绝东北地区与原政府的组织关系与影响力,形成新的统治秩序。在此基础上,土肥原贤二确立了鼓动东北地方自治以脱离国民政府统治的方针。他提出“对本次为维持奉天治安组织的治安维持会进行指导,使之逐渐成为行政中心。”[8]23从中可以看出,日本希望把伪辽宁地方维持会塑造成地方政权组织,这带动了伪辽宁地方维持会的进一步变异。
为了塑造这一组织的执政“合理性”,日方开始了舆论引导工作。1931年10月1日,《盛京时报》发表了《时局讨论会独立政权宣言》一文。借以宣传所谓的“独立政权”理论。[9]1931年10月16日,伪辽宁地方维持会根据日方要求,开设了财政厅,并促令简任各机关一律开始办公,由此伪辽宁地方维持会的工作范围开始扩张到行政领域。同时,关东军也在辽宁各地开展了成立维持会的地方自治运动,旨在消除原有的奉系势力在东北的影响力、脱离国民政府的统治秩序以构造新政权。到10月下旬,辽宁各地的维持会都已建立起来。“开原、四平街、昌图、铁岭、抚顺、营口、本溪湖、安东等各地都渐次成立自治团体,此等团体概以治安的维持为本旨,专念于增进满蒙人的福利,和张学良断绝关系。”[10]10为了进一步促进政权的独立,日方一方面提倡新设自治指导机关统制这些维持会,一方面追求建立省一级的独立政权。为了建立省级独立政权,日方先在媒体上继续制造舆论抨击东北的旧日政权,以宣扬治安维持会扩大职权的合理性。如其在大连中日文化协会的会刊《东北文化》杂志上刊《地方治安维持会权限扩大后应有之表现》,称“辽宁旧日之政治,乃一军阀官僚铁腕下之腐朽政治也。”[11]1又如日方指使袁金铠于10月15日的《盛京时报》发表《袁洁老对内田伯说明意见:张家殃尽三省民,新政权勿武装》一文,指责“东北民众所以饱尝凌虐至今日之极夜,要不外为张家父子之野心牺牲。”进而提出“为东北将来记,亟宜树立'非军阀的'政权,换言之即无军队的政权之确立是也。”[12]接着,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会见袁金铠,提出希望维持会行使省级职权,并转移到省政府办公。最终,袁金铠在日方威胁下,被迫接受日方主张,于11月7日发布声明,与旧政权断绝关系,称“东省自事变以来,政权停顿,本会出面维持。所有交涉事件,不管既往,不问将来,维在此过渡时期,不得不代行政权。与张学良旧政权,与国民政府均断绝关系”,并进入省政府办公。[13]138同时改组内部成员,除去佟兆元、李友兰、孙祖昌三人,添入新任财政厅长翁恩裕、新任实业厅长高毓衡为维持会委员。11月10日,在日本控制下指导奉天各政府“自立”运动的奉天自治指导部成立,由于冲汉任自治指导部部长,辽宁地方维持会负责自治指导部管理。由此,一个地方自治外衣下的政权体系开始构成。这些实践最终为伪满洲国的成立创造了条件。不过,伪辽宁地方维持会并非真正的省政府。因为伪辽宁地方维持会尽管负责“自立”运动,但它与当时辽宁省地方上代替地方政权的维持会、自治会组织的关系只是不同层次上的以自治为旗号试图脱离东北地区旧政权的傀儡组织。尽管伪辽宁地方维持会对他们也具有一定的管控权,但他们本身并不具有明确的、制度上的上下级从属关系。故伪辽宁地方维持会至12月解散前也非正式政府,仅是一个准政权组织。
2.调整经济秩序为社会控制服务
出于日方希望从恢复经济入手实现社会控制的计划,调整经济秩序成为了伪辽宁地方维持会展开的重点工作。其工作内容如下:
(1)管控金融秩序
九一八事变最直接的影响即金融秩序混乱。由于战乱导致东三省官银号及边业银行停业。至1931年10月前后辽宁地区的主币种奉票与银元兑换“已跌至百二十元兑现洋一元,去事变前官厅维持之六十元兑现一元之法价,相差亦至一倍。”[14]73故而调整金融秩序势在必行。在关东军的指示下,伪辽宁地方维持会先于9月25日重新开放了中国银行、交通银行。而后,于10月12日制定东三省官银号及边业银行管理办法。这一管理办法体现出了明显的限制货币兑换,以期币值提升的特征。如东三省官银号管理办法第二章第四条规定“存款者如有贷款时,先得以存款划抵押。”第三章第九条规定“(纸币)兑换限度每人每日以现大洋五十元为限”。[7]278在此基础上,东三省官银号与边业银行于10月15日重新开张营业。后又由辽宁省地方维持会成立金融维持委员会,对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东三省官银号、边业银行等金融机关行使监督指挥权,并严控各县滥发纸币[15]、组织重新铸造钱币[16]。在地方维持会的组织下,基本的金融秩序得以恢复。
(2)恢复政府金融管控部门
在恢复了基本的经济活动之后,恢复原有的金融管理部门对经济活动进行管控是必要的。因此伪辽宁地方维持会在日方的要求下,维持会首先从10月16日起陆续恢复了原辽宁省政府内部的民政厅、财政厅、建设厅、农矿工商厅等部门下属的各科。[17]342分别管理民政、财政等诸多方面的经济事宜。后伪辽宁地方维持会又任命翁恩裕为财政厅长,任命高毓衡为实业部长,由他们先行统计各部门于九一八事变所遭受的损失,接着着手展开金融管控工作。
(3)整顿财政税收
伪辽宁地方维持会恢复设置财政厅之后,即颁布了财政厅临时办法。从这一临时办法之第三条我们可以看到财政厅基本保留了原有辽宁省政府财政厅的组织及权限。“财政厅之组织及权限,除稍加修正外,仍悉如其旧。”同时,日方的影响力明显注入财政厅,使之呈现出傀儡性特征。如第六条“财政厅长经地方维持委员会之核准,得发布报告,但事先应请日本军之承认。”另外,从第八条我们看到财政厅的设置还希望从财政上断绝原辽宁政权的经济基础。“旧政权之税吏如有将各种税款送交敌对者之行为,本会即请日军严予处分。”[4]32-33
财政厅的具体施政体现在税收调整上。首先由财政厅组织各科长与商会代表成立税则委员会,接着由税则委员会修订税收办法。主要有如下要点:其一,公开财政税收。其二,针对九一八事变后社会经济凋敝状况,确定新征税原则,即“税制以不害实业振兴及开支政治费用为宗旨,其行政费并可于可能范围内节缩。”其三,削减部分税收款项。其中,全部豁免税种为参税、木植税、中江税、蒙盐税、烟酒及牌照税中附加二成用于军费支出部分、各项票照费。减半征收税种为豆税、粮油税、出产税及茧丝税。其四,划分地方征收部分税种。为田赋税、牲畜税、营业税、物产税及车盐捐。[18]14从以上税收改革举措来看,伪辽宁地方维持会虽然表面上借此减小沦陷区内民众的生存压力,促进社会稳定。但更深层的目的在于收买人心,以让沦陷区民众甘心居于日本的殖民统治秩序之下。
综合来看,伪辽宁地方维持会设立经济管理部门、重新开放各大银行、调控货币的发行与兑换等举措的确推动了正常经济秩序的恢复。财政方面的税收削减也体现了亲民的特征。但这些举措是在日方的影响下实施的,所实行的目的是为日军的殖民控制服务。如《申报》报导披露:“辽地方财政厅恢复后,维持会与日军关东军司令部缔约,每月供给日军军费现洋九十万元。指定粮捐并卷烟税拨充,存东三省官银号,由日方自己提用。”[19]
3.管控治安与开展社会控制
在这一方面上,实则伪辽宁地方维持会成立初期多依仗间接控制社会秩序。在省城沈阳,伪辽宁地方维持会主要直接施政工作是调集警察,召集旧有警察成立自卫警察局,并任命冯子敬为局长。但其所调集警察力量不足,管控社会和维持治安的能力极为有限,故各大住宅只能依靠电网维持安全。在省内其它地区,伪辽宁地方维持会主动出面实行社会管控较少,且效果也不佳。如当时伪辽宁地方维持会曾经日军授意,委托原法库县公安局局长赵梦周为新民、康平、昌图、彰武四县清乡局局长,集合各县警队3000余人并散兵800余人维持治安,控制社会秩序。但以“其后赵不仅不能维持治安,而辗转被张学良军队拿获,以附日枪决”的结局告终。[3]22故伪辽宁地方维持会对治安维持的主要工作还是监管各地自行管理治安。伪辽宁地方维持会主行此举的意图在于待地方自行维持社会秩序后,再直接在稳定的秩序上建立日伪主导的统治秩序,以坐收渔翁之利。这一时期各地方治安举措虽因情形不同细节有所差异,但大体上无外乎四项工作。其一,调集人员维持社会稳定。以辽中县政府为例,该县要求“整顿自卫团,每主村设常住团丁四十名,设分队长一名;每区设总队长一名,统领全村团丁,负剿匪救援之责。”[7]271其二,保护各国侨民。以沈阳县为例,县长李毅要求“对于各国侨民,不分国籍,均需认真保护,不得稍存歧视,致生误会。”[7]274其三,剿匪。以海城县为例,该县河西一带“自中日事变发生以来,胡匪乘时局不定,乃大肆号召党羽,以致一般散兵游勇及无业之人相继为匪,啸聚七八百人之多。敝县长据报后,当派公安局长崔文铠带同得力警队三百余名集中牛庄,严加缴捕。”[7]275其四,控制谣言安定人心。如辽阳县“凡非常暴动,危害外人生命财产与造作谣言,扰乱地方治安,以及破坏交通、窝济通匪者,均处以极刑。”[7]268
从各县市反馈给维持会的治安报告来看,在伪辽宁地方维持会的监管下,地方秩序并没有得到完全平复。有如海城县等地区由于子弹等物资奇缺,无力维系地方秩序:“(土匪)复拟再度反攻牛庄。县中警队人数虽不甚单薄,但子弹异常缺乏,不足以资防御。”[7]276但也有部分市县实现了社会秩序的勉强维持。如清源县报告:“昨日(1931年10月2日)午刻有骑兵日军二百名,后有步兵三百名……兵仅来至县属五区大孤家子地方,武装齐整,并架有大炮,地方人民颇逞不隐[稳]状态,但商民首领出而应付,未致扰民,吃午饭回返。”[7]263又如通化县报告“三日,是日地方秩序如常,军警布防仍未稍疏。”[7]265再如辽阳县报告:“至于城乡学校,莅未停课;他如各机关及农工商贾;亦均安心工作,无异平时。”[7]268辽中县报告“现在地面尚告安靖”。同时,各地方政府纷纷提交治安报告给辽宁省地方维持会,这在制度程序上体现了一种自上而下的管控体系的形成。故综合而看,尽管社会秩序没有完全平复,但伪辽宁地方维持会已经借地方势力之手实现了治安基本维持。并且,一个自上而下的社会管控体系在这个进程中开始形成,这体现了日伪对社会控制的加强。伴随着这个进程的进行,地方维持会对地方的管控关系越来越强。并开始主动调查各县吏治[20]、委任相关官员[21]、对地方派遣清乡队长[22],甚至还筹组了省防军及军事厅[23]。这种社会控制的加强,为日本后续阴谋东北“自治”、分裂出伪国提供了可能。
4.组织“自治”活动以建构殖民秩序
伪辽宁地方维持会所组织的“自治”活动是以其对于辽宁社会秩序的管控工作基本完成为前提的。最早在一些地方秩序基本恢复的地区,已经有仿照辽宁地方维持的县级维持会产生。如天津《益世报》报导:“沈阳地方维持会扩大权限,管理辽全省民政,已令各县取消县政府,改组维持分会。”[24]后伴随着日本对维持会的改造,尤其是11月7日维持会宣布与旧政权断绝关系及11月10日隶属于伪辽宁地方维持会、由副会长于冲汉管控的“自治指导部”的成立这两件重大事情发生后,在日本指使下,阴谋让东三省“独立”的活动愈演愈烈。这种活动主要表现在伪辽宁地方维持会下属的"自治指导部"对一系列“自治”活动的组织上。11月中旬,在“自治指导部”的驱动下,沈阳县首先启动了编订“自治”大纲行动。随后,为了与张学良在锦州成立的辽宁省政府区别,日伪控制下辽宁省被改称奉天省[25],这更加强化了分离的趋向。至11月下旬,奉天省47个县一律开办了自治会,并颁布了“自治大纲”。[26-27]12月初,这一分裂活动的势头又进一步强化:自治指导部又设立了自治训练所,并颁布了自治训练所教育大纲。在这个大纲中,日伪合作建立伪国的行径昭然若揭,竟公然宣称:“满洲新国家建国大精神之所存,即在内扫清兵匪政匪学匪土匪等……同时在外使日鲜满蒙汉五组相互融合在太平洋西岸,以东洋文化为基础,建设世界的国民文化,向治国平天下之道,一路迈进。”[28]同时,自治指导部还召开了各县执委会参加的“自治会议”,这标志着在伪辽宁地方维持会组织下,辽宁全省基本实现了自上而下的全省范围内的“自治”,这为未来伪满洲国的地方伪政权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三、伪辽宁地方维持会的社会控制作用
总体而言,伪辽宁地方维持会主要在服务日本的社会控制方面发挥着作用。首先,这一组织维持了社会秩序并创造了社会控制实现的前提。它借助地方势力之手,实现了辽宁地区社会治安的基本维持。同时,伪辽宁地方维持会重新开放了银行系统并采取了一系列减税手段。这在客观上促进了辽宁地区的战后恢复和社会秩序维持,同时也为日本收买人心、实行社会控制及奴化殖民统治创造了基础。
其次,在辽宁地方秩序趋于稳定,尤其是日本控制了伪辽宁地方维持会的主导权之后,伪辽宁地方维持会基本沦为日本殖民者的傀儡机构,并为日本构建其殖民统治秩序服务。第一,伪辽宁地方维持会借监管各地治安工作的机会,构建了一个自上而下的社会管控体系,这加强了日本殖民者对地方社会的控制。第二,该组织按照日军的要求,建立了服务于日军统治的金融管控系统管控金融秩序,并任用日本人担任要职,这为日本的经济攫取活动创造了条件。第三,该组织在日本的操作下逐渐发展为准政权机构,这为日本初步建立了殖民统治的政权级机构。此三项的实现,标志了日本在辽宁地区殖民统治秩序的初步建立。这种殖民统治的秩序亦为后来的伪辽宁省政府继承,并逐渐演变为东北沦陷区的基本社会控制特征。
另外,作为日本九一八事变后建立的最早的伪组织之一,伪辽宁地方维持会实现了日本殖民统治秩序的初步建立。这为日本在其他地区的社会控制提供了模板,因此也起到了推广日本社会控制模式的作用。继9月24日伪辽宁地方维持会建立后,10月9日,铁岭成立了“辽宁省自治会”取代旧铁岭政权。10月10日,在安东成立了“安东自治维持会。”10月11日,抚顺县成立了人民自治会,并设县自治局临时执行县政。10月12日,开原县在日军组织下成立了“开原自治分会”取代旧政府。这些地区自治组织与辽宁地区维持会一样,都是以“自治”为外衣的日伪合作代政权组织。同时,伪辽宁地方维持会的用人原则、组织形式、基本施政要领等内容也运用于日本全面侵华后其他地区的地方社会控制工作中。如1937年天津沦陷后成立的天津治安维持会,也同样任用大量原北洋政府或直系军阀出身背景的地方大员出任主要职员,也同样利用暂免营业税的方式收买人心。也同样采取了限制提款的方式阻止资金外流以实现社会控制。[29]118-120这体现出了明显的继承性关系。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到,伪辽宁地方维持会是日军在九一八事变后失序的背景下,基于日军与其勾结者们的相互利用关系建立起来的过渡性组织。这种相互利用的关系促成了伪辽宁地方维持会的产生,同时在这种相互利用中的利益冲突导致了日本选择单方面控制伪辽宁地方维持会,并使之逐步演进为傀儡性准政权组织。在日军主导下,这一组织在从调节经济秩序、强化社会管控、组织“自治”活动等方面入手,为日本充当鹰犬,并创造了建立伪满洲国的前提。由于伪辽宁地方维持会在为日军实现社会控制方面成就明显,因此伪辽宁地方维持会也成为了随后日本在其他占领区殖民统治建设工作效仿的典范。
[注 释]
①李云涛在《日本侵华工具——辽宁地方维持会》(李云涛.日本侵华工具——辽宁地方维持会[J].兰台世界,2003(10):37)中对于伪辽宁地方维持会的发展过程进行了简单介绍。李楚在《东北沦陷初期投敌军政人员群体形成研究》(李楚.东北沦陷初期投敌军政人员群体形成研究[D].辽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中对伪辽宁地方维持会的人员构成进行了考察,认为这一组织是东北沦陷后最早的投敌军政人员组织,其成员来源复杂,也不尽都是投敌军政人员,有些人员是非自愿加入,具有强迫性。这一组织受制于最高顾问金井章次,是日本操纵下维持地方的傀儡组织。澁谷由里在其博士论文《張作霖政権の研究:「奉天文治派」からみた歴史的意義を中心に》([日]澁谷由里.張作霖政権の研究:「奉天文治派」からみた歴史的意義を中心に[D].日本京都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8年)的第四章中以伪辽宁地方维持会中的袁金铠和于冲汉为中心进行了研究。论文认为,二者尽管在对日态度上略有差异,但都试图在东北沦陷恢复推行张作霖时代保境安民的地方主义政策。而他们的抱负最终都成为了被日本用于构建伪满洲国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