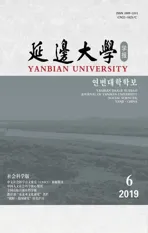东北沦陷区朝鲜作家的自然抒写和文学治愈
2019-03-02裴虹
裴 虹
1910年朝鲜半岛沦陷后,许多朝鲜作家、知识分子选择流亡或移民中国,以施展他们的报负。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在中国体验的朝鲜作家达到了130余人,当时被称为“文化部队”。这支“文化部队”又分为长期居住型作家和短期体验型作家。以安寿吉、金昌杰、玄卿骏、姜敬爱、李鹤城、金朝奎、沈连洙等为主的长期居住型作家,在定居中国东北时期用亲身经历书写了朝鲜族的移民史和定居史,承担了当时最重要的文学创作与精神文化传播的任务;而短期体验型作家则以朝鲜半岛的报刊记者和编辑等为主,同时也有为了取材而来的作家,如著名小说家李萁永。如果说长期居住型作家的文学成果主要集中于小说和诗歌,那么短期体验型作家的文学成果则主要体现在散文的创作上。
散文创作具有纪实性特点,因此,对于了解当时的政治、文化环境具有相当重要的文献价值。本文旨在运用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学地理学、文学人类学、文学治疗等相关研究方法,通过整理和分析东北沦陷时期朝鲜作家的散文作品,一是探讨这个时期朝鲜作家创作的作品如何通过自然抒写表达对政治时局的主张和批判,同时了解其主张和批判如何反映这个时期散文创作的主要特点和功能;二是探讨这个时期朝鲜作家如何通过文学创作表达内心的愤慨、抑郁等复杂感情,将文学作为自我治愈的方式,这对探讨文学在不同历史时代承担的不同功能具有实证性的意义。
一、朝鲜作家笔下的东北自然环境及其意义
(一)东北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和民族意识
我国的东北曾经被称作“满洲”,曾出现在许多历史文献和文学作品中。作为地理名词的“满洲”,一般指包括内蒙古东部赤峰市、兴安盟、通辽市、锡林郭勒盟、呼伦贝尔市在内的我国东北四省区,以现在的吉林省长春市为中心可以划分为“东满”“南满”“西满”“北满”。在朝鲜作家的散文中,“南满”和“北满”常见,而“东满”和“西满”往往被“间岛”(1)“间岛”一词起初指清朝时期以图们江流域为边界线的中朝边境地区,其位于图们江中间的一块无人管辖地带,即现吉林省龙井市开山屯镇船口村。日本侵占东北后将整个延边地区称为“间岛”。和“西间岛”所代替。
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移居中国东北的朝鲜人而言,东北有着特殊的含义,虽然也有民族和历史等原因,但总体来说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应该是最为重要的。这种地理位置上的特殊性,在战争的特殊年代,甚至可以超越曾经在历史、文化或者理念上的冲突。而且距离上的临近感足以让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朝鲜人,相信中国能够有作为避难所或“希望的彼岸”的可能性。
1930年代,朝鲜作家移民到中国东北的人数达到了最高峰,这个时候离朝鲜半岛沦为日本殖民地也已过了20余年,朝鲜单靠自己的力量取得独立已经成为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因此,中国的形势自然成了朝鲜人最为关心的焦点问题。尤其是“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更是将世人的目光聚焦到了中国东北。
申荣雨在《满洲纪行》(2)[朝]申荣雨:《满洲纪行》,《朝鲜日报》1932年2月26日-3月11日。收录于金春善:《中国朝鲜族史料全集·语言文学篇》第3卷,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99-513页。一文中就谈到“满洲”问题对朝鲜的重要性。他认为,“满洲”问题之所以重要,首先毫无疑问就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仅考虑其地理位置处于朝鲜边境这个理由,在“满洲”发生的一切大大小小的事件都会对朝鲜起到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因此“满洲”问题绝不容忽视。申荣雨接着提到,从历史原因来看,“满洲”曾是朝鲜祖先的发祥地,曾经的高句丽、渤海国在这里留下了历史踪迹,使得朝鲜人对这片土地具有亲切感,这也成为他们关心“满洲”问题的另一个原因。但申荣雨在散文中很明确地指出,这种关心不能单单停留于历史问题,而更加重要的是现实问题。
申荣雨写这篇散文时恰逢伪满洲国建立。作家曾先后三次来到中国东北地区进行考察,在第三次考察时,正好赶上了伪满洲国“建国大典”。对此,作家的内心可以说是五味杂陈,他深感东北亚格局的动荡,且对朝鲜及朝鲜人民的命运无比担忧。虽然申荣雨在文章中只是以“直接或间接影响”一笔带过,并没有确切下结论,即“满洲”问题对于朝鲜半岛到底具体有怎样的影响。他呼吁人们应当认识到“满洲”的过去和历史虽与朝鲜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目前更为紧要的是深刻认识当下的“满洲”问题,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申荣雨具备了一定的东北亚人民命运共同体意识。
(二)东北的气候特征和生存意识
说到东北的地理环境,除作为中朝俄三国枢纽的中心位置外,不得不提它自身的环境因素,尤其是东北的气候和水土。气候对人的影响分为短时间和长时间,短时间形成的影响一般是因气候突然变化所带来的,且往往以舒适、愉快、不适、烦躁、发怒等情绪和感觉表达出来;长时间影响一般是人们长期居住在某地并适应气候后所形成的一种气质特征,如坚毅、浪漫、豪情、孤僻等。
伪满洲国时期朝鲜作家散文的创作群体范围很广,其中较为有名的一些作家和记者还有史料记载可考证,但他们的身份大部分已无法查询,这些作家可以分为长期移居者、短期移居者、自发来“满”体验者、受某种组织邀请来“满”考察者、其他自由撰稿者等。从大多数作家的散文中可以看出,朝鲜人来到东北后最强烈的一个反应就是对气候的敏感,更确切地说是不适感。金日均在《新兴满洲人文风土记——新京篇》(3)[朝]金日均:《新兴满洲人文风土记——新京篇》,《满鲜日报》1940年9月23日-10月1日。收录于金春善:《中国朝鲜族史料全集·语言文学篇》第3卷,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02-210页。一文中就谈到,“‘满洲’的气候并不是那么好,这种大陆性气候,与故乡(4)指朝鲜半岛。的风土比起来简直就是天壤之别,很不适应”。根据他本人的描述,因为环境相对较为恶劣,如果想要在东北某个地方生存下来,“就必须学会抵抗”。
可以看出,对于朝鲜人来说,东北一带的气候和风土与朝鲜的差异要比想象中大得多,因此,适应东北不是一个简单的适应过程,是需要以一种抵抗精神去努力适应的,这样才能够得到在东北生存下去的机会。这听起来或许有些让人感到诧异,适应气候居然还需要抵抗精神,是否有夸大其词的嫌疑呢?但是再重新回味这段话,作者其实是在传达另一种抵抗意识——抵抗的不只是自然环境,更重要的是去抵抗社会环境,因为这样方可得到真正的生存空间。作者在对所谓伪满洲国国都“新京”的文化批判上更加证明了这一点。
总体来讲,朝鲜作家通过对气候的描写表达了身处中国东北的朝鲜人民“生存第一”的生活态度和基本信念,同时,对战争和殖民统治具有一定的抵抗意识。
(三)东北的水土特征和批判意识
除气候外,东北的水土也与朝鲜半岛有天壤之别。李箕永在散文《寻找大地的儿子》(5)[朝]李箕永:《寻找大地的儿子》,《朝鲜日报》1939年9月26日-10月3日。收录于金春善:《中国朝鲜族史料全集·语言文学篇》第3卷,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83-293页。一文中就提及到朝鲜南阳与中国图们各自非常明显的土质特征。他在文章中谈到,“两地只不过是被一条图们江所隔着,但土地和江水就如所处的不同国度,是截然不同的。……脚踩黑土地,听着滔滔汹涌的河流声,迎面凛冽强风,这是非常鲜明的北方大陆性气候”。
其实,这种自然景象的差异,现在看来也是很明显的。坐落在中朝边境的吉林省图们市,若站在图们江畔,望向朝鲜的山脉,就会发现它确实与我国境内山脉完全不同。因此,即使是从远处看去,根据山的特点,也能判断出哪座山是中国境内的,哪座山是朝鲜境内的。
安容顺在《北满巡旅记》(6)[朝]安容纯:《北满巡旅记》,《朝鲜日报》1940年2月28日-3月2日。收录于金春善:《中国朝鲜族史料全集·语言文学篇》第3卷,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879-885页。中就提到,“无论是谁妄想混淆国境,大自然总是会将事实默默地告诉你”,以此表达了对客观自然和真理的认识。这不仅仅是对自然的感叹,也是从作者内心深处所传达出来的强烈的社会意识。这种写作方式也是这个时期大部分作家的一种普遍的表达方式,这样可以在避开文字审查的同时实现内心的告白,并且带有浓厚的社会批判意识和自我反省意识。
二、环境因素对朝鲜作家文学创作的影响
(一)自然环境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以往对伪满时期文学的研究,多半是从历史背景和时代角度进行研究的,很少涉及地域性研究。然而,伪满时期文学,尤其是作为移居群体的朝鲜作家文学,其地域性即文学的地理学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最重要的原因是朝鲜半岛地域环境与中国东北地域环境有着明显区别,尤其是大陆气候与海洋气候的差异,显然自然环境对这个时期移居中国东北的朝鲜作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气候影响文学包含了三层关系,第一层是气候与物候的关系;第二层是物候与文学家的审美感受的关系;第三层是文学家的审美观感受与文学作品的关系。(7)曾大星:《文学地理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85页。这三层关系是层层递进的,从而形成了文学创作的基本机制,在这一种机制的形成过程中,气候的影响是最初、最基本的,也是最强有力的影响。(8)曾大星:《文学地理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86页。如谈到春天,朝鲜半岛的三月应该就是春暖花开时节;而中国东北的三月却仍然飘着白雪,仍然刮着凛冽寒风,除了挺立的松树找不到带有一丝生机的东西,这使得作家感到很是懊恼,其实更多的懊恼来自于对这种气候的不适应和对故乡的思念。
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气候的反差虽不能说是巨大的,但多多少少还是有差距的。朝鲜半岛以海洋性气候为主,空气湿润,且四季分布时间比较均匀;中国东北地区是明显的大陆性气候,空气干燥,冬季持续时间比较长,相比之下,秋天和春天就显得很短暂。土生土长在朝鲜半岛的朝鲜人,初到东北当然不会习惯这种气候,他们最难以忍受的就是冬寒、风沙和干燥。同时,环境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居住在东北的朝鲜人,也包括朝鲜作家,这种变化通过作家笔下的人物形象以及作家本身的文风变化呈现了出来。通过对朝鲜作家创作的诸多文学作品的分析就可以发现,有中国体验或居住经历的作家所创作的作品,生活写实性很强,能够给予读者直视现场、直入主题的感觉。如崔署海的《逃出记》、姜敬爱的《盐》《人间问题》等诸多小说。相比之下,朝鲜本土的作品则抒情性、浪漫性较强,作家往往通过象征和隐喻表达思想感情,如罗稻香的《哑巴三龙》《水车》以及金裕贞的《山茶花》《春春》等。
(二)自然环境对人的影响
对于解放前移居中国东北的朝鲜人而言,一是因自然环境的变化,二是因人文环境的变化,再加上时局动荡,周围每一个微小细节都在影响着他们的生存方式和意识形态。有人坚毅、有人懒散,也有人堕落,因此朝鲜人来到东北后首先是欣喜,欣喜这里的景象好似与朝鲜曾经的景象别无二样,人们用朝鲜语交谈,村落、房屋也有朝鲜本土的样子。但随后他们会感到伤情,伤情那些懒散、堕落、迷惘和无奈。
申荣雨在《满洲纪行》(9)[朝]申荣雨:《满洲纪行》,《朝鲜日报》1932年2月26日-3月11日。收录于金春善:《中国朝鲜族史料全集·语言文学篇》第3卷,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99-513页。中在写到“满洲”朝鲜农民的变化时就谈到这些农民不再保留昔日那温良的性格,其原因不单单是因为他们本身的无知和不良,而是与这里粗犷的环境分不开的。作家来到“满洲”20余天所感受到的是,站在那荒漠的狂野,一切事物和人都显得无比渺小,一年四季总是要与寒冬、酷暑、干旱等恶劣天气和灾难抗衡,加上时不时要看本土人的脸色,对于只会埋头种田的农民来说,克服这种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实属不易。这种环境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朝鲜农民温良的性格,从而使他们变得粗暴、放荡,面对生活的态度是得过且过、毫无定性。同时,作者也并非将所有原因都归结于恶劣的环境,作者更注重从人的内在本质中寻找答案,指出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终究是人本身的懒惰和放荡加之恶劣环境所引起的。并指出,朝鲜人如果想在此生存下去,就必须学会适应这种环境,扎根一处、吃苦耐劳、勤俭力行,这样才是生存之道。可以看出,作者在对朝鲜农民的评价上,不是无条件怜悯,而更多的是方向性指明,指导他们如何走出逆境,总体来讲这篇文章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申荣雨写道:“我只不过来到这里20余天,就如此念想故乡的春天,更何况是这些农民”。作家也很难适应东北的气候,因为他所念想的不是故乡本身或别的什么,而是其故乡的春天。对于中国体验朝鲜作家的作品,散文题材中所占比例最多的是描写春天题材的作品。中国东北的冬季持续时间较长,初到这里的朝鲜人的确很难适应。因此,也就是那些体会过东北的气候的人才会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寒冬腊月,为什么四月仍不见春色迹象,也才能够在心中萌发出对春天迫切的思念和向往。而终年居住在朝鲜半岛的人,是绝对不会产生这种情感的,自然也写不出那种对于春天的无比渴望和迫切感。
(三)自然抒写中隐喻的社会问题
在不同朝鲜作家的不同作品中,不约而同地表现出对东北的春天一致的看法,那就是太冷、太短。居住在北方的人们都知道,那里冬天显得格外漫长,而且寒风刺骨,虽然24个节气将四季划分得很均匀,但是北方的冬天从人们的感知上似乎占了全年的一半,也就是从10月中下旬一直到次年的3月末4月初。在这期间人们几乎没有室外活动,人们对于春天的期待就如同常年被束缚的人急切地渴望自由般迫切和宝贵。因此,人们产生了对于东北下一个春天的念想,即期盼它早日真正到来。这种情感是移居中国东北的朝鲜人所特有的,也是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整体变化给他们带来的一种情结。而且,从散文的细节描写中可以看出,人们对于春天的期盼不是只停留在被动地等待,而更多是在主动地寻找,寻找掩盖在暗处的春的气息,哪怕只是寒风中的一丝暖意、冻土萎草中的一颗绿芽。
然而,现实总是不尽如人意,还没有饱受春意,失望、恐惧便随之降临。一个是战争,另一个是饥饿。姜敬爱的《间岛的春天》(10)[朝]姜敬爱:《间岛的春天》,《东亚日报》1933年4月23日。收录于金春善:《中国朝鲜族史料全集·语言文学篇》第3卷,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1-12页。描述了一段令作家难以忘怀的春天镜像——一道煞风景。散文开头以作者陶醉的心情迎接丝丝春意开始,但是这种美好心情并没有持续多久,突如其来的轰炸机和爆炸声惊醒了所有人的思绪,人们落荒而逃。驰骋在大街上的日军汽车队伍和有些滑稽的伪满洲国警察,预示了一场即将来临的风雨。尽管时局如此,对于姜敬爱来说,她的信念却总是那么坚定,如同文章结尾中所述“你用一颗勇敢的心迎接这个春天的到来……”,这种情感可以说是姜敬爱绝不屈服于任何黑暗势力的精神表现。
如果说姜敬爱通过一个不合景象的春天表现了时局动荡、人心紧张的现状,那么金永一的散文《默想录》(11)[朝]金永一:《默想录》,《满鲜日报》1940年4月13-15日。收录于金春善:《中国朝鲜族史料全集·语言文学篇》第3卷,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88-190页。同样是面对东北的春天,则更加注重作者内心的彷徨与无助。作者用“悲惨”“寂寞”“暗黑”“虚无”“幻灭”等来谈论东北的春天,表达了内心深处的痛苦与悲哀。面对仅靠一己之力已无法挽回的黑暗现实,作者表现出一种坦然的态度,试图体会人生真理,表现出对于“赤身而来、空手而去”的短暂人生的感慨和释然。他所说的“从一个黑暗到另一个黑暗;从一种虚无到另一种虚无”,用极其简单又不失象征意义的手法表达了对人生的释怀。如同作者所说,人出生时从黑暗中得到了第一缕光明,然而不过几十载又将走向另一个黑暗,因此人的存在本就是虚无,也不必执念过多。这是一种达人的境界,作者的情感没有因为环境的变化和条件的恶劣而变得低迷,他说到:“在这流逝的岁月中哪怕是能找到内心的一丝慰劳,也是一种享受”。作者所流露的情绪好似低迷不振,再细细品味就会发现,实际上他是在传达一种达观的思想,因为人本身就是渺小的,何况是由人而产生的这些事件。
三、通过自然抒写和表露内心情怀达到自我治愈
如前所述,东北的气候对于朝鲜移民以及写作者的影响,尤其是来之甚晚的春天。因为东北气候十分寒冷,以致在朝鲜人想象中的东北好比北极,白雪皑皑、白熊群群。除了给予人强烈感触的气候以外,东北的旷野也给朝鲜人带来了震撼般的深刻印象。中国国土本就辽阔,东北平原又是中国最大的平原,面积达35万平方千米,而整个朝鲜半岛也就22万多平方千米。同时,这种开阔胸怀、自然抒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治愈内心创伤的作用,作家通过体验和抒写达到内心治愈的作用。
文学治愈可以分为两种:一是读者治愈,也就是接受文学作品的读者通过阅读使其身体或精神得以治愈;二是作者治愈,这属于作者的自我治愈过程。作家通过自身的写作经历和过程,使其身体或精神从束缚和抑郁中解脱出来。但是在文学作品的实际创作和传播中,这两种形式往往共存。尤其是在经历战争、灾害以及某种较大的社会动荡时,文学的这种功能则更加突出。如近代诗人泰戈尔于191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吉檀迦利》,其之所以在西方大受欢迎,正因为它所发出的天国般的声音对于刚刚经历了世界大战浩劫、对西方文化前景感到绝望的民众心灵起到了巨大的抚慰和疗救作用。(12)叶舒宪:《文学与治疗》,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8年,第18页。再如,鲁迅弃医从文,将文学视作拯救民众溃烂的精神世界的一剂良药;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相继在我国文坛出现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也都属于特定时期出现的文学治愈形式。
纵览东北沦陷时期朝鲜作家的文学创作,其通过写作达到自我治愈乃至读者治愈倾向十分明显。朝鲜人在本国沦陷后,抱着生存的希望来到东北,当他们在中国东北却再次遭遇沦陷受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所受的打击和创伤是加倍的。因此,这些文人们开始将希望寄托于无形的力量——写作上。
姜敬爱在《间岛的春天》(13)[朝]姜敬爱:《间岛的春天》,《东亚日报》1933年4月23日。收录于金春善:《中国朝鲜族史料全集·语言文学篇》第3卷,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1-12页。中以“视力不够”来描述了“满洲”田野的广阔。姜敬爱是曾定居在延边地区的作家,与那些为了创作“满洲”题材作品而来东北小住的作家不同,姜敬爱的作品更贴近生活实际和注重自身感受,因此很少出现对于山川田野的描述,而文中竟然也提到了旷野无沿,证明了东北平原的确给朝鲜人带来了至深感触,同时也成为对内心的一种宽慰。
洪钟仁的《哀愁的哈尔滨》(14)[朝]洪钟仁:《哀愁的哈尔滨》,《朝光》1937年8月。收录于金春善:《中国朝鲜族史料全集·语言文学篇》第3卷,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833-838页。更是将这种震撼发挥得淋漓尽致。“一望无际的‘满洲’地平线上荒蓼的‘北满’田野”“如果是阴天恐怕连方向都难以分辨”,面对这样一个不见边际的广阔平原,作者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波浪,伤感瞬间被触发,深受感慨。同时,人们被这广袤平原的伟大所吸引,作者在自然景色的冲击中开始探寻自我、重视自我。洪钟仁的这一段文字就好似发现了新大陆一般,富有对自然的冲动和欲望,令人回味无穷。
李泰俊的《满洲纪行》(15)[朝]李泰俊:《满洲纪行》,《无序录》,首尔:博文书馆,1941年。收录于金春善:《中国朝鲜族史料全集·语言文学篇》第3卷,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46-359页。将“满洲”的田野风光和特点表达得同样恰到好处,文中使用“土壤”一词而不是“土地”一词来描述田野,使文章充满生动感,也增加了人们对于自然的亲切感。作者写道:“深棕色的土壤上划出的一道道地垄如奔马留下的蹄印,坐在列车里却感到仿佛登上泰山般的感觉,眼前广漠的视野,即使以一介书生的胸襟,也是感到无比感慨的”。“满洲”之行给朝鲜作家带来了一次开阔胸怀的机会,在这一体验过程中,作家的写作视野显然也拓宽了不少。这不仅体现在散文体裁中,在许多小说和诗歌中也有所呈现,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作者的写作风格,形成了大陆文学和半岛文学的差异。李泰俊还借景赞人,说道:“在这无边的土壤之海,第一次铺设铁路,手持铁锤,试开第一班列车的那些黑红面孔,不尽散发在脑海,所有的舞台终会将这些荣誉给予那些主角们”。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后,铺设铁路、公路是一项非常庞大且重要的工程,动用的劳动力几乎全部来自当地农民,包括朝鲜人。因此,手持着铁锤铺设铁路的那些被烈日晒成黑红的脸庞的人,显然不是日本人。而随后所指的历史舞台的主角们显然也不是日本人,是这里的农民。作者运用暗喻法,为那些付出了汗水甚至生命的劳动者送上了最宝贵的赞誉。
东北的春天来得比较晚,有些作家就利用这一现象巧妙地实现了现实批判的目的。金伊俊的《满洲的春天》(16)[朝]金伊俊:《满洲的春天》,《满鲜日报》1941年6月13日。收录于金春善:《中国朝鲜族史料全集·语言文学篇》第3卷,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00-201页。是其中之一。金伊俊运用讽刺和暗喻的手法表达了对于现实的批判。其文章看似是对于自然现象的客观描写,实则包含深刻内容,如“街里年轻的小姐们忙于挑选漂亮的衣料,以便置办几件春装,却丝毫没有察觉到她们脖子上的狐狸毛围脖正发出阴笑表情”。在这一段描写中,看似是对爱美的富家小姐们的讽刺,其实是对那些没有以正确清晰的判断力去面对社会现实,只看到表面现象就沾沾自喜、忘记自我的小资本家的批判。大街上行走的人们为了避风,将身体缩着捂着,作者将这一场景描写为“若只看头和脚,根本就看不出是男是女”。从中也可以看出作者强烈的批判意识,即身上穿戴再怎么飘逸好看,在风沙满天的天气中也丝毫看不出是否是妙龄女子。如同在被统治的黑暗时局中,如果摆不清方位、随波逐流,民族的身份也不会被认同的。金伊俊更是将这种批判意识扩展到社会层面中,“‘满洲’本身就无法对毫无音讯的春天有任何质疑或抵抗的情绪,因为对于连大衣的领子也不敢敞开的弱者们而言,‘抗议’两个字毫无意义”。谈到此,作者的内心明显显露出愤慨,文章的语气也愈发深重。这种对现实的批判性表达,同样也承担着对病态现状揭露和治愈的意义。
姜敬爱的散文《漂母的心》(17)[朝]姜敬爱:《漂母的心》,《新家庭》1934年6月号。收录于金春善:《中国朝鲜族史料全集·语言文学篇》第3卷,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7-18页。中写道,“原以为脏得无法再穿的衣裳,在洗衣棒的敲打下、河水的清洗下重新变回那原来的白色,这种喜悦和快感比换一件新衣裳还要兴奋,而且不是亲自去洗是无法体会到这种快感的”。洗衣不再是村妇们生活中的一个简单细节,更多是一种心灵的洗涤、创伤的洗涤和战争的洗涤,通过这种“洗涤”,唤醒真正的春天——和平和自由。
俗话说“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人们对春天的向往不仅仅是为了走出寒冬,舒展心情,也有对新一年崭新规划的期望,不论是战争岁月还是和平年代,这一设想总是不变的。就像田蒙秀在《春心》(18)[朝]田蒙秀:《春心》,《满鲜日报》1940年3月20日。收录于金春善:《中国朝鲜族史料全集·语言文学篇》第3卷,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33-534页。中所写道,“就算是将自己暴露于风雪中虐一虐,终究想抓住那一片春心”。至少这能够给予人们积极的生存态度,不至于沉沦放纵。但重要的是,这种念想和期望不能与伪满洲国
建设混为一谈,要认清民族受难的根源,不应将希望寄托于侵略者。权忠一的散文《病床随感》,(19)[朝]权忠一:《病床随感》,《满鲜日报》1940年2月4-5日。收录于金春善:《中国朝鲜族史料全集·语言文学篇》第3卷,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11-213页。就没有认清这一事实,赞美“兴亚建设”,表现出不够成熟的价值观。
总体来讲,东北沦陷区朝鲜作家的散文创作具有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价值和意义,一方面对于了解当时的政局、时代特征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文学史意义;另一方面,从文学与精神治愈之间的关系来看,这个时期散文创作不仅具有作者自我治愈的功能,也在某种程度上对受压迫的广大读者进行创伤治愈,值得我们继续研究和探讨。
四、结语
对于解放前移居或是游历到我国东北的朝鲜作家来说,东北既是寄托希望的“彼岸”,又是使人深感绝望的“地狱”。这些朝鲜人期待着能够重返他们的祖国,重回故土,就如同在冬天的刺骨寒风中等待着春天的到来一般。等待他们的现实却依旧是饥饿、寒冷,使人们感到绝望。因此,中国体验朝鲜作家笔下的东北自然景象,有不尽如人意的一面,也有令人震撼欣喜的一面,表达了作家的民族意识、生存意识和抵抗意识。
同时,中国体验朝鲜作家们通过写作达到了作家的自我治愈以及读者治愈,可以总结为两个方面:一是他们通过感受自然,开阔胸襟、拓展视野,抚慰内心的伤痛,以达到自我治愈的效果;二是他们通过一种间接表达或者暗喻、隐喻的形式,对黑暗现实作出批判,道出心中的真语,达到治愈病态社会和读者的效果。这种创作形式是战争时期黑暗势力压迫下的自然选择,也是殖民统治下的普遍写作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