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是矿工
2019-03-01辛峰
辛 峰
1
我刚出生,父亲就去了煤矿工作。到了七八岁的时候,我每个暑假都要跟着父亲去煤矿玩,便不免对矿山和矿山里的人印象深刻。
父亲是个顶老实的人,没有读过几天书。在我最早的记忆中,他的工作日志都是求着同事帮忙填写的。于是,刚上四年级的我,一到父亲的单位,便承担起了帮父亲填写工作日志的重任。那些数据我当然不懂,都是看着父亲同宿舍叔叔们的日志照猫画虎,誊抄过来的。却也是一笔一画,非常认真。遇到觉得不对的日期,还要追着叔叔们打破砂锅问到底。
每次父亲从矿井上来,叔叔们都会说:“老辛,你家小辛将来要考北京大学啊!”父亲便会呵呵地笑着,用一只手摩挲着我的后脑勺,另一只手拉着我的手去买西瓜。同事们都叫父亲“大手”,后来我才明白这是因为父亲花钱很大方。比如买西瓜,别人都是一次能吃多少买多少。甚至吝啬到一次只买半个瓜,更甚至四分之一。可父亲每次都买一个大的,和同事们一起吃。尤其是我到了单位,他会一次买好几个西瓜,用装化肥的蛇皮袋子提溜回宿舍,囤积在床板下面的水泥地上,每天下班回来给我杀一个瓜。在矿山的时候,我便每天吃饭都很少,肚子里全是西瓜水。一走路就哐啷哐啷地响。
父亲的宿舍是四人间,有时候有的叔叔倒班或者请长假回家,我便会独占一张床。白天我会在矿山的大院子里玩耍,到处搜集能看到的新报纸,把感兴趣的故事和文章剪裁下来,贴在自己的笔记本里面。夏天的矿山,马路上的柏油常常被晒得发烫。院子和路边的树木上都顶着一层黑色的煤灰,散发着一股混合着柏油味道的异样气味。偶尔有拉煤的卡车呼啸而过,卷起漫天灰尘,久久不能停息。
午睡过后,我揉着惺忪的睡眼一骨碌爬起来,先去矿山外的草地上撒泡尿。然后在院子的水龙头上洗洗手,便回到宿舍猫着腰钻进床板下面掏西瓜。扁的不要,只挑圆溜溜的带绿色瓜把儿的。一只手拉出来,双手抱到胸前,先凑起鼻子从瓜把儿的地方闻一会儿,清冽的香甜气味便会一点点地散发出来。我把瓜抱到案板上,用切面刀咔嚓一声一切两半,有时用力不匀,就会切成一半多一半少。这时我就会愣愣地盯着两半的西瓜看半天,最终选定一半。一般都是先吃小一半的,用勺子挖着吃,这样不会弄脏衣服。
2
儿时的农村是没有洗澡条件的,很多家庭的孩子一整个冬天都很难洗几次澡。即便洗头洗脚,也因为寒冷的西北风而瑟缩着手脚,匆匆了事。记忆中特别深刻的是,有个叫小牛的玩伴,家里三个兄妹,个个脖子上都累积着一层如铜钱般厚的垢痂,一旦父母要拉着让洗澡,他们便杀猪一般哭喊嚎叫,如同上杀场受刑。听说污垢积得太厚,搓起来会特别疼。我每每也总是躲着他们,就是一起玩打面包(一种纸叠的玩具,有三角形和四方形两种)的游戏也会刻意避开。到了夏天,我们只能跑几十里山路,到附近的河川里去洗澡。反正,在家里也只能用大铁盆舀水,坐在里面洗,盆小水浅,一不小心还会割伤手脚,洗澡的感觉总是憋屈的。
矿山里最不同的是,有很大很大的澡堂子。一般都是水泥砌就,一个池子有一百多平米。澡堂子里往往有四五个这样的大池子,早晚都冒着腾腾的热气,因为矿山的职工都是黑白两班倒。池子内四周砌有矮矮的台阶,可供蹲坐搓澡。
职工的澡堂进出的都是一个个刚从矿井里上来的汉子,他们全身只有两只眼睛是干净的,剩余的部位全裹着一层厚厚的煤灰,漆黑闪耀。本来在洁净的池水冒着蒸腾的热气里,我们玩得正欢,一群脱得赤条条的职工踢开大门就闯了进来。他们一边嘿嘿地笑着,一边张开嘴露出白牙开始叫骂:“你们这群龟儿子,谁让你们进来的?”嘴巴一张一合,黑嘴白牙在灯光下闪烁着,如同突然降临人间的地狱阎罗。我们正惊慌间,他们的一条腿便刺进了热水中,另一条腿还搭在池外,一瞬间整个池子就变成了黑色的泥汤。
接着是一条又一条腿扑通扑通地刺了进来,池子里的水开始如同大海一般汹涌起来。有人站在池子中间,憋住气将打满肥皂的头脸闷进水中濡湿,狠搓一阵,猛地一抬头,哗啦啦的水花带着肥皂泡儿便四溅开来,吓得我们小孩子四处躲闪,可终是难逃他们的黑手。他们只洗了个大概,就将临近身边的小伙伴们猛地提将起来,一边啪啪啪地拍打着他的屁股,一边审问着他们父亲的名字。小伙伴被半吊在水面上,嘴里吱哇吱哇地叫唤着,双脚踢腾着池水,双手在空中四处抓挖,整个澡堂子里便到处都是飞溅的水花。机智的伙伴们开始偷偷地溜出池子,准备逃跑,却往往被围拢的汉子们重新捉住丢进池水中。于是,小孩子的喊叫声,汉子们的大笑声,还有踢里哐啷的水声一起,在几百平的职工澡堂里不断地撞击着墙壁,散发出更加响亮悦耳的回声。他们硕大的骨节和赤裸的胸膛上闪耀着一撮撮粗长的毛发,在浑浊的热水之中开始用粗野不羁的言语来释放井下一整天紧张疲惫的情绪。
去洗澡的次数多了,我们也便知道了很多汉子都是父亲们的同事。粗野的矿山职工们之间,却往往有着豪爽豁达的友情。后来我才明白,那是因为井下的世界是一个黑暗、残酷,甚至血腥的世界。很多人早上下井的时候,都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看到明天的太阳。矿山职工与职工之间,互相搭伴,便相当于性命相托。这是正值玩龄的我们根本无法体会的一种情感。
在矿山中,工种的不同,便是命运的不同。父亲是在经历了数年的掘进工之后转为安检工的。掘进工在井下承担着挖煤的重任,安检工则负责矿井中各种数据的正常维护。尤其是瓦斯数据,一旦超标便会引起重大责任事故,这个时候的安检科往往是要被严厉问责的。而掘进队则负责着搭建支柱、掏煤、放炮等各种细分工种。在矿山之中,安检科的人员是要经常进行学习培训的。文化知识短缺的父亲,基本上是靠着多年累积的工作经验在煤矿工作了一生。
每次出现瓦斯爆炸、人员伤亡和矿井渗水事故,他们便要接受责任追究和处罚。表面上看,他们每天只是提着检测仪和矿灯,在矿井里四处转悠。实际上,整个坑道的安全都维系在他们身上。尤其是矿井的空气,煤柱纹路的变化,基本上是通过他们在常年工作中“望、闻、问、切”的经验来做出判断的。
在我的记忆中,安检工每个人都有一大一小两个紫红色的词典。一本是《矿山安全知识条例》,一本是《矿山员工知识手册》。大的足有六厘米厚,抛出去能砸死人;小的不到一厘米,能轻松地装进口袋里。只是,我从来没有见过宿舍的叔叔们看它们,更没有见过父亲碰过它们。
3
矿山职工们的娱乐生活相当丰富,每个职工大院都配有一台彩色电视机。每天晚上吃完晚饭所有的职工都搬个小板凳走出宿舍,围拢在电视机前开始看电视剧。电视机都是放在大院中间播放,就显得格外热闹,完全可以用众声喧哗来形容。父亲却不喜欢看电视剧,或者说父亲有时候完全看不懂电视剧情节的起承转合。每天晚上去大食堂吃完饭,父亲把我领到电视机前坐稳当了,就一个人抽着烟去睡觉或者和同事们聊天去了。
20世纪90年代初,也就是我十岁左右的年龄,电视剧的节目多以香港拍摄的剧集为主,不管是什么内容,我都能看得全神贯注,津津有味。尤其是武侠片和警匪剧,更能引发小孩子心目中的英雄情结,每次播放我都会提前搬着板凳出去,寻找有利位置。一直看到整个院子鸦雀无声,回头的时候才发现大多数人都回去睡觉了。只剩下三五个人,边喝酒边聊天,围着电视机坐着。这个时候,父亲往往会专门出来领我回去睡觉。电视剧还没有播完,我死活都不愿意离开。我的性格特别腼腆,但犟起来谁都没办法。有的叔叔便专门跑过来,问我看得懂吗?我往往会回头瞪他们一眼,转身继续看我的电视剧。叔叔们便会在我身后哄堂大笑,父亲也跟着一起笑。其实这个时候的剧目往往是外国片,也就是译制片,是放到黄金时间段之后来播放的西方剧集,大多数人觉得外国人不好看,就都提前散场了。
当然,最有趣的是每个周末,职工影院会播放一两场电影。一般在周六晚上八点开始,五六点的时候整个矿井的职工与家属们都会闻风而动。中午三点的时候,布告栏便会用一整张大黄纸贴出电影的剧目,是一场还是两场,是武侠片还是文艺片,抑或警匪片,布告中都会写个明白。布告的每个字都有拳头那么大,但他们会把武侠片写成武打片,把文艺片写成恋爱片,把警匪片写成枪战片。影片的精彩自不必说,因为那个年代在农村孩子们一年半载才能看一次政府的放映员轮派到山村的电影,矿山里的职工们一个月却可以看四次电影,这简直就是天大的福利。所以在那一个月暑假的矿山岁月里,电影便是我期盼和等待的文艺大餐、精神盛宴。虽然很多时候,看到的也只是《上甘岭》和《烈火金刚》这样的英雄片,而能看到大兵团作战的中越战争的影片就是烧高香了。对于小孩子来说,巨大的银幕上,刀山火海的战争场面无疑是最具吸引力的,英雄人物的牺牲甚至能让我们流下惋惜的泪水来。那种童真的感动,是我们在以后的岁月中逐渐磨灭和永不再生的一种情感。
另一种职工生活的娱乐方式,则是私人放映厅中的录像。录像的内容比电影会更精彩,也是职工生活中最带色彩的部分。一般能进录像厅的都是青年人,小孩子是不许进去的。即使允许进去,也是看到一半的途中就被清场了。直到多年之后,录像厅遍布县城的大街小巷时,我才明白童年之中的矿山录像厅里意味深长的神秘色彩究竟是什么。
4
夏天特别热的时候,蚊虫到处飞舞,一咬身上一个红疙瘩。矿山大院的蚊子尤其厉害,腿长个大,全是职工食堂倒掉的油水流到很远的排水沟中喂养起来的。那个时候并没有花露水之类的驱蚊药,顶多就是清凉油,风油精也不多见,蚊香我只在干部的办公室里见过。父亲就经常和同事们晚上去矿山外面的山上拔蒿草,回来之后把蒿草搓成草绳晒干,晚上在房间点燃,用来熏驱蚊蝇。
我却对这种驱蚊的方式特别反感,因为蒿草点燃后的烟太浓烈,有时候熏得人睁不开眼睛。风一吹,烟就会钻进眼睛,不由得就涕泪横流起来,还连带着咳嗽。我反对了好几次,父亲便只能等我彻底睡着了,才下床去开始他的驱蚊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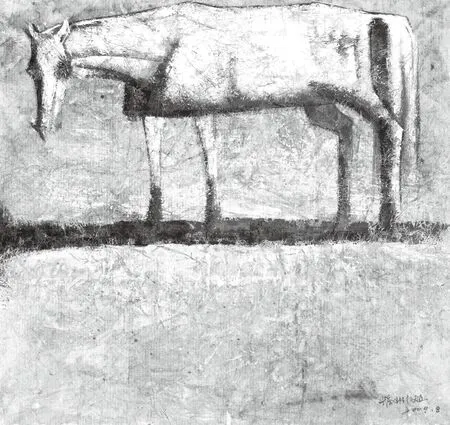
拔割蒿草搓草绳,似乎是我在童年看到的父亲唯一的娱乐方式。他不懂象棋、不会扑克,对打麻将、喝酒都没有兴趣。往往很多同事们玩得不亦乐乎的时候,也是他最闲得无聊的时候,这时,搓蒿草就成了他唯一的精神排遣。而父亲喜欢的秦腔,在职工之中很少有人喜欢,小时候的我几乎一听到秦腔就想把耳朵捂起来。
原来,我一直以为父亲枯燥、单一的生活方式是因为文化水平低,后来又觉得并不全是。也许至今,我也无法给父亲没有太多娱乐的生活做出最明确的解释。如果真要去解释,那只能说父亲是个农民,是一个太过老实本分的农民,一个从来不懂得投机取巧、动用关系,只会默默无闻付出的农民。尽管他在矿山里生活了一辈子,从不满二十岁被招工,到六十岁退休。四十余年的矿山生活,并没有把父亲养成一个工人。就好像在别人下象棋、看电影,甚至读书、进修,不断地升级进步的时候,他只会一如既往地坚守着自己本分的工作,甚至黑白不分地为同事顶班,从来不会有更多的向往。
也许,只有秦腔这种源发于陕西黄土地的古老艺术,才能让他在沉闷的生活中获得一种生命的释放。所以,秦腔就成了父亲一生中唯一喜欢的娱乐方式。多年之后,当我终于能听懂秦腔艺术之中的铿锵唱词与余音绕梁的时候,父亲却已经不在了。
于是,我才真正地想起父亲一个人抱着收音机蹲在墙旮旯,一边晒着太阳,一边听戏的场面。那个时候的父亲是快乐的,也是孤独的。而秦腔这种艺术形式,很多时候是需要人们一起坐在戏台下看着演员们的念唱作打来细细地欣赏品评的。于是,我又想起了父亲和母亲一起赶庙会的那些场景。惭愧的是,我对秦腔这种剧种了解的太晚,对人生中的悲苦苍凉体会的太晚,所以才错过了走进父亲生命深处的机会,只是看到了他生命表面上的枯燥和沉寂。
我想,我真是个不孝子。
5
父亲的矿山并不是一个安逸的地方,而是每天都伴随着生死、伤亡,伴随着人与石头,人与命运的较量。在工作中,父亲的脚趾,手指甲盖,都先后被煤块砸裂,留下终生的残缺。但他面对这些,往往只是嘿嘿一笑了之。我甚至有时候特别怨恨他的这种笑声,觉得那是一种太过宽厚和笨拙无能的笑声。可是,每一次,他都是在这种笑声的陪伴中趟过生命的河流,带给我们最踏实的依靠。那种五味杂陈的内心感受是根本无法用语言来陈述的生命冲动,是爱与恨,快乐与悲伤,幸福与痛苦相互交织的咸涩味道。
在我们村,父亲可能是第一批走进矿山的人。在他之后,还有更加年轻的力量都在他或介绍或帮扶的关心之中走进了矿山。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农村,是真的穷,真的缺钱。虽然不至于饿死,不进煤矿,手头是连一点零花钱都需要从鸡屁股里去掏的。
可进了矿山的人,是几乎等同于把命交给了阎王的人。一进去就再也没有出来过的,比比皆是。往往进去的时候是一个活蹦乱跳的人,出来的时候就成了一团模糊的血肉。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各种生命的悲剧都在矿山里上演,却依然有人前赴后继。而父亲,却从来没有因此流过一滴眼泪。属虎的父亲,命是真的硬呀,瓦斯爆炸、矿井渗水、煤柱坍塌,各种险情在他的面前一一经历。每一次矿难过后,他们都是第一批下井检测的人,他却始终没有倒下。因此不知道有多少同事,在他的面前竖起大拇指,他却依然只是嘿嘿地一笑了之。
母亲一直说,进了煤矿的男人,都是两块石头夹着一块乳,这“乳”便指的是人的血肉之躯。矿山是父亲一生的安身立命之处,也是我走向自我人生路途的基石。离开了矿山的父亲,就真的成了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老农。虽然他做的活路总是被母亲瞧不上,总是粗糙笨大,却总归是我们依靠的一份力量。直到最后,我一日日地远离了乡土,而他一日日地把自己变成了乡土的一部分。
站在苍凉而浑厚的坟土之上,我不知道究竟是谁背叛了谁,又是谁在依靠着谁?父亲血脉相依的矿山,如今已成了千疮百孔的沉降区;母亲所依赖的土地,也不免要遭受“田园将芜胡不归”的现实。只有我,踏着他们人生的履历在怅惘着、追寻着,看那滔天巨浪的乌金之海翻涌奔腾出明天的期冀,看这无声沉寂的乡土田园不断催生出沾满晨露的根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