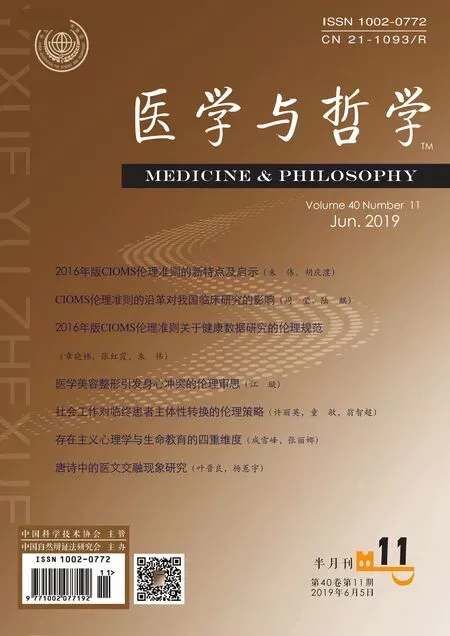论“基因编辑婴儿”对人的尊严的挑战*
2019-02-25刘亚飞马小敏孙洪岩王云岭
刘亚飞 马小敏 孙洪岩 王云岭
“基因编辑婴儿”遭到科学界和社会公众的一致反对,但是很少有人能够真正清晰地指出“基因编辑婴儿”到底涉及哪些伦理问题,尤其是很少有文献涉及对人的尊严的讨论。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一事件的详细梳理,从科学层面分析对人的胚胎进行基因编辑可能对人的尊严带来的影响。
1 “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的回顾与梳理
1.1 “基因编辑婴儿”事件
2018年11月26日,南方科技大学生物系副教授贺建奎宣布,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婴儿已于11月在中国健康诞生,其宣称,由于这对双胞胎的CCR5基因使用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进行了修改,使得她们出生后即能天然抵抗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事件发生后,引发了科学界和社会公众的强烈关注,贺建奎本人也因此受到强烈谴责。
“基因编辑婴儿”事件所利用的科学原理是,CCR5 蛋白是HIV侵染机体的辅助受体[1-2],当CCR5 基因缺失32个与胞外第二环结构相关的核苷酸(C-C chemokine receptor type 5 Delta-32,CCR5Δ32)导致的移码突变,使CCR5蛋白表达提前终止[3]。而此种突变对 HIV-1 (艾滋病毒的一种亚型,目前发现的还有另外一种亚型——HIV-2)的感染有高度抵抗力。因此,从理论上来讲,通过基因编辑技术人为制造出缺陷型CCR5Δ32,即可阻断 HIV-1的入侵途径。
1.2 是否一定要通过基因编辑技术阻断HIV母婴传播
实际上,目前已经有相当成熟的技术手段来阻断HIV母婴传播,且已被大量的研究所证实。文献表明,通过HIV孕前检测、三联高效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治疗(highly active anti-retroviral therapy,HAART)、产科干预以及产后人工喂养等一系列措施,能显著降低HIV母婴传播率[4]。此外,对于HAART的治疗效果,研究者们经过科学的临床试验后也得出相同的结论,如庞俊等[5]对39例HIV感染的孕妇于13周~38周进行了HAART,并结合安全分娩和人工喂养,结果显示HIV母婴传播率为0 ;王奇等[6]的研究显示,与未使用抗病毒药物阻断以及单一药物进行阻断的方案相比,联合抗病毒药物阻断方案预防HIV 母婴传播效果最佳;刘冬梅等[7]采用相同HAART方案对孕14 周、孕28周的HIV 孕妇进行母婴阻断后发现血浆病毒载量明显下降。即便是男方为HIV携带者,也可以通过精液洗涤等技术手段阻断HIV的传播。由此可见,以阻断HIV为目的所进行的胚胎基因编辑本身就是不必要的。
1.3 胚胎基因编辑的理想前景
基因编辑技术从很早的锌指核酸酶技术(Zinc finger nucleases,ZFNs)和转录激活因子样效应物核酸酶技术(transcription activator-like effector nucleases,TALENs)到NgAgo再到 CRISPR/Cas 9,其发展已经经历了三代更迭,其编辑效率以及编辑特异性也有显著提高,目前已经有应用此技术进行疾病治疗的报道,因不涉及到胚胎的基因编辑,故此部分不在本文的研究范围内。
研究者们热衷于基因编辑技术尤其是胚胎的基因编辑,是由于其巨大的应用前景。如对胚胎进行基因编辑后,可以避免一些遗传性疾病的发生,如地中海贫血、某些癌症以及一些心血管疾病等;对某些疾病从根本上达到预防、改善或治疗的效果,如PKD1/2基因突变导致的成人型多囊肾,dystrophin 基因异常导致的杜氏肌营养不良综合征(Duchenne muscular dystrophy,DMD)等;增强人体某项机能,如身高、体能、智商等;调节机体免疫功能以降低或消除同种异体器官移植的排斥反应。因此,基因编辑技术也被誉为“上帝之手”,掌握此项技术就可以扮演“上帝”的角色。
现在研究最多且热度最高的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自2012年应用于真核细胞以来就一直被研究者们所青睐。尽管目前此项技术还存在诸多不足,如基因编辑效率较低,无法避免脱靶效应,基因编辑后出现嵌合体比例较高等,但随着科技的发展,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基因编辑技术一定会发展成熟,那时是否就可以将此项技术应用于胚胎干细胞了呢?实际上,目前国内已有一些研究做过此类尝试,如2015年中山大学的黄军就博士利用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修复了异常胚胎中一个引发β-地中海贫血基因 (β-globin gene,HBB)的突变;2016年广州医科大学的范勇对人三原核受精卵的CCR5进行了基因编辑,这些研究一经报道,立刻引发了人们对生命伦理的热烈讨论。但以上研究均未遭到如“基因编辑婴儿事件”那样大规模的强烈谴责,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所用的实验材料为先天有基因缺陷的个体或三原核(异常)胚胎,均不以生殖为目的;另一方面则是他们使用的实验胚胎在体外发育14天内即行销毁,相关研究只局限于个体,没有对人类基因库造成污染和影响。而贺建奎团队则完全不顾相关规定以及伦理争议和基因编辑技术的瑕疵,以生殖为目的,致使“基因编辑婴儿”出生,而且在试验过程中贺建奎曾在一枚胚胎中通过全基因组测序检测到1个脱靶位点,但其并未由此停止试验,虽然贺建奎声称在出生后的婴儿脐带血中采用桑格测序和深度测序并未检测到脱靶位点,但目前尚不知道这个曾经检测到的脱靶位点会给这名婴儿带来什么影响,这是令学界和公众无法接受的。
1.4 科学界和社会公众的反对
“基因编辑婴儿”事件遭到了一致反对,然而反对“基因编辑婴儿”的理由大多都是基于基因编辑技术的不安全。例如,存在脱靶效应的问题,也就是在基因编辑过程中未能准确编辑预先设定的目标基因,反而对非目标基因造成影响的现象;基因编辑造成医源性疾病的问题,如外来遗传物质导入生殖细胞后,会参与其他复杂的代谢反应,动物实验已经提示子代会出现医源性疾病[8],等等。其中,由122名中国科学家发表的联合声明说:“此项技术早就可以做,没有任何创新,但是全球的生物医学科学家们不去做、不敢做,就是因为脱靶的不确定性、其他巨大风险以及更重要的伦理。对在现阶段不经严格伦理和安全性审查,贸然尝试做可遗传的人体胚胎基因编辑的任何尝试,坚决反对,强烈谴责!”[9]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艾滋病研究所所长陈志伟认为,“对健康胚胎进行CCR5编辑是不理智的,不伦理的”;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艾滋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张林表示,“这事件已经远远超出了技术问题的范畴,后果将是不可预测的严重”[10]等。美国哈佛大学干细胞研究中心教授穆索努拉表示:“艾滋病并非一定致命,况且对广大贫穷地区来说,有比基因编辑更便宜的疗法。相反,为了获得所谓的艾滋病免疫,便将基因编辑婴儿暴露在未知的其他疾病风险中,得不偿失。”[11]
这些反对理由大多基于技术安全性不足和后果不确定,但这些问题本质上都属于技术问题,可以通过技术进步得到解决,这些问题也没有深入触及基因编辑所涉及的深层次伦理问题,故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本文将对胚胎基因编辑技术可能对人的尊严造成的影响进行深入探讨。
2 胚胎基因编辑与人的尊严
康德[12]46认为,“那些其实存不以我们的意志为依据,而以自然的意志为依据的东西,如若它们是无理性的东西,就叫作物件。与此相反,有理性的东西,叫作人身,因为他们的本性表明自身自在地就是目的,是种不可被当作手段使用的东西,从而限制了一切任性,并且是一个受尊重的对象。”这说明,至少在康德看来,人的尊严是以尊重人的自然存在属性为基础的,享有尊严的依据则在于人有理性。据此,我们可以分析以下三个问题。
2.1 基因编辑婴儿的尊严被贬损
在深入分析胚胎基因编辑技术与人的尊严之间的关系之前,我们首先来看这一做法的大致过程:胚胎基因通过基因编辑技术按照预定的方案进行修改;通过辅助生殖技术移植回子宫并经过十月怀胎分娩成人;被编辑的基因随着人体的发育逐步发挥其预定的功能。从宏观角度来看,基因被编辑个体,其实存并非完全以自然的意志为依据,而是部分以基因编辑者的意志为依据。也就是说,其实存状态是一种人为干预的结果,是他人目的的体现。尽管基因被编辑个体仍然可能拥有理性,但其所拥有的理性在一定程度上亦是基于他人的意志,是一种作为他人干预结果的理性。而人的尊严的核心在于以人本身为目的,人应该基于自己的自然存在属性能够自治自决,而不应处于被操控的他治他决的地位[13]。韩丹[14]曾经论述过克隆人的尊严被先天贬损的问题,基因被编辑个体的尊严实际上也被先天贬损,其逻辑与克隆人的尊严被先天贬损如出一辙:基因被编辑使得基因被编辑个体的生理特征和先天禀赋预先被其他自由意志主体决定;这种预先决定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基因被编辑个体自由意志的实现;这进而导致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基因被编辑个体自由做出选择和行动的机会,由此意味着基因被编辑个体的尊严被先天贬损。实际上,基因被编辑个体的出生作为基因编辑者远方图景的实现已经沦为基因编辑者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然而,康德[12]81教导人们说:“你的行动,要把你自己人身中的人性,和其他人身中的人性,在任何时候都同样看作是目的,永远不能只看作是手段。”因为任何东西作为手段的价值都依赖于与之相联系的人类欲望,而只有那种作为目的的价值才是一种自在的绝对价值,人才因之拥有地位和尊严。当然,也许有人会辩护说,基因编辑的目的之一就是使得基因被编辑个体获得更好的人类遗传性状,虽然这里面掺杂了基因编辑者的意志而使得基因被编辑个体在一定程度上沦为基因编辑者的手段,但是这绝非仅仅把基因被编辑个体作为手段,而是同时也作为目的,如基因增强就是如此。然而,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经过基因编辑后,基因被编辑个体失去了基于自然理性的那种发展可能性,在一定程度上,其存在的每一种状态都是基因编辑者意志的产物。而根据康德的思想,人的尊严,就是那种超越一切价值的、在人格上所具有的不可冒犯、不可亵渎、不可侵越、不可剥夺的一种社会性的精神特质[15]。基因被编辑个体的这种社会性精神特质则因出生前的基因编辑被冒犯和侵越,从而尊严被先天贬损。
2.2 胚胎是否有尊严
假如只是对胚胎进行基因编辑,而不使其出生呢?这样做是否符合伦理?这就涉及到“胚胎是否具有尊严”的问题,或者说“胚胎是否应当被当作自然人一样对待”的问题。
国外一些宗教组织认为胚胎是人类生命的开始,销毁损坏胚胎无异于谋杀人的生命,这是对人的亵渎和不尊重[16]。因此,他们强烈反对把胚胎用于科学研究。根据这种观点,任何针对胚胎所做的科学研究都是不合伦理的,那么人类也永远无法得知发育中的自然科学规律,也无法用相关科学知识进行疾病的预防和治疗,这种观点显然过于极端。目前,主流的观点认为,胚胎不具有自然人一样的权利和地位,因为胚胎尚不具有自然人的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但仍应被给予尊重,因为其具有发育成自然人的潜能。但这种观点只是指出胚胎应被给予尊重,但并未涉及胚胎是否拥有尊严的问题。
科技部和原卫生部早在2004年就对我国人类干细胞研究规定了相关的伦理指导原则[17],其中指出“利用体外受精、体细胞核移植、单性复制技术或遗传修饰获得的囊胚,其体外培养期限自受精或核移植开始不得超过 14天”,而且明确规定“不得将获得的已用于研究的人囊胚植入人或任何其他动物的生殖系统”。这一规定表明,从配子到受精卵再到14天之前,原则上是允许进行相关科学研究的。这显然是考虑到胚胎干细胞研究对于再生医学的发展以及治疗某些退行性疾病方面的重要医学价值。但这种考量并没有涉及尊严议题。
为什么把研究用囊胚的发育期限限定在14天以内?这是因为在这一阶段,胚胎尚无神经系统的发育及对外界的感知能力,不具备自然人所拥有的意识和个性特征。这一规定实际上预设了一种伦理观点,这种伦理观点认为,如果胚胎具有了感知能力和意识,就会发展出理性从而拥有尊严,对胚胎的研究操作就会侵犯其尊严。那么14天之前的胚胎是否就可以进行相关研究以及基因编辑了呢?这就需要从基因层面的微观角度进行分析。因为从宏观角度来看,自然人具备感知能力,拥有理性,因而拥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这是康德尊严思想的一般原理;但从微观角度来讲,自然人感知能力的获得受到基因控制性表达功能的决定。因此,人的尊严的神圣性,从微观层面乃是因为控制人的感知能力的基因具有自然属性,亦即其不是受制于某个特定人类意志,而是天生如此,或者天性如此,亦即康德所说的“自在”。如果从根本上改变了基因的秩序,将来其感知能力自然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其“自在”的属性也在一定程度上遭到破坏,成为某个人类特定意志的产物,其尊严也就必然被侵犯。所以,笔者认为,尽管14天之前的胚胎可以进行相关的研究,如发育学、再生学等,但其整套基因因其自然属性而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虽然可以采用各种技术手段进行观察,但不得进行修改,更不得被当作基因编辑的研究对象。因此,笔者认为,人的胚胎与自然人一样,是拥有尊严的。
但是,对于那些已经明确知道发育中出现了异常的14天以内的胚胎,由于其尚无神经系统的发育及对外界的感知能力,不具备自然人所拥有的意识和个性特征,同时因其发育中的异常而不可能有机会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类个体出生,因此其就不拥有上文所论证的尊严,是允许作为科学研究对象的。这也是黄军就博士和范勇团队所做的研究并未引发强烈反对的主要原因。
是否人体的每个细胞都具有和胚胎相同的尊严呢?因为其所包含的遗传物质都是相同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尽管人体的其他细胞和胚胎具有相同的遗传物质,但发育潜能是完全不同的。体细胞作为细胞分化的终端,在人体各个部位自有其特殊的作用,但其无法再回到胚胎的原始阶段而重新分化成人,因此他们的尊严与胚胎的尊严无法相提并论。然而,作为人的体细胞或组织,仍然是需要被尊重的,如器官移植中供体的器官需要得到供体的同意才能被应用于他人,不得随意处置;手术中切除的人体组织也不得随意被拿来进行使用,如用于科研等,必须事先征得主体的知情同意。
2.3 现代辅助生殖技术是否损害胚胎的尊严
当下所运用的现代辅助生殖技术,如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n vitro fertilization and embryo transfer,IVF-ET),卵胞浆内单精子注射技术(intracytoplasmic sperm injection,ICSI),胚胎植入前遗传学检测(preimplantation genetic testing,PGT)等,都涉及到对胚胎进行的体外操作,这样做是否损害了胚胎的尊严呢?根据上文对胚胎尊严的分析可知道,现代辅助生殖技术操作是否损害胚胎的尊严取决于这些操作是否会伤及人类基因的控制性表达,也就是是否会导致借辅助生殖技术出生的个体的“自在”属性遭到破坏。我们知道,IVF-ET只是改变了人类生殖细胞结合(受精)的场所,人工授精[夫精人工授精(artificial insemination by husband,AIH)/供精人工授精(artificial insemination with donor semen,AID)]则是改变了受精的方式,ICSI是挑选特定的健康精子与卵子进行结合,PGT也只是利用客观的技术手段,如基因测序等,对胚胎的遗传物质进行分析检测以证明这枚胚胎是否携带有某种不可逆转的遗传病,它并没有对胚胎的遗传物质做出改变。可见,上述操作都不涉及对基因的操控,因而不会伤及人类基因的控制性表达,也就不会出现借辅助生殖技术出生的个体的“自在”属性遭到破坏的问题。所以,笔者可以有把握地说,现代辅助生殖技术不会损害胚胎的尊严。
3 基因被编辑个体的尊严受侵犯的具体体现
对胚胎进行基因编辑进而使其出生,被编辑的个体被他人作为实现某种目的的手段或工具进行操控,其尊严已被先天贬损。笔者认为,人的尊严有三层含义,分别为人性尊严、生命尊严和人格尊严。基因被编辑个体的尊严被侵犯也具体体现在这三种意义上的尊严被侵犯。
3.1 基因被编辑个体存在被工具化状况,贬损其“人性尊严”
康德指出:“人性尊严就是指人的尊贵和庄严,指人具有一种高于物和其他生命形式的,且令他人敬畏、独立而不可侵犯的身份和地位。”[18]人性尊严在伦理上拥有至上的价值,它展示了人权的一个重要方面,体现了一种核心的道德价值。人性尊严最基本的属性是独立和自主,不受他人的操控,表现为尊贵和庄严这种独立自主的属性不仅仅体现在后天的不受他人利用或不被他人侵犯,更体现在人体最根本的遗传物质的“自在”属性。受精卵作为一种全能的干细胞,从发育学的角度来看待的话,其生长具有全能性。正是依靠基因及染色体的自在有序的控制,受精卵才逐渐从一个细胞发育为具有无数细胞的婴儿,进而继续分裂增殖,有序生长,从少年到青年,从成年到老年。而一旦胚胎的基因被编辑,就意味着最原始的干细胞所携带的遗传物质的自然属性受到人为控制,每分裂增殖一次所带来的生理特征或先天禀赋都蕴含着他人意志的属性,如本该生长至170cm就停止的人经基因编辑后增强了身高这一特征,最终长到190cm,且其后代也都稳定遗传这种特性,也就意味着他的后代也都蕴含着被他人控制的属性,其人性尊严被先天贬损。这与优生优育截然不同。尽管人们在选择另一半的时候带有自我偏好和意图,如自己身高较矮而在选择伴侣时寻找高身材的异性,从而使得下一代可以弥补身高这一缺陷。从结果上看,两者是相同的,即后代的身高都得到了增强。但过程是完全不同的。前者的基因被他人的主体意志所干预和控制,是他人意志干预的结果,后者尽管人为选择另一半,但在基因自由组合过程中,染色体遵从自然法则重组配对,将来具体发展状况不受他人干涉,没有人为因素的干预,从遗传物质角度来讲,是遗传物质“自在”属性发挥作用的结果。
3.2 基因被编辑个体的生命被操控,贬损其“生命尊严”
《世界人类基因组与人类宣言》第一章第一条指出:“人类基因组是人类家庭所有成员根本统一的基础,也是承认他们生来具有的尊严与多样性的基础。” “生命尊严”的价值内涵是: 人的生命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人只有健康地活着才能体验并享受其他一切价值,尊重人首先必须尊重人的生命健康[9]。“生命尊严”的主体是生命,基因组决定人的生命样貌,即便基因编辑技术已经完全成熟,能够达到人们所讲的“定制属性”的程度,但其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也难免利用一些生物化学试剂进行基因编辑反应的控制,这一过程已经对其生命构成了一定的威胁。正如王坤平[19]所讲:“因为自然生命力的选择,是几万年、几亿年进化的结果,而这绝不是简单的、机械人工选择所能模拟的;再精致的技术,对于生命本身的精致而言,依然是粗糙的;再高明的手段,对于生命尊严而言也是下位的。坚守生命尊严,敬畏生命的自然力量,就是对人类的最大关爱。”因此,胚胎基因编辑实则是损伤了胚胎的生命价值。
3.3 基因被编辑个体对自我评价和外界评价的感知无法预测,贬损其“人格尊严”
“人格尊严”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所表征的是人的尊严的一个组成部分,强调的是人格的价值地位和对人格予以尊重的伦理态度,即人格尊严是主体对自己尊重和被他人尊重的统一,是对个人价值主观评价和社会评价的结合[20]。“人格尊严”亦是一个法学概念,指的是人格权,即公民所具有的自尊心以及应当受到社会和他人基本尊重的权利,包括隐私权、名誉权、姓名权、肖像权等。通俗来讲,“人格尊严”可分为两部分,自尊和尊严感。自尊是主体对自身的评价,如是否能够接纳并肯定自己等;尊严感则是主体对他人评价的感知,如受到他人夸奖时的自豪感或受到他人责备批评时的耻辱感等。
那么,基因被编辑个体的自我评价应当是怎样的,他是否对自己的“前世”具有知情权?基因被编辑个体如何看待自己的“自尊”,即主体能否接纳被编辑过基因的自己,也就是能否肯定自己的存在意义。这类似于那些被领养的孩子,他们对自己的身世具有绝对的知情权,当他们了解一切之后会如何看待自己?这一答案非常重要,因为它决定了这些孩子如何看待他人以及如何看待周围的一切,即连自己都接受不了的人也很难去接受他人。基因被编辑个体也一样,他对自己的身体具有完全的知情权,但在他得知自己是经基因编辑而来后,其“自尊”很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混乱,后果难以预知。
此外,基因被编辑个体的“尊严感”又如何呢?假若技术成熟的情况下,基因被编辑个体不需付出特殊努力就可轻易获得某种特征,如高智商、强体力等,当他受到他人的夸奖和赞誉的时候,是会感到自豪还是会感到可笑?如果基因被编辑个体的身世一直不被告知,按照自然人相同的培养模式,再加上他自身的“先天因素”,很有可能成为别人眼中的“佼佼者”,但这种成功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作弊”的嫌疑,他的一生对自身的知情权早已完全被剥夺,这对基因被编辑个体来说是不公平的。因此,无论基因被编辑个体如何挣扎,其“尊严感”势必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扭曲。
4 结论与主张
随着医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体的终极密码——基因逐渐揭开其神秘的面纱,使得人们有机会去了解并利用基因技术,来改变自身的属性。如找到某种疾病的致病基因,从基因层面进行治疗;发现某些遗传疾病的基因突变位点,利用基因操作技术及胚胎植入前遗传学检测等手段避免遗传给下一代;根据个人基因信息预测是否对某些疾病具有易感性,从而防患于未然等。然而,与此同时,对基因层面的操作也使得人的各项基本权利,尤其是人的尊严,面临巨大挑战。在新的技术背景下,有必要从基因科技角度出发,完善各项法律、法规、伦理原则等,如基因完整权、基因信息权、基因隐私权等,以规章制度的形势颁布,从而更好地指导人体基因相关技术的快速发展,避免基因编辑技术对人的尊严造成挑战,甚或贬损人的尊严。与此同时,无论有没有相关规章制度,任何技术的应用,也包括基因编辑技术,都应当在充分尊重人的尊严及生命伦理规则的前提下适当进行,本着“有利”大于“有害”的原则进行考虑,从而更好地把握科技进步造福人类与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之间的动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