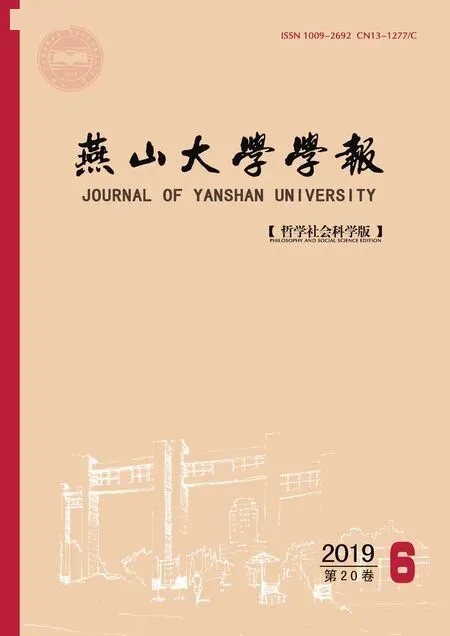贾平凹《山本》中“陆菊人”形象阐释
2019-02-24王俊虎白翻琴
王俊虎,白翻琴
(延安大学文学院,陕西延安716000)
一、引言
近年来,贾平凹继2011年的《古炉》、2013年的《带灯》、2014年的《老生》、2016年的《极花》等四部长篇小说之后,2018年又出长篇新作《山本》。纵观这几部长篇小说,不难发现,四部作品贯穿着一条强烈的越来越具有反思色彩的主线。如《古炉》,通过对故乡小山村的描绘,来打开反思文革的一扇窗子,其间也贯穿着对贫苦中人性恶的描述;如《带灯》,通过乡镇女干部带灯来反映社会基层的问题,他称自己“不能女娲补天,也得杞人忧天”;《老生》则通过对过去的国情、世情、民情的呈现来反思人性人情;《极花》通过妇女被拐卖引发的一系列道德与伦理上的悲剧来反思当下凸显的社会问题。在以上四部作品中,作者的反思有来自民间、传统的,又有对现代意识的反思。例如《古炉》中所用到的原型——陕北铰花花的老太太周平英及其剪纸画册,《带灯》中对“地藏菩萨”的极度崇拜,均具有浓厚的民间色彩。《山本》似乎有继承这一传统的意味,但又不仅限于此,在这部作品中,作者除了以往的反思,更将现代性、传统性与民间性置于同一时空下,即二三十年代一个充满秦岭气息的涡镇之中,通过这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故事的讲述与被讲述,连同着秦岭中的山石草木,共同编织起一个关于“三性”的经纬网。纵横交错的“三性”经纬网正是作者主观意识中对“三性”间相互冲突与调和的认识的外现,外现为人物间命运的纠葛。随着人物间关系由紧张到舒缓,作者的态度也渐趋明朗,对于“三性”的态度是贾平凹站在较以往更高层次上对过往的一个反思。如贾平凹本人在访谈中所提到的:“年轻时阅读,好技巧,好那些精美的句子,年纪大了,阅读看作品的格局和识见。现在人阅读习惯于看作品讲了个什么故事,揭露了什么,宣传了什么主义,或者有趣不有趣,其实人类最初谈小说,就是为了自己怎么活人,里面有多少值得学习的生活智慧。《山本》是我60多岁后的作品,我除了要讲一个完整有趣的故事,就是一有机会就写进我60多年的生命经历中所感知和领会的一些东西。”[1]
笔者认为,在作品中,女主人公陆菊人是寄托了作者愿望的一个理想人物,有学者将她称作不食人间烟火的“地藏菩萨”,笔者更愿意将她作为一个有女儿性、妻性、母性的普通女子来看,并由她来看与她有着联系的各类世俗人。通过这些世俗人,让我们更真实、真切地还原各类世俗人身上所具有的“三性”特点,以为生活在当下的我们提供借鉴,即作为个体如何以一个健康、积极、和谐的姿态来面对生活乃至生命中的有常与无常。
二、在民间自由舒展着本性的“陆菊人”
因家境贫寒无力偿还债务,年仅12岁的陆菊人就被父亲许为杨家的童养媳,要嫁给一个仅七八岁、两筒子鼻涕、整天玩“占山头”的小孩子。虽不情愿,小小年纪的陆菊人倒也忽然能想开了:“自己给爹当了一回女儿,现在再去给杨家的儿子当一回媳妇,这父女、夫妻原来都是一种搭配么,就像一张纸,贴在窗上了是窗纸,糊在墙上了是墙纸。”[2]2陪嫁的除了三分胭脂地还有一只猫。如同终日卧在门楼上的瓦槽里的老猫,陆菊人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圆了房,有了身孕。
此处描写被学者诟病为描写得不真实,认为小小年龄的陆菊人思想未免太过老成,笔者却认为恰是这类看似有失妥当的心理刻画才成功地塑造了陆菊人的形象。陈思和先生将《山本》分析为一部民间说野史,认为其继承了民间说史的特点,即“老百姓对于历史真相并不感兴趣,替古人担忧只是一种审美功能,并无功利实效”[3]。按照这个思路,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有关陆菊人的这类写法:井宗秀邀请陆菊人担任茶总领一职,替他料理茶坊生意,陆菊人始终不能做出决定。虽先后有公公的鼓励和陈先生的点拨,她还是不能定下心来,于是将决定权交托出去——如果能够摊个完整的饼,如果能见到不常见的野兽,便是上天的安排,她就应承井宗秀。让人意外的是,陆菊人的这些念想竟全部实现,她也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这份差事。按照语境推测,陆菊人最后会答应井宗秀的邀请,一来因为两人有不浅的交情;二来通过前面陆菊人帮助井宗秀的几桩事情足以说明陆菊人的才干;三来有公公和陈先生的支持。但此处,作者为何要费如此多的周折,来写陆菊人一连串的心理活动呢?笔者认为,深受传统的“天时地利人和”观念的影响,作者只有把陆菊人“求神拜佛”的矛盾心理刻画出来,才能使得她最后接受茶总领这一身份合情合理化,也增加形象的立体真实感,即从侧面完成了对民间的陆菊人形象的塑造。
提及民间及民间性,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莫言和他笔下的一片红高粱,有落后、有野蛮、甚至是充满血腥与暴力的,但事实上,民间也有它所对应的温情。在《山本》中,同样有提及五雷一类土匪身上野蛮的民间性,但在笔者看来,这并不是作者描写民间性的重心所在。相反,与这类民间性相对应,真正代表着作者心目中理想的民间性的应是在涡镇中生养并成长起来的陆菊人一类的秦岭人,暂且将他们称为“陆菊人们”吧。剩剩每次生病,陆菊人总要抱着他跑去给陈先生看看,陈先生的存在,对于陆菊人来说,不仅是个医者,更是可以指引她人生道路的智者。因为陈先生眼睛看不见,陆菊人总是隔几天就到陈先生家里或帮他洗衣服或擀一案板面或拿起扫帚扫院子,即使在她后来当了茶总领,还时常跑过去干这些零活。在井宗秀给她送去三盒特色糕点时,她都没忘记给陈先生送去一盒;看到花生后,虽然陆菊人对井宗秀也有特殊情愫,但想到自己已是寡妇之身,便有意撮合花生与井宗秀,并且将花生当做亲妹妹一般时时教导提携,花生结婚当晚,她为自己有一丝丝醋意而发笑;阮天保攻打涡镇时,几个妇女因为见不到井宗秀,于是将怨气发泄在陆菊人身上,当周一山要责罚她们时,陆菊人主动替将要受到责罚的她们求情;公公因为从别人口中听到井宗秀与路菊人的风言风语,便劝陆菊人改嫁,陆菊人看到公公年事已高,眼睛看不清楚还做好了饭,她心里愧疚又自责,“她在检点自己:为什么惹得那些人说自己的不是呢,是自己和井宗秀走得太近了?”“陆菊人倒恨了一句杨钟:你不担沉你走了,让我受这号罪!却又想:这也怪不得杨钟,那些人是对井宗秀怨恨了又不敢对井宗秀怎样,拿我发泄了。”[2]252在这里,贾平凹极力彰显一种民间伦理关照下人与人之间所呈现出的人性关怀。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民间伦理则是不定型的、由普通民众在其实际生活中自发形成的、在话语表达上居于主流之外的价值观念,它广泛地表现在人们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非理论化的现实状态之中。”[4]由此来看,“陆菊人们”身上的这些品质正是“民间伦理”这一“小传统”[5]所赋予的:勤快、善良、淳朴、憨厚、知恩图报等。
除了陆菊人,在民间伦理关照下,这里还生长了一群豪气冲天、侠肝义胆的涡镇人:如因发小情谊,心甘情愿跟着井宗秀出身入死的陈来祥等人;平时会因蝇头小利斤斤计较,但在预备旅最艰难时刻,却甘愿拿出自家米、面、柴、油的店掌柜们;又如在战事集中时,预备旅一声令下,全家出动或是参与战事或是帮忙做饭送饭的人家。即使生活在涡镇上有各种各样毛病的小人物们也都有各自的可爱之处:夜里敲着警锣,几十年如一日地为涡镇人报送平安的老魏头;像跟屁虫一样忠诚地追随着井宗秀,不允许别人对井宗秀有丝毫不敬的蚯蚓;又如浑身长满毛病,但在大是大非面前却有几分责任担当的杨钟;慈善本分的杨掌柜;就连土匪也懂得知恩图报。
涡镇上更生活着一群有着顽强而又多彩的生命力的“陆菊人”。老魏头在被土匪砍了数刀之后,抱着神像祈祷,后来竟奇迹般康复;刑瞎子在被砍掉双腿之后,竟存活数日,直至剥皮剜心才死;在土匪玉米被毒蜂群攻,生命奄奄一息时井宗秀发动全镇人对其又是吐唾沫又是抹鼻涕的土方治疗……然而,这却仅是贾平凹笔下关于民间性的显性表现,其真正的内涵却蕴藏于人物的骨髓之内。如陆菊人,由出身贫寒的童养媳成长为显赫一时的茶总领,陆菊人的经历可谓传奇,但与之相伴的亦是人生的大起大落:丈夫早年离世,儿子年幼又残疾,年迈的公公虽时常呵护她却也在意外中悄然离去,被寄予了自己人生希望的井宗秀在到达事业的巅峰时遭仇家暗算丧命。面对着人生的无常与遭遇,陆菊人身上散发出的是一种超生命力的生机。这种生机来自民间,是自由的,更是无穷尽的。
最后,涡镇在炮火的轰击之下遭到重创,三分胭脂地的梦境随着井宗秀的死亡而彻底破灭,故事的参与者也大多丧生在这次战役中。陆菊人活了下来,踉踉跄跄地跑向安仁堂,安仁堂安然无恙,延续着陆菊人生命的剩剩也安然无恙。作者在某种程度上正暗示了充满生命力的民间精髓的一种延续。
三、多重身份关照下回归传统的“陆菊人”
军阀、土匪、逛山和刀客在秦岭一带的出现,使得一向安宁的涡镇变得不安宁起来,涡镇的人开始开凿石窑,恐慌也成了人们议论中的主要话题。老魏头与陈皮匠老婆一次偶尔的对话唤醒了陆菊人内心的秘密与惊喜,赶龙脉人的预言与陪嫁的三分胭脂地在陆菊人的心里生根发芽,希望随着腹中胎儿的成长而萌生着。或许是命运的安排,在陆菊人坐月子期间,井掌柜意外地去世,不知情的杨掌柜将她的三分胭脂地转而送给井宗秀安葬父亲。阴差阳错的安排,使陆菊人的注意力不自觉地转向了井宗秀,在改变井宗秀命运的同时,也为自身命运的起承转合埋下了伏笔。
杨钟生性顽劣,做事又不着边际,陆菊人在公公的帮衬下,渐渐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从五雷刚进村时陆菊人在寿材铺上演空城计到后来巧妙化解三副棺材的困境再到后来利用毒蜂与老魏头巧妙脱身,我们不难看出陆菊人的胆识与智慧。更有意味的是,在杨钟这一“现实丈夫”的映衬下,陆菊人近乎完美地阐释了“好女人”的含义:面对着杨钟的不务正业,她先是多次为他寻找出路,让他和井宗秀一起做酱笋生意,让他跟随井宗秀一起起事有一番作为;在杨钟我行我素,不通人情世故时,总是她不断为他做善后的工作,如在陈先生没能治好剩剩的腿,而杨钟当面责难陈先生时,是陆菊人从中劝阻,还请陈先生不要记怪;在杨钟经常不分场合地直呼井宗秀的姓名且一次次逞能地骑井宗秀的马时,是陆菊人不断地警告他要注意自己的身份。但即便如此,陆菊人在外人面前还是处处维护着杨钟作为一个男人的面子,如在她去阮天宝爹家送礼钱时,她坚决要求写礼单的人记上杨钟的名字,这是她自觉对杨钟作为一家之主身份的尊重与维护。而作为儿媳妇,陆菊人的行为也无可挑剔:在杨钟时不时顶撞杨掌柜时,陆菊人总是从中劝和,时常为公公宽心;她自己对公公说话却总是客客气气,还察言观色着公公对自己的态度,如在井宗秀当了预备团的团长时,她心里高兴又自豪着,因而连着几天的饭都做扯面,“杨掌柜却说:明年有个闰二月的。她心里咯噔了一下,觉得是自己轻狂了。”“就自己没敢多吃,端了碗去给剩剩喂。”[2]141杨钟走后,为了不再听到别人的闲言闲语,她一段时间坚决不与井宗秀往来,而且比之前更加孝顺着公公。作为剩剩的母亲,她同所有的母亲一样,不仅关心呵护他,在杨钟走后,便将剩剩带在身边。考虑到剩剩腿有毛病又早早没了父亲,陆菊人便想把剩剩送到陈先生那里去,而当陈先生答应收剩剩为徒弟时,她激动地留下了眼泪。从这个角度讲,陆菊人是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身为人媳、人妻、人母,她不仅坚守本分,而且通透睿智。
在三分胭脂地阴差阳错成了井家坟地,而儿子剩剩看着也是不成气候时,陆菊人开始将希望寄托在井宗秀身上。从最初的彼此敞开心扉到后来帮助井宗秀成家立业,她就是照着井宗秀一步步走向高峰的那面铜镜,井宗秀成了他的“理想丈夫”。在井宗秀设计消灭五雷,要向她借手镯时,连杨钟都嫌弃从死人胳膊上摘下来晦气,她却说“有啥晦气,灭了土匪我这镯子还有一份功劳哩”[2]125;在预备团成立之初,面对杨钟的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她对着杨钟又是发脾气又是摔盆子,“你这是打井宗秀的脸!预备团脚根还没站稳,你就起了这么个坏头,都像你这样,那预备团不散伙了”[2]142,既是对杨钟恨铁不成钢的无奈与斥责,更是对井宗秀事业的帮衬与扶持。在井宗秀收拾完五雷一伙土匪而被任命为预备团团长时,陆菊人初期的心理活动很丰富,却也很真实,“她真的高兴,井宗秀当上团长了,就暗暗有了些得意”[2]142。随之又想到:“这井宗秀一下子当了团长,该怎么个当法?那保安队队长就瞧不起他啊,而他是和杜鲁成、阮天保一块儿闹起的事,杜鲁成、阮天保能服气吗?涡镇上那么多人也都参加了,又都肯受他管?”[1]142接下来便有了替井宗秀“造势”的系列举措:把众人都感兴趣的“因果报应”事件与城隍转世为井宗秀联系在一起,经杨掌柜之口散播开来,在众人的口耳相传中,井宗秀的威望便树立起来。后来陆菊人又替井宗秀经营茶坊,为他的预备旅提供经济支援,在井宗秀每每犯错误时,总是她在旁提醒或者为他善后。从这个角度讲,陆菊人更是传统意义上的“贤内助”。
而与之相对应,涡镇上同样生存着一群向着传统、向着秩序靠拢的“陆菊人”,如安仁堂的陈先生,在他这里患者并无高低贵贱之分,他的眼睛虽然看不见,心中却始终洞若观火,于他而言,在涡镇开诊所是谋生,更是对救死扶伤这一传统的自觉坚守;又如130庙的宽展师傅,面对着繁复变幻的涡镇局势,她宠辱不惊,世间的丑恶美善于她而言,并没有绝对的界限,她守候的是庙里的香火,更是在乱世中对世间人心的安定,这是自觉向传统礼教的回归。
通过这些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对于“陆菊人”这个形象,作者毫不吝啬地给予了称赞,对她身上的诸多品质,作者也是流露出欣赏的,以至于让读者觉得她就是那个光芒四射、不食人间烟火的地藏菩萨。在笔者看来,不论陆菊人还是她身上的这些品质,都成了作者建构他心中理想大厦的材料,这里简单质朴,各人安分守己,不论为父为子、为夫为妻,都在做自己分内的事情,安仁堂的陈先生如此,130庙的宽展师傅也如此。
四、现代意识统摄下的“陆菊人”
有学者称《山本》中最具现代性的是接受了现代性观念熏陶的井宗丞与具有民主平等观念的麻县长,两者集中体现了现代性的两面——“柔弱的理性与充满暴力的冷酷”[6]。但何谓真正的现代性?韩庆祥在《现代性的本质、矛盾及其时空分析》中指出现代性是“用来在总体性上反思一定历史发展阶段(即现代社会)生产方式、交往方式、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及其蕴含的思想观念,并寻求发展的再生之路的一个核心概念,是指现代社会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根本特性,是对现代化的本质、特性的概念的概括和表达”。[7]
笔者认为,作者在书中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井宗丞、井宗秀在起初是被作者寄予了期望的两个年轻人,“大儿子井宗丞黑是黑,但能说会道,办事干脆”,“小儿子长得白净,言语不多,却心思细密”[2]10,加之又有陆菊人“三分胭脂地”的保佑。兄弟二人虽然走上不同的革命道路,起初的出发点却是相同的:为一方安宁、为民谋利益。随着各自势力的膨胀,井宗丞成了红15军团的团长,井宗秀成了6军预备旅的旅长,却离各自的初心越来越远。井宗丞三番两次地得罪战友阮天保,井宗秀为了自己的私欲逐渐失去涡镇人的拥戴,这都是导致他们最终丧命的重要原因。至于麻县长,书中写道:“他原本一心想要造福一方,但几年下来,政局混乱,社会弊病丛生,再加上自己不能长袖善舞,时时处处举步维艰,便心灰意冷,只兴趣着秦岭和秦岭上的植物、动物。”[2]37如果麻县长仅是一个文人,在乱世之中,或许我们对他的这一行为倒也不必太过苛责,但现实是,他身居县长之职,若不能担负起相应的职责,便是一种罪过。所以他后来一次次受到各方势力的要挟,最后沦为井宗秀扩张势力的工具。面对着同样象征着现代文明的枪火炮弹,麻县长的亲民爱民、平等民主等观念似乎只剩嘲讽意味了,所以等待他的也只有自杀结局。从这个角度讲,作者所倾向的或者说想要建构的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性并不在此。
笔者认为,在《山本》中作者将对现代性的认识与思考更多地熔铸于陆菊人身上,她的成长历程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作者心路历程的反映。由出身贫寒的童养媳到逐渐成为茶行的茶总领,这一脱胎换骨的改变,不仅是身份的转换,更是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独立成熟的女性的崛起过程。
如果说前期的陆菊人对现代性的认识尚处于一个模糊的探索阶段,那么后期的陆菊人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可以说已经进入清晰的自省阶段。依照西方对现代性的认识,现代性主要从经济、社会和政治三维结构中体现出来。那么我们也从这三个方面对陆菊人身上的现代性作以简单分析。
关于井宗秀与陆菊人,有学者称,两人是一种相互凝望、相互依存又相互背离的关系。[8]与研究二人之间关系的关注点不同,此处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对两人这种关系形成原因的探讨上,即陆菊人对于井宗秀的存在价值。
首先体现为陆菊人在政治方面关于现代性的实践:陆菊人在发现三分胭脂地的秘密后,面对着丈夫与儿子的不成气候,转而将希望寄托在井宗秀身上。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井宗秀通过他的权力机构(6军预备旅)帮助陆菊人实现着她所认可的安宁、自由、平等等现代理念,如让涡镇人过上不再遭受土匪刀客威胁的安宁日子,陆菊人是井宗秀实现理想抱负路上不断照清他自己的一面铜镜。在这个过程中,一旦井宗秀的行为偏离陆菊人这一理念,她就有责任和义务去给予纠正:在井宗秀要杀阮家十几口人以泄心头之恨时,是她跑去找麻县长劝阻;在涡镇人传说井宗秀在年轻女人的家门口挂皮鞭时,陆菊人当着井宗秀的面撕掉了那截对他们来说有着特殊意义的褐步,要他对着祖坟发誓并答应立马迎娶花生;在井宗秀对刑瞎子剜心掏肝要替井宗丞报仇时,陆菊人虽然也觉得刑瞎子死有余辜,但仍然“见不得血是那么个流法”[2]497。在井宗秀中弹身亡后,“陆菊人站在井宗秀尸体前看了许久,眼泪流下来,但没有哭出声,然后用手在抹井宗秀的眼皮,喃喃道:事情就这样了宗秀,你合上眼吧,你们男人我不懂,或许是我害了你。现在都结束了,你合上眼安安然然然去吧”[2]506,这是两位知己最后的告别。陆菊人心中有难过、有自责,可能也有对这种寄托无疾而终的无奈与遗憾。
受井宗秀之托,在帮助他经管茶行生意时,陆菊人表现出了精明的才干与先进的管理理念,是她在经济方面关于现代性的实践。拜访麻县长时,她敏锐捕捉到黑茶这一商机,并随之安排伙计去外地学习制作,进而将黑茶作为茶行的主推,不仅创建了茶铺自己的商号,扩大了茶铺规模,而且为井宗秀的预备旅提供了大把的银子;新官上任,她先是通过实地考察各个店铺的经营实况,随之又制定出一系列的规章制度与经营条例,股银制与赏罚分明的奖惩制度的实行,使得各个分店利润大增;在用人方面,面对着不服气却有能力的店铺掌柜,陆菊人恩威并施,将一大伙平时趾高气昂、看不惯女人的大老爷们收拾得服服帖帖,说到底这都是陆菊人过人智慧的表现。
陆菊人打算将花生嫁给井宗秀,便开始对花生全方位地调教。陆菊人对花生的这番调教,作者有意无意流露出他的欣赏与赞叹,是陆菊人在社会方面的关于现代性的实践。她不仅把花生收拾得漂漂亮亮,纠正她的言行举止,更通过一次次的对话,渗透了她对男女两性关系的认识。文中这样写道:“要对男人好,就得知道他的胃,把他的胃抓住了,也就把他人抓住了。”“遇着男人,即使做了夫妻,女的都不要黏人,把男人黏得紧或者啥事都管,虽然你一心为他好,他也会反感。女人不能使强用狠,你把你不当女人看待,丈夫也就不会心疼你。”“他在外边少不了有烦心的事,受气或者委屈,回来要给你说,就是他的所作所为是错的,你也要给他宽慰,不能指责他,一定要待事情安然过去了你再说他的不对。”“你要他不花心,你首先是一朵花,你不要以为过门了,是他的媳妇了,就松松垮垮、邋里邋遢,你一直要开你的花,时不时让他惊喜,让他离不开你,他就离不得你,只对着你好。”[2]327从这些话语中,我们不难看出,这里的陆菊人虽然是贾平凹从男性立场出发塑造出来的具有现代意识的优秀女性,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当下这样一个社会中,同样是对一个优秀女性的要求与评判标准。基于经济独立基础上的精神独立,使陆菊人很好地阐释了一个现代女性的特质。
五、结语
以上三部分,分别从民间的、传统的、现代的陆菊人出发,对她身上三性的探索与认知,是作者在《山本》中对现代性、传统性、民间性这一宏大命题进行思考的一个小切口。正如贾平凹自己在《山本·后记》中所言,“作为历史的后人,我承认我的身上有着历史的荣光也有着历史的龌龊,这如同我的孩子的毛病都是我做父亲的毛病,我对于他人他事的认可或失望,也都是对自己的认可或失望”。[2]526如此说来,陆菊人形象的建构,除了表现作者对生活在当下的现代人的一种不可名状的忧虑之外,更是他自觉寻找出路的一个过程,即人如何以一个健康、和谐的姿态来面对生活乃至生命中的有常与无常?
对这一命题的思考,作者在文中其实是有暗含的:民间既是生命胚胎的发源地,又是为生命不断输送养料的动力站,它代表着野性的同时也代表了顽强,它的浩大与包容,在滋养着人性的同时,也在塑造着合理的人性,涡镇上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就是见证。其次传统并不意味着回到过去的,更不是停留在世代相传的习俗礼节中,而是在靠近传统秩序的同时,安定着内心的一亩三分地,井宗秀等人由起事到发展壮大预备旅依靠的正是这种传统的秩序。而现代性并不等同于某种先进的理念或象征着文明的仪器,而是寻求一种合适的既能为自身的发展提供良好机遇,又能被大环境所容纳的思想观念,陆菊人的成长便很好地阐释了这一点。
由此可见,“三性”问题小至关系到我们个体,即个人如何在现代性、传统性与民间性之间找到一个好的平衡点,以促进自身的发展;大至关系到民族国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既保持自身特色,又能在回归传统与走向现代中找到一条适合的道路。笔者认为对这一问题的探索与思考,不论个体还是国家,可能都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