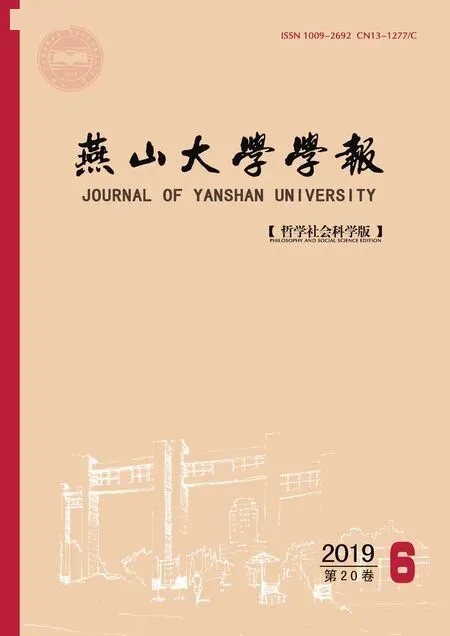单语与多语主义视角下的语言政策研究
2019-02-24张祖瑞王彦军王林海
张祖瑞,王彦军,王林海
(1.秦皇岛广播电视大学,河北秦皇岛066004;2.燕山大学外国语学院,河北秦皇岛066004)
一、引言
“语言政策是国家和政府关于语言地位、语言作用、语言权利、语际关系、语言发展、语言文字使用与规范等的重要规定和措施,是政府对语言问题的态度的具体体现。”[1]54。显然,语言政策是一种官方行为,是政府对语言交际、语言使用和语言维护等领域的态度。语言政策制定专家约瑟夫·洛·比安科认为:“语言政策的制定需要从实际情况出发,有意识地采取明确措施去解决已出现或者预防将要出现的语言问题。”[2]15解决或预防这些语言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以语言思想作为参照,以及对语言意识的重视。语言思想主要涉及到语言学的相关知识,而语言意识则更多地与“民族国家”相关的政治学话语相关,体现出语言的政治属性。这就要求在语言政策制定过程中相关政府部门介入、参与、调研、组织,也需要语言学和政治学等领域的专家来进行指导,即语言政策的制定要以相关的语言学和政治学知识为理论依据。
语言政策制定本质上是一种语言政治实践,是一种政治学意义上的语际整合,而语际整合的终极目标则是通过语言政策制定实现的。虽然语言规则与政治无关,但是,个体生命或民族共同体对语言的使用则属于法国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言的“生命权力(biopower)”的范畴,即语言的使用与个体或民族共同体的健康权、生育权、工作权等同等重要,都是生命权力的具体表现形式;对于福柯而言,生命权力是以生命为目标的权力,是以人口为治理对象的权力理性,以人口的欲望等要素为依据,制定相应的政策,对人口进行管理。[3]语言的生命权力属性势必使其牵涉到国家层面对语言的管理,制定关于语言的具体政策,即语言政策的制定是一种福柯所言的治理技艺,是国家以一种有效的权力形式对人口的语言活动进行操纵或控制。因此,语言政策的制定既是民主平等基础上协调各方面利益的行为,也是国家在政治层面上对语言的治理行为。
大多数国家都不是单一民族、单一语种的国家,因此,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语言政策制定既要顾及到国家的整体性和共同的价值观,还要关涉到各族裔语言和文化中存在的差异因素,这样才能在维护国家整体发展和利益的基础上,充分照顾到各族裔的“个体”利益和对少数族裔语言的保护。这实际上,就是语言政策制定中“单语主义(monoligualism)”和“多语主义(multilingualism)”思想。简而言之,语言政策中主张使用单一语言就是“单语主义”,主张多语并存就是“多语主义”。传统的民族国家通常秉承单语主义的语言理念,“单一语言”已经成为这些国家根深蒂固的国家意识。当前,人口全球化流动的频率和规模不断扩大、全球各地多族裔交杂聚集成为常态、多元文化主义盛行对传统的单语意识构成了严重挑战,这意味着单语主义语言理念已经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状况。由此,本文在对单语主义和多语主义辨析的基础上,解析单语主义对多族裔国家语言政策的负面影响,揭示出多语主义成为现代国家解决国家语言问题、制定语言政策的主要理论依据,对国家制定语言政策有积极的指导意义,以及多语主义在现代民族国家语言政策中的具体表征形式。
二、单语主义与多语主义辨析
语言政策本质上是一种福柯所言的“话语—权力”关系,反映出一个国家内部占主导地位的民族和少数族裔之间的权力关系。在《他者的单语主义:起源的异肢》中,法国哲学家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反复强调,我只说一种语言,但是这种语言不是我的。这个语言永远不是我的,它从来就不是。我自己的语言,对我而言,是无法被内化的。我的语言,我唯一能听到自己说,也是自己同意说的语言,其实是别人的语言[4]2-5。德里达认为,他是从他的单语状况中吸收空气[4]1。在此,这种状况实际上与德里达作为阿尔及利亚移民的身份有关,对他而言,法语实际上是一种外语,他旨在通过描述自己的单语状况诠释出单语主义本质上永远是由他者,确切地说,是由起源的异肢强加给少数族裔的。这种语言意识抹杀了少数族裔排斥的语言权力,是一种典型的暴力性语言意识。
周蕾(Rey Chow)将德里达所处的单语主义状况称为“语言的后殖民情景”(the postcolonial scene of language)”。德里达明显的逻辑上的或述行上的矛盾,即总是讲和书写法语,然而却声称这种语言不是他的,但对他来说也不是外语”[5]20。显然,这是德里达在语言上处于尴尬状况的外在表征形式,在周蕾看来,德里达身处单语状况的矛盾感实际上是在突出语言、所有权和归属感三者间的关系,其根源依然与其孩童时期在法属阿尔及利亚殖民地的生活经历相关。对于德里达而言,他讲法语和用法语进行书写并不是因为法语是一种传统的祖辈自然而然地传承给他的语言遗产,而是一种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殖民地强行施加给他的殖民遗产,最终演变成一种殖民主义的语言政策遗留给他的创伤感。在此意义上,德里达旨在通过对单语主义的论述阐释一种殖民化的种族主义现象。由此,德里达所言的“他者(the other)”指的是殖民者,相应地,“他者的单语主义”指的是殖民者以强制的形式施加给被殖民者的单语主义。周蕾认为,德里达所言的单语主义实质上是殖民者以被殖民者总是被认为是劣等的为背景,以压制性统治为基础,要求被殖民者遵守单一的语言,同时,他者的单语主义通过使被殖民者的本族语越来越边缘化和无用化的方式清除掉其潜在的竞争者,从而赋予其自身合法化的地位。[5]23-24因此,德里达的单语主义思想映射出一种以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语言政策为表征形式的殖民者对被殖民者的压制。由此,单语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所谓的“语言帝国主义(linguistic imperialism)”,是一种压制性民族关系的外在表现形式。实际上,从殖民地语境转换到民族国家内部,德里达的单语主义思想依然适用,只不过表征的不再是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关系,而是一个民族国家内部占主导地位的族裔和少数族裔之间的关系。同样,以单语主义为指导原则的语言政策势必造成一个国家内部的族裔、政治、文化和语言矛盾和冲突。
如果说德里达阐释的单语主义概念本质上是一种语言与人的身份之间的关系,即语言和族裔、以及集体或个人身份认同之间的相互影响,那么,在多语主义语言环境中,官方的语言政策对塑造个体,尤其是少数族群个体的文化身份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简单而言,单语主义关涉对少数族裔群体语言的排斥,多语主义则强调社会语言的多样性、身份认同、生命权力等。周蕾在谈论德里达单语主义遗产时,以较短的篇幅分析了单语主义与多语主义的内在关系。一方面,周蕾认同德里达赋予单语主义的贬义内涵,将单语主义视为排外主义的标志,是与多语主义相对的一种现象;另一方面,她认为,相对于单语主义思想缺乏文化多样性的特点,多语主义具有国际性和复杂性的特征。此外,对于周蕾而言,多语主义具有伦理内涵,体现为当今多语主义语言环境中各种语言之间正在出现不平等的趋势。
Yasemin Yildiz认为,在某特定的地区已经出现了“单语偏见(monolingual bias)”和“单语习性(monolingual habits)”,而且,单语主义并非只是一个简单的只有一种语言存在的量词性术语,其已经成为一种组织整个现代社会生活的关键性准则[6]2。但是,单语的排他性致使生活在单语环境中的人很容易在种族、文化和民族等方面保持严格的界限区分。由此,在后现代民族国家语言政策的制定和实践中,应该超越单语主义范式,构建起一种以多语主义为指导原则和制定依据的语言政策。实际上,后现代时期的全球化趋势客观上也要求民族国家的语言意识必须要从单语主义迈向多语主义。“多语主义是对传统国家意识的挑战,也是解决多民族国家语言问题的现代理念,更是当今全球化、多元文化时代的强烈要求。”[7]7
20世纪90年以来,越来越多的西方语言学家开始关注多语主义,从多个角度对多语主义做了定义。 例如,对于 Jan Blommaert,Sirpa Leppänen和Massimiliano Spotti而言,多语主义属于社会语言学的范畴,表征为语言和社会层面丰富的文化多样性[8];John Edwards将多语主义视为实际存在的生活现象,就最简单层面而言,多语主义是一种源自于跨越言语社区的交流所必需的现实生活状况[9];在Édouard Glissant看来,多语主义不仅指的是具有讲几种语言的能力,而且还是接受和理解我们邻居的语言的强烈愿望,以及正视西方对语言持续施加的侵蚀力。[10]
根据以上分析,单语主义和多语主义具有深刻的政治含义,对少数或弱势族裔身份的认同与建构、语言权利、语言教育具有重要影响。以单语主义和多语主义思想作为国家语言政策制定的参照,可以揭示出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出现民族矛盾、冲突的背景下,少数族裔语言的多样性应该如何应对强势的单语主义思想的冲击,政府在制定语言政策时,应该如何维护少数族裔的语言权利、发展少数族裔语言、加强少数族裔的语言教育等。
三、单语/多语主义视角下语言政策类型
在论述族裔与语言政策的关系时,Teresa L.McCarty将语言政策视为社会文化的产物,以语言调控交往、协商、生产方式中的权力关系,族裔间复杂的权力关系对语言政策的本质、语言实践、身份、意识形态等具有深刻的影响。[11]2-8实际上,无论是德里达对单语主义思想的阐释,还是周蕾强调单语主义是造成殖民国家中各种语言之间出现不平等趋势的主要因素,都表明单语主义是语言霸权的具体表征形式。秉承单语主义语言政策传统的国家则是形成一种单一语言的共同体,按照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分析,“尽管今天几乎所有自认的民族——与民族国家——都拥有‘民族的印刷语言’,但是却有很多民族使用同一语言,并且,在其他一些民族中只有一小部分人在会话或书面上‘使用’民族的语言”[12]54。显然,单语主义语言政策是现代民族国家理论的产物,是国家意识形态对语言的操纵,对于少数族裔语言而言,以单语主义为导向的语言政策本质上就是安德森所说的“怀有敌意的群众性语言民族主义”[12]51。安德森含蓄地指出,当代民族国家的具体形态与单语主义所涵盖的确定范围绝不相符,这就要求当代民族国家在语言政策的制定过程中,要自觉地超越民族主义,在立足民族语言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到少数族裔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切不可像安德森列举的那样,“为了要强化说土耳其语的土耳其的民族意识,阿塔土克‘凯末尔’不惜以一个更广泛的同教认同为代价,强制实施了强迫式的罗马字拼音”[12]54,这种做法在造成语言冲突的基础上,最终演变为民族国家的分裂。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如何避免单语主义语言政策对民族国家的和谐稳定发展造成负面影响逐渐成为语言学家关注的新课题,相应地,从单语/多语主义视角介入对语言政策制定的研究也为社会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大体而言,根据具体的研究路径,单语/多语主义视角的语言政策制定研究可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从族裔政治视角探究多语主义语境中的语言政策;第二类从社会文化层面关注多语性国家中影响语言政策制定的因素;第三类批判性地剖析了单语主义语言政策对弱势族裔的意识形态和国家认同的影响。
Jan Blommaert,Sirpa Leppänen 和 Massimiliano Spotti指出,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社会语言学家就宣称,多语主义是一种积极的社会现象,提倡种族和语言之间的平等性[8]1。因此,多语主义与种族平等观念是相伴相生的。多语主义本身更多地是针对社会群体而言的,单语主义语言政策造成的对少数族裔语言权力的损害只能通过多语主义加以补偿和弥合。高度现代化的政府治理必然包括多语主义语言政策,在制定语言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到当代社会中频繁出现的民族的糅杂性、多样性和混合性特点,使语言政策体现为“融合性政策”,表征为以平等意识为特点的族裔关系。很大程度上,从平等的族裔政治视角介入语言政策制定是一种解决多民族、多语言国家语言问题和族裔冲突的现代国家治理理念。对此,Kathryn Anne Davis分析了在卢森堡多语共存的背景中,政府制定语言政策时,首先考虑各个族裔的人民对自己族群语言的维护和诉求[13];Michael Herriman和Barbara Burnaby解析了在六个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里,弱势族裔为了在教育和社会服务中争取语言权利进行的斗争,以及对这些国家语言政策的影响。[14]
单语主义本身是与多元社会文化现实相冲突的,在单语主义语言政策的共同体中,族裔之间的语言冲突,在体现为福柯所言的争夺“权力话语”的表层冲突之外,更多地隐含着一种深层次的社会文化冲突。多语主义则是与多元文化社会现实相适应的,处于施行多语主义政策共同体中的各个族裔都具有文化共同感。合理的语言政策是个体或族群获得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的重要依据。德里达虽然用法语言说和写作,但是他始终无法体验到法语文化的归属感,原因就在于法国在殖民地阿尔及利亚推行强制性的以法语作为单语主义的语言政策。语言的多样性体现为文化的多元性,单语主义语言政策在造成语言冲突的同时,势必会扼杀文化的多元性。Adrian Blackledge认为,“语言意识形态是在话语、新闻媒介、政治、民族归属、广告、学术文本和大众文化中产生的”[15]44。Jan Blommaert认为多语主义属于一种语言意识形态,是特定符号资源的复合体[16]6。法国哲学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认为,语言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资本。在现实生活中,多种社会因素会影响到语言的文化资本内涵,比如,宗教、经济、政治等。因此,归属于语言意识形态的多语主义与社会文化有多重关联,以其为依据的语言政策必须要突出语言的文化资本属性,而多语主义语言政策则是对语言的文化资本属性、多元社会、尤其是多元文化主义维护的基础。John Edwards指出,多语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大体上是重合的,而且在政策层面上,对多语主义的认可就包括了对多元文化主义的认可[9]175。例如,Richard B.Baldauf Jr.与Robert B.Kaplan解读了墨西哥等拉美国家在语言多样性的历史与政治背景中,媒体和宗教等文化因素对语言政策的制定以及族群身份建构的影响。[17]
语言是与族裔身份紧密相连的,如上文所言,德里达在单语主义中的状况表明,单语主义语言政策本质上是对少数族裔语言权利的侵犯和剥夺。按照民族语言学的观点,在传统的民族国家中,整个民族国家属于一个民族语言共同体,而这样的共同体是由单一的语言和文化所界定的。在这样的共同体中,政府在语言治理中必然会选择单语主义为原则的语言政策,由此会造成“主导民族语言和少数族裔语言”的“中心语边缘”对立关系,其后隐含着“主导民族和少数族裔”之间的对立关系。John Edwards指出,少数族裔的身份认同由族群和民族主义两个因素构成,而少数族裔面临的危机之一是其语言正在被同化。[9]125-133因此,从族群和民族主义层面应对少数族裔语言危机就要求认同少数族裔的语言权,而制定多语主义语言政策是要尊重和保护少数族群语言,摆脱语言权力政治中的主导地位的族群语言的霸权地位,构建起一种新的、平等的语言生态环境的基础。例如,Liesbeth Minnaard和Till Dembeck通过对西欧国家语言政策的分析指出,在大多数施行单语主义政策的西欧国家里,弱势族裔对国家民族性的抵制中隐含着单语主义语言政策的挑战,寄托着一种对多语主义语言氛围的憧憬。[18]
四、单语/多语主义视角下语言政策的形式和演变
E.Annamalai从多语主义视角对语言政策进行反思时指出,国家之间的差异在于多语主义的性质。他将多语主义分为两个范畴:递减的多语主义(subtractive multilingualism)和增添的多语主义(additive multilingualism)。对他而言,在递减的多语主义中,存在于或进入一个国家居民中的多种语言会被其主导性语言所取代,但是,新的语言会进入,被取代的语言也可能会复活;增添的多语主义不仅指的是语言数量的增加,还意味着增添的语言能够给现存的语言系统增添一系列新的节点。[19]113-114在具体分析中,Annamalai从民族国家、语言政策的构成、客观性和目标、治理的局限性、公众的语言选择、语言的价值、以及语言政策的决策权等方面阐释了多语主义和语言政策关系。实际上,现代国家语言政策的制定和演变正是按照Annamalai分析的这几个方面逐渐超越单语主义,迈向多语主义语言政策。
李宇明教授认为,“传统国家大都秉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语言’的观念,语言规划的理念基本上是单语主义的”[7]7。按照他的分析,这种以单语主义为理念的语言政策与对“民族国家”认识和理解有密切的关系,体现出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概念,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单语主义是一种语言层面上的政治共同体,是构建民族国家的重要因素之一。法国是第一个秉持“民族国家”思想的国家,其一贯坚持社会、文化、语言的统一性理念,因此,以单语主义为基础的语言政策成为法国政府语言治理的不二选择。根据李宇明教授的考证和总结,早在1539年,法国政府就通过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法语作为全国性语言的至高无上的地位。直到400多年后的1994年,为确保法语作为单一语言的地位,“法国议会通过了《杜邦法》(Toubon Act),重申宪法关于“法语是法兰西共和国的语言”的规定,明确法语应用的规范标准和法律制度”[7]8。因此,毫不奇怪,作为从殖民地移居到宗主国的德里达无法适应法国的单语主义语言环境。
除了法国之外,欧洲的德国、英国、俄罗斯等传统的民族国家也都坚持秉承单语主义语言政策。对于这些国家而言,语言和民族国家是一体的,其实施的单语主义语言政策反映出政府在生命治理方面以一种单一或统一的语言意识将各个族裔捆绑在一起,将法语、德语、英语、俄语政治化,把语言上升到民族身份认同的高度,其背后却隐含着对少数族裔语言的忽视。此外,李宇明教授将现代多语民族国家的单语主义语言意识和语言政策分为两种类型:多语制传统国家中的单语主义倾向和二战后新独立的多语国家的单语主义语言政策。对于第一种类型,他认为,单语主义语言意识,“即使是在实行多语制(包括双语制)的国家中,也仍然具有明显的单语主义倾向”[7]8。这种情况主要出现在比利时、瑞士、意大利等多语并存的国家,在这些国家,语言呈现为多样性的存在方式,这主要体现在国家内部以语言为依据,被划分为多个语区或语州,在每个语区或语州实施单语主义语言政策。因此,尽管表面上这些国家表现为多语并存的现象。但是,这种多语现象实际上属于Annamalai阐释的“递减的多语主义”,因为在这些州内占主导地位族裔的语言才是该州的官方语言,其他族裔的语言逐渐演变为法国哲学家德勒兹(Gilles Deleuze)所言的“弱势语言(minor language)”。例如,比利时由多个族裔构成,每个族裔都有属于自己的语言,这就造成比利时的语言呈现为多语并存的语言景观。但是,每个地区的官方语言都是该区主导性族裔的语言,因此,尽管比利时奉行多语主义语言政策,然而,各个区自身依然坚持单语语言政策,成为顽固的单语区,地区单语化自然演变为政党单语化。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单语主义语言政策是造成比利时政治冲突和危机的罪魁祸首。至于第二种类型,李明宇教授指出,20世纪六七十年代摆脱殖民地身份,亚非新独立的一些国家,“在这些国家的建国理念中,在语言规划的意识中,底色也仍然是单语主义的,是新形势下的旧观念”[7]9。例如,作为拥有54个民族的越南,独立后将占全国人口86%的京族讲的越南语定为越南的官方语,少数民族的语言完全被政府忽略掉了[7]9。
如上文分析的那样,单语主义关涉的是对少数族群语言的排斥、多语主义强调的是社会语言的多样性、身份认同、生命权力。虽然单语主义语言政策对增强各个民族的民族国家观念、建构统一的国家身份认同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却会造成各个民族之间产生文化冲突等负面问题,而多语主义语言政策对少数族裔语言应用、语言教育、语言维护、语言传承等具有积极的促进意义。因此,以多语主义为理论依据和参照制定民族国家的语言政策是保障少数族裔语言权利和族裔平等的重要基石。多语主义在语言政策的规划和制定中表现为语言的多元性或语言的多样性,即各个族裔的语言具有平等地位,强势族裔的语言不会以“暴力”的形式压制弱势族裔的语言。当前,我国对地方语言和少数民族语言实施了语言保护工程,尤其是在民族语言政策方面采用了“主体性”和“多样性”兼顾的语言政策,即这种语言政策兼顾了单语主义和多语主义的优点,坚持以汉语为主体可以增强各个民族的国家认同和国家意识感,同时,兼顾“多样性”原则能够保护少数民族的语言权利和民族地位,这种语言政策充分体现出Annamalai所言的“增添的多语主义”的特点。实际上,文革期间,我国的语言政策、语言实践和语言教育等方面出现了干扰和破坏现象,某种程度上违背了法律规定的“主体多样统一”的民族语言政策,表征出汉语至上的单语主义倾向,少数民族语言的教学、出版、广播、翻译等事业遭到重创,这种现象在某种意义上是德里达所言的单语主义思想对民族语言政策的影响,影响了少数民族的语言传承、民族识别和民族身份的认同。文革后,政府对这种现象进行了纠正,回归到“主体多样统一”的原则上。
正视其他族裔语言的意义,以及如何应对强势族裔语言对弱势族裔语言明显或潜在的语言暴力是当前很多国家在语言政策制定中首要考虑的问题。单语主义语言政策造成的民族和社会冲突促使很多民族、多语言国家不得不调整语言政策,从单语主义意识形态转变为多语主义意识形态。随着经济、文化、信息、语言、人口的全球化流动频率加快,同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欧盟等国际组织的提倡和推动下,保护和实践语言的多样性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以此,在语言政策制定中由单语主义语言意识迈向多语主义语言意识成为当代很多国家达成共识的语言治理策略,尊重和保护少数族裔的语言权力成为语言政策制定的核心要务。英国、法国、德国等传统的单语主义意识形态国家也开始重视新移民和少数族裔的语言权力,印度等多民族、多语言国家也在国家语言政策的调整中,从单语主义迈向多语主义。
五、结语
在国家治理中,语言政治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语言政策制定中的语言利益直接关涉到各个族裔能否和谐共存。这就要求在具体语言政策的制定中要合理、有效地利用国家治理技艺,对个体或族裔共同体的言语进行合理的治理或管控,以便使各种语言能够和谐共存,以此建构起一套良好、和谐的语际关系。因此,在国家语言治理层面,单语主义和多语主义理论具有重要指导和参照意义。单语主义语言政策能够促进少数族裔民众增强国家认同和国家意识,同时,多语主义语言政策对少数族裔民众维护语言传承、民族识别和民族身份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多语主义隐含的语言和族裔的平等性、多样性最终使其成为民族国家制定语言政策的主导和主流思想。单语主义意识形态在历史上长期占据着民族国家语言政策制定的主导思想,迄今已经流行了数百年,但是,当前全球化趋势不断深入,多元文化主义成为时代的主导潮流,这在客观上要求国家在语言规划治理中必须要放弃单语主义,以多语主义思想为指导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