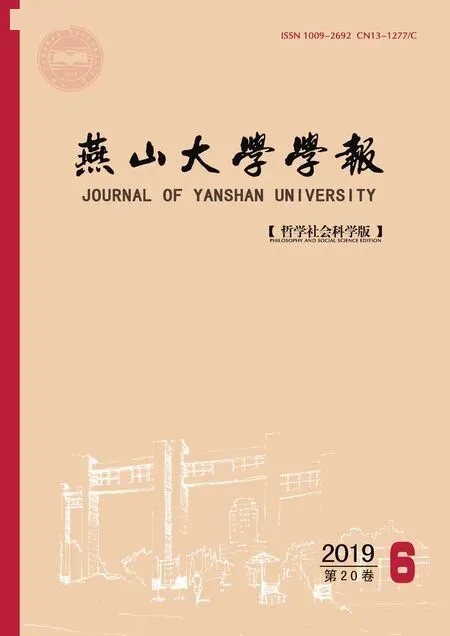比较哲学视域下古典汉语特征及对典籍英译的思考
——美国汉学家任博克教授访谈录
2019-02-24郭晨
郭 晨
(燕山大学外国语学院,河北秦皇岛066004)
任博克(Brook A.Ziporyn)教授(1964—),当代美国知名哲学与宗教学家、汉学家、《庄子》译者。1996年在密歇根大学获中国哲学博士学位。他曾先后任职于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美国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西北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2012年,他接替《西游记》译者余国藩(Anthony C.Yu)教授,成为芝加哥大学神学院中国哲学与宗教、中西哲学比较方向终身教授。主要研究道家思想、天台宗思想、无神论、中西哲学与宗教比较、典籍英译等。2009年,他的《庄子》选译本一经出版便广为好评,其“以中释中”的翻译路径也得到美国汉学研究界的广泛认同。目前,他应美国哈克特出版社之邀,正着手《庄子》全译本的翻译工作。2018年12月,笔者借参加芝加哥大学举办的汉学会议之机,通过英文对任博克教授进行了学术专访,现整理翻译,以飨读者。
一
郭晨(以下简称“郭”):尊敬的任博克教授,您不仅在中国古代哲学与宗教研究界声名斐然,也是一名成功的典籍译者。根据您的中国学研究及翻译体验,典籍英译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任博克教授(以下简称“任”):典籍译者必须了解古典时期的汉语特征及其对人们思维方式的影响,才能成功地进行翻译实践,这点在典籍英译中尤为重要。
郭:您曾在多个场合指出中国先秦时期的哲学典籍展现出与西方哲学迥异的世界观体系。您强调“古典时期”的汉语特征是否基于这个原因?
任:是的。首先,我认为人类历史存在两种发展成熟、能够自我维持的书面传统:印欧语和汉语。汉语有古汉语和现代汉语之分。古汉语根据语法结构,可以粗略分为佛教传入前的“古典汉语”和受佛经汉译影响后的“中古汉语”。中国先秦时期的哲学典籍塑造了中国古代哲学的主流形态,在哲学史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这些典籍属于古典汉语的范畴。
19世纪时,西方开始关注印度哲学与宗教,发现它和西方哲学宗教极为类似,都得出了超验、永恒、形而上的本体。尼采认为这背后的原因是:印度语和西方语言拥有类似的语法结构,它们都非常重视主语。西方无法摆脱语法的控制,也就无法摆脱上帝的影子。“上帝”的观念成为印欧语法的副产品。无论主体单向控制客体、客体单向控制主体,都是重视主语的产物,都具有目的论的特征。当然,现代科技的发展削弱了客体单向的控制能力,但仍无法脱离这种精神需求。这是西方以“有为”为终极的宇宙观的重要来源,也是西方强调“表象”与“事实”之间不可逆关系的重要原因。
这和早期中国思想的情境主义、去中心主义、对“此世”的关注不同。尽管中国拥有世界最早的文化传统,对人与自然也有丰富多样的思考,但中国的宇宙观以“无为”为终极。最早期的中国没有出现创世神话,对探讨世界起源也缺乏过多热情。当然,《道德经》和《太一生水》等文本确实探讨了世界本源,但《尚书》《诗经》《论语》等都不涉及这个话题。即便之后创世神话最终出现,也不过是将已存的整体划分为天、地两极,没有人质疑这种“已存的未分整体”从何而来。
郭:所以说,英文中对大写的“我”(“I”)的强调实质体现了目的论,是一种“有为”的世界观。古典汉语中经常省略主语,这也体现了“无为”的宇宙观。
任:是的。印欧语法结构导致哲学家深信单向的、因果的线性思维的正确性,由此导致“万物皆有目的”的创世论和“万物皆物质”的原子论。这两个理论看似相悖、实则殊途同归。古典汉语不区分单数、复数,过去、现在、将来,主语、宾语,定冠词、不定冠词与无冠词,不区分抽象名词和具体名词,也就不会产生类似理论。当然,汉语承认一物是另一物出现的基础,承认物与物之间的联系,讨论了物体的“在场”(“有”)和“缺席”(“无”),也有表示本末关系的概念,却没有明确的“存在”和“不存在”、“假象”和“实体”、“主动”和“被动”的二分。
可以说中西方对“一”和“多”的关系有完全不同的见解。古典汉语辨识物体时常用“取”这个字。“取”是从整体挑出一部分,不是凭空创造这个物体。也就是说,先有一个整体,再从这个整体辨别出个体。西方哲学不存在“取”这个动作。我们认为先存在一个个体,在此基础上不断添加更多的东西,使之形成一个整体。
举个简单的例子,《庄子》中的“其成也,毀也”。中文很好理解,若直译为英文的“Completion is destruction”(“成是毁”),多数西方人会无法理解:“completion”(“成”)就是 “completion”(“成”),“destruction”(“毁”)就是“destruction”(“毁”),两个不一样的观念不可能出现“is”(对等)的关系。这种直译大概只有如斯宾诺莎①等极少数的西方哲学家才能理解。斯宾诺莎认为世界只存在一种实体,你、我、我们所有的人和所有的空间都属于这个实体。唐君毅②将这个实体翻译为“太一”,中国人觉得很好理解。但是西方人无法接受他的观点:你、我、他物都是分割开的、不同的物体,不可能是一个实体。因此,斯宾诺莎在中国的接受度也就比西方高。由此观之,译者翻译时要注重这种整体和部分的关系:个体事物是先从整体中分割出的,任何个体事物的形成都是整体的毁灭,也是其他事物出现的可能的毁灭。我的翻译是“Their completion is destruction”(“他/她/它们的成是毁”),西方读者也更能接受些。
郭:安乐哲③教授曾就“一多关系”提出“一多不分”的中国模式:中国的“一”是“一中有多”、“多中有一”。他也进一步指出了中西方词语在翻译中的不对等性,您是否持有相同的看法?
任:“一多不分”实际是唐君毅首先提出的观点,很多西方汉学家都接受了。安乐哲对这个观点进行了强调,但好像没有解释背后的原因。我是从中文的语法结构和语言特征分析翻译的困境,对“一多不分”也进行了语言学源头的解释。从哲学典籍英译的特定语境而言,我非常赞同安乐哲所说的中西词语的不对等性。西方已经存在一套哲学传统,每个哲学术语都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一旦用来翻译中国哲学典籍中的相关观念,容易给西方读者造成一种错觉,认为中西方哲学探讨的是相同的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我不认为语言之间存在完全、彻底的不可译。中西方任何内容都可以通过不同的语言表达出来,只是表达的难易程度不同,让听众或读者接受的程度不同。某些内容在某种语言中比较难表达,需要译者花大量时间寻求处理办法。译者翻译中国典籍,如果遇到很难用目的语翻译的情况,需要先审视这些观念在中国哲学传统脉络中的各种语境,确定是哪些语境导致它们比较难译。然后确定译介的目标群体,再针对性地处理。譬如,宋明理学的“理一分殊”很难翻译,但这个命题很符合汉语深层结构中存有论的直觉。如果译介的目标读者是海外汉学家或者对汉语有一定了解的人,我们翻译时不用做过多解释。但如果要翻译给普通读者,我们可能要通过副文本详细说明。
郭:美国语言学家沃尔夫(Benjamin Whorf)认为语言决定了思维,语言结构决定思维的结构。您的解释是否也受到了语言决定论的影响?
任:我本人坚决反对语言决定论。语言决定论是一种文化本质论,或者说种族本质论。它常被用于从语言的角度强调本族文化、贬低他者文化,或被当作以自我文化为中心,不接触他者文化的借口。我不认为有所谓“民族性”这种迷信的东西,也不认为语言有本质的限制。我认为印欧语言和中文存在显著差异。这不是说有些意思不能被表达,而是表达得容不容易、复杂不复杂,能不能沟通、能不能持久的问题。不同的语言结构的确比较容易展现一些特定的意义,体现该语言使用人群看待事物的方式。了解源语言和目标语言之间不同的语言结构、语法和修辞的特征后,也能让译者和阐释者在两种语言间更容易地进行转换。
我在反驳语言决定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关于语言的假设:任何语言的语法强调的内容最终都和本民族对本体论的理解相关。只有了解了目的语国家的本体论,才能更好地理解目的语国的语言内涵。这不是文化本质主义,不是种族本质主义,甚至不是语言本质主义,也不是某种新沃尔夫语言决定论。这是一种常识性的趋向统计,用于分析语言创造意义的过程。它能够跨越种族、地理和历史,分析所有使用特定语言的思维方式并进行哲学写作的人。这种对语言结构、语法、修辞的假设,能更直观、更容易地解释目标语中的观念。这不是说有些观念不能用某种语言表达,也不是说如果语言中不存在某种意思,就不能对这种意思进行传达。只是说从语法的角度,这种语言表达有些意思比较吃力,需要花点功夫。
郭:印度佛教传入中国、梵语与汉语在翻译中交融前,早期中国没有出现探讨语言如何运作、探究通用语法规则的著作。那么,您是如何从古典汉语语法的角度建立这种语言的假设?
任:通常来说,语言的作用方式、单位和结构的特殊用法确实存在一些规律。但语法教科书不能用源于非汉语的语言学标准,同化汉语语法。因为汉语并不按照规定的方式(事先出现的更高级的权威)运作,而是以先例法、普通法的方式存在:确定权威的特定用法,需要找到同级别大量词或短语以同样方式使用和理解的先例。通过这些用法及其语境的三角测量,能概括出特定的语法倾向,但也仅是倾向。当然,有些语法特例能让某个观点在本地语境中能被理解,这种可理解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语境,也取决于构成语法规则的先例语境。
郭:所以您认为古典汉语重要的总体特征是以先例法、普通法出现的存在方式?您在翻译实践中还注意到哪些比较重要的古典汉语特征?您又是如何处理的?
任:是的。我在翻译中还发现汉语最明显的细节特征则是没有时态的区分,从语法的角度而言甚至连“事实”和“可能”也不分。只能通过添加“过去”“昨天”“明天”或“彗星出现的那一年”等信息表示过去、现在或将来,句法结构和篇章结构不会发生任何变化。由此可以预期中国早期哲学家(统计学意义的多数)虽然也有时间概念,却不把时态当作存有论中不可或缺的因素。中国古代的“存在”不需要时间性也是实实在在的“存在”。其次,同一个字或词可以作名词、动词、形容词或副词,可以表示动作、对象或质量,这取决于语境和作者的灵活性。如“美”可以表示“美”这个抽象的概念,也可以表示“美的”“美化”“被看作美”“美丽的事物”“美丽的人”等。但在西方哲学传统中,“beauty”(美),特别是大写后的“Beauty”只能表示抽象的“美”的观念。所以也可以推测中国早期哲学家不把抽象与具体、普遍与个别当作存有论的终极范畴。这就又牵涉“一多不分”的问题,“一”与“多”不是存有论的终极范畴。举一个很有趣的例子:“God exists”古文可以说“神在”。但英语明显强调了那一个特定的神,中文里可以是一个神,也可以是多个神。我们把中文的“神在”翻译成英语时,需要进行这个单数和复数的选择。译者选择时要注意文本的整体脉络,否则会给西方读者造成极大的文化误导。
因此,如何分析句子成了阅读中国古典文本时面临的最常见挑战。一个汉字用不同的方式和其他字捆绑时,不仅整个句子、句中每个单独的字可能都会出现完全不同的含义。一个字可以被理解为动词,也可以被理解为名词。古典汉语中,句子的其余部分决定了一个字在句中的最终意思,一个句子的最终意思又由周围的句子决定,以此类推、循环往复,最终回到整个现有的文献,从中得出语法规则。这个规则不过是意义不确定性的延伸。语言连贯了经验、用于沟通,所以它也是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共存。中文意义依附于上下文,不依附于句子的词语形态。随着更多上下文的出现,我们总能找到一个翻译的方法。这是汉学家公认的汉语的总特征,在翻译中特别明显。这和西方从语法、从二元进行分辨的角度获得句子的意义完全不同。
以《庄子》为例,若我不确定某词的含义,不知道该怎么翻译,就会先去阅读这个词的上下文,再阅读这一章,再阅读这本书,再阅读如《论语》《孟子》《道德经》《墨子》等同时代或更早的文献,寻找类似的用法,获得更好的理解。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诗歌。西方人阅读中国诗歌会觉得非常震撼。只有在需要阅读完下一行,确定了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之后,才可能理解第一行的意义。这种体验不仅限于诗歌,中国的古典哲学文本亦会如此。文本的意义是通过背景脉络的回顾间接构成的。这意味读者可能在阅读过程中无法理解正在阅读的句子,只能等回顾背景和脉络时突然发现实际的内涵。由此而言,初次阅读时句子意义的连贯与否,意思的通顺与否,都不是太大的问题。第一次阅读时得出的语句的含义可能并不准确,还会受到后续句子的推翻。
郭:英语世界对“道”的多种翻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您对“道”的翻译有何看法?
任:“道”本身不分一和多。我的学生有人不翻译“道”,使用小写的拼音“dao”,也有人用“adao”“thedao”“somedao” “daos”“thedaos”。 这应该是受到陈汉生④比较大的影响。我也不反对这想法,但道家文献也确实出现了不同于一般“道”的“道”,如“不道之道”“道可道,非常道”或所谓的“大道”。我将这类特殊的“道”翻译成“The Course”。 英文中“course”比“way”多了“规范”和“行动”的内涵。“道”不只是所行的道路,也是行的过程,如《道德经》的“周行而不殆”。
二
郭:您把中国古代文本分为了古典文本和中古文本。那么,您能举例谈谈区分这两者对典籍英译有什么影响吗?
任:以典籍中“所+动词”结构的翻译为例,现代汉语中“能见”“所见”这种用法受到汉译佛教典籍的影响,属于翻译中的一个语法创造。“所+动词”结构在古典时期的文本中非常常见,其中的“所”很多时候指代“处所”,如《道德经》第62章的“道者万物之奥。善人之宝,不善人之所保”。马王堆甲本写得更清楚:“善人之保也,不善人之所保也。”只有理解为“处所”,“之保”和“之所保”才会出现差别。《庄子》中“万物之所造”不是“万物造出的东西”,而是“万物从那里造出”(万物之“能”造)。但也有比较容易忽略的例子,像“万物之所系,一化之所待”。很多人用现代汉语的理解思路翻译为“What all things are tied to,what all transformation depends upon”(“万物所系之物,万化所待之物”)。但这句的意思也可能是“What ties itself to all things,what depends upon all transformation”(“连于万物之物,待于万化之物”)。如《道德经》的“道法自然”,道没有指导万物,而是随顺万物。我翻译《庄子》选译本时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现在重译《庄子》时就进行了相应更改。译者在翻译古典时期的文本时,这些都是需要重视的问题。
郭:2006年,您的《庄子》的英文选译本出版即受到广泛好评,被誉为“以中释中”的典范,也被多本学术著作、多篇学术论文作为《庄子》原文的英文底本援引。您的译本整理、翻译了大量的中国历代传统评注,这在《庄子》英译史中尚属首次。这是否是您“以中释中”最显著的表现?
任:我认为是。与其他译者相比,我更重视对中国传统注释的翻译。中国古代哲学典籍有其特殊性。因种种原因我们无法看到《庄子》本文的原貌,仅能通过郭象的编注本探究《庄子》意涵。因此,《庄子》历代传统注解属于《庄子》的母体文化,是《庄子》文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我选择翻译了很多传统注释,希望通过翻译体现《庄子》厚重的研究传统,让读者从多个维度感受《庄子》哲思。
同时,历史注疏中的《庄子》意蕴是多元的,这样也能让历代传统注释者发出自己的声音。我阅读《庄子纂笺》《庄子集解》《庄子诠诂》《庄子翼》等时,总会被书中引用的一些注释深深地吸引,由此深挖这些原本陌生的评注者的思想,得到了很多乐趣。我希望西方读者也能从我的译本获得这种独特的体验。但中国的庄学研究传统非常厚重,历代注解数量巨大,我只能有选择地翻译。我尽量选择从道家哲学出发、紧扣原文本、彼此观点迥异的注解,希望展现传统中一些不同的声音,激发读者的进一步思考。
郭:目前,您正在翻译《庄子》的全译本,不知您现在的进度如何?除了选译和全译,这两个译本有哪些不同之处?
任:全译本的翻译工作已经完成,预计2019年7月交稿。全译本不仅翻译了选译本中遗漏的大部分文本,也对之前的翻译做了一些比较重要的修改。自选译本出版后,我开始系统地在课程中教授《庄子》,也和国内外学者进行了愉快的讨论,对文本产生了新的理解。同时,近年来,用于研究中国古典文本的数字工具有了飞速发展。通过线上工具,我可以即时对比大量数据,也可以获得很多以前没有接触到的资源,收获了很多新的观点。不过,我对《庄子》哲学的总体认识多年来并未改变,两个译本的主体思想没有太大的改动,我仍然认为视角主义是《庄子》哲学的重中之重。
为了方便读者理解,我在两个译本最后都附上了术语表,对原文本一些重要观念或者有特殊用法的关键词语进行了说明和解释。但在全译本中,我进一步扩充了术语表,希望读者能够有更多的材料把握一些意义相关或存在紧密联系的术语。同时,我也极大地扩充了脚注、尾注中的解释性材料,为读者详细解释了我的翻译背景和哲学思考,为西方读者解释了源语言中相关的语法结构,也为中国读者指出了目标语中的相关修辞含义及暗示。我不认为自己的翻译选择都是正确的,但我希望读者能够至少一目了然地重建我的翻译过程,能够意识到我在翻译时遵循的是原文本哪一个模棱两可的可能性。
郭:您的选译本全译了《庄子》内篇,选译了外、杂篇的部分段落。您在译本的“前言”部分明确指出,您仅选择翻译了外、杂篇中与内篇思想连贯、一致的段落。那么,您的全译本如何解决《庄子》原文本中思想的不连贯性?
任:这是个很好的问题。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我承认《庄子》解读的多种可能性。也就是说,《庄子》整个33章也可以被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呈现出复杂的多种学派思想。我翻译选译本时,从思想连贯性的角度展现了一个和《庄子》内篇一以贯之的思想体现。但我在全译本中尝试从语言、历史、风格和主题等方面,构建一个既具有连贯性、又显然不同的故事。读者能在译本中遇到逻辑严谨但也无比诗意的哲学家、神秘主义者、怀疑论者、不可知论者、相对主义者、存在主义者、宿命论者、原始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等。由此,《庄子》成为了一本“选集”,反映了中国古代道家学派的某些时期的特征及道家思想的多样性。书中每位哲学家,不论观点与庄子哲学是否吻合,都形象丰满表达。激进的政治批评家和保守的调解主义者都拥有发言权,没有失去扩大影响的机会,也为读者提供了更多有趣的思路。我们或许可以将《庄子》文本视为中国延续了千百年的注疏传统之始。一些哲学家阅读《庄子》的内篇后,在外、杂篇的相关段落中传达了他们对庄子哲学的理解,随后又出现一批哲学家对这些读者反应作出回应。这种阅读方式能让读者体会到思想对话的乐趣,也能进一步激发读者的思考。我认为这两个译本的不同处理方式,为读者提供了两种不同的侧重和思路。
郭:非常期待您的《庄子》全译本。经过多年的《庄子》翻译实践,您对典籍翻译这个活动有哪些新的想法?
任:很多人都承认翻译不是科学,而是艺术,却很少有人指出翻译如同建筑,是一门需要大量精确知识和准确信息的艺术。创造一个既美观又人性化的建筑,需要的不仅仅是精确度。同样,一个好的翻译也需要有足够的美学构图决策,围绕一些精确的子结构去贴合原文本。翻译中国的古典文本尤为如此——我们需要在精确性和诗意性之间进行平衡。哲学精确性是建筑的基本框架,译者应该在保持哲学精确性的基础之上探求诗意。翻译古代文本时过于保持源语言的措辞和结构,可能会导致目标语难以理解,如葛瑞汉⑤的《庄子》翻译;过于追求语言的诗意可能会掩盖原文的哲思、表达的独特、论证的连贯,如华兹生⑥的《庄子》翻译。但哲学性和文学性之间、保持字面义和展现诗意性之间并不排斥。
郭:您作为一名成功的译者,对中国国内的翻译家有什么其他建议?
任:我们一定要尊重中国文字,尊重中国特殊的宝贵文化,尽量避免文化同化。我们也要避免所谓的“意义合理化”。合理化实质就是同化,让中国文化符合西方语言的逻辑。我们在翻译中也不能操之过急,一定要慢慢来。翻译是很微妙的艺术,不能动手太快。有时候需要把翻完的译稿放在一旁,一个月以后再返回来修改,可能会产生不同的认识。
郭:非常感谢!我相信中国的典籍英译学者能从您的实践经验中获得有益的借鉴,进一步完成“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战略。
注释:
① 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1632—1677):荷兰知名哲学家,著名的泛神论者,西方近代三大理性主义者之一。他认为并非神创造了自然,自然才是神本身。他的学说极大地影响了西方唯物主义的发展。
② 唐君毅(1909—1978):中国著名哲学家,新儒家思想的杰出代表。1949年时,他与钱穆等在香港创办了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之一新亚书院。他的代表作之一《中国哲学原论》从观念史的角度将“理”和“心”视为中国哲学之端,梳理了“理”“心”“名辩”“致知格物”“道”“太极”“命”等核心观念,从新语境诠释了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中心议题,在中国哲学史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③ 安乐哲(Roger Ames,1947—):加拿大著名哲学家、汉学家,现为美国籍。早年他与郝大维(David Hall)合著的中西方比较哲学书籍使其在学界声名鹊起。他也翻译《论语》《道德经》《中庸》《孙子兵法》等。他主张中西方观念的不对等性。为避免与西方哲学中相关观念混淆,他对很多中国古代哲学核心词进行了创造性的翻译,引起了国内外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④ 陈汉生(Chad Hansen,1942—):美国著名哲学家、汉学家。他从语言哲学的角度研究中国先秦哲学,构建了以“道”为中心的中国哲学语言理论体系,代表作是《中国古代的语言和逻辑》(The Language and Logic in Ancient China)与《中国思想的道家理论》(A Daoist Theory of Chinese Thought)。
⑤ 葛瑞汉(A.C.Graham,1919—1991):英国著名哲学家、汉学家。他的《后期墨家的逻辑、伦理学与科学》《论道者》等著作及《庄子:内篇及其他作品》等译作,在海外汉学界影响深远。他从哲学的角度翻译、阐释《庄子》文本,激发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庄子》翻译史中的哲学转向。
⑥ 华兹生(Burton Watson,1925—2017):美国著名汉学家、翻译家。他翻译了《论语》《道德经》《庄子》《史记》及大量的古代诗歌。他的翻译更注重文学性,文辞优美,在西方读者甚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