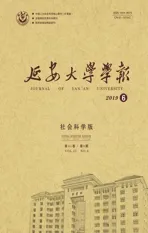从冲突到合作
——印(尼)马对抗和东盟成立之间的关系分析
2019-02-24罗永忠
罗永忠
(石家庄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00)
印(尼)马对抗和东盟成立是冷战时期东南亚的重大事件,这两个事件有无内在关系?传统的观点是,印(尼)马对抗和东盟成立是两个孤立的事件,二者之间没有关系。但是,笔者通过对材料的梳理,发现二者之间有着内在联系。本文就是探究印(尼)马对抗和东盟成立之间的内在逻辑。
一、马来西亚计划的提出及各方反应
二战前,英国在海上东南亚的殖民地主要包括马来联邦、马来属邦和海峡殖民地,三者互不统属,以不同方式被英国殖民。二战期间,东南亚被日本占领。二战后,英国仍想恢复其在东南亚的殖民统治。但是,战后的国际形势已出现了重大变化,一方面是英国的衰落,一方面是东南亚各国的觉醒,国际形势的变化使得英国的殖民“梦想”难以实现。
迫于东南亚各殖民地的独立运动,英国不断调整其在东南亚的殖民政策。1946年英国公布了马来亚联盟白皮书,白皮书赋予非马来人平等的公民权利,这侵蚀了马来人的固有特权,因此这一计划受到马来人的抵制。为维护其权利,马来人于1946年建立马来民族统一机构(巫统)。从此,马来亚的政治斗争有了一个坚强的本土政党领导,进入到新阶段。代表华人上层利益的马华公会、代表印度人利益的马来亚印度人国大党和巫统在1955年合并为华巫印联盟,该联盟在东古·拉赫曼带领下和英国谈判,谋求马来亚的独立。经过马来人民的斗争,马来亚于1957年8月在英联邦内实现独立。
同时,新加坡也出现了独立运动。迫于新加坡人民的压力,英国在新加坡进行了宪政改革,允许新加坡组建政党,并逐步实现自治。1954年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成立,李光耀担任该党秘书长。根据英国和新加坡方面达成的协议,新加坡在1959年进行了立法会选举,获胜的人民行动党领导人李光耀出任新加坡总理,新加坡在英联邦内实现独立。虽然新加坡宣布独立,但是人民行动党内阁成员只是掌控教育、文化、劳工等次要权力,重要部门如国防、外交和国内安全等仍由英国人控制。同时,鉴于新加坡军事基地的重要性,英国仍有权占有和使用它。
虽然新加坡被英国人为地从马来亚联盟中分离出来,并因此发展成为两个独立的政治单元。但是,两国的地理、历史、经济和族群联系难以隔断。新、马之间仅一柔佛海峡相隔且有路桥连接,历史上长期由共同的英国总督管辖,经济上相互依存,新加坡依赖马来亚的水源、粮食等,马来亚则依托新加坡做为贸易港口;从族群来看,两国有很多亲缘关系。所以,新、马合并的呼声在两地一直存在,但1961年之前,两地合并的呼声并未成为主流,其阻力主要来自马来亚,一是“马来亚政府的种族安全担忧,因为合并后华人人数将占优势,加之华人的经济地位,联邦担心种族平衡会受到破坏”;[1]二是截止到1960年,新加坡的共产主义势力发展迅猛,马来亚政府担心新马合并后,共产主义势力会从新加坡蔓延到整个马来亚。但是,看似希望渺茫的新马合并在1961年忽然出现了转机。
1961年5月27日,马来亚首相东古·拉赫曼在东南亚记者协会上指出,“马来亚正着手进行一项计划,使马来亚、新加坡、婆罗洲、文莱、沙捞越和英国在政治和经济上合作,带来更密切的联系。”[2]这是东古首次公开提出“马来西亚计划”。东古的态度为何忽然发生逆转?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新加坡安全形势的发展,东古认为根据新加坡反对殖民主义的发展形势,新加坡可能会在1963年实现完全独立,届时英国将不再负责新加坡的安全和国防事务,而新加坡共产主义势力的发展形势已经威胁到人民行动党的执政地位,如果英国完全从新加坡撤离,新加坡将可能出现一个共产主义政权,更为严重的可能会出现新加坡的左倾政权和马来亚共产党“勾结”,威胁到巫统的统治地位;二是马来西亚计划可以化解新马合并的种族安全隐忧,按照马来西亚计划,五地合并后,马来人和土著居民之和会超过华人总数,这将保障马来人的优势地位。
东古的马来西亚计划引发了各方不同的反应。其中,菲律宾反对马来西亚对婆罗洲(马来西亚成立后,婆罗洲成为马来西亚的沙巴州)的合并,菲律宾总统马卡帕加尔宣称婆罗洲是菲律宾领土的一部分。(1)沙巴在历史上曾隶属于苏禄王国(Saltanah Sulu),在英国胁迫下,苏禄苏丹将沙巴割让给英国,而苏禄王国后来并入菲律宾,所以菲律宾从历史的角度宣称有权继承苏禄王国的领土。菲律宾和英国关于沙巴的纠纷,主要是沙巴到底是“割让”还是“租借”给英国,两国各执一词。菲律宾认为是租借,英国认为是割让,历史纠纷为菲、马争夺沙巴埋下了隐患。但对于马卡帕加尔而言,争夺婆罗洲更多的是一种姿态,他的目的是向菲律宾国人展示其强硬的外交政策,赢得国人支持。
马来西亚计划出台后,印尼并未公开反对,因为这一时期印尼主要聚焦于西伊里安问题的解决。1961年8月,印尼外长苏班德里约对到访的英国驻东南亚专员薛尔克表示,“印尼同意马来西亚计划”。[3]在1961年11月20日联合国大会发言时,苏班德里约再次重申印尼不反对马来西亚计划。时任美国驻印尼大使琼斯也表示,印尼总理朱安达认为印尼宁愿在其北边出现一个独立的国家而不是英国的殖民地。显然,印尼的官方表态是不反对马来西亚计划,但是印尼内部对于马来西亚计划也有反对之声,其中印尼共产党(PKI)从一开始就反对马来西亚计划,他们宣称这一计划是“英国压制五地人民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表现,不利于当地人民取得真正的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4]因为印尼当时的主要关注点是西伊里安问题,所以对于东古提出的马来西亚计划,印尼并没有明确表示反对。但是,文莱起义给印尼反对马来西亚计划提供了借口。
1961年12月8日,文莱人民党领导人阿扎哈里以马来西亚计划违背了当地人民的意志为由,发动文莱起义。文莱起义表明,马来西亚计划在文莱是不受欢迎的。印尼以此为由,反对马来西亚计划。但是,文莱起义只是印尼反对马来西亚计划的借口,其根本原因是,到1961年底,印尼已基本解决西伊里安问题,西伊里安问题的解决进一步激发了印尼的民族主义。但是,印尼为解决西伊里安问题也付出了很大代价,不仅严重恶化了国内经济,还激化了国内种种矛盾。为了转移国内矛盾,苏加诺需要一场新的外部斗争,文莱起义恰恰为苏加诺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
文莱起义爆发后,英国速调军队镇压。在文莱苏丹和英国的联合镇压下,起义旋即失败。但起义对文莱苏丹产生了重要影响,鉴于这一事件所产生的压力,文莱苏丹决定不加入马来西亚,这是文莱不参加马来西亚计划的原因之一;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文莱苏丹基于自身利益考量,他认为加入马来西亚后,文莱在石油利益分配上会受到损失,以及文莱苏丹对自己在马来西亚国家元首中的地位也不满意,最终没有加入马来西亚。(2)参见:J.A.C.MACKIE.Konfrontasi:The Indonesia-Malaysia Dispute 1963-1966.Kuala Lumpur: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4,pp.112-113.文莱起义不仅影响了文莱苏丹加入马来西亚的决定,也给印尼和菲律宾反对马来西亚计划提供了借口,两国认为马来西亚计划违背了被合并地方的民意。菲律宾总统马卡帕加尔宣称要“捍卫婆罗洲主权,并称马来西亚计划没有依据民族自决的原则,是殖民主义保护自身利益的权宜之计”;[5]181印尼方面,在文莱起义后不久,苏班德里约宣称马来西亚计划是“亲殖民主义和亲帝国主义追随者的阴谋,展示了对印尼的敌意。”[6]1963年2月,苏加诺宣布对抗马来西亚,印(尼)马进入正式对抗阶段。
二、印(尼)马对抗演变及各方调节的努力
文莱起义发生后,马来亚和菲律宾、印尼的关系迅速恶化。仅在1962年12月27日至1963年2月3日期间,印(尼)马就在领海发生了多起对抗事件。印尼空军和陆军也积极参与对抗马来亚。在军事对抗加剧的同时,印尼还发动文宣攻势,以唤起北婆罗洲三邦人民的“觉醒”。
关于印尼对抗马来亚的动机,不同国家有不同认识,不同认识又导致各国采取了不同政策。英国认为“印尼对抗马来亚是苏加诺野心使然,必须以强硬手段来回应苏加诺”[7]112;而马来亚领导人东古和拉扎克认为印尼共才是印(尼)马对抗的根源,“两国关系只有在印尼共被清除之后才可能得以改善。”[5]246总体而言,美国是赞同马来西亚计划的,认为建立一个亲西方的马来西亚能够和日、韩、菲、台、泰一起构筑一条遏制中国的封锁链,但是美国政府和国会对印尼和苏加诺的认知也存有分歧,肯尼迪总统认为印尼采取对抗政策,是印尼国内脆弱性和各种政治势力竞争的体现,是苏加诺平衡印尼陆军和印尼共的策略,为此需要援助印尼,对内增强印尼陆军和苏加诺制约印尼共的实力,对外防止印尼倒向共产主义阵营,如果西方的援助能使印尼站在西方阵营或者至少保持中立的外交政策,就有利于印(尼)马对抗的解决。美国国会则认为苏加诺是有地区野心的政治家和亲共分子,经济和军事援助只会纵容苏加诺。
随着印(尼)马对抗和菲、马沙巴纠纷的加剧,印尼、菲、马都有意通过高层会谈来化解冲突。1963年6月7-11日,印尼外长苏班德里约、马来亚外长拉扎克、菲律宾外长佩莱兹在马尼拉开会协商因马来西亚计划引发的地区冲突问题。苏班德里约认为马来西亚计划没有征询北婆罗洲三地人民的意见,违背了自治原则;拉扎克则辩解说,1963年春,在沙巴和沙捞越的选举中,赞成马来西亚计划的政党获胜已是当地人意愿的检验。苏班德里约和佩莱兹承认在婆罗洲和沙捞越进行正式公民投票的困难性,但是在联合国指导下开展某种形式的民意确认也可以给印尼和菲律宾一个放弃反对马来西亚计划的台阶可下。经过博弈,三国外长签署了《马尼拉协定》,其中第10、11和12款内容为:
“10.部长们重申他们的国家恪守非自治领地人民的自决原则。关于这一点,印尼和菲律宾表示他们将欢迎建立马来西亚,如果一个独立和公正的当局,即联合国秘书长或他的代表确定婆罗洲领地人民予以支持的话。11.马来亚联合邦对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态度表示欣赏,并承允同英国政府和北婆罗洲领地政府进行磋商,以便邀请联合国秘书长或他的代表采取必要的步骤来确定这些领地人民的意愿。12.菲律宾清楚地表明,它对北婆罗洲并入马来西亚联邦的立场由菲律宾对北婆罗洲的要求的最终结果来决定。部长们注意到菲律宾的要求以及菲律宾根据国际法和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继续提出该要求的权利。他们同意北婆罗洲并入马来西亚联邦将不会损害这一要求和上述提到的任何权利。”[8]167
这些条款非常模糊,各方均可按照于己有利的原则来进行解释。但即便如此,三方还是兼顾彼此利益,为了对方利益而适当做出让步,印尼、菲律宾同意马来亚进行“某种形式”的民意确认,马来亚同意进行民意确认以保存苏加诺的颜面,同时“部长们注意到菲律宾的要求”,[8]167这种为解决地区冲突而产生的相互理解是后来冲突各国进行合作的重要因素之一。
马尼拉外长会议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印(尼)马之间的敌意,马尼拉精神的达成使人们看到了解决地区冲突的希望,但这种希望很快就被伦敦会议所打破。1963年7月9日的伦敦会议是英国为建立马来西亚协调合并各方的一次会议,与会几方达成了《伦敦协议》。《伦敦协议》规定,“不管内外阻力如何,马来西亚联邦都将在1963年8月31日成立。”[5]214《伦敦协议》和马尼拉外长会议是相悖的,马尼拉外长会议规定沙巴和沙捞越的民意确认是成立马来西亚的前提条件,而《伦敦协议》则具体规定了马来西亚的成立日期,给人一种马来西亚成立已是既成事实的感觉,这一规定显然漠视了沙巴和沙捞越两地的民意,也漠视了马尼拉外长会议的和解精神。苏加诺以此为借口,再次威胁要“粉碎”马来西亚计划,他说,“印尼和印尼人民不仅反对马来西亚计划,还要彻底粉碎它。”[9]印(尼)、马、菲三方之间的争议留待首脑峰会解决。
1963年7月30日,苏加诺、东古和马卡帕加尔在马尼拉召开三国首脑峰会。此次峰会主要有三个议题:调节印(尼)马对抗和沙巴之争、创立马菲印联盟、商议东南亚的外国军事基地问题。(3)马尼拉峰会的三个议题由笔者梳理而成,具体可参考:Ann Marie Murphy.From Conflict to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1961-1967:The Disputes Arising out of the Creation of Malaysia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 (ASEA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2002,pp.139-150.
由于马尼拉首脑峰会距离《伦敦协议》中确定的马来西亚计划成立日期只有一个月时间,东古建议在马来西亚成立后再在沙巴和沙捞越两地进行民意调查,印尼和菲律宾可待民意确认赞同加入马来西亚后再承认马来西亚。马来亚受到英国的压力,不愿推迟马来西亚的成立日期,印尼和菲律宾虽然理解东古的难处,但拒不妥协。为了减轻英国对马来亚参加地区谈判的束缚,马卡帕加尔还致信英国,他认为英国的施压只会加剧印(尼)马对抗,还可能引发更严重的后果,使得印尼加入共产主义阵营,从而在东南亚引发新一轮的冷战。英国消极回应菲律宾的调节,因为英国认为印尼对抗马来西亚是苏加诺的地区野心使然,必须加以遏制。同时,联合国秘书长认为在一个月完成民意确认是不可能的。鉴于在8月31日完成民意确认的困难性,各方相互妥协,最终达成一致,马来亚同意推迟几周成立马来西亚,目的是为了允许联合国指导两地民意调查。东古推迟成立马来西亚日期引起了英国和新加坡、沙巴、沙捞越的反对,他们威胁会如期在英联邦内宣布独立。
三国首脑峰会的另一个成就是组建马菲印联盟。马菲印联盟是一个马来人的地区组织,这一组织强调政治安全合作,虽未言明,但“反对华人的影响和威胁是其成立的根基”。[10]586虽然对华人和共产主义势力的威胁认知相同,但印尼、马来亚和菲律宾对如何限制华人威胁和共产主义传播的认识又有所不同:马来亚认为将新加坡合并进马来西亚,可以防止社阵上台,从而预防新加坡演变成共产主义国家;印尼和菲律宾则认为,“将新加坡纳入马来西亚会使华人和共产主义的‘癌细胞’通过马来西亚的北婆罗洲地区传给相邻的印尼和菲律宾。”[7]148对于成立马来西亚究竟是有利于助长还是抑制共产主义传播,三国虽有分歧,但关于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有助于三国之间加深理解。
会议的第三个议题是讨论东南亚的军事基地问题。印尼对军事基地问题尤其关注,因为印尼被西方军事基地包围:东有菲律宾的美国军事基地,北有马来西亚的英国军事基地,南有澳大利亚的英国军事基地。印尼担心英美利用这些军事基地来颠覆它,外岛叛乱期间,美英就是利用这些军事基地协助了外岛叛乱,这一历史记忆还深刻影响着印尼领导人。经过磋商,三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外国军事基地的性质都是临时性的,不允许外部势力利用他们领土上的军事基地来颠覆区域内邻国。
马尼拉峰会看似是个三赢的结果:印尼迫使马来亚对沙巴和沙捞越进行民意确认,并迫使马、菲承认其领土上外国军事基地的临时性质;马来亚对沙巴和沙捞越两地的民意确认满怀信心,象征性地推迟成立马来西亚会使得印尼和菲律宾欢迎马来西亚的成立;菲律宾实现了成立马菲印联盟的梦想,作为印(尼)马对抗的调节者,化解了地区对抗同时无损沙巴主权的声索。从表面上看,由马来西亚计划引发的地区冲突至此已经解决。
但是,新加坡、沙巴和沙捞越反对推迟成立马来西亚,三地领导人威胁东古如果推迟成立马来西亚,他们还会在8月31日宣布独立。英国驻东南亚总督桑迪斯支持新加坡、沙巴和沙捞越的做法,在压力面前,东古宣布马来西亚将于1963年9月16日成立。印尼和菲律宾认为,民意调查还未结束,东古就宣布马来西亚的成立日期,东古“提前预判”当地居民调查结果的做法明显违背了马尼拉会议精神。印尼宣布不承认马来西亚,菲律宾将菲马关系降低为领事级,马来西亚则以和两国断绝外交关系来回应。
1963年9月17日,印尼、菲律宾和马来西亚断交意味着对抗升级,标志着印(尼)马对抗进入第二阶段。此前,印(尼)马对抗主要为文诛笔伐,双方在报章、广播上相互攻击,军事冲突较少。马来西亚成立后,印(尼)马对抗加剧,主要表现为:经济方面:双方断绝贸易往来;军事方面:印尼派军队向马来西亚本土渗透;政治方面:印尼宣布不承认马来西亚,印尼民众攻击英国驻印尼大使馆,劫掠英国在印尼的人员,“自发接管”英国在印尼的企业资产等;同时,印尼还发动宣传攻势,鼓动沙巴和沙捞越居民起义,脱离马来西亚。印尼的行为印证了英国对印尼对抗马来西亚意图的判断,即苏加诺对抗马来西亚不是平衡国内各种政治势力的策略,而是其地区野心之表现。
印(尼)马对抗升级不仅加剧了地区冲突,还卷入了更多国家和引发了冲突各国国内政局的变化。面对印尼咄咄逼人的行为,美国对印尼政策逐渐发生微妙变化,主张对印尼实施强硬政策的决策者逐渐占了上风,美国开始向马来西亚倾斜。但此时美国在越战中越陷越深,美国担心印(尼)马对抗升级,由于盟约关系,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会卷入其中,最终导致美国卷入。美国的一份“东南亚特别研究报告”指出,“当前印(尼)马之间的冲突,从某些方面看,和越南战争一样潜在地威胁着世界和平。如果印尼对马来西亚采取军事行动,英国自然会卷入冲突,和英美有安全互助条约的国家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菲律宾也会依次卷入。因此,这一区域的任何武装冲突,都可能升级为一场主要战争,最终将美国卷入。”[11]为此,美国再次尝试调节,在1964年1月,约翰逊总统委派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作为总统特使来调节印(尼)马冲突。但肯尼迪调节印(尼)马冲突时,两国对抗正酣,从印尼方面来看,刚刚过去的收复西伊里安运动给苏加诺提供了很多经验,苏加诺对待荷兰人所采用的策略——“边打边谈、以打促谈”十分有效,印尼也期望通过这种策略让马来西亚屈服,但马来西亚背后的支持者是英国,印(尼)马对抗的实质是印尼和英国的对抗,英国不会像荷兰那样轻易妥协;从马来西亚方面讲,1964年年初的马来西亚对印尼更加强硬,因为印尼在沙巴和沙捞越的渗透以及煽动当地人起义都没有什么效果,相反,这种渗透和煽动反而激发了当地人对马来西亚的认同。1964年4月的马来西亚大选中,东古领导的联盟党以压倒性优势获得胜利即是这种认同的体现,马来西亚大选给东古带来了对抗印尼的信心。印尼和马来西亚都不妥协,肯尼迪虽然费尽周折将冲突各方带到了谈判桌前,但是印尼和马来西亚在谈判桌上陷入了僵局。
为了挽救走入僵局的肯尼迪调节,泰国外长他那·科曼在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之间穿梭外交,终于促成了三国外长参加曼谷会议。在三国外长会议上,“印尼坚持停火之前应先达成政治决议,马来西亚则坚持先停火再召开峰会。”[12]由于印(尼)、马互不妥协,曼谷外长会议宣布破裂。
肯尼迪调节的失败和曼谷会议的破裂对冲突各国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对菲律宾而言,美国和泰国调停失败后,美国开始反对马卡帕加尔的马菲印联盟计划,澳大利亚也强调依据《五国防务协定》,它将援助马来西亚对抗印尼和菲律宾。在外部压力下,国内反对马卡帕加尔的呼声渐高,很多菲律宾人认为苏加诺拒绝美国和泰国伸出的橄榄枝是其地区野心的体现,如此发展下去,菲律宾可能就是苏加诺的下一个对抗目标,因此要求结束和印尼的准盟友关系,1964年5月,“亲印尼”的赖佩兹去职,“亲马”的门德兹出任菲律宾新外长,随后菲律宾和马来西亚恢复了领事级外交关系,两国关系逐步缓和。
如果说肯尼迪调停和曼谷会议的失败使得菲、马走向缓和,但是对印尼却产生了相反的影响。对于印尼而言,调停失败使得印尼进一步左转。苏加诺对于调停的顽固态度验证了英国之前的判断,英国向美国施压,美国彻底站在马来西亚一边。美英对马来西亚的支持,使得苏加诺在外交上别无选择,只能进一步依赖中苏;从内部表现来看,印尼共利用对抗马来西亚激发的民众狂热得以大力发展,苏加诺对印尼共更加倚重。苏加诺激进的内政外交政策和日益恶化的健康情况引发了印尼陆军的担忧,陆军开始转变对抗马来西亚的政策,陆军担心苏加诺去世后,印尼共在中国和苏联支持下上台,从而削弱陆军的地位。印尼陆军在肯尼迪和他那·科曼调节之前一直支持苏加诺的对抗政策,他们认为对抗可以增加军费和延长《军管法》从而提高陆军的地位,但是美、泰调节失败后,陆军逐渐认识到对抗的危害:对抗提高了印尼共的地位,打破了陆军的政治垄断地位;苏加诺以对抗为名,将印尼陆军部署在对抗马来西亚的前线,削弱了陆军在雅加达的影响力;再者,印尼共借机在陆军内部发展成员,“腐蚀”印尼陆军,印尼共已经掌控了印尼空军即是明证;最后,陆军还担心印尼共和中苏的密切关系,从而将印尼拉入社会主义阵营。1964—1965年,印尼和中国的关系发展迅速,印尼共在国内的地位上升很快,印尼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使得陆军态度发生转变,以苏哈托为首的部分军官认为如果印尼共和共产党中国内外联合,必将严重威胁陆军的地位,由此陆军开始将中国视为其最主要的威胁,而过去印尼认为英国成立马来西亚联邦是包围印尼的殖民阴谋,随着形势的发展,印尼陆军认为马来西亚不仅不再是印尼的威胁,反而是阻止中国威胁的北部屏障,当时陆军的智囊团陆军参谋指挥学院发表了一篇题为《自由与积极的印尼对外政策》的文章,该文强调印尼面对一个来自“北方”潜在威胁的事实,并推荐了对抗这个威胁的措施。它首度透露苏加诺和陆军反共领导层之间的分歧。在苏加诺看来,来自“北方”的威胁基本上是来自在此地区设有军事基地的西方强权,特别是来自英国的殖民与新殖民存在;在反共的陆军领导层眼中,这种威胁来自共产党中国。(4)参见:[印尼]安华的《印尼与东南亚国协——外交政策与区域主义》,蔡百铨译。台北国立编译馆,1998年版,第102-104页。对威胁的认知不同,所要采取的政策就有所不同,苏加诺主张对抗英国和马来西亚,陆军高层认为应该和马来西亚发展外交关系,以其作为抵制中国威胁的北部屏障。由是,陆军高层开始和马来西亚秘密接触,寻求结束对抗。陆军战略指挥部司令苏哈托成立“特别行动小组”,由穆托波主持,穆托波和马来西亚副首相拉扎克、外交部常务秘书加扎利·莎菲联系,双方达成默契,在苏加诺和东古都持强硬态度的情况下,印(尼)马对抗一时难以结束,双方的秘密接触主要是避免冲突进一步恶化。
总的来看,1964—1965年,印(尼)马之间的对抗关系是官方对抗和秘密渠道接触同时并行,这种“双轨政策”体现了马来西亚内部东古和拉扎克对印尼政策的分歧,也体现了印尼陆军和苏加诺、印尼共之间对马来西亚政策的分歧,随着印尼共和陆军之间矛盾的加剧,印尼内部爆发了“九三〇事件”,关于这一事件的起因很难说清楚,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印尼共挑起的一种夺权行为,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印尼陆军的内斗,但不管其起因和性质如何,结果却是鲜明的。印尼陆军战备司令苏哈托迅速镇压了“九三〇运动”,并以印尼共卷入该事件为借口,对其大肆屠杀,同时也因苏加诺对这一事件的暧昧态度,逐步架空其权力。1966年3月11日,苏加诺发布“三一一政令”,将权力移交给苏哈托,但苏加诺仍是印尼名义上的总统,对印尼政治事务有一定影响。“三一一政令”后,印尼逐渐形成三人负责的政治体制:苏哈托负责国防和安全事务,马立克负责外交和社会事务,日惹苏丹汉孟库·布乌沃诺九世负责经济和发展事务,印尼从此进入“新秩序时期”。
三、从对抗结束到东盟建立
印尼“新秩序”的确立是印(尼)马对抗的分水岭。苏哈托政府迅速调整内政外交政策,对内恢复秩序、发展经济和取缔印尼共产党,对外采取务实的外交政策,逐步放弃对抗政策,印(尼)马开始由冲突走向和解,进而合作,并最终建立了东盟。
诚如上文所述,早在1964年印尼陆军和马来西亚就有结束对抗的意愿,双方开始秘密接触。但是在官方层面上,印尼在“九三〇事件”后并未立刻放弃对抗马来西亚的政策,于是东古怀疑印尼结束对抗的诚意,但是参与秘密接触的拉扎克和加扎利·莎菲更能体谅印尼陆军领导层的掣肘因素:一是苏加诺的影响还在,二是因为印尼民众长期受到苏加诺左倾政策影响,陆军领导人担心突然转变政策会引发民众抵制。同样,参与秘密接触的印尼领导人苏哈托和马立克也能理解马来西亚的苦衷,东古不仅要保存颜面地放弃对抗,同时马来西亚还受到英国和沙巴、沙捞越的牵绊,印(尼)、马领导层的这种同理心使得彼此能够保持秘密接触不再中断。虽然,印(尼)、马最初的秘密接触没有就结束对抗达成一致,但双方同意两国之间应保持一个永久的通讯渠道。印(尼)、马官方已经断绝外交关系,所以两国之间的秘密接触大多在泰国举行,这也是以后泰国在东盟成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个原因。恰巧的是,印尼新秩序确立后,苏哈托和马立克都成为印尼的主要领导人,从而使得秘密接触得以维持并转为公开。
我们先来看看新秩序确立时印尼的国内外状况。从印尼国内情况来看,1966年初印尼经济已处在崩溃边缘,通货膨胀率达到600%,恶化的经济容易引发国内持续动荡;从国际环境来看,新秩序确立时的印尼在国际上空前孤立,不仅西方国家敌视印尼,就连在第三世界中,印尼也很孤立,这是因为苏加诺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以及1965年初印尼退出联合国的决定所致。内政外交是密切相关的,但不同领导人会采取不同措施。苏加诺面对恶化的经济形势,采取对抗政策,将经济恶化引起的国内矛盾外移;新秩序领导层采取了相反的解决措施,因为苏哈托和马立克认识到需要发展经济来解决国内矛盾,而发展经济就需要争取外援,争取外援则需要放弃对抗政策、摆脱孤立的国际环境,为此印尼新秩序领导层需要扭转外交方针,其第一步就是要放弃对抗马来西亚的政策。新任外长马立克在其第一次媒体访谈中说:“必须重新审视印尼的外交政策……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我们必须面对外部世界的现实。”[10]37虽然新秩序领导层一致认为应该结束对抗,但对于结束对抗的条件却存有分歧,尤其是印(尼)马对抗的发起人,比如纳苏蒂安(印尼、马对抗发起时的国防部长,主张对抗马来西亚)认为,如果印尼无条件结束对抗将会危及印尼名声,关键是损害这些对抗发起者的声誉。同样,陆军中苏哈托的竞争者担心苏哈托如果成功结束对抗,必将提高其威信,他们不愿将所有功劳置于苏哈托一人身上。所以,新秩序刚刚确立时,印尼官方并未放弃对抗,这无疑增加了邻国的疑虑。为了减少邻国的质疑,印尼有时通过泰国或菲律宾,有时通过秘密渠道和马来西亚沟通,这些接触为1966年4月末的曼谷会谈提供了基础。在曼谷会议之前,印(尼)马进行了多次秘密协商,其中马立克和加扎利·莎菲秘密协商,以证明印尼文职官员像陆军一样希望结束对抗,“特别行动小组”成员在1966年春多次和马来西亚方面联系,此外穆托波和穆达尼也秘密前往马来西亚拜会拉扎克,共商结束对抗事宜,双方达成以下共识:“1.解决冲突不让英国或其他大国卷入;2.以一种能确保印(尼)、马保存颜面的方式结束对抗;3.如果东古对印尼结束对抗仍然怀疑,印尼可派出军事代表团访问马来西亚以示诚意。”[7]279总之,1966年春,冲突各国进行了一系列秘密接触,这些秘密接触为1966年4月30日的曼谷会议打下了基础。在曼谷会议上,马立克表达了印尼结束对抗的愿望,“如果你问我个人观点,我想如有可能,明天就愿看到和平。”[13]马立克同样谈到了东南亚的外国军事基地,“外国军事基地对和平和安全没有任何作用,只是和平和安全的威胁。政府想创造条件让东南亚的人民和谐相处、相互信任和建立真诚友谊。外国军事基地的存在使这些变得完全不可能。”[14]
过去印(尼)马对抗难以解决,主要是因为双方对马尼拉精神的理解不同。在此次曼谷会议上,马立克不拘泥于民族自决的形式,认为沙巴和沙捞越任何形式的民族自决均可。但是,双方国内的阻力仍然束缚着冲突的解决,苏加诺仍是名义上的总统,强烈反对结束对抗;鉴于过去苏加诺的屡次食言,东古对印尼结束对抗的诚意表示怀疑。为了打消东古的怀疑,印尼决定派出“粉碎马来西亚”军事代表团拜会东古,这一军事组织访问马来西亚势必面临极大危险,但是越是如此,越能显示印尼结束对抗的诚意,印尼的这一做法终于打消了东古的疑虑。至此,印尼、马对抗事实上已经终结。
印(尼)、马关于结束对抗的谈判相对于以前的谈判,两国表现出更多的互谅精神,双方更愿意合作。马来西亚认识到苏哈托及其盟友在印尼政治体制过渡时期的脆弱性,印尼则为拉扎克和加扎利·莎菲劝说东古提供配合,这种互谅有利于更好地解决东南亚的地区冲突。1966年8月11日,印(尼)、马签署《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和马来西亚关系正常化协定》,标志着印(尼)马对抗正式结束。该协定第一条为,“马来西亚政府为解决由于马来西亚的成立而在两国间产生的问题,同意让直接有关的沙巴和沙捞越人民有机会尽速以自由和民主的方式,通过普选重新确认他们以前所作出的关于他们在马来西亚的地位的决定。”[15]双方都可以按照于己有利的原则来解释该条文,印尼可以解释为该条文证明了1963年联合国民意调查存有缺陷,因此有必要有一个新的确认;马来西亚则解释“重新确认”证明了是对1963年联合国民意调查的再次确认和肯定。
印(尼)马对抗的缓和有利于菲马关系的发展。早在1964年,菲马关系就已经开始缓和,两国恢复了领事关系。1965年底,马克斯当选为菲律宾总统。马克斯希望改善菲马关系,一则因为菲律宾南部和沙巴之间的走私问题严重影响了菲律宾的财政税收,二是因为印尼拒绝调停的态度引起更多菲律宾人的反感。马来西亚为了孤立印尼,也想和菲律宾恢复全面外交关系。但马克斯受制于国内因素,国内的自由党反对为了恢复菲马关系而放弃沙巴主权。为了减少马克斯的国内牵绊,东古在1965年12月确认菲马恢复正式外交关系并不妨碍菲律宾对沙巴主权的声索。菲、马决定在1966年4月8日恢复外交关系,但是这一决定遭到了苏加诺的强烈谴责,面对印尼的抵制,菲律宾决定推迟恢复和马来西亚的外交关系。经过这一事件,菲、马双方相互了解到对方恢复外交关系的诚意。1966年4月的曼谷会议意味着印(尼)马对抗事实上的结束,印(尼)马结束对抗为菲马恢复外交关系扫除了最后障碍,1966年6月3日,菲马恢复全面外交关系。
四、结论
印(尼)马对抗是战后东南亚发展进程中的里程碑式事件,印(尼)马对抗不同于越南战争,这一事件中虽有英、美、中、苏等大国的影子,但冲突的缘起、调节直至对抗终结主要是东南亚几国之间博弈的结果。当事几国经过冲突以及化解冲突的努力,他们一致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新的地区组织将解决冲突的方式、方法机制化,从而避免再出现类似印(尼)马对抗的事件。”[7]304在冲突和调节冲突的过程中,这些国家增加了互动,他们希望将这种沟通、调节和合作机制化、制度化,于是就有了建立地区组织的动力。
但是,在东盟之前,东南亚就已有一些地区组织,比如东南亚联盟和马菲印联盟,是恢复以前的组织还是重新建立一个新组织?各国存有分歧,马来西亚主张恢复东南亚联盟,因为这是它主导创立的一个地区组织,但是东南亚联盟三个成员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都是亲西方国家,一向主张自由不结盟的印尼不愿加入一个亲西方的地区组织,同时作为东南亚地区大国,印尼不愿以新成员的身份加入已有的国际组织;对于马菲印联盟,它是基于马来人的一个区域组织,这种带有种族性质的地区组织对于华人为主的新加坡以及华人有重大影响力的马来西亚而言,都不是最好的选择。各国决定建立一个新的地区组织,尤以印尼最为积极。
1967年8月5-8日,印尼、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新加坡在曼谷开会,发表了《曼谷宣言》,组建东盟。东盟的诞生标志着东南亚的地区合作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印(尼)马冲突和东盟成立都是冷战时期东南亚的重大事件。二者之间究竟有无关系?有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笔者认为,印(尼)马冲突和东盟创建有着内在的联系,东盟创建应被视为调节印(尼)马冲突的必然结果。这主要表现为:
第一,调节印(尼)马冲突和组建地区组织是相关国家后期磋商、调节的并行话题。早在1966年春的曼谷会议上,马立克、拉扎克和他那·科曼就讨论了地区国家之间合作和创建地区组织的问题,随后几次会议的主题大多围绕这两个问题。
第二,卷入冲突的深度和建立东盟的热度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卷入冲突的国家也正是东盟创始的国家,印尼和马来西亚深深卷入对抗之中,对冲突之害理解最深,为化解这些冲突投入精力最多,故而印(尼)、马也最渴望将这些沟通、通信机制化从而限制未来的冲突和加强地区合作。菲律宾虽未放弃沙巴主权要求,但较早地缓和了和马来西亚的关系,陷入冲突远不如印(尼)马那样深刻,对化解对抗的机制需求也不那么迫切,没有深度探讨和解决与马来西亚之间的分歧,所以对建立东盟并不热情。无论新马合分,新加坡和印尼的关系都从属于印(尼)马关系,比如李光耀决定在印(尼)马恢复外交关系后才恢复和印尼的关系,所以直至东盟成立的前一刻,新加坡才决定加入这一国际组织。缅甸和柬埔寨没有卷入对抗,虽经印尼力邀,他们还是决定不加入东盟,因为他们没有卷入地区冲突事件中,不像其他涉事国那样深刻理解建立东盟的必要性。虽然泰国没有卷入冲突,但是泰国在调节冲突中发挥的作用也解释了它是东盟创始国的原因。总之,印(尼)马冲突及其解决过程,加强了这些国家之间的联系,增强彼此认同,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印(尼)马对抗和调节过程是东盟成立的一个催化剂。正如理查德·布特维尔(Richard Butwell)所说,“东南亚国家之间几个世纪的互动都没有现在几年多”。[16]
第三,印(尼)马冲突的调节方式是东盟方式的来源。“东盟方式主要表现为偏爱非正式协商和松散安排,坚持保留原则,依赖领导人个人的关系。”[17]33-34任何一个国际组织在做出正式决议之前都会事先在成员国之间进行协商,但东盟却将这种非正式协商作为一种主要机制,其内容更多,操作更复杂,执行更有技巧和耐心。东盟不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刚性决策方式,而是在非正式协商中寻求达成一致。东盟不是靠强制某成员国放弃自身立场,而是寻求共同点和相互妥协让步,保留原则主要表现为10-X机制,东盟十国就某一议题协商时,如果多数国家赞同通过,个别国家有保留意见的权力,本国可以暂不执行。
前东盟秘书长塞韦里诺(Rodolfo C.Severino)也提到,“我们也同样能够看到历史因素、国家环境和国家关系共同塑造了作为一个组织的东盟,并且设立了东盟方式。”[17]塞韦里诺所说的历史因素和印(尼)马对抗及其调节的过程不无关系。东盟方式的历史源头其实就是印(尼)马对抗的调节机制,在调节地区纠纷中,冲突当事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以及泰国、新加坡,为了结束地区冲突,这些国家的领导人穿梭外交,他们的会谈有时是在高尔夫球场,有时是在餐会上,这种漫谈式的非正式协商虽然看似不正规、不正式,但往往更容易达成一致意见。因为,这种非正式的场合能给他们提供更自由的空间,即使非正式会谈不成功,也可以避免失败带来的尴尬。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卷入印(尼)马对抗及其调节的国家和东盟创始国、卷入冲突深度和创建东盟的热度、调节冲突方式和东盟方式都有深刻的联系,所以从这一角度来看,印(尼)马冲突是东盟创建之因,东盟创建是印(尼)马冲突之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