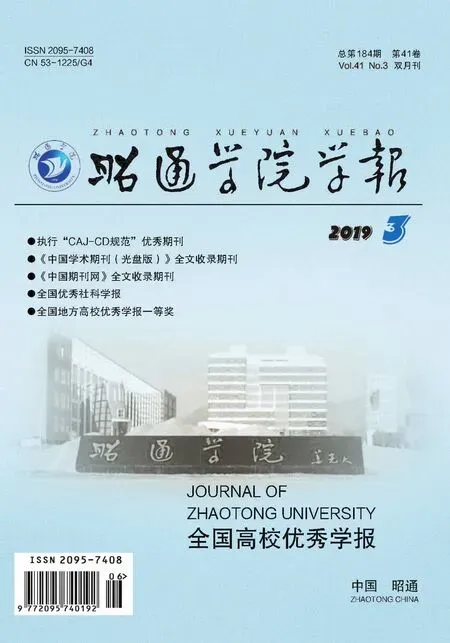李荣“重玄”思想融摄佛教“三论”缕析
2019-02-22
(新疆师范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7)
李荣,号任真子,绵州巴西人(今四川绵阳)。他与成玄英同为唐初重玄学派的代表人物,著有《老子注》《西升经集注》。李荣自小习道出家,享誉蜀中。后唐高宗时期居长安,据《集古今佛道论衡》记载,李荣作为当时的道教领袖,常与佛教徒进行教义辩论而成为当时的“老宗魁首”。高宗末年,李荣投身道教理论建构,影响了后世陈抟、司马承祯等著名道教学者。李荣虽处辟佛的立场,却时常援佛入老,尤其是以三论宗的思维模式来完善与丰富其重玄思想。自魏晋南北朝至初唐,佛教哲学的发展与三教的论争延续激起了道教自身理论完善的迫切感,道教学者也在隋唐统治者的扶持下习三教之学,整理道教教义。李荣生于初唐的蜀地,正当是三论于蜀广为流传的时候。据《续高僧传》记载,释惠暠、释灵睿、释世瑜都曾在南北朝至初唐时期至蜀弘三论,因此李荣可熟练援三论的思想资源以倡明“重玄”理论亦是有迹可循。
三论宗是隋唐颇具影响的宗派之一,旨在阐扬“三论”以树己之要。三论宗立足于佛教基本的中观问题,详尽论述了诸多佛教范畴。其讨论之丰富与思辨之精到赋予了中观思想更为深刻的内涵,进而影响了后起的禅宗,天台等教派。同时三论宗的思想也对儒家与道教有一定启发与影响,特别是道教的重玄思想。正如董群先生所说:“三论宗深深地影响了道教,道教阐释的三论学主要体现为重玄学派对三论宗中道思想的吸收。比较道教对三论的理解和三论宗思想本身的异同,也是对三论宗研究地深化。”[1]蒙文通先生疑李荣为成玄英的弟子[2]347,思想上对成氏有较多继承。成玄英虽已用佛教中观思想与词旨发挥老庄思想,正如胡兴容先生认为的,成玄英仍有义理乖格和名相未消化的现象,但李荣在其注老作品中廓清其弊。[3]李荣阐述重玄的方法论有着明显的三论宗痕迹,也为后世道教学者贯通佛道思想开了先河。
一、道体论
魏晋先有王弼“以无为本”的本体论,后有裴頠的“崇有论”,致力于讨论“有”“无”的本末先后问题。李荣认为“魏晋英儒,滞玄通于有无之际”[4]648,执着于有或无都非正观。他把自己的本体论建立在对魏晋玄学和道教自身内部逻辑的扬弃深化,对佛教三论宗义理吸纳上。李荣把“双遣”作为泯除对道本体进行分别式规定与认识的方法,实际是借鉴佛教中观学为方法论,早在三论第一人鸠摩罗什将印度佛学般若中观介绍到中国,就将“中”的意义表现在不滞“空”“有”两边上,如其言:“佛法有二种,一者有,二者空。若常在有,则累于想著;若常观空,则舍于善本。”(僧肇《注维摩诘经》卷六)且其有以中观学注《老子》之举,如蒙文通先生即认为重玄思想之流派虽始于孙登,但以遣两边之训与三翻之式注《老子》却是由鸠摩罗什开创的。[2]348鸠摩罗什以中观的模式来注道家,即已为为重玄学者融通两种思想开了先河。因以,重玄家们以中观不滞两边的思想模式来注老庄,多是受罗什的启发。卢国龙先生将重玄方法论定义为“通过非目的论的理论方法去寻找最终目的。”[5]218李荣的道本体是“有无非常”和“存亡不定”的超越性本体。他旨在找到一个比“有”和“无”更有存在意义的精神实体,以之为宇宙与人生的最高原则。李荣将之诉诸到道论的开发,他说:“道则非无非有”“非有非无之真,极玄极奥之道。”[4]595他标举“真常之道”,并描述为“道之为物,唯恍唯惚,不可以有无议,不可以阴阳辩,混沌无形,自然而成,故曰混成。”[4]597从李荣对“道”的界定可看出,它是“混成”而“无形”的,不可用分别式的认知去认识道的整体性。因此,他以“重玄之道”作为认识超越有无的道本体的方法。“重玄”出自老子“同谓之玄,玄之又玄”(《老子·第一章》)。李荣认为,首先是“玄之”,“借玄以遣有无”用超越的眼光认识到事物非有非无的性质,做到不偏滞于“有”和“无”。佛教对于不滞两边,最精彩阐述当推僧肇,其“有”“无”的认识使“空”的内涵更为深刻。僧肇阐述“不真空”义为“欲言其有,有非真生;欲言其无,事象既形。象形不即无,非真非实有”。[6]认为事物无自性不是真有,所以“非有”;另一方面,事物又都是由因缘和合而成,所以“非无”。就如幻化人一样,并非真的人但却仍然存在。同时,这样的“无”不是绝对的、虚无的,否则成“顽空”。说“有”的时候,也需看到事物是“缘起性空”由因缘和合的并无自性,不是真有的性质。其次李荣说为“又玄之”,“有无既遣,玄亦自丧。”[4]566从非有非无到“非非有非无”。李荣用了佛教病药之喻,解释“中道之药”为可以“破两边之病,病除药遣,偏去中忘,都无所有”。[4]570这是典型佛教四句模式,论证的方式有很浓厚的三论宗色彩。因吉藏立其三论宗旨广破不立,即破即立。这种否定性破执的方法,作为了一般方法论来把握真理。所以吉藏说:“破邪亦即是申正,以破有无二见,得脱二见,即是解脱。”[7]16而这种“破”的彻底则是连“破”本身的否定,吉藏认为若是相对于偏执来说显出的“尽偏中”虽是尽了偏执,还是有“中”的名相, 所以他进而提出“偏病既除,中亦不立。非偏非中,为出处众生强名为中,谓绝待中”[8]14的认识。吉藏对“中”的见解是在能诠之教的基础上的,随其宗旨来说若是病除却了,则“教药亦尽”,说“中”亦是教,最终是归其无所得的境地。
可以看出,李荣从“玄”到“重玄”的论述过程与吉藏思想极为相似,以“双遣双非”的论述模式注“重玄”,“玄”之否定意味类似三论以破为立,其实已经偏离了老子的原意。李荣较此前重玄学者更为深刻之处在于“三翻不足言其极,四句未可致其源”。[4]566认为这种重玄的思想方法不局限于几个步骤,而是引导出了一种可不断进行的否定式的认知方式,是为了到达那个“虚通无碍”的本体处,主客体都不滞,不断地否认两端,至完全的绝对。任继愈先生认为李荣的重玄三翻说与龙树中道思想有比较直接的渊源。[9]256他引用了龙树在《大智度论》里对中道的阐述“此般若波罗蜜是一边,此非般若波罗蜜是一边,离是二边行中道,是名般若波罗蜜。如是等二门,广说无量般若波罗蜜相。”认为佛教在“非有非无”之后,仍有“般若波罗蜜”与“非般若波罗蜜”相对,仍然是两边。因此还要“非非有非无”,以此破了又破,致于“广说无量般若波罗蜜”无所破的“言忘虑绝”的至虚空无的境界,才是绝对的真理。在佛教传入中国后,僧肇在此基础上提出“损之又损”以至于“无损”的双遣法,汤一介先生引元康疏认为,僧肇以般若为一玄但未至极,所以涅槃为又玄,互为因果,可证“重玄”。[10]这种依次由浅至深否定过程在吉藏四重二谛思想上,表现的更为细致。如其释义四重二谛,因世谛悟真谛,而每重的世谛都建立在上重真谛的否定上,其真谛也由“空无自性”到第二重的“非有非无之不二”,再到第三重“非二非不二”,再到最后一重即是彻底之否定前三重“前三皆世谛,不三为真谛。”[11]15以连续之否定的逻辑而显出无所得的实相,即“绝名字,断思虑。理不可得,不可说。” 而之所以李荣能将三论宗的思维方式援入道教,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即是三论宗与重玄对其本体实相的认知即“毕竟空”与“重玄之域”有其融通之处。
在阐述如何运用三翻说来体认道体时,李荣发展了重玄学的“三一”说。最早是道经《太平经》提出了“三一”说,指的是天地人三者合一致太平,精气神合一以长生的基本认识,后世多用这种模式来阐述道教思想。到了臧玄靖建构的“三一”说对唐朝重玄学者有重要的启示,他认为本体的无形无声无色的性质,表现在人的现象即是精气神,道体杳冥却非顽空。他力图找到本体与现象的连接,即“精气神”。李荣并没有像成玄英一样沿用臧玄靖“精气神”之论,而是专通过注解老子的“夷”“希”“微”来阐述自己的观点。认为:“一不自一,由三故一,三不自三,由一故三。”[4]581道作为本体“一”,有无形、无声、无色之“三”的属性,本体不自有。因为其属性而存在,分别的这些属性也不自有,因有本体而存在。所以他推出了“三不成三则无三,一不成一则无一”[4]581的判断,认为“一”与“三”相互包含其中,不可称其为独立的存在。任继愈先生称李荣的这种思想是突破了形式逻辑的“整体就是局部的结合”命题,具有质变和辩证逻辑的因素,较前诸家有所深化和提高。[9]258以此,李荣说:“执三执一,翻滞玄通之教也。”[4]581一与三都是需要遣的对象。较前人不同,李荣抛开了精气神旨在阐明“无一无三”的超越本体超越属性之理,阐明本体的真相。这样的论证似于吉藏“三法一体”,即以一切物“体成”“义成”“名成”三法互成,用中道性空与三法和物的关系联系起来,认为“亦有亦空,非有非空”。由此可见,李荣的重玄与吉藏之中道思想较前人都有较思辨性的内涵提升。
而这思辨的目的在于阐明道本体的属性,李荣说:“道者,虚极之理也”[4]564。“道”不可以“有无分其象”或以“上下格其真”。李荣特别之处则是通过双遣“有”“无”来确立起了“虚极之理”。“虚”则包纳了有无的统一,万物万象也囊括其中。所以李荣认为这样的道体,是具有最抽象的一般特征的,是“无分别性”的,如他说是不以“分内外”,不依“有无定形质”,不用“阴阳定气象”,不靠“因缘究根叶”[4]564。在此意义上,李荣否认了道本体具有空间广延性。所以,李荣认为这样的道体不依赖人们的感觉,不是我们的感觉对象,是不可名辩的。其言:“不可以言言,言之者非道,不可以识识,识之者乖真,故云不可识。”[4]583人们惯于“分别式”的思想准则与行为法式条律是无法把握具有超越分别性的抽象的道本体。李荣实是延续了老子对超验而不可言说的“道”的认识。他认为,“多言”也是“滞”的表现,“多言则丧道”。言语无法把握思维之外的对象,若是执着用言语把握,则越离道越远,所以只有“得意忘言”。“忘言契理故言得”,唯有不凭借言语把握到的才是真正的道体的性质,颇有魏晋玄学“得意忘言”意味。李荣认为重玄认识之至是“理冥真寂”,这正如上文所引吉藏的“理不可得,不可说”,是忘言绝虑之寂。而这样道体的建立,是旨在为人在道教修炼实践提供一个合理的理论基础出发点。
从道教的重玄学内部发展逻辑来看,用重玄方式作为体证真道,是道教从神仙道教转向精神超越的重要起始。其深受魏晋玄学重选《庄子》且以庄注老的转变,重玄家们亦是转向了对个体精神世界解脱法的注重。隋唐之际《本际经》用重玄方法的开出了“无本可反”当下即是解脱的观点,否认了精神实体的存在。其后成玄英接续这样的路线,否认了真君真宰,否定一切价值与道德约束进行个人精神超脱之路。到了李荣的重玄思想可以说是重玄学发展的必然,他在寻找重玄解脱后有可立之处,从“无本可反”到“虚极”道体,重新给予了有可寄托的肯定性的精神实体。可以说,李荣的重玄思想是在接受三论思想基础上,沿着道教义理的自身内在矛盾的不断发展与改进的结果。
二、道用论
对于“理”,道教学者开始所表达的只是规则性的理解。而自李荣开始,开启了以“理”释“道”,把“理”的内涵上升到了“道”的地位,其言:“道者,虚极之理也。”直接用“理”来规定了“道”,把“理”作为“道”的体现。李大华先生认为重玄学派的论理过程就是道的具体化过程,这是道教的自我超迈,让“道”这个最高本体不脱离具体事物,存在于具体事物中。[12]在李荣这里,“理”是“道”在现实世界的表现。同时,李荣也继承汉代的元气生发论,以“元气”作为万物发生的根源。所以在李荣看来,道体在落实到现象世界的宇宙观上就成了一幅理气二元合一的图景。宇宙始于“一气之未分”,从无形无相到动而生天生地。
道教不同于佛教之处就在于其有一套以“气”为媒介的宇宙化生论。如李荣认为我们的现实世界是一个经历由无生有又归于无的过程性存在,“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从无生有,自有归无,故曰相生”。[4]567这个过程由无生有,由静到动,起体为用,李荣称之为“通生”。其造化之功,由“虚中动气”,即由道生元气,元气又分了阴阳两气,通过阴阳二气的运转推移,有了天地人,随之生万物。概而言之,这个过程即是:道→元气→阴阳→天地人→万物。李荣把“元气”作为媒介,将不可言说的“道”拉到了具体可“观”的“物”性存在上。他对“道生物”的勾画,填补了从“无”生具体之“有”理论空白,同时也使“道”具备了气论的意味。作为道教理论而言,构建“虚中动气”的宇宙生成论的气化模式是重要的,因为只有作为本体性质的“道”依于气化论才可作为可以为人把握的内容。陈鼓应先生提出:“老子的道论是开创了中国哲学史的形而上学传统,其后,黄老及庄子等进一步发展了这一传统,并提出气论来补充道论之不足。气化论的提出主要是为了便于说明道化万物的过程,以及万物之间的统一性。因此,气一般是做为道和万物之间的中间环节。”[13]19-20李荣的注本是基于河上公的注,河上公是以元气解道的典型,他的重心是落在气的运动与养生实践体道上,所以李荣在他的宇宙观和修养论上很大程度是延续了这种以“气”来沟通万物与“道”本体的论调,但他也没有忽视于与超越道体的连接。
其体用观除了宇宙化生论之外,还表现在对“教”与“理”关系的论说。李荣说:“教具文字为有也,理绝名言为无也”。[4]578“教”是以人们可把握的文字形式落实经验的“理”,“教”的实现具体表现为圣人的教化。李荣模仿佛教的“真谛”与“俗谛”的二谛模式区分了“非常道”与“常俗之道”,但不同在于他认为“常俗之道”是人们追寻礼仪,浮华,名利的价值取向。李荣看到了人的社会生活被欲望牵袭而儒学却陷入僵化的现状,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大圣老君,痛时命之大谬,愍至道之崩沦,欲抑末而崇本,息浇以归淳。”[4]616因此,李荣“教”的实行是彻底否定“常俗之道”,认为其是不可能通向“非常道”的,如其言“以俗观之,垢净善恶,咸以为有,以道观之,并悉是空,故云反也。”[4]663若在俗中求真,只会失真,李荣说:“顺俗求道,失之于真,反俗修德,入之于妙。”[4]649这是不同于佛教可由俗谛悟入真谛的,李荣对俗的态度是全盘否定的。所以李荣的“教”的目的正如其言“圣人设教,义在无为,欲使反浇还淳,去华归实也”[4]665。但“教”也并非是“理”,理是“超于言象”的,所以正如“病去药遣”之法,“教”亦不可执,“劝以守中之得,使无滞教,内契忘言”[4]572。李荣这样的教理区分可谓是脱胎于吉藏的二谛说,吉藏亦是在体用观基础上提出“于谛”与“教谛”。体是超绝四句的实相,用则是“一都随顺众生故说有二谛,即教谛”[14]103。“于谛”是“教谛”的所依。进而,认为真俗二谛是教谛而非理,是为教化众生以“对缘破”的方便,如“二谛唯是教门,不关境理”[11]15。吉藏引其师法郎《二谛疏》中“道非有无,寄有无以显道。理非一二,因一二以明理。故知二谛是教也。”[14]86认为虽理非二谛,但是可通二谛进行阐述的,更为明确了二谛为“教”的立场。再者,吉藏也再次强调了至理的不可言说,他说:“一往开教理者,教有言说,理不可说。”[14]15因此,“教”更是不可执的,他说:“住教遗理,岂非失也?”[14]79认为如来说二谛旨在不二之道,“有方便者,闻二悟不二,识理悟教,名教谛”[14]79。相较于李荣否认了俗道中有真道而将“教”寄于圣人的“开方设教”,吉藏则认为二谛是有相待性的,即真谛显俗谛同时以俗谛显真谛。表现在他的四重二谛里,第一重以因缘生法之有的世谛悟空无自性的真谛,第二重以空有之二悟不二,第三重以亦二亦不二悟非二非不二,吉藏认为第四重即是自教门入至理,终显无所得之理。可见,李荣的教理之分多借鉴于吉藏对二谛的分析,但还是有其不同之处。
传统道德的虚伪性和残酷性,使李荣感悟到经国理家和修身立行的迫切。他所处的初唐时期正是统治者扶植道家道教的时期,作为负有“应诏佐明君”责任感的道士,李荣站到了“民”的立场,对统治者提出施政原则,企图匡正君德来限制君权的滥用。如其言:“君上守质,臣下归淳。” 再如“欲劝帝王抱式于道德、取则于天地也”。也就是,在他看来,人文主义是本质,社会秩序应为“理”所定,所以理国治安在于统治者行正道,合于“道”。也唯此,才可使得社会趋向和谐。李荣实际是为了给社会伦理找一个精神依据,即“理”。《老子》本是反思历史反思政治制度的理念,李荣继续了作为道家原本的理国关切,所以其理论作为道教的色彩反而有所淡化。他希冀于“人人皆自足,家家俱有道”[4]665,认为人们都“相忘于道术”才是“道”最完满的实现。但李荣在阐述社会政治理论的实践时,没有放弃他作为一个道士的宗教意识,带入了一个有意志的天命的观念,认为“天道虽远,玄鉴孔明。赏善罚恶,著在于冥司”,主张天道于社会有“福善祸淫”的作用,以之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但在这一点上实是与他的道体论相冲突的。但这并不是李荣关切的重点,李荣建立一个“虚极”道体来“推天道以明人事”,其重心还是转换到人的内在精神的追求上,由本体论不断推进到修养论上。
三、修道论
李荣洞察到了道生之任其本性自然的非目的性,提出了物性与人性的自足,如其言:“道则信之以独化,物则称之于自然。”[4]608再如“不逆物性,任之自然,斯大顺也”。[4]649万物有其自身的规律性,而道的创生正是这种规律的体现。李荣认为对于“道”本体来说,是常寂不动的,之所以会“虚中动气”,是因为“应物斯动,化被万方”[4]612,“为化众生”才能动能寂。正是因为顺应了万物之性,才有了创生的过程。而又因为“道”具有“反”的运动特性,所以“自有归无”是形成“道”创生的一个循坏过程部分。如陈鼓应先生归纳老子开创的道家思维方式为两种“一是推天道而明人事及天地人一体观,一是对立及循环观”。[13]14李荣接续了这种思维方式,认为万物从物生,也当复归于道。他把这种关系称为“母子相守”,守母归根。同时这也是他养生论的理论基础,万物只有具有道性的复归的特征,才有修行的必要与可能。“道”本是具有整体性规律的出发点,本身是不可分割的联系,而人们对具体的事物的把握却往往建立在分别式、对立式的认识意识上,在《老子》里运用了很多对立的言辞力求人们认识到超越这种认识的必要,《庄子》更是力主破除是非观念而“齐物”。李荣注解多发挥这种方式,如“和以不和标称,孝因不孝立名也”[4]588。力图让人们去分别以归于“道”,他说:“毁誉齐一,利害不能干,荣誉同忘,贵贱无由得,能行此者,可以天下贵。”[4]639不仅是把相对的观念等同看待,更重要的是超越这种对象。这也是体现李荣以庄解老之处,正如他总结的“丧偶而无对,故言独立。”[4]597同于庄子“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庄子·齐物论》)只有破除是非,分别才可实现超越中的复归。
李荣认为,道在人身上的存在形式即是“性”。“心性”何以复归?重玄学家们都认为“心性”是可以从个人的存在通达到道的整体性存在的,如成玄英认为“心神凝寂”,人就可复“真性”。重玄家们在热衷讨论的“道性”问题,实是借用佛教“佛性”之词旨,在人身上寻找可得道的根据。而这种道性是基于人有“识”,宋文明阐明了重玄家的基本趋向,他说认为一切有“识”的存在都是具有道性的。因人有心识,而心识又有明暗程度不同,所以能取舍。他以识性规定道性,随之排除了水石这类无识性的物有道性的可能。李荣认为“争由心起”,其言“言人一心攀缘万境,其事非一,故曰芸芸。” 心识一旦滞于外,则会失其真性。因此李荣致力于“虚心”,在其“识”上下功夫。李荣认为“人之受生,咸资始于道德。同禀气于阴阳,而皎昧异其灵,静躁殊其性”[4]565。人从道而来,受生时自然也秉承了道性,对性的描述似是继承成玄英而来,如“性无染浊,体实常存,质真也”。[4]620而不同于成玄英的是,李荣承认了人禀性里属于感官的欲望本能。这些本能促使人们有了得失、情欲,所以对于本能的态度是承认它存在的合理性,但需要“远欲制情”。对于认识“真性”的方法,李荣提出“内视反照,复归其明”[4]633向人自身内求的认识方式,认为“内明体同虚寂者”才是上德。内求能够体证虚寂之道,道性的无分性和整体性决定了其不能为我们的感官把握的对象,但可以通过心性,以内求作为认识道性的方式,即是直观体悟,李荣称这种个人直观体认为“体之”“洞之”“玄悟”[4]581。卢国龙先生理解这种认知方式为“对道的认识(知)和本身(体)混而为一”。[5]263因为人由道生,继承了道性,所以李荣说“人性自足”,认为人可以去体证道体。这较似于老子的“玄同论”,老子所说“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为玄同。”(《老子》第五十六章)即是对道的直观把握。正如康中乾先生认为把握“道”唯一方式就是理性直观法,人们必须排除感性经验和理性认识的干扰和影响,在主体纯净、清净环境中直接体悟到整体性的“道”以及它的特征。[15]这是与经验世界相背的方式,要做到这种内求,李荣的基本立场是从人的身心不滞,皆“导之以归虚静”,落实于自身与外界环境都“损之又损”的双遣法,即是行“重玄之道”。心体的统一并不是靠剥夺官能来实现,不能常态的感官功能作为途径,所以需要对这种常态的意识进行“双遣”以归“虚静”。所以李荣反复提到“虚心”,即在主观上似庄子的“坐忘”来破除成心,他说:“明虚心实腹,坐忘合道。”[4]652同时又于客观上破除具体对象与目的,他说:“有累之业遣去也,无为之道来取也。”[4]579人能做到不滞于外身,则自然可体认道。同时,他也讨论“智慧”与“烦恼”的关系,认为它们是“抗兵相加”的,归结于“因缘不会,智慧不起”[4]654。企图消除烦恼已经是在肯定它了,如庄子“类与不类,相与为类”的看法。所以要“内亡智慧”从而认识“因缘之皆假,达理教之俱空”的至理,同时也就消解了烦恼与智慧的对立关系。鸠摩罗什曾指出不离不断烦恼而入涅槃,认为“烦恼即涅槃,故不待断而入也”[16]。他以中道精神说明烦恼与涅槃不二。李荣将其达到之境界直接借用佛教词汇义理进行阐述“所照之境,触境皆空,能鉴之智,无智不寂,能所俱泯,境智同忘,不知也”[4]655。
三论宗对“佛性”的讨论更为详尽,吉藏以中道理解佛性,认为“离断常二见,行于圣中道,见于佛性。”[14]86吉藏深入论证众生佛性分为两个方面:首先,人有“心迷”继而有“觉悟之理”,可由迷尽悟。以此草木无“迷”则无佛性。其次,认为众生同草木皆从无所得之理,所以在此意义上皆有佛性,如“以依正不二故,众生有佛性,则草木有佛性”[11]40。吉藏认为“佛性”之说亦是方便假言,实则是超越真俗二谛。吉藏进行了会教,将诸多佛教概念如真如,涅槃等等同于“佛性”。在此意义上,吉藏同李荣一样,将“见性”引向了心的工夫上,他说:“生心动念,即便是魔。若怀无所寄,方为法尔。”[17]更有说“心不能缘”在四句上,体现佛教由关注“空”转向心性的关切上。
在心性修养之外,道教一贯是有精气神三位一体的养生之道。气即是广义的形,心则是主神的。李荣认为人是“禀气而生”的存在,同时神形关系即心气的关系是“智与道合,神与形同,故曰无离。”[4]576心气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可看出他的修养论始终都是围绕心气两方面阐述,并且始终是心气不二趋向统一的,如其言:“一身心则纯合不散,专气也,得长生之道。”[4]576卢国龙先生提出从唐玄宗开始就有了一种新的体道论观点,第一是“心性修养可以复归道本”。第二为“从本降迹”相对应的“摄迹归本”的养气可以复归生命本初,以全生或长生。[5]435李荣的修养学说也是从这两个方面进行阐述的。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养生论是摒弃了神秘因素而立足身体健康之道的。其言:“精散则身枯,身枯则命竭。含德之人,外情欲而爱其精,去劳弊而宝其气。”[4]636主张人们除去嗜欲等不良的行为与念头,就可以获得健康长寿,从而踏实地安顿自己的现世生命。李荣说:“若能存之以道,纳之以气,气续则命不绝,道在则寿自长,故云不属天地”。[18]在此,李荣是肯定了人能够通过自身的修养来决定自己的命运的,而养生的目的还是在于体证道体,所以他进而提出了“息心以归本”。
李荣的修养论是“现世”的,因为他所主张的在解决生死问题以安顿人们生命是“现世”的。他否定佛教因果轮回的观点,认为“有轮转处生死,皆为邪也,无轮转绝生地,为天下正也”。[4]626在他看来,有轮回所以有生死的观念是“失于真性”的。李荣说:“有生有死不可言道。”[4]572他认为这种生死观仍然是需要被“双遣”被超越的,所以他倡导“绝生死”。但他也承认人需要面对生死的过程,如其言:“物则有生有死,人则有存有亡者,皆为天也。”[4]508生死的过程是人不可避免的过程。在此,可以看出他放弃了自“上清派”以来崇尚的肉体上长生不死的观念。作为一个朴素踏实面对生死问题的道士,他把最终的生命归宿安顿在“死而不亡”上。他说:“修道者以百年将尽之身,获万劫无期之寿,此亦死而不亡也。”[4]508李荣的超凡入圣学说是归根于精神的超越,认为肉身只可尽养身健体之力,而人可以通过精神境界来体认道体,达到天人合一。如其言:“空其形神,丧于物我,出无根、气聚不以为生,入无窍、气散不以为死,不死不生。”[4]572李荣吸收佛教的人身是缘起的认识,认为“肉身非实,人本无形,我本无身”将人身称之为“虚假之生身”。因而人当“观身非有,”随任变化,齐一生死,达生死不二之理。最终的精神解脱法上,李荣融通了庄学与佛教生死的认识作为重玄最终指向的精神解脱之路。李荣超越生死而归旨于人精神内在超越多是受佛教影响,吉藏十分重视八不中道,认为八不统摄一切佛法是“诸佛之中心,众圣之行处”[11]25。因为从因果说有无,则会执着在生灭、常断、一异、来去等现象上。吉藏力主破此八邪见,将八不与四重二谛等同之,第一重以生灭为俗,不生灭为真;第二重一生灭不生灭为俗,非生灭不生灭为真;第三重将生灭与不生灭看做二与不二皆俗,以非二非不二为真;进而不三为真。[7]28以此来明不生不灭等之理,不落于常见。生死是人最重要的现象,也是在人解脱之法上无法逃避的问题。从不执有无到一切现象,最终忘言绝虑到达无所得的“毕竟空”境界。李荣重玄思想下人的解脱之道与三论宗不谋而合。李荣之前的道教炼养多是重炼形,而在李荣这有了一个重大的转变,即转到对人自身的心性操练为主的心气统一,以人的精神超越为目的。正是由于他的这个理论转变,影响了道教后世兴起的性命双修内丹学的基本样态。这也是佛道逐渐趋于一致之处,道教愈发转移重心于精神的超越于心性的炼养,佛教渐将主体空观与心性结合。而李荣完全之否认肉身解脱而偏向于心性之操练,很大程度是得益于三论宗中观哲学指明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