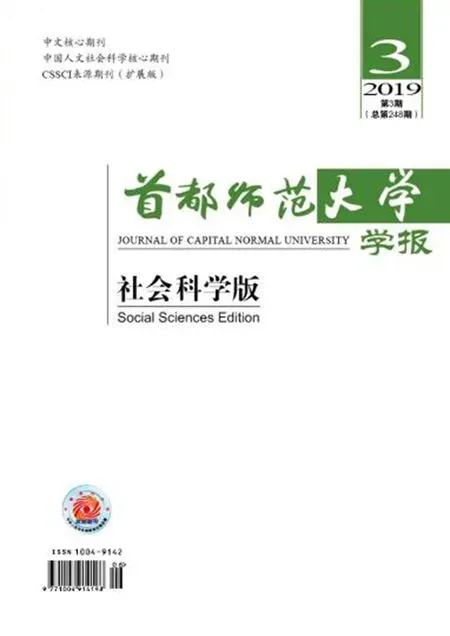身体与文体之间
——重读郭沫若历史剧《屈原》
2019-02-22周海波
周海波
1942年元旦过后不久,郭沫若开始奋笔疾书,写作历史剧《屈原》,到1月11日,“夜将《屈原》完成,全体颇为满意,全出意想之外。……计算二日开始执笔至今,恰好十日,得原稿一二六页,……真是愉快”[注]郭沫若:《我怎样写五幕史剧〈屈原〉》,《郭沫若剧作全集》,第1卷,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年版,第487页。。郭沫若在自己的日记中一方面表示对剧作“颇为满意”,另一方面又表示整个剧作“全出意想之外”,创作完成的作品与其最初的构思差别之大,出乎意料,完全打破了开始设计的情节和场面,“各幕及各项情节差不多完全是在写作中逐渐涌出来的”[注]郭沫若:《我怎样写五幕史剧〈屈原〉》,《郭沫若剧作全集》,第1卷,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年版,第485页。。郭沫若在创作过程中所打破的原来设计的内容,他本人已经在有关《屈原》的创作谈中有详尽的阐述,围绕这种“意想之外”的各种讨论和阐述,尤其将作品与时代的特殊背景的联系,学术界已经进行了大量讨论,而关于郭沫若为什么要打破这种设计,这种创作变化与其作品文体特征的关联,仍需要进一步研究。
一、阐释的空间:文本理解的可能性
历史剧《屈原》于1942年1月至2月《中央日报》发表,3月,又由文林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在此期间,历史学家侯外庐曾作《屈原思想的秘密》,认为屈原的思想中存在矛盾,而郭沫若在创作中并没有真正还原屈原的真实形象。由此开始,学术界、戏剧界一直围绕着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展开《屈原》的讨论,形成了不同的甚至针锋相对的观点。从已有的研究来看,当人们把《屈原》置于抗战语境进行考察时,着重把握的是作品与政治的关系,特别强调《屈原》“借古讽今”的意义。特殊的时代背景与创作题材之间的关系,给人们解读《屈原》提供了诸多的可能性,由此更多地看到了作品的现实讽喻意义,看到了作品对时代的呼应。这种看重作品的现实讽喻意义的观点,应当说对作品与时代的把握是非常准确的,非常明确地意识到郭沫若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创作这部作品的目的。但这种观点也往往忽略了文本自身,从某种观念出发对作品进行阐释。1942年10月17日,郭沫若在致杨树达的信中曾说:“迩来只就历史逸事编为剧本,已成《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诸种,实一逃荒解闷之策,不足以登大雅。”[注]郭沫若:《致杨树达》,黄淳浩编:《郭沫若书集集》(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90页。作者本人的解释虽然不能等同于作品本身,一方面作家有其客气谦虚的成份,另一方面作品艺术上的客观效果可能是作家无法把握的。但是,面对如此重大题材和具有重要美学意义的作品,在作者眼中却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逃荒解闷之策”,这与人们对作品的分析评论格格不入。某种意义上说,郭沫若创作《屈原》的初衷与评论界学术界的较大出入,构成了作品阐释的矛盾现象,为我们重新解读作品提供了足够的空间。
人们之所以将《屈原》的现实讽喻意义突出到特殊的高度,也与郭沫若本人后来对作品不断修改有关。金宏宇在《〈屈原〉版(文)本演进考释》一文中指出,郭沫若对《屈原》的两次重要修改,主要涉及对剧情和细节方面的改动,这些改动在“古”与“今”、“事”与“似”之间的调整中,逐渐使剧本在文本世界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的关系结构中,进一步确立作品借战国时代的故事来表现抗战时期的现实主题。在这些修改中,作品所呈现的屈原性格与思想更加趋于完整。[注]金宏宇:《〈屈原〉版(文)本演进考释》,《中国文学研究》,2007年第3期。也就是说,作家在几次重要修改过程中,突出了人物与现实的关系,将屈原的现实政治性通过文本获得了与历史真实的相似性表现。《屈原》虽然是历史剧,但作为戏剧的主要功能是“发展历史的精神”,是在戏剧文本的创造中传达出某种历史意识及其这种意识所呈现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戏剧性。从这个意义上再看郭沫若对原来设计的剧本情节的修改,以至于最后作品“全出意想之外”,正是对《屈原》戏剧性的不断调整。从原来的设计看,郭沫若过于注重屈原的生平经历,试图表达屈原一生经历的重大事件,去完成一位历史学家所要做的事情。而最终的文本却以屈原一天内的命运转折为题材,表现了屈原被陷害之后的情感变化和人生归宿。郭沫若之所以进行这种调整,主要从强化戏剧冲突的角度出发,将人物立于戏剧冲突的主要位置,以动作作为表现人物的主要手段。这种调整不仅使剧情更加集中、矛盾冲突更加激烈,而且更强调了从发掘与发展历史精神的角度强化人物的戏剧感。
近些年来,人们开始重视对戏剧文本的解读,试图寻找打开《屈原》的新的方式。当政治性解读和文化解读不能完全阐释《屈原》时,人们试图回归到戏剧本体,从戏剧的矛盾冲突以及艺术模式等方面寻找答案。沈庆利在《郭沫若〈屈原〉:性与政治的偷情》一文中认为,郭沫若在作品中“将政治、爱情乃至‘性’一类的‘传奇’巧妙地扭结在一起”,“最大限度地刺激起人们敏感的神经”,从而发现了《屈原》的“历史消费主义”[注]沈庆利:《郭沫若〈屈原〉:性与政治的偷情》,《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08年第1期。现象。刘奎在《情感教育剧:〈屈原〉的形式与政治》中从“美学与伦理的双重空间”打开了作为历史剧文体形式的剧本空间,在深入探究“情感与形式”的问题中发现了“情感教育剧”的美学意义。刘奎论文的突破在于,他不仅没有回避政治与文学的关系,而且在回答抗战的政治问题的同时,从情感教育这一独特角度讨论了《屈原》戏剧文体的本质特征,并恰到好处地论述了情感在推动《屈原》戏剧情节发展中的意义,突出了“雷电颂”将“诗人内在的愤怒、激情等强烈情感,不仅经由独白而得到宣泄,也转化为了驱使万物的动力,情感因而有可能成为一种有效的政治或社会能量”[注]刘奎:《情感教育剧:〈屈原〉的形式与政治》,《文学评论》,2017年第2期。。
毫无疑问,无论人们怎样看待《屈原》的现实讽喻,都没有改变其现实政治的属性,认定《屈原》是在40年代抗战政治背景下的一次目的性明确的创作。但从单纯的政治性考察,到对剧作的情感、性等问题的涉足,研究角度与方法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开始趋向对剧本文体的讨论,人们试图从剧作的艺术形式方面寻找郭沫若创作的美学意义。当然,创作《屈原》时的郭沫若已经不仅仅是一位诗人,而且也是以一位剧作家的身份进行《屈原》等戏剧的创作的。因而,讨论《屈原》的文本创造,就不仅是关注剧作的诗的特征,也不仅是关注其浪漫主义艺术风格,而是回到戏剧文体的自身,讨论戏剧艺术的创造。在这方面,沈庆利已经注意到了《屈原》“情节设置的不合情理”“忠奸对立”以及“贞女牺牲”的原型模式,从而判断《屈原》是一部“大众审美中的‘政治剧诗’”。[注]沈庆利:《现代视界与传统魅惑——重读郭沫若历史剧〈屈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第4期。他与刘奎一样接触到了剧本文体比较深入的一些问题,并在这些问题的探讨中涉及到了戏剧研究的核心内容。无论刘奎发现的《屈原》作为情感教育剧的文体意义,还是沈庆利论述的文体意义上的戏剧模式,都能够触及戏剧文体,是在戏剧的艺术范畴讨论问题。
二、身体作为文体的隐喻
首先从人们都非常关注的剧情突变的第二幕说起。《屈原》第二幕是剧情突变的一幕“宫廷戏”,故事发生在“楚宫内廷”,在这个联结宫内与宫外的半开放性场所,几乎聚集了矛盾双方的主要人物,屈原、南后、楚怀王、张仪、靳尚等人物渐次出场,集中表现了宫廷斗争及其政治观念的矛盾。这种剑拔弩张的矛盾却是在歌舞升平中开始的,又在歌舞声中发生巨变,剧情因此而急转直下。楚宫内廷就要进行的一场歌舞宴会,一方面为宫廷的平和氛围进行渲染,一方面又为杀机四伏的剧情进行着铺设。如果仅仅这样看第二幕戏,郭沫若的这种戏剧设计就显得比较平淡,但是,在这些平淡的故事中,屈原、南后、子兰等人的身影时隐时现,为平淡的剧情埋设了不平淡的情节。就是在这种舞台氛围中,剧情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突转,南后佯装头晕,倒在屈原怀中,屈原“因事起仓卒,且左右无人,亦急将南后扶抱”,这一幕恰恰被出现于青阳左房的楚怀王、子椒、上官大夫诸人看到。南后“及见楚怀王已见此情景”,立刻态度大翻转,“忽翻身用力挣脱”,一遍遍地大呼“你太出乎我的意外了”。随后,“宫廷淫乱”的屈原被解除职位,驱逐出楚宫。在这个剧情突变中,南后的身体可谓充满了政治的隐喻,屈原也以身体为南后提供了道具。这个以身体与身体的矛盾冲突,当然可以理解为政治斗争的表面化,是早有预谋的政治陷害。但是,如果仅仅是一部表现政治斗争的宫廷戏,作家这样书写也许并没有什么独特之处,很可能会被认为是“人为制造的冲突”。但是,这个情节直接将整个剧情引向紧张、对立的矛盾冲突,把对立的双方很快彰显于剧情的发展阶段,具有戏剧剧情发展的突变性、偶然性,增强了剧情的艺术力量。一般来说,戏剧剧情的突变往往与戏剧矛盾冲突达到高潮相关,屈原在宫廷被陷害是剧作情节发展的第一个高潮,是戏剧冲突中矛盾的双方集中表现的一幕。
不过,人们一般认为第二幕“宫廷戏”并不是剧情的最高潮,第五幕“雷电颂”才是剧情的高潮,是最具张力的一幕。认为“雷电颂”以政治抒情诗的方式展现了屈原与南后的政治斗争,将矛盾引向讽喻现实的高潮。这种将政治主张的矛盾作为戏剧冲突的观念,反映了人们戏剧艺术上的一个盲区。当人们将《屈原》解读为以屈原为代表的联齐抗秦派和以楚怀王、南后、上官大夫、张仪为代表的拒齐亲秦派的矛盾冲突时,已然将政治主张的矛盾理解为戏剧冲突,或者说将宫廷政治斗争解读为艺术。如果以这种戏剧观念看屈原与南后的关系,第二幕显然是突兀的,影响到了戏剧发展内在联系的严谨性,与第一幕以及第三幕、第四幕的剧情发生了游离。已经有学者指出过,第二幕是“全剧的关键一环”,因为这一幕“诗的品格减少了而戏剧的品格加强了”。[注]魏建:《得失之间的“戏”——郭沫若历史剧戏剧本体的再探讨》,《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6期。魏建观点的最大贡献在于,他把对历史剧的研究重新拉回到“戏剧本体”,从戏剧本体的角度理解戏剧创作。正是这样,他看到了《屈原》第二幕的动作性加强了,看到了这一幕在动作性基础上的戏剧冲突,看到了“诗”并不等于戏剧。这个观点是突破性的、建设性的,也是我们进一步理解《屈原》的重要支点。
因此,我们可以说,第二幕中屈原与南后的戏并不是政治分歧的戏剧冲突,而是在动作性基础上的身体冲突,是一幕以身体叙事为基础的宫廷戏,是在舒缓、平和的戏剧发展中构造紧张、激烈戏剧的一幕。郭沫若于1942年1月8日“上午将《屈原》第二幕草完,甚为满意”[注]郭沫若:《我怎样写五幕史剧〈屈原〉》,《郭沫若剧作全集》,第1卷,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年版,第486页。。这个“甚为满意”不仅仅在于他的意外收获,而更在于这一幕写得更具有戏剧文体的特征,更有戏的因素。所谓戏剧的“戏”,既是文本自身所呈现的动作性,包括人物语言、剧情等戏剧因素,也是舞台艺术演员的表演,是作家创作与演员演出的完美度。在第二幕的创作中,郭沫若为了突出这种动作性,特别强调了人物的身体特征,将身体与政治结合起来,既写出了身体的私密性,又表现了政治的宽广空间。屈原与南后的一幕戏,恰恰是因为身体上的冲突而完成了剧情的突变,当南后将身体倒在屈原怀中的时候,不仅仅是早已设计好的政治陷害,而且也有身体的满足,或者试图获得身体上的满足。南后倒向屈原怀中的动作是极具夸张特征的,既有政治的欲望也有身体的表现,当南后能够获得身体的满足时,身体是自我的,当身体无法获得满足时,身体变成了政治。就这场被称之为“宫廷淫乱”的戏来说,南后所表演的政治性陷害,带有鲜明的目的性,但当政治陷害诉诸于身体时,政治与身体的结合就是非常可怕的。恰恰是南后作为一位女性,她意识到身体的意义,并以身体作为自我打开的方式。所以,当她的身体倒在屈原怀中的时候,渗透了身体的多重象征意义。
还可以注意南后在陷害屈原前后分别与屈原和张仪的两段对话,这两段对话都谈到了身体,都是以身体作为人物心理与情感的表达方式的。南后与屈原有关身体的对话,是在屈原进宫后不久,他与南后之间就南后的儿子子兰的身体进行了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南后反复说过子兰因为身体衰弱、容易出毛病,而屈原则回答南后说:“公子子兰很聪明,只要身体健康,随后慢慢学都可以学得来。”屈原的回答显然与南后的意思不相对应,南后想表达的是子兰这个孩子“真是难养”,是让屈原注意子兰身体所带来的问题,而屈原的回答则是只要身体好了,“功课可以慢慢学”,并没有明白南后所说的身体衰弱包含的意思。这种对话的错位形成了内在的张力,戏剧冲突也在这种不经意间开始形成。南后让屈原到宫里来看歌舞演出,却对屈原大谈身体的事情,而当屈原将对话引到关于南后让他进宫的目的后不久,南后却不再谈论子兰的身体,而将话题转向屈原的诗,赞美屈原诗中的辞句是多么芬芳、甜蜜、优美、动人,这种赞美虽然带有夸张的成分,却不失大体。但屈原的回答却再次出现与南后的怪诞不对应:“啊,南后,你实在太使我感激了。你请让我冒昧地说几句吧:我有好些诗,其实是你给我的。南后,你有好些地方值得我们赞美,你有好些地方使我们男子有愧须眉。我是常常得到这些感觉,而且把这些感觉化成了诗的。我的诗假如还有些可取的地方,容恕我冒昧吧,南后,多是你给我的!”这种献媚式的夸奖可以理解为诗人的语言,但这种夸张性的赞美其实带有对南后身体的赞美,恰恰流露出屈原对南后的真实态度。
屈原自己说他的一些诗是写给南后的,从作品所叙述的语境来看,这些诗应当就是第一幕中他读给宋玉的《橘颂》。人们一般认为《屈原》第一幕是写屈原对宋玉的期望,是将独立不移、坚贞顽强的品格传授给宋玉的,从屈原所说的《橘颂》是为宋玉所写的话中,可以判断屈原对宋玉能够形成完满人格有所期望。在这里,屈原对宋玉的期望有一个值得深思的假借,当宋玉展读完了《橘颂》的后半部分问屈原“你这真是为我写的吗”时,屈原回答说:“是,是为你写的。”当宋玉再次问“先生这首《橘颂》是可以给我的吧”时,屈原又说过另一句话:“我为你写的诗,怎么会不给你?”这里就更明确地告诉人们,《橘颂》是屈原写给宋玉的,却并不一定是写宋玉的。这两层意思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同时,我们还应当注意的是,屈原在与宋玉的对话中,“仍不断抚琴,时断时续”,而当宋玉说自己“怎么当得起”时,屈原则说得更明确了:“我希望你当得起。”这里可以明确的一点是,宋玉至少在现时的语境中是无法“当得起”屈原所写的诗的,也不可能“当得起”园中的橘树。那么,既然宋玉无法当得起,这里所说的就是借宋玉而完成的一种寄托,这种寄托就是第二幕中屈原对南后所说的那番颂扬的话。我们注意到,《橘颂》所写的橘是一种女性化的象征,除诗的下半部分是写对青年的期望,上半部分所描写的橘的形象则给人以女性形象的联想:“多么可爱呵,圆满的果子!由青而黄,色彩多么美丽!内容洁白,芬芳无可比拟。植根深固,不怕冰地雾霏。赋性坚贞,类仁人志士。”这里描写橘树的“美丽”“洁白”“芬芳”,都是用在女性身上的,而“坚贞”一词当然也是对女性精神的概括。而当婵娟表示不喜欢南后时,屈原对她说,南后“是那样聪明、美貌,而又有才干的人”。这里所说的“聪明、美貌”又是对应他所说的橘树品格。因此可以说,屈原所期望的宋玉能“当得起”这首《橘颂》只是一种寄托,这种寄托到第二幕屈原与南后同时出现时,就可以找到准确的答案了。当屈原对南后说出“我有好些诗,其实是你给我的”这句话时,首先让人联想起屈原所描写的橘树的形象,联想起南后对屈原的诗的赞美辞。
屈原被逐出宫廷之后,南后、楚怀王和张仪之间也有一番与身体相关的对话。张仪与南后在楚怀王面前见面后,装作第一次相见,然后说出一句既是谄媚南后又是诬陷屈原的话:“我今天第一次拜见了南后,要请南后和大王恕客臣的冒昧,我才明白……屈原为什么要发疯了。”并且再一次补充说:“客臣走过不少的地方,凡是南国北国、关东关西,我们中国的地方差不多都走遍了。……我实在没有看见过,南后,你这样美貌的人啊!”这些博得女性欢喜的谄媚之词,是送给南后的,赞美南后的身体,同时又是为了加害于屈原,在南后的身体与政治之间架构一起“宫庭淫乱”剧。在楚怀王面前,张仪的这番话暗示了屈原因南后美丽的身体而疯的原因,加重屈原“淫乱”的罪行。可以看到,郭沫若在考虑戏剧的矛盾冲突及其剧情发展时,着意于以人的身体为矛盾冲突的中心,屈原对南后身体有意无意地抱扶和张仪对南后的谄媚,构成了戏剧情节发展的主要线索。第三幕写靳尚、子椒、宋玉等人对屈原被逐出宫廷之后的反应,子椒反复强调屈原的病“实在很深沉啦”,为什么病?子椒解释说:“他的太太去世了两年多,我早就劝他再讨一位,他总是拖延着。你想,一个四十岁的鳏夫子,又到了百花烂漫的春天,怎么不出乱子呢?”子椒试图通过对屈原的身体叙事强化屈原作为一个“疯子”而做出的荒唐行为,让屈原的行为成为“合理”的存在,从而达到诬陷屈原的目的。同样,那位以宫庭演出行列中的钓者,因为说自己听到了南后倒在屈原怀里时所说的话,也被作为疯子被抓进了监狱中,这里所寻找的理由同样可以作为身体叙事的材料,为屈原被陷害进行了必要的艺术补充。
三、文体作为身体的呈现
《屈原》戏剧冲突的高潮无疑是屈原在东皇太乙庙中那一幕“雷电颂”。这幕长达数十分钟的屈原独白,学术界向来有不同的评价,大多学者认为这段“雷电颂”是郭沫若40年代“女神”式抒情,也有认为这种抒情独白是作品的“不协和弦”[注]徐迟:《徐迟先生来信》,《郭沫若剧作全集》,第1卷,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年版,第499页。,已经“逸出于戏剧情节进程”,“形成了情节的中断”。[注]刘奎:《情感教育剧:〈屈原〉的形式与政治》,《文学评论》,2017年第2期。对“雷电颂”的不同认识反映出人们对《屈原》作为戏剧文体的不同理解。当人们赞同“雷电颂”时,实际上不是在赞同其戏剧文体的美学特征,而是认为这是新的《女神》,是赞同《屈原》具有诗的美学特征。徐迟认为,《屈原》的第五幕第二场应当写出屈原的“天问”,他担心“将来上演了,从演员到批评家,假使不能消化了屈原的人与诗”,全辜负了这部戏剧的。刘奎的观点直指《屈原》的戏剧结构问题,点到了要害的部门。但他紧接着又从“情感教育剧”的角度认为这种情节中断恰恰是对戏剧的突破,一个契机,能够使观众“感受其情感的强度、愤怒的力量,对浪漫的崇高主体形成某种心理认同”。理解“雷电颂”也必须从戏剧艺术的角度重新解读这篇长篇独白式语言,解读“雷电颂”的戏剧艺术。郭沫若是诗人,他的戏剧中具有诗的成分是一个被所有郭沫若研究者所认同的事实。但是,戏剧毕竟还是戏剧,不是诗,郭沫若可以以诗的方式写戏,但戏剧不等于诗。“雷电颂”之所以成为《屈原》戏剧冲突的高潮,就在于它是戏剧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在于它的诗的特征。
中国古代文体学多以诗文为主体,突出强调身体与文体的关系。北朝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中就说:“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注]颜之推:《颜氏家训》,檀作文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54页。这里以人体比喻文体,将人体的内在与外在结构等同于文体的构成要素。颜氏所指当然首先是文章的构成,包括外在的形状、面貌或者架构和内在情志、气调等在内的文体特征。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说:“夫才童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注]刘勰:《文心雕龙》,王志彬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478页。这里也将文体与人体结合在一起,把文体比喻为人体部位。所谓“正体制”也就是指文体与人体一样的正,不仅缺一不可,而且如人体部位一样生长正常。与古代诗文理论相比,中国戏剧理论出现较晚。人们一般认为汉代张衡的《西京赋》是最早的戏剧理论,而到清代的李渔那里,才有了比较系统的戏剧理论。李渔在论述戏剧创作时认为:“古人作文一篇,定有一篇之主脑”,“传奇亦然。一本戏中,有无数人名,究竟俱属陪宾”,而其中的“一人一事,即作传奇之主脑也”。[注]李渔:《闲情偶寄》,杜书赢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47页。这种对戏剧文体的认识与古代诗文理论基本一致,即把一本戏作为一篇文章来看待,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看待。李渔还将作家的戏剧创作视为附着在人体上的衣服,写戏如缝衣服。这些观点也都表达了古代戏剧理论看重戏剧人物或者把一本戏作为人以及与人相关的事物对待。如果从古代文体学的角度来看“雷电颂”,这一独白无疑是整个戏剧的“心肾”或者“神明”。它将屈原内心的积郁、愤怒以及对未来的期望都集于这段独白之中,或者说,是从第一幕“橘颂”开始的情节上的演绎,到“雷电颂”的情感抒发,是诗人屈原相同表达方式的不同情景,是同一情感表达的不同方式。也可以说,《屈原》从戏剧情节上来看,“雷电颂”正是从“橘颂”而来,是对“橘颂”的提升与强化。屈原与“颂”构成为《屈原》“一人一事”的主脑,屈原作为剧作的艺术形象,当然是全剧的“主脑”,而“颂”则是全剧作为“事”的主脑。从“橘颂”到“雷电颂”是屈原情感世界的发展变化,也是剧情的发展演变。在这个演变过程中,屈原从对南后的想象性赞美,经过宫廷“淫乱”的剧变,屈原遭到陷害,从理想的世界坠落到现实的残酷状态。屈原以“颂”的文体完成了他对生活世界的认知。在中国文学史上,《诗经》中的“雅颂”是正音,即孔子所说的“思无邪”。屈原说他的诗“是受过‘典谟训诰’、‘雅颂’之音的熏陶”,所以他的文章仍然保留了《诗经》正音的那种格调。屈原表达了这样一种意思:他的诗《橘颂》既保留了雅颂的正音,是“思无邪”的表现,但他的诗又有所突破,是正音之变,是屈原“橘颂”寄寓的一点点别的心思。当他在这首《橘颂》中抒写了他心目中的美貌、聪明的南后时,心中实际上起了那么一点“邪”的念头,而正是这种“邪”的念头让他在受到南后的陷害之后,表现出自己的非常不能理解和不能接受,同时又有所期望:“唉,南后!我真没有想出你会这样的陷害我!皇天在上,后土在下,先王先公,列祖列宗,你陷害了的不是我,是我们整个儿的楚国呵!”由此而形成最后的“雷电颂”,出现了带有强烈动作性的情感愤怒。正是这“一人一事”构成了戏剧的矛盾冲突,推动了剧情的发展。上文曾说过,屈原的“橘颂”是写给宋玉的,更是写南后的。写给宋玉是屈原对未来的期望,对一种精神品格的颂赞,写南后则是对一个女性人物的赞美,这种赞美寄寓着屈原一定的身体渴望和政治理想。但是,当他受到这个女性的陷害,当他的学生宋玉背叛了他的时候,这种期望变成了愤怒的情绪,化为“雷电颂”倾吐出来。
如果仅仅这样理解“雷电颂”,还不能真正说明其戏剧的美学意义,不能真正理解这一幕屈原的内心独白在戏剧文体创造上的独特贡献。同样,如果仅仅将“雷电颂”理解为一首长诗,是不能解释其在戏剧冲突中的意义。
在西方诗学理论中,诗起源于摹仿,摹仿是人的本能,所有的艺术都是摹仿。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对于幕仿的作品总是感到快感”[注][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53页。,由于摹仿的对象不同而区分为悲剧和喜剧。梁实秋在解释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时说:“戏剧的对象是人生,其工具是文字,其体裁是动作的。”[注]梁实秋:《戏剧艺术辨正》,《浪漫的与古典的·文学的纪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1页。亚里士多德承认戏剧是诗的一种,同时也承认悲剧是动作的摹仿,而这个动作必须是严重的,是有一定长度的。在戏剧理论中,动作不仅是指舞台演出中演员的演出动作,而更是指戏剧对动作的摹仿。我们虽然不能完全套用西方戏剧理论研究中国戏剧,但徐迟所指出的《屈原》与《李尔王》的关系,至少可以提醒我们郭沫若对西洋戏剧的熟悉程度,我们可以说,“雷电颂”是屈原在特定情景下的动作,而且是有一定长度的动作。出现在第五幕第二场的这段长独白,不仅是屈原的抒情诗,而且也是屈原作为戏剧人物的人生摹仿,是对悲剧性格的摹仿。正如梁实秋所概括戏剧的定义那样:“戏剧者,乃人的动作之模仿也。其模仿的工具为文字,其模仿的体裁乃非叙述的而是动作的。”[注]梁实秋:《戏剧艺术辨正》,《浪漫的与古典的·文学的纪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2页。如果从这一戏剧的命题出发,“雷电颂”的戏剧冲突与动作的摹仿就当另行看待。
“雷电颂”出现在《屈原》第五幕第二场,这是作品的最后一场,也是戏剧冲突的高潮。在此之前的第五幕第一场主要叙写了宋玉、子兰、婵娟等几个人物之间围绕屈原的下场而进入的辩论,尤其通过宋玉和婵娟对待屈原不同的态度,表现出二人绝然不同的人生境界。这一场戏为屈原出现在东皇太乙庙,高歌“雷电颂”进行了必要的铺垫,也为婵娟以自己的身体替代屈原进行了必要的交待。这几个人物的动作性主要表现在他们内心的世界与现实情景之间的失衡,尤其是对“橘颂”品格的重新阐释,表现了宋玉的萎缩与婵娟的张扬。剧情发展到此,宋玉无法担当得起“橘颂”已是事实,而婵娟则成为屈原期望中的独立不移品格的实践者。第五幕第二场的前半段,主要是靳尚和郑詹尹两个人为谋杀屈原进行的准备,也为屈原的“雷电颂”做了恰当的引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屈原,无论其形象,还是其举动,都具有一种内在动作性。因此,屈原出场的同时,作者所作的一段形象提示就显示出特别的意义:“屈原手足已戴刑具,颈上并系有长链,仍着其白日所着玄衣,披发,在殿中徘徊。因脚有镣行步其有限制,时而伫立睥睨,目中含有怒火。手有举动时,必两手同时举出。如无举动时,则拳曲于胸前。”这是具有相当动作性的叙述,或者说是“悲剧中的人物既借动作来摹仿,那么‘形象’的装饰必然是悲剧艺术的成分之一”[注][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58页。。虽然婵娟代替屈原而死,屈原成功逃向汉北“做一个耕田种地的农夫”,但屈原形象仍是作为悲剧人物进行艺术处理的。从早上屈原出现在橘园,朗诵《橘颂》,到夜间屈原手足带着刑具出现在东皇太乙庙,这个巨大的变化已然尽显悲剧人物特点。如果比较橘园中的屈原,那么在东皇太乙庙的屈原形象,不是颓丧与落魄,而是悲愤、崇高。橘园里的屈原“着白色便衣,巾帻”,“左手执帛书一卷,在橘林中略作逍遥”,这个典型文人形象的屈原与夜间东皇太乙庙中愤怒者屈原形成了极大的反差,而这个反差对于悲剧人物来说,是一种带有张力的动作,即人物形象自身的动作性。一个人物的两种不同形象,两处不同背景,构成了屈原这个悲剧人物在“雷电颂”时的从内到外的强力。这种力量支配人物的动作,使其向天追问过程中的每一个音符都具有强烈的内在冲突,与人物形象一起构成对动作的摹仿。
从这个意义上说,“雷电颂”之所以在舞台演出中能够产生极强的戏剧效果,不是因为“雷电颂”抒情诗的文体形式所具有的抒情力量,而是因为雷电独白所呈现出来的动作性及其戏剧冲突的艺术力量。在这里,需要重新理解什么是戏剧表现中的动作性。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认为,动作是戏剧的特殊表现手段,戏剧摹仿的对象是行为,而摹仿的方式则是动作。或者说,戏剧是行为的艺术,其表现手段则是动作,用动作去摹仿人的行为,这就是戏剧艺术的表现形态。在这里,如何理解人的动作是一个关键。根据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人的动作分为外部动作和内部动作,人的言语、独白等语言形式是一种外部动作,如屈原的“雷电颂”作为屈原的内心独白,首先是一种外部的动作,是以语言的方式传达屈原的处境、命运、情感等。但是,如果仅仅这样理解屈原的动作显然是不够的,作为动作的言语,应当具有鲜明的对话性。对话既包括两个人或两个以上的人之间的对话,还包括个人的内心对话,也就是说,屈原的内心独白本身就是具有动作性的艺术表现。这个动作来源于屈原所处的生存环境、政治环境和人际关系,具有一定的行为流动性。屈原由“橘颂”这个期望的动作到“雷电颂”这个悲愤的动作,是连续性的、发展的。第五幕第二场,当屈原出场之时,作家已经提示了屈原的形象特征及其动作,因此,当屈原展开内心独白的时候,他的外部形象与内面形象已经完美融合在一起,长篇的内心独白既具有动作性,也是对外部动作的阐释。“雷电颂”以呼告风的咆哮开始,构成了屈原(“我”)与风的心灵对话。在这个对话中,屈原再次带回到洞庭湖的思念,回到“浩浩荡荡的无边无际的伟大的力”。随后,屈原对雷的呼告承继了风的力量,从湖与海的心路历程中追寻心灵的更广阔的自由。对电的歌赞是屈原情感的进一步升华,内在张力已经将屈原的情感推到雷电轰鸣的境界,将“宇宙中的剑”和“心中的剑”融为一体,使独白的动作性更加明晰和突出。正是在与风、雷、电的心灵对话中,屈原的呐喊或者内部的动作与光明形成一体化的“宇宙的生命”。如果说这些对话带有形而上的意味,那么,在风雷电光明之后,屈原再次回到现实,开始了与“高坐神位上的”东君、大司命、少司命、湘君、湘夫人、河伯等展开了另一种形式的对话,让风雷电光明与这些庙里的神构成了一组矛盾,让这组矛盾暗示屈原的情感世界。可以看到,作家在表现屈原的精神世界和心理活动过程中,让人物内在的动作落到实处,形成戏剧冲突的内在张力。在这一点上,《屈原》与《李尔王》具有相当的共同性。
但是,与《李尔王》相比,屈原内心独白的戏剧冲突显然并不充分。在这方面,《李尔王》立意于人物的命运,将命运悲剧与内心独白结合在一起,在强烈的动作性基础上,达到了戏剧的美学效果。而“雷电颂”作为戏剧冲突的紧张性显得不足,人物的悲剧命运更让位于某种现实政治理念,这也是《屈原》紧张有余而艺术感染力尚有空间的主要问题。
如果说在古代诗文的文体学中,以身体比喻文体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一个突出特点的话,那么,将身体与文体联系在一起,对于话剧文体来说,则是更为恰切的文体关联。话剧既是一种文本创作,又是一种舞台演出,当文本移动于舞台时,演员需要以自己的身体与动作阐释剧作文本。当然,作家在创作中已经将身体与文体联系起来,以身体展示文体,以文体表现身体。在这里,作家笔下的身体与文体无法等同于戏剧舞台上演员的身体,而舞台上演员的身体当然也不能等同于戏剧文本中的身体与文体,但二者之间又存在着某些联系,是相互依存的文本关系。因此,当我们重新解读《屈原》时,不能不关注郭沫若笔下的身体与文体的关系,关注郭沫若将自我体验融入戏剧创作的艺术追求,由此才有可能更好地理解与解读《屈原》的戏剧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