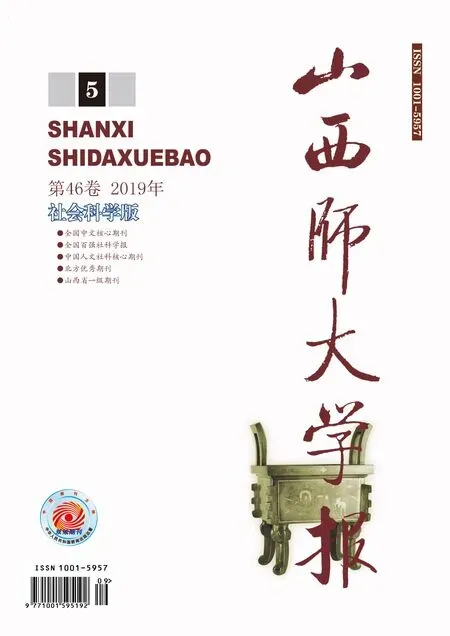1940年代解放区诗歌的美学变革
2019-02-22罗振亚
罗 振 亚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由于受重写文学史浪潮的猛烈冲击,近些年来不少评论者心中默默认同着一个奇怪的观点: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后,解放区的诗歌创作在功利观念与审美价值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与思想意蕴的积极意向探索同步,它在艺术上浅淡粗糙,走了一条日趋衰颓的下坡路。事实果真如此吗?否!那种奇怪的观点是背离历史主义批评原则的估衡误差,是文学观念错位铸成的意识迷津。无论怎么说,《讲话》后解放区诗歌创作的空前繁荣,引起了一场新诗美学的伟大变革,是谁也难以否认的客观事实。
一、艰难选择:民族心灵历史的构筑
政治与艺术的关系似乎是永远也回避不了的话题,它在大多数情境下表现为不是文学选择时代,而是时代选择文学。1940年代的中国是光明与黑暗搏斗、方生与未死交错的时代,是中华民族探求解放的时代。革命战争的紧张残酷与硝烟炮火容不得嗲声嗲气、娇媚柔婉的娱性诗生长,不需要夜莺般歌唱的琴师,而是急切地呼唤着杜鹃啼血与鼓手迸出。在时代与现实的感召下,那些具有强烈艺术良知的诗人们的诗歌观念发生了惊人的蝉蜕与变化,他们已无法再把写诗当作纯个人化的技术操作,而开始在纯诗之外的宽阔地带寻找缪斯与时代、现实重新交合的途径。一度停驻于象牙塔中的李金发此时唾骂周作人“认贼作父”[1],甘当汉奸;曾经沉迷于风花雪月、如烟似梦的何其芳也抛弃了云、月,而要“吱吱喳喳的发议论”(《成都,让我把你摇醒》);现代派诗人徐迟则更公开地表明,战争“炸死了抒情”[2],逼走了人们抒写自然的情怀。于是,走出书斋、亭子间,走向火热斗争生活与战场的诗化作了匕首与投枪,化作了旗帜与炸弹;在人间烟火味十足的生活与生命气息的拂动中,缪斯的功利效能被高扬至峰巅状态,它以民族奋起解放战斗雄姿与心态情绪由表及里、由形而质的多方位展现,与时代豪迈高昂的心灵脉动达到了谐和共振,在时代氛围统摄的救亡革命总主题下,传递出一曲曲色调斑斓的向上情思音响。
在《讲话》的深入生活深入工农兵的精神指导下,不少诗歌直接源于生活情热,以现实土壤里新斗争新风貌的歌咏,升腾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感受、期待、渴盼的心音。若说国统区诗歌侧重暴露黑暗,那么此时的解放区诗歌则更善于表现革命者在战争中的英雄行为与高尚品格。张志民的《欢喜》可视为这时期诗歌情思的典型缩影。“雨停了!天晴了/杨柳梢儿发育了/翻身的日子过红了。”诗趣盎然的俊美观照中,闪动着生活变化与人民命运向解放转换带来的明朗与喜悦。陈辉的《为祖国而歌》似乎更像用鲜血、生命与智慧凝聚而成的战斗誓言,“祖国啊,你以爱情的乳浆,养育了我/而我也将以我的血肉,守护你呀。”祖国与“我”的互为渗透里,洋溢着勇于为国捐躯的爱国情怀与慷慨悲壮的革命志向。而田间的《英雄谣》则在不无夸张的浪漫抒唱间,汹涌着一段改造自然的豪情,“岩石啊,我叫你,变成一枝花哟!”空前高涨的生产积极性与移山造海的生命幻想令人感奋。
解放区的光明与欢乐、希望与生机使解放区诗歌充满了热情的赞歌,生活在那片自由而幸福的土地上,诗人们自然是笑脸看世界,乐观地表现解放区的生活情趣。如鲁藜的《延安散歌》就多方面地歌唱延安,“山花开了,灿烂地/如果不是山底颜色比夜浓/我们不会相信那是窑洞的灯火/却认为是天上的星星……我是一个从人生的黑海里来的/来到这里看见了灯塔。”透过山、河、野花等娇好隽美的意象,读者可以触摸到诗人对宁静清丽、富于理想的延安城的挚爱礼赞之情,可以感受到诗人坚定的信念与无限的温暖。在这方面,何其芳更具有代表性,他在此间写下的《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生活是多么广阔》已洗尽早期诗歌的忧伤哀愁格调,明快清新的节奏与语言歌颂的是解放区的生活与对青年一代的热爱,昂扬向上,仿佛是投向未来的希望源,给人以力量与启迪。
战争生活与战争情怀大量奔涌于诗人笔下,成为解放区诗歌的重要主题。许多诗人的革命化、战士化,使他们理所当然地把抒唱对象瞄准了战争领域,既展示了战争的正义性,又凸现了工农群众的昂扬斗志、雄风英姿以及精神自由。前者如贺敬之的《送参军》、曼睛的《女房东》,单从题目本身,即可领略到战争与群众血肉鱼水般的密切联系,和人民群众对人民战争的热情支持。后者如徐明的《宿营》中的战士“做梦也喊捉俘虏”,不松懈革命斗志;林采的《向前进攻》写到,“没有刀枪的地方就没有自由”,发掘了战士杀敌威力的精神源泉,即为祖国而战为自由而战,有了如此信念支撑,即便面对残暴与苦难也绝不屈服,一种英雄主义的力之美已巍然耸起。同时,这些诗也表现了诗人的乐观信念与在战争中视死如归的献身精神。如表现战争的能手魏巍,在子弹的呼啸声中竟捕捉到了独特的诗意,“我们的子弹/每一粒都闪着民主的光和平的光/都带着人民的仇恨、微笑和希望”(《开上前线》);而田间《坚壁》中的人民面对暴政却临危不惧、大义凛然,面对诱惑与死亡,喊出“枪、弹药,统埋在我心里”,其间的胸怀与气概惊魂夺魄,撼人心动。
以上还只是解放区诗歌情思显示的几个方面,但仅此便足以看出,民族解放主题的拓进、英雄主义的高扬、群体意识的强化,已使解放区诗歌体现着一种蓬勃奔突的东方“日神”精神;尤其是对群体和力的崇尚,使众多抒情个体的鸣唱都突破了一己化个人的情思樊篱,使诗的背后站着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巨大影像,并以明朗雄健的声音替代了以往诗感的绮靡柔婉,逼近并构筑起了1940年代中华民族的心灵风貌与历史,以个人化的方式达到了非个人化的效应,达成了诗与时代的合流,密切了诗与现实的联系,而且拓宽了现代新诗题材的广阔疆域,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可贵的突破。但也有人就此认定,民族意识的复兴、群体的觉醒带来的民族与阶级解放的主题取代了个性解放的主题,以浮浅的乐观替代了深沉思索,这显然是一种缺少历史主义常识的简单认识。从1920年代人的文学向1940年代人民的文学转换,是历史的隐匿超越,它并未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以救亡压倒了启蒙,而是对人的解放、人的个性全面发展的进一步探求,可以视为更高层次上的人的启蒙。
放眼1940年代的世界诗坛,正是存在主义灌注于西方现代主义艺术之时,在异化的哀叹与抗衡中,反崇高与反英雄的荒诞、孤独、虚无、死亡等已上升为普通的精神命题。可远在世界一隅的中国,诗人们正以创造新世界热情的荡动、对英雄的渴盼、对崇高与乐观的追索,造就着一种与工农大众真正对话的崭新革命文学。必须肯定,它在某种程度上矫正着世界诗坛文学意识的倾斜,显示出在文化选择上明智与优卓的特质;尽管它充满了坎坷与艰难,尽管它付出了一定宝贵的代价。因此解放区诗歌有不可替代的思想和认知价值。
二、体式突破:民歌体叙事长诗的繁荣
解放区“复活”的土地上,到处生长着令人欣喜、感奋的现实:革命战争势如破竹日趋胜利,社会变革风起云涌地覆天翻,民主政治精神广为发扬,人民群众的热情空前高涨。这种种洋溢着光明与欢乐、如诗如画的现实,无时不在激发、鼓荡着诗人们的创造热情,于是他们在《讲话》的要以社会生活为文艺的根本源泉与文艺要实现群众化、民族化的美学精神烛照下,应和暴风骤雨般的壮阔生活斗争的需要,顺应同时期“诗”与“歌”合流的趋势,以对解放区人民心灵信息挚爱而敏感的捕捉,催化了一种新写实品格诗歌的萌动与生长——民歌体长篇叙事诗的崛起。一时间里,用戏剧化方式观照重大的历史事件、表现英雄人物的艺术追求风行起来,长篇叙事诗创作迎来了一个硕果累累的丰收季节,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阮章竞的《漳河水》是风骚于这一潮流的航标,除此之外尚有张志民的《王九诉苦》《死不着》、田间的《赶车传》《戎冠秀》、阮章竞的《圈套》、李冰的《赵巧儿》等。长篇叙事诗如此繁荣、盛行,是中国新文学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它们动辄上千行,少也几百行,洋洋洒洒,汪洋恣肆,以民歌体的启用与解放区新生活的讴歌描绘,取代、超越《讲话》前表现战争氛围、开阖自如的自由体,在恢宏气势与雄伟构思的基础上,构筑起了一幅幅史诗般波澜壮阔的生活画卷,从“抒情到叙事”,“从短到长”,实现了“新诗的再解放和再革命”[3]261—262。
这些长诗的主题虽色调纷呈,各有开拓,但在宏阔背景上讴歌抒写抗日根据地和人民翻身解放新生活这一点上,却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如被誉为《讲话》发表后结出的第一朵精神花朵的《王贵与李香香》,以王贵与李香香曲折恋爱为视角,传奇性地复现1930年代初期陕北土地革命的历史风暴,揭示出“咱们闹革命,革命也是为了咱”的深刻主题。《漳河水》匠心独运,抓住封建传统习俗对农村妇女精神面貌影响的一点,在荷荷、苓苓、紫金英三位女性命运转换过程的摹写中,传达出妇女只有在经济上取得独立才能算彻底解放的思想。《王九诉苦》通过王九对孙老财的血泪控诉,凸现了农民的悲惨、地主的贪婪残暴以及两个阶级间的势不两立。而《圈套》则是揭示农村阶级斗争的隐蔽复杂性。这些诗多角度、多层次地再现了三四十年代中国革命的历史风貌,宣扬了只有进行革命和斗争才能走向欢乐与幸福的哲理命题,为读者提供了宏阔的认识价值。
《讲话》考虑文化问题的一个出发点就是深刻指出文艺“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从而与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文艺划开了界限,《讲话》后解放区诗歌实践了这一光辉思想,使工农兵大众以主人公的硬朗姿态走进了宽阔的抒情空间。需要指出的是,此时的叙事长诗不同于一般速写式的画面,它开阔而完整,优越于生活表象的浮光掠影,而以人物性格为艺术结构中心,通过其命运与性格冲突以及波澜起伏的情节故事展示,塑造出血肉饱满、内蕴丰厚的英雄形象,他们不再是人们在以往书中邂逅的才子佳人、达官显贵,诗人刻画他们时也常把他们置于苦难和冲突的困境中,使其爆发出时代气息浓厚的精神美光辉,不但善良勤劳,顽韧坚强,并且顶天立地,铁骨铮铮,有着强烈的革命热情与视死如归的献身精神。王贵的性格美就是在一系列冲突与困境中闪现出来的,无情的阶级压迫使他在革命一到来便参加了赤卫军,表现出极大的革命热情;死羊湾解放前夕,他被崔二爷打得皮开肉绽、死去活来,却始终泰然自若,对胜利充满信心,新婚后没沉湎于甜蜜的爱河而继续追随革命。旧婚姻制度的牺牲品荷荷,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嫁了四十多岁的狗子“黑心肝”,还要每日遭受婆婆的暴虐辱骂;可在这苦胆拌黄连般的处境中她没绝望,而是苦苦挣扎,革命一旦来临便呼啸而出,大胆斗争,告别不幸婚姻并重组家庭,成了妇女解放的楷模。《赶车传》中的兰妮面对地主朱桂棠强娶后的利诱威胁,也喊出了“你有铁的门,关不住我的心”的反抗声音。可见诗人们描写苦难只是手段,目的是以之为背景衬托凸现主人公英雄主义的品格与无私无畏的精神境界,这种在个人自发性反抗与党领导的自觉性斗争统一的阔大历史背景上刻画人物、寄寓丰厚历史人生内涵的表现手法,不失为一种美学原则的开拓,它强化了诗的时代感,体现了史诗性的力度和深度,恢宏深厚;使读者在阅读时获得的不是雪泥鸿爪似的触动,而是灵魂的震颤与启迪。
这些诗在艺术上更充分体现了《讲话》对待民族文化的批判继承态度,不断向民族化、大众化、通俗化美学方向靠拢,没有单调叙述故事,也不平淡地直抒胸臆,而是从主人公生活环境与审美习惯出发,向民间文学吸取营养,综合新诗长于内心独白的抒情性与民间说唱艺术重情节展示长于叙事性的特点,用“旧瓶装新酒”,以传统的民间形式传递最富时代色彩的主题,达成了以往叙事诗中常顾此失彼的叙事和抒情的完美融合。不少诗人都是直接从民歌的语言、节奏、形象、比兴手法等接受效益展开艺术追求的。《漳河水》应和内容需要,将“四大恨”“绣荷包”“开花调”等多种曲调改造成和谐又丰富的交响乐,表现情节的过渡和节奏变化,以景寄情,将漳河人格化为情思的载体,随人哭笑喜怒,有强烈的抒情性。《赶车传》则用快板唱本的句式、韵律与节奏表达主题,更多叙事的记诵功能。《王贵与李香香》据信天游方式连缀而成,它以比兴手法运用造成了情节的跳跃发展,偏重于叙事,作者主观情思大都深隐在人物描摹中。如写到革命到达陕北人民喜悦心情时,只写道“千里的雷声万里的闪/陕北红了半边天”,人们喜爱而熟悉的比兴手法中融入了浓郁的时代气息,表现了新的世界与新的人物,这是一种创造。诗人们在综合叙事与抒情过程中,借助民间文艺手法表达情思的追求,使诗在现实主义精神烛照下又不乏浪漫主义的火花闪烁,写实而不拘泥,朴素又有灵性,获得了永久的生命魅力。
1940年代民歌叙事长诗的崛起,使叙事诗暗合了传统叙事诗的结构模式与外在形态;而它那种简净的构图方式、传奇性结构框架与清朗刚健的民族化特征,无疑又以其特有的素朴清新,矫正了五四以来的新诗民族化不足的缺点,从而确立了叙事诗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独特地位,在一定程度上缩短了与世界叙事诗艺术发展的时空距离。
三、艺术深化:现实主义的全面胜利
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如何为之服务的问题,从新诗问世那天起就一直困惑着诗人们。《讲话》的一个突出贡献便是解决了诗坛的方向,在当时艺术要求与艺术现实、知识分子喜雅老百姓爱俗等矛盾尚未解决的情境下,起了指导性作用。
说穿了,“五四”以来的新诗在对传统诗的反叛意义上功不可没;但它始终是贵族性的,违反精神生产都有内在继承性原则的对于传统文化的偏废,使其从西方诗中引发而来的艺术手段只宜于表现知识分子情感,而面对工农大众尤其是1940年代纷纭流转的繁富现实与工农兵的复杂向上心态时,则显露出传达的无力性。如1941年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上的《悒闷的残片凋零了》还有这样的句子,“快乐的泪在地上开花了/悒郁的残片凋零了/它未曾结下青涩的果/新的种子从心里抽出绿芽。”这种艰涩抽象的诗歌今天看来似乎也无可厚非,可对于当时百分之九十以上不识字、无文化的工农大众来说,却无异于谁也接受不了的“阳春白雪”,呈现出“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的病态特征。
所以在这样的特殊背景下,毛泽东同志便在《讲话》中总结了五四以来新文学的经验教训之后,说明当时工农兵群众需要的是“下里巴人”与普及,需要文艺以革命化、大众化和民族化的探索,创造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作品来。出于史诗品格的意味到史诗品格形式外壳的呼唤,出于“理想抒情”向“现实抒情”的更迭转换,出于对诗坛艺术不能完好传达思想不合理状态的定向反拨,诗坛迫切需要一种契合于鼓手时代的、且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民族化大众化美学风格的出现。于是在诗坛方向获得解决,审美选择空气自由,有大量艺术传统可资借鉴等有利条件综合的适宜土壤上,广大诗人纷纷摈弃从象征派、现代派等流传下来的婉约精巧诗风与高难技巧,在不排斥“横的移植”同时更重视“纵的继承”,把审美触角面向本土,面向民间文学传统的浩瀚空间,将建立“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内化为共同的信念,从而释放出一种清新刚健、朴素遒劲的全新诗美。具体说来,是使二十多年一直居于统治地位的自由体退居次要地位,借用民间诗与古典诗形式创造民歌体民族体新诗形式成为一种普遍的追求。如徐明、邢野等人的短诗借用的是山歌的外壳,阮章竞基本是用七言体民歌来写作“俚歌故事”;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严辰的《新婚》、张志民的《死不着》都采用了陕北民歌信天游形式;田间的两部叙事长诗用的是五言体民歌。甚至自由诗的代表人物艾青居然也尝试着写了民歌体长诗《吴满有》。这些诗大都音调铿锵、节奏热烈明快,严谨而又变化,整饬而又活泼,在古诗与自由诗间架起了一道艺术桥梁。
当然,这种对民歌与古典诗的借鉴不是亦步亦趋、毫无出息的模仿和简单意义上的形式回归;而是根据内容需要对民间诗与古典诗的改造与创新,不少诗在继承民歌的语言、节奏、对比和比兴手法、形象体系,甚至沿用一些现成句子的基础上,以一种当代意识与主体心灵的投注,赋予了民歌更丰富更广阔的表现力。如《王贵与李香香》沿用了民歌与传统诗的比兴手法;它取譬起兴的对象则既熟悉朴素,符合劳动大众的审美习惯,又有着新时代的精神内涵,如突出共产党的领导作用的诗句“草堆上落火星大火烧/红旗一展穷人都红了”,既显示了革命星火燎原的威势,增加了诗的形象质感,又可引发读者的再造联想空间;《漳河水》写到紫金英内心愁苦倾诉时,用了这样的句子,“三月里花开娶过门/十月初一上新坟/紫金英泪盈盈”,传统的“四大恨”曲调有着古典散曲的神韵,可它寄寓的却是旧式妇女不幸婚姻的悲痛与怨艾。贺敬之的《搂草鸡毛》重叠回环的说唱文学式的章法与解放区青年你追我赶、踊跃参军的豪情相吻合,内容与形式相得益彰。用最传统的形式表达最现实的情思,是解放区诗歌创作的一种开拓,是毛泽东《讲活》思想促成的一种特殊精神文化现象。不少诗人更利用民歌影响改造新诗,如艾青吸取了民歌的清新纯朴,剔除了早期诗的忧郁情调,在事物的直觉印象捕捉中寄托情思;田间则在典型细节上做文章,努力使之提升为一个统摄全诗的整体性象征意境,从而避免了诗的浮面概念化,有一定的暗示性,深化了现实主义艺术的内涵。
另外,此时诗歌的语言也大多实现了为工农兵服务的目的,新鲜活泼,生机盎然,大量生活口语、土语的入诗洗去了以往诗中的洋八股与学生腔的缺点,浅显而清新,平朴而警策,不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有如出水芙蓉,有种洗尽铅华、去除雕饰的特色,真正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如“妹妹生来就爱庄稼汉/实心实意赛过金钱”,活生生的口语烧出了生命力,既渲染了香香对王贵炽热情爱,又渗透着诗人的理性思考,达到了知性与感情的综合平衡。再如《王九诉苦》中的“进了村子不用问/大小石头都姓孙”,诗意的比喻里隐含着对贪婪残酷地主阶级的憎恨。
总之,对清新活泼、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的借鉴吸收,给新诗注入了无限新鲜的生机与血液,促进了民族化、大众化风格的形成,显示了《讲话》后新诗现实主义美学原则的全面胜利。
我们如此肯定解放区诗歌的探索,并不是说它就是一种高度理想的艺术模式;相反,它在探索中也留下了许多不可逆转的遗憾和倾斜,或者说曾付出不少昂贵的代价。如文学救亡政治功能的过高期待,压倒了文学美感的期待,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艺术的个性魅力;内视点的诗歌一味向大众化通俗化拓进,也难免限制了诗人抒情个性的伸展与多样化风格的形成;对民族文化的空前肯定的拒外心理,也铸成了一定的闭锁与简单;文学战斗性加强,同时忽视了生活复杂性的反映……所以说,解放区诗歌的经验与教训同样值得沉思与总结,同样无法回避。但仍然可以断定,《讲话》后解放区诗歌创作的选择是明智而优卓的,是值得人们理解并尊敬的。尽管它有这样或那样的缺憾,但它在那个特定的时代里,毕竟尽了自己应尽的义务,它以高度民族化、大众化的艺术方式传递出了中华民族1940年代的情感精神与心灵历史,使现实主义诗歌真正走向民众,汇聚成一股汹涌的历史潮流,构筑起一种恢弘庄严的中华民族的阔大诗风,从而促成了现代新诗一次伟大的美学变革,因此文学史对之应大书特书。今天,历史发展了,我们不能用纯美的观念去贬低它,也不能用纯社会学批评标准盲目抬高它,负责的态度应该是遵循历史主义精神,指出它的优优劣劣、是是非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