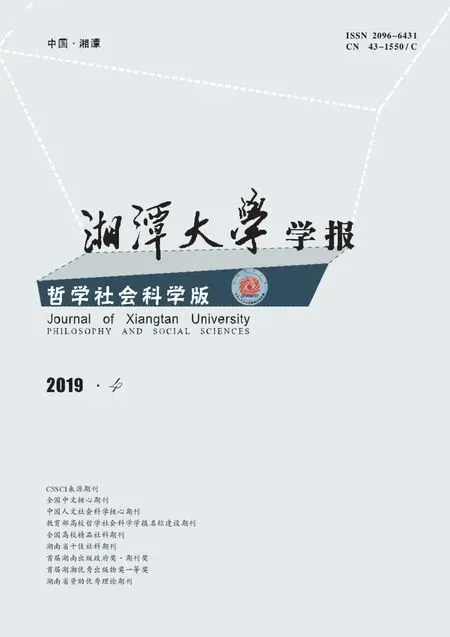从尹文和公孙龙的兼名思想看其传承关系*
2019-02-22肖中云张长明
肖中云,张长明
(湖南工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2)
在先秦诸子中,比较系统地探讨过兼名问题的,主要是同列为名家的尹文和公孙龙。后期墨家学者有“牛马非牛非马”之论,这是对兼名与构成其单名之间关系的揭举,但在《墨经》中并不见有何以为兼名或兼名何以生成的相关论述。大儒荀子的《正名》篇虽有“单足以喻则单,单不足以喻则兼”之说,但除此之外,另无余说,不足以成论。从现代语言符号学观点来说,兼名问题属于语形学方面的问题,相对于我国先秦丰富的语义学思想来说,兼名思想无疑有其独到与独特之处。因此,我们将尹文和公孙龙的兼名思想放在一起讨论,不仅可以一窥先秦兼名理论的基本面貌,也可为历史上对于二者之间的沿承之说,提供某种佐证与参考。
一、关于兼名的合成方式
在我国汉语言文字系统中,单音词或字是最基本的语言单位,相应地,名的最基本存在形式也就是单音节的名词或字,如“牛”、“马”、“人”、“好”等,这也就是荀子所说的“单名”。客观存在的万事万物依照其类属关系而相互联结成一个整体,而人们要认识事物、区别事物,也总是首先要辨识一类事物与它类事物之间的类属关系,即墨家所谓“察类”。然而,事物之间的类属关系又是相对的,大类之下有小类,小类之下还有更小的类;大类之上还有更大的类。因此,随着人们认识的不断拓展及对事物认识的不断深入,命名的范围也不断扩大,仅靠单名已不足以称谓和表征世上的各种具体事物。这时,需要组合新的名称形式即兼名来称谓事物。所谓兼名,就是指由两个以上音节的词或两个以上的字组合而成的事物名称。因此,兼名是在单名基础上重新组合而成的,单名是构成兼名的基本要素和主要成份。那么,如何在已有单名基础上来合成新的复合形式的兼名呢?这就是关于兼名的合成法则问题。在我国古代名学史上,尹文是第一个具体探讨兼名生成问题的名学思想家。
尹文对“兼名”问题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尹文子》之《大道上》篇。从《大道上》可以看出,尹文是从“名、分不可相乱”的角度,来展开对兼名的具体分析的。《大道上》云:“五色、五声、五臭、五味,自然存于天地之间,而不期为人用,人必用之。终身各有好恶,而不能辨其名分。名宜属彼,分宜属我。我爱白而憎黑,韵商而舍徵,好膻而恶焦,嗜甘而逆苦。‘白’、‘黑’,‘商’、‘徵’,‘膻’、‘焦’,‘甘’、‘苦’,彼之名也;‘爱’、‘憎’,‘韵’、‘舍’,‘好’、‘恶’,‘嗜’、‘逆’,我之分也。定此名、分,则万事不乱也。”[1]113尹文认为,对于有形之物,人们自然可以据其形而得其名,但有的名称所指称的对象并不具有明显的形状特征。对于这后一类型的名称,尹文区分了两种情况:一是“彼之名”。颜色、声音、味道等是客观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性征,它们并不受人们的主观意志或个人好恶所支配与左右,不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它们都是客观存在的而不会有所改变。因此,“白”、“黑”、“甘”、“苦”等这些表征事物本身性征的名称,属于“彼之名”。二是“我之分”。“爱”、“憎”、“好”、“恶”等这种名称,虽然在生成方式上也不是通过“形以定名”而得到的,但它们表征的不是事物固有的性征,而是表征人们对于某一特定事物性征的某种接受或不接受的意向、态度,它完全是由个人的主观意志、兴趣爱好和好恶倾向所决定和左右的。因此,尹文将这种名称称之为“我之分”,并强调必须将它与“彼之名”严格区分开来,否则,就会导致名实关系混乱。
尹文虽然力主将“彼之名”与“我之分”加以区别,但他并不否认可将二者组合成一个新名。《大道上》云:“我之与彼,又复一名。”这就是说,将“我之分”与“彼之名”相结合,“合彼我之一称”,可以生成新的复合形式的名称。《大道上》又云:“语曰:‘好牛’。又曰:‘不可不察也’。‘好’则物之通称,‘牛’则物之定形。以通称随定形,不可穷极者也。设复言‘好马’,则复连于‘马’矣。则‘好’所通无方也。”[1]116尹文认为,“牛”、“马”是表征客观存在的具体物类的名称,它们是通过“形以定名”的方式而制订出来的,“牛”名是对牛这个物类的外貌形征进行摹拟而得到的,“马”名是对马这个物类的外貌形征“依类象形”而制订出来的,因此,尹文将“牛”、“马”这类名称统称为“物之定形”。事物之形是事物本身具有的性征,而事物的好、坏并不是事物固有的特征,客观事物本身无所谓好与坏,好、坏只是人们对于客观具体事物的一种价值评价,并且人们作出的这种价值评价又通常是受个人兴趣、好恶倾向等主观态度所制约的。因此,人们既可以用“好”这个名来称谓此事物,也可以用“好”名去谓述彼事物。尹文将“好”这样的名叫做“物之通称”。他认为,将“好”这样的“物之通称”,与“牛”、“马”这样的“物之定形”相联结,就可以生成“好牛”、“好马”等“不可穷极”的复合形式的名称。这也即尹文说的“以通称随定形”的兼名合成法则。尹文虽然没有对这一兼名合成规则作出详细的具体解释或说明,但“以通称随定形”这一高度概括与精当表述,不仅深刻揭示了以汉语言文字系统为依托的兼名生成规律,而且其涵义丰富,用“以…随…”这样的表述方式,突显了“物之定形”在兼名生成中的主导与支配地位,指明了“物之通称”在兼名生成中的从属与依附的次要地位,从而内在地排除了“牛牛”、“马马”、“好好”、“牛好”、“马好”等诸多不规范、不合理的属于“乱名”的组合形式。从现代符号学观点来说,“以通称随定形”实质是一条符号形成规则,它属于语形学范畴,而这在以探讨语义学问题见长的我国古代名学史上,可谓是一个极其罕见、极其重要的符号学成就。
继尹文之后,公孙龙也探讨了兼名的合成问题。他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类似于尹文“以通称随定形”这样的兼名生成法则,但对于这一法则所涵括的具体内容,则全部都涉及到了,并作出了较详尽的阐发分析。《公孙龙子·坚白论》即是探讨兼名合成问题的专论。我国先秦名辩思潮中的重要辩题之一即是“坚白之辩”,而公孙龙因执“坚白石二”之论而被视为“离坚白”一派的重要代表。从《公孙龙子·坚白论》可看出,该篇全篇都是围绕“坚”、“白”、“石”三个单名可否合成第三种兼名“坚白石”这一主线而展开分析论证的。作为反方的客方认为,由于坚、白相盈,即它们可以同时为同一类事物所具有,因而,当人用“坚”、“白”、“石”三个单名合成兼名时,可以生成“坚石”、“白石”和“坚白石”三个不同的兼名,这也就是“坚白石三”的基本涵义。公孙龙则认为,以“坚”、“白”、“石”三个单名,只能合成“坚石”和“白石”这两个兼名,但不能生成“坚白石”这样的兼名,也就是说,“坚白石”是一个不规范的“乱名”。公孙龙力主“坚白石二”的主要依据是:第一,视、拊“异任”。人们对坚、白相种事物性征的认识,是借助不同的感官感知的,即《坚白论》“视不得其所坚而得其所白者,无坚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坚者,无白也。”[2]83-85人们通过视觉只能感知到物之色白,而不能感知到物之质坚,此时,对石物的认知只有白石,没有石之质坚;人们通过触觉只能感知到物之质坚,而不能感知到物之白色,此时,对石物的认知只有坚石,没有石之色白。这表明,坚、白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事物性征。第二,坚、白“相离”。《坚白论》云:“得其白,得其坚,见与不见谓之离。一一不相盈,故离。”[2]138公孙龙认为,人们视物只能感知物之色白,事物即使具有质坚的特性,也是“自藏”于物而未被认知;同样,人们拊物只能感知到物之质坚,事物即使也有白色的性征,它也是“自藏”于物而没有被感知。这表明,事物的坚、白二性虽然可以为同一事物所具有,但它们是各自独立的性征,在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第三,“离也者天下,故独而正。”[2]241在公孙龙看来,既然坚、白是事物两种不同的彼此独立的性征,它们又是人们借助不同感官而被感知的,因此,表征事物坚、白性征的“坚”名与“白”名,也是相互独立的,不能将二者合成“坚白”这样复合形式的名称,自然也就不存在再将“坚白”与“石”组合成“坚白石”的可能性。到此,公孙龙力主的“坚白石二”之论,其涵义也就非常清晰了。所谓“坚白石二”,它是指由“坚”、“白”、“石”三个单名,只能组合成“坚石”和“白石”这两个兼名。这显然是尹文“以通称随定形”的另一种表达,二者的思想实质是根本一致的。除《坚白论》外,《公孙龙子·通变论》在论及兼名独立性过程中,也涉及到了对兼名合成问题的分析,因其认识与主张与《坚白论》并无二致,这里不再作具体讨论。
不难看出,公孙龙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兼名的合成法则,但他对于尹文提出的“以通称随定形”原则,作出了具体的阐释与分析,不仅完全沿承和坚守了尹文的基本主张,而且对尹文的主张展开了详尽而系统的分析论证。
二、关于兼名的独立性
兼名研究涉及到两个最基本的也是最主要的问题,除上述关于兼名的合成问题之外,关于兼名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兼名的独立性问题。
《尹文子·大道上》云:“设复言‘好人’,则彼于人也。则‘好’非‘人’,‘人’非‘好’也。则‘好牛’、‘好马’、‘好人’之名自离也。故曰:名、分不可相乱也。”[1]119在尹文看来,“好牛”、“好马”、“好人”等兼名,它们虽是“合彼我于一称”,是将两个不同单名组合而成的新的事物名称,但由于构成兼名的两个单名,一个是属于“彼之名”,另一个则是属于“我之分”,二者分别属于不同的两类名称,作为“我之分”的“好”名,不是作为“彼之名”的“人”名,反之亦然。因此,“好”与“人”这两个名称具有彼此相离、各自独立的符号性质。在尹文看来,由“好”与“牛”、“马”、“人”组合生成的兼名“好牛”、“好马”和“好人”,也是“自离”、相互独立的。伍非百认为,“按此为公孙龙《白马论》之先声。‘好非人,人非好’,为‘形非色,色非形’之论式所取资”[3]136。
公孙龙之论兼名的独立性,主要集中在《白马论》和《通变论》两篇。在《白马论》中,公孙龙借“白”、“马”分别喻指两个不同的单名,而借“白马”指代新组合的兼名。在该篇中,公孙龙详细阐发了“白马”不是“马”的道理,深刻揭示了兼名作为一类事物名称的相对独立性。公孙龙提出的主要理由是:第一,“命色”不是“命形”。《公孙龙子·白马论》云:“‘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4]98公孙龙认为,“马”名是用以命名事物之形的,“白”名是用来表征事物之色的;命色之名不是命形之名,因此,“白马”不是“马”。第二,“所求一者,‘白马’不异‘马’也。”《白马论》云:“求马,黄、黑马皆可致;求白马,黄、黑马不可致。使‘白马’乃‘马’也,是所求一也。”[4]96在公孙龙看来,“马”名仅是命形,因而黄、黑马都可以其形征而应“马”之名。但是,“白马”是一个兼名,它既马类之白色,又命马类之形征,黄、黑马因其色征不同而不能应“白马”之名。如果是“所求一者”,使“白马”名失去了命色的根据,它就与仅命形的“马”名无法区别开来了。第三,“‘白马’者,‘马’与‘白’也。”《白马论》云:“‘马’未与‘白’为‘马’,‘白’未与‘马’为‘白’,合‘马’与‘白’,复名‘白马’。”[4]117公孙龙认为,“马”名和“白”名在“相与”结合之前,它们是各自独立的单名,将“白”名和“马”名相结合,就组成了一个新的名称即兼名“白马”。因此,从名称的存在形式或者说符号形式来看,由两个不同单名组成的兼名“白马”与单名“白”、“马”,二者之间有着显著的根本性的差异。第四,“无去者非有去者”。在公孙龙看来,说有“白马”就不能说没有“马”,这实际上是一种“离白之谓”。因为,“白马”是“白”与“马”相结合而成的,它指称的是既具有白之色征又具有马物形征的白马,而不是指称仅具有马物形征的马。如果要说“白马”名中有“马”,这就是一种从兼名“白马”中分离和舍弃单名“白”这一组成要素的“离白”之说了。而如果不使单名“白”从兼名“白马”中分离出去,那就不能说兼名“白马”的指称中有“马”了。因为,在兼名“白马”中,“白”和“马”只是构成兼名的要素、成份,而不再是独立的事物名称。总之,在公孙龙看来,单名“马”名只命马之形征,没有命色的依据,因而,凡是具有马之形征的事物,都是“马”名所称谓的对象。而兼名“白马”,既命马之形征,又命物之色白,相对于单名“马”来说,它附加了命色的依据,因而,凡不具有色白之马都不是“白马”的表征的对象,而只有既具马之形征又兼有白之色征的白马物类,才是“白马”所称谓对象,才可以应称“白马”之名。由于命色之名与不命色之名是根本不同的,因此,“白马”不是“马”。不难理解,公孙龙《白马论》所阐发的中心论题“白马非马”,实际上是揭举兼名“白马”与构成它的单名之间的“相非”关系。这种表述形式上的“相非”即相互否定关系,其实是指明了兼名的独立性。也就是说,兼名虽由单名构成,但与单名不存在任何隶属关系,它是具有自己确定指称对象的独立存在的一种事物名称。“‘白马’非‘马’”命题所揭示的即是这个道理。
关于兼名独立性思想,公孙龙在《通变论》中作了更直接也更精当的阐明。《公孙龙子·通变论》云:“曰:二有一乎?曰:二无一。曰:二有右乎?曰:二无右。曰:二有左乎?曰:二无左。曰:右可谓二乎?曰:不可。曰:左可谓二乎?曰:不可。曰:左与右可谓二乎?曰:可。”[2]183公孙龙这段文字,我国研究者作出过各种各样的解释。有的研究者干脆将其斥之为诡辩,更有甚者则将《通变论》当作“伪书”而“一笔勾销”了之。实际上,当我们了解了公孙龙“假物取譬”的论说特点,那么,上述引文就很好理解了,而且它的思想内容与公孙龙整个名学思想体系高度契合,并成为其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根据《公孙龙子》一书的论说特点,引文中的“一”、“左”和“右”都是喻指不同的单名,而“二”则是兼名之喻。按照如此提示,对上述文字就很容易理解了,公孙龙的“可”或“不可”的回答,与他在《白马论》中的基本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在我们看来,作为《通变论》的中心论题,“二无一”是对兼名独立性的一种最高概括。“二”作为兼名之喻,它是由两个单名如“左”和“右”“相与”结合而成。公孙龙为什么说“二无一”呢?公孙龙认为,兼名中的单名只是组成兼名的构成要素或者说部分,它们已不是独立存在的名称符号,与作为独立名称存在的单名是不同的。换言之,作为独立存在的单名“白”和“马”,与兼名“白马”中的“白”与“马”,虽然符号的形状等物理性征没有发生变化,但其功能、地位改变了,已经不再具有独立名称符号的性质和特性。在这里,公孙龙用“二”来喻指兼名,可谓恰如其分、十分精当。我们知道,在我国古代,人们常以“二”表征整体。这表明,公孙龙也如墨家那样,将兼名看作是一个整体,相应地,构成兼名的单名就是部分。由于两个单名只是构成整体的两个不同部分,它们原来作为独立名称的性质、特点和地位,也就在兼名中被消解和剥夺了。反过来,由于两个单名组成了新的兼名,兼名也就整体地获得了具有自己特定指称对象的独立名称符号的性质、功能和地位。简言之,就是“二无一”,即在兼名中不存在或者说没有具有独立符号性质的单名,兼名是一种独立的事物名称。至此,《通变论》这一让许多研究者捉摸不透的篇名的涵义也变得清晰与明朗了:相对原来的独立存在的单名而言,兼名中的单名已发生了质的变化,它已由原来的一个独立的事物名称,变成了一个事物名称的组成部分,即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名称了,其性质、功能、地位等,被完全、彻底改变了,即“通变”。由此可见,公孙龙对于兼名独立性的理解和把握,已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认识水平,也代表了我国古代名学的最高水平。
三、关于公孙龙与尹文的思想传承关系
在讨论公孙龙与尹文的思想传承关系之前,我们首先指出二者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所存在的并非关键性的差异。主要表现在:
第一,从理论的概括程度及系统性来看,尹文重点探讨并明确提出了“以通称随定形”的兼名生成法则,但对兼名的独立性问题只是有所涉及,而并没有作具体的阐发。公孙龙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兼名的合成规则,但他的“坚白石二”之论,实际上也可看作是兼名合成规律的另一种形式的表述,并且,对兼名生成中可能出现的不合理、不规范情形作出了具体剖析,进而逐一排除。对于兼名独立性的探讨,公孙龙已远远超出了尹文的认识眼界,不仅用“二无一”、“‘白马’非‘马’来揭举和表征兼名与构成其单名之间的关系,而且非常详尽地阐明了兼名之具有独立性的依据、理由。也正因为此,无论是探讨兼名合成规律,还是分析兼名的独立性,公孙龙的论述较尹文明显具有系统性、理论性,并表现出一种体系化特征。在《公孙龙子》一书中,《名实论》奠定全书的理论基础,《指物论》专论名称与事物之间的指称关系,将《名实论》之论名实关系,推进到更具一般性的指物关系。除这两篇外,《坚白论》主论兼名合成问题,《白马论》专注于兼名的独立性,《通变论》则综合《坚白论》和《白马论》两篇,对兼名的两个基本问题,进行集中的阐发和更高的概括,体系性特征十分明显。
第二,对“物之通称”理解上的差异。尹文严格区分了“彼之名”与“我之分”,并将“白”、“黑”、“甘”、“苦”等归于“彼之名”,而将“爱”、“憎”、“好”、“恶”等归于“我之分”。从现代符号学分类理论来看,这种区分是很合理的,也是很有意义的。按照美国哲学家莫里斯的看法,“彼之名”属于“指谓指号”,它“意谓对象或情况的特性”;而“我之分”属于“评价指号”,“这种指号使它的解释者倾向于喜爱或不喜爱某事物”,像“‘好’、‘较好’、‘最好’、‘坏’、‘最坏’这样一些指号,在人的水平上,是作为颇有分别的评价指号而起作用的。”[5]176在对名作上述区分的同时,尹文又将“牛”、“马”、“人”等名称之为“物之定形”,而将“好”名叫做“物之通称”,并明确指出“彼于人也”。由此可见,在尹文那里,“彼之名”除了表征事物性征的名,如“黑”、“白”等,还包括“物之定形”的名,如“牛”、“马”、“人”等。在莫里斯的符号分类中,前者称之为“性质-指谓指号”,它表征的是事物具有的性征;后者称之为“对象-指谓指号”,它指称的是具体事物本身。[5]98在尹文关于名的分类中,它们又被统称为“命物之名”。从一般意义上说,白、黑、甘、苦等事物性征,虽为事物所固有,但并不是某一特定物类所独有,因此“白”、“黑”、“甘”、“苦”等表征事物性征的名,都是属于“物之通称”。但在论及兼名合成规则时,尹文例举的“物之通称”仅有一个“好”名,对于“白”、“黑”、“甘”、“苦”等名是否也属于“物之通称”,尹文并没有指明。而在公孙龙那里,“物之通称”主要是指“白”、“坚”等表征事物性征的名,它是属于“彼之名”。
第三,兼名组合形式上的差异。不难看出,在尹文的“合彼我于一称”中,实际描述和分析了两种复合型组合形式:一是“爱白”、“憎黑”、“好膻”、“恶焦”这样的复合形式。由于这里的“爱”、“增”、“好”、“恶”表征的是人们一种喜爱不喜爱的行为状态,因而,这种组合形式实质上已经不是事物名称意义上的兼名,而是一种更高级、更复杂的语言表达式。这是尹文对于中国古代名学的一个独特的贡献。二是“好牛”、“好马”、“好人”这样的复合形式。很显然,尹文在这里有明显的失察之处:这里的“好”与上述作为评价指号的“好”,完全是不同义的,但他仍然将其归于“我之分”。“好牛”、“好马”、“好人”中的“好”,并不是表征人们对于特定事物的某种喜爱或不喜爱行为,其本义应当是“好的”,用作形容词,因而与“白(的)”、“黑(的)”等更相类似。而“好膻”中的“好”,本义是喜欢、偏爱,用作动词。实际上,对于这两种意谓,尹文在表述上也作了明确区分,如“我爱白而憎黑”。这其中的“我”即表明,“好”总是要与评价主体联系在一起的,离开评价主体,评价的意义就无法确定。“好牛”、“好马”、“好人”中的“好”,表征的是事物所具有的某种特殊状态,比如说“这是一匹好马”,这里的“好”表征的主要是这匹马健壮的优良状态,而不是个人的某种偏好。因此,在我们看来,尹文将“好牛”、“好马”、“好人”中的“好”,归于“我之分”,是明显失察的。公孙龙所论及的兼名组合形式是上述尹文的后一种形式,并且,他使用的“白马”、“黑马”、“黄马”、“坚石”、“白石”等,都是标准的兼名组合形式。
我们认为,上述公孙龙和尹文在兼名思想方面的某些差异或区别,并不排斥或否定二者在根本上的相似性或相类性。主要理由是:
第一,在对名的理解和认识上,尹文和公孙龙是根本一致的。在以表意为特征的汉语言文字系统中,单名是最基本的事物名称,兼名则是在单名基础上重新组合形成的新的事物名称。因而,对兼名问题的探讨,是以对名的认知为基础的。《尹文子·大道上》云:“名生于方圆,则众名得其所称也。”“名者,名形者也。”“形以定名。”[1]96在我国古代,人们常以“形”泛指具体有形事物,并将事物之形看作是区别物类的主要依据。这是对事物的一种最朴素的认识。尹文认为,名是对具体有形事物的称谓,它是根据一类事物的外貌形征而摹拟、描画出来的用以称谓和标记该类事物的名称。客观存在的万事万物原本是没有名称的,人们为了认识它们、区别它们,而赋予其各种不同名称,进而这些事物名称就成为了人们相互之间交流思想的重要工具。给事物命名的方式,在不同的语言文字系统中是不一样的,并形成了不同的命名传统。我国先人命名事物的方式,是与我国古汉语文字的特质密切相关的。汉文字起源于象形文字,它是“依类象形”而生的。由于名的存在形式即是汉语言文字系统中的名词或字,所以《墨子·经说上》云:“名若画虎也。”又云:“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6]76尹文对名的认识是完全符合以表意为特征的汉语言文字体系的实际情况的。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明确指出:“一个词只用一个符号来表示,而这个符号却与词赖以构成的声音无关。这个符号和整个词发生关系,因此也就间接地和它所表达的观念发生关系。这个体系的典范例子就是汉字。”“对汉人来说,表意字和口说的词都是观念的符号;在他们看来,文字就是第二语言”。[7]100尹文所论形名关系,在公孙龙那里亦有所反映,如《白马论》云:“‘马’者,所以命形也”。公孙龙没有专门讨论形名关系,但他从更高的认识层面,给出了“名”的经典性定义:“夫名,实谓也。”名即是对客观具体事物的称谓。可见,不仅公孙龙和尹文对“名”的理解是根本一致的,而且他们与后期墨家学者、荀子等其他先秦诸子对“名”的认识,也是没有本质区别的。换言之,公孙龙和尹文对兼名的探讨,有着共同的关于名的一致的认知基础。
第二,在兼名问题上的基本主张,公孙龙和尹文是根本一致的。他们虽然都没有给出“兼名”的界说,但对兼名的一些基本特点,有着共同、一致的理解,如兼名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单名的组合形式,兼名是不同于单名的另一类事物名称等。对于这些基本认知,我们虽然看不到明确的语言表述,但明显是他们探讨兼名合成和独立性问题的不必言说的逻辑起点和立论基点。正如前面所分析,在兼名的合成和独立性问题上,公孙龙和尹文之间存在着某些具体的差异,但是,对于“以通称定随形”的兼名组合法则,对于兼名的相离即独立性,两人的基本认识和主张,是完全一致的、相同的。表述方式的不同,分析论述的详略,探讨问题的侧重点不一,这些都没有消解和影响到他们在主要问题、基本主张方面的一致性、共同性。
第三,在重要观点表述和一些关键性术语的使用上,二者也具有很大程度上的相通与相似性。如《尹文子·大道上》云:“我之于彼,又复一名。”[1]176《公孙龙子·白马论》则有“合‘马’与‘白’,复名‘白马’。”[2]156这两段引文虽然分别出自尹文和公孙龙的著作,但二者表达的都是对于兼名的基本认知,即兼名是由两个不同单名组合而成的新的事物名称;并且,其中的“与”、“复一名”、“复名”等关键性用语,都是完全一样或大致相同的。又如,尹文将“好”这样的名叫做“物之通称”,也就是说,它是许多事物所共有的名称。公孙龙《坚白论》则说,“不定者,兼。”认为坚、白等性征并不是某一具体物类的特有,而是诸多物类所共同具有的性征,因而,表征事物坚、白性征的“坚”、“白”名,是诸多物类兼而共有的名称。“物之通称”与“不定者,兼”,虽表述方式不同,但它们的基本涵义是一致的、没有区别的。再如,“离”是揭举兼名独立性的一个十分重要和关键的术语,而在公孙龙和尹文对兼名问题的探讨中,它都“及时”出现了,这似乎也不是巧合。诚然,在不同作者的不同著作中,个别术语或用语的相同或相似,这当属正常现象。但是,在不同作者的不同著作中,探讨的问题完全相同,对问题的认识和主张根本一致,关键性术语和用语也是完全相通或类似,并且又明显不是彼此之间的简单“复制”,对于这种情形,用“偶然”、“巧合”来解释,是无法让人信服的。
据史载,尹文,战国时齐人,为稷下学宫的重要成员,《汉书·艺文志》列为名家第二。关于尹文的生卒年代,一说先于公孙龙,一说学于公孙龙,实则已难确考。公孙龙,战国时赵人,也被《汉书·艺文志》列为名家的重要代表。从上面对尹文和公孙龙的兼名思想所做分析来看,尹文学于公孙龙之说实难成立,明显缺乏依据;而我国学术界有关公孙龙上承尹文形名思想之说,虽然不是定论,却也决非是空穴来风。一个难以否定的事实是,公孙龙以尹文形名思想为研究基础,对兼名学说作出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并将其推进到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