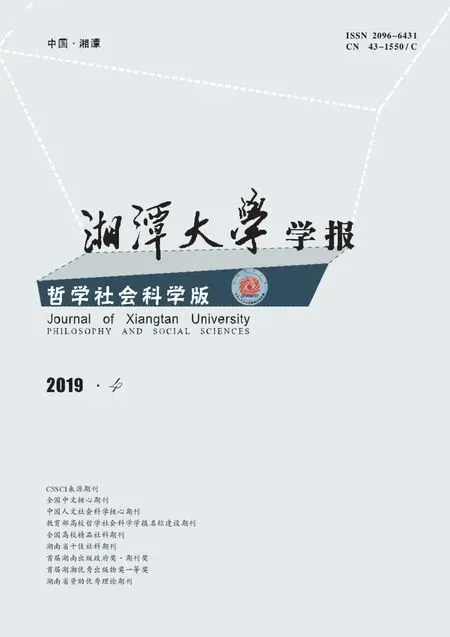内容到形式:“社会性别”研究的新路径*
2019-02-22孙桂荣
孙桂荣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社会性别”(1)2015年8月,将gender译为“社会性别”的海外华人学者王政教授在同笔者的谈话中曾直言“社会性别”这个概念在很多领域已经常识化了,但文学界还喜欢用“性别”。作为一个四字词语在现代汉语中是随着西方女性主义关键词gender在中国的翻译、使用而出现的,目前已被广泛应用于各个学科的人文社科研究成果中。对于新时期文学研究来说,尽管“妇女问题的提出和尖锐表现,最早是在文学而不是在社会领域,无意中使得有关妇女的文学成为社会学讨论的导火索和先驱”[1],但是在语词运用上,“妇女意识”、“女性意识”、“性别意识”、“社会性别意识”等均被不时提起,而“社会性别”在使用频率上并不高,最起码不像在妇女学、社会学那样受到格外重视,这一现象已经引起了某些倡导者的关注与质疑。[2]按照海德格尔“语词破碎处,无物存在”的现代语言学理论,语言、语词有着影响言说者思维的“话在说我”的功效,女性文学研究关键词的多元和概念界定上的众说纷纭性,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学研究界对这一问题理解上的差异性与驳杂性,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女性文学研究的一些未尽之处。本文旨在辨析“社会性别”意识在新时期文学研究中发生、发展的话语脉络,探究其从文学文本的内容研究到形式分析的新世纪研究新路径。
“社会性别”意识在新时期文学中的发生
赛义德认为理论旅行不是偶然的,“首先有一个起点,或类似起点的发轫环境,使观念得以产生或进入话语。”[2]改革开放为“社会性别”意识在中国的传播、发展提供了历史条件,但这一观念的形成却是经历了一个相对曲折的过程。新时期之初中国文学界更多是从“性别”这一语词的传统语境来理解这一问题的,对于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相区分的观念尚相对淡薄。 在1980年代的中国,作为对“阶级”话语的反拨,“性别”成为标识“人性”的主要认知方式[3]。以性别差异冲破政治一体化时代“男女都一样”藩篱是当时学界的首要任务,学者们基本认同长期以来尽管身为女人,但“不知道女人是什么”的性别缺失感[4]1;要求女性文学“无性化”、“去性别化”是以男性/文学的固有标尺去裁定女性/文学,是一种男性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5]等。西方女性主义者“要成为一个主体就必需有性别”[6]的性别主体论受到了学界高度关注,中国20世纪初性别是“男女之别,性sex之别也”[7]的界定也被重新提起,“性是身体的,本原性的;而性别则是一种身份,由性而生的社会身份”。[8]2
强调女性的“有性”状态容易导向以男女自然之性(sex)为基础的性别言说,这从“只要女作家本身不是个中性人,她的创作中就会自然而然流露出女性风格和魅力”[9],“由于女性生理、心理上的特点,也由于女性比男性经历了更多苦难,女作家的创作有自己独特的风格”[10]之类说法在当时频频出现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与从区分生理性别(sex)角度上,批判男权机制、揭示性别生产与再生产[11]的“社会性别”理论还是有一定差别的,“人们生为女性或男性,但却是学做女孩或男孩,长大后更是学做女人或男人”[12]ix,这种后天的性别“学习”是男权文化所在,但当将人们的性别获得当成一件自然而然/天经地义的事情时,批判性思维便大大削弱。有学者指出,1980年代的中国学界是以“女性意识”或“妇女意识”(female consciousness)为核心概念来界定女性文学的[13],而这个female consciousness主要是由女性生理性别(sex)的自然属性来界定的。直到gender在女性学界广为传播的1990年代及新世纪,文学界仍不愿使用“社会性别”一词,而只是深化和发展中文原有的“性别”意涵(2)像刘思谦、乔以钢等女性学界资深学者直到21世纪学术会议或论文中谈到女性文学研究关键词时还是用的“性别”而非“社会性别”,见李祥林:《文献研究:从“女性”到“性别”——“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性别”学术研讨会述要》(《新余高专学报》2005年第6期),乔以钢《性别:文学研究的一个有效范畴》(《文史哲》2007年第2期)。,不能不说与这种female consciousness影响之深没有一点关系。gender的汉语翻译是有争议的,倡导者认为汉语中没有gender在西方女权主义中所表达的“社会性别机制”的对应词,“用‘性别’来指称gender不但对我们的理解造成限制,也会造成意义的混乱”[14],但另一些本土女性学人则认为汉语可以用“性”指称sex,用“性别”对应gender(3)如李小江曾言,“性别身份中的自然身份与社会身份是同时并存,客观存在的,涉及到人的‘性’,从来说的是‘男女有别’,既有正视和认同‘性’的自然属性的一面,也有顺其自然,人为规范性别差异的社会导向的一面”。《导言:从Gender(社会性别)在译介中的歧义性谈起》,李小江《文化、教育与性别——本土经验学科建设》,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1页;李筱琳、石爱忠《对gender译为“社会性别”的几点质疑》,《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7年10月第5期。。“社会性别”的译法在中国基层地区的现实适用性也遭遇一定挑战[15]。而译成中文原有的“性别”并在中国社会中逐步推进gender所包含的“社会性别机制”理念,既是出于对中国本土文化与汉语习惯的维护,也包含对西方话语霸权的反制倾向,从这个角度上说,文学批评更接近妇女研究中的“本土派”。
应该说,1980年代是复原传统性别认知与“社会性别”观念在朦胧中自发形成的并立阶段,如围绕张洁、张辛欣创作而来的“雄化”论争,“‘女人雄化’不是妇女解放的方向……是长期的左倾宣传灌输了可悲的盲目性”[16],“‘女性雄化’现象足以引起现实人们最直接的疑惑和反感”[17],“它是一种妇女压迫的矫枉过正,是在恢复女性本来面目的必经阶段”[18],秉持的就是一种“自然性别观”;而女性“雄化”是“女子身上原本存在的异性气质终于得到了合理发展的机会”,是“男子气质与女子气质同时在一个个体身上得到均衡的发展”[19]则有点接近女性主义的“雌雄同体”理念。还如女性“需要两个世界”[20],“女作家的文学眼光既应关照女性自身的‘小世界’,同时也应投射到社会生活的‘大世界’”[21],“女作家应以“女人”的意识表现‘内在的世界’,以超越‘女人’的‘人’的意识表现‘外部世界’”[22]等二元论话语,一方面含有将女性对应于“小世界/内在世界”,而且是在价值上低于男性对应的“大世界/外部世界”的性别本质主义思维,另一方面对“大世界”的强调也将女性性别同其他身份构成的社会性在场联系起来。这一切都构成了汉语翻译词“社会性别”在文学研究中的知识“前见”,在此意义上,有关这一阶段只与新启蒙话语结合,“不是在客观地描述自然现象,而是对男女社会行为提出规范”[23],“通过叠加上‘女性’这一‘身份’政治/差异政治的维度,进一步将原本在阶级政治框架内定义的‘主体’还原为‘自然’的多元的主体”[24]之类激进批判,笔者并不完全赞同,在西方自觉的女性主义理念影响中国之前,“社会性别”意识已以一种朴素、零散的方式在各类争议中有所闪现。
观念流变与以内容研究为中心
19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性别”概念被正式译介到中国,加之个人化写作的潮流之势及1980年代“有性的”主体理念的深化,从性、身体等微观政治层面阐释“社会性别”意涵蔚然成风。凯特·米莉特的“性政治”成为学界热点,谁的性,怎样的性,向谁言说及被谁言说的性等激发了对身体写作的集中关注,并与“个人的就是政治的”女性主义话语相勾连,是社会性别意识集中出现,并进一步分化、流变的一种表现。
翻检1990年代的社会性别论争,我们会发现学界在“个人的就是政治的”的“个人”理念上是有争议的:一种是张扬其拒绝公共话语的“个人”(极端化表达是“私人”)观念,认为个人化本身就具有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颠覆性价值,如“最个人的才是最为人类的”[25]282,“‘私人化’的核心在于它与公共/公众(public)的对立与区别……标志着以国家、民族、人民等‘大我’和私人化的‘小我’之间的关系得到了调整”[26];另一种则认为以“个人”对抗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不是无条件的,而应该有某种前提或限制,如“漠视公共领域的私人化书写反而会加深私人领域的危机……文学自身的本性不允许文学是完全个人化或纯私密性的”[27],“个人永远是群体称谓与个体称谓的辩证统一,只承认后者的唯一特性,事实上就是对写作主体的现实阉割”[28],“真正的个人化写作,应该依托个人自我的视角和体验,并寄予广博而又深刻的人间关怀。”[29]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对个人化写作的质疑从批判女性写作中“个人”意识的绝对性、极端性出发对女性立场本身的绝对性、极端性进行了批判,甚至抽空了女性主义批判“男权中心”的基石,如“承认我是一个女性主义者是一种公正,宣称我是一个男性主义者也是一种公正”[30]189,“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内,如果还存在人的权利不完整的话,那么这种不完整已经不是性别间的差异,经过‘第二次’解放之后,新的生存理想的内容比女性进一步挣脱男权文化的禁锢要重要得多”[31]等。
也可以说,在对个人化写作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更多学人将目光投向多重主体与身份政治的呼唤,“在进行女权/女性主义批评时应用社会身份疆界说的关系论、情景论、流动论的观点,将社会性别(gender)同社会身份的其他构成成分协调起来进行研究”[32]424,苏珊的这种观点对中国女性学界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影响,原因并不仅仅是其提出的“超越女作家批评和女性文学批评”的“超越性”正好契合中国深厚的社会历史批评理念,还与新世纪前后文学研究发展的特定时段息息相关。1980年代初的文学研究中亦不乏呼吁女性超越性别执迷、投身社会的声音,如“《方舟》所流露的偏激情绪实在是不足道的。社会主义社会为妇女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梁倩她们应当从心造的‘方舟’里把自己彻底解放出来”[33],但这首先遭到了为女性精神鼓与呼的女性学界的强烈批判[34]41-42。不过,新世纪以来一如“女性视阈中历史与人性的双重书写”[35]等呼吁女性走进“广阔天地”的声音却得到了包括女性学人在内的主流学界的认同,究其原因,笔者在一篇论文中曾将其概括为两点,一是“女性学界思虑的中心由此前如何张扬女性特殊性、主体性,渐渐转向如何应对‘个人化’写作屡被男性文化市场收编改写的理论难题”,二是困扰1980年代的女性特殊性问题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认可与张扬,使得宏大的超越性立场“有可能因为女性主体的在场而避免此前经常出现的性别遮蔽问题”[36]。这里,笔者想再补充一点的是,努力摆脱前人影响的学术创新意识与对模式化了的女性叙事的审美疲劳也推动了学界去拥抱这种多重主体的身份政治批评。不过,这种“将社会性别(gender)同社会身份的其他构成协调起来进行研究”的思路在将gender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时,必须保证性别因素的在场及在同社会身份其他成分的关系中居于重要位置,否则就抽空了“社会性别”的研究基石。在主流意识仍十分强大的中国学界,女性主义边缘立场的自我调整与自觉不自觉被体制化之间的界限,相对模糊。西方女性学者往往在追问种族、性别、职业,何者为先,种族问题在中国并不鲜明,但道德、阶级、国族意识却十分强大,其与“社会性别”的结合也异常复杂。
除了与国族、阶级、社群等其他社会范畴的叠印交叉,“社会性别”在新世纪文学研究中的另一发展趋向是理论上增加了流动性、解构性的后现代因子。作为gender概念基础的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区分在巴特勒等人的后现代观念中被解构了,“所谓的性别没有社会与生理之分,它只是一种社会法则,具有建立在权力基础上的合法性,并且相对地封闭(也就是必须排斥不符合这种法则的她者),被反复引用……书写我们(具有性别特征)的身体,建立起我们的主体”[37]4-5。身体、主体、父权制、女人/男人这些曾被视为基础的概念是并非天然的“表演性”存在,后现代性别观在解构经验主义、本质主义思维,拓宽学术视野的同时,也以理论修辞的方式对“社会性别”的原有研究模式产生了一定冲击,甚至动摇了其某些曾经的基础。像如果将sex与 gender的区分当做“生理上性别化的身体和文化建构的性别之间的一个根本的断裂”的二元对立[38]8,gender翻译论争中“社会性别”的提法本身是否已经成了问题?如果是,该如何处理与标识性别机制的权力内涵;如果不是,又该怎样认识二者的建构性层级关系?如果说“建立在特定社会的话语中的、偏离中心的、碎化的、多元的女性主体可用来作为女权主义政治的杠杆”[39]35,这种放大了话语修辞性与个体差异性的“女性主体”在社会与文化运作中作用几何?既不是“有性的”主体,也不是社会化的主体,而是碎片化、流动性的主体,成了后现代女性主义的关注对象,其对性别稳定性的解构力量是非常大的,并衍生出了酷儿理论。这种后现代主义“社会性别”观念本身对中国大陆来说固然有一定经院气息,但其所连接的换装、变身、女同/男同、双性恋、跨性别等现象却是网络与大众文化热衷的议题。“性少数”群体在中国的弱势与边缘也并未妨碍其文化书写的发展,甚至以文化反弹的方式恰恰催生了表征这些酷儿现象的文学作品的流行,像已经类型化的穿越、变身、耽美等小说类种,尽管不乏娱乐性、消费性痕迹,其在社会性别观念层面却体现了不同于前代女性写作的新特质、新气象,并呼应了解构性、流动性的后现代性别伦理。这是“社会性别”在传媒时代观念流变的一个新的症候。
形式研究:新世纪以来新的可能性
从复原生理、心理层面上的传统性别差异到批判性别生成中的男权文化机制,从执着于提升被压抑的个人、身体价值到强调公共领域中的女性参与,从建构多重主体的性别维度到解构生理性别与文化性别的二元对立,从注重精英叙事中的女性话语到开始与大众文化结缘,社会性别研究在新时期文学中经历了繁富的发生、发展与争议,或者说其本身见证了改革开放40年来当代文学研究的话语流转。
不过,从以上的梳理中我们会发现,内容研究——从文学文本所表达的主题话语、塑造的人物形象、展现的故事情节等层面,阐释有性或无性的主体、表征强烈的性别立场或将性别与其他社会身份相结合,一直都是新时期以来文学文本中“社会性别”研究的主流样式。与之相对的形式研究——叙述人、叙述视角、叙述距离、叙事结构、叙事时空等最鲜明体现热奈特所说的故事与话语相区别的文学文体中所蕴含的“社会性别”意涵,却往往被有意无视或无意忽略。这当然不仅存在于女性研究界,而是文学研究领域始终未能有效正视的一个问题。对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罗岗教授的意见是颇为中肯的:“一方面,社会历史不单只在内容层面上进入文学文本,更重要的是它必须转化为文学文本的内在肌理,成为‘形式化’了的内容;另一方面,文学在文本层面上对‘巨大的社会历史内容’的把握,同样不能是‘反映论’式的,而是要想象性地建构新的社会历史图景,把文本外的世界转化为文本内的‘有意味’的‘形式’。”[40]如果说文学中内容与形式本身就存在着深层次的深刻互动,则其在“社会性别”意识的文本表达中亦必然会有所体现,该如何把握这一问题的机理?女性写作与男性写作的区分究竟在何处?或者说文学文本中的男性声音或女性声音仅依赖于写作者的生理性别是男性还是女性,亦或主要表现的是男性生活还是女性生活?这些问题无疑将“社会性别”研究推向更深处。
学界对女性文学的界定大体有这么三种看法:一是只要女性写的就是女性文学;二是按性别加题材加风格的分类,即女性所写的表现女性生活体现了女性风格的文学;第三种是性别加女性意识,即女性所写的表现女性意识的文学[41]。对于如何界定女性文学不同学人有着各自的主张,但是叙事形式的社会性别研究无论在女性文学概念界定还是具体文本分析中均被普遍关注不足。沃霍尔曾言,“男性写作与女性写作文本的差异毕竟不在于所谓的内容,而在于他们的讲述方式、话语的特征(感伤的、反讽的或是科学的等)。”[42]56这个说法当然也有诸多可进一步追问之处,像所谓讲述方式、话语特征究竟有没有决然的男女之别,“感伤的、反讽的或是科学的”话语方式是从哪个层面界定的等等。但它却将性别形式分析,这一女性学界相对边缘和薄弱的问题带到中国学界,对上文所梳理的新时期以来长期纠结于内容研究的社会性别分析有着鲜明的开拓作用。在詹姆逊、伊格尔顿看来,审美或叙述形式本身就是某种意识形态,是作家与他(她)所面对现实之间的一种关系隐喻,但传统研究多是文学表述中放大了哪些女性形象/情节,又压抑了哪些等内容层面的研究,对其所采取的是吸引性叙事还是疏离型叙事、隐含作者与叙述人/人物之间有无话语距离,内中体现出怎样的社会性别问题等的关注尚相对较少。
形式研究关注叙事人、叙事视角、叙事结构、叙事修辞等形式要素体现的性别权力关系,新世纪以来随着私人化写作的相对沉寂这方面的研究热度似乎下降了。然而,当下文本中的文体创新并未终止,出现了“超越既往的社会层面和实验层面,走向文本和人本,走向生活世界,外表老实,骨子里其实是很现代的”[43]86的趋向。也可以说,新世纪文学的形式实验不像20世纪末那么张扬、极致、不避极端,而是深入到文学文本的叙事机理,以包容性较强的方式呈现出来。另外,群体性的叙事形式变革也相对少见了,作家的个性意识、独立品格进一步彰显,无论是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相比,还是在写作者个人的作品谱系中,似乎更加努力追求叙事文本的独树一帜性。因此,并非新世纪文学中不再有女性主义叙事学的文体因子,而是学术界缺乏对它们的发现、阐释。具体来说,笔者认为可以从这样几点推进其研究策略:(1)叙述人、叙述视角、叙述距离层面的叙述主体研究,像暴露叙述、介入性与情绪性叙述等追求话语权威感的叙述转向,经验自我与叙述自我在阶层、趣味、性别层面刻意拉开距离的反差性、反串性叙述在新世纪文学中何以可能,其内在机理是什么;(2)集体型叙事与叙述对象的复数化研究,像个人化叙事的自传体写作在新世纪文学中相对沉寂,但关注弱势人群的集体型叙事态势发展势头良好,有些女性非虚构写作关注内容上不限于女性议题,形式上却暴露了性别倾向,像针对农民、打工者等边缘性群体采用的共言、轮言等集体型叙事方式等,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3)叙事结构、叙事语言、叙事风格层面的叙事话语研究,像繁复枝蔓的叙事语言、旁逸斜出的叙事风格所构成的碎片化叙事特征,其与伊瑞格瑞“女人话”理论有什么内在联系,拉长叙事时间、减缓叙事节奏的细节描写也有以颠覆文学成规的方式呈现边缘化性别处境的阴性特质吗?为什么“慢时间,碎生活”的碎片化叙事会从私人化写作时期的同故事叙述蔓延到面向社会历史的异故事叙述?(4)传媒时代微博、微信、手机文学的零散化、片段性存在,呈现出的个性化情感、自恋性表达、互粉性阅读等与女性特质有什么联系?这些文本的流行能够促进社会性别建构朝向更中性化,甚至女性化的方向发展吗?网络文学中女性社群的建构能够顺理成章地衍生出那种只面向女性受众的“女性向”叙事吗?其与传统女性写作有什么区别和联系?这一系列问题均可以在叙事形式的社会性别研究层面得到更充分的学理阐释,修正传统上性别政治研究的简单化、模式化思维,打破多以盘点、概览、新作快评、个案追踪等应对新世纪文学现象的感性化、浮泛化、零散化弊端,增强女性文学研究的学理性、专业性、国际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