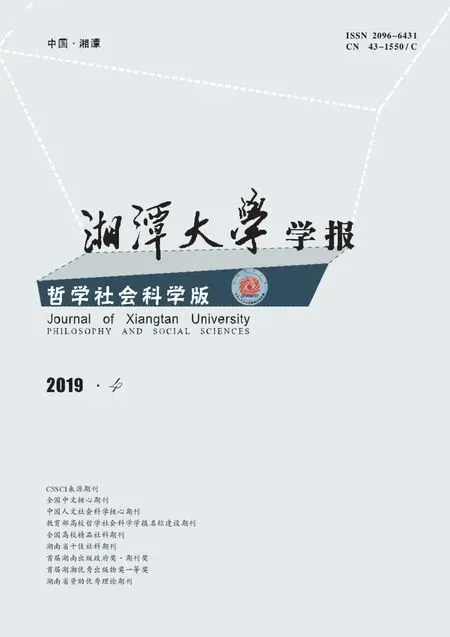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的可专利性及权利归属*
2019-02-22刘友华魏远山
刘友华,魏远山
(湘潭大学 法学院, 湖南 湘潭 411105)
随着深度学习与算法技术的快速发展,人工智能逐渐从“工具”转向“创新实体”,参与到发明创作过程。雷·库兹韦尔预言,到2045年人工智能将全面超过人脑(称为“奇点”)[1]2。那么,在“奇点”之后,强人工智能(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AGI)或超人工智能(Artificial Super Intelligence,ASI)独立完成的某项技术设计是否应当得到专利法的承认呢?立足于现行专利法框架下或许难以给出明确答案,这映射出人工智能异于自然人的特征导致专利制度难以囊括人工智能生成的技术方案,这无疑对现行专利法提出新挑战。因此本文主要讨论“奇点”之后人工智能可能对专利制度产生的冲击。主要体现在:一是为何要用专利法保护人工智能生成的技术方案?二是人工智能是否具有专利法意义上的主体资格?三是人工智能生成的技术方案是否属于专利法保护的客体范围?四是如人工智能生成的技术方案属于专利法保护的客体,那专利“三性”的审查要求又是什么?五是若人工智能生成的技术方案应当授予专利权,那么权利应当如何配置?
一、以专利法保护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确有必要
在回答为何要以专利法保护人工智能生成的技术方案之前,需明确为何要对人工智能生成的技术方案进行保护。
(一)为何要保护人工智能生成的技术方案
人工智能生成的技术方案是否要保护,争议颇大。其中,持反对意见的学者认为,“先行者优势”为人工智能生成的技术方案提供了足够的激励,无需再对人工智能生成的技术方案提供特殊保护,否则将损害市场秩序。[2]312-313在经济运行过程中,供需关系的改变导致价格波动会对资源进行分配、组合、再分配和再组合。据此,在人工智能领域不需对人工智能生成的技术方案进行特殊保护,直接通过市场予以调节即可。另外,人工智能的研发团队主要集中在企业或高等院校,企业追逐经济利益,高等院校的科研人员为了名和利,不会怠于研发。[3]65因此,人工智能的发展可不再需要专利制度的保驾护航,不授予人工智能以专利法主体资格,也不授予人工智能生成的技术方案以专利权也合乎法理。
但多数认为应保护人工智能生成的技术方案。理由如下:
一是保护私权的要求。人工智能产品或系统作为民法上的“物”,权利人对其享有所有权。保护人工智能产品就是保护权利人的私有财产。人工智能生成的技术方案自然也是权利人的财产,应当得到法律保护。也就是说,人工智能生成的技术方案是人工智能的“自然孳息”,按照民法的基本教义,“孳息”的权利归属遵循(物权法)“母物主义”与(债法)“交付主义”[4]13-19,因此,人工智能生成的技术方案应当根据具体情形归相应的权利人所有,并受到现行法律的保护。
二是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的需要。保护人工智能生成物能够有效促进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需要激励相关从业者进行研发。对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保护能够激励人工智能相关从业者更加愿意投入精力研发。另一方面,当技术不能获得保护时,权利人将需耗费大量精力去阻止他人使用该技术。尽管将技术作为商业秘密是一种较为便捷的保护方式,但不利于技术信息的传播与共享,不利于技术创新与进步。为此,对人工智能生成物提供保护是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三是增进社会福祉的需要。人工智能技术具有重要的价值,其发展与应用不仅极大地便利了生活,同时也可以产生较好社会利益。若人工智能生成的技术方案能满足实用性要求,则说明其具有投入商业使用的价值,可能产生较好的经济效果。因此,通过保护人工智能生成的技术方案,不仅能促进技术变现和投入商业使用,还可激励相关权利人发展人工智能技术,以达到“连锁”激励效应,增加社会福祉,让公众享受技术发展的红利。
(二)为何要用专利法保护人工智能生成的技术方案
促进技术发展的方式有很多。直观的反射意识多将技术保护与专利法连接,其以一定时期的垄断保护发明人的利益并促进相关技术的公开。人工智能生成的技术方案可选择专利法保护。理由主要有:《专利法》第1条开宗明义地指出专利制度的目的是保护专利权人的合法权益、鼓励发明创造、推动发明创造的应用、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经济发展。授予人工智能生成的技术方案以专利权完全符合专利法的立法初衷。
首先,授予人工智能生成的技术方案以专利权是保护人工智能使用者合法权益的当然要求。人工智能本身是研发者们追求的目标,由人工智能产品所生成的技术方案则是使用者使用人工智能的结果,是个人劳动所得。若该技术方案属于可专利的客体,应得到专利法的承认,以保护人工智能使用者的合法权益。
其次,授予人工智能生成的技术方案以专利权是促进技术创新的要求。专利法保护技术方案就是为了促进技术创新。通过授予专利权激励发明人进行发明创造和公开技术信息,以便社会公众可在前人基础上继续努力,避免重复发明,从而促进技术创新。保护人工智能生成的技术方案符合专利法促进技术创新的目的。
再次,授予人工智能生成的技术方案以专利权有利于推动发明创造的应用。专利法通过肯定技术的专利属性,将专利技术公布于众,避免技术持有人因担心他人模仿而将技术作为商业秘密保护,增加专利技术被许可实施的可能性,减少或避免社会闲散资源被浪费。人工智能生成的技术方案在面世时也面临此种困难。如果专利法不将人工智能生成的技术方案视为可专利的主体,那么很可能导致这些技术无法问世,不利于推动发明创造的应用。
最后,授予人工智能生成的技术方案以专利权有利于促进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自人类进化开始,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离不开技术的支持,技术进步与发展的速度不仅决定着生产力,还改变了既有的生产关系。正如党的十九大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并对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做出战略部署。”[5]“创新始终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的重要力量,也始终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6]以专利法保护人工智能生成的技术方案,引领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通过技术创新带动社会经济发展。
二、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属于可专利主题范围
一项技术方案欲获专利法保护,就必须属于专利法保护的范畴。我国《专利法》采取了“正面定义”与“反面排除”的方法阐释了可专利的主题范围。《专利法》第2条对专利法保护的客体做了相对明确的界定,同时又在第5条和第25条列明了例外情形。人工智能生成的技术方案是否满足《专利法》第2条规定,又不属于第5条和第25条所列举的范围是其能否获得专利法保护的关键。
人工智能生成的技术方案是否属于《专利法》第5条所列出的违反法律活公共道德的情形很容易甄别。一般而言,人工智能生成的技术方案多属制造方法或操纵方式。《专利法》第5条第2款规定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获得”或“利用遗传资源”的情形显然与人工智能生成的技术方案相去甚远。至于是否属于第5条第1款之规定,则应看具体情形,在既不违反法律规定、社会公共道德,也不妨害公共利益的情况下,应给予人工智能生成的技术方案以继续审查的机会。
在《专利法》第25条列举了六种不授予专利的情形中,人工智能生成的技术方案面临的最主要的诘难是不属于“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这一情形。人工智能归根结底是在计算机技术的基础上诞生的,而计算机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是运算和数据处理技术。若人工智能生成的技术方案不是计算机程序算法,则受到《专利法》第25条挑战的可能性不大。但生成的技术方案是计算机程序算法,就涉及到一个复杂的问题——计算机程序算法是否受专利法保护?
程序算法可否成为专利法意义上的客体历来颇具争议。自程序算法出现至今,其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程序代码被视为作品,背后的算法被视为思想而得不到专利法的承认与保护;第二个阶段,部分与计算机结合的程序算法被专利法所接纳;第三个阶段,计算机程序与传统工业系统结合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系统已顺利进入专利法客体范畴。[7]134-136但仅程序算法本身是否可以获得专利法保护呢?考察专利保护客体自物理产品扩展到方法的发展史,就可发现从具体产品到抽象方法的扩张采取的是“物质状态改变”的审查思路。如早在1795年的英国,Boulton v. Bull案法官认为“原则”不能获得专利保护,但体现在有形物质中或者与之相联系,表现为操作步骤、产生效果的“原则”可以获得保护。(1)Boulton v. Bull (1795) 126ER 651.随后英国在前案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单纯的方法可以获得专利保护。对此,美国亦有相似的判例。在Cochrane v. Deener案法院认为“一种方法是指处理特定物质材料以产生预期结果的一种模式,它是一个行为或者一系列行为,作用于客体并改变其状态或将其变成另一物体”。(2)Cochrane v. Deener, 94 U.S. 780, 1877.这种要求方法专利与有形之物结合的观念对专利制度影响深远,正是“物质状态改变”要求使专利审查时相对明确便捷,也使专利权利范围更加清晰,使侵权相对更易认定。
程序算法不能获得专利保护的主要理由是由于程序算法被认为是数学计算方法(思维步骤)且作用于抽象意义的数据。首先,抽象思维不可被专利制度接受的原因在于思想的共有性和不同主体思维方式之差异导致技术方案的不确定性。其次,算法天然与数学计算规则紧密相关,数学计算规则作为公有的基础研究工具不能因专利制度的存在而阻碍相关研究推进。最后,程序算法作用于抽象意义的数据意味着程序算法无法产生“物质状态改变”的现实有形结果,不符合方法专利所要求的“对计算机外部对象或内部对象进行控制或处理”。[8]260
但由“抽象思想不得获得保护”催生出的“单独的计算机程序本身视为数学计算规则而不可授予专利权”的观念,忽略了程序算法的目的是为了运行独立于人脑的计算机系统,也忽略了程序算法运行后导致“对计算机外部对象或内部对象进行控制或处理”的“物质状态改变”的客观现实。首先,程序算法作为操作计算机的方法是独立于抽象思维步骤的。在程序算法与计算机结合之前将其视为抽象思维步骤尚具一定说服力,但程序算法本身作为一项操作计算机的方法,在与计算机结合的刹那就独立于思维步骤。其次,程序算法作用对象虽是数据但依然符合“物质状态改变”要求。一方面,计算机作为一种物理装置,程序算法运行计算机必然导致计算机本身出现变化或使计算机作用对象发生改变,这与传统操作机器的方法专利技术方案并无不同。另一方面,程序算法依然符合“物质状态改变”的要求。程序算法作用于计算机装置(晶体管、二极管等)改变了计算机内电子、电磁等物理状态并最终以数据变化显示出来。
程序算法并没有颠覆经典专利理论基础,并严格遵循这些理论的指引,承认程序算法的可专利性并不会导致专利制度的萎靡。在人工智能生成的程序算法技术方案可否得到专利法保护问题上,延续上述进路分析答案是肯定的。
三、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的专利“三性”问题
在解决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属于可专利范畴后就需考虑专利审查的问题,即人工智能生成的技术方案欲获专利法保护须接受专利“三性”的考验。
(一)实用性:技术的可再现性和价值性
实用性要求专利技术能投入产业使用,并能产生积极效果。包括:一是技术能够再现;二是技术具有积极效果;三是达到实用程度。[9]150-151考察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的可实用性需要逐步解析上述要求。
首先,可再现性问题。《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第29条第1款规定,发明人必须以“清楚且完整的方式”公开其专利技术,以便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能够实现该技术。充分公开发明创造的内容既是专利取得的前提条件,也是取得专利权后专利权人应尽的义务。同时,这也是体现专利权人和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平衡。人工智能以算法为核心,但算法素有“维度的诅咒”之称[10]78,其复杂性可想而知。但人工智能复杂的工作原理并不影响技术方案的可再现性。第一,再现技术方案需要分两种情况:由自然人自主实施以及由自然人控制人工智能机器实施。如果由自然人实施,那么应当注重技术方案的可理解性,由一般技术人员“无需过度实验”(3)“无需过度实验”标准是指熟练技术人员“无需付出创造性劳动”就能实施一项技术方案,但在某种程度上“无需过度实验”标准要优于“无需付出创造性劳动”标准。参见崔国斌.专利法:案例与原理[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318-319.就可再现专利技术;如果由自然人控制人工智能机器实施,则对可理解性要求更低。因此,技术的可再现性并不影响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的可专利性。
其次,就技术方案效果达到实用程度和技术方案具有积极效果要求而言,这两个要求与人类发明的技术方案判断并无二致。人工智能生成的技术方案与人类生成的技术方案同样面临这两个要求的考验,其判断方式并不会因技术方案生成主体的不同而有所差别。因此,这两个要求并不能遏制人工智能生成的技术方案进入专利法保护的客体范围,且具体的判断方式可参照既有规则。
(二)新颖性:绝对新颖性的澄清
新颖性是指在申请日以前没有同样的发明或实用新型在国内外出版物上公开发表、在国内公开使用过或以其他方式为公众所知。[11]181新颖性要求技术方案与现有技术相区别。具体表现在专利技术在申请日之前不存在使其无效或丧失新颖性的证据。据此,需要对现有技术进行界定。专利法上对现有技术的界定采用了“绝对新颖性”标准,即要求在该技术申请之日之前不是国内外为公众所熟知的现有技术。
在现行审查规则下,以审查员人力检索为限,验证拟申请专利的技术方案是否因现有技术而丧失新颖性。但人力之可及有限,加之术业有专攻,作为“普通人”的专利审查员难以穷尽所有领域的现有技术。即使美国采取了“专利申请人信息披露义务”制度,要求专利申请人诚实善意地披露在先技术,并以“审查员标准”和“初步证据标准”进行限制,要求披露更多的信息以维护公共利益,[12]134但也难免存在疏忽,无法完全排除现有技术被纳入保护范围。人工智能强大的检索能力和学习能力,以现行新颖性审查标准(人力审查)考察人工智能生成的技术方案,因人力之有限,将给人工智能无限大的空间去挖掘现有技术的组合,造成不必要的技术垄断,甚至可能妨碍创新。
但从绝对新颖性角度看,新颖性并不是阻碍人工智能生成的技术方案获得专利法保护的绊脚石。在理论上,现有技术范围并不因人工智能的出现而扩大或缩小。出现人工智能影响新颖性错觉的原因有二:一是人类检索能力较弱导致将本不应授权的技术方案纳入专利法保护范围,并被人类视为理所应当;二是以人力极限作为衡量人工智能的标准将导致制度混乱。绝对新颖性要求在专利申请日之前国内外已有的公知技术即可使技术方案的新颖性丧失,人力所限致使本不应授权的技术方案获得授权实属技术局限,但其不是专利制度所盼,不具有制度正当性,理应被肃清专利制度之外,人工智能技术恰好为此提供了契机——将人工智能引入专利新颖性审查可完美解决上述问题。即在进行新颖性审查时,以人工智能强大的检索能力为助力,不论是自然人设计的还是人工智能生成的技术方案,均以人工智能检索为准,不仅有利于肃清人力所限(无法检全)之“毒果”还专利制度以纯洁性,还能较好应对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之挑战。
(三)创造性:提高“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的标准
新颖性和创造性在专利审查中属于一种递进的关系。只有该技术方案具备新颖性的条件下方有必要对其进行创造性审查。创造性要求专利技术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非显而易见性。创造性虽以虚拟的“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眼光判断,但实践中还是需要依靠审查员根据其知识水平进行甄别,导致创造性判断具有一定的主观性。
不过,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创造性审查被质疑的原因主要在于人工智能生成的技术方案将轻易满足现有创造性要求,挤压人类发明空间,实质上提高了发明创造的门槛,可能抑制创新的积极性。从人类的角度看,将不同学科或领域的知识或技能组合是可能具有创造性的,按照现行的专利制度属于专利法保护的范围,即选择发明和组合发明(4)“选择发明”是指从许多公知的技术方案中进行选择,取得了预想不到的效果的发明;“组合发明”则是指将新技术与现有技术进行组合,或将几种现有技术进行组合,组合后技术效果超过了各种技术的综合。参见冯晓青,刘友华.专利法[M].法律出版社2010(2012年重印版):115.。但对人工智能来说,因其具有强大的学习能力、超凡的信息获取能力和处理能力,对不同领域或学科的知识进行组合实属稀松平常,无法体现创造性。在相同标准下人工智能因技术优势会较为轻易地通过创造性审查,实质上是提高了人类发明家发明创造的门槛,按照现有的以自然人为中心的创造性判断标准来衡量人工智能生成的技术方案的创造性,这种判断方式反而降低了人工智能生成的技术方案的创造性标准,可能打击人类发明者的积极性。
如没有人工智能的出现,人类发明出人工智能生成的技术方案只是时间问题。人工智能的出现仅仅是提前将这些技术方案发明出来,并未减损社会公众的利益,反而提前将技术变为现实促进了技术发展。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会成为发明创造的主力军,届时以自然人发明时代的“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标准衡量难免不当。因此,可适当提高“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的标准,严格限制非显而易见性的要求。
四、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的专利权归属
在讨论完人工智能生成的技术方案专利“三性”问题后,如果人工智能生成的技术方案符合“三性”要求,则应进一步讨论专利权利归属问题。
(一)人工智能专利主体资格之辩
知识产权制度的目标分为直接目的与终极目的,直接目的主要是保护知识产权人的权利,终极目的是促进知识和信息的广泛传播,促进科学、文化进步与经济发展。[13]44-45专利制度又以“保护专利权人的利益,促进技术发展、技术应用”为宗旨。[14]357-379知识财产是自然人的智慧成果,体现了作者、专利权人或商标权人对创造物的独有个性,通过赋予权利人一定期限的专有权利,来促进科学技术、文化产业的创新与发展,进而推动社会经济。人工智能是人造的智慧机器,按照既定的算法程序进行运作,虽智能化而逐渐摆脱人为的干预,但不能体现人的思维过程。因而人工智能不可成为专利法主体。
首先,法律和经济学理论无法适用于人工智能发明创造场景。“交易论”或契约理论认为如果有奖励,将会鼓动人们从事发明创造。[15]10在人工智能发明创造过程中,激励作为人类特征的概念通常被认为是没有意义的。人工智能开始创造之前、创造过程中以及之后,人工智能不需要任何激励——这种激励只与人相关,机器无法回应激励。
其次,洛克劳动理论无法为人工智能发明创造提供理论支撑。洛克劳动理论的前提是“上帝将世界以共有的形式赐给全人类”。[16]42人类享有生存与发展权,为了生存和发展需要“个人从共有物中拿走自己的劳动及附加物,给其他共有人留下足够且同样良好的东西”具有正当性。[17]75-76在自然人发明创造过程中,思想是共有的,个人的构思使知识共有物总量扩大,个人仅就构思应用申请专利权,知识共有物的总量不随专利权的授予而减少,反而因专利技术的公开扩大。但人工智能无生存与发展权利需求,不存在生存和发展需要而撷取公有物,不属于洛克劳动理论适用对象。
最后,黑格尔的人格权理论适用困难。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构建了“意志—人格—财产”的基本范式,当抽象意志发展到实在意志时,意志就成为单一意志——人。黑格尔进一步指出人的本质是人格,抽象的人格与自由意志的定在需要工具主义的财产,当人将自己的意志体现在物内就衍生出“所有权”的概念,并进一步论证了“精神所有权”的概念。具象的财产就是抽象的人格,精神产品是人智力的创造物,与特定的主体的人格相关,从而为知识产权的合理性提供了依据。[14]96-99然而,人工智能只是人为制造的机器,虽然能够独立发明,且有部分学者也致力于论证应赋予人工智能以法律人格,但目前通说观点依然认为人工智能无法取得哲学上的“人格”,不能获得财产,不具有法律主体资格。
因此,人工智能作为人为创造的机器,不论能否产生自己的意志,在现阶段其不具有人格权,也就不能占有财产,更谈不上获得专利权。质言之,人工智能既不属于专利法意义上的发明人,也不是专利权的享有者。
(二)人工智能:名义上的发明生成主体
如前所述,人工智能既不属于专利法意义上的发明人,也不是专利权的享有者。但考虑到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确实不是自然人发明的事实,应就专利技术方案本身做一定区分,以提示技术方案使用者哪些专利技术是人工智能生成的,哪些是自然人完成的。对此,我们认为可将技术方案发明主体署名做一定分类,以便于表征人工智能生成的技术方案:将发明主体一栏分为自然人和人工智能主体。即如果技术方案是由自然人发明创造,则在自然人一栏进行填写;若是人工智能生成的技术方案,则在人工智能一栏写明由人工智能生成,并注明人工智能的所有者、生产者等信息。
在专利申请文件中可以表明某一项技术方案由人工智能生成,并不是承认人工智能作为专利法意义上的主体,也不是承认人工智能具有法律人格。我们如此主张是出于社会公众的信赖利益和诚信原则,告知潜在的技术使用者,其欲使用的技术是由人工智能生成。
标明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的另一好处在于避免自然人以欺骗的方式谎称该技术方案由其生成。虽无法完全杜绝自然人谎称自己是发明人而申请此类专利,但至少给了人们选择诚信的机会。
(三)自然人:专利经济收益权享有者
既然人工智能不可取得专利权,那么相关的自然人是否可以得到专利权利?在世界范围内,将人工智能生成物权利归属于自然人的立法已有可鉴之本。英国《著作权、设计和专利法》第9(3)条规定对作品的生成做出必要安排的人是著作权人。(5)UK Copyright, Designs and Patents Act 1988. § 9(3) In the case of a literary, dramatic, musical or artistic work which is computer-generated, the author shall be taken to be the person by whom the arrangements necessary for the creation of the work are undertaken.在专利法领域也可借鉴著作权领域的规定,赋予相关自然人以专利权。人工智能系统的成熟涉及到多方主体,如数据提供者、AI研发者、AI所有者、AI使用者、社会公众、政府或国家、投资者等。不过,按照贡献重要程度,能够有权主张专利权的主体并不多,数据提供者、社会公众、政府或国家、投资者贡献小,充其量也是候补人选,唯有人工智能研发者、人工智能所有者和人工智能使用者有权主张权利。
在弱人工智能时代,研发者为了人工智能的诞生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在强或超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研发者的角色逐渐式微。人工智能研发者的主要任务是提高人工智能的智能化水平,因其研发而对人工智能本身享有权利。随着深度学习等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逐渐摆脱了人类的预期,当人工智能“独立”发明时,人工智能更多根据所拥有的素材输出技术方案。人工智能研发者对人工智能生成的技术方案干涉甚微,无法主张权利。
由上可知,人工智能生成的技术方案的专利利益分配集中在人工智能所有者和使用者之间。当人工智能所有者和使用者为同一主体时,人工智能生成的技术方案的权利归属自不待言。但二者不为同一主体时,人工智能生成的技术方案的权利应如何分配值得深探讨。有学者认为可效仿英国《著作权、设计和专利法》之规定,对人工智能生成物进行实质或必要安排的自然人享有权利。[18]163也有学者认为,出于社会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的考量,将人工智能生成的技术方案的专利权授予人工智能所有者,可能较授予人工智能使用者更为可行,而且还能促进技术的进步。[19]331-332可见,不论是将权利授予人工智能使用者还是授予所有者均有其理由。但我们认为,相比于将人工智能生成的技术方案的权利赋予人工智能所有者而言,将权利赋予人工智能使用者更合理。具体理由如下:
第一,人工智能使用者使用或操作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工智能使用者的精神情感或智力投入,相比于人工智能所有者而言,更具合理性。因为在人工智能参与发明的情形中,人工智能使用者对素材进行筛选,由此得到的人工智能生成的技术方案实际上体现的是人工智能使用者的智慧或安排,人工智能使用者也更加重视人工智能生成的技术方案。当人工智能所有者与使用者非同一主体时,人工智能所有者将人工智能出借或租赁给他人使用,其对人工智能使用者的操作意图和发明意向并未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帮助,当然不可获得专利权。这符合专利法一般法理。即使在传统环境下,将某一物品(不可从该物品中轻易得出发明构思)提供给他人用于发明,物品提供者也不可以获得专利权。
第二,从经济效益角度看,将人工智能生成的技术方案的权利赋予人工智能使用者更属最优化配置。市场资源的最优配置,不仅是经济法追求的目的,也是专利法,乃至知识产权法追求的价值目标之一。按照科斯定理的论述,在信息对称、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如果产权明确,不管产权最初如何分配,资源都会得到有效配置。[20]104-117在忽略交易成本的假定下,相较于人工智能所有者,人工智能使用者更加重视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只要在收益大于成本的情况下,不论初始权利如何分配,人工智能使用者都愿意交易获得人工智能生成的技术方案,达到效益最大化。但现实的交易成本不可忽略,为了达到效益最大化,应尽可能地将权利赋予最重视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的人——人工智能使用者,或者尽可能地减少交易环节。相比于后一种方案,将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的权利直接赋予人工智能使用者更为简洁,也更符合经济原则。
五、结语
人工智能生成的技术方案属于可专利客体,若符合“三性”要求应得到专利法保护。囿于人工智能不具有法律主体资格,无法享有权利,比较人工智能使用者、所有者和开发者的贡献程度,将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权利赋予人工智能使用者。总体而言,当前对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专利保护的正当性论证较多,但对于不同发展阶段,就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应确定何种专利权利分配规则,才能平衡开发者、所有者与使用者利益,更好推动相关技术及产业发展,仍值得深入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