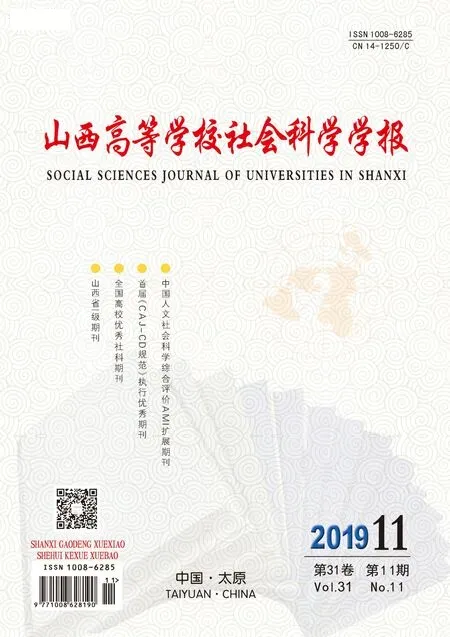朱熹《大学》“正心”工夫研究
2019-02-21陈清春
陈清春,李 彤
(山西大学 哲学社会学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一、引言
南宋时期,朱熹集结《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称为四书,并为此四书详细做注,以阐释其理学思想。朱熹尤其重视对《大学》文本的注释,作《大学章句》,恐学者尚有不理解之处,又作《大学或问》来释疑,自称“章句”是《大学》的注脚,而“或问”“乃注脚之注脚”。对于《大学章句》,朱熹一生用功最多,曾言:“我平生精力尽在此书,先须通此,方可读书。”[1]258对于《大学或问》,他则认为“学者且去熟读《大学》正文了,又仔细看章句。或问未要看,俟有疑处,方可去看”[1]257。由此可见,为了让学者能完全掌握《大学》一书,朱熹做了大量的解释工作。在儒家思想中,无论是理学还是心学皆把成为圣贤作为最终的目标,而在朱熹看来《大学》就确定了成为圣贤的总“规模”与“纲领”,确定了为学需要遵循的“等级次第”。《大学》同时也是学以成圣的“根脚”,而且“论孟中庸”都有待于《大学》的“贯通浃洽”,所以为学需从《大学》起,掌握了根本才能再进一步扩充完善和深入。
《大学》中具体的“八条目”工夫,从本末论,朱熹以“修身为本”,此修身是广义上的修身。有人问朱熹:“《大学》一书,皆以修身为本。正心、诚意、致知、格物,皆是修身内事。”朱熹回答:“此四者成就那修身。修身推出,做许多事。”[1]252也就是说“格致诚正”统一于修身,皆为本。朱熹又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这五个工夫条目分成知和行两个方面。朱熹言:“格物、致知,便是要知得分明;诚意、正心、修身,便是要行得分明。”[1]264他论知行关系:“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1]148朱熹论知行,言轻重先后并不是要截然划分这些工夫,而是强调知行工夫的相互作用,强调两个工夫的不同作用。他说:“徒明不行,则明无所用,空明而已。徒行不明,则行无所向,冥行而已。”[1]1575所以对于朱熹来说,每一个工夫环节都是至关重要的,需要“节节用工”,并且各个工夫之间需要遵循次第顺序,节节展开。
“正心”在朱熹的工夫论中为“本”,属于“行”的工夫,是为学成圣贤的重要环节之一,但目前学界对朱熹“正心”工夫的研究较少,且不够深入。笔者认为,“心”在朱熹的理学体系中是非常重要的范畴之一,它的内涵极为丰富。作为工夫论,需要在“正心”的语境下,详细厘清“正”与“心”的内涵,才能更明确地认识“正心”工夫论,才能进一步明确朱熹工夫论的主旨。
二、正心之“心”
朱熹认为人区别于万物,就是因为人之有心,而且“人心虚灵”可以包含众理,因而为学成圣贤的关键就在于人有心。因此,“心”在朱熹的哲学思想中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朱熹的哲学系统中,“心”可以从纵横两个向度来理解。从横向看,“心统性情”;从纵向看,它是沟通宇宙界、本体界(天理、道、太极)和人生界的桥梁[2]。本文从《大学》中“正心”工夫入手,所讨论之“心”仅限定在朱熹注释的《大学》文本中,即心性层面的意义,因此对“心”的研究从其横向展开,强调在“正心”这个范畴下理解“心”的内涵(1)为了清楚区分“心”的多重意义,用带引号的“心”特指“正心”中的“心”。。
首先,先从朱熹对“中和”这一命题的理解上认识他的心性情论。朱熹早年受教于李侗,李侗传承道南学派重视《中庸》的“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之说,特别强调“体验未发”的工夫,李侗着重引导朱熹在此处用功,但朱熹并未得到任何体验,不过,这引发了他对中和问题的深入思考。“丙丑之悟”后,朱熹悟出心不分已发和未发,凡言心皆是已发的状态,在《中和旧说序》中他说道:“人自婴儿以至老死,虽语默动静之不同,然其大体莫非已发,特其未发者未尝发耳。”[3]所谓“中和旧说”的主旨如他所言就总结为“心为已发,性为未发”,此时的性与心是体用的关系,工夫的所在就在于心之已发处。后来经过“己丑之悟”,才确立了他的心性观,认为心是兼有已发未发。他说:“已发未发,只是说心有已发时,有未发时。方其未有事时,便是未发;才有所感,便是已发,却不要泥著。”[1]1509心时刻都在,未与事相接时保持寂然不动,只要遇事有所感就是已发。他还说:“据性上说‘寂然不动’处是心,亦得;据情上说‘感而遂通’处是心,亦得。”[1]90他将心看成是一个更高的主体,包含已发未发之时。心与未发之性、已发之情是不同的概念,有不同的意义,性与情是心的一体两面,心可以统摄性情。中和新旧之说,对心的已发未发问题的探讨实际上也直接影响了朱熹的心的工夫,“中和新说”之后,对“心”之工夫的说明更加全面,既有“寂然不动”的涵养工夫,又有“感而遂通”的工夫。
其次,再从朱熹对“心统性情”这个命题的理解上认识他的心性情论。“心统性情”这一命题由张载提出,朱熹经过长久的思考,在经历了“中和新说”的思考之后,基于理学思想对这一概念又进行了更为详细、更合逻辑的解释。朱熹认为“心统性情”之“统”是心统得体用、动静、已发与未发。“统”字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从心的结构上说,有“兼”之意,“‘心统性情。’统,犹兼也”[1]2513。心包含体用和已发未发两种状态。他言:“心统性情,故言心之体用,尝跨过两头未发、已发处说。”[1]94在朱熹看来,在心、性、情的三分结构中,心包含性情,而性与情是心这个总体的不同层面,都从属于心。从心的功用上说,“统”有“主”“管摄”“主宰”之意,即正心的工夫、主体之心,心“主乎性而行乎情”,是做工夫处。从其主宰意讲,心主已动和未动。朱熹言:“性是未动,情是已动,心包得已动未动。盖心之未动则为性,已动则为情,所谓‘心统性情’也。”[1]93心从总体上对性和情有主宰作用,也就是理性思维对情感的控制和调节。
由此可知,朱熹将《大学》中“正心”之“心”,当情之意讲。《大学》原文云:“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朱熹在注释中依程子将“身有之身当作心”字讲,并且认为“忿懥”“恐惧”“好乐”“忧患”此四者“皆心之用”[4]9。“忿懥”之类皆是心之所发而来,谓之情。情是心之动、心的已发状态,也就是心之思虑与事物相接时的状态,应物而产生喜怒哀乐之情,所以所“正”之“心”皆是此“忿懥”之类的情。从这些情的善恶的问题上看,他认为“性无不善,心所发为情,或有不善”,“心之本体本无不善,其流为不善者,情之迁于物而然也”[1]92。在他看来性是纯善无恶,而情有善有不善,这不是说情本身为不善,而是由于情会“迁于物”而为不善。与物相接时,心发出喜怒哀乐之情,这些并非是要做工夫的情,要做“正”工夫的是由于心迁于物、有所偏、有滞留的情。朱熹不是要反对人情感正常表达和流露,要人彻底没有喜怒哀乐之情感,而是强调人当有此情。他说:“心有喜怒忧乐则不得其正,非谓全欲无此,此乃情之所不能无。”[1]343当遇事时,心不得其正,情有所偏时,才是做工夫之时。做工夫的主体之心,若不主宰情,情就会受物欲的遮蔽,为物所动而陷溺本性。因此需要做“正”的工夫,使心恢复本来的“湛然虚明”的状态或情的无偏的状态。
朱熹所讲的主宰之心就是我们所说的理性;需要做工夫的“心”是有所偏的情。理性对情感以调节和制约,即通过“格物、致知”而来的理性道德观念对情之偏而产生的非道德观念进行制约,使情之发合乎理。
三、正心之“正”(2)为了区分形容词和动词意义下的“正”,将工夫论意义上的“正”用带引号“正”标注。
对于正心之“正”要在两个语境下理解。一是在“心正”一词中,作为形容词意讲,是做工夫的目标所在,从概念上来理解,需要区分什么是正的“心”,什么是不正的“心”;另一个则是在“正心”一词中,作为动词意讲,表示工夫的具体办法,“正”不正之心是工夫论的层面。
有人问朱熹,是否心在遇事时像槁木死灰一般没有喜怒哀乐就可被称为正?朱熹不同意此说,认为人遇事时必当有喜怒哀乐之情,若如槁木死灰一般反倒不能称之为正。遇事时当喜则必然要喜,若当喜却怒了就是不正;遇事时当怒也必须要怒,若当怒时不怒也不能说是正。他说:“好、乐、忧、惧四者,人之所不能无也,但要所好所乐皆中理。合当喜,不得不喜;合当怒,不得不怒。”[1]343因此,喜怒哀乐之情不光是人所必然有的,更重要的是要在人该有此情的时候有,这样此情的表现才是合理的。而工夫所在之处就是要在遇事的过程中,在这喜怒哀乐的所发之“情”中展开。
1.从正的形容词意义上讲,朱熹明确区分了什么是正,什么是不正的情况。什么是正?首先,从朱熹对“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庸》)这句的注释上来理解。前一个“中”字是“体”、是“时中”的含义,形容未发时的本体状态;后一个“和”字是说情之发中节,也就是《大学》中的正的状态。从程度上说,朱熹认为无过无不及的情之发才是正,是一种时中的正的状态。他说:“且如喜怒,合喜三分,自家喜了四分;合怒三分,自家怒了四分,便非和矣。”[1]1512同时,当喜则喜,当怒则怒就是“通达”了,通达了也就是心正的状态。其次,从朱熹对“不迁怒”的注释上来理解正。朱熹认为,并不是说遇可怒之事却叫人不去怒、去做静的工夫,而是要当怒则怒,其关键之处就在于对某一物的所怒之情“不迁”于另一物之上,即是正。他认为:“且如当怒而怒,到不当怒处,要迁自不得。不是处便见得,自是不会贰。”[1]772也就是说,我们在遇一当怒之事怒了,再遇下一事时就不能再延续上一事怒的情,这样才是正。朱熹用镜子类比人心,镜子在照物前不可先有一影像在,同样人心在应物之前不可先有一喜怒哀乐在,否则就会“失其正”。他认为,心要“随感而应”,过了恢复“湛然虚明”即是正。同时,朱熹认为,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也正是在于此。君子过则“不迁”,而小人会随着喜怒哀乐而去。朱熹言:“人心本是湛然虚明,事物之来,随感而应,自然见得高下轻重。事过便当依前恁地虚,方得。”[1]347对于朱熹来说,心之正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情之发无过无不及,另一个则是要过则平。
那么,什么是不正?《大学》言:“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何为“有所”?朱熹认为:“四者人不能无,只是不要他留而不去。如所谓‘有所’,则是被他为主于内,心反为它动也。”[1]344“有所”就是把喜怒哀乐留于心上并成为主导,本心为其所动。喜怒哀乐之情本是应物而生,也应随物而去,在心中滞留,就会主导了心,失掉心本来的“湛然虚明”的状态,失去公正,就成了不正。他又说:“因人之有罪而挞之,才挞了,其心便平,是不有;若此心常常不平,便是有。”[1]344简而言之,喜怒哀乐过则平就是“不有”,就是正;喜怒哀乐过则“滞留”“念念著”,心有“私意”就会不存,心之不存就会有偏,就是“有所”,也就是不正。
2.从“正”的动词意义上来理解,作为工夫论的“正”就是要通过省察克制的工夫来“正”其不正。心是身之主,心常常要检查自己的内心,时刻“警醒”是否有过和不及的情感。做“正”的工夫之前,朱熹首先区分了与释老工夫论的区别,他否认做“正心”工夫是在怒事来时做静的工夫,就可得“不迁怒,不贰过”之结果,他认为只求静的工夫,连当怒都不怒了,反而不符合天理。“正”的工夫应当是如颜子般“不迁怒”。朱熹言:“‘必先明诸心,知所往,然后力行以求至’,盖欲见得此道理透也。”[1]772也就是说,圣人做“正”的工夫,首先,要在遇事时明白自己的心,也就是“察”得本心的“湛然虚明”。“察”是朱熹工夫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有不“察”就会失其正。他说:“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则欲动情胜,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4]9还要“察”得事之当喜还是当怒。其次,就是去行其所当行。遇当怒之事则怒,遇当喜之事则喜,知心之所往,情之所发,不能将对甲的喜怒之情加于乙之上。最后,要在喜怒随感而应的同时保持“警醒”,看情之发如何是合理的。“只当于此警省,如何是合理,如何是不合理。”[1]772所谓合不合理就是说是否有所偏倚,是否有过和不及的状态。而“正”的工夫就是在时时的“警醒”中和“察”之后对有所偏倚的过和不及的情感进行纠正,使其恢复“湛然虚明”之状态。
四、正心工夫
朱熹将“正心”的工夫过程分为三个时间点,即与物相应的三个不同阶段,分别是遇事前、遇事中、遇事后。朱熹言:“其所以系于物者有三:或是事未来,而自家先有这个期待底心;或事已应去了,又却长留在胸中不能忘;或正应事之时,意有偏重,便只见那边重,这都是为物所系缚。”[1]348首先,遇事前的“正心”的工夫是要保持心本体的“湛然虚明”,使其无有预先“期待底心”来应物,也就是不能在应接事物之前有喜怒哀乐之心。其次,应接事物之时,也就是遇事中的“正心”工夫,就是保持心之“和”,即通过“察识”保持情之发的适中,无过无不及,无所偏倚。最后,遇事之后,情合理而发,不“滞留”于心,过则休。朱熹以水涨潮比喻,涨潮过了,水就又恢复平静,说明人在应事之后,情也应当随物而去,心不为其所动。
朱熹在注释《大学》时,也特别重视工夫的效验。曾奕认为,朱熹改定《大学》新本及其对《大学》新本的阐释,始终贯穿着“功夫与效验”这样一条线索[5]。他对朱熹工夫和效验的探讨是纵向展开的,从朱熹的整体工夫论入手,强调下学而上达。笔者也关注到“功夫与效验”这条线索,却是从“正心”工夫本身入手横向展开,即“正心”工夫是如何和如何检验“正心”的结果。“不迁怒”在朱熹的工夫论中不光是工夫的实践也是工夫的效验。有人问朱熹:“不迁怒、二过,是颜子克己工夫到后,方如此,却不是以此方为克己工夫也。”朱熹回答:“夫子说时也只从他克己效验上说。但克己工夫未到时,也需照管。不成道我工夫未到那田地,而迁怒、二过只听之耶!”[1]767从工夫的过程上讲,如前所说,就是喜怒哀乐的不“滞留”“随感而应”,不将对一事之怒迁于另一事上;而从“正心”工夫的效验上讲,“不迁怒”就是中节,就是颜子所呈现的和乐的状态。由此可以看出,关于“正心”的效验都是从做工夫之人的外在表现来评判的,心遇事后有喜怒哀乐之情,过后则恢复本体“湛然虚明”的状态,外在表现如同静止悬挂的镜子和平静的水面;也如颜子“不迁怒”时的和乐状态。
综上,朱熹的“正心”工夫,就是讲使情之发合于理,工夫的对象是“心”,是情之所发。所谓“正”的工夫就是使情之发无过无不及,无所偏倚,无迁于他物,保持一种和乐的精神状态。
括而言之,本文对朱熹“正心”工夫的研究仅从“正心”是“八条目”工夫之一的角度入手,从概念上厘清“正”与“心”的结构和内涵,就《大学》文本的研究来把握“正心”的工夫过程,此时的“正心”是从为“修身”工夫做准备的角度而论。对于朱熹整体的工夫论来说,“正心”还有更高层次的意义,朱熹的 “正其心”是为了更高层次的“养其性”做准备的,而“养其性”也正是朱熹所追求的最高的精神层次。对此,需要在后续的研究中继续扩展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