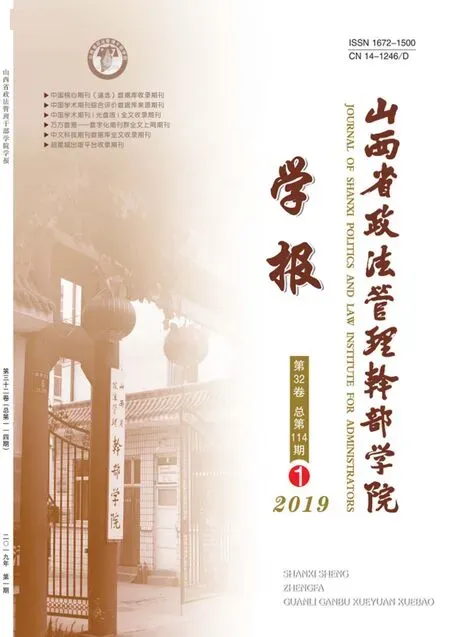我国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探究
——以新旧刑诉法机动侦查权条款变化为切入点
2019-02-21娄力斌
娄力斌
(新疆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检察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1400)
一、以法律词语为支点,依原理解释为驱动面,对机动侦查权概念进行逻辑分析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检察机关可以对特定案件进行立案侦查。其中机动侦查权的运行效力法定依据: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重大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时候,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机动侦查权,并非实证法上的法定术语,仅指在学理上的叫法,与之相当的,是“侦查”。其从基础侦查权衍生而来的,必然带有基础侦查权的上述属性,也有自身自动生成特点。依基础本源和衍生特点双驱动逐步展开论理分析。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侦查”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对于刑事案件,依照法律进行的收集证据、查明案情的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侦查权是侦查意志的体现,基于社会秩序利益,可以强加侦查对象的意志之上,对涉嫌具有刑事特征的反社会行为做出反应。这种反应是指强制措施。强制措施的适用,要在专门调查工作过程中因地制宜采用合理有效地方法。侦查权所具有的运行弹性,凭借侦查的价值理念和内在逻辑体系,动态协调侦查权的体系,反映出机动侦查权存在的价值。本文将机动附加在检察机关侦查权基础上的属性,相关特征的限制表面上缩小了侦查权的属性范围,实质上是更为严密发挥侦查权的能动性,进而发挥侦查权的应有价值。当事物的属性在法理中已经阐释清楚,就应将其加以完善随之规则化。具有规则意义的机动侦查权理应存在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权的法治价值。但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对机动的立案侦查权规制范围过窄,基本上没有适用空间,只具有一定的宣示意义。从目前的诉讼实践看,现行的机动侦查权实际运用其实并不理想,主要问题是通过机动侦查权开展立案侦查案件罕见,在检察院每年侦查的案件总量中,所占比例较低。[1]由此,制定法律时应该切实注意,防止法律违背事物的性质。借助对新旧刑事诉讼法有关机动侦查权条款的逻辑分析,新机动侦查权条款遵循机动侦查权运行属性,符合机动侦查权有效运行的刚性要求。
二、对新旧机动侦查权条文逻辑比较分析
制度体系的完整性是法治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表现,是司法人员可资运用的法治资源。按照体系解释逻辑,修改前的《刑事诉讼法》第十八条前一部分规定了检察机关对特定案件的侦查权:贪污贿赂犯罪,渎职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报复陷害、非法搜查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以及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的犯罪,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本条文后部分规定了机动侦查权条款。法律条文之间并非各自孤立存在,其经常是不完全的法条,只有相互结合才能构成法条的内在逻辑,构成完全的法条规范类罪。基于国民可预测性、公法的谦抑性和机动侦查权的程序价值,对机动侦查权启动程序采取审批制的泛侦查权模式,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间,亦勿失公正性。按照最新法律援引,将渎职犯罪和反贪污贿赂犯罪纳入到监察法体系中来调整,将带有权力谋利型和权力渎职型的职务犯罪从检察机关自侦案件剥离出来,保留了对权力侵犯公民权利的刑事侦查权。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职权过程存在违法犯罪情形,大多数涉及渎职犯罪和贪污贿赂犯罪,如将刑事诉讼法规定公安机关管辖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重大犯罪案件,有条件地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实质上将不归监察机关管辖的部分渎职犯罪,且由公安机关管辖的权力侵犯公民权利的案件,纳入到机动侦查权调整之中。出于监督体系的完整性考量,防止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和监察机关在部分权力渎职犯罪管辖上的冲突,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十九条前一款隐含的司法逻辑是有权力必有有效监督以及有权利必有救济。新机动侦查权条款的出台,衔接了监察体制改革和监察法治规则,保障机动侦察权的正常运行,有利于法律监督的实现。检察机关在法律监督后发现公安机关办理的权力侵犯权利案件中存在不合适宜的情形,应依法适用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对权力侵犯权利的刑事案件进行侦查,保证受到侵害的权利一定会得到保护和救济,有效打击犯罪,保障公民权利,维护司法公正。
侦查权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保障,增强法律监督的权威性和实效性,法律监督为侦查权运行提供程序导向意义。法律监督能力高低和是否有效,影响侦查程序的产生和是否能同步运行侦查权。论理至此,将机动侦查权的启动纳入到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与侦查一体化体系中来,更符合司法实践的需要。
三、新旧机动侦查权条款变化对司法实践的积极影响
法律的本质秩序,就是一个由法律目的出发,随时代经过而确定的法律体系。[2]司法行为合理化走向应贯彻立法者立法目的变化和保障制度体系的完整性,更好地实现正义原则。因此,结合新机动侦查权条款的规范思路,为了维护法律监督的职能,保证法律统一实施,检察机关保留了一部分侦查权力,对司法活动是否正确必须及时进行监督,以罚代刑的问题必须坚决予以纠正。是目的的力量促成法律向前发展的,而不是受规范者主观的确信。[3]新机动侦查权条款指向的立法目的凸显法律监督与侦查权的衔接机制,确保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实质化存在,增强法律监督刚性。明确机动侦查权的启动条件,理顺立案侦查和机动侦查之间的关系,防止互相放任推诿,影响打击犯罪的有效性。例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的,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本条中,法律没有对公安机关不立案监督的渠道甚至立案后消极侦查做出明确的制度安排,只提到检察机关对案件可以进行法律监督,却未能与机动侦查权衔接,也不能明确机动侦查权是否能适用这种情况,对公安机关管辖的公权力僭越刑事规则案件的监督处在相对失灵的状态。按照法律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比西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具有更强的客观性和中立性,应当主动发挥其效能。侦查、搜查、扣押、监听、羁押等侵犯个人基本人权的活动,原则上也应当受到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和控制,由起诉机关做出相应的程序性评判,使审判前的程序也呈现出一定的“诉讼”特征。只有当裁判前的整个诉讼过程普遍采用了“诉讼”的刑式时,履行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客观义务,才能更好地实现保障人权的目的。[4]对此,具有法律监督特点的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应以正义为指导原则,将蕴含在法律中的客观义务、目的考量付诸实现,并据之有效监督,在监督中根据情势适时进行机动侦查。在实践中应在符合立法目的和规范意义的情况下,可适当拓展条文援引空间,规范以下做法:(1)人民检察院在实施法律监督过程中,认为公安机关管辖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犯罪案件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办理立案手续后不行侦查、消极侦查,经上级人民检察院批准,人民检察院可以直接立案侦查。检察机关启动机动侦查权后,侦办案件被生效判决确定为有罪的,可据此作为追究公安机关直接责任人渎职的刑事责任、行政责任或者纪律处分的依据,从而强化法律监督刚性要求。(2)对共同管辖案件的监督,则应考虑司法成本差异等把握机动侦查权是否优先适用。
综上,借助法律词语和法学原理认识机动侦查权逻辑概念,理解机动侦查权的属性,有助于对新机动侦查权条款展开论证评析,从立法者目的、制度体系的完整性和司法过程中规范指引的视角,来具体分析规则的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摸清规则向实践的有效转化路径,确保转化的实际效果。对新旧机动侦查权条款比较论述,把握机动侦查权运行逻辑体系,理顺法律监督与机动侦查权以及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与机动侦查权的关系,综合立法意旨与实际需要,突出法律监督与机动侦查权衔接原则以及机动侦查权与立案侦查权的新型权力关系,切实实现机动侦查权的规范有序运行,发挥其应有的法治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