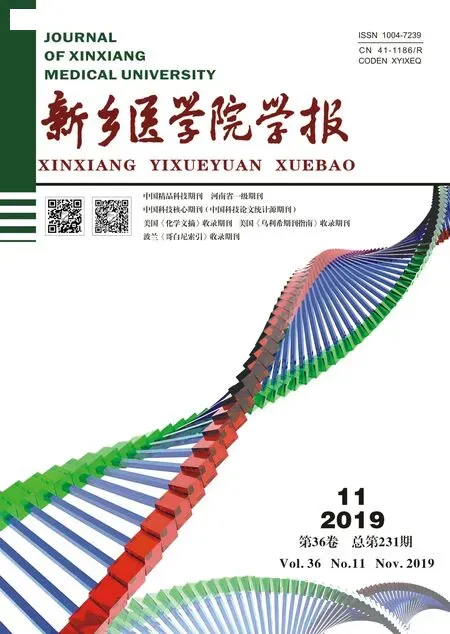儿童哮喘相关危险因素研究进展
2019-02-20温西苹李元霞
温西苹,李元霞
(延安大学附属医院儿科,陕西 延安 716000)
全球儿童及青少年哮喘发病呈逐年增长的趋势,据2015年资料统计,全球哮喘患病率为16.4%,比1990年的9.0%增加了7.4%[1]。我国1990年、2000年、2010年的3次大规模儿童哮喘调查中,14岁以下儿童哮喘患病率分别为1.09%、1.97%、3.02%,增长了近2倍[2-4]。保守估计,全球约有3.34亿儿童患有哮喘,其中在发达国家儿童哮喘人群相对较多;而在低中收入国家儿童哮喘相对较少,但重症哮喘的比例相对较高[1,5]。哮喘的损害呈持续性,一项前瞻性研究显示,在10岁前有过哮喘的儿童,其中64%到50岁时仍有哮喘;而50岁的哮喘患者中,有47%的患者在6岁前曾有哮喘持续状态;重症哮喘患儿到50岁时发展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s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的风险增加75%[6]。哮喘的相关危险因素分为可控因素和不可控因素,可控因素包括感染、烟草烟雾环境(environmental tobacco smoke,ETS)、肥胖、抗生素使用、运动等;不可控因素包括性别、过敏体质、遗传因素等。儿童哮喘呈现高发病率及持续性损害的特点,因此,了解其可控因素对于该病的预防和控制有重大意义。本文就ETS、肥胖和抗生素的使用等哮喘的可控因素进行综述,旨在指导临床减少暴露,预防和降低儿童哮喘的发生。
1 ETS与儿童哮喘
1.1 家庭ETS暴露对哮喘的影响多项研究表明,家中烟草烟雾暴露可增加儿童毛细支气管炎的风险,且孕产妇吸烟增加了其胎儿在婴幼儿期患喘息的风险[7-10]。张浩玲等[11]对中山市11 611名儿童进行随机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儿童室内被动吸烟、母亲吸烟、母亲被动吸烟、母亲妊娠期被动吸烟和儿童2岁前被动吸烟均为儿童哮喘及哮喘样症状的危险因素;其中,家庭成员每天吸烟量≥5支,儿童患病率和喘鸣发生率均明显增高;2岁前被动吸烟是哮喘的最主要危险因素之一。杜向阳等[12]对上海市4 101名4~14岁儿童的调查结果显示,父母居室吸烟是儿童哮喘的危险因素,并且室内二手烟暴露量越高,发生呼吸系统疾病与症状的风险越高;王雪梅等[13]的一项meta分析显示,被动吸烟与中国儿童哮喘的总相关优势比值达3.19。
国外研究表明,EST暴露增加了儿童毛细支气管炎的严重程度,孕期EST暴露增加了儿童患哮喘的风险[14-15]。儿童早期暴露于ETS会影响发育,增加肺部健康状况不佳的终生风险,被动吸烟使哮喘儿童的发病率至少增加20%[16]。西班牙研究者对136 403名因暴露于二手烟而导致下呼吸道感染的0~14岁儿童的调查显示,约8.5%的儿童因为长期暴露于二手烟环境而患哮喘,住院儿童中约8.5%为哮喘患儿[17]。由此说明,二手烟使儿童患哮喘的风险增加。
1.2 ETS暴露与儿童哮喘发病机制烟草烟雾化合物可直接影响肺细胞功能,表现出促炎性、细胞毒性、诱变性和致癌性,特别是吸入氧化剂导致直接肺损伤和炎症反应激活,造成进一步的损伤。吸烟者吸入的烟草烟雾产生的活性氧和活性氮物质导致其氧化负担增加,并通过活化的炎症细胞-巨噬细胞使上皮细胞、嗜中性粒细胞和T淋巴细胞释放到肺部环境中,导致氧化应激,黏膜炎症增加,炎性细胞因子如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8、IL-6和肿瘤坏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TNF)-α表达增加[18]。另一方面,ETS对上皮细胞的直接作用导致细胞通透性增加,黏液过度生成,黏膜纤毛清除受损,促炎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释放增加,巨噬细胞和中性粒细胞的募集增加以及通过削弱1型T辅助细胞(T helper 1 cell,Th1)和增加2型T辅助细胞(T helper 2 cell,Th2)依赖性反应使淋巴细胞平衡趋向Th2来扭转免疫反应:Th1和Th2是CD4+T淋巴细胞的2种亚型,Th1细胞产生干扰素(interferon,IFN)-γ、IL-2和TNF-β,其作用是激活巨噬细胞,并负责细胞介导免疫和吞噬细胞依赖性保护反应;Th2产生IL-4、IL-5、IL-10和IL-13,其负责增强抗体合成、嗜酸性粒细胞活化和抑制巨噬细胞功能,从而提供不依赖吞噬细胞的保护性应答。EST增加免疫球蛋白E(immunoglobulin E,IgE)水平,促进前变应细胞的分泌,通过改变各种免疫细胞的免疫功能而加剧过敏性炎症的发生[16,19-20]。生命早期ETS暴露与肺功能降低有关,这主要与烟草中的尼古丁有关。据报道,产前尼古丁暴露通过上调胎儿早期肺和脑中表达的烟碱型乙酰胆碱受体来改变正常的肺部发育,特别是胎儿气管、支气管、软骨和内皮细胞中a7受体的表达增加可能潜在地导致胚胎干细胞向成纤维细胞的分化增加,使肺生长和肺泡发育受损,这些都与后代的肺功能和肺发育不良相关,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暴露于EST的新生儿肺功能降低的风险增加,以及整个儿童期出现哮喘症状的风险增加[21]。吸烟母亲的新生儿脐带血中可检测到改变的细胞因子,如IFN -γ 减少、IgE和IL-13水平升高,支持产前吸烟暴露增加感染的风险,并可能在早期诱发过敏反应[22]。近年来研究表明,EST暴露作用于6、18号染色体,从而参与哮喘的发生[23]。此外,吸烟也与较高的黏蛋白5AC(human mucin-5 subtype AC,MUC5AC)-核心基因表达相关[24-25]。 MUC5AC是小气道上皮细胞分泌的主要黏蛋白,它代表对环境损害的急性反应。吸烟者中MUC5AC表达增加可能导致黏液分泌减少和黏膜纤毛清除损伤,这种损伤主要是通过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信号转导作用实现的。
目前一般认为,避免儿童暴露于烟草环境中可降低儿童哮喘的发生。RANDO 等研究表明,引入无烟法后,各个年龄段哮喘患者的入院率显著下降[26-27]。而BUTZ等[28]的一项关于222名儿童的随机对照试验表明,室内环境二手烟的控制并不能降低中重度哮喘患儿急诊率。因此,控制ETS对中重度哮喘的效果尚需大样本研究。
2 肥胖与儿童哮喘
LANG等[29]对507 496名2~17岁儿童的一项回顾性研究显示,肥胖或超重是儿童新发哮喘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23%~27%的新发哮喘与肥胖有关;如果没有肥胖或超重,有10%的哮喘可以避免发生。而且有研究也表明,肥胖可以增加哮喘的严重程度,但超重和肥胖状态只是一种适度的影响因素,它与肺活量测定证实的哮喘风险增加无关[29-31]。
2.1 肥胖对哮喘患儿肺功能的影响国外的一项meta分析显示,与无哮喘的肥胖者相比,肥胖受试者的第1秒用力呼气量(forced expiratory volume in the first second,FEV1)下降2.2%,其中成人较儿童下降的更为显著; 用力肺活量(forced vital capacity,FVC)也下降了2.2%,儿童FVC下降与成人相比未见明显差异;而肥胖哮喘者FEV1/FVC下降了1.5%,肥胖儿童FEV1/FVC下降较成人更为明显,这可能是由于儿童正处于生长发育期,其呼吸道口径与成人相比较窄所致;肥胖对肺容积也有影响,与非肥胖哮喘者相比,肥胖者的功能残气量下降了17.1%,肺总量下降了4.2%,残气量下降了6.6%[32];由此可以看出,肥胖哮喘对肺容量的影响更为明显。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过多的脂肪堆积于腹部、胸部、内脏,胸壁负荷增加,限制呼吸肌运动,使肺弹性回缩力增高,肺和胸廓顺应性降低,产生限制性呼吸功能障碍,引起低潮气量呼吸,使肺容量、补呼吸量均有一定程度降低,引起呼吸道狭窄,从而导致哮喘。肥胖长期作用可能引起支气管平滑肌萎缩,气管和支气管扩张作用降低,最终导致肺不张、肺动脉高压、肺间质水肿等并发症。梁樊梅等[33]对230名4~11岁儿童的调查显示,肥胖非过敏哮喘儿童的肺功能低于肥胖过敏儿童,说明肥胖对非过敏儿童的肺功能有明显影响。但国外对小鼠的实验证明,肥胖可增加呼吸道高敏性[34-35],这与临床研究所说的肥胖影响非过敏儿童的研究结果相悖[32]。故肥胖是否会引起呼吸道高敏状态尚待商榷。
2.2 肥胖对哮喘儿童免疫系统的影响肥胖与抗炎调节性T细胞的减少、CD8+T细胞的增加以及脂肪组织中巨噬细胞从M2型向M1型的转变有关[36]。有研究表明,肥胖相关性哮喘主要与中性粒细胞增高、皮质醇激素抵抗相关,这可能与脂肪细胞分泌脂肪素、瘦素和脂联素等有关[37-39]。脂肪组织可以分泌促炎脂肪因子,包括瘦素、脂联素、IL-6、TNF-α、血浆纤溶酶原激活物抑制剂1、嗜酸性粒细胞趋化因子、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和单核细胞趋化蛋白等,肥胖哮喘患者脂肪介导的炎症主要是因为脂肪细胞缺氧后释放促炎脂肪因子瘦素,其将M2型巨噬细胞转化为M1型巨噬细胞,导致Th1细胞增殖,从而使Th1分泌的IL-6、IL-10、IFN-γ和TNF增加[37];而且血清瘦素与较高的Th1/Th2细胞比率和血清IFN-γ水平相关,与哮喘、下呼吸道阻塞和肥胖哮喘患者的支气管收缩有关[40-41]。而脂联素与肥胖和体质量指数呈负相关[42]。据报道,在肥胖个体中,脂肪运动因子(瘦素、脂联素和抵抗素)、IL-6、TNF-α和氧化应激水平升高均与哮喘有关,但与最常见的过敏性哮喘无关[37-38]。
据文献报道,出生后前2 a内的体质量快速增加与10岁前儿童哮喘及肺功能降低有关,尤其是出生后前3个月体质量快速增加与1岁前患哮喘及5岁后肺功能下降密切相关,而且此相关性与婴幼儿出生时体质量无关;而2~6岁时体质量增加与哮喘关系不密切,3~7岁时体质量增加与15岁时的FEV1、FEV相关[39,42-43];提示控制体质量对哮喘症状的改善尤为重要性。
3 抗生素使用与儿童哮喘
研究表明,抗生素的使用与儿童哮喘的发生呈正相关[44-48]。谢梦瑶等[49]关于孕期使用抗生素的meta分析显示,孕早期抗生素的应用增加了子代哮喘的风险。YOSHIDA等[50]的一项回顾性研究显示,调整家族因素后,在胎儿期使用抗生素仅轻微增加哮喘的风险,1岁前抗生素的使用与哮喘最为相关,这种风险在3岁后消失。AHMADIZAR等[44]的研究结果显示,儿童3岁前使用抗生素增加了患哮喘的风险,其中1岁前使用抗生素患哮喘的风险更高,但与哮喘发作严重程度无相关性。由此说明,1岁前使用抗生素对儿童患哮喘的风险最高。
3.1 抗生素类别与哮喘的关系YOSHIDA等[50]研究证明,大环内酯类抗生素的使用与儿童哮喘发生的风险关系最大。孕期青霉素、大环内酯类及磺胺类药物的使用与儿童哮喘相关[45]。美国田纳西州的一项队列研究显示,婴儿患哮喘的风险与1岁前抗生素应用的数量有关,使用广谱抗生素可以增加儿童患哮喘的风险,但在婴儿期抗生素应用的时间、等级或厌氧覆盖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45]。苏艳艳等[46]对孕期抗生素使用情况进行meta分析,结果显示,β-内酰胺类抗生素对后代哮喘影响最大,磺胺嘧啶和其他抗生素与后代哮喘关系不大,这与国外相关研究有所不同[44-45,50]。孕妇及儿童使用哪种类型的抗生素对儿童哮喘的影响最大,尚需大样本调查进一步研究。
3.2 抗生素使用次数对儿童哮喘的影响苏艳艳等[46]的meta分析显示,1岁前使用抗生素增加了儿童患哮喘的风险;1岁前使用抗菌药物>4 次比使用 0~1 次者哮喘风险有所增加;高风险儿童(至少有1位直系亲属曾患有哮喘)1 岁前使用抗生素患哮喘的风险与未使用抗生素的高危儿童相比有所增加,1岁前儿童抗生素暴露疗程次数>4次时,儿童哮喘的发病风险增加将近1倍。余巍等[47]的研究表明,婴儿期使用抗生素次数分别为 1 次、2~3 次、≥4次时,5~7 岁儿童哮喘的发病风险分别增加了16.5%、29.1%和40.8%。墨西哥一项横断面调查研究显示,儿童使用抗生素的次数>3次比使用1~2 次者患哮喘的风险明显增加[48]。美国田纳西州的一项队列研究显示,儿童期使用抗生素超过1次者,其6岁时患哮喘的概率增加近2倍,而婴幼儿期使用抗生素的次数每增加1次,其在6岁患哮喘的危险性会增高18%~20%[45]。国内外研究均说明,儿童患哮喘的风险与抗生素的使用次数有关,次数越多,患哮喘的风险就更大。
3.3 抗生素增加儿童哮喘的发病机制多项研究证明,抗生素对儿童哮喘的影响主要是由于改变人的微生态环境尤其是胃肠道菌群所致,而微生态环境对人体免疫系统有重要作用[48,51-54]。微生物暴露能诱导CD4+T细胞中IFN-γ基因的去甲基化(活化),使IFN-γ表达,从而影响免疫系统发育。IFN-γ的产生是对病毒的反应,具有激活巨噬细胞、增加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物分子表达和对受感染细胞施加直接抗病毒活性的功能[53]。如果降低IFN-γ的产生,会增加过敏性疾病的风险,这是由于IFN-γ能够降低对Th2细胞分化的负性调节,对过敏原的免疫反应有利于特应性相关的Th2记忆细胞的发育[52-53,55]。微生物被认为通过病原体相关分子模式反复刺激来影响免疫成熟过程,这些分子模式被模式识别受体如在先天免疫系统细胞上发现的Toll-受体(Toll-like receptors,TLR)识别,同时TLR刺激多种配体,在微生物富集环境中模拟暴露,然后诱导新生儿树突细胞成熟,产生Th1的极化细胞因子IL-12[52,56-57]。而过度使用抗生素减少了婴幼儿体内的微生物。研究表明,抗生素诱导肠道菌群失调后小鼠的细胞及体液免疫功能均降低,并可导致Th2增高,其可诱发小鼠哮喘等变应性疾病,但并不影响哮喘的严重程度[54]。抗生素的使用使宫内及婴幼儿体内微生物菌群失调,致使Th1向Th2转换增多,使免疫功能降低,这种影响与1岁前尤其是出生3个月的儿童哮喘和过敏性疾病的发生有密切关系,1 岁后这种风险明显降低,因为随着食物的引入和母乳喂养的停止,微生态环境逐渐平稳[58-59]。故1岁以前婴儿如使用抗生素,可使其患哮喘及过敏性疾病的风险增加。
我国是抗生素生产大国,也是使用大国,有超过75%的抗生素应用于呼吸道感染,其中儿童最为常见[60]。据统计,我国儿童抗生素使用率为58.37%,单用占71.14%,门诊儿童抗生素使用占 55.37%;住院儿童抗生素使用占77.56%,不合理使用率为19.95%,表明我国滥用抗生素现象非常明显[61]。故降低儿童抗生素的使用从而减少哮喘及过敏性疾病的发生是非常有必要的。
4 结语
综上所述,孕期及儿童早期采取减轻体质量、脱离ETS和减少抗生素使用等早期预防干预措施,对降低儿童哮喘风险有重要意义,但其机制目前尚无定论,希望以后有更多的研究能够进行相应解释,并有助于解释及早期防治儿童哮喘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