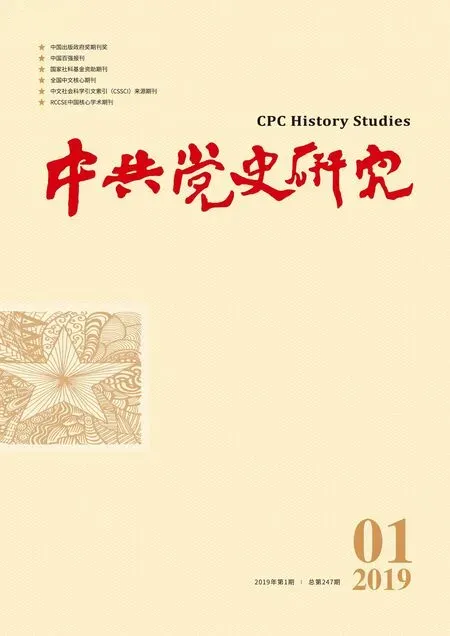再议退押运动与一九五一年农业税的关系
2019-02-20黄柘淞
黄 柘 淞
一、问题缘起
押金是佃农交给地主的地租保证金,欠租扣除,辞佃退还。1949年起,中共在南方新区发起退押运动,要求地主退还佃农押金,这是新区农村在土改前的一件大事,也是近年来土改史研究的热点之一。
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陈云传》提供了这样一则史料:1950年11月,陈云在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上提出“适当增加农业税,一九五一年农业税按照原概算增加百分之十”[注]《陈云传》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731页。。一些研究者认为,陈云说的“原概算”是指1950年农业税,这条史料暗示起码在1950年11月这次会议时,中央已对1951年农业税作出了打算,要比1950年农业税增加10%。
同期的另一件事是西南区的退押运动。西南区退押运动开始筹划(1950年7月)、地方试点(1950年10月)虽然早于这次会议(1950年11月),但运动大面积开展是从1950年11月开始的[注]关于西南区退押运动的时间线,来自以下史料:“自七月中央局第三次委员会上确定今冬明春清匪、反霸、减租、退押的方针和步骤后,各地为了贯彻此一方针,随即利用整风及党代会议传达,并进行了整顿农协,训练农民积极分子,召开农代会、各代会及制定减租退押的条例和实施办法等一系列的准备工作。西南军政委员会首次会议亦以此为中心议题,各地并于十月以后与征粮同时组织了若干县份,开始进行了典型试验”,“西南各区于迅速完成征粮工作后,均在十一月份内先后转入减租退押运动。从两个月的情况看来,运动的发展一般尚属正常”。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4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32页;《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重庆出版社,2006年,第314页。。
于是,一些研究者认为,退押运动和增加1951年农业税这两件事,看似风马不接,但背后是有关系的。例如,曹树基说:“江津县委依据什么确定退押数额?这(指江津县的退押数额与农业税数字有关)是江津县独有的做法,还是全国性的现象?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为了从根本上稳定金融物价以保障抗美援朝战争的需要,陈云提出要尽力增加财政收入,具体办法是‘适当增加农业税,一九五一年农业税按照原概算增加百分之十’。江津县农业税的增加,就是这一计划的产物。”[注]曹树基等:《江津县减租退押运动研究》,《清华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换言之,在时间关系上,增税决策在先,退押运动在后,增加农业税是发起退押运动的一种目的。
娄敏进一步指出,除了时间先后关系外,退押运动和增加1951年农业税还存在数量关系:“曹文的猜想与论证反映出,江津县的退押数额与1951年农业税增加的任务是相挂钩的,所以增加农业税是退押运动的目的之一……曹文并未认为江津县委对退押之‘两倍公粮’的预估是准确的,相反,这是根据中央传达的‘按照原概算增加百分之十’的农业税任务而制定的退押计划。在政策逐层传达过程中,为防止不能完成上级的硬性规定,江津县委有意在10%的基础上将标准拉高到1950年两倍公粮的标准。从实际执行过程中来看,中央要求增加10%的农业税的要求,是不惜任何代价都要完成的最低标准,而江津县委提出的‘两倍公粮’之退押任务则存在很大的弹性空间。”[注]娄敏:《再论江津县退押运动的几个问题——对〈江津县退押运动再研究〉一文的学术回应》,《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11期。娄敏指出的数量关系是,1951年农业税任务较1950年增加多少,那么地方退押任务最低就要设置成多少,即地方依据这笔农业税增量来设置自己退押的硬性任务,为了确保任务完成,可以在此基础上拟一个更高的数字。
上述研究者从时间关系和数量关系两个层面归纳了退押运动和增加1951年农业税的关系。本文拟证明,研究者对增加1951年农业税一事(即“一九五一年农业税按照原概算增加百分之十”)存在两点误会。第一,在时间上,研究者是依据《陈云传》的一则脚注判断出这一决策是陈云在1950年11月全国第二次财政会议上提出的,但实际上《陈云传》的这则脚注还值得探讨,这一决策是晚至1951年6月才提出的,远远晚于新区退押运动,所以不可能是退押运动的政策背景,也不可能是退押任务的设定依据。第二,在句意上,“一九五一年农业税按照原概算增加百分之十”的意思是要把1951年农业税任务较先前版本(根据财政形势的变化,1951年农业税任务有多个版本)提高10%,而不是要把1951年农业税任务较1950年农业税提高10%,研究者误以为这句话说的是两年度农业税有差额,并将之与退押运动做了不当联系。
二、关于《陈云传》的一个脚注
相关研究者讨论的增加1951年农业税一事,出自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陈云传》,史料原文如下:
为了从根本上稳定金融物价以保障抗美援朝战争的需要,必须增加收入,削减支出。陈云提出“对支出用‘削萝卜’的办法,对收入
用‘挤牛奶’的办法”[注]请注意本句后有脚注,脚注内容如下:“陈云在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上的报告,1950年11月15日。见《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页。”。
“挤牛奶”就是尽力增加可能增加的财政收入。具体办法是:适当增加农业税,一九五一年农业税按照原概算增加百分之十;对酒和卷烟用纸实行专卖;开征契税,增加若干产品货物税和进、出口税;加强征收管理,堵塞漏洞,把偷、漏的税统统收回来。[注]《陈云传》上册,第731页。
《陈云传》在上述引文的第一段末用脚注指出,此为陈云在1950年11月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上的报告。结合这个脚注,上述引文向读者造成的印象是:1950年11月,陈云在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上提出财政增收的“挤牛奶”的四条办法,其中一条是“一九五一年农业税按照原概算增加百分之十”。
如此一来,《陈云传》就暗示了“一九五一年农业税按照原概算增加百分之十”起码早在1950年11月就已提出。基于这种暗示,相关研究者才会认为在时间关系上,增税决策早于退押运动,在数量关系上,地方退押的硬性任务就是1950年农业税的10%。
但是,1951年农业税按照原概算增加10%一事,真的是1950年11月陈云在会上提出的吗?为了解答这一问题,我们先回到对《陈云传》的考察上来。
《陈云传》的脚注说,它提到的“挤牛奶”措施引自陈云《抗美援朝开始后财经工作的方针》一文(该文是陈云在1950年11月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上的讲话)[注]《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1—120页。。比较二者可以发现,《陈云传》在引用时做了一些筛选和改写,示如表1。

表1 《陈云传》对陈云讲话里“挤牛奶”措施的筛选和改写(原文引用)
④ 需要说明的是,《陈云文选》提到的“增加公粮附加”和《陈云传》提到的“一九五一年农业税按照原概算增加百分之十”是两码事,后者不是对前者的文意转述。增加公粮附加,是指增加1950年农业税的地方附加税率,9月份决定是15%,11月全国第二次财政会议后决定提高到30%。1951年农业税按照原概算增加10%,是指1951年农业税总任务比先前版本增加10%。特此说明,以防细心的读者产生疑惑。1950年9月对农业税地方附加税率为15%的规定,参见《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1950年9月5日),财政部农业财务司编:《新中国农业税史料丛编》第5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6年,第91页。1950年11月把农业税地方附加税率提高为30%的规定,参见《关于一九五〇年公粮征收的决定》(1950年11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财政卷)》,经济管理出版社,1995年,第521页。
根据表1可以看出,虽然《陈云传》暗示“一九五一年农业税按照原概算增加百分之十”是陈云在1950年11月全国第二次财政会议上说的,但追溯陈云讲话原文,查无此事。这一决策可能不是发生在1950年11月,具体时间还需要进一步考证。倘若是发生在1950年11月之后,就很难说这是退押运动的背景了,因为开展退押运动最晚的西南区在此时都已经将运动铺开了。
三、“一九五一年农业税按照原概算增加百分之十”的决策时间
这一决策实际发生在1951年6月。1951年6月6日,中共中央向各行政区发电,告知目前财政困难,拟将1951年农业税任务增加10%,向大区征集意见,全文如下:
(一)近两三个月以来,由于军事费用和其他费用不断增加,今年三月份修改的全国财政概算,已大大突破,不可能继续维持……这是不可能完全用银行透支的办法来解决的,必须从增加收入减少开支着手。
(二)兹提出如下解决办法:(1)增加税收六万七千亿元(按成留给地方的约三万亿元在外),这是比较可靠的。(2)增加企业利润和减少经建投资两项可挤出三万亿元。(3)举行全国抗美援朝捐献运动,估计可得一万七千亿元。(4)农业税,在原分配任务基础上,再增加一成,共二十三亿斤,合一万八千亿元。以上四项,共为十三万二千亿元。二十六万亿元减去十三万二千亿元,赤字仍有十二万八千亿元。
(三)现在夏征即将开始。如按上述方案实行,则公粮任务须从原公粮任务二百三十二亿七千七百六十五万斤,增加到二百五十六亿零五百四十一万斤。各区分配如下:华北原任务为三十二亿一千二百六十五万斤,增加三亿二千一百二十六万斤,共计三十五亿三千三百九十一万斤;华东原为五十二亿斤,增加五亿二千万斤,共计五十七亿二千万斤;中南原为五十九亿一千万斤,增加五亿九千一百万斤,共计六十五亿零一百万斤;西南原为三十二亿五千万斤,增加三亿二千五百万斤,共计三十五亿七千五百万斤;西北原为十三亿八千万斤,增加一亿三千八百万斤,共计十五亿一千八百万斤;东北原为三百万吨,增加三十万吨,共计三百三十万吨,折合细粮为四十四亿八千八百万斤;内蒙原为二亿四千五百万斤,增加二千四百五十万斤,共计二亿六千九百五十万斤。这一方案,除增加各项税收和增加企业利润外,增加农业税和抗美援朝捐献两项,共四十亿斤米,实际要大部加在农民身上。是否可行,请将你们的意见即日电告。因为夏征已到,能否增加农业税需要迅速决定。[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6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97—198页。
半个月后的1951年6月21日,中央再次发电,告知地方此事已成定局:
中央六月六日电所提出的提高各项收入以弥补赤字的方案,经征求各地意见的结果,对提高各项税收任务数字和提高企业利润上缴数字,均无异议,即决定照所提数字列入预算。关于农业税增加一成的问题,各地意见不完全一致。中央考虑,为了弥补赤字,为了国家能确实掌握一定的粮食和经济作物(这是根据今年买不到棉花所得出的一条经验),今年公粮仍以增加一成为有利。这样做有其困难的一面,如新解放区因土地改革的结果,地主富农累进部分减少了,新翻身农民的生产资料仍感不足,以及去年农业税并不算轻等等;但亦有有利的一面,去年全国丰收,土产品、特产品大部推销出去,今年夏收一般也算是丰收的,加上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三大运动的普遍和深入,农民爱国主义情绪增高等等,估计动员得好是可以完成且不至于出危险的。因此,最后仍决定增加一成。请即根据中央六月六日电报所分配的数字和政务院公布的关于一九五一年农业税收工作的指示的办法,迅速布置保证完成。[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6册,第233—234页。
1951年7月8日,政务院发出《关于追加农业税征收概算的指示》:“为了适应国防和财政的需要,为了使国家掌握足够的粮食,以保证军粮、稳定粮价,政务院决定本年农业税照原概算增收1/10。”[注]陈如龙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大事记(1949—1985)》,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第43页。另有著述也有相同表述,参见高培勇编:《共和国财税60年》,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402页。至此,6月的党内决策落实到了行政上。
以上就是“一九五一年农业税按照原概算增加百分之十”一事的基本过程[注]当然,这一过程除了笔者已列出的中共中央文件、政务院指示外,还包括1951年6月全国财政会议的讨论等资料可以证明。限于篇幅,恕不一一引用。。通过上述电文,我们能够得知以下两条重要信息。
第一,在时间上,1951年农业税按照原概算增加10%一事是晚至1951年6月份在财政危机下的因时制宜之举。《陈云传》在撰写“抗美援朝中的财经工作”一章时,将此决策表述为抗美援朝时期“挤牛奶”的措施是没问题的,但因为其他几条“挤牛奶”措施引自1950年11月的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就把这条措施也顺带脚注成这个时间,有些欠妥。
第二,在句意上,1951年农业税按照原概算增加10%的意思,不是指1951年农业税任务比1950年要增加10%,而是指1951年农业税任务要比前一版本增加10%。这提示我们,1950年农业税任务可能有不断修改的多个版本,笔者将在下一节进一步考察。
再回头看相关研究者的论点,娄敏解释曹文说:“曹文并未认为江津县委对退押之‘两倍公粮’的预估是准确的,相反,这是根据中央传达的‘按照原概算增加百分之十’的农业税任务而制定的退押计划。”这就相当于在说:江津县委在1950年11月成功预测到了中央会在1951年6月考虑“按照原概算增加10%”,于是根据这笔农业税任务增量,提早设定出了当地的退押任务。这种论点就属于过度联想了。[注]需要说明的是,笔者虽然反对娄敏的这种说法,但在理解“一九五一年农业税按照原概算增加百分之十”的句意时也犯了相同错误,以为1951年农业税任务真的比1950年增加了10%。下面这段话体现了笔者的错误:“1951年中央决定全国农业税概算较1950年提高10%,一是出自1951年平均税率的上浮,二是出自地方附加的提高,这样大体形成了10%的农业税概算额提高。”参见黄柘淞:《江津县退押运动再研究——与曹树基教授等讨论》,《清华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
四、1951年农业税原概算也与退押运动无关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追问,上一节提到过,1951年农业税概算有多个版本,如果曾有某一版本的1951年农业税概算先于退押运动出炉,且较1950年农业税有增加,那么“退押任务是根据1951年农业税较1950年的增量而设定”之说依然可能成立。所以,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考察两个问题。
第一,在时间关系上,退押运动与1951年农业税最早概算谁先谁后?如果退押运动早于1951年农业税最早概算,那么退押任务就不可能是根据1951年农业税较1950年的增量去设定。
1950年12月31日,中央对大区发出一则电文:“一九五一年度全国财政收支总概算,经过全国财政会议的商榷,各大行政区财委的同意,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座谈,业于十二月二十六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提出并得到批准……一九五一年度全国财政收支总概算及其附件,将由中财委密送各中央局、分局,你们收到这些文件后,根据本指示原则,望在适当会议上进行口头传达并下达。”[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4册,第451、454页。这则电文提到了概算出台的几个环节,最早的是“经过全国财政会议的商榷”。此应指1950年11月的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因为陈云在这次会上的讲话稿也提到说,召集各大区财经委来开会,任务之一就是讨论“明年度的财政概算”[注]《陈云文选》第2卷,第111页。。据此可以推测,1951年最早的农业税概算很可能是在1950年11月至12月期间出炉的,且晚至1950年12月31日,中央才把最终数字下达给大区。
再来对比退押运动的时间。华东区的退押运动,在1949年11月指令停止[注]“目前已发生退押金和清算的地区,应当根据实情妥善加以处理和结束,不再扩大;尚未退押金扩大清算的地区,应立即停止进行。”《华东局关于减租运动中若干问题给浙江省委的复示》(1949年11月),《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615页。;中南区在1950年4月指令停止[注]“望令各地停止退押,已退者,亦不要送还,地主自愿退还者,农民亦可接受,但不要再去动员群众退押,不要向地主追逼”,“关于退押问题,同意中央指示,取消退押口号,已退者不再倒退,未退者停退”。参见《中央关于停止向地主退押金问题给中南局的指示》(1950年4月),《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629页。;西南区解放最晚,退押运动因此也晚,于1950年7月开始筹划,10月试点,11月铺开。所以基本可以确认,新区退押运动早于1951年农业税最早概算出炉的时间(1950年11月至12月),更早于“一九五一年农业税按照原概算增加百分之十”的时间(1951年6月)。因此,基于时间先后关系,谁都不可能根据1951年农业税较1950年的增量来制定退押任务。
第二,1950年、1951年农业税谁多谁少?如果1951年农业税历次概算相对于1950年没有增加,那么退押任务也不可能是根据1951年农业税“增量”来设定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军事战争仍在继续,经济环境也不稳定,计划赶不上变化,所以财政概算不断调整,以新代旧,形成多个版本。1950年的全国财政概算进行过四次,每次包含的农业税概算示如表2。

表2 1950年全国财政概算里的农业税概算
数据来源:《1950年度全国财政收入执行计划变动情况表》《1950年度国家岁入总决算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财政卷)》,第276、658页。表格里四次概算的原数据单位为“万斤”,决算的原数据单位为“斤”,为便于读者阅读,笔者四舍五入后全部统一为“亿斤”。
由表2可见,1950年农业税前三次概算稳定在200亿斤附近,但第四次概算提高到286亿斤,大增约43%。那么,在第三次概算(1950年8月)到第四次(1950年12月)概算之间,有哪些原因导致农业税概算意外提高呢?
首先是1950年秋征前后的查田。中共知道国民政府的田赋册并不真实,瞒田抗粮司空见惯,中共1949年的秋征虽然有“挤黑田”之类的口号,但因为新区各方面条件不足,实际上还是依据国民政府的田赋册来征粮。第一次“查田定产”“依率计征”是从1950年秋征开始的。由于农业税概算的公式是“农业税概算额=核定总产量×每人平均农业收入额的税率”[注]《财政部关于改进农业税征收业务中的几个问题的指示》(1951年6月28日),财政部农业财务司编:《新中国农业税史料丛编》第5册,第195页。,查出的黑田越多,农户的产量就越高,既扩大了税基(即“核定总产量”一项),又提高了税率等级(因为人均农业收入提高后会导致对应税率等级提高),两者叠加相乘后,查田定产较小的变化,就能带来农业税概算较大的变化。时任财政部农业税司副司长彭晓帆说:“在一九五〇年农业税征收过程中,查田定产,也获得了相当的成绩……(省略部分是作者大段举例各地查出黑田的数据——笔者注)查田工作的成就,不但促进了负担的公平合理,而且也防止了地主富农的瞒税,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注]彭晓帆:《一九五〇年农业税工作的经验与教训(节录)》(1951年4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财政卷)》,第556—557页。
更重要的原因是1950年下半年中央因为财政压力决定临时加派农业税。中财委当时报告说:“(1950年)八月以来,财政上感到很大困难,比二月财政会议后还难过……现在每天所有收入尚不敷零星支付,迄今日止,库存款仅一百亿元左近,而积欠则达一万二千余亿元。”[注]戎子和、王绍鏊:《八月以来财政情况》(1950年10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财政卷)》,第632页。农业税占政府财政收入的半壁江山,当财政面临困难时,自然会考虑打农业税的主意。1950年11月24日,邓小平对云南省委的一则电文透露了这种动向:“对公粮征收,中财委及政务院正考虑比原派数加征百分之十五,同时增加地方粮比例到百分之十五至二十五。你们布置时间较迟,为避免再来一次起见,请即作恰当的调整。”[注]《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953页。三天后,政务院也确实下达了指令,把1950年农业税的地方附加一律从正税的15%提高到30%,与邓小平所言“比原派数加征百分之十五”吻合[注]1950年9月的规定参见《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1950年9月5日),财政部农业财务司编:《新中国农业税史料丛编》第5册,第91页。11月的修改参见《关于一九五〇年公粮征收的决定》(1950年11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财政卷)》,第521页。。若中央确实如邓小平提及的方案那样去加派农业税,则可以计算出会提高15%至30%的农业税概算[注]邓小平说的这两种方案,第一种方案是正税提高15%,地方附加不变,仍然为正税的15%,则农业税增加(1.15×1.15)÷(1×1.15)-1=15%;第二种方案是正税提高15%,地方附加提高到正税的30%,则农业税增加(1.15×1.3)÷(1×1.15)-1=30%。。这是1950年第四次农业税概算大增的主因。[注]或有人问,既然1950年11月中央要求增加1950年农业税,那么这是否可能是退押运动的背景呢?实际上,这仍然不可能是退押运动的背景,因为华东、中南、西南的退押运动在时间上决策得更早,增加1950年农业税是后来的事情,在决策退押运动时是不可能有所料及的。
以上是1950年历次农业税概算的情况,着重分析了第四次概算增加的原因。下面再来看1951年的全国财政概算。1951年也进行过四次概算,每次包含的农业税概算示如表3。

表3 1951年全国财政概算里的农业税概算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财政卷)》,1995年。各页的原文已在本表列出,便于读者细读。
数据说明:1.编制1950年财政概算时,人民币物价不稳定,所以概算用粮食为单位;编制1951年财政概算时,人民币物价基本已经稳定,所以农业税概算既用人民币为单位,也用粮食为单位。2.本表的概算一、概算三、决算的“亿斤”数据空缺,文献只提供了“亿元”数据,对应的“亿斤”数据是笔者测算的,其后标注了“测算”。3.测算方法是这样的,先查到人民币和粮食的三种折价:“东北收支按每斤高粱米525元折合;内蒙收支粮价按每斤400元折合;关内粮食收支部分,按每斤平均840元折合。”(第796页,文献来源同本表)。虽然现在已知有东北、内蒙古、关内三种折价,但全国概算里的“全国折价”还需要测算。由于每次修改概算时,东北、内蒙古、关内的任务在比例关系上不变或者变化极小(都是集体上浮、集体下调),所以历次概算里的“全国折价”是基本相同的。又由于概算二同时提供了“亿元”和“亿斤”两个数字,所以据此可算出“全国折价”是179107亿元/233亿斤=769元/斤,再据此测算出了概算一、概算三、决算的“亿斤”数。笔者对这种测算有信心,概算四同时提供了“亿元”和“亿斤”两个数字,可以用来做一个检测,概算四按笔者的方法测算数是256.05亿斤,而文献提供的直接数字是255.75亿斤,笔者的测算偏差只有0.1%,已足够准确。另外,本表的目的是与表2的数字做大小比较,对数字精确度要求也不高。
由表3可见,1951年农业税前三次概算都稳定在230亿斤左右,但第四次概算提高到257亿斤,增幅约10%。原因已在上一节考证,系因财政支出超出预计,因而决定“一九五一年农业税按照原概算增加百分之十”。
梳理了1950年、1951年农业税历次概算的基本情况,我们再回到本节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比较1950年和1951年农业税任务到底谁重谁轻?是否存在“增量”?
如果用决算比较决算。1950年的决算是259亿斤,1951年是222亿斤,所以1951年农业税更轻,不存在“增量”。
如果用概算比较概算。因为概算是以新代旧的,当有了“1951年农业税概算”这个概念时,“1950年农业税概算”就是指最近一次的概算,也就是第四次概算的286亿斤。而1951年农业税的四次概算均远低于286亿斤,仍然是1951年农业税更轻,也不存在“增量”。
至此,本节的第二个问题,即1951年农业税任务较1950年是否存在“增量”,已经考察完毕。笔者认为,所谓“增量”并不存在,所以不宜去说“增量”和退押运动有什么关系。
五、总 结
《陈云传》提到的“一九五一年农业税按照原概算增加百分之十”实际决策于1951年6月,远晚于新区退押运动,不可能与退押运动有关。相关研究者误会了决策的时间和含义,因而在时间关系上认为增税决策早于退押运动,在数量关系上提出地方根据中央传达的“按照原概算增加百分之十”的农业税任务而制定退押计划。
退一步讲,1951年农业税原概算也和退押运动没有关系。在时间关系上,先有新区退押运动,后有1951年农业税最早概算的出现;在数量关系上,1951年农业税无论是概算还是决算都低于1950年农业税。所以,退押任务不可能根据1951年农业税较1950年的增量来设定。
客观地说,退押运动让农民分割了地主财富,农民更加富裕了,对政府将来可能的加税行为有更高的容忍度,从这个角度去解说退押运动和农业税的关系是有意义的。但误会了时间关系,认为政府是怀着增加次年农业税的目的去发起退押运动,说地方是根据两年度的农业税差额去设定退押任务,则是猜想的成分稍多。
(本文作者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北京 1008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