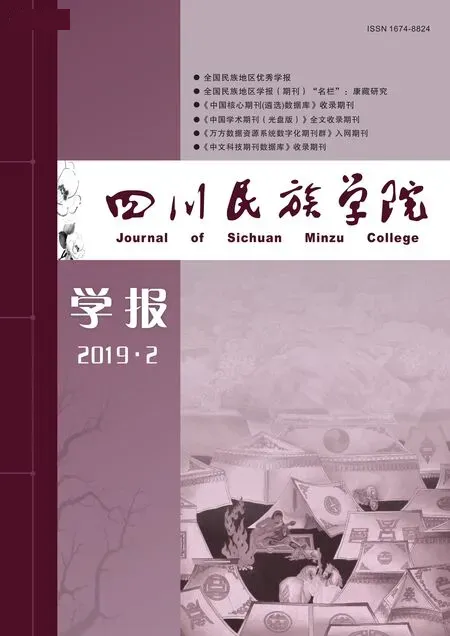儒家人文思想产生的内在理路
2019-02-19李汶陕
李汶陕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间曾出现过极其璀璨的文明,这一时期所产生的思想对后世带来了重大影响。雅斯贝斯将这一时期称之为“轴心时代”。雅斯贝斯曾指出:“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点燃,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归,或者说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1]依雅斯贝斯所言,轴心时代所带来的文明对于后世的发展有着原动力的作用,比如文艺复兴就是站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带来了新的具有创造力的文化的进步。
有学者认为,“轴心时代”是人类文明的一次“井喷式”的发展。它决定着一个民族的发展方向。在中国的“轴心时代”先后出现了孔子、老子、墨子等诸子百家。为何春秋时期会出现如此大的文化的绽放?主要是由于,一是礼坏乐崩,社会秩序混乱,有理想有抱负的知识分子开始思索社会发展的理想模式;二是西周时期人文主义的萌芽,人们开始关注世俗社会的发展以及人的发展;三是知识分子地位的逐渐提升,使得社会的精神层面不再由统治阶层所把控。雅斯贝斯曾指出:“前轴心期文化,像巴比伦文化,埃及文化,印度河流域文化和中国土著文化,其本身可能十分宏大,但没有显示出某种觉醒的意识,古代文化的某种因素进入轴心期,并成为新开端的组成部分,只有这些因素才得以保存下来。”[1]那么在中国的前轴心期最为突出,转变最为剧烈的应该是西周。
西周时期,人们逐渐将天命与道德相联系,把政治与德行相挂钩,注重祭祀带来的心理层面的影响,形成完备的礼乐体系。儒家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文化,对民族性格的养成、精神的培育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西周时期的重要改革者周公是孔子一直所追寻的对象。孔子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自己只是追寻前人的脚步。余英时先生在《轴心突破和礼乐传统》一文中曾指出,儒、墨、道三家都是突破了三代礼乐而兴起的。所以,本文认为西周时期文化的转变对于后来形成的儒家文化有很大的影响。本文将主要从巫的理性化、周朝的天命观嬗变以及周礼的重构三个方面来阐述西周时期基本观念与儒家文化之间的联系。
一、巫的理性化
巫作为从古至今与人类始终相伴随的文化,人们常常将它与“萨满”“巫术”“迷信”“神秘”等词语相联系,一般被作为“陈腐”的迷信文化来对待。但在上世纪90年代,有学者提出不同的观点,认为“中国上古思想史的最大秘密,是巫的特质在中国大传统中以理性化的形式坚固保存、延续下来,形成中国思想的根本特色,成为了了解中国思想和文化的钥匙所在。”[2]我们基于此点开始讨论巫的理性化过程对于儒家人文主义形成的影响。
巫在殷商时期就有记录,但巫的缘起应早于此时,甚至无法确定它的具体产生时期,马林诺夫斯基曾指出:“巫术永远没有起源,永远不是发明的编造的,一切巫术简单地说都是存在的,古已有之的存在。”[3]《说文解字》中记载:“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褎舞形,与工同意。古者巫咸初作巫。”陈来曾指出:“‘无形’指神,‘褎’即袖。事无形即事神,此说以事神为巫主要功能。”[4]也有学者认为巫原为“舞”,郑玄《诗谱》中记载:古代之巫实以歌舞为职。《公羊传·隐公四年》何休注:“巫者,事鬼神祷解以治病请福者也。”认为巫与医相通。因此,古代的巫是具有事神,以歌舞为职,与医相通的多重角色。
首先,“绝地天通”将人神分离,人们开始更加关注世俗世界的生活。所谓“绝地天通”就是绝地民与天神沟通之道。在远古社会时期,各部族之间或攻伐或联盟,大大小小的部族有上万之多。那时的人们主要通过巫与上天沟通,或祈求风调雨顺或驱灾驱病。有学者认为曾出现过一段民神同位的时期,即家家为巫。据说,自蚩尤作乱之后,三苗之民,风气大坏,统治者依靠刑法来整治社会,一时间,人民苦不堪言,凡是遇到有无辜、不幸之事都要祷告“天”。为了不让“天”被人间的“琐事”所烦扰,开启了“绝地天通”。
《国语·楚语下》中记载观射父关于“绝地天通”的解释:“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威严,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灾祸存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恢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我们可以看到在远古时期曾出现民神同位、民神杂糅混乱现象。有学者认为观射父对于“绝地天通”的解释是站在人文理性的立场上为中国宗教指出的一条道路,即如何处理人与神的关系。在《论语·雍也》篇中:“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春秋时期,孔子把“以神设教”作为“鬼神”的主要功能,对它的态度是“敬而远之”。
“绝地天通”的开启,是将地民与天神之间相隔离。从此人神分离,各司其业。与神沟通的能力逐渐成为统治者的专享。他不仅是国家的领袖也是巫的首领。“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当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简在帝心,万方有罪,即当朕身;朕身有罪,无及万方。’”(《墨子·兼爱下》)当出现天灾时,作为国家最大的巫要亲自向天祷告,承认自己所犯的过失,以祈求风调雨顺。统治者将神权与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并出现将道德与民心作为统治的依据的倾向,这无疑是人文主义的发展。
其次,《周易》的形成使得人们的认识由具体经验提升到普遍概念。人们对于《周易》的理解通常是占筮之书。《周易》包括《易经》和《易传》,相传,《易经》为周文王所作,由卦、爻演变为64卦和384爻,以“阴阳”转化为内容,并对万物进行性状归类;《易传》由孔子所作,是对于卦辞和爻辞的解释。并将其配于相应卦之后形成《周易》(文中所指《周易》均为《易经》)。《易》有三本,包括《连山》《归藏》和《周易》,其中前两本已经失传。
巫作为人间与神沟通的特殊身份者,自有独特的一套方法。人们常常将萨满与巫混为一谈,认为两者为一物,都是通过跳舞、特殊的感受、神的附体来表达神意。当然这些大多数情况都是为了驱灾辟邪。在一般的选择中,则是由占卜来表达神意。常见的占卜方式有兽骨占卜、龟甲占卜和蓍草占卜。无论哪种占卜,人们都需要占卜得出的一些现象,根据《周易》上的记载进行解释。在夏商周三代时期,占卜行为已经是具有一定的规则。有学者推测占卜的行为应该在这之前就有,到夏商周三代逐渐形成体系。
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这是孔子对于《周易》的高度评价。孔子为何为《易经》作注?陈来曾指出:“《周易》是以数为基础,这使得摆脱神鬼观念而向某种宇宙法则转化成为可能,这虽然不见得是始作《周易》者的意愿,但却是人文化过程得以实现的内在根据。”[4]这也就是说《周易》具有内在转化的潜质,孔子正是看到了《周易》的这种特质,才开始为《周易》作注,当然孔子的根本目的仍是“托古御今”,通过古典的研究、注释,赋予其新的内涵。《周易》以阴阳变化为内容,打破了长久以来人们对于具体事物的具体经验的认识。正是它存在这种阴阳变化的内容,使得孔子有把它转向具有人文性的可能性。
最后,西周时期的祭祀和鬼神观念的转变。西周的祭祀对象包括:天神、地袛、人鬼。祭祀原本是由巫觋文化发展而来,到西周初已经形成一套完整的祭祀体系。祭祀的行为也由驱病驱灾、占卜问天,转变为具有更多人文意义上的祭祀。在《祭神》中记载:“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此皆功烈于民者也。”把有功于人民的人列为可以祭祀的对象,这无疑是将人民地位的逐渐提升,突出了民本思想。
海鸟曰“爰居”,止于鲁东门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国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文仲之为政也!夫祀,国之大节也,而节,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为国典。今无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国语》)陈来指出:“展禽所说,参以《礼记》,不但突出了先祖先王人世功德的一面,而且这种功德祭祀已多少带有纪念性的意味,而非纯粹的宗教性祭享祈福,这显然是文化理性化过程的产物。周代以后祖先祭祀越来越突出并且社会化,其主要功能为维系族群团结,其信仰的意义逐渐淡化。”[4]在《国语·楚语下》中,观射父对于上古祭祀行为解释道:“祀所以昭孝息民,抚国家、定百姓也,不可以已。”其中我们可以看出祭祀的作用在于展示孝道,以安抚百姓,稳定国家。
《礼记·祭法》中记载说:“万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对于祭祀和鬼神的观念,西周时期已经发生转变,在“绝地天通”之后,“天”已属于统治阶层的权力来源的手段,而对于祖先的祭祀,其主要的功能也是维系族群的团结。“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春秋时期,孔子对于“鬼神”的观念是“敬而远之”不去讨论。“未知生,焉知死”更多的是对于现世生活的关注。祭祀和鬼神在孔子那里也成为为现世世界服务的对象,通过“以神设教”对百姓进行教化,以达到安稳现世生活的作用。
巫作为远古时期与神沟通的代表者,其不仅具有一定的权力,而且也是当时人群中具有一定知识的人。从“家家为巫”到“绝地天通”是将权力集中、团结和巩固社群的表现。具有一定知识的巫,在殷商时期就已具有巫史的身份即既是与神沟通的人又是记载其占卜的人。因此《周易》的产生不能仅仅作为一本占筮之书,其文化的转变更为深刻。巫通常用舞蹈、唱歌等形式做为祈祷上天或与神沟通的方式之一。他们往往有固定的特殊的形式。王是巫的首领,最大的巫,王将神权与政权相结合掌握在自己手中。巫的祭祀行为逐渐演变成一种具有文化功能的礼乐系统。由此,巫由作为企图控制天的非理性行为内化为具有一定文化功能的礼乐系统即由非理性向理性的逐渐转变。
二、周朝天命观的嬗变
在早期先民,对天的认识往往形成了一个民族的宗教信仰。在“轴心时代”,以色列的“先知”通过与神的交流,传达着平和、忍耐的信念,这对于以色列民族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在中国,人们从对自然宗教的信仰逐渐转变为伦理宗教,这就意味着人文主义在中国文化中的一大发展。殷商时期,人们对于天的观念仍是“先王有服,克谨天命。罔知天之断命。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盘庚》),认为“天”授予人间王朝的政治权力和政治寿命。到文王时期,对于“天”有了新的解释,在《牧誓》中有:“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一个王朝的生存与否不再是由“天”赋予其权力的直接决定,而是要依靠统治者的德行。对于“天”的信仰发生了微妙的转变,使得人文主义开始逐渐登上思想史的舞台。
周公作为西周时期统治阶层的精英知识分子,他所做的一系列改革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大部分思想体现在周公摄政时期所作的三诰之中。无论是出于政治的需要,还是个人理性的自觉发展,他主要思想表现在提出“天命靡常”和“敬德保民”,将统治者的合法性问题归于德行之上,并将统治阶层注重个人的德行发展为德政的现实性问题之上。周公所作的改革产生的影响对于后期儒家的发展,尤其是对于儒家创始人孔子的影响是无可比拟的。
首先,“天命靡常”(《大雅·文王》)的提出。《康诰》:“惟命不于常。”《君奭》:“又曰:天不可信。”殷商时期人们对于天的观念还停留在统治者只是天在人间的代理人,天具有决定一个王朝的统治寿命的神秘权力。到西周时期,则转变为“天”是变化无常的,甚至是不可信任的。这种对于“天”观念的转变奠定了中国几千年的天命观思想。 从“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一部分人对于“鬼神”避而不谈的态度,可以看出春秋时期对于“神”的信仰已经不具有十足的信任。
三代时期,商灭夏,殷灭周,其打的旗号均是“天命”所致。《尚书·汤誓》:“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牧誓》:“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在连续的王朝更替之后,周朝的合法性问题以及周朝如何才能在历史的行进当中避免被其他王朝所代替,这或许是周公思想发生的关键点,是对于王朝更替的忧患意识。
“天命靡常”提出对“天”不再完全的依赖,确实具有进步意义。人们将更多的关注点放在世俗社会之中,既然“天”不再是完全可靠的,那么什么将成为统治者依存的支点呢?由此,发展出对于统治者德性的要求,以及对于民的关注。
其次,重民思想的产生。“天命靡常”作为基本的认识点,周公希望统治者认识到“民”的重要性。在《召诰》中记载:“夫知保抱携持厥妇子,以哀吁天,徂厥亡,出执。呜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百姓抱着妻儿哀告上天,上天哀怜百姓,将治理人世的大命转移给周人。这体现了“天命”依据民意,强调了人民民意对于王朝统治的重要性。
《泰誓》:“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泰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上天”的惩罚会根据人民的民意。随着“民”的地位的提升,“天”的地位逐渐下降。《无逸》:“周公曰: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劳稼穑,厥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乃逸。”从对“民”的关注逐渐增加到对“民事”的关注,对于世俗世界的关注。
重民思想的产生,无疑是将关注点落实在现世社会,这就不同于西方国家对于“神”的强烈的依赖。从对“民”的关注,对“民事”的关注逐渐发展出对于统治者的要求,需进行“德政”。
最后,德政观念的出现。在讨伐商纣王的《牧誓》中就有指出,商纣王无德,武王天命所受。在《召诰》中:“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可以看出“德”对于一个王朝的重要性。
武王死后,因成王年幼,由周公摄政。而武王的弟弟管叔、蔡叔、霍叔本是受命监视商人,却在周公摄政后勾结武庚叛乱。由此发生了三监之乱。周公出兵用了三年时间平定叛乱。这期间周公的天命观逐渐形成。在《康诰》中有强调:“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体现了民本思想。《康诰》:“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有身,不废在王命。”这里就将天命与道德相联系。在《康诰》中提出:“惟命不于常。”天命是变化不定的,因此统治者要依靠自己的德行去治理天下。
《召诰》中说:“呜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惟王受命,无疆惟休,亦无疆惟恤。呜呼,曷其奈何弗敬。”这里是说皇天收回了对于殷的受命,而让周王作其长子。周王得到了治理天下的大命,幸福与忧患与之俱来。君权神授的思想一直作为统治者证明其政权合法性的有力依据。所以,他们仍然相信天命。但是需要解释如何防止天命未来由姬周转向他姓,这就要依靠“德政”来实现。
西周时期所形成的天命观,对于人民认识世界的态度带来极大的转变,对于儒家后来形成的人文主义精神和“德政”观念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天命靡常”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把“民”的地位逐渐提升,也形成了具有伦理道德意味的“德政”思想。将伦理与政治相联系,弱化了“神”的权威,将人们的关注点引向世俗社会,引向对人本身的关注。
三、周礼的重构
儒的职业虽早有存在,但是儒家真正的起始应在孔子思想的形成。因此孔子之前并无儒家文化,孔子及其弟子组成儒家,并以孔子的思想体系作为最初儒家的思想体系。孔子自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其一生最为推崇的便是“周礼”。孔子名为推行“礼乐制度”,实则“托古改制”,以期达到“大同”社会的理想。西周时期所构建的宗法血缘关系的等级制度以及相配合的礼乐制度,使得西周在一段时期内社会秩序井然。西周经过变革带来的人文的转向对于孔子人文主义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甚至在整个中国思想中对于“天”“神”等概念的认识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中国思想中以人为本突出人的重要性以及更关注于世俗社会的表现不同于西方世界对于“上帝”“彼岸世界”的理解。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以儒家文化为主流,儒家文化决定着中国人的大部分思想观念。儒家文化的起源应追述到西周时期人文的转向,这并不能说明中国文化的源头唯有西周文化。而是说,中国文化经历了很长时间的积累到西周时期或因为政治的变革或因为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等原因通过一系列改革完善了长久以来形成的文化体系,并带来了人文意识的转向。
西周时期经过一系列的改革,产生了“敬德保民”“明德慎罚”的思想,形成了与宗法等级制度相配合的礼乐体系。由祭祀的礼仪制度以及社会中的礼仪规范发展而来的礼乐体系,规定了社会等级,规范化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的行为,巩固了社会组织,稳定了社会秩序。同时,起到了教化百姓的作用。当然,最重要的是通过礼乐制度让人们形成具有感性认同的共同的心理情感。这对于形成国家意识、民族意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首先,礼乐制度巩固了社会等级制度。西周初期,对于刚经过大战的周族如何管理国家,如何避免重蹈商朝的覆辙,充满了忧患意识。西周通过分封建国的方式,希望建立起以血缘为纽带的分封国家,通过礼乐制度确立起等级分明的社会制度。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向组织成具有网状的、严密的、有弹性的国家形式。
祭祀的礼仪以及社会中的礼仪规范经过周公的系统化形成周朝的礼乐制度。这套礼乐制度具有严格的等级划分,祭祀的人员安排、场地大小,用的音乐等都与其身份地位有关。人们按照自己的等级执行相应的礼,这是合乎规矩的。礼的等级代表了一种身份。在《论语·八佾篇》中记载: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按照周礼规定天子用八侑,卿大夫用四侑,士用二侑。季氏是正卿,只能用四佾,他却用八佾。孔子对于这种破坏周礼等级的僭越行为极为不满。天子有天子的礼,卿有卿的礼,各在其位,各行其礼。
这套礼不仅用于朝廷,还延伸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家庭是这个社会中一个普遍而又极为重要的场合。在家庭中也有等级秩序,父要行为父礼,子要行为子礼,男行男子的礼,女行女子的礼。从家庭到社会,各行其礼,秩序井然。从一方面来说,它形成了尊尊、亲亲的传统;另一面,从家庭到社会都是上下有序,巩固了社会等级制度,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礼乐制度对于西周建立一个统一稳固的国家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同时在西周形成的具有完备系统的礼乐制度,到了春秋时期,孔子将其发展为具有人文主义内涵的一套礼乐文化,道德仁义成为其主要的内容。
其次,礼乐制度具有教化百姓的作用。《国语·周语》中记载:“古者先王即有天下,又崇立上帝、明神而敬事之,于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诸侯春秋受职于王以临其民,大夫、士日恪位著以儆其官,庶人、共、商各守其业以共其上。犹恐其有坠失也,古为车服、族章以旌之,为贽币、瑞节以镇之,为班爵遗践以列之,以闻嘉誉以声之。”由此可以看出统治者的主要目的是用礼乐制度来教化百姓。
礼要求对于长辈,兄弟的规范行为,要求男女有别,这是道德的教化。将道德与礼相结合,礼就成为规范人们行为的一套外在的行为标准。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论语·学而》)礼成为道德与政治的纽带。
礼乐制度与道德相结合形成一套具有人文主义的现世的规范体系,在关注人的同时,更强调其内心的真挚的情感,逐渐转变为具有个人内修的行为,这形成了中国不同于西方世界的“他律”宗教的“自律”行为。人人心中自有法典。
最后,礼乐制度具有建立共同心理情感的作用。孔子时期已将仁寓于礼之中,对待父母、兄弟、姊妹,要行其礼,更重要的事行礼时要具有内在真挚的情感。礼乐与道德相联系,人们愿意主动的遵循礼,维护社会的稳定,国家的统治。
对于鬼神的祭祀也是同样的,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场合,经过一定的礼仪,人们相聚在一起,由统治者代表世俗世界的人去向“鬼神”祷告,形成了严肃、独特的氛围,日久天长,逐渐成为人们内心某种共同的心理情感。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天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爱于父母乎!”(《论语·阳货》)李泽厚指出:“孔子把‘三年之丧’的传统礼制,直接归结为亲子之爱的生活情理,把‘礼’的基础直接诉之于心理依靠。这样,既把整套‘礼’的血缘实质规定为‘孝悌’,又把‘孝悌’建筑在日常亲子之爱上,这就把‘礼’以及‘仪’从外在的规范约束解说成人心的内在要求,把原来的僵硬的强制规定,提升为生活的自觉理念。”[5]礼经过孔子的重新诠释成为具有内在依据,人们自觉向往的行为规范。
礼乐制度从祭祀的仪礼逐渐走向具有人文主义的丰富内涵。祭祀礼仪经周公的重新整合形成了具有规范社会行为,稳固社会秩序的作用。其内在已经具有了培养人文主义的土壤,再经由孔子的重新诠释,道德与礼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特有的礼乐制度文化。共同的心理情感的培养对于一个民族的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西周时期作为中国传统天人关系改变发生的第一站,其产生的影响和意义不同凡响。对于形成中国伦理道德的政治体制,儒家人文主义的思想,都起到了基础作用。这对于一个民族而言是具有方向性的改革。西周的文化同样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也是经过了历史的积累,在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前提下,实现了人文的转向。儒家思想作为中国文化的主干,其形成的伦理道德的文化体系成为了中国的文化基因。我们对儒家的人文主义思想起源的探析旨在对于文化传承的连续性,寻找其发生的多重因素,将其系统的展现出来,从而为文化的复兴与振兴汲取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