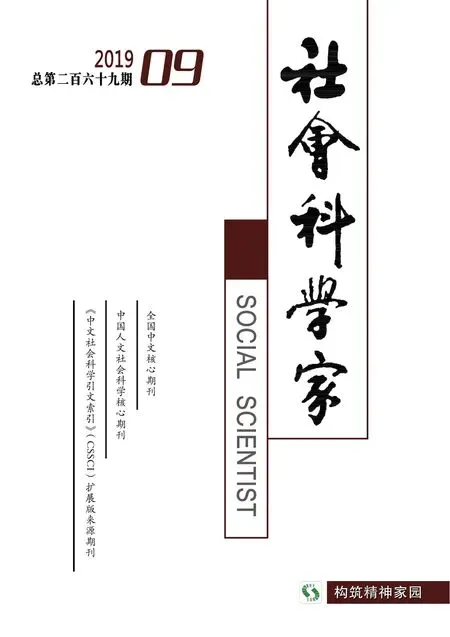中国早期教育的政治向度
——基于《尚书》的探讨
2019-02-19辛晓霞
辛晓霞
(天津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384)
关于中国传统教育学界已经积累了比较多的研究,普遍认同其以儒家教育思想为主导,以德性修养、人格完善为特点,重人文教育轻技能教育。这些定位是恰当的,但需要注意的是,教育事实和制度在孔子之前就已存在,由儒家塑造的传统教育是一定历史序列的产物,探究其中一些特点的形成应回到孔子之前。同时,思想领域往往从人性论或道德发生的角度讨论传统教育的逻辑性,但教育不是历史主体的主观产物,它首先是立足实践的需要而产生,教育实践在先,分析传统教育的构建理路首先应当关注其开始时的实践指向。
中国文化的特点是“政治优先”,政治对社会各个层面的塑造皆有很大影响。①阎步克:“中国是一个‘政治优先’的社会,政治体制在塑造社会形态上是一个巨大权重。”参见阎步克:《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前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页。教育作为文化、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源起、发展与政治密切相关。中国早期教育演变的一个鲜明轨迹是从“学在官府”到“学在四夷”,这看似是教育制度的变革,其实深层的原因是政治的变动,是伴随着权力下移、阶层流动的学术下移。
一、教育的政治实用性指向
“学在官府”是早期教育的特点,受教育权为贵族特有,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教育与政治利益密切相关。教育和政治的这种逻辑构成是由中国早期政治文明发展的历史所决定的。
根据战国时文献记载,唐、虞已有大学与小学之分,②《孟子·滕文公篇》:“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礼记·王制》上说,“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虽然这可能不完全符合上古实际③陈青之:“自商代以上,通称上古时代,即我们所谓原始氏族社会时代。在这个时代,文化程度极其幼稚……优闲的教育制度当然无法产生……要知以上所举各书,除《孟子》较古外,其他全属汉人的作品;汉儒最爱关门造谣的,此处所谓上古教育制度,完全由他们捕风捉影,假托古制以见己意,毫无疑义。”参见陈青之:《中国教育史》,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第5页。,但商以前即便没有成形的教育制度,教育事实却是存在的。根据《尚书·舜典》记载,舜继位后任命大臣,其中明确以“教胄子”要求夔:《尚书·舜典》: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
舜命夔做典乐之官,同时教授胄子。“胄,长也,谓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1]嫡长子继承制确立于西周,这里的“胄子”应当包括君主之子和其他贵族子弟。中国传统政治体系中,历来重视继承者的教育,一般都是聘请师、傅朝夕训诲,陈以嘉言,教以礼乐。老师的地位也极其尊崇,从《仲虺之诰》《伊训》《太甲》《说命》诸篇,多可见师、傅对君、君主继承人严厉的训诲。舜希望贵族子弟通过学习诗歌音乐,陶冶性情,达到正直而温和,宽弘而庄栗,刚毅而不苛虐,简易而不傲慢。
这一教育内容很容易被视为中国传统教育以德行培养为核心的例证,但就此时的政治语境来说,提升心性修养只是教育的一个必经阶段,是一种实现目的的手段。培养适于治国理政的后备人才,能够有效地参与政治才是真正的教育诉求。马克斯·韦伯认为,以儒家教育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教育,以人的自我完善为根本追求,但是又将受教育与做官紧密地结合起来,并落实于人们的日用常行之中,因而带有明显的工具理性特色。①参见《儒教与道教》第五章“四、儒家教育在社会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孔子是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儒家教育是对早期教育的继承和升华。以教育培养做官必备的素养,在孔子之前,文明发展早期就已形成。
从尧选任大臣的标准可看出,德是很重要的依据:
《尚书·尧典》:帝曰:“畴咨若时?登庸。”放齐曰:“胤子朱启明。”帝曰:“吁!嚚讼,可乎?”
帝曰:“畴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鸠僝功。”帝曰:“吁!静言庸违,象恭滔天。”
帝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佥曰:“於,鲧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
上古时期,重要的官职由贵族代表或重要大臣推荐,被选中后要通过一定期限的政绩、品格考察,确认合格后擢用。同时,君主通过臣的言行考察其德,根据不同的能力、德行,任命不同的官职,并以功绩大小赐车服。这里呈现的是帝尧求用贤能,大臣推荐人选的场景。放齐推荐胤国子爵朱,理由是他“明”,心志开达,性识明悟,但尧认为他“嚚讼”,正义有“言不忠信为嚚”,[1]不忠信且好争讼,所以不可用。可以看到,放齐的推荐,以及尧的拒用,当事人的德都是主要要素。
当帝尧再次征召,驩兜推荐共工,认为他颇有政绩,但帝尧评价他“静言庸违”,阳奉阴违,“象恭滔天”,貌象恭敬而心傲慢,不可用。尧反对任用共工,缘由与拒用朱一样,德性不好。同样,当四岳推荐鲧时,尧认为其“方命圮族”,正义解为“言鲧性很戾,好比方名,命而行事,辄毁败善类。”[1]性情乖张,不遵守命令。
对比舜希望胄子通过教而形成的品性,“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尚书·舜典》),“嚚讼”“静言庸违”“象恭滔天”“方命圮族”都是鲜明的反面例证。这说明,培育德,不仅在于提升修养,更在于由此获得担任政治职务所必需的素养。可注意,“德”在《尚书》中也有“否德”(《尚书·尧典》)、“凶德”(《尚书·盘庚下》)的用法,“验之于中国的历史,在最早的时候,‘德性’或‘德’的意思还曾笼统地指人的‘各种属性、特性’,所以还有‘吉德’‘凶德’之分,例如说‘孝、敬、忠、信为吉德,盗、贼、藏、奸为凶德’。”[2]所以,此时“德”并不专指道德层面的美德,也指内在素质,一种使个人能够履行其社会角色的品质。
早期文献中肯定的德,大都体现于政治实践中。②陈来先生在分析《尚书》《周礼》《逸周书》等记载唐虞三代文献中关于“德”的记载时,大体分疏为三类,“第一类属于个人品格,第二类是社会基本人伦关系的规范,第三类可以看作前两类结合的产物,”其中“大体上看,第三类出现要晚于前两类,其中有的地方可能已融入了早期儒家的思想。”从内容上看,这些德目似可看作两大类,一类是立基于家庭和家族乃至宗族关系的人伦规范,主要是家庭道德(domesticmoral)。一类是作为个人,主要是向统治者提出的个人的品格的要求。参见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336页。“二典中肯定的德行多体现为政治德行,是在政治实践中获得评价的。正如以前我们所说的,价值建立的方式主要通过政治领域来表现,是早期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3]德与政治的关联性在中国文明早期是如何形成、确立的,这里暂且不讨论。总之,在当时的政治话语体系中,为政需要具备一定的德,德不匹配可以作为不能任职的合理原因。
当然,尧的拒用,可能不仅仅是由个人品格的缺陷,不排除是君臣间不同政治利益的博弈。阎步克先生在评述周代贵族世卿世禄的制度时说“现实政治中的君权是动态的,其贯彻的强度和运作的空间,是受各种政治势力制约的,是君臣‘博弈’而达到的动态平衡。”[4]虽然这说明的是周的君权情况,但也适用于部落联盟的上古时期。上古是中国的氏族部落联盟时代,联盟中存在大量邦国、方国,它们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都具有较大的独立性。一部一族之长,又在联盟中担任官职,他们的政治影响力由个人能力和各自的部落实力构成。在君臣相互制衡的权力格局下,政治人选的确定往往是政治实力和利益的博弈。所以,尧虽不愿意用鲧,但迫于四岳的压力最终还是任用。①《尚书·尧典》:岳曰:“异哉!试可乃已。”帝曰:“往,钦哉!”
即便政治语境中德的运用背后真实的逻辑是利益博弈,但就这套话语体系本身来说,无疑表明,德在当时的政治话语结构中已具有一定的位置,德作为选人用人标准的合理性是共同认可的前提,所以才有可能以德名正言顺地掩饰真实的利益诉求。
麦金太尔指出要回到某一概念所产生的语境中,去了解它的意图。②参见〔美〕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追寻美德——道德理论研究》,“第3 章情感主义:社会内容与社会语境”,宋继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在上古的历史语境中,培育德作为教育的内容是出于实用的需要,其指向性是明确的——获得更有竞争力的从政资格。或者说德主要是依据有用来界定或辨识,更多地指向手段和途径,而非目的。不仅德育,上古教育内容的整体设定思路都是针对参政议政的。
二、针对政治实践确立教育内容
教育是人的社会化的主要方式和途径,它的功能除了传播知识之外,还有使受教育者了解和掌握主流的社会观念和规范。“人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5]上古的政治活动以及建立于其上的思维模式影响了中国早期教育内容的设置。
以祭祀为例,它在上古、三代的政治、社会生活中是重要的常规化活动已是学界共识。祭祀是一种需要协作、配合的团体活动,“更重要的是原始社会中祭祀乃是团体的活动,而团体的祭祀活动具有一定的团体秩序,包含着种种行为的规定。礼一方面继承了这种社群团体内部秩序规定的传统,一方面发展为各种具体的行为规范和各种人际关系的行为仪节。”[3]每一个参与者恰当完成符合自己身份的礼仪内容,整个过程才能井然有序,和谐庄严。祭祀不仅有宗教意义,还具有政治、文化职能,作为被赋予诸多象征意义的团体活动,政治人物在其中的不当表现,必然影响其在团体中的声誉和权威。那么,学习、掌握相关知识就是必要的。
受命教胄子的夔,曾在举例中描述过一次祭祀过程:
《尚书·益稷》:夔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虞宾在位,群后德让。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镛以间,鸟兽跄跄。箫韶九成,凤皇来仪。”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庶尹允谐。”
因舜功成道洽,所以祭祀礼备乐和。作为典乐之官,夔是其中的专职官员之一。相关研究表明,上古时期由巫觋、祝、宗等共同主持国家或公共的祭祀活动,各司其职,“巫觋之职能主要是对祭祀的位次和牲器进行安排,是祭祀体系中的一种操作人员。比较起来,祝是具备较多的有关地理、历史、宗族和礼仪知识的人,宗是对祭品的时令、种类及祭器、祭坛的制度有系统知识的人。”[3]祭祀中无论是器物使用、摆放规范,还是相关的历史、天文知识,都具有相当的专业性,负责人员需要具备相应的知识和技能。历史学界认为,上古曾有过巫官合一的时期,③李宗侗:“君及官吏皆出于巫。”参见李宗侗:《中国古代社会史》,台北:华冈出版社,1954年,第118页。陈梦家:“由巫而史而为王者的行政官吏;王者自己虽为政治领袖,同时仍为群巫之长。”参见陈梦家:《商代的神话与巫术》,载《燕京学报》第二十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35页。即祭祀中的巫觋、祝、宗这些专职人员同时也是行政官吏,具体职位的名称等不同时期或许有调整,但就“损益”的角度来说,各时期祭祀中涉及的内容、专职人员应该是类似的。那么,可推知,相关官员要具备专业的知识技能,没有接受过相应的教育,无法胜任。
另外,除专职官员,祭祀对于参与人员也存在知识门槛。在这场祭祀中,夔提到“虞宾在位,群后德让。”(《尚书·益稷》)正义注有“丹朱为王者后,故称宾。言与诸侯助祭。”[1]丹朱是帝尧的儿子,因其不德,①参见《尚书·益稷》:“帝不时,敷同日奏罔功。无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傲虐是作,罔昼夜昆仑。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另,正义有“丹朱之性下愚,尧不能化”,参见孔安国传,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81页。帝尧选择了舜继位。从这里的记载可见,丹朱虽未继位,但也是舜的群臣之一,在重要的朝廷祭祀中,以王者后的身份做宾,与其他诸侯一起助祭。无论丹朱是否真的不德,但顺利完成祭祀,至少表明他懂得且能践行祭祀的礼仪,这也是参与祭祀的基本前提。“考查《舜典》,唐、虞二代的学官有三部:一曰司徒,主宣布五教的,以契为之长;二曰秩宗,主持三礼的,以伯夷为之长;三曰典乐,教导诗歌音乐之类的,以夔为之长。”[6]除典乐之官外,主持三礼的秩宗,负责五教的司徒也承担着教育贵族子弟的工作。丹朱具备参与祭祀的基本素养必然是他少年时接受诸种礼乐教育,并反复演练而习得的。
现代社会通常将教育区分为人文教育和技能教育,但在上古时期,这两者是合一的,礼乐教育既是人文的也是技能的,旨在培养贵族子弟为政所需的品质和技能。在《尚书》记载中,各种祭祀颇为频繁,既有禅让、继位、战前誓师等重大事项,也有作为公共生活一部分的祖先祭祀等。既然祭祀是常规的政治活动,参与政治,担任官职,至少要懂得相应的礼乐知识。类似丹朱,即使是王者后,可享有世袭的爵位,但如果他不具备参与政治活动的基本素养,那么,在上古生产力低,实力、功绩是核心竞争力的政治格局中,他享有权益,继承爵位的合理性、合法性必然大打折扣。
除礼乐外,先王典、训等也是贵族子弟必须学习的内容。在《国语·楚语》中,申叔时曾列举了教授楚国太子的文献,有“春秋”“世”“诗”“礼”“乐”“令”“语”“故志”“训典”,②《国语·楚语》卷十七:庄王使士亹傅太子葴,辞曰:“臣不才,无能益焉。”……王卒使傅之。问于申叔时,叔时曰:“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这些都是培养贵族子弟成为精英所必需的文献。上古的文献没有此时丰富,教本难以如此齐全,但从文明发展的连贯性来说,思路是类似的。《尚书》中多次强调贵族子弟学习先王之“典”“训”的重要性:
《尚书·五子之歌》:其四曰:“明明我祖,万邦之君。有典有则,贻厥子孙。关石和钧,王府则有。荒坠厥绪,覆宗绝祀。”
典即经籍,是先王所遗,包含有治国的法则。这些文献不仅有知识上的重要性,而且具有思想上的权威性。从太康之弟的抱怨中透露出,太康也曾学习先王之典,但他遗弃所学,所以导致覆宗绝祀。
可见,上古时期教育的内容是基于政治实践而设置的,其最初动因蕴含着设计者的这样一种愿望:培养贵族子弟有效参与政治实践的基本素养,奠定他们获得政治成功的基础。
三、基于知识垄断的权力世袭
历史反复证明藉由教育而获得阶层的提升是有效可行的,(董仲舒)“最有关于中国社会组织的,是他主张设学校,立博士弟子,变春秋、战国的‘私学’为‘官学’,使地主阶级的弟子套上‘太学生’的外衣,化身为官僚,由经济权的获取进而谋教育权的建立与政治权的分润。”[7]读书科举之所以在中国古代社会备受重视,就在于接受教育,获取知识是通向政治权力的有效路径。相应的,文明初起时,教育是贵族的特权,知识被垄断在少数人手里,就是既得利益群体出于保障权力和维系利益的精心设计。
即使在上古,统治者也深知教育和政治权益的关联性,为使子孙后代永享富贵,垄断教育是最佳选择。最初“学在官府”的目的不仅是知识在贵族内传递,更是由此保障政治权力只在贵族内流转。在此思路背景下,有些家族甚至为确保某些官职仅在家族内部传递,相关知识也是家族世袭的。
《左传》载“官有世功,则有官族”(《左传·隐公八年》),由于祖先的功绩,族名以祖先所担任之官命名,同时,官职世袭。从《尚书》来看,世官在中国社会渊源颇久,羲、和二氏即是例证。“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作《胤征》。”(《尚书·胤征》)掌管日月天地之事的羲氏、和氏沉迷于酒,玩忽职守,夏王仲康派胤前往征讨。正义注“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时之官,自唐虞至三代,世职不绝。”[1]羲、和二氏担任四时之官一直贯穿于唐、虞、三代。据《尧典》记载,这一历程最晚开始于尧:
《尚书·尧典》: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申命羲叔,宅南交……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釐百工,庶绩咸熙。”
尧任命羲、和二氏共掌天地之事,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别居治东方、南方、西方、北方,仰观天俯察地,确定春夏秋冬的时节,合理安排农事。四人尽职尽责,所以尧赞叹他们的定历授事,使众功皆广,风俗大和。
羲、和二氏得以世官世职是由于祖先之功。在《尧典》、《吕刑》两处,正义解羲、和为重、黎之后。①“尧育重黎之后,是此羲和可知。”参见孔安国传,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1-43页。“重即羲,黎即和。”参见孔安国传,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775页。
据说,重、黎是颛顼高阳氏之后,为帝喾高辛氏火正,甚有功,②《史记·楚世家》:“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更为后世所熟知的是重、黎“绝地天通”(《尚书·吕刑》)的宗教改革。大致是由于这些功绩,其族便世袭掌管天地之事。
不过,到了夏仲康时,“羲和废厥职,酒荒于厥邑”(《尚书·胤征》),羲、和纵酒荒迷,观测星象不准,甚至不知道日食的发生,也或许是因为其势力威胁到夏的统治,故遭到征伐。但仲康只是处罚羲、和二氏中此时担任官职的人,并不剥夺二氏继续担任此职的权利,“羲、和之罪不及其嗣,故知杀其身,‘立其贤子弟’。”[1]即,此后将从族人中挑选其他贤能者继任,所以二氏世职“至于夏、商”。[1]
天地四时之官,需要懂得较为专业的天文、地理知识,如果官职世袭,则与职务相关的知识必然也在家族内部传递。“殷周的各种官职,其基本情形是,一经最初的某人担任某职之后,子孙相承,其管理技能和专官知识也成为父子相传的家族世业的财产。所以,世袭社会里不仅身份财产家族世袭,技能知识也家族相传。世官制自然形成知识传承的家族方式。”[3]那么,官职世袭是基于知识的世袭,知识垄断是保障权力垄断的有效手段。
羲、和二氏世官的情况并非个例,典型的如史官,其相关专业知识就是家族相传的。直到西汉,史官之守仍然为家传。所以,在贵族等级和部分官职长久世袭的世卿世禄制度中,与生俱来的血缘是决定政治身份的主要因素,在此前提下,教育的特权,知识的垄断也是有效的长远保障机制。
当然,《尚书》中也有平民而被选拔为官的案例,傅说就是高宗得于野,“使百工营求诸野,得诸傅岩。”(《尚书·说命》)据说舜也是“发于畎亩之中”(《孟子·告子下》)。虽有个例,但就整体的制度安排来说,教育和文献为官府把持,知识和学术由贵族垄断,贵族以外的阶层获得从政知识、技艺的可能性较小,担任官职的渠道有限。
可知,早期教育的构建,主要是来自政治运作的动力,使其呈现教育内容与政治实践、教育制度与政治利益密切关联的形态。但是,制度的运行、历史的发展并不总按主观预期行进,各种不可控的因素总是以某种力量推动文明向公平、合理的方向前进。
四、“不学”而权力下移
最初统治者设置教育的构想是通过知识、受教育权的垄断来保障贵族子弟永世担任官职,确保权力是一个凝固的世袭体系。但是再周全的制度安排也无法确保利益永存,一则,贵族子弟虽享有教育特权,但若没有学的意愿,再优越的教育资源也无意义。再则,非贵族通过其他途径积累了一定的社会资源后,必然挑战现有的利益格局,分享教育权难以避免。
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贵族祖先凭借艰苦创业建立事功,为保障子孙永享,精心设置了类似教育的制度保障,但没经历过创业的子孙未必能体会其中的苦心。他们养尊处优,失去了学的动力和意愿,
昭公十八年,鲁国大夫闵子马感叹:“周其乱乎!”(《左传·昭公十八年》)这是因为有人告诉他,周王室的大臣原伯鲁,“与之语,不说学。”(《左传·昭公十八年》)闵子马由此窥见周贵族中存在着“不学”的风气,“又曰:‘可以无学,无学不害。’不害而不学,则苟而可,于是乎下陵上替,能无乱乎?夫学,殖也。不学,将落,原氏其亡乎!”(《左传·昭公十八年》)即,贵族子弟认为不学没有什么害处,依然可以由世袭而享有高官厚禄,因而不学。
所谓一叶知秋,作为政治人物,闵子马由“不学”推导至乱、亡,这种逻辑关联可透露出统治阶层的学与不学不仅涉及认知层面,更与政治治理密切相关。如其所分析,不学则不懂得为政的知识,所以政事苟且即可,懂得更多的下级便趁机凌驾于上,如此则出现政在诸侯,政在大夫,政在陪臣的权力下移现象,那么乱不可避免,灭亡也就不远了。“不学,将落,原氏其亡乎!”(《左传·昭公十八年》)以小见大,闵子马由“不学”而预测到乱、亡。伴随着权力下移,“学在官府”变为“学在四夷”。王官失守,官府系统的一些知识人士、没落贵族因社会的变革而失去了职守,大量的教官、文化官吏和百工带着官府的典籍、文档、礼器、乐器流向民间,由此古代文献及知识、技术逐渐由官府垄断转而为多个阶层所共享。再后来,私学兴起,许多平民得以接受教育,并可能因其所学而获得服务新的政治集团的机会,实现阶层提升。知识改变命运,阶层有了更多流动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