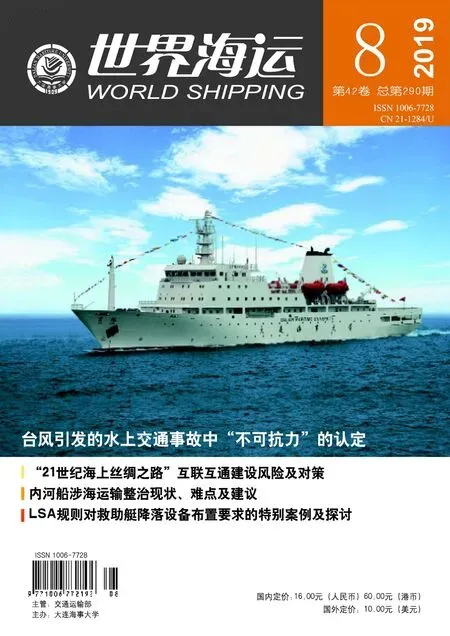台风引发的水上交通事故中“不可抗力”的认定
2019-02-17许岩松
许岩松
一、前言
2016年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印发的《水上交通事故报告编写指南》中指出“对于不可抗力直接导致的事故,应认定为非责任事故”。但指南对什么是“不可抗力”未作进一步的解释,事故调查人员对“不可抗力”的理解不尽相同,对“不可抗力”的认定不一定准确,从而引发相关人员的质疑或不满。数年前广东某市曾发生一起案例:台风中,一艘走锚的外轮将附近水域的渔排触损,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当地海事局认为台风属“不可抗力”,简单调查后将外轮放行,受损养殖户不满调查结论后发生聚众冲击海事办公场所的群体性事件。2017年强台风“天鸽”过境广东辖区时,发生多起事故,广东省各分支海事局在事故调查中做法不一:有些认为该台风属“不可抗力”,船舶不负责任;有些则认为即便是强台风,船舶也应负全部责任。同一台风,不同事故调查报告的观点引起相对人的困惑。这些事故引起的纠纷被诉讼至海事法院后,法官则面临裁判难题:若均认同海事部门的事故报告,则会出现相似情况下,判有些船承担责任、有些船不承担责任,裁判尺度不一;若不认同某些事故报告,则按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中国海事局《关于规范海上交通事故调查与海事案件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有“充分事实证据和理由足以推翻海事调查报告及其结论意见”。最终,法官在公平、公正理念的指引下,势必要推翻其中的一些报告或结论意见。到底什么是“不可抗力”?水上交通事故中“不可抗力”如何认定?本文拟通过一起实例,探讨应如何认定“不可抗力”,试图统一事故调查做法,树立海事部门的威信。
二、事故案例
(一)事故经过
2017年8月22日约1100时,P轮从东莞装载约2 000吨水泥管桩拟驶往珠海斗门白蕉镇灯笼村。约1700时,该轮航经磨刀门水道珠海大桥下游约500米处,因防抗“天鸽”台风,船长石某决定驶往磨刀门水道左岸灯笼山水闸附近水域锚泊避台,约1900时,抛锚避风。船上共有船员2名,为船长石某和驾驶员邓某。
8月23日约0900时,东北风,风力加大,船长和驾驶员开动双主机顶风,船舶未走锚。
约1230时,风停了约10分钟后,风向立即转向为南风,风力很大,周围附近船舶开始走锚。该轮继续开着双主机顶风,船上两人穿上救生衣。
约1245时该船开始走锚,船舶被吹向左岸,当时水位较高,船首大量上浪,水涌进船舱。
随后,该轮受风浪影响,走锚至灯笼水闸上游约400米处水域,船长石某决定弃船逃生,两人爬到驾驶室顶部,并先后跳入水中,向岸边游去。后邓某游到岸边后获救,石某失踪。
(二)船舶情况
P轮为内河A级干货船,船长为56.75米,船宽为12.50米,型深为4.30米,总吨为978,参考载重吨为2 093吨,建造日期为2012年3月。该轮在发生事故时缺少1名轮机员。
(三)锚泊水域情况
该轮锚泊水域为磨刀门水道左岸灯笼山水闸水域,水面宽约1 000米,为内河船舶习惯防台水域。事发时,P轮周围有多艘船舶锚泊避风。在强风和大浪的袭击下,该水域的多艘船舶均发生不同程度的走锚或断锚漂移现象。
(四)台风情况
1.中央气象台的预报
根据中央气象台资料,20日1400时,热带风暴“天鸽”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中心最低气压1 000百帕。预计,“天鸽”将以每小时25千米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可能在8月23日凌晨到上午在福建南部到广东东部沿海登陆。
孩子出世那年,我们没有回家过年,毕竟,孩子太小了,不适合跟着我们一路颠簸。当婆婆在电话里听到这一消息时,她的声音中充满了失落:“不回来啊?还给你们养了只羊呢。”我笑了:“养了就养了啊,你和爸爸自己吃吧。”
根据中央气象台21日0600时预报,台风“天鸽”预计在广东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登陆风力23~28米/秒,9~10级(热带风暴级或强热带风暴级)。
22日0800时,“天鸽”加强为强热带风暴级。中央气象台预计,“天鸽”将以每小时25千米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持续加强,最强可达台风级或强台风级(35~42米/秒,12级~14级),并将于23日白天以台风级(33~40米/秒,12级~13级)在广东惠东到吴川沿海登陆。
1800时,中央气象台发布“最强可达台风级或强台风级(35~42米/秒,12~14级),并将于23日白天在广东深圳到茂名一带沿海登陆(33~40米/秒,12~13级,台风级)”的警报。
23日约1250时,台风“天鸽”(强台风级)在广东珠海南部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45米/秒)。
2.当地气象台预警及实测风力
当地气象台于8月22日0755时将台风预警信号升级为蓝色,8月22日1456时发布黄色预警信号,8月23日0645时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信号,8月23日0910时将台风预警信号升级为红色。
三、对“不可抗力”的理解
什么是“不可抗力”?在法学理论界主要存在三种观点[1]:一是主观说,主张以当事人的预见力和预防力为标准,凡属当事人虽尽最大努力仍不能防止其发生者,均为不可抗力。二是客观说,主张以事件的性质及外部特征为标准,凡属一般人无法抵御的重大的外来力量,均为不可抗力。三是折衷说,兼采主客观标准,凡属基于外来因素而发生,当事人以最大谨慎和最大努力仍不能防止的事件,均为不可抗力。从上述三种观点我们可以看出主观说和客观说都存在片面性,与此相比较,折衷说采用主客观相统一的标准比较合理。我国的《民法通则》和《合同法》采纳此观点,《民法通则》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本法所称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使用三个“不能”作为判断不可抗力的标准,即当事人主观上不能预见,客观上不能避免和不能克服客观情况。这个标准看似清楚,但在解决本案时仍存在较大争议。
如一些调查人员认为,按《民法通则》关于“不可抗力”的标准,中央气象台在20日就已经预报,且船长在22日1700时也知道台风“天鸽”的存在,因此不构成“不能预见”,也就不能算“不可抗力”。
另一些调查人员则认为,船长在决定去锚地避台时(22日1700时)所知道的气象信息是中央气象台0800时所发布的预报,该预报虽预测台风最强可达强台风级,但预报登陆位置为广东惠东到吴川沿海登陆,范围过大。若台风在惠东登陆,由于该锚泊位置处于左半圆,且在周围有山遮蔽的内河水域,风浪相对较小,在该锚地是安全的;若在吴川登陆,因台风中心距离较远,按以往的经验,在此处锚泊也较安全。船长不能预见台风就在锚地水域附近登陆,且一艘内河A级船舶不能抵抗14级以上的风力,因此,应构成不可抗力。
还有调查人员认为,要援引“不可抗力”,其中一个重要条件是自己没有过错,P轮在配员上少一名船员,存在过错,不能算“不可抗力”。并举出海南法院近期审判的案例,该案例是关于一起台风中围墙倒塌砸伤男童的案件,法院认为被告的围墙不符合建筑标准,存在过错,不能引用“不可抗力”,判决被告赔偿。
各调查人员观点均有一定道理,那么事故调查中到底应该如何认定“不可抗力”?
四、水上交通事故中如何认定“不可抗力”
水上交通事故有一定的特殊性,若完全按《民法通则》中“不可抗力”标准的字面解释去认定,不一定符合水上交通事故的实际情况。与水上交通关系密切的《海商法》也有关于“不可抗力”的条文,其第167条规定:“船舶发生碰撞,是由于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能归责于任何一方的原因或者无法查明的原因造成的,碰撞各方互相不负赔偿责任。”司玉琢、吴兆麟合著的《船舶碰撞法》对该条作进一步解释,对于台风中锚泊船走锚碰撞他船,若欲归因于“不可抗力”的风力造成碰撞,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风力不可预见;二是船舶曾妥善地系泊或锚泊;三是照管船舶方面不存在疏忽。
显然,司玉琢、吴兆麟教授对“不可抗力”的解释更符合水上交通事故的实际。但此三个条件仍存在一定的争议。
一是要求风力不可预见存在争议。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目前几乎没有未被预报的台风,那么是否说台风构成“不可抗力”的条件不存在呢?答案是否定的。首先,气象台对台风的风力、路径很难准确预报,气象预报是面对社会的,其本身具有不确定性,这种预报与法律上的“预见”是不一样的[2]。其次,即便气象台准确预报,也和当事人预见的最后“时间点”有关,如甲乙双方三个月前签订运输合同,在实际运输过程中因台风延迟交货,虽然该台风被准确预报,但甲乙双方在签订合同时不可能预见,因此,属于“不可抗力”。对于船舶防台,也有一个最后“时间点”,如内河船舶在台风前已经根据预报选择远离台风路径的内河水域锚泊抗台,在台风登陆前数小时,台风突然转向,气象台及时预报台风路径将经过锚泊水域,但此时由于内河防台锚地狭窄,内河船舶密集,航道已被堵塞,船舶不可能再起锚避台。这时即便气象台预报准确,对内河船舶而言,也应属不可预见。那么船舶防台最后“时间点”如何确定呢?是5小时还是10小时?国内尚无此方面的研究。笔者认为中国气象局发布的《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及防御指南》可以作为判定的依据。在防御指南中,在发布台风橙色信号(12小时内可能或者已经受热带气旋影响,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10级以上)时,要求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应回港避风;在发布台风红色信号(6小时内可能或者已经受热带气旋影响,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12级以上)时,要求回港避风的船舶要视情况采取积极措施,妥善安排人员留守或者转移到安全地带。结合防台实践,本文认为船舶安全防台的最后“时间点”在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信号期间内,再晚,如发布台风红色信号时,则由于风力过大,船舶并不能安全到达指定的锚位,船舶丧失安全防台的机会;对于发布台风橙色信号前已经锚泊防台的船舶,在发布台风橙色信号后,即便气象预报变化的台风路径和风向对本船不利,由于此时附近风浪已经很大,再次起锚另找锚地可能更加危险。因此,这些船舶的最后“时间点”应为发布台风橙色信号时。对于发布台风橙色信号前已经前往锚泊的船舶,在发布台风橙色信号时即便预报的路径和风力已经变化,但对该船而言除了去预定的锚地别无选择,或去其他附近锚地更不安全,则该船的最后“时间点”仍应为发布台风橙色信号时;对于在发布台风橙色信号后才决定前往锚泊,且在台风橙色信号期间已经妥善锚泊的船舶,该船防台的最后“时间点”应为船舶决定前往锚泊时。对于在台风红色信号才锚泊的船舶,因为已经不符合防御指南要求,存在过失,不适用“不可抗力”,讨论最后“时间点”没有意义。在船舶防台最后“时间点”后,即便气象预报精确地预测了台风路径和风力的改变,也应属于不可预见。
二是要求船舶妥善锚泊或照管船舶不存在疏忽也存在争议。什么才是妥善锚泊?什么才是照管船舶不存在疏忽?观点不一。本文认为锚泊过失或照管船舶过失是指与防抗台风相关,且和事故的发生有因果关系的工作的过失。如船舶在防抗台风过程中发生事故,后发现船员未按要求填写航海日志。虽然未填写航海日志违反相关规定,但由于未填写航海日志和事故的发生没有因果关系,所以不应认为是防台存在过失。
对于本文案例而言,当地气象台在8月23日0645时发布橙色台风信号,而此后的路径、风力的预报并无太大变化。因此,对P轮而言,在最后“时间点”气象预报已经精确预报,因此台风是可预见的。由于“不可抗力”的标准未满足,该起事故不属于“不可抗力”导致。
五、“不可抗力”并非船舶免责的唯一事由
该起事故不属于“不可抗力”导致,那么是否一定是责任事故呢?其实不一定,根据《海商法》第167条规定,“不可抗力”属于“不能归责于任何一方的原因”中的其中一种情况,其他情况是什么呢?有学者认为,其他情况是指意外事故,即船方已做到了通常的谨慎和技术[3],仍不能避免的事故。对于意外事故,船舶同样对他方不负责任,和“不可抗力”的法律后果相同。
对于本文案例而言,船方是否做到了通常的谨慎和技术,是考察船方是否负有责任的关键。P轮在本航次未配备轮机员,很难说船方做到了通常的谨慎和技术,因此不属于意外事故的情形,该起事故应为责任事故。
为了便于探讨意外事故的情形,本文假设案例中P轮配员合格,其他条件不变。该轮在台风橙色信号之前就已经前往习惯防台锚地锚泊避台,且锚泊时中央气象台预报的路径并不直接经过锚地水域,当时该水域已有很多船舶在锚泊抗台,说明船长对锚地的选择符合通常的谨慎和技术要求;在发布台风橙色信号后,由于该水域已经有众多船舶锚泊,航道不畅,且在不到3小时的时间内就升级为台风红色信号,船舶没有机会选择或驶往其他锚地,防台过程中P轮船员也无过失。由于台风风力远超P轮抵御能力,后该轮走锚导致事故。结合该水域其他船舶发生走锚的情况,可以认定该船船员已达到通常的谨慎和技术要求,该起事故构成意外事故。
值得注意的是,不论“不可抗力”还是意外事故,对于民事责任而言,不负有责任是指对他方而言,本船自己的损失还是应由自己承担。对于行政责任,根据《水上交通事故报告编写指南》,若为不可抗力或意外事故,应认定为非责任事故。
六、结束语
从本文案例可以看出,在现有的气象科学条件下,要认定“不可抗力”条件比较严苛,且即便符合本文探讨的标准,若直接认定也同样存在来自其他学者、法官、调查人员、相对人的争议。因此,建议事故调查人员在调查时不要过分纠结去认定“不可抗力”,而是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搜集证据以认定船舶在防台时是否达到通常的谨慎和技术要求上,若已经达到,没有防台方面的过失,则可认定该起事故为非责任事故,否则,应为责任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