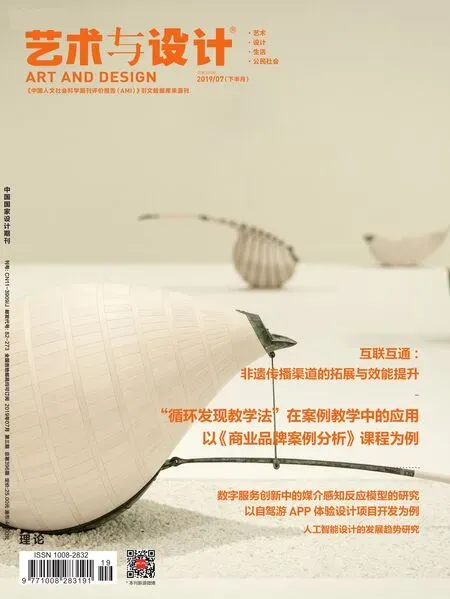从艺术到商品
——顾绣从明代到清代的演变
2019-02-10邓莉凡
邓莉凡
(四川大学,成都 610065)
一、顾绣的起源与兴盛
刺绣是中国优秀的传统艺术,又称“女红”。工艺美术界一般认为刺绣略迟于纺织,是随着缝纫的产生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刺绣以物质文化形式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与思想,并上升为不同的审美观念和心理倾向。最早出现的刺绣完全是实用性的,观赏性的刺绣作品大约从魏晋时期就已出现,在顾绣之前,宋朝的画绣便已有一定水准。而顾绣的出现,则将“画绣结合”这一艺术形式推向了巅峰。
江南是明中后期商业最为发达的地域,而松江府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繁盛的手工业和独特的人文环境使其开出了顾绣这朵奇葩。顾绣能在这片土地上枝繁叶茂,除了地域优势外,更和时代背景、家族文化积淀与个人艺术修养以及文人雅士的密切参与有关。
明代,特别是明中叶以后,社会风向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彼时经济的繁荣和商业的发展让世人——特别是文人有了“求新”和“尚奢”的思想。该时期的艺术发展也深受这种时代精神的影响,新兴的艺术样式被文人士大夫们所推崇。这种大环境为顾绣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而在这种环境下所产生的顾名世家族也拥有着良好的文化积淀。顾家家族成员显贵众多,礼乐簪缨,科甲不断,崇尚高雅文化与新奇的生活意趣。
在这种家族氛围中,顾氏女眷也深受影响。她们日日耳濡目染,深受士大夫文化影响,拥有着极高的个人文化修养。除此之外,明中后期道德观念的改变与女性自由程度也为顾氏女眷的艺术创作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明中后期的江南一带女性受教育程度较高,文人雅士们对于有艺术才华的女性多持欣赏态度。加之顾氏一族与众多文人雅士多有来往,名士对于露香园顾绣的品鉴与推动对于顾绣的发展有如神助,如董其昌为顾绣所作的题跋便对其赞美不绝。这种种因素,让顾绣在刺绣艺术这一门类中脱颖而出,确立了其艺术地位。
二、顾绣之艺术化
(一)顾绣之美
顾绣之所以为画绣一绝,其风格之美,技法之美,艺术之美是其他刺绣作品无法比拟的。如画之境、如天之工、如染之色,是顾绣公认的三大特点。如画之境是顾绣最本质的特点,其作品绣画结合、意境超然,董其昌更是称韩希孟的作品超越了黄筌父子的写生画作。如天之工是对顾绣超绝技艺的最好表述,其针法多变、用料特殊、字顺笔势,无一不见绣者的高超技术。如染之色则指顾绣用色灵秀,所谓“配色有秘传”,顾绣善于运用中间色和补色、善于借色,其色彩多淡雅细腻,富于虚实变化,深刻展现了顾氏女眷的绘画功底。这三大特点无一不彰显出顾绣极高的艺术性。
顾绣之美恰恰就在于它的艺术性,其文化性就是艺术化的外在表达。顾绣与其他画绣作品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它所表现的文化性,这种文化性就包括文人趣味中的“雅”与世俗情怀的“俗”。其早期作品中所表达的文人趣味和后期作品中所展现的世俗情怀虽是“由雅化俗”,但也可以说是雅俗共赏。早期顾绣作品多表达文人理想,文人理想又有“出世”与“入世”之分。出世之理想落点于隐一字,绣品意在表达文人士大夫出世而隐逸的思想,大隐于朝,中隐于市,小隐于山水。而入世之理想则期冀于获取功名或拯救世人,绣品多表现文人士大夫对于功名利禄和百姓苍生的积极态度。这种种文人理想,是顾绣之美。后期顾绣作品因为其本身的商品化,转而表现出了对于世俗情怀的愿景。此类绣品或表达对婚姻爱情的期待,或表达对富贵长寿的憧憬,或表达对平安善果的希冀。虽然是世俗情怀,但因为绣者的精湛技艺与艺术风格,这类绣品依然保存着顾绣的艺术特色。
顾绣之美,从董其昌于顾绣的题跋“人巧极、天工错。奇矣!奇矣!”中,我们便能窥得一斑。可以说,顾绣之美不仅仅是创作者的艺术表达,其背后更是蕴涵着时代、不同阶层的理想或追求,展示着不同的文化之美。顾绣之美,涵盖了艺术化与商品化这两极,而下文则将分析顾绣为何会从艺术往商品演变。
(二)明代顾绣的艺术特色
顾绣大约于明代嘉靖年间开始著称,可以说,顾名世长子顾汇海之妾缪氏是为顾绣发源第一人。顾汇海的文人朋友们第一次见到缪氏的画绣作品便惊为天人,其“所绣人物、山水、花卉大有生韵”。而到了顾汇海侄寿潜之妾韩希孟时,顾绣发展至艺术化的顶峰,其绣品多绣有“韩式女红”或“韩式希孟“,后人称其绣品为“韩媛绣”或“韩秀”。
张美芳在《浅谈顾绣的艺术特色》一文中便总结到,顾绣选材独到、因画施绣、绣绘结合、因材施艺。明代的顾绣绣稿来源丰富,最大的来源便是文人画,包括了历代名迹与本朝画本。除了文人画之外,这一时期的顾绣绣稿还有传世粉本、自创绣稿和出版物。以文人画为绣稿的绣品题材多是山水、人物,用色又高雅内敛,意图达到笔墨晕染的效果,这样的绣稿来源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此时顾绣的艺术风格,绣品给人以雅致而恬静的审美体验。明代顾绣达到了较高的艺术境界,不仅深得名家的笔法画意,更是师法自然、将自然景物融于绣作之中,刻画精细而巧妙传神。在这样的艺术化氛围中,顾绣的绣作极力贴近绘画效果,针法不能及之处便以画代绣,如此风格自然独一无二。
明代顾绣之所以能保持极高的艺术化,原因是多样化的。这一时期文人地位较之以往大有提高,大有一股“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风潮。此时的顾绣不是以缝补度日的糊口手段,而是“敢将十指夸针巧”的修身养性。对于缪氏与韩希孟这样的上层女性来说,刺绣就如同琴棋书画一样是她们修身养性的创作。她们自持夫人身份,不愿将绣作商品化,为了一幅完美的绣品,她们甚至不惜用上数年的岁月。也因为身份地位,她们拥有这不同一般的艺术品位,她们将文人雅士所偏好的平淡自然的绘画风格用画绣的形式表现,创作了顾绣这一与众不同的艺术形式。而董其昌等对于顾绣的推崇更是将其推到一个极高的艺术地位,甚至于夺丹青之妙,分瀚墨之长。
极富艺术特色的顾绣在明代一幅难求,民间绣坊也无一不以其为标榜。明嘉靖以后顾绣甚至被纳为宫廷贡品,专为皇室所享。顾绣声名远扬,它的艺术化顺应了时代潮流,为世所珍。
三、顾绣之商品化
虽然说顾绣从明代到清代完成了从艺术化到商品化的转换,但它早期的艺术化并不是完全与商业无关的。从缪氏时期顾绣的名声开始打响,到韩希孟以其极其精湛的绣技和极高的艺术造诣成为顾绣第一人,顾绣一直在提升其品牌形象和艺术价值。而顾绣的商品化其实并不仅仅存在于其发展后期,明末时顾绣的交易活动就已经存在,最早是赠予和回馈的形式,绣品一般作为家藏或友人礼赠。这样的活动潜移默化地提高了顾绣的商业价值,致使民间开始仿制并在市场出售,甚至“顾绣”二字一度成为刺绣工艺的代名词。然而,顾绣并不像普通刺绣一般,经过有序培训和长期练习便能绣出像模像样的成品。顾绣不仅仅是传统手工艺的展现,也不仅仅是对绣稿的简单摹画,它以娴熟的绣艺和绣者对于书画艺术的别样体验对绣稿进行了再创作,成品甚至已经超越了画作本身。可以说,它的本质就是女红功能向书画领域的拓展和延伸。顾绣对于绣者艺术修养的要求是极高的,她们必须集书画艺术与刺绣艺术于一身,才能完成一幅优秀的画绣。民间的普通顾绣从业者数量基数大,艺术造诣也参差不齐,顾绣在逐步商品化的同时质量也有所下降,可谓有得有失。
事实上,顾绣向商品化转换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顾氏家族的逐渐式微。露香园由顾名世建起,顾氏一族终日在园中以文会友,过着不问世事的贵族雅士生活。顾名世过世后,其子孙依旧每日挥霍,生活起居与以往无二,这样的生活方式致使顾家日渐入不敷出,最终家道中落。这一时期顾家已经在靠顾绣交易来维持生活开销,只是大约是顾忌到所谓贵族民生,虽然打破了顾绣不拿来牟利的规矩,但这时的销售活动依然只是半公开进行的。直至清初,顾绣声名鹊起,富商达官争相购买,其价格越炒越高,各个地区都开始设有顾绣绣庄。
顾氏家族中,张来妻顾氏在顾绣走出深闺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如上文所说,她“传针黹以营食”,通过售卖绣作营生养家。而历史上经常和她混淆的一位女子顾兰玉更是进一步让顾绣商业化和社会化了。张来妻顾氏活跃于明清之交,她对于顾绣商业化进程的贡献主要在于让顾绣彻底走出顾家。而顾兰玉活跃于乾嘉之间,与顾家并无直接关系,她只是一位能诗善绣的清朝女子,然而也正是她“设幔授徒”让顾绣彻底地社会化,也借着顾绣本身的商业价值和品牌效应维生。因为市场需求的逐步加大,顾绣便不仅仅是顾氏女眷的艺术活动了,民间开始逐渐出现顾绣从业人员。到了清代中叶,顾绣的从业人员已有一个很客观的数量。一方面来说,这是供需关系改变的后果,顾绣的声名远扬导致市场需求激增,而市场对于顾绣需求的增大进一步导致了顾绣的商业化。可以说,顾绣由纯粹的艺术化向商业化转变,是其发展的必然结果。
顾绣从艺术化转向商业化的一个明显影响就是其审美风格和艺术特色的改变。清代顾绣较之明代色彩更为丰富,已少有淡雅简洁的艺术特色,且选题也具有很强的社会性,相当一部分都是吉庆颂祝和民间志趣,这都是适应商业化生产的结果。
四、结语
顾绣作为“女中神针”,其艺术特征和历史价值或许可以称得上是历代之最,而其对于女性价值的解放和体现也是独树一帜的。它从诞生至衰落虽然仅有短短百年,因为保存问题存世作品也较少,但这都无法抹去它对中国刺绣,或者说画绣这一传统艺术门类的贡献。它的出现对于当时的社会与如今的研究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从明代到清代,顾绣经历了从闺阁艺术到社会商品的转变,它的题材内容、绣者阶级和艺术风格都发生了很大转变,但不变的是其与书画艺术的融合。艺术化的顾绣是上层妇女的闲暇自娱和文人雅士的观赏雅趣,而商业化的顾绣是民间的馈赠礼物和社会的规模传承。商业化当然是有恶性影响的,过大的规模让顾绣质量参差不齐,直至式微,但顾绣的传承却也因为这样的大众化而保持了下来。顾绣将刺绣与文化相互交融这一精髓流传到了清中后期的闺秀女子手中,现如今又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式被保护。这一特殊的传统艺术文化形式终将在现代化中得以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