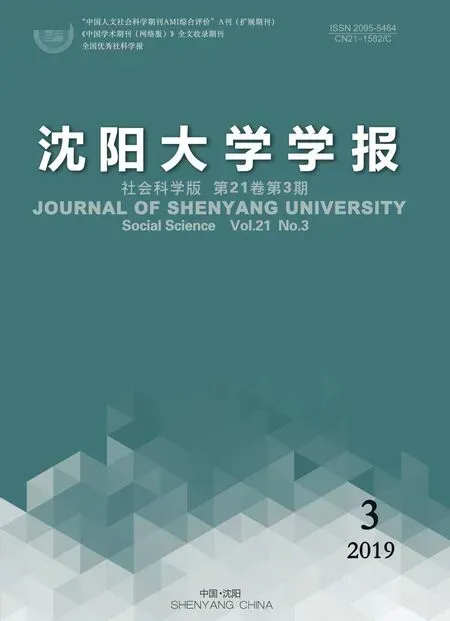沈阳故宫大政殿独特建筑规制下的人文内涵考略
2019-02-09张欣
张 欣
(沈阳大学 学报编辑部, 辽宁 沈阳 110041)
宫殿建筑是古代建筑的精华,记录和体现着历史上某一朝代的历史变革和发展进程,体现了不同朝代独特的政治和文化传统。中国古代宫殿建筑一般分正式建筑和杂式建筑两类,正式的宫殿建筑强调规范性、正统性和等级性,以长方型建筑为主体,配以庑殿顶的砖木屋顶[1]41。古代皇宫建筑多为宫殿一体,前朝后寝,即宫殿建筑的主体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为“殿”,是帝王上朝理政、举行大典的处所;后为“宫”,是皇帝与后宫嫔妃居住、生活的处所。研究宫殿建筑规制能够揭示历史、追溯文化。大政殿是沈阳故宫建筑群中最早完成的建筑,沿袭了满族建元之后一贯的独特八角型宫殿建筑规制,是“八角重檐攒尖顶大木架结构”建筑[2]。大政殿在沈阳故宫中具有特殊的地位,清初重要的大典都在大政殿举行。此外,大政殿有“殿”而无“宫”的自由、随宜、粗犷、开放,不拘于正统的建筑格式,也呈现出等级较为模糊的特色,是具有浓郁满族特色的“杂式建筑”[2]。大政殿与其前方雁翅式排开的十座王亭构成了故宫最早的东路建筑群,巍峨神武,有如白山黑水间的满族武士,严密地守护着努尔哈赤的后金政权。本文试从战略思想、传统沿袭、民族政策几个角度,对大政殿的人文内涵进行考略。
一、征讨大明、入主中原的战略“殿帐”
建都赫图阿拉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在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的赫图阿拉城创建大金国,年号天命,史称后金。赫图阿拉城依山傍水,易守难攻,努尔哈赤由此一步步入主中原。《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以下简称《实录》)载:万历十一年(1583年),“太祖欲报祖、父之仇,止有遗甲十三副,遂结诺密纳,共起兵攻尼堪外兰。时癸未岁夏五月也,太祖年二十五矣。”[3]32从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城建立后金,至天命六年(1621年)迁都辽阳,再至天命十年(1625年)迁都沈阳,十年间共建都三次,即迁都二次。两次迁都都是在重大战役收取重要城池之后不久作出的决定。
第一次迁都,从赫图阿拉城迁至辽阳,兴建东京城。天命六年(1621年)三月,经过浴血奋战,攻下重镇辽阳后,努尔哈赤与诸王、大臣商议说:“皇天见佑,将远东地方付与我等。然辽阳城大,且多年倾圯,东南有朝鲜,西北有蒙古二国,俱未服。若释此而征明国,难免内顾之忧,必另筑城郭,派兵紧守,庶得坦然前驱,而无后虑矣。”[3]351当时,诸王臣在大战之后,归乡之意甚浓。努尔哈赤出于战略考虑,不顾将士连续征战的疲意,坚持迁都辽阳。从战略角度看,辽阳地理位置重要,处于大明、朝鲜、蒙古三国之间的中枢要地,占据辽阳可以制衡大明、朝鲜、蒙古三国。因此,占据辽阳能够为日后入主中原作充足的准备。努尔哈赤的迁都理由使众王臣敬服,“遂于辽阳城东五里太子河边,筑城迁居之,名其城曰‘东京’。”[3]351金迁都辽阳后,在东京“城内二个高点各建‘八角龙殿’和‘寝宫’。”[4]
第二次迁都,从辽阳迁至沈阳。天命十年(1625年,天启五年)正月,大明遣兵一万至旅顺口葺城,攻打满洲。十四日,努尔哈赤命三王领兵六千迎战,尽杀明兵后,毁掉旅顺城。三月,帝与诸王臣商议迁都沈阳,众王臣皆进谏反对,认为“东京城新筑,宫廨方成,民之居室未备,今欲迁移,恐食用不足,力役繁兴,民不堪苦矣。”[3]377对此,《清实录》记载:“帝不允,曰‘沈阳四通八达之处,西征明国,从都儿鼻渡辽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至;南征朝鲜,自清河路可进。沈阳浑河通苏克素护河,上流处伐木,顺流而下,材木不可胜用;出游打猎,山近兽多,且河中水族亦可捕取矣。”[3]377这里,不顾“力役繁兴,民不堪苦”而再次迁都的理由完全出于战略考虑。因为沈阳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更适宜于进入大明,攻打蒙古和攻取朝鲜,且有充足的自然资源,如木材、食物等供应战争所需。沈阳作为战略要地,对稳定蒙古局势、遏制朝鲜势力都极其重要。于是,放弃仍在兴建中的辽阳东京城,迁都沈阳。这种步步为营,通过迁都占据领土,扩大势力的策略,卓有成效地使满洲的影响日益扩大。
二、满洲帝王的“八角衙门”
从赫图阿拉老城建筑,至辽阳东京城建筑,再到沈阳故宫大政殿,清初的宫殿建制始终如一地以八角亭式建筑形式呈现在后金的都城。这种宫、殿分离的八角亭式“殿帐”建筑格式,反映了游猎民族的生活习惯和擅长征战的作风。从建筑规制上看,大政殿没有明显的等级制式,属于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的宫殿。大政殿的“八角重檐尖顶大木架”建筑样式没有“严谨、正规、森严、端庄”的正规宫殿建筑气氛,而“给人一种散在、开放、粗犷、自由的感觉”[1]41。后金迁都沈阳后,大政殿成为后金政权处理军政事务的办公场所,被称为“大衙门”。大政殿是努尔哈赤与诸王贝勒集会或筵宴的重要场所,也是后金理政的最高权力机关。从大政殿有“殿”而无“宫”的建筑规制上看,用于办公的“衙门”功能更为突出,是兴建八角殿意图的充分体现。“大政殿是盛京皇宫内举行重大活动的最庄严和最神圣的地方。凡新君继位、颁诏、元旦庆典……举行国宴等均在此举行。”[1]42“除元旦之外,万寿节(皇帝生日)、冬至节、皇帝登基、出征凯旋等大规模庆典仪式也都在大政殿前举行。”[1]42
努尔哈赤从建立后金政权到迁都沈阳,始终在征战中,孔武尚勇是满族的重要特色和一贯风格,反映在宫殿建筑上,就是大政殿呈现出游猎民族的生活、征战风貌。大政殿的“殿帐”式建筑模式,外型如蒙古包或行军帐篷。大政殿沿袭自赫图阿拉城建制以来一贯的八角亭式建筑风格[5],既是女真人日常生活及征战露宿状况的真实反映,也是女真人早期游牧征战习俗在建筑上的因袭和保留。
从建筑的整体布局上看,大政殿有“殿”无“宫”是其主要特色。大政殿与其前方雁翅式八字排开的十王亭,共同反映后金政权最具特色的、军政合一式的八旗制度。大政殿是清初决定国家大事的最高权力机构所在地。在大政殿,“太祖五日一朝,当天设案焚香,以善言晓谕国人,宣上古成败之语。”[3]184对讼诉大事,努尔哈赤更是在大政殿“详问之,将是非剖析明白,以直究问。故臣下不敢欺隐,民情皆上达矣。”[3]185由于太祖在大政殿“日夜忧勤,上体天意,下合人心,于是满洲大治、欺诈不生、拾物不匿”[3]185,可见,大政殿充分发挥了其八角“殿帐”的实用功能,为后金政权的崛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努尔哈赤经过三十余年的征战才统一了女真各部落。《实录》载:“太祖削平各处,于是每三百人立一牛禄额真,五牛禄立一甲喇额真,五甲喇立一固山额真。固山额真左右立梅勒额真。原旗有黄、白、蓝、红四色,将此四色镶之为八色,成八固山。行军时若地广,则八固山并列,队伍整齐中有节次;地狭则八固山合一路而行,节次不乱。”[3]183这就是有名的八旗制度。这种行军征战使用的八旗制度也应用到生产耕作中去。对这种军事、生产与行政三位一体的八旗制度,《实录》载,八旗制度的建立,使金统治者“用兵如神,将士各欲建功;一闻攻战,无不忻然。攻则争先,战则奋勇;威如雷霆,势如风发。凡遇战阵,一鼓而胜。”[3]184迁都沈阳后所建的大政殿,除了体现地方政权外,还是满族军政合一的八旗制度的建筑体现。大政殿前面,除了左右翼王亭,按照八旗制度,左侧建造分属于镶黄旗、正白旗、镶白旗、正蓝旗的四座王亭,右侧建造分属于正黄旗、正红旗、镶红旗、镶蓝旗的四座王亭。大政殿与其前两侧的十王亭大气排开,外观巍峨神武,如外出征战搭设的营帐,又如白山黑水间的满族将士跋涉出征小憩后,时刻准备迎战敌军。沈阳故宫大政殿不但有“殿”无“宫”,而且其前方雁翅形左右排开的十王亭保留了行军征战时的布局,记录了满族生活和征战的原始风貌,以及满洲兴国以来的赫赫战功,使满族人孔武尚勇的精神展露无疑。同时,巍峨神武的大政殿及十王亭也向世人彰显着努尔哈赤征战大明、入主中原的勃勃雄心。
三、“满蒙一家”的庄严殿堂
沈阳故宫大政殿高21米余,由殿顶、殿身、殿基三个部分组成。即使是在早期兴建的沈阳故宫东路宫殿建筑群中,大政殿的殿顶设计与装饰也独具特色。“满族是能征惯战的民族,也是富有艺术气质的民族。”[6]大政殿的双层殿顶全部由黄色琉璃瓦覆盖,边缘饰以绿色琉璃瓦镶边,即“黄琉璃瓦加绿剪边”[2],装饰风格上充满艺术格调。殿顶是八角形建筑自然形成的八条垂脊,垂脊上“各立有一个彩色琉璃烧制的胡人力士,深目高鼻、紧衣小帽,虽然姿态各异,但都好象是在用力牵引绳索加固宝顶,其构思巧妙,仪态生动。”[2]大政殿此处的设计集中反映了当时满蒙相亲相助的结盟关系。从万历十一年(1583年)至天命十一年(1626年,天启六年),努尔哈赤仅用了33年时间,迅速从一个落后的女真少数民族部落的酋长崛起,统一满洲、建元天命,被颂为“列国沾恩明皇帝”[3]186;之后,再用十年时间,统一东北地区,为满洲贵族入主中原、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努尔哈赤崛起之初,满洲地区的局势错综复杂,除了女真各部落互不统属、互相残杀、强凌弱、众暴寡,客观上迫切需要形成统一的民族势力外,满洲地区的复杂局势也是客观原因。相邻的朝鲜对后金政权怀疑、敌视,拒绝努尔哈赤的示好,视努尔哈赤的后金政权为“犬羊”[7],且有蒙古族对后金虎视眈眈、叛服无常,蒙古与朝鲜构成努尔哈赤政权南下攻打大明的后顾之忧。此外,在南下征服汉人地区时,努尔哈赤对抗拒的辽东军民进行残酷的屠杀,遭到被征服地区汉人的激烈反抗,汉人被掳后大量逃走。这一切使努尔哈赤不得不依据当时局势,调整与明、朝鲜、蒙古诸国的各种关系,在平衡中寻求成功崛起的道路。在诸种复杂民族关系中,满蒙关系在满洲成功崛起之途上至关重要。为排除南下征战明国的后顾之忧,努尔哈赤推行了一系列与蒙古族各部落和好的政策,包括联姻、礼待和“恩养”投奔后金的蒙古王公贵族、尊崇蒙古族信奉的藏传佛教等。其中的联姻使满蒙关系“两国如一国,两家如一家”[7],“努尔哈赤时代,满洲与蒙古科尔沁部落联姻,达10次之多”,“有清一代,满洲皇帝多从科尔沁娶纳福晋、皇妃,而科尔沁蒙古亲王贵族亦多娶清皇室或宗室公主。”[8]早在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成立后金之前,努尔哈赤已在统一女真部落的征战中拥有赫赫战功,科尔沁蒙古贵族已在努尔哈赤恩养、抚恤、约为兄弟的民族政策下开始与之通婚联姻。《实录》载,甲寅年四月十五日,“蒙古扎鲁特部钟嫩贝勒送女与太祖次子古英巴图鲁贝勒为婚,贝勒亲迎、大宴,以礼受之。二十日,蒙古扎鲁特部内齐汗送妹与太祖三子莽古尔泰贝勒为婚,贝勒亲迎、大宴,仍以礼受之。蒙古科尔沁莽古思贝勒送女与太祖四子皇太极贝勒为婚,贝勒迎至辉发国扈尔奇山城处,大宴,以礼受之。……十二月,蒙古扎鲁特部额尔济格贝勒送女与太祖子德格类台吉为婚,台吉亲迎、设宴,以礼受之。乙卯年正月,蒙古科尔沁部孔果尔贝勒送女与太祖为妃,迎接、设大宴,以礼受之。抡卫桩农贝勒,送女与太祖次子古英把土鲁贝勒为婚,贝勒亲迎,大宴,以礼受之。”[3]169-171短短八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满蒙频繁联姻达五次之多。通过联姻,蒙古科尔沁部落成为后金最早的同盟,孤立打击了其他的蒙古部落敌对势力。在联姻的基础上,后金政权对叛逃、投奔到后金的蒙古贵族及王臣倍加安抚恩养,加深并巩固了与蒙古各部落的同盟关系。《实录》载,天命六年(1621年,天启二年)十一月,“蒙古喀尔喀部内古尔布什台吉、莽果尔台吉率民六百四十五户,并牲畜来归。帝升殿。二台吉拜见毕。设大宴,各赐貂裘三领、猞狸狲裘二领、虎裘二领、貉裘二领、狐裘一领、镶边貂裘五领、镶边獭裘二领、镶边表鼠裘三领、蟒衣九件、蟒锻六疋、细锻三十五疋、布五百疋、金十两、银五百两、雕鞍一副、沙鱼皮鞍七副、镀金撒袋一副、又撒袋八副、弓矢俱全盔甲十副、奴仆牛马房田凡应用之物皆备。以聪古图公主妻古尔布什,赐名青卓礼克图,给满洲一牛录三百人,并蒙古一牛录共二牛录,授为总兵。其莽古尔以宗弟济伯里都济呼女妻之,亦授为总兵。”[3]336-338上述的种种赏赐、加官、恩养,对来后金投奔、归降的蒙古首领的礼遇之隆重、恩养之慷慨可见一斑。同时,在称帝前已开始大兴土木建造庙宇,以表示对蒙古佛教(藏传佛教)信仰的尊重。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四月“于城东阜上建佛寺、玉皇庙、十王殿,共七大庙,三年乃成。”[3]172通过一系列的通好、联姻、招抚、结盟策略,满蒙之间建立起了互不侵犯的亲善关系,解除了后金与明国对抗的后顾之忧,为下一步后金顺利南下攻打明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系列的满蒙民族政策和策略,在大政殿的建筑规制及装饰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如大政殿顶的蒙古力士,大政殿殿柱顶端的佛教神兽兽面,甚至两米多高的“须弥座式”大政殿殿基,都在彰显佛教氛围的基础上,浓重地渲染了满蒙友好、亲如一家的关系。
四、结 语
努尔哈赤在金戈铁马的开国进程中,以攻城掠地的征战拓展疆土。“满族作为一个文明程度低于汉族的少数民族,在攻伐明朝过程中自然被明人视为夷狄”[9],因此受到汉人的抵抗,且清初南下征战,又采取“抚养满族,诛戮汉人”[8]的政策,满汉矛盾十分激烈。故努尔哈赤的民族政策虽然有对蒙古部落怀柔的一面,也有武功胜于文治的残暴的一面。沈阳故宫只是清代帝王南下征明的前沿驿站,努尔哈赤及其后的各满族皇帝的目标,远不限于以沈阳为中心的东北地区,这在清代开国大政殿有“殿”无“宫”,征战意味十足的建筑规制中彰显无遗。尽管如此,在团结北方蒙古民族,征战辽宁广大汉族地区,励精图治、蓄意入主中原的过程中,为成功崛起而努力构建满蒙关系,南下征战过程中的逐渐汉化过程等,都体现在大政殿独特的建筑规制,以及富有创意的满蒙装饰风格的大政殿中。大政殿高居在砖石须弥座式台基上,“由于十座王亭以大政殿为中心向两侧外展,形成了一个开阔的梯形广场。两列亭子向南的开展和向北的收拢,使人们在视觉上增加了空间的深度感,突出了大政殿的高大宏伟和尊贵地位,反映出汗王与八旗王公共创军国大业的情景。”[10]51乾隆皇帝在回乡祭祖时赞美了大政殿“规模迥不群”[10]51,也突出了大政殿在历代皇家宫苑中的罕见。综上所述,大政殿可谓在中外宫殿建筑史上独树一帜,是清代宫殿建筑群中一道奇丽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