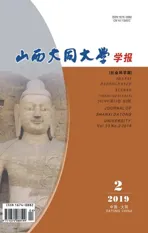汉语史中“更”类程度副词历时更替的原因分析
2019-02-09杨振华
杨振华
(河北大学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0)
一、引言
现代汉语中,表示事物特征、行为、数量程度加深、加重的副词有“更、更加、越发、越加”等,这类程度副词介于“稍微、略微”与“很、太、非常”之间,也称之为比较级程度副词。古代汉语中,表示比较的程度副词有“愈、益、弥、滋、加、倍、转、更、越、更加、越发”等,它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段,使用的情况有所不同,即便是在同一个历史阶段内,它们的用法和出现频率也不尽相同。
汉语史中表示比较的程度副词产生于汉语史的不同阶段,在上古汉语阶段产生的有“愈、弥、益、滋、更、加”,其中“更”出现的最晚,最早的文献用例见于战国末期的《战国策》中;在中古汉语阶段产生的有“倍”“转”,其中“倍”的文献用例始见于《汉书》中,“转”始见于《三国志》中。在近代汉语阶段产生的有“越”及复音词“更加”“越发”,“越”始见于宋代文献《朱子语类》中。这些表示比较的程度副词在汉语史中发展演变的基本面貌为:上古汉语时期,“愈”“益”“弥”出现次数较多,占主导地位,“滋”“加”使用频率较低,“更”只有零星用例;中古汉语时期,“益”发展成了比较类程度副词中最主要的成员,“愈”“滋”“弥”“倍”“更”居次要地位,“转”出现次数最少,而上古时期的“加”在这一时期已经退出了该类语义范畴;近代汉语时期,“更”占据了比较类程度副词主导词的地位,新产生的“越”“越发”发展迅速,在明清时期成为了该类副词的主要成员,而“愈”“转”“益”“倍”等使用频率较低,且逐步消退。
那么,为什么在汉语史上会出现这么多的同类副词?它们又是因何原因逐步发生了历时更替?我们从两个方面来探讨汉语史中比较类程度副词历时演变的原因。
二、汉语史中比较类程度副词递相类聚的原因
汉语史中表示比较的程度副词大都由动词语法化而来。杨荣祥(2001)认为:“决定和促成副词的形成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条件:语义基础是副词形成的基础条件;句法位置是副词形成的决定性条件;语用因素是副词形成的外部条件。”[1]“语法化”理论所说的“词义滞留”规律,就是指语法化的成分总是保留了其来源词的一部分意义,反过来,也就是说虚词的语法化总要有一定的语义基础。所以,比较类程度副词与它们所自出的动词在意义上一定是有联系的。
“愈”的本义为胜过。如《论语·先进》:“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表胜过意义的“愈”修饰、限制动词或形容词时,就表示胜过限制对象的程度了,就发展有了更加、越发义。例如:
(1)昔我往矣,日月方奥。曷云其还?政事愈蹙。(《诗·小雅·小明》)
(2)夫以汤止沸,沸愈不止,去其火则止矣。(《吕氏春秋·尽数》)
“愈”也写作“俞”、“逾”。《说文·辵部》:“逾,越进也。”“愈”应是由“逾”发展而来的,行动上的超越是“逾”,行事上的超越就是“愈”。“愈”的病情好转义是由胜过义引申来的,而非本义。
“益”,本义为水从器皿中溢出,是“溢”的本字。《说文·皿部》:“益,饶也。从水皿,水益之意也。”“益”后来泛指增加,《广雅·释诂》“益,加也”。程度上的加深也是增益的结果之一,所以表示增加的“益”修饰、限制形容词或动词时,就表示与之前相比程度加深。例如:
(3)及壬子,驷带卒,国人益惧。(《左传·昭公元年》)
(4)治邦者行此节,则乡之有德者益众,故曰:“修之邦,其德乃丰。”(《韩非子·解老》)
“弥”表比较程度副词应是由其“满、普遍”的意义发展而来的,“满”与“普遍”皆含有程度深之义,置于形容词前便虚化为副词,表示程度的加深。例如:
(5)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论语·子罕》)
(6)王者之封建也,弥近弥大,弥远弥小。(《吕氏春秋·听言》)
“滋”,本义是滋生、生长。《说文·木部》:“滋,益也。”引申有增益之义。增益的结果一定程度上是对原来情况或事物的超越,可造成程度上的加深,后虚化为比较程度副词。例如:
(7)邾子望见之,怒。阍曰:夷射姑旋焉。命执之,弗得,滋怒。(《左传·定公三年》)
(8)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史记·周本纪》)
“加”,《说文·口部》“语相增加也”。“加”由本义虚夸引申有增加之义。程度副词“加”是由表示增加意义的“加”虚化而来的。例如:
(9)小邾穆公来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实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犹惧其贰,又卑一睦,焉逆群好也。其如旧而加敬焉。(《左传·昭公三年》)
(10)易王母,文侯夫人也,与苏秦私通。燕王知之,而事之加厚。(《史记·苏秦列传》)
“更”,《说文·攴部》“改也”。改变这一动作造成结果与原有情况不同,程度的变化(加深或减轻)就是改变的结果之一,程度副词“更”就是从其改变义发展而来的。例如:
(11)修士不能以货赂事人,恃其精洁而更不能以枉法为治。(《韩非子·孤愤》)
(12)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
“倍”有增加、增多的意义,放在形容词或动词之前时,表示动作行为或事物特征在原有程度上有所增多,便虚化为程度副词“倍”。例如:
(13)元帝嗟叹,以此倍敬重焉。(《汉书·外戚传》)
(14)向大母拜,恭敬孝顺,倍胜于常。(《杂宝藏经·卷十》)
“转”,由转变的意思逐渐虚化为表示更加意义的程度副词。清刘淇《助字辨略》卷三:“转,犹浸也。”例如:
(15)由是琬遂还住涪。疾转增剧,至九年卒,谥曰恭。(《三国志·蒋琬传》)
(16)桓公伏甲设馔,广延朝士,因此欲诛谢安、王坦之。王甚遽,问谢曰:“当作何计?”谢神意不变,谓文度曰:“晋阼存亡,在此一行。”相与俱前。王之恐状,转见于色。谢之宽容,愈表于貌。(《世说新语·雅量》)
“越”,本义是跨过、度过。《说文·走部》:“越,度也。”“越”由跨过、度过的意义引申有超越、胜过之义。当“越”置于动词或形容词之前,在句中充当状语时,超过、胜过义的“越”便语法化成了表示比较的程度副词“越”。例如:
(17)若小者分明,大者越分明。(《朱子语类·卷六十四》)
(18)而今诸公看文字,如一个船阁在浅水上,转动未得,无那活水泛将去,更将外面事物搭载放上面,越见动不得。(《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一》)
以上所列举的9 个程度副词,只有“弥”是由形容词语法化而来,其余皆是由动词语法化而来。副词“愈(逾)”“越”来源于表示超过、胜过意义的动词,副词“益”“滋”“加”“倍”来源于表示增长、增加意义的动词,副词“更”“转”来源于表示改变、变化意义的动词,这些所自来的动词有一个相同的核心语义特征,那就是[+使原有事物发生变化],这一核心语义特征不是词的本义,也不是词的主要意义和常用意义,而是从本义中抽取概括出来的,贯穿于所有相关义项的核心部分。这个核心语义特征会保留在所有的与之有引申的关系的实词中,也会保留在由它虚化而成的虚词中。副词的语义相对于实词而言比较“虚”,但相对于介词等其他虚词而言又比较“实”,比较类程度副词表示动作行为、事物特征及数量程度加深的意义,其核心语义特征也是[+使原有事物发生变化],它们与所自来的动词具有共同的语义特征。由此可知,“愈”“益”“滋”等词语所具有的共同语义特征是使它们能够递相类聚到比较类程度副词这一词类范畴的原因,同时也是后来比较类程度副词之所以能够递嬗更替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三、汉语史中比较类程度副词历时更替的原因
张家合(2010)认为:“造成‘越发’衰落的主要原因是‘更’在近代时期的发展极其迅猛,成为表达更加义最常用的程度副词,使用频率远远高于其它更加义程度副词。因此,‘越发’等其它表示更加义程度副词的使用必然会受到‘更’的挤压。在这种大环境下,‘越发’的使用频率定会受到影响。”[2]我们认为,这只是描述出了近代汉语时期比较类程度副词的竞争演变情况,并非揭示出了这类副词更替的内在原因,即副词“更”为什么会取代别的副词,而别的同类副词为什么会被取代?
(一)比较类程度副词的历时更替与它们自身语法化的程度有关 汉语史中的比较类程度副词绝大部分是从动词语法化而来的,语法化的路径大体相似,都是由动词作谓语,到可以置于谓词之前作状语,随着句法功能扩大,修饰限制的成分越来越丰富,然后逐步虚化为程度副词。我们以“更”为例,来描述其语法化的过程及发展。
“更”本为动词,表示更改、改变的意思。由改变之义引申有替代、交替等意义。“更”的这两个意义在上古汉语中常见。“更”在句中主要是作谓语,带体词性宾语。如:
(19)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论语·子张》)
(20)若使中山之王与齐王闻五尽而更之,则必不忘矣。(《吕氏春秋·先识》)
(21)祭不用牺牲,用圭璧更幣。(《淮南子·时则》)
例(19)何晏注:“更,改也。”例(20)高诱注:“更,犹革也。”例(21)郑玄注:“更,代也。以圭璧皮幣代牺牲也。”
“更”也用在动词之前,例如:
(22)国更立法以典民。(《管子·任法》)
(23)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为主,大王更为臣也。(《战国策·秦策一》)
(24)自中丁以来,废適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史记·殷本纪》)
例(22)尹知章注:“更,改也。”例(23)(24)“更”也是改变的意思。“更”句法位置的变化为其发展为副词提供了前提条件。
“更”用在动词之前,有的文献用例可做两种解释。例如:
(25)虞不腊矣,在此行矣,晋不更举兵矣。(《左传·僖公五年》)
(26)与之,即无地以给之;不与,则弃前功,而后更受其祸。(《战国策·韩策一》)
(27)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史记·货殖列传》)
例(25)-(27)中的“更”可看作动词,也可看作副词。例(25)既可以解释作“更换”,又可解释作再、又;例(26)(27)既可以解释为改变、变作,也可以解释为更加。从语义引申的序列来看,表示又、再意义的副词“更”是从更换、轮流意义的动词“更”发展来的,表示比较的程度副词是从改变意义的动词“更”发展而来的。由于“更”所处的句法位置和语义的相宜性,使得“更”可以做两种解释。这是语言中的一种“临界”状态,即同一种语言现象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作不同的解释,在语言演变中,这正是词汇、语法变化的关键。这种“临界”状态为语言演变提供了一个契机,也为重新分析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在《史记》中,“更”副词用法的用例已较多见,但多是表又、再意义的副词,表更加意义的副词很少。例如:
(28)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史记·五帝本纪》)
(29)郦生曰:“举大事不细谨,盛德不辞让。而公不为若更言。”(《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30)佗封赐皆倍军法,其他故爵邑者,更益勿因。(《史记·吴王濞列传》)
例(28)(29)都是表再、又意义的副词,例(30)“更”“益”同义连用,“更”为表更加意义的副词。从文献用例来判断,表又、再意义的副词“更”,其形成时间要早于表示更加意义的副词“更”。虽然它们语法化的语义基础不同,一个是更替意义,一个是改变意义,但是它们所处的句法位置是相同的,又、再意义的副词“更”在一定程度上对更加意义的副词“更”的形成起了一定的带动作用,或者说是促成作用。
中古时期,“更”句法环境有所扩大,不仅可以用在动词前作状语,还可以修饰、限制形容词,还可以放在动宾短语之前。例如:
(31)王朗每以识度推华歆。歆蜡日,尝集子侄燕饮,王亦学之。有人向张华说此事,张曰:“王之学华,皆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远。”(《世说新语·德行》)
(32)王长史与刘真长别后相见,王谓刘曰:“卿更长进。”答曰:“此若天之自高耳。”(《世说新语·言语》)
(33)自步阐之后,益更损耗。(《三国志·陆逊传》)
(34)猴王知之,怆然而曰:“吾为众长,祸福所由。贪果济命,而更误众。”(《六度集经·卷六》)
例(32)刘淇《助字辨略》“更,犹益也、愈也。”词条引用此例。值得注意的是,“更”置于形容词并不一定是副词,置于“愈”等副词前也不一定副词。如《论衡·道虚》:“服食良药,身气复故,非本气少身重,得药而乃气长身更轻也,禀受之时,本自有之矣。”从上下文来看,其中“更”显然是动词,表示改变之义。又如《三国志·周宣传》:“帝复问曰:吾梦摩钱问,欲令灭而更愈明,此何渭邪?”其中“更”也是动词,表示变化之义。
近代汉语时期,“更”搭配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了,除沿用前代用法之外,还可以用在动补、状中、主谓等谓词性短语前做状语,还出现了“更……更”的格式,还与同义副词形成组合式“更加”。例如:
(35)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李煜·清平乐》)
(36)今晨太子散烦,愁忧更加转极。(《敦煌变文集新书·卷三》)
(37)这杀场上是那个孩儿?这车车里是谁家上祖?这个更藉不得儿孙,这个更救不得父母!(《元刊杂剧三十种·冤报冤赵氏孤儿杂剧》)
(38)女子见了光景,便道:“此处无人知觉,尽可偷住,与郎君欢乐,不必到吾家去了。吾家里有人,反更不便。”(《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九》)
(39)那驸马更不心慌,把月牙铲架住铁棒,就在那乱石山头,这一场真个好杀。(《西游记·第六十三回》)
(40)因又吩咐公子道:“至于你身受你祖岳、岳父的栽培,从此更当益加感奋,勉图上进;却不可仗着这番鬼神之德,稍存一分懈怠。”(《儿女英雄传·第三十六回》)
以上描述了“更”语法化的过程:语义上逐渐虚化、句法环境逐步扩大。此外,副词“更”在语法化的过程中,还通过语音的变化与动词“更”区别开来。副词“更”与动词“更”的词形(字)相同,但读音不同。“更”在《广韵》中有两读:古衡切与古孟切,声、韵相同,声调不同,平声为动词,去声为副词。而其他表比较的程度副词与其所自来的动词读音与词形都相同,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更”语法化的程度较高。
汉语史中“更”类程度副词的语法化路径大致相同,但是,它们语法化的程度却不同。石毓智(2011):“从一个普通词汇到一个语法标记的发展过程是渐进的,其过程为一个连续统,即语法化是一个程度问题。根据Hopper&Trangott(1933:97-103),判断一个词的语法化程度的高低,可以是(一)语义上的虚化、(二)可出现句法环境的扩大和(三)在新语法结构中使用频率的增加。”[3]
在汉语史中,“加”“转”“滋”“弥”“倍”这五个副词,产生之后,仅仅被使用一段时间后,就先后退出了该类副词范畴,究其原因,这与“加”“转”“滋”等副词语法化的程度不高有关。我们这里主要以使用频率来说明它们的语法化程度。如上古汉语时期的副词“加”,它由表示增加、增多意义的动词“加”语法化而来,但是“加”在上古时期更多用作动词,用作副词的用例很少。《左传》中“加”共见69 次,用作副词 2 次,约占总数的 2.8%;《荀子》中“加”见38 次,用作副词4 次,占总数的10.5%,《史记》中“加”共见96 次,用作副词6 次,约占总数6.2%,虽然在发展过程中副词所占比例有所增高,但总体来说还是很低,这说明“加”的语法化程度不高。再如“转”的副词用法所占的比例,《世说新语》中“转”共见28 次,用作副词2 次,占总数的7%;《封氏闻见记》中“转”共见12 次,用为副词3 次,占总数的25%,《朱子语类》中“转”共见402 次,用作副词17 次,占总数的4%,这些数据也说明“转”的语法化程度不高。相对而言,“更”“越”的语法化程度就比较高,在现代汉语中已经发展为纯粹的程度副词,动词“更”与副词“更”不仅读音不同,而且动词“更”不单独使用,只用作构词语素,副词“越”与动词“越”读音虽相同,但动词“越”也是只用作构词语素,不再单用。副词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功能词,语言中常用功能词的语法化程度都较高,如常用介词“把”,常用连词“而”等。所以,“加”“转”“滋”“弥”“倍”等副词之所以先后被替代,是因为它们的语法化程度不高。
(二)比较类程度副词历时更替受到了遵循“语音象似性”倾向的影响 汉语比较类程度副词遵循“语音象似性”规律的倾向是它们发生历时更替的另一动因。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在不同程度上遵循着象似性原则。所谓象似性,就是指语言形式与所指意义之间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其中语言形式包含有语音、词汇和语法形式。语言里每个层面都有象似性成分,如语音层面、语法层面等。语音象似性,国际上通常称为语音的象征性或者音义联觉,指某种语言形式与某些意义相关联,如元音[i]往往象征小,如teeny(极小的)、weeny(极小的)等。汉语中不仅拟声词具有语音象似性,如“叮咚”“砰”等,一些名词、动词也表现出语音象似性,如名词“鸦”是模拟乌鸦的叫声,“崩”是模拟山崩的声音,“咬”模拟咬齿动作口腔张大的形态特征。汉语中的一些虚词也具有语音象似性,如表示比较的程度副词。
汉语史中表示比较的程度副词,它们在中古时期各自的声调分别为:“弥”“滋”“加”为平声,“愈”“倍”“转”为上声,“更”为去声,“益”“越”为入声。进一步根据声调的升降曲折和高低变化来归类,“弥”“滋”“加”为一类,“愈”“倍”“转”“更”“益”“越”为一类,前一类音高是平直的,没有变化,后一类音高是高低起伏的,有变化。汉语史各个历史时期表示比较的程度副词中,使用频率高、占主导地位的词语往往是有音高变化的词语。汉语词语的语音形式表现为音节,完整的音节包括声、韵、调三部分,语音象似不一定是语音形式的各部分都要与意义有对应关系,有时仅仅是其中一部分与所表意义发生关系,或声,或韵,或调。王珏(2014)论证了现代汉语声调与词类范畴之间的象似关系,指出汉语中存在有同一语义或语法范畴的词同属于一个调类的情况。[4]汉语史中比较类程度副词的语音形式中音高的变化正好与意义方面程度变化的表达相对应,具有一致性。程度是人类对事物性状等的一种认知方式,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认知范畴。不同事物的性状、动作行为具有程度方面的差异,人们对事物的具体感知因时间、空间、主观感受度的不同也具有程度差异,这些程度差异必然要通过语言表达出来。表达程度差异的语言形式有许多,当采用程度副词来表达时,往往倾向于选用有音高变化的词语,这些词语的发音形式与程度加深、突出变化的意义之间具有很高的象似性。所以,“弥”“加”在与“愈”“益”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滋”在与“更”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后来“弥”“加”“滋”逐渐被更加符合语音象似性原则的“愈”“更”所替代。
(三)比较类程度副词的历时更替是语言系统自我更新与调整的结果 “愈”“弥”“益”等词语先后类聚到同一副词范畴之后,它们并非共存于语言中,而是在汉语史中发生了历史兴替。语言系统的自我调整是该类程度发生递嬗更替的动因之一。汪维辉(2000)指出:“一个词用久了以后,常常会被一个新的同义词所取代,许多词看来是这样的。这也许跟语言使用者的喜新厌旧心理有关。”[5]这种解释有一定的道理,但这是语言发展的外部原因,而更应该从语言内部来解释。张海媚(2015)进一步指出:“语言的演变如同生物进化,存在着一种自我更新的机制。”[6]“愈”是上古汉语比较类程度副词的核心成员,也是同类副词中产生最早的成员,而且“愈”在上古时期主要用作程度副词,以致于我们难以去描写其逐步虚化的轨迹。这一古老的副词,在与后来新产生的副词“益”的竞争过程中,逐渐处于劣势,而“益”曾一度发展成为比较类程度副词的主要成员。后来,“益”也逐渐衰落,在明清时期,又被新兴副词“更”“越”等所替代。在语言发展演变的过程中,词汇的变化常表现为新成员的加入与旧成员的退出,这应是语言自我更新机制起作用的结果。
同时,“愈”“益”等副词发生递嬗更替是受到了语言经济原则的制约。张家合(2013)认为:“更加类副词在程度磨损和求新求异的共同作用下不断发展变化。程度磨损指一些程度副词在使用过程中,程度义不断减弱的现象。同时,在语言经济原则的作用下,旧有成员也在不断消亡。”[7]关于求新求异的因素,上文已经讨论过。对于程度磨损的因素,我们认为这并没有解释比较类程度副词更替的原因,例如产生于上古汉语末期的程度副词“更”,经历了中古时期的发展,到近代汉语时期成为了比较类程度副词的核心成员,一直沿用到现在。“更”的使用时间很长,如果说存在程度磨损的话,其程度磨损较为厉害,应该是被其他产生时间比它晚的程度副词替代。但事实并非如此,在“更”之后产生的程度副词“倍”“转”“越”,并没有成功替代“更”,在与“更”的竞争中反倒是逐渐衰落或形成新的分布。我们赞同他提到的语言经济原则的影响与制约,但是他并没有指出语言经济原则之所以会对这类副词的历时更替起作用的前提条件。语言经济原则起作用的前提条件是一组词语意义、功能相同,如同异体字一样,是语言的一种冗余现象,在发展演变过程中,有的会被逐渐淘汰不用。汉语史中比较类程度副词的语义相同,都具有[+使原有事物发生变化]核心语义特征,且具有相同的功能,都是在句中作状语,用以修饰限制动词或形容词,表示比较的程度;都有相同的对举格式,如“愈……愈”“益……益”“弥……弥”“更……更”“越……越”等等,或者表示两项有因果关系的事各自的程度成比例地变化,或表示两种及两种以上行为或状态在原有程度上都有所增多。语言中出现了语义相同、功能相同的一组副词,受语言经济原则的制约,势必会促使这些相同成员进一步演变发展。[8]演变的结果有二:一是在演变过程中发生更替,如中古时期“益”“更”替代“滋”“加”,近代汉语时期“更”“越”替代“愈”“益”。二是在发展过程中各自产生了不同的用法,形成了不同的分布。如“更”与“越”,在明清时期,“更”常常单独用于动词、形容词前作状语,而“越”常常用于“越……越”格式中,构成框式副词,表示倚变。
四、结语
语言内部要素的演变既有外在的原因,也有内在的原因。外在的原因只是起一定的推动作用,真正促使演变的一定是语言内部的原因。语言使用者喜新厌旧、求新求异的心理是汉语史中比较类程度副词历时更替的外在原因,而语法化的程度、语音象似性倾向、语言系统的自我更新与调整是比较类程度副词历时更替的内在原因。当然,任何事物的发展演变都不是一种因素起作用的结果,是多种因素共同影响、作用下的结果。语言的演变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