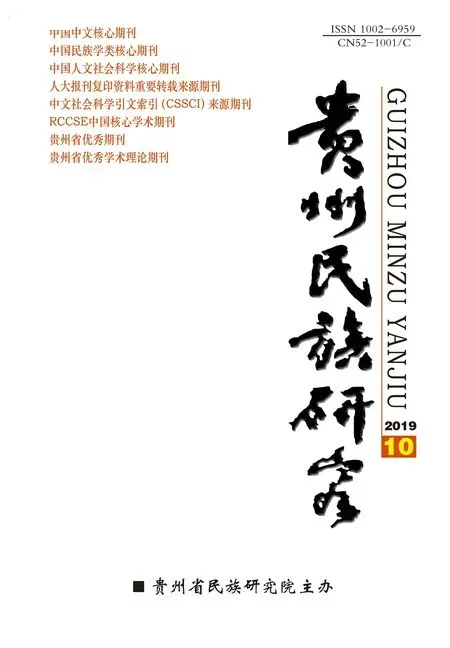对当代少数民族舞蹈创作的审思
2019-02-09马亮亮格日南加
张 帆 马亮亮 格日南加
(1.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音乐舞蹈学院,承德·河北 067000;2.中央民族大学 舞蹈学院,北京 100081)
一、当我们谈论舞蹈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从艺术语言本体论出发,舞蹈相比于文学、电影、戏剧,似乎具有优于抒情,拙于叙事的特征,另一种看法则是舞蹈长于抒情,能于叙事,囿于说理。文学本身所依赖的文字符号拥有无与伦比的深刻性,众多艺术形态簇拥着作为一门综合艺术的电影的身边,戏剧这一古老的形式拥有广泛的受众基础,正如文学拥有艺术的深度,电影拥有艺术的强度,戏剧拥有了艺术的广度,而舞蹈却似乎一个度也不占有。与其相反的是,慕羽教授视“舞蹈身体语言的多义性、不确定性和隐喻色彩”为舞蹈的一种特点而不是缺点,她指出了“观众主动去寻求心理、心智上的接触,去体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境界。”[1]任何舞蹈的残影都能被其富于象征性的母题收于囊中,并像水面上的涟漪那般拖曳在身后。事实上,我们也能从苏珊·朗格那里找到此类看法的源头,她曾经指出“舞蹈中的情感与姿势是虚幻的”[2],在此基础上,拉康认为能指永远无法找到所指,正因为不具备任何锚定,它能找到的仅是一个又一个构成链的虚所指(拉康实践性地批判了索绪尔的观点),不过我们要指出两者之间的区别是舞蹈总是伴有审美意识而存在,因此舞蹈将自身的能指投射成一个横向切面上的所指光谱,拉康所说的无意识中的线型的能指链,在这里却成为了一种伞状花序状的模式。罗兰·巴特很久以前就意识到读者与“可读性文本”和“可写性文本”两者之间不同的关系,在后一种文本之中,所谓的锚定能力反而成为一个人审美趣味的体现,因为正是这种能指的不确定性,使得它的所指具有了丰富的内涵和联想,而这些内涵不需要在雅各布森的“语义场”中借助拆分和对立获得,从而给“虚像”开放式的解读提供了可能性。为此,列维·斯特劳斯提出了“空洞的能指”这一概念,他通过对“MANA”(构成魔法的物质)这个英文单词进行词源性分析后,得出它的指称具有浮动性的特点[3],因为舞蹈演员的动作本身并不具有任何实际的意义和具体的指向。
少数民族舞蹈的编舞者多会持有较为保守的第一种观念的倾向,即默认上述舞蹈的某些特征是由其先天性不足造成,因此他们将自己脑海中的缪斯囚禁在一个精致的笼子里,小心翼翼创作出一部又一部作品,却只是用来反映民族的某种风俗、某幅场景、某个节日。这使得少数民族舞蹈更多地变成了一种展示手段,而非一种表现手段,它在表现手段上的缺位让它还处在前现代主义阶段。当这样的舞蹈作为少数民族舞蹈创作最为讨巧的一种表达后,多数编舞者们便蜂拥而至地挤进同一个阵营了,如此创作的“好处”是只需“拿来”素材,制造一个“宏大”的主题,并冠以编舞技法的整合,一盘“好看”的“佳肴”便诞生了。通常情况下,这类舞蹈在作品立意、音乐结构、队形调度上表现出了惊人的步调一致,最终导致的却是作品的单调重复和形式的固化。展现出来的不过是由服饰、动作、演员、舞台背景和灯光组成的这种拉伯雷式的大杂烩,一具没有灵魂的躯体而已。
具体到单个少数民族舞蹈来说,我们会发现,许多少数民族舞蹈形式都依附于这样一个母题之下,比如“毛古斯”是一种追求与神灵之间对话的、带有萨满意味的祭祀舞蹈,“锅庄”则主要是反映人们庆祝丰收和各种农事活动的舞蹈。我们已经看到事物原本规矩的外延已经伸到“毛古斯”和“锅庄”两个词语的内涵之中。编舞者用这些舞蹈去表现少数民族已有的传统仪式与习俗同时,无法赋予作品新的意义(更确切地说,是无法塑造一个可以施加意义的空间),究其原因,恐怕仍要归咎于编舞者们创新不足,固步自封,也就是说,我们很少将舞蹈置身于比如哲学和美学这些更加深刻的层面中去思考,缺乏试图在新的语境中去重新解构少数民族舞蹈内核的勇气,从而造成了少数民族舞蹈创作目前的困境。
二、不能承受舞蹈语素之轻
如果我们将舞蹈动作看成语言学里的音位,调度就属于符号层面的概念(调度在独舞中表现为位置),透过这种陌生的视角去看待舞蹈。和音位、语素、词语和句子一样逐级搭建出整个语言世界,动作和调动的组合也构成了舞蹈。从更加广泛的意义上说,调度也具备语素的特征。
经过两次彻底的革命———第一次是玛莎·格雷姆,第二次是默斯·坎宁汉,前者眼中的范式在后者那里也不存在了,一切舞蹈都是即兴和偶发的——现代舞崇尚身体的自由和不受限,他们追求绝对意义上的“可舞性”[4],似乎将一切都纳入自己的体系,因此也就不存在舞蹈语素的问题。从这个层面上说,我们要将少数民族舞蹈划于中国古典舞和芭蕾舞所处的那个向度,它们代表舞蹈的传统势力。我们的少数民族舞蹈多数已进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行列,这决定了它的形式和语言会相对固定。少数民族舞蹈此时面临和中国古典舞一样的困境,尽管少数民族舞蹈与古典舞有着不同的侧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古典舞是一种重现与恢复,是将目光投向画像砖、壁画、乐舞俑、舞谱、文献资料,要求编舞者回到历史中去,而少数民族舞蹈,更多的是一种展现与探索,是将注意力集中横向世界中一切,即现实世界中仍然具有生命力的各种民俗、文化、人物。两者之间的关系让人想起语言学里共时性与历时性。
因此,对各个民族的舞蹈元素体系的建立,不仅有助于研究者对少数民族舞蹈的根源性认识,也有助于为舞蹈编创者提供规范性的把握。需要补充的是,我们赞成将舞蹈动作纯化为相对固定的语素,并非与前文中所阐述的舞蹈可作开放性解读相矛盾,就像文字作为象征符号,仍然能用来创作诗歌和撰写枯燥的说明书一样,两者之间并行不悖。另一点要补充的是:这种中国少数民族舞蹈语素的恢复和保护是介于巴拉塔舞和舞蹈之间,前者作为印度古典舞,从摩羯陀国一直延续至今,后者则完全是当代日本舞者创作出来的一种全新的舞蹈,它和日本传统的歌舞伎和净琉璃之间的联系只存在《菊与刀》里所深刻描述的那种病态的美学。中国少数民族舞蹈既不是原生态,也不是衍生态,我们觉得它更接近于再生态这个维度。就像前文所说的那样,除了动作以外,调度是舞蹈中最重要的元素。所有舞蹈演员通过构建的整体变成了一个有机身躯的部分,通过聚散或变形的调动解构了它们自己。我们可以把调度看成是另一种舞蹈姿态,是依附于群体、并由群体展示其作为统一体的变形,有时,它在舞蹈创作者的脑海里就像是一只不停抖动触手的八爪鱼。动作与调度共同构成了所谓的语素。
三、舞蹈创作的局外人
一位编舞者,即使自身的涵养学识足够,如果他想创作出一部了不起的少数民族舞蹈,也需要将自己的目光投向他所准备创作的这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中去,甚至将自己想象成贝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说的“被想象成一个共同体的民族”中的一员[5]。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源泉,旅行似地到少数民族地区,浅尝辄止,走马观花,不应是一个严肃的艺术工作者对艺术所持有的态度。因为一位编舞者既没有创作他身处的那个民族的舞蹈,又缺乏其他民族地区生活的经历,仅仅依靠短期田野调查是不够的。而更糟糕的一种情况是:他们或许进行了一次准备充分的田野考察,有各种现代器材傍身,有当地向导陪伴,甚至用好奇的目光欣赏所见的一切,可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既不善于对民族元素的观察提取,收集相关资料,也不真正重视与当地民俗艺人的交流,他们将自己置身于游览者的位置,试图以窥见的某个细节去描摹整个民族的面貌,偶有所得便以为如获至宝,接着就带着这种一知半解或误解,返回自己的舞蹈室里。
我们姑且不说田野调查有一整套体系,从参与观察,经过动态学习,再到绘图记录,最后提炼出舞蹈语素。从民族舞蹈创作“同质化”等现象上可以发现,作为田野调查者的我们与被我们调查的对象(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和民间艺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而尴尬关系,究其原因是我们极少赋予他们健全的人格特征,即使在与他们交流时,也大多采取一种单向方式,未能视他们为平等的主体,而是把他们当作一种纯粹客体。这也是许多西方人类学家身上的通病,如果我们丧失了人文关怀,那么我们的精神和肉体,就与那些糟糕的人类学家一样走向了不同的目的地。
中国的每个少数民族都拥有自身丰富的历史文化和风俗,几乎不需要深入理解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理论,就能明白即使这些民族应对相同的外部因素,其现实生活中也必然呈现出多姿多彩的特点。少数民族舞蹈以其鲜明的民族风格和传统特色而闻名于世,与民族音乐、民族戏剧等艺术形式并存,但在那些未有自己文字的民族里尤其占有重要的位置。同样,对于众多面临消亡的少数民族文化,许多民间艺人的主体意识还未完全觉醒,学院派的编舞者又不具备少数民族文化、生活、精神记忆,因此我们只有通过自身努力将少数民族客体与自身审美经验主体结合起来,再付诸于舞蹈这一形式,并将哲学思考隐藏其中,揭示人在少数民族之中的处境。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要警惕自己不要变成加缪笔下荒唐意味十足的局外人或者俄罗斯文学中反复出现的“多余人”的形象。
四、小径分岔的舞蹈题材
舞蹈作品题材的分类纷纭繁杂,很难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去定义,除了情绪性题材舞蹈以外,还有现实题材、历史题材、神话题材等诸多题材,现实题材的创作相比历史题材(拥有与神话题材相似的内核)的创作更加困难,实际上,即便现实主义题材内部———按照刘建教授的说法——也分为宏大叙事和私人叙事两种类型[6],这三种题材依附典型人物形象和经典故事情节的比例不同,在历史题材中,由于观众们对这些舞台形象到了耳熟能详的地步,因此编舞者几乎不用过多关注舞蹈以外的任何故事构架方面的问题,比如说舞蹈《济公》,我们知道那将是一个喜剧故事,主人公最后不会孤独地死去,而是像千菊丸那样睡去;而舞蹈《孔乙己》呢?我们知道那将是一个悲剧故事,主人公最后会像济公那样睡去,但实际上他是孤独地死去。在宏大叙事题材中(它似乎是介于历史题材和私人叙事题材之间一个过渡性的产物),编舞者也可以借助业已发生的事件来减轻某种困扰,将舞蹈置于背景之中,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是去年涌现出来的三部有关青藏铁路的舞剧——《天路》《雪域天路》和《天之路》,即使我们摘取舞剧中的某个章节,改编成为一部独立的舞蹈作品也无需怀有过多的担心。但是私人叙事则与前两者不同,它几乎不享有前两者的优势,编舞者用自身思维的钉子和榫卯,去用从民族舞那里借来的建筑材料和装饰材料来构建整部舞蹈的地基,如果稍有不慎,那么他建立起来的不过就是一幢像是特列安农瓷屋那样四不像的建筑了。
借助中国艺术史的概念,我们既可以把少数民族舞蹈现实主义题材的时间追溯到1949年,也能将它的上限框定在20世纪70年代。但其划分标准的差异却并未从根本上影响人们对于现实题材的定义,关于现实题材的定义随着时代的洪流前进而不断被刷新,因为每个人也无法两次踏进这条历史长河里。从艺术史来说,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相对立,从文艺理论上说,现实主义又与浪漫主义处于艺术谱系遥远的两极,但是从创作来说,毫无疑问,“现代性”又是一切现实主义题材的首要标志,现实主义题材所要反映的世界恰恰又是后现代主义理论占据至高点的时期。
无论如何,现实题材的现实就是一个具有特殊含义的词汇,从来不是简单地指向一个时间范围、一种表现内容,更不是仅仅指向艺术的表现对象,而是一个具有语境背景的概念,是一种创作上的要求,是一种明确的创作导向。在少数民族舞蹈现实题材这个领域里,如果现实题材脱离了少数民族舞蹈这个载体,那么将会造成舞蹈本身特征不明的印象。反过来,如果空有少数民族舞蹈的表象,而这个现实题材并非是与少数民族时代精神紧密联系的现实,并且也会走向一条完全失控的道路上。编舞者将少数民族舞蹈作为表现自己内心世界的一种形式,只是在整部个人化的舞蹈作品中加入了少数民族舞蹈的元素,这些以现代技法为实,披上了少数民族外衣形式的舞蹈无法反映真实的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布洛克说:“通过把内在的再现性内容和表现内容包括起来,形式同艺术品之各种要素组成的整体关系便成为一回事。”[7]因此,将现实主义与少数民族舞蹈相结合,在舞台上同时客观地再现少数民族的民俗景观和时代精神便是我们每个少数民族舞蹈编舞者的天然追求了。这互为一体不可分割的概念成为了编舞者重要的创作来源,也体现出他们对于不同地域民众当代集体精神的强烈观照,同时也反映出处于变革期的当代舞蹈作品中的审美嬗变痕迹。
五、结语
编舞者在进行少数民族舞蹈创作时,如何将民族从国家这个背景中抽离出来,使得其在固守传统与时代发展这一对矛盾体里得以发展,从而进入场域之中,完成不可避免的雅化和个人化的创作过程,是每个编舞者面临的共同诘问。此外,少数民族舞蹈创作理论的建立和完善,也离不开学者们从哲学和美学等更高的层次上深入探讨、研究和解放思想。在这一过程中,舞蹈创作实践和舞蹈创作理论势必将相互促进,从而使整个少数民族舞蹈创作进入一个螺旋向上的循环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