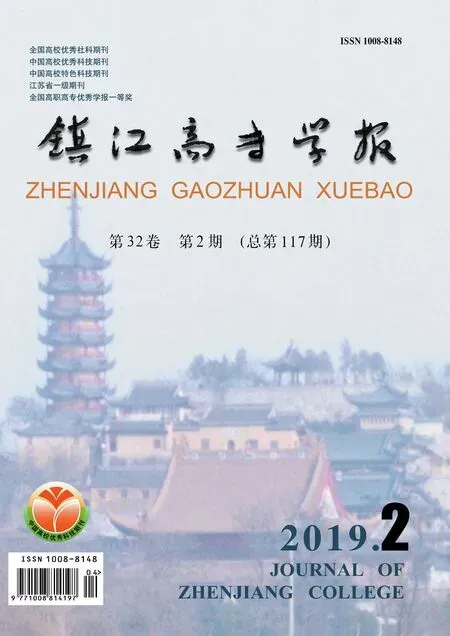精神分析批评视野下的《活动变人形》研究
2019-01-31廖应莉严运桂
廖应莉,严运桂
(1. 温州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温州 325000; 2. 长江大学 文学院,湖北 荆州 434023)
《活动变人形》的创作与王蒙自身经历密切相关,小说中的人物在《王蒙自传》中都可以找到相应的人物原型。特殊的家庭背景及其早年间生活经历的影响、从小广泛阅读的大量优秀中外文学作品的熏陶,使得王蒙对人性有一种敏锐的洞察力。王蒙以个性化的表达方式,对自己的人生进行了一次认真的审视。在某种程度上说,这部小说是王蒙生活的投影,是王蒙基于其现实生活所撰写的一部自叙传。透过知识分子在20世纪80年代对自己苦难人生的书写,我们可以体验到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痛楚。
1 倪吾诚:王蒙之“父”——西方文化孕育的畸形儿
1.1 弑父情结
“弑父情结”体现了子辈对父辈权威的一种反抗。在《活动变人形》中,王蒙以独到的视角和笔触刻画了一位自私、自负、冷酷的父亲形象,字里行间透露出父子间的格格不入以及子辈对父辈的不满甚至仇视的情愫。
倪吾诚旅欧两年,接受的是西方现代文化教育。西方文化教人独立、自强,强调人的自由、尊严,但是这并没有让倪吾诚变得更加精明睿智,反而让倪吾诚变得浮夸自私、外强中干。他将自己一厢情愿的想法施加在妻子和孩子身上。他要求妻子“文明”起来,学习洋人生活方式,他给儿子倪藻买洋玩具、喂儿子洋营养品,以欧洲人言谈举止的行为方式为基准,指出儿子在言辞上的失当以及诸多生活习惯上的错误。倪吾诚在这些生活表层的形式上下足了功夫,却无视妻子儿子内心的情感需求。这一切招致了儿子对他的厌恶,他曾用一长串词藻来尝试对父亲倪吾诚定性,“知识分子?骗子?疯子?傻子?好人?汉奸?老革命?堂吉诃德?极左派?极右派?民主派?寄生虫?被埋没者?窝囊废?老天真?孔乙己?阿Q?……”[1]253倪吾诚与儿子之间存在一道深深的鸿沟,鸿沟体现出父辈与子辈的断裂,这种断裂并非生理血缘上的断裂,而是文化上的断裂。倪藻近乎本能地排斥父亲,甚至在巷子口“站岗”“放哨”,像做贼一般监视倪吾诚的举动。
这部小说体现出现实生活中王蒙的“弑父情结”。在回忆这部小说的创作过程时,王蒙表示“很痛苦”,“这部长篇小说,可以说是我写得最痛苦的一部作品,有时候写起来要发疯了”[2]230。王蒙的父亲王锦第有着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留学经历,回国后担任高校校长。对于儿子王蒙的教育,王锦第不是做好孩子精神成长的引路人,而是如小说中的倪吾诚一样,只是将他所认为的现代文明生活方式教给儿子,如反复教育王蒙不得驼背,要求王蒙每天洗澡,要王蒙会优雅地吃西餐等。王蒙自小无法理解和接纳父亲,对父亲怀有一种仇视、隔阂的复杂情感。幼年的王蒙爱讲家乡话,还反复强调自己是沧州南皮人,这一动机的背后,是王蒙对父亲王锦第“崇洋媚外”的反叛,这一反叛正如同他笔下的倪藻对倪吾诚的抗拒,是作家潜意识中的“弑父情结”在小说中的体现。
1.2 自恋情结
弗洛伊德认为,力比多(Libido)是一种自我指向其性欲对象的能量。自恋源于力比多,这种原始的爱的力比多投向自己和养育自己的人,是一种原发性的自恋。随着个体的发展,这种能量投向客体,但如果由于某种因素的影响,这种朝外的爱的力比多返回个体,就会形成继发性的自恋,也就是病理性的自恋。这些人在爱的选择中,不以他人为模型,而以自我为模型,将理想化的自我作为爱的对象[3]347。
倪吾诚自留学回国后就有一种特殊的优越感,爱自我夸耀。他看不惯家人的行为举止,强迫妻子儿子执行他那一套文明礼节;他在经济窘迫的情况下还一味要维持他所谓的文明与体面……他在同周围人相处的过程中,全然以自我为中心,认为别人想法一定与自己一样。他摈弃中国传统文化,为人浮夸,好高骛远,志大才疏,却常常自我标榜为新时代知识分子,常常胸怀“大志”,年近花甲的时候,觉得自己人生的黄金时代还没开始。
由于这种“自恋情结”,倪吾诚对自身的关注要超过对任何人和事的关注。对家庭,他过于自我,只顾自己在外花钱享受,全然不顾家庭,他没有担起作为丈夫和父亲的责任,所以处理不好家庭关系;在家庭之外,他太关注自身,不懂得换位思考,所以他处理不好与同事、邻居等的人际关系。他太在意别人对他的看法,努力把自认为最好的形象示人,但即便以一副温文儒雅的形象同他人进行接触交流,他也不会把更多的关注点投注到别人身上。殊不知,健康的人际关系必须要建立在彼此尊重和信任的基础上,而他的“自恋”,直接或间接导致了自己与妻子、孩子乃至周围人的对立。他追求西式的文明富裕的生活,从这一主观愿望出发,一味地模仿西方人生活方式,却全然不去思考当下中国社会环境是否具有实现这种肤浅的生活方式的可能性,他求而不得,最终与整个社会格格不入,选择了以死亡的方式结束这种矛盾、迷茫与痛苦。
“自恋情结”使倪吾诚沉浸在不切实际的幻想中,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缺乏清醒的认识。正是这种错误认知导致了他的悲剧人生。
2 静珍:王蒙之“姨母”——封建文化桎梏下的悲剧女性
2.1 自虐——欲望的宣泄
在《活动变人形》中,静珍的原型是作者王蒙的姨母。在丈夫少华死后,静珍恪守封建伦理道德,为丈夫“守志”。妹夫倪吾诚劝其改嫁,她“没有接受、没有理睬、没有予以考虑,甚至连一刹那的犹豫或波动也没有”[1]111。在“守志”中压抑着所有的本能欲望,因为找不到生活的意义所在,静珍陷入了精神的荒原之中,常常感到孤独和空虚。“我今天做什么呢?在每个早晨,在她的生活道路上的每一天的开始时分,都有这样一个恼人的老问题横在面前,沉重如山,无边无天。我今天做什么呢?她永远回答不上来。她永远害怕回答这样的问题,她永远为这样的问题而痛苦,甚至是羞愧。”[1]166
欲望被压抑久了,人会处于一种非常态的状态。尽管她恪守封建伦理道德,但是这种泯灭人性的封建道德并不能完全禁锢一个人潜意识里的生命本能。弗洛伊德认为,潜意识在心理学上指的是一种无知无觉、全无意识的心理活动,是有机体对外界刺激的本能反应,这是一种潜伏在意识之下的精神实质,却往往能够支配人的整个思想和行动[3]83。意识只是水面之上的冰山一角,而潜意识则是隐藏在水面之下的巨大部分。潜意识是一种无意识,它代表人类最深处、最隐蔽、最原始、最本能的欲望,这欲望代表着“本我”的一面,会受到“自我”和“超我”的约束,但是仍然会寻找机会暴露出它的存在。被压抑的本能寻找突破口,表现在人物身上则是欲望的宣泄。静珍的欲望宣泄表现在她每天晨起时的梳洗打扮仪式上。“她一丝不苟地叠起了自己的被褥,神态严肃,好像即将出发去履行意义重大的使命。”“她一遍又一遍地洗脸。”“她开始梳妆。一天之中,只有在这个时候她感到一种神秘的力量在酝酿,在积累,在催促她,她感到一阵紧迫的心跳……”“大白脸扑完了,开始上胭脂和唇膏。”“她开始静静地梳理自己的头发。”[1]24她坚持这一套仪式十年如一日,这是她内心隐秘的无意识的表征,即本能欲望的表达。由于内心对传统伦理道德的认同,她没有越雷池一步。她决心“守志”,表现出“超我”的一面;女为悦己者容,她精心打扮自己,则是“本我”的一面。她徒劳地打扮,她反反复复地洗脸,她在梳妆过程中莫名其妙地自言自语和吐唾沫,她抽自己的嘴巴,她甚至让静宜在她失声痛哭之后给她一大耳光,这种种非常态的行为实质上都是一种自虐、一种寂寞的排遣、一种欲望的宣泄。处在封建伦理道德和个体生命本能冲突的矛盾中,她不得不以“自虐”的方式宣泄着生命的能量。
2.2 他虐——欲望的转移
中国传统女性形象有三种:淑女、荡妇、巫女。静珍虽恪守封建伦理道德,却一反传统女性温润贤淑的形象,成为当代文学史上的“巫女”的代表。“本我”被压抑导致她内心生出无限的哀苦,化作一种无名的邪火和仇怨,喷向周围的存在,演变成一种“他虐”。
在小说第二章中,猫的夜半求偶行为刺激了静珍敏感的神经,致使静珍的怨恨情绪如火山爆发,使她失去了心理平衡。静珍一出场,便拿着扫帚将一只叫春的虎皮花猫打得遍体鳞伤。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静珍的仇猫源于对“本我”浮现的恐惧。虎皮花猫的求偶行为无疑唤醒了守寡的静珍“本我”的一面,而她的欲望是永远也得不到满足的,这种不满足的心理需要通过转移矛盾才能够得到平衡,于是静珍便产生了他虐的行为,表现在心理上就是希望他人也遭遇不幸或者比自己更加不幸,表现在行为上就是把自己的不幸与痛苦转嫁于他者,无休止地伤害他者。小说中“她的扫帚疙瘩每一下都打在这魔鬼的猫的下腹部,打得猫遍体淋血”,这骇人场景表现的就是一种“他虐”,主人公通过这种“他虐”的行为,释放无处排遣的“力比多”。此外,静珍在与叔叔争夺家产时的行为虽说是出于自卫,但不免有些过激,带有一种非理性色彩,这种行为也透露出主人公“他虐”的倾向。第二十章中,在邻居“热乎”前来告知倪吾诚请律师要和静宜离婚一事时,静珍表现出一副气势汹汹的模样,将“热乎”打发离去后,静珍走向镜子,“看到了自己影像的无助、悲惨、绝望和残酷。她又‘哼’地冷笑一声。想算计我么,想让我进你的圈套连环计么,想剥我的皮,抽我的筋,喝我的血,吃我的肉么,你算瞎你的眼睛”[1]23。由此种种不难看出,自身命运的不济及生活的不幸已经泯灭了静珍内心的爱和善良,她内心充满了自卑和仇恨,人也变得丑陋不堪、自私麻木,她与周围的世界失去了平衡,一旦遇上一丁点儿的刺激,她就会出现大爆发的行为,在种种猜忌、谩骂、疯癫之中实现久被压抑的本能的变态发泄。弗洛伊德说:“人的性本能是生命的原动力,在人类生活中是异常活跃,像地下奔腾的岩浆,无时无刻不在奔腾、冲动、寻求着爆发。”[4]163静珍就像一座活火山,随时可能爆发。
传统伦理道德对静珍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在静珍的意识中,“守节”重于一切,这已经内化为她的道德信条。但她的潜意识就像冰山的底部,蕴藏的丰富能量会不断寻找时机宣泄,所以她时常呈现出疯癫和变态的一面,通过“他虐”消耗着生命能量。
2.3 寻求宁静——欲望的升华
前文分析了静珍通过“自虐”和“他虐”这种种非理性手段排遣和转嫁痛苦,以缓解内心的焦虑紧张,从而使心理达到平衡状态。这里的“寻求宁静”是指通过符合礼法的正当途径来使力比多得到升华,从而使生命的层次得以提升。
静珍的癫疯和迷狂并非完全陷入到不可控的程度。她虽觉得周围邻居想要算计她,但她的发泄行为仅仅停留在口头上的骂战,并没有演变成“一发不可收拾”的武力冲突,可见她的精神理性并未完全泯灭。她时常还会通过背诗、读书、与家人谈天、抽烟、饮酒等方式来打发痛苦无聊的时光。如小说第十一章中,晚饭后的闲暇时间,静珍会和母亲聊起家乡,她觉得北京总像是虚的,是人家的,而家乡虽无令她留恋的人和物,但提起家乡总觉得是实的,是她们的。故乡是一个人的生命之根,每个人或多或少会眷念自己的故乡,昔日的故乡在内心唤起一种美好的乡思情感,让静珍忘却眼前的痛苦。她甚至还记得水月庵,“水月庵似乎对静珍有某种吸引力”,“想起水月庵似乎能点缀一下她在北京的单调无聊的生活。想起水月庵也能使她觉得平静,好像得到一种安慰和休息。好像是在遥远的地方还有一个亲人,有一个老家,她还有另一块领地,她总可以最后栖息在那里”[1]106。水月庵乃佛门清静之地,丈夫已逝,水月庵似乎成了静珍寻求解脱的精神家园,偶尔想起这片圣洁之地,她便会感到稍许安慰。静珍的这些行为方式,少了许多火药味,多了一些理性的成分,其生命的境界得以提升,灵魂得以净化与超脱。
静珍也时常陷入对少华的幻念中。幻念是一种白日梦,弗洛伊德认为,梦是被压抑的欲望的满足。在梦中,静珍表露自己真实的欲望,她像母亲一样对少华充满了怜爱。她还梦到他活了过来,做了官,八抬大轿来接她,然而“醒来后泪水杀得脸生疼”。当明白这一切是梦,她开始默念唐诗、背诵“鼓儿词”等,还唱许多民歌小调。“那诗的内容词句也与娘儿俩眼下的心情无涉。但在这种常常反复进行的吟诵活动中,她们似乎寄托了自己的许多情感,单是那种摇头晃脑的姿势,抑扬顿挫的声调,恰到好处的韵脚,一唱三叹的拖腔和古色古香的气氛,就使她们得到了某种满足。”[1]112幻想是一种想象,在这种想象和憧憬中,静珍被深深压抑的欲望得到某种程度上的满足,其内在的生命欲望得以升华。
人都有归属和爱的需要,静珍也有爱与被爱的需求,但是生活并没有给她多少温暖,她只有通过自我调节,在苦涩的生活中寻求片刻的宁静,使世俗的生命欲望得以升华。其实她本可以挣脱封建枷锁,追求女性该有的幸福生活,但封建伦理道德对她的影响根深蒂固,从她19岁决心“守志”开始,便注定了她一生的悲剧。
3 中西文化碰撞所激起的一代人的精神创痛
《活动变人形》开篇将叙事时间定位在20世纪80年代,作者以成年倪藻的视角展开叙述,通过倪藻对往昔生活的回忆,将读者的视线引入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以现代的眼光重新审视父辈们的生活。
倪吾诚是留洋的知识分子,崇尚西方文化,但他无法摆脱传统文化的影响,其归国后在行动上碌碌无为,在精神上无比痛苦。“倪吾诚的性格悲剧和命运悲剧的根源是他始终徘徊于两种文化相互撞击的中间地带,同时受到来自不同方向的两股力量的牵引,摇摆不定,犹豫难决,并在这犹豫摇摆、困惑和迷茫中渐渐耗损了他的灵气、他的可贵的热情。”[5]277归国后,他想要通过革命去改变中国现状,但并没有付诸行动。他追求自由的爱情,也以失败告终……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以内省的方式来达到和谐状态,不支持通过向外的努力去改变现状,而倪吾诚一心追求新事物,崇尚物质层面的西化,这种难以调和的文化冲突不仅表现在个体身上,也表现在家庭成员之间。总体上看,小说中的倪吾诚代表了西方文化观念,静珍等三位女性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生活在同一屋檐下,两种文化呈现难以调和的冲突,给这个原本和睦的家庭带来无尽的争吵、猜忌、怨恨与冲突,使一个完整的家庭溃散。
小说中,处处可见由两种不同的文化观念的碰撞所激起的波澜。静珍19岁丧夫,深受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决心“守志”。受西方文明影响的倪吾诚建议静珍改嫁,静珍破口大骂。两种文化观念的碰撞,引起了一场家庭大战。倪吾诚不想待在家里,他在外面请杜慎行吃饭,对西方现代文明夸夸其谈,吃完饭后没有回家,又去了早晨刚去过的澡堂洗澡,进了当铺当了手表,去了药店买了鱼肝油,进了儿童玩具店买了“活动变人形”玩具,借钱买了“寒暑表”……这一系列延迟回家的行为是倪吾诚对中国封建式家庭环境的一种逃离,然而他终究要回到那个家,冲突终究难以避免。他进了胡同后,静珍帮着静宜对付他,静珍向他泼完绿豆汤,又拿起一个凳子向他冲过去……一场恶战爆发,闹得鸡犬不宁。倪吾诚和以静珍为代表的三位女性的对立与冲突,是不切实际的生活理想和赤裸裸的生活现实的冲突,是西方文明同中国传统封建伦理的对立,这种冲突对立直到倪吾诚离开人世才告终。
王蒙将自己大半生经历都写进了这部小说。小说中的倪藻审视父亲倪吾诚的一生,也是王蒙审视父亲王锦第的一生。王蒙父亲王锦第是被边缘化的知识分子形象,不论是在家庭中还是在社会上,他都没有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他自命不凡,自以为人格精神独立,实际上并未建立起自己的一套价值观,行动上也未能有丝毫建树,他不能在时代的洪流中站稳脚跟,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一个悲剧性存在。他的悲剧具有普遍性,是千千万万和他一样处在同样时代背景下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遭际。静珍和静宜两位女性分别对应着王蒙的二姨和母亲——封建文化桎梏下的悲剧女性,她们的人生苦难重重,生活的不幸导致了心理扭曲。对于这两位女性,王蒙有着知识分子特有的同情和悲悯,在小说的结局,静珍和静宜谋求了一份生计。鲁迅认为,生存是第一要义。她们首先在经济上摆脱了对男性的依附,实现了人格上的独立,逐渐成长为新时代独立自强的女性,实现了个人价值。其实,时代给予每个人相同的机遇和环境,无论是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以倪吾诚为代表的“现代知识分子”,还是以静珍为代表的传统女性,在时代变迁的大潮中,只有建立自己独立的价值体系,才能实现自我救赎。
《活动变人形》是作者的一部自叙传,建立在作者刻骨铭心的生活体验上。“对于倪吾诚在气节上的没有骨气,作者是鄙视的,对于倪吾诚在道德上的缺失,作者是愤恨的,对于倪吾诚在生活上的失意与落魄,作者是哀怜的”[6];对于被封建文化吞噬了灵与肉的静珍,作者是同情的。透过作者着力刻画的倪吾诚与静珍这两个主要人物,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内心巨大的伤痛,体会到在时代的巨变下,作者在成长过程中的那种撕心裂肺的痛感。《活动变人形》不仅是王蒙一个人的郁闷、矛盾、惆怅的精神体验,而是中国文化处于蜕变时期的一代人痛苦灵魂的写照。过去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成长的伤痛却成为王蒙一生中难以忘却和无法抹去的记忆。审视过去是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王蒙在新时期重新审视自己的过去,敢于直面自己苦难的生命历程,意味着知识分子对过去、对未来、对生活、对生命的一种彻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