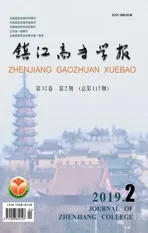乡土贵州的呈现与守望——蹇先艾乡土小说研究
2019-01-31龙丽萍
龙丽萍
(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乡土文学为现代文学注入了活力。“乡土文学”的概念最初由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的导言中提出,“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的人们,无论他自称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1]10鲁迅被称为“乡土文学”的开山鼻祖,他以《阿Q正传》《故乡》《孔乙己》等充满浙东水乡色彩的小说开拓了乡土文学的道路。在鲁迅乡土文学的影响下,自偏远的贵州走出来的蹇先艾(1906—1994),用弥漫着泥土气息的文字绘制了一幅幅贵州乡野图景,他关注故土生活、审视故土现实,向世人呈现了贵州独特瑰奇的地貌环境和地域风情,描绘了处于贫困中的山民野蛮、蒙昧甚至异化的精神状态,指出罪恶的烟盐经济和军阀混战给贵州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1 原生态独特瑰奇的乡野风景图
20世纪20年代的乡土文学一出现便表现出浓郁的“土气息”“泥滋味”,即浓郁的地方特色,如鲁迅笔下的鲁镇和未庄、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沙汀笔下的川西北村镇。贵州峡崖险峻、山路崎岖。一位学者曾如此描述:“贵州地表支离破碎,奇峰突起,地下溶洞发育,‘无山不洞’。贵州土地资源呈现‘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结构形态,喀斯特山地、丘陵所占比重极大,利于农业发展的溶蚀洼地即喀斯特盆地,在贵州一般称为坝子的平整土地较少。”[2]这样的自然环境造成了贵州交通不便、经济落后。但福祸相依,闭塞落后的贵州也因此保留了原生态的自然风光,让世人看到了一个独特的乡土世界。受到“五四”新思潮影响的蹇先艾,以一个既作为“局外人”又作为“局内人”的特殊视角来反观自己的故土,对有着特殊地域特色的贵州山区进行了精心的塑造和描写,将一系列贵州风、贵州景、贵州人、贵州情真实而生动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首先,作家通过精炼的刻画让世人看到了黔北独特的地理与气候环境。如小说《贵州道上》的开篇描写:
多年不回贵州,这次还乡才知道川黔道上形势的险恶,真够得上崎岖鸟道,悬崖绝壁。尤其是踏入贵州的境界,映入眼帘的都是奇异高峰:往往三个山峰并峙,仿佛笔架;三峰之间有两条深沟,只能听见水在沟内活活地流,却望不见半点水的影子。中间是一条一两尺宽的小路,恰好容得一乘轿子通过[3]261。
地面崎岖不平、地貌类型极为复杂,可以看出这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分布的地区。山峰连绵不断,凸显贵州山区面积范围的广大;“只听见水在沟内活活地流,却望不见半点水的影子”,写出了峡谷之深;“一两尺宽的小路”,说明山高路窄。这种复杂险峻的地势地貌不仅让乘客发出“行路难”的叹息,还让身强力壮、具有翻山越岭本领的轿夫望而生畏。小说后面的文字中,除了介绍贵州独特的地理环境外,还介绍了贵州特殊的气候环境。山里经常下着蒙蒙细雨或倾盆大雨,道路常常是泥塘深坑,有时还会发生山洪。险峻的地势加上恶劣的天气,让行走在道路上的人惴惴不安。作家用细腻的笔触将雨中的山路、雨后泥泞的小道以及行路之人细微的情感都生动描摹了出来。
其次,作家赞美了贵州瑰奇的自然景色。在蹇先艾的笔下,一幅幅美丽的贵州山水图随处可寻、一张张动人的生活画随处可见。在小说《到镇溪去》中,作家描写了摆渡所见的秀丽景色:
船靠着左边走,慢慢驶入峡口去,曲长的山峰并着,只看得见一线蓝的天光。这里真像四川的瞿塘与巫山。谷中一片清幽的景致,没有岸,从两山之间,哗哗流出银沫飞溅的小瀑布,像微雨似的凄零飘动,使人生幽幽的感觉。还有玲珑秀丽的小石山,真可爱,上面丛生着绿叶红边的虎耳草,寄生在大的山峡之中[3]152。
连绵不断的山峰、清幽的峡谷和清澈的涓涓流水,在船上能看得见“一线蓝的天光”,瀑布溅起的水花如小雨一般零星飘动,连小石山都是如此玲珑剔透和可爱,这仿佛是一个人间仙境。作家字里行间洋溢着对故乡景色的喜爱和赞美之情。
在小说《乡间的回忆》中,作者描绘了一幅幅惬意的生活图景:金黄色的晚霞映照下,与嫂子们一起在绿绿的柳荫下捉泥鳅、在清澈见底的河流中捉螃蟹;夕阳西下,放牛娃赶着水牛,唱着歌回家……这些正是我们古已有之的“天人合一”的和谐生活。
此外,小说《濛渡》中写道:
连绵的微雨在天空飘飞着,天气阴沉得看不出是什么时候。我们已经登上到处都是黄泥的脚迹的宽板渡船了,茫然望着澄碧闲静的水,偶尔也被风掀起几团起伏的波纹,旅客们的心头都泛溢着舒展松快的感觉[3]440。
作者笔下连绵的微雨、阴沉的天气,正是贵州“天无三日晴”气候特征最真实的写照。生活在这一方水土之上的人们,并没有因为天气的阴沉而感到不快,而是沉浸于澄碧闲静的山水中,连那起伏的水波都成为人们心情舒展的缘由。作者对贵州独特自然环境的细致描写,让人身临其境、沉醉其中。
故土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已渗入作家蹇先艾的灵魂,他向世人展现了贵州“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的自然景象,勾勒了边远山区的奇峰峡谷、悬崖峭壁、崎岖鸟道,描绘了山高水蓝、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独具地域特色的贵州图景,让世人看到自然、本真的山区原始生态环境,看到有别于其他地域的乡土文学的美学景观。
2 守旧鄙陋风习下麻木扭曲的人性解剖图
如前文所述,贵州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分布的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阻碍了贵州与外界的沟通与交流。这不仅造成了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物质上的贫瘠与艰难,还使得乡民们思想闭塞与精神麻木、民风野蛮落后与守旧鄙陋。
鲁迅一直致力于通过文艺改变愚昧国民的精神。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4]5离开故土到北京求学的蹇先艾,受到“五四”运动新思潮和鲁迅乡土作品的影响,他深刻认识到,贵州物质上非常贫瘠,但比物质贫瘠更可怕的是人们精神上的麻木与扭曲,所以他也毅然拿起笔批判野蛮落后和守旧鄙陋的风习,解剖麻木与扭曲的人性,以引起疗救的注意。
《水葬》是蹇先艾乡土小说的代表作,曾与《到家的晚上》一起被鲁迅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鲁迅称:“……但正如《水葬》,却对我们展示了‘老远的贵州’乡间习俗的冷酷,和出于这冷酷中的母性之伟大,贵州很远,但大家的情景是一样的。”[1]9
《水葬》描写了骆毛这个阿Q式人物的悲剧,骆毛因为不守本分做了贼,被乡人用“水葬”的方式加以惩戒。小说中写到:“文明的桐村向来就没有什么村长……,犯罪的人用不着裁判,私下都可以处置。而这种对于小偷处以‘水葬’的死刑,在村中差不多是‘古已有之’的了。”[3]27时间到了20世纪20年代,社会不断发展、人类文明不断进步,可在偏远的贵州山区,这种陈规陋习依然存在,并且是“古以有之”,可见社会的落后闭塞,守旧鄙陋风气根深蒂固。与这种守旧落后风气比起来,更让人痛心的是“看者”和“被看者”麻木扭曲的人性。前来观看骆毛被处“水葬”的看者很多,场面不是一般的热闹,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媳妇和婆婆、有奶奶和孙女、有姑娘和奶娃……大家争先恐后、挤进挤出,顾不得各种汗的味道。这个“文明”的桐村,大家平时听到不干净的粗话都会脸红,会说“丧德”,可是当看到骆毛遭遇这种残忍的惩罚时,他们只是把它当成一种热闹,甚至是娱乐,没有一丝的同情、伤感和愤怒之情,可见人心的冷漠、麻木,甚至无人性。而对于“被看者”骆毛而言,死到临头之时,只是满嘴脏话、粗话,用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来安慰自己,“尔妈,老子今年三十一”,“再过几十年,不又是一条好汉吗?……”[3]30骆毛的潜意识里是认识不到这种礼教制度的罪恶的。在这种守旧鄙陋风习的影响下,无论是“看者”还是“被看者”,他们都不会反抗,也不知道反抗,他们从不思考这一习俗的合法性,而是自觉地接受和顺从,这是人性的扭曲,更是人性的悲哀。
在小说《初秋之夜》里,作家描写了一群虚伪腐朽的官吏、文人、士绅,如县里女子中学的校长吴惟善就是其中之一。吴校长的办学标准是“女子无才便是德”;他不教白话文,用《女四书》当作课本;当五卅惨案发生,群情激愤,全城的学生高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时,他不准女子学校的学生参加,认为爱国不是女学生的分内之事。这么一个受封建守旧陋习影响、强调培养恪守宗法制礼教文化的校长,竟被县长乌元富夸为“教育家”。当地许多文人、官吏与士绅对吴校长的作为是“为之感动”“大为动容”;作为地方的希望并且受到新思想影响的年轻北京学生竟然也默默地表示赞许。由此可知,封建守旧陋习已根深蒂固,人性在封建思想影响下已极度扭曲和异化。
诗人刘大白谈到故乡的山水时是满怀眷恋与讴歌,谈到故乡的城市、故乡的社会时充满厌恶与诅咒。蹇先艾也厌恶生活在故土上的麻木不仁、异化扭曲的人们,憎恨他们的不觉醒。爱之深、恨之切,作家将这种守旧落后的生活原貌一一呈现,以期引起人们的注意,进而采取疗救方法来改变贵州现状。
3 烟盐经济与军阀统治下的人生悲剧图
“地理环境毕竟给人类文化的创造提供了物质材料,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类文化创造的发展方向。”[5]17在蹇先艾的小说中,我们看到了烟盐经济与军阀统治下的一幕幕苦难的贵州山民人生悲剧图。
烟盐经济是造成贵州百姓人生悲剧的主要原因。贵州地处云贵高原东部,主要以山地为主,土地比较贫瘠,良田本来就少,再加上出产量比较低,导致贵州极其贫困和落后,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贵州是全国最落后的省区。当时的政府为解决财政困难,一方面怂恿民众种植鸦片、出售鸦片甚至吸食鸦片,以此获取暴利;另一方面,因贵州不产盐,需要从外面特别是从邻省购买,政府便通过收盐税来获取财政收入。畸形的经济结构产生了许多穿梭在川黔道路上的盐巴客、轿夫,也让许多人成为鸦片的牺牲品,越抽越穷,越穷越抽,上演了一出出人生悲剧。
在小说《盐巴客》中,作家描写了一群穿梭在崎岖山道上的下力人——盐巴客。他们干的是最苦的活,常常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他们的地位极为低下,常常被人以挡道为由呵斥,被骂为“盐巴老二客”;更为糟糕的是,如果遇上军队,他们还有可能被推下几十丈深的悬崖。艰难的生活把他们压得很苦,生命又没有保障,种种重压下,他们原本淳朴善良的性格变得暴躁、扭曲,甚至一些人做出异化的非人的行为。
在《盐灾》里,作者向我们呈现了一幅幅缺盐成灾的悲惨图景。“今天我下坡去在村里走走,我所遇到的每一个人面貌都非常黝黑,没有一点笑容,像丧亡了一样;不说话,低着头,拖着鞋,不扣衣服,无目的地乱走。”[6]3因为盐被垄断了,乡下的老百姓买不起盐,只能吃灰盐、淡盐,甚至只好不吃盐,大家如行尸走肉的僵尸一般,“一点精神没有,全身的骨头都觉得酥软,比没有吃饱饭还难受。肩不能挑了,背也不能驮了,走起路来提提脚都很费力,只想坐在那里或者躺在那里”[7]。盐灾让人精神萎靡,让家庭变得不安宁,让社会变得不安定,人们就在这种畸形的烟盐经济中受着煎熬。小说《酒家》里的张大娘有很严重的烟瘾,为得到更多的烟钱,不惜将自己的宝贝女儿嫁给巴团长作小妾,葬送了女儿的青春和幸福。褚梦陶的父亲贪恋酒色和吸食鸦片,恶劣的基因使得褚梦陶从一出生身体就很孱弱,大哥在幼年时就疯了,二姐的身体也非常单薄。这些都是烟盐经济酿成的人生悲剧。
军阀统治是造成贵州百姓人生悲剧的重要根源。掠夺性是贵州军阀统治最突出的特征,他们毫无人性地压榨百姓、掠夺财物。在蹇先艾的笔下,我们看到了军阀统治给广大民众造成的深重灾难。原本已贫困落后的贵州在黑暗的军阀统治下变得更加民不聊生。如在《酒家》中,师范生褚梦陶劝说女友的母亲不要将女儿嫁给有三妻四妾的巴团长,最后劝说不成,反遭设计陷害,被士兵乱枪击毙。《盐巴客》中的盐巴客们,经常背上都是百多斤的东西,当军队经过来不及让路时,便被推下万丈深渊。小说中的“我”遇到的是一个骨头全部跌断的盐巴客,还有很多像他一样的盐巴客,也过着同样悲惨的生活,不仅身体要抗着重担,连精神也要时刻紧绷着,因为这种悲剧随时可能发生。《安癫壳》中,安癫壳原是一个体魄强健的农民,妻子被土匪抢走了,为了付客栈的房钱,只得将女儿卖给了公馆当婢女,最后自己沦为乞丐。在《到镇溪去》中,“春云栈”老板娘的丈夫王松寿,原本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壮小伙,能挑能抬,被军阀部队拉去干苦力后,变得又黑又瘦,最后悲惨死去。《蒙渡》中的一乡下女人,丈夫被川军拉夫拉去了,家里有三个孩子要抚育,婆婆又犯病了,苦难的日子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她每天都祈祷自己的丈夫不要被打死……军阀统治导致了人们物质上的贫瘠,还给人们带来了精神上的恐慌。
在烟盐经济和军阀统治下的贵州是贫穷的、黑暗的,人民生活在苦难的悲惨世界里。贾剑秋认为蹇先艾笔下的乡土小说“集中了现代贵州各种阶层、各种身份、地位的社会角色……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在军阀统治与盐烟经济桎梏下的哀乐苦痛、生死兴衰,构成了一幅立体的20世纪上半叶贵州地方社会的现实图景。”[7]作家关心故土的百姓,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和人生困境,展现了一幅幅悲惨的20世纪上半叶的贵州图景,对造成这一系列人生悲剧的烟盐经济和军阀统治进行了鞭挞和控诉。
4 结束语
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蹇先艾一生致力于乡土小说创作,是贵州乡土文学的奠基人。他向世人展现了贵州山区独特瑰奇的生态景观,展示了贵州山区人民的生活场景以及这种生活场景之下守旧鄙陋的生活方式,刻画了在烟盐经济和军阀统治下贵州人民的悲惨命运。何光渝在《20世纪贵州小说史》中认为蹇先艾的小说“真正地直面人生,直面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现实”[8]73。从对原生态独特瑰奇的乡野风景图的描绘,到原生态土地上淳朴自然的人文精神的展现,到造成20世纪上半叶贵州贫困落后根源的揭露,我们看到了一部20世纪上半叶贵州的社会史,一幅现代乡土贵州图景。作为黔之子,蹇先艾从现代知识分子的视角,以充满哀痛而愤懑的情感,描绘了贵州的崇山峻岭和崎岖山道,以及在那悬崖峭壁下绝地求生的苦难人们,用充满乡愁的笔墨不动声色地将一幅幅贵州的社会图景呈现在世人面前,让人们认识贵州、走进贵州,让偏远的贵州不再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