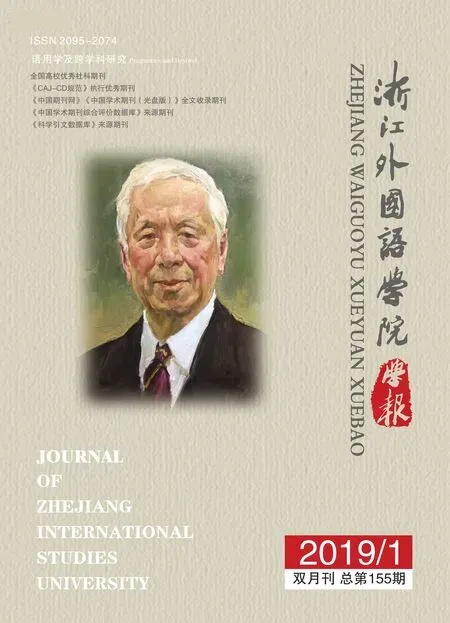《地下铁道》中身体绘制的文学地图
2019-01-30刘露
刘 露
(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中国药科大学 外语系,江苏 南京211198)
一、引言
当代美国非裔作家科尔森·怀特黑德(Colson Whitehead,1969—)的长篇小说《地下铁道》(The Underground Railroad,2016)以16 岁的黑奴少女科拉沿虚构的地下铁道寻找自由的经历为主线,书写了一则关涉蓄奴历史亦隐喻当今美国种族状况的寓言。小说问世后不久便相继获得2016年美国国家图书奖和2017年普利策小说奖,亦收获了主流文学评论界的关注。《纽约时报》 书评人角谷美智子(Michiko Kakutani 2017)认为小说主题与风格杂糅,令人想起“托尼·莫里森的《宠儿》、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拉尔夫·埃里森的《看不见的人》;同时小说亦“借鉴了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弗兰兹·卡夫卡和乔纳森·斯威夫特的技巧”。国内亦有学者从小说对超越种族的人性的展现(孙燕 2018)和对创伤的书写(承华 2018)等方面研究了作品的主题呈现。
正如书名所揭示的,《地下铁道》的核心叙事线索是一条位于地下、横贯美国版图的铁道。美国废奴运动史上帮助黑奴逃往北方自由州的秘密组织“地下铁道”的名字,在小说中成为了实体的存在,这不能不说是小说最富有创意的地方之一。从佐治亚州种植园出逃的女主人公科拉正是沿着它一路北上寻找自由,结尾时仍在逃亡的路上。小说以铁道的实体和隐喻功能作为线索,不仅描写了人物的活动路线,也勾勒出科拉逃亡沿途不同地域空间的景观与文化,更涵盖了与美国种族问题有关的广阔历史图景;小说的章节标题亦以地名和人名相互交错的形式呈现,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可以进行充分的地理想象,进而获得观看地图之感。可以说,《地下铁道》是一部具有鲜明地图意识的作品。
西方文论界对文学创作中地图隐喻的关注由来已久。卢卡契(George Lukacs)(1974:121)在《小说理论》(The Theory of the Novel)一书中提到,哲学的真正任务就是绘制一幅“原型地图”,而小说作为对人类超验的漂泊状态的回应,则通过创作一个地图般的世界为个体和群体指明方向。詹姆森(Frederick Jameson)(1991:51-54)则将各种文化文本描绘空间地图之方式命名为“绘制认知地图”(cognitive mapping),认为其对于我们理解世界和我们在其中的位置至关重要。研究空间叙事的批评家们更加重视文本与地图的联系,比如弗兰克(Joseph Frank 1991)在《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Spatial Form in Modern Literature)一文中论述了小说中各种元素相互参照联系形成的空间图景;佐伦(Gabriel Zoran)则将文本视为一幅隐喻世界的全景图,“包含着远与近、内与外、中心与边缘等各种关系”(1984:316)。
文学与地图的密切关系让不少学者将“文学地图”(literary map)的概念运用于文学作品批评。在《小说、地图与现代性:空间的想象(1850—2000)》(Novels,Maps,Modernity:The Spatial Imagination,1850-2000)一书中,布尔森(Eric Bulson)援引美国国会图书馆文学地图展览会组织者的定义,指出文学地图是“对与作家及其作品有关的地理信息的描绘,是引领读者进入作家想象世界的向导”(2007:21)。实际运用中,研究者眼中的文学地图常分为实体性与借喻性两种,亦即狭义和广义文学地图。实体性概念的文学地图具有相对完整的图文结构与互文功能,而借喻性概念的文学地图则“主要借鉴和汲取了‘文学地图’理念与方法应用于文本分析与意义阐释”(梅新林2015:162)。前者指以实体形式收录于文本中的图形,或评论者根据作品中的地理、叙事结构、主题等特点绘制的地图;后者则往往有文无图,常用来隐喻作家以文字描绘的、存在于读者想象中的地理景观。美国学者小泰利(Robert Tally Jr.)用“文学绘图”(literary cartography)来比喻作家创作过程中的语言和想象活动,认为作家和地图绘制者一样必须“界定疆域,决定描述、强调或省略哪些风景……确定叙事的范围形状”,因此将作家称为地图绘制者、将作品称为文学地图,其“字面和比喻意义同时存在”(2013:45-46)。
《地下铁道》即可被视为一幅隐喻意义上的文学地图,不仅描绘出地理空间的特点、人物的活动走向和对生命意义的追寻轨迹,也呈现出与美国种族问题相关的历史、地理和文学景观。本文拟以文学地图为研究视角,从被规训的身体、游牧的身体和叙事的身体三个维度来考察小说中作为叙事核心元素的身体的意义。
二、被规训的身体:书写美国种族问题的历史图景
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知识权力论是文学地图研究的理论基石之一。正如福柯(1998:221)所说,“权力的空间化乃是现代社会规训操控的基本策略和方式”,权力的实现伴随空间感,地理景观的形成与意识形态密不可分。文学文本中的权力书写常常蕴含“知识与权力的流通和分配、空间与意象的契合与张力、身份和图示的统一与分化等重大问题”(郭方云 2013:110),由此给读者带来地图想象。《地下铁道》中通过文字书写所呈现的横跨大西洋两岸的地理人文景观图,高度表征了种族主义权力的运作方式。而这幅地图与奴隶科拉的身体有关——“人体是权力的对象和目标……那些权力强加给它各种压力、限制或义务”(福柯 2007:155),使异己力量驯服,确保持久运作。对奴隶身体的规训则是《地下铁道》中文学地图的主要脉络,小说以科拉在美国各州的经历和见闻为线索,向读者呈现出一幅美国种族制度与思维的演变图。
小说开篇便通过对科拉的外祖母阿贾里从西非被贩卖到美国的过程的书写,描绘出贩奴贸易的地理图,以及奴隶身体被征服的历史景观。奴隶制下,黑奴的身体被视作私产,其作为生产力越是“非人”和驯服,就越能为奴隶主带来更多利益。阿贾里的身体先遭奴隶贩子绑架,失去自由;继而成为商品,经历无数次转卖;来到美国佐治亚州的兰德尔种植园后,又成为严密监视下超负荷运转的机器,终生劳作。阿贾里“认识到自己身体中蕴藏的科学,并不断地观察到,每样东西都有自己的价值……美国的规则就是把人当作事物”(Whitehead 2016:8)①本文中小说《地下铁道》的引文皆出自同一版本(Whitehead,C.2016. The Underground Railroad[M].New York:Doubleday),因此后文出自该作品的引文皆随文直接标注页码。。出生和成长在种植园的科拉见证了诸多奴隶主对奴隶身体的暴行,“砍掉奴隶的脚是为防止他们逃跑,砍掉他们的手是为防止偷窃”(45),私刑均当众进行以示惩戒。惩罚奴隶身体的目的在于制造驯服的灵魂,几十年间兰德尔种植园没有奴隶敢反抗或出逃。作为女性黑奴的科拉,身体更是蒙受双重压迫:不仅被当作劳动力而遭受驱遣和鞭答,而且成为白人奴隶主性暴力的目标。此种遭遇迫使科拉最终在黑奴西泽的劝说下一同踏上了逃亡之路。
科拉沿着地下铁道一路向北逃亡的地理路线,覆盖了美国东部的版图。在实体层面上,小说每隔一章便以科拉流亡所到的州名为标题,给读者以地图想象,在隐喻层面上则描绘了种族主义对奴隶身体控制的历史全景图。小说并未在开始处交代故事发生的具体年代,自科拉出逃起,故事的场景便逐渐模糊。科拉落脚的第一站是南卡罗来纳州,因为有电梯和摩天大楼的存在,所以明显并非蓄奴时代。这里的种族政策看似较为开明,政府为黑人制订住宿、工作、教育和医疗等帮扶计划,但同时却以国家和科学的名义对黑人的身体实施暴力:公立医院对前来诊疗的患梅毒的黑人男性不采取任何治疗措施,而是将其作为研究对象任由病毒在人体内发展,这一情节影射了历史上美国公共卫生署的“塔斯克基梅毒研究”(1932—1972);19世纪白人医学界利用盗墓等方式滥用黑人尸体进行医学实验的传说,在“南卡罗来纳”一章中也曾被当作真实事件加以描述;科拉在医院接受工作体检时被医生劝说接受绝育手术,影射的则是20世纪上半叶美国的“优生”运动,黑人妇女在非自愿情形下被实施绝育手术的情况到20世纪70年代仍十分普遍。这几处情节均暗示了美国历史上的种族主义势力运用国家权力对黑人的身体进行规训。对黑人的医学实验体现了现代科学支撑下的种族歧视:20世纪初,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下的人类学、生物学和医学均认为黑人属于低等物种,更易生病或沾染恶习,因此要加以研究与控制。“优生”运动用科拉的话来说则是“白人正急切地把未来偷走”(159)——种族主义势力通过夺走黑人后代的方式,剥夺其未来的希望和境遇改善的可能,从而实现更加持久的规训运作。
在这张呈现美国不同时期种族主义思维的地图上,奴隶的身体还受到另外一种形式的规训与控制。科拉在南卡罗来纳州“自然奇迹”博物馆获得了一份充当活体展示品的工作,在橱窗中向白人游客表演三个黑人生活的场景,即“黑暗非洲掠影”“贩奴船上的生活”和“种植园的典型一天”。“花花绿绿的非洲服饰,无袖短上衣、长裤加皮靴的水手打扮让她像个街头流氓”(149)。黑人的身体被渲染为充满神秘感的异类和野蛮愚昧的化身,以迎合白人观众心中有关黑人的刻板印象。作为被观看者的科拉,身体被囚禁于橱窗中,处于沉默失语状态。正如萨特(Jean-Paul Sartre)(1997:344)所认为的那样,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注视是一种否定性的存在关系,来自他者的凝视会让自我的主体性失落,被异化为物一样的客体。在博物馆的这种视觉实践中,白人极力强化自己凝视者的主体地位,通过对黑人身体的凝视将其边缘化、客体化,以实现种族权力的规训。这一情节也讽刺了20世纪美国“多元文化主义”语境中,白人文化霸权将黑人的身体形塑为被凝视和被奚落的对象,使其以顺从、无知、暴力的刻板印象存在于主流话语与大众文化之中的种族歧视行径。
科拉沿着地下铁道继续向北,进一步见证了种族主义对黑人的迫害。在北卡罗来纳州,不断增长的黑人数量引发了白人群体的恐慌:“在绵延不绝的黑色面前,南方传统不堪一击。”(216-217)对黑人身体力量的恐惧致使该州实施种族清洗,鼓吹建立“白人国家”。这一虚构的情节影射着美国历史上在居住区域、学校教育和婚姻方面一直存在的种族隔离制度,以及20世纪废除种族隔离法后仍存在于政府和民众之中的歧视与抵制。躲藏于废奴主义者家中的科拉,见证了市中心公园每周举行的“周五盛典”:猎奴者向公众展示他们的“猎物”,将其当众处死,而后将尸体悬挂于一条名为“自由小路”的道路两旁的树上,挂满尸体的小路长达数英里。这一情节描写反映了美国历史上曾极为普遍的对奴隶处以私刑的情形。当科拉逃亡至印第安纳州,在带有乌托邦色彩的瓦伦丁农场刚刚开启新生活后不久,便见证了新生的黑人自治社区在白人的血腥围攻中毁灭的一幕,这一情节无疑指向美国至今仍存在的种族主义袭击事件。
从佐治亚州到印第安纳州,科拉始终无法摆脱猎奴者里奇韦如影随形的追踪。里奇韦心目中的“美国精神”则是这幅逃亡地图上的种族主义思维轨迹,贯穿了整个美国历史:“去征服、建设、开发。让我们去摧毁必须摧毁的一切。去提升劣等种族,不能提升就降伏他们,不能降伏就消灭他们。”(302)里奇韦的信条实际是“天定命运论”(manifest destiny)的翻版。19世纪中期,“天定命运论”作为论证美国领土扩张正当性的理据,和种族主义思维融为一体,其将盎格鲁-撒克逊人视为被上帝选中的优等种族,将其他种族看作劣等种族,从而使前者征服和改造后者的权力合理化。正如里奇韦对科拉的追捕一直在进行,支撑白人势力扩张的种族主义思维在美国历史中也一直延续着,这一点也由小说时代背景的模糊性所暗示。作家在接受《纽约时报》旗下Vulture 网站的访谈时曾提及,在20世纪80年代的纽约,针对黑人的警方暴力十分频繁,以致他出门时都担心成为攻击目标;种族主义思维在当今美国社会仍有余绪,针对有色人种的例行搜查、政治家竞选演说中反对移民进入美国的言论、影视中频现的种族主义笑话……如此种种,不胜枚举②参见2016年8月Vulture 网站编辑鲍里斯·卡奇卡(Boris Kachka)对怀特黑德的访谈(https://www.vulture.com/2016/08/colsonwhitehead-author-of-the-underground-railroad-c-v-r.html)。。
地图“不仅是现实空间关系的仿真描绘,也为艺术虚构提供了基本的描摹图示”(郭方云2013:110),《地下铁道》中科拉的身体旅程则是一幅兼具地理和寓言意义的文学地图。科拉在地图不同区域所见证的种族偏见、排斥与清洗,凝缩了美国社会种族主义势力对黑人身体的规训与操纵的历史。在这一意义上,小说中这幅与身体有关的地图不仅具有空间性,而且具有时间性,连接着美国的过去和现在。
三、游牧的身体:绘制自由主体生成的轨迹图
《地下铁道》在呈现美国种族主义的历史与地理图景的同时,也通过科拉的身体绘制了奴隶个体成长为自由主体的轨迹图。身体虽是权力规训的对象,但亦是个体反抗权力的策源地,其能动性在西方思想史上一直受到重视。比如,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2005:194)认为“身体是我们拥有一个世界的一般方式”,身体的行为生成意义;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1990:1)则提出“美学是作为有关身体的话语而诞生的”,身体的感觉和经验可以颠覆现有的秩序。小说中,科拉在身体被控制、侵犯与规训的同时,也有意识地利用身体行使权力、改写身份,以其沿地下铁道的游牧绘制出一幅自由主体的生成轨迹图。
科拉意识到白人群体于她而言是一个枷锁,但如果“对准这个枷锁,时刻注意挑选薄弱处下手,总能有所收获”(172)。这与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加塔利(Felix Guattari)在《千高原》(A Thousand Plateaus)中提出的“块茎思维”对“树形思维”的突破颇为相似。树形系统中,根、枝、叶层级分明,“整体先于个体存在,个体在整体中拥有一个确切的位置”(德勒兹、加塔利2010:20),这种总体化、中心化、层级化的思维模式“主宰了西方的思想和现实”(德勒兹、加塔利2010:22)。而与之相对的块茎思维,则具有不断突破、逃逸、再生和成长的功能,是一种解构的、破层级的游牧式思维。在政治领域,代表树形思维的国家机器通过制度、法律、道德和意识形态等手段对社会进行管辖;而被德勒兹和加塔利喻为游牧主体的社会群体,则利用社会系统各个方向上的漏洞,在对抗中冲破控制和编码,走出禁锢,从而进入开放空间。《地下铁道》中以科拉为代表的奴隶的身体,可谓是种族主义地图上的“块茎”,在游牧中不停冲击着种族主义势力为其划定的红线。
《地下铁道》中科拉的身体游牧意识,可以追溯到其外祖母阿贾里和母亲梅布尔对个人空间的追寻。阿贾里尽管终生未走出种植园,却在自己居住的棚屋前开辟了一块土地。这一位于种植园中央的小小地块由她个人支配,犹如在奴隶主树形权力帝国图上打开的一个缺口,有着丰富的象征意义:奴隶在土地上劳作并收获粮食,又用粮食维持生命的延续,暗示着其身体力量的持久性;奴隶对自由的渴望亦在土地上萌芽,并延伸到他们的后代。阿贾里的女儿梅布尔带着小小地块上产出的甜薯踏上了逃亡之路,去向成谜,令奴隶主至死不能释怀。作家在小说最后透露,梅布尔终因不忍丢弃女儿科拉,在返回种植园的途中被泥淖吞噬,然而,她还是看到了种植园外的自由天空。科拉从外祖母和母亲那里继承了土地,小小地块成为其破解辖域化、生成自由主体的策源地;同时她也继承了她们追求自由并付诸身体行动的力量。
沿地下铁道的逃亡途中,科拉的旅伴和救助者们纷纷死于袭击或牢狱,而科拉却每次均能化险为夷,其身体似乎被作家赋予了刀枪不入的特异性,这一特异力量源自于作为“块茎”的科拉身体的能动性。在逃离种植园的路上,科拉用石块砸中前来追捕的白人男孩的头部,得以成功逃脱;在被猎奴者里奇韦抓回的路上,科拉在后来成为她恋人的黑人罗亚尔的帮助下,用链子勒住里奇韦,并用木靴踢他的脸,得以重获自由的同时也展现了自己的身体力量。在博物馆充当展示品时,科拉一次次瞪视将黑人当作奇异物种参观的白人游客,目光坚定、凶狠,直到对方逃走,以身体行动反击了种族主义的凝视。在北卡罗来纳州废奴主义者马丁家中,科拉透过藏身的阁楼顶天花板的小孔俯视奴隶主对奴隶的私刑时,更是完全由凝视客体变为凝视主体,以自己的目光对奴隶制的暴行进行审视和批判。科拉还学习像自由人一样走路,“挺直了背,保持头部直面前方”(127)。生活稍微安定后,她开始欣赏和构建自己身体的美,用劳动收入购买喜爱的裙子,用帽子遮住头部因鞭笞留下的伤痕。小说结尾处,再次踏上逃亡之路的科拉在地下铁道中发动了手摇列车,“她舞动着胳膊,全身心投入到这一动作中,发现了一种节奏,向着北方”(413)。科拉以肢体、语言、目光等形式进行反抗,她在身体游牧的过程中不断冲击着种族主义的辖域,拓展着地图上属于自由个体的空间。
德勒兹、加塔利(2010:20)认为,与界定事物本质的“克分子线”不同,“逃逸线”源自体系内部却向外扩张延伸,让主体冲破体系的稳定边界,在运动中生成主体意识。而“妇女们对父权制家庭的逃避……有色人种对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攻击,这些都是逃离克分子线的逃逸线的进一步例证”(凯尔纳、贝斯特 2006:118)。作为科拉的“逃逸线”,地下铁道首先令她在逃亡中体验到了暂时的自由;继而让她来到南卡罗来纳州的黑人膳宿机构,拥有了工作、住所、收入和教育,并逐渐形成了自己对奴隶制和种族主义的批判意识;然后使她在印第安纳州的瓦伦丁农场这个黑人自治社区进一步收获了基于平等的友谊、爱情与尊敬。正如科拉自己所总结的那样,地下铁道和这个国家的所有事物一样由黑人建成,而她经由这一凝聚着黑人身体力量的铁道,在不断的游牧中践行着主体对自由和幸福的追求。“《独立宣言》就像一张地图,你知道它是对的,但你要走出去亲自验证,才能真正理解这一点。”(326)
文学地图视角下的《地下铁道》,亦可以被视为一幅科拉的空间实践图,图上清晰呈现了科拉由奴隶变为自由个体的轨迹。在某种意义上,科拉在地图上的轨迹亦寓言了作为整体的美国黑人在争取民权的道路上取得的历史成就。这幅地图更是动态的:流亡过程中科拉一旦在某处稍作停留,危险和追捕便接踵而至,她只有不断地通过地下铁道继续逃亡,让身体“保持运动,哪怕是在原地,也要不停移动”(德勒兹、加塔利 2010:221),才能成为具有后现代意义的游牧主体,在永恒的运动中冲破权力的边界,奔向新的生命形式。结尾处的科拉仍在逃亡的路上,这是作家对美国黑人仍在追寻自由和平等的征途中的隐喻。
四、叙事的身体:描绘美国非裔文学传统的景观图
研究者指出,隐喻意义上的文学地图,其描绘对象不仅可以是地理或历史景观,也可以是与作家和作品相关的文学传统,一些文学地图“凸显了整个国家的文学遗产”(Bulson 2007:21)。从这个意义上说,《地下铁道》可以被视为一幅有关文学传统的地图。而这一地图仍然是通过科拉的身体来绘制的:科拉的身体旅行不仅是小说叙事发展的动力,同时也以其与众多文学作品尤其是美国非裔文学作品的互文与对话关系,反映了美国非裔文学的地理意识、历史演进和主题关切。
《地下铁道》通过科拉的身体旅行,集中体现了美国奴隶叙事文学的主题和美学传统。小说承袭了《道格拉斯自传》(Narrative of the Life of Frederick Douglass)、《女奴自传》(Incidents in the Life of aSlave Girl)等早期奴隶叙事作品中,奴隶从南向北迁移寻找自由的传统主题,人物地理位置的迁移背后蕴含着政治文化方面的意义;小说亦以主人公的创伤经历和见闻,暴露出奴隶制的罪恶与残酷;更为重要的是,和《道格拉斯自传》等作品一样,小说通过描写科拉摆脱枷锁的过程,展现了黑人对自由独立的追求以及思想境界和生存能力的提升,从而由对种族压迫的控诉,上升为对凝缩于《独立宣言》中的美国精神的发扬,书写了主人公既是黑人又是美国人的双重身份。在写作风格与艺术手法上,《地下铁道》所使用的也是现实主义的基调,并与不少奴隶叙事作品一样采用了附加文本——小说各章节间插入了多篇来自史料的真实逃奴悬赏启事,增强了叙述的实感;致谢部分,作家列出了其所参考的有关奴隶制、种族关系和秘密组织“地下铁道”的文献资料。然而,《地下铁道》中以奴隶的身体旅行呈现的种族记忆却不再拘泥于严格的现实,虚构的地下铁道及其沿线并非发生于同一历史时期的景观,给作品带来了时空交错的超现实色彩,与《逃往加拿大》(Flight to Canada)等近期奴隶叙事作品中采用的时空交错、戏仿等后现代手法有异曲同工之妙。此外,小说一方面沿袭了早期奴隶叙事作品中的离奇、惊悚、悬疑等元素,另一方面也吸收了近期奴隶叙事小说和电影中的方言俚语,增强了作品的通俗性和可读性。可以说,《地下铁道》是一幅全方位呈现奴隶叙事传统的文学景观图。
逃亡过程中的科拉,从隐匿到暴露,从顺从到反抗,从形单影只到融入群体,其身体书写的故事在诸多地方体现着之前美国非裔文学中的重要关切,可以说是一幅反映美国非裔文学主题演进的文学地图。科拉东躲西藏,在地下铁道的列车中面对着深不见底的黑暗,在地上时则生活于与白人隔离的空间。这一主题呼应了20世纪美国抗议文学对黑人边缘化身份的关切。20世纪初,美国黑人大规模移居城市,其在社会文化中的隐形性和边缘化地位引起了作家的关注,无论是《土生子》(Native Son)中土生土长于美国却没有美国公民身份的黑人托马斯,还是《看不见的人》(Invisible Man)中无名无姓、生活在城市地下室中的黑人主人公,抑或是《地下铁道》中拥有着看不见的身体、无法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科拉,都寄托了作家对社会现实的反思与批判。除种族抗议之外,小说还通过科拉的身体续写了美国非裔文学中常见的性别抗议主题,继承了《最蓝的眼睛》(The Bluest Eye)等作品所采用的女性身体叙事策略,在反映白人主流文化对于黑人女性的压制的同时,也让身处“边缘的边缘”的黑人女性步入话语中心。小说中的身体叙事还呼应了美国非裔文学对历史的关怀传统。科拉的身体旅行延续了其外祖母和母亲的故事,书写了不同代际黑人的经历,以个体故事表现了有关美国黑人群体的重大事件,如黑人由南往北的迁移、种族隔离制度、民权运动等,同时也挖掘了种族问题所不为人知的细节,让人想起以《宠儿》(Beloved)为代表的美国非裔文学作品对于历史的关注,以及个体声音对官方话语的颠覆。
科拉的身体旅行,不仅以其行进路线给读者以地图想象,也成为小说的结构线索,回应着同类体裁的作品,呈现出一幅生动的文学传统图。《地下铁道》采用了流浪汉小说(picaresque novel)的结构模式,即“以流浪汉的冒险经历为主线,将主人公和其他人物的生活插曲串缀起来”(李志斌2009:69)。这一经典叙事体裁在西方文学史上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奥德赛》(Odyssey),在美国非裔文学中亦十分常见。小说中,科拉的身体感知和欲望,尤其是她对身体自由的渴望驱动她不断流浪,而流浪的经历不仅串连起沿途内容丰富的历史画卷,也展现了她不断探索世界、发现自我的过程,呼应着美国非裔文学中的相关传统。和《看不见的人》中的无名叙事者或《所罗门之歌》(Song of Solomon)中的奶娃一样,科拉每经一处均通过和外界的接触,来实现对自己身份的重新理解和认识。在逃亡过程中,科拉接触到凶残的猎奴者、种族偏见根深蒂固的狂热民众、恐惧矛盾的废奴主义者、主张渐进改革的民权人士等对种族问题持不同态度的人,更充分地认识到自己作为黑人的身份和处境,视野的拓展促进了其心智的成熟。作为女性的科拉与《他们眼望上苍》(Their Eyes Were Watching God)中的珍妮、《紫颜色》(The Color Purple)中的西丽等人物颇有相通之处,其身体流浪的过程也在不断拓展着属于女性的空间:从小说开始时在厨房劳作到最后进入属于男性的火车驾驶室,从依赖男性废奴主义者的庇护而藏身于阁楼到在黑人社区拥有属于自己的女性房间……空间的变化映射出科拉眼界的逐步开阔和独立意识的不断增强。作家本人曾说:“科拉的旅程是《格列佛游记》,但也是《奥德赛》和《天路历程》,其实也就是任何这样的故事——男女主人公在逃亡、启悟或回归的路上经历一系列具有寓意的插曲。”③参见美国国家图书基金会网站劳伦·威尔金森(Lauren Wilkinson)对怀特黑德的访谈(http://www.nationalbook.org/nba2016finalist_f_whitehead-underground-railroad.html)。由此可见,科拉不仅是黑人,而且代表了更广意义上的全人类,以身体绘制的文学地图呈现着关于逃离和启悟的普遍经验,书写了跨种族、国别和性别的人类共同寓言。
五、结语
在众多经典作品已从不同角度再现奴隶制之时,《地下铁道》以科拉的个体经历为线索,运用丰富的层次和杂糅的风格呈现了关于美国非裔历史、地理和文学传统的地图想象。小说中的地图元素将严肃的史实和诗意的寓言结合在一起,不仅实现了时空跨度较大的文学要素的重组融合,而且丰富了层次感与审美性,拓展了小说这一文学体裁的可能性。
“文学创作是一种绘图,是赋予世界形态的一种方式。”(Tally 2013:50)和真正的地图一样,小说展现的世界样貌——文学地图对作家和读者来说亦具有导向和促进认知的作用。作为文学地图的《地下铁道》既呈现了美国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也描绘了人物身份探索和欲望表达的历程,以便读者更好地理解历史上的奴隶制及其在现实生活中的影响,以及美国黑人寻找自由与正义的历史,从而把握小说和现实之间的平行关系,更好地思考美国的过去和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