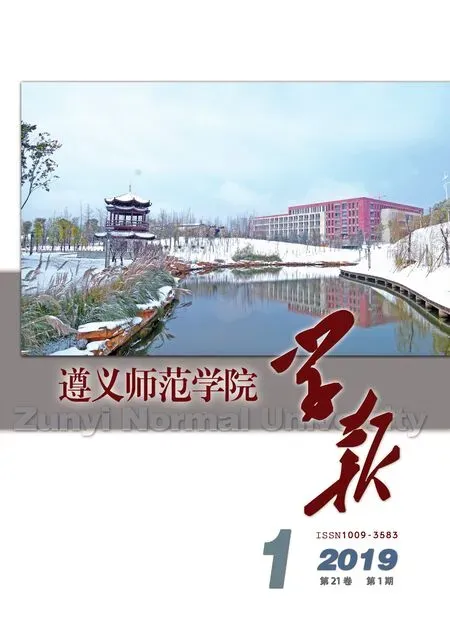从涓生看现代知识分子的心理禁闭
2019-01-28褚连波
褚连波
(遵义师范学院人文与传媒学院,贵州遵义563006)
《伤逝》是鲁迅唯一的一部描写爱情的小说,对于这部作品的研究成果集中于以启蒙为话语核心,以子君和涓生的爱情悲剧及其根源为研究对象,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几种:一种是结合时代氛围与鲁迅自身经历,分析社会环境对悲剧产生的影响[1];一种则着重分析子君和涓生的性格弱点,这种分析的结论认为子君的思想退化和对人生的狭隘理解以及涓生的懦弱是造成他们生活悲剧的根本原因[2];还有一种观点是认为鲁迅不是单纯的就爱情写爱情,而是借婚恋的悲剧表达一种和《孤独者》《酒楼上》等相似的主题,那就是一种普遍弥漫的孤独感以及鲁迅对逃离孤独之路的探索[3]。此外,一种不很普遍的观点是周作人在1963年的《知堂回忆录》中所说的对兄弟之情的哀悼,“《伤逝》不是普通的恋爱小说,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我这样说,或者世人要以我为妄吧。但是我有我的感觉,深信这是不大会错的。”周作人的说法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对于《伤逝》的研究,还有一类是从男主人公涓生的角度进行的。这类研究除了揭示子君与涓生爱情悲剧的成因之外,还从现代文化与精神分析的角度对涓生的心理与性格进行了详细的阐释,指出其在现代与传统交替的过程中,所呈现出的矛盾形象。[4]
《伤逝》这篇小说充满着无限的伤感和内心的酸楚,在情感意蕴上,《伤逝》是鲁迅小说中最接近《野草》的风格的,情感的极度压抑与宣泄使人阅读起来觉得难以呼吸。如果《伤逝》仅仅是对造成爱情或人生悲剧的社会的控诉,这样的情感显然有些过度,如果只是对兄弟反目的痛楚的描述,似乎又难以涵盖整篇文章的悲苦与激情,因为鲁迅是将人生最痛苦的生离死别的体验融入了《伤逝》的写作之中的。鲁迅是将对启蒙的反省和对知识分子(包括自身)的批判化为艺术形象融合到作品之中,在这个意义上,涓生的忏悔既是一种有罪的告解也是无罪的辩白,他的自我谴责建立在其自我真实性的袒露之上。《伤逝》中的子君和涓生在他们各自的人生轨迹上偶然相遇并放射出短暂的光亮,此后子君在悲凉中死去,涓生在迷茫中生活,其悲剧根源除了经济与社会原因之外,还有现代知识分子心理上的问题,即一种极端的心理禁闭。心理禁闭是人在缺乏安全感的环境中所产生的一种自我保护心理,是一种心理上的焦虑、自闭与自恋。
一、焦虑软弱
涓生逃避现实而又充满着愤怒的狂躁心理,他的习惯保留且善于保护自己的人格特征跃然纸上。《伤逝》的悲剧不仅仅是男人和女人的爱情或婚姻的悲剧,也不仅仅是孤独的启蒙者的悲剧,它是男性知识分子在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中的性格与人生的悲剧。在最初的示爱中,面对子君的“独立宣言”——“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涓生当时的反应是震惊,既震惊于子君觉醒速度之快,也震惊于子君的勇气。因此,在之后的生活中当他发现子君“勇敢”的背后是“虚无”之后,便放弃了对子君的爱与承诺。这是一种退守的策略,涓生时时强调的是子君所给与他的错觉,那就是他一直以为子君是一个坚强的可以承受一切的女性,和家庭决裂都不怕,何怕再次“出走”——放弃没有爱的婚姻(其实是同居)呢?直到子君死去,涓生还在逃避着责任。
在和子君的同居生活中,涓生潜意识里是有着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的,他缺乏勇气,没有担当,对现实不满却又无力改变。子君要和家庭决裂和他在一起追求自由的爱情时,他认为子君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求婚的情节中,他一直在回避自己对子君的最热烈的示爱方式,把跪下的行为看作是对电影镜头可笑的模仿,其实这是需要负责的承诺,这个行为也使子君误入歧途,使她坚信涓生对她的爱是最坚实的。涓生把婚姻的失败和职业的失去都归结于不合众意的同居亦即子君的不肯进取,其实是他逐渐厌倦了婚姻与工作,涓生对他逐渐厌倦的婚姻与早已厌倦的职业的失去,他都看作是子君的错,认为是子君不懂得人生的要义;他想摆脱子君又怕被子君质问,就拿出娜拉来鼓励子君走出无爱的婚姻,甚至主动要求子君抛弃自己。
《伤逝》中反复渲染的是涓生对整个感情事件的感受以及他的情绪变化,这种情绪变化不在于如何揭示了悲剧的根源,而在于这一事件不论是怎样的结局,它本身就是一种悲剧,如果局限于对情感悲剧及其根源的探讨,就无法走进鲁迅丰富的内心世界和他对于人的丰富性与矛盾性的理解。涓生并没有认识到自己性格中的弱点,当然也无法意识到自己的心理焦虑。他反复强调的说真话的后果,实际上是为他自己的懦弱与自私的一种开脱,他即使不说真话,按照他对子君的种种也会使子君陷入到精神绝望甚至崩溃的深渊,在他说真话之前他就已经杀死了一个曾经活泼的有着勇气和无畏精神的子君,一个除了涓生之外毫无依靠的女人。
涓生的性格弱点是他不敢或者无法正视自己的内心世界,虽然在子君死后他有过忏悔,但这种忏悔不过是他借以摆脱罪恶感的一种方式,他把自己的厌倦生活归咎于子君的改变:子君变胖了,子君的手变粗糙了,子君总是要回忆自己最不愿意记起的一幕,子君没有高尚的生活情趣,子君没有对生活更高的追求,总之子君不再是令他心动和爱慕的对象,甚至子君没有因为生活的苦恼而“瘦损”竟然也成为她的罪过。他把自己的失业也归咎于子君,但这样的失业竟然在他们同居几个月之后,这就不单涓生自己奇怪了。其实是涓生想要逃走了,但他最终发现即使没有子君,他的生活也不会有新的改变,新的道路只是他逃避现实的却又无法逃避时候制造的一个幻影。所以他会怀念有子君的日子,他在子君离去后竟然还会幻想子君会在某天不期然地来访问自己,但子君的死彻底断绝了他的退路,使他永远也不会再回到曾经充满希望的生活。
涓生并没有给予子君以切实的新生的希望,他最终感到那纠缠自己的新的生路却没有自己的一份,这是彻底的绝望和悲哀。涓生始终不敢正视自己的情感,他对自己的过高估计使他把子君对他的爱和眷恋当作他展翅飞翔的最大的障碍,他追求的是一种想象中的生活。但生活是实实在在的东西,虽然没有理由去谴责涓生对生活的梦想,但把别人作为牺牲对象,鼓励别人成为娜拉式的叛逆者,仅仅是凭借着一句“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又怎样去找到自由幸福的生活?一个男人尚且无法谋到职位,一个弱小的女子出走也就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肉体或精神的死亡)。涓生的忏悔也是他的焦虑情绪的一种表现,这种不满现状但又无路可去的悲哀是会纠缠他一生的情结,即使他可以忘却子君的死亡,他也仍然不会获得灵魂的安宁。普通的爱情悲剧的抒写难以达到如此的高度,鲁迅的深刻性在于他从涓生的自我辩解的所谓忏悔与自白中发掘了他灵魂之中的卑鄙和怯懦,发现了他的自恋自怜和自我迷失,涓生的焦虑与软弱也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心理问题的一种表现。
二、孤独自闭
鲁迅不是一个可以重复自己的作家,茅盾曾说过鲁迅是小说形式的先锋,其实鲁迅也是小说主题上不断创新的作家。《伤逝》这篇小说的形式很特别,一般的日记体小说是属于作者自传性质的,如果不是,叙事者是要负责交代日记的来源的,例如《狂人日记》,鲁迅就在序言中交代了这篇日记的来源,但是作为仅有的两篇日记体小说中的另一篇,《伤逝》却有意忽略了这一点,小说的副标题是“涓生手记”,而且在文章的开始部分有这样一句话,“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既然这是涓生的“手记”为什么又要使用“如果我能够”这样的假设句式?而且这篇小说在写成的那一年并没公开发表,而是作为小说集《彷徨》中的一篇收入集中,或者可以想象这并不是一篇纯粹虚构性质的文本,而是类似于讲述故事性质的复述性文本。
将这篇小说和鲁迅其他的双主人公叙事的模式相比较就会发现,涓生和魏连殳、吕韦甫甚至祥林嫂有着极其相似的心理特征,那就是强烈的倾诉欲望与这种欲望的受阻。在鲁迅的小说中都存在一个“我”,虽然这个“我”也常常陷入无话可说的境地,但对于魏连殳、吕韦甫和祥林嫂等人的命运还是有着同情的成分,也还可以勉强地敷衍几句,但在另外的一篇小说《头发的故事》中,面对N君的牢骚,“我”却自始至终没有说过一句话,因此可以把《伤逝》看作是旁观主体“我”的缺省的叙事文本。由于主人公涓生的激烈的情绪表达,使得作为叙事者的“我”无话可说,而这种无话可说,是由于涓生对于事件的叙述和自我谴责的言说的时间和空间的密度所决定的,也就是说在这样的文本中,容不下主人公思想流程之外的其他语言和思想的存在。《伤逝》是非常纯粹的密度性叙述文本,它是一个严密的心理空间,同时也是封闭的心理空间,这个空间又交叉着混乱的时间。在文本的叙述中,涓生的思维中会突然地出现子君的死,“我突然想到她的死”这样的句子意外地插入涓生对整个事件的叙述中,打乱了文本的时空秩序。子君的死是涓生心理上最难跨越的障碍,对于这样交织着“死亡”与“彷徨”(认罪的不确定性与忏悔的回转性)的事件不但是作为旁观者的“我”,就是作为读者的任何人都无话可说。
从文本的问题意义来讲,子君和涓生的情感悲剧实际上是一个新的生命被满怀希望地创造又被无情地毁灭的悲剧,这个悲剧既不是社会造成的,也不是周围环境的压抑造成的,更不是性格的懦弱和对生活的简单理解造成的,这是个无人负责的悲剧。涓生真情的忏悔使人感动,但是面对一个曾经热情鲜活的生命的消失,不是悔恨就可以释怀的,可以说子君的死亡是涓生永远的梦魇。
旁观者纵然没有权利谴责涓生对待爱情和婚姻时候的懦弱,但是却无法忽视他在面对责任时候的退缩。涓生常说的振翅高飞,是要在把子君这个对他而言的负担解除之后,那么在认识子君之前他何以就不能飞翔呢?涓生对子君所说的“携手同行”其实也是虚妄的,他自己都未必清楚。涓生一生都会在一种追逐的行程之中,得到了就会厌倦了。他用幻想来逃避现实,用子君来驱赶空虚,他没有确实的行为准则没有确定的人生目标,他无法脚踏实地像子君一样地生活。
《伤逝》中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场面——涓生在向子君求婚时下跪,对于这个场景两个人有着不同的理解:子君认为这是涓生向自己表示了最热烈最真挚的爱情,因为一个男人为了表达自己的情感竟然会采取最极端的方式;但对涓生而言这却是最可笑的行为,因为这意味着没有说出口的最庄严的承诺。这是一种认识的错位,而就是这种错位预示了他们不可挽回的情感毁灭的悲剧。种种事件的上演都在封闭的空间之内——会所与赁屋,但这个封闭的空间其实是对涓生自闭的心理与性格的一种暗示,当子君的到来打破这种封闭,将涓生从会馆带出,涓生又因为恐惧而逃回会馆。
三、自恋自怜
《伤逝》中涓生最显著的性格特征是焦躁和不自信。他几乎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即使是在会馆中和子君交往的日子也不见他和什么样的朋友或同事往来。他是一个寄居异地的漂泊者,会馆就是提供给那些在外地谋生而居无定所的人暂时的栖身之所,因此涓生比子君更身感着极大的寂寞和空虚。他在不同的人生阶段用不同的方式来排解自己的寂寞,书籍、爱情和幻想以及心灵忏悔。排解的方式最初并不是以爱情的形式出现,而是他暂时充当了一个思想启蒙者,这启蒙的对象给了他无限的欢乐和极大的自信。可以说是子君的反应暂时满足了涓生对于被他人承认的欲望,也许在那样的环境下,除了子君不会再有第二个人对涓生怀着如此崇拜的情感和由此而来的爱恋,子君满足了涓生需要被肯定的欲望,这种欲望始终贯穿于文本之中。涓生有着传统知识分子怀才不遇的愤慨,他的自我欣赏与自恋自怜是他悲剧性格的核心。
鲁迅在作品中并没有交代子君为何离开父亲的家而来到叔叔的家,但是可以知道的是,子君是一个受过新式教育的女子,但她同时具有传统的淑女风范与勇敢无畏的现代精神,对雪莱的半身像都不敢正视的她却能够与人私奔而毫不畏惧流言,能够说出“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样的话,也能够在同居生活中努力做一个贤良的妻子。那句话使涓生震惊更使他深陷入自大的夸张的想象之中——他竟然会认为由此可以见出中国妇女的可以拯救,却不知道子君是因为爱而勇敢无畏。涓生的欣喜可以说是来源于对自己能力的过高估计,那就是他终于不再是一个天赋颇高却陷入平凡普通境遇的人。涓生爱上子君其实是爱上了自己,因为只有这个时候,他才能够从子君的身上找到自我肯定的信心,找到自我力量的确证,由此而来可以推断,一旦这种内在的缠绵之情随着时光无情地消散,那么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爱情也将消失。
涓生爱子君其实也就是爱他自己作为创造者的身份,他从子君决绝的态度和昂然无畏的姿态上似乎看到了前途的光明,这光明的希望是子君给与的——一个尚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徘徊的女子,都能够无畏地走自己的路,那作为导师的涓生的欣喜是可想而知的。涓生渴望着社会的承认与赞扬,当他和子君一同走路时,他畏缩的表现与其说是一种懦弱,不如说是一种对外在世界规则的趋同。涓生并不想做一个与世隔绝的人,更不想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在他的内心世界中孤独与不爱肯定是他最难以忍受的空虚,他怀念和子君在会馆中的争执,他在子君离去之后去找久已没有交往的世伯,他注重朋友的冷和子君的冷,都说明了他对热闹生活在潜意识中的肯定。涓生幻想的摆脱子君之后的生活,虽然是高贵与低贱混杂的梦幻,但也是一种充满着热气的生活,成为不会被时代抛弃不会被时代遗忘的角色是他的追求。
渴望和社会与人们的期待保持一致是所有人的追求,一旦人感觉到自己脱离了人群,陷入孤独甚至与他人敌对的境地,就会在心理上感到焦躁不安,“我们成功地说服自己做决定的是我们自己,而事实上,由于惧怕孤立,害怕对我们的生命、自由及舒适的更直接威胁,我们与别人的期望要求保持一致。”[5]涓生和子君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在心理上对于社会承认的渴望程度不同,对于婚姻的理解不同。涓生把爱情、婚姻看作是拯救与鼓励,他认为婚姻是可以携手前行的路;子君却把自由的爱情看作通向美满婚姻与幸福的路,她认为这场婚姻就是终点,对于爱情与婚姻的认识错位,来源于他们对于爱情与婚姻的不同的心理期待,也源自于他们不同的性格。子君善于为别人牺牲,她的世界只有涓生和涓生对她的爱,如果失去了这两者之一,她都会丧失生活的目标,会丧失精神的支柱,她的坚决的宣言也是为了获得和涓生在一起生活的权利和自由。涓生是了解子君的,他说子君的勇敢是出于爱,就是他看清楚了子君并不是解放了的、觉醒了的女性的代表。除了爱情子君并没有清醒的自我概念,缺乏自我表现和自我认知的能力,她习惯于牺牲自我,并把这种牺牲的本身看成生活应该有的意义。涓生厌倦的是一种固定不变的、无法与外界交流的生活,爱情的新鲜一旦消逝,他就必然要去寻找另外一种生活来弥补空虚的心灵。涓生常常不满于生活,但又无力改变周围的环境,因此他只能在小范围内改变自己的生活,向子君宣讲新的道德观念和文学家的诗文与生活,这是一种逃避现实却又肯定自我的方式,和子君恋爱使他暂时逃离了空虚,几个月幸福的婚姻生活让他可以抗拒工作的乏味和无聊。涓生的爱不是一种纯粹的精神之恋,而是一种手段,当他一旦发现这种手段无法达到他想要的目的——自由、充实与被肯定之后,他内心深处的激情就会很快冷却并且无可挽回。
涓生在人生的道路上面临着诸多的生活与心理的困境:婚恋自由后的经济与精神的痛苦,事业(在职无聊与失业困苦)的抉择以及对生命与未来的不安。涓生不满于现实却又无路可走,他试图挣扎改变自身的困境,但结局却是子君在他人的冷眼中死去,自己最终也失去了如魏连殳(《孤独者》)与吕纬甫(《在酒楼上》)似的苟活者的资格。涓生与巴金、老舍以及沈从文笔下的男性形象,有着强烈的谱系关系,纵观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无论是男性作家还是女性作家,其笔下所塑造的女性形象,相对于男性而言,其精神与肉体大多具有健康的色彩,她们乐观、坚韧,尤其是在家庭中担当了绝大部分的责任,她们敢爱敢恨,她们自强自爱,她们在苦难中支撑起家庭的天空。鲁迅通过爱情悲剧的书写,为我们描述了传统与现代纠结中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心理上的迷茫与彷徨,尤其是男性知识分子责任感的缺失与行动力的匮乏。
1919年,胡适创作了戏剧作品《终身大事》,剧中收到陈先生纸条(“此事与别人无关”“你该自己决断”)鼓励的田女士毅然收拾了金银细软,坐了陈先生的汽车私奔了,似乎只要有勇气能决断,自由恋爱进而私奔同居就必然会有欢乐的结局。1925年,鲁迅创作了《伤逝》,其中的子君和涓生却是除了爱情和勇气以及鸡肋般的工作之外别无其他,更别说汽车和细软了,悲剧的结局似乎在相爱之前既已注定。但有自由恋爱又有经济基础就必然幸福么?这似乎是古往今来的世界性问题,是超越了时间与空间的人类的普遍困惑。《伤逝》是一部充满诗意与悲情色彩的爱情小说,子君的死亡与涓生的消沉有社会原因,与涓生的心理禁闭也有密切的关系,这种禁闭使他敏感却又缺乏行动力,使在他终于勇敢地伸出触角却不断碰壁后,又缩回了丰富而疯狂的内心世界,自我禁锢自我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