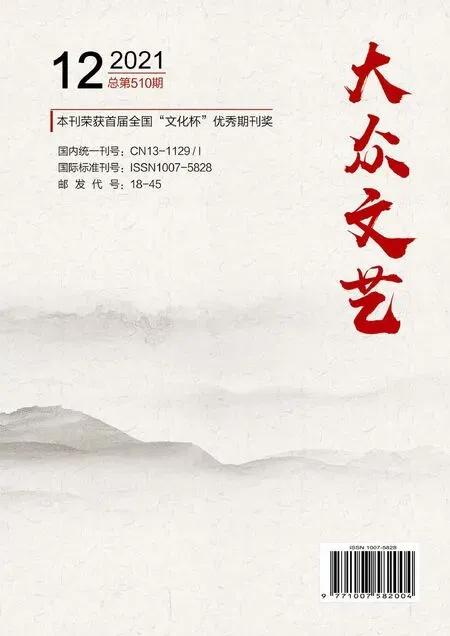对父权体制的消解与颠覆
——论李碧华“吃”系列小说的批判主题
2019-01-27江南大学人文学院214122
(江南大学人文学院 214122)
针对李碧华本人及其作品的研究,一直存在着严重对立的两极分化。一方面,因其作品多涉及痴男怨女、情爱纠葛,传统学者倾向于把她归入言情作家之列;另一方面,也有学者从文化角度出发,视其作品为文化反叛的精英文学。在笔者看来,李碧华的小说确实有迎合市场的成分,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中也掺杂着知识分子自觉的文化批判意识。她的“吃”系列小说1便依托了男女情爱纠葛的皮囊,抒发了对传统父权体制的批判之情。李碧华从丑化男性形象和描摹女性压抑扭曲的人生两个角度出发,对父权体制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和颠覆。李碧华之所以采取这两种批判视角,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此外,作家本身的家庭背景、成长经历也是影响其写作方式的重要因素。
一
李碧华的“吃”系列小说用浓淡不一的笔墨描绘了五个女人的故事。虽然她们的社会角色、人生境遇各不相同,但都呈现出女性在男权社会倾轧中艰难困顿的生存境遇和扭曲变异的情感结构。因此,批判传统父权体制,解构男性主体话语的强势地位是这五部小说最核心的主题思想。而作家如何让这一批判主题在小说中得到力透纸背的展现,是文章接下来要讨论的重点。
这五部中短篇小说对父权体制的解构主要通过对男性——尤其是父亲形象的丑化展现出来。这些男性形象在精神或身体上都有兽欲、贪婪、猥琐的特征,失去了父亲权威,由此揭露出父权社会淫靡的本质,从而形成对父权体制的正面批判。在《吃卤水鹅的女人》中,父亲谢养虽身材健硕,长得英挺,但性欲泛滥,先是不顾母亲的哀求强行同房使其流产,后来又借生意之由在大陆包养情人。前者是父亲为发泄兽欲对母亲身体上的折磨,后者是其贪婪本性对发妻精神上的背叛。此外,父亲对女儿暧昧不明的态度使父亲权威进一步崩塌。父亲经常“亲我,用胡子来剌我,洗澡时又爱搔我痒”,这也许可以看作父亲对女儿天然的亲近和喜爱,但“我”越长越大,母亲不准父亲给“我”洗澡时却受到阻拦,“怕什么?女儿根本是我身体的一部分。我只是‘自摸’”2。显然,在谢养看来,女儿是自己的所有物,自己当然有行使任意行为的权利。有时候喝醉了,他会用“一张臭嘴来烘我。长大后,我也能喝一点,不易醉,一定是儿时的熏陶。想不到三岁童稚的记忆那么深沉”。表面上谢养的行为并没有给女儿带来任何实质性的伤害,但他的“过分”亲近无疑给女儿幼小的心灵罩上一层阴影,或许成为潜藏在她内心深处的心理障碍,对其成长产生负面影响。尽管李碧华在这个故事中对父女间暧昧不明的关系只一笔带过,但这看似无足轻重的描写却使父亲形象走下高大、庄严的神坛,不可避免地沾染了猥亵的成分。
在《吃婴胎的女人》中,父亲对女儿意味不明的态度直接转变为明目张胆的强奸行为。十五岁的小琪怀有五个月的身孕,却始终不肯说出那个男人是谁。在母亲的逼问和猜测下,发现将小琪强暴成孕的竟是她的亲生父亲。“过年那会儿我到将军澳替工倒垃圾,他搞你吗?那个衰人,又失业,又没钱叫鸡,是他搞你吗?你肚里头是他的孽种吗?”,随着母亲惊讶、愤怒、绝望的再三诘问,猥琐、无能、堕落、禽兽不如的父亲形象跃然纸上。
除了对男性形象性欲泛滥和不伦关系的书写,李碧华在文本中还倾向使父亲角色直接缺失于小说主人公的成长过程中。比如《吃眼睛的女人》中,一直都是“我”与母亲、姐姐相依为命,生活中、回忆里并不见父亲的踪影,直至小说的后半部分,才用寥寥数语提到父亲于三年前辞世,算是给父亲角色做了一个简之又简的交代。又如《吃燕窝糕的女人》中,一直都是赵品轩与母亲的来往和对话,父亲从始至终都未曾露面,未曾有过片语只言。父亲形象在主人公的人生中是模糊的、缥缈的甚至可有可无的,通过弱化或者直接忽略父亲在小说中的作用达到消解男性话语权利的目的,这是区别于直接丑化父亲形象的另一种言说方式。
总而言之,在李碧华笔下,父亲形象成了性欲泛滥、猥琐无能甚至禽兽不如的代名词,又或者直接缺席主人公的人生,构成“无父文本”的书写,将男性家长放逐在文本之外,丑化和缺失的父亲形象直接消解了父亲权威,构成对父权体制的正面批判。
二
除却对男性形象的正面批驳,李碧华还通过展现女性在父权社会中被压抑被扭曲的宿命,完成对父权体制的侧面批判。她们虽然同在父权社会下艰难求生,但面对威逼压迫时却呈现出不同的姿态:一种毫无反抗之力,完全沦为父权社会的牺牲品;另一种在重重压迫下扭曲变异,成为父权社会秩序的施行者、维护者,甚至主动利用父权社会规则达到自身目的;又或者彻底毁灭、放逐男性,建立起一种极端的、不正常的女性主体意识。
第一种类型的女性是毫无反抗之力的牺牲品。她们多处于意识和行为还没有发育成熟的少女阶段,完全寄生和依附于男性,尤其是父亲身上,这就从根本上为她们的悲剧命运埋下伏笔。《吃婴胎的女人》中,十五岁被兽父强暴成孕,堕胎手术后血流不止、死于非命的小琪便是父权体制下单纯的牺牲品。面对父亲的残忍兽行,她只能一边颤栗一边承受,面对母亲歇斯底里的诘问,她只是沉默,深深地沉默。“父亲压在她身上时,一边喘息一边威胁:‘不准告诉妈妈。很快完事的,如果妈妈知道我就斩死你!’”,我们在对小琪遭遇的一切感到惊讶、恐惧、愤恨之后是深深的无力感,在强势的父权体制牢笼中,女性永远是作为他者的沉默群体,所有的挣扎也只是无谓的困兽之斗。《吃眼睛的女人》中,“我”的高中同学田岛千裕同样处于牺牲品之列。她因遭受继父强奸而退学,身体和心灵的双重创伤使这个原本天真烂漫的女孩自甘堕落,踏上“援助交际”的灰色道路,在各色男人的倾轧下周旋求生,绝望是延绵不绝的。
第二种类型的女性则是父权体制压迫下的顺应者。她们努力迎合男权社会为自己设立的价值标准,甚至主动利用规则达到自己的目的。吃婴胎的女人——艾菁菁就是如此。不再青春靓丽的她为挽回丈夫的心,不惜花高价吃婴胎做成的饺子。她从一开始面对饺子时的惊惧恶心到后来的品咂享受,思想障碍的突破和转变充分显示出女人对于青春的变态迷恋和向往。不过青春逝去纵然可叹,但人们仍有智慧的沉淀和情感的支撑,何以变得如此畸形扭曲、丑恶毒辣?究其原因,自然便揭露出女性依附于男权社会,不得不以男性审美标准来束缚奴役自己的可悲命运。西蒙·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说到:“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在生理、心理或经济上,没有任何命运能决定人类女性在社会的表现形象。决定这种介于男性与阉人之间的、所谓具有女性气质的人的,是整个文明。”这句话意在表明,女人在生理构造上区别于男性是她的自然属性,但女人的社会属性却是由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文化传统规定和赋予的。什么是女人,怎样做好一个女人其实暗含了男性社会对女性的规约和期许。在这样的父权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女性很容易形成一种自我认同,她们会认为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的,她们生来就必须要遵循三从四德,要温良恭俭让,要迎合男性的审美和要求。“父权制对女性的性别期待经过社会化已为女性所内化,成了女性生存的必备知识”。于是,女性逐渐在男权社会中彻底放弃本真自我,以男性为中心展开自己的生命。菁菁的一生不就是被“正统”男性审美价值肆意歪曲的惨剧吗?
被男性社会背弃的女人,有的通过极力迎合男权社会的价值标准使自己再度“得宠”,有的则走向血腥复仇的极端,在“杀夫”中得到变态满足和安慰,这便是第三种类型的女性——父权体制下的“复仇者”。在《潮州巷·吃卤水鹅的女人》中,母亲为了阻止父亲抛妻弃子,竟然用计将父亲肢解杀害。她“刀起刀落,刀起刀落。把爸爸一件一件一件……地,彻底分批搬进那一大桶卤汁中。他雄健的鲜血,她阴柔的鲜血,混在一起,再用慢火煎熬,冒起一个又一个的泡沫与黑汁融为一体”,恶心、惊惧、浓厚的诡异感从后脊梁骨森森细细地爬上来。母亲那样一个温柔、坚韧、肯为爱义无反顾的“好女人”,何以会做出如此癫狂的行为?是谁逼疯了她,逼迫她一步一步走向杀戮、变态、血腥的复仇深渊?是那个负心的男人,是那个负心男人背后的男权社会体制。出人意料的是,作为女儿的“我”在目睹了母亲杀死父亲的全部过程后,不仅没有愤怒惊惧,反而对母亲表示出一种深深地理解,这种理解是男权体制倾轧下女性复仇心理的交接和延续,不难想象如果女儿结婚后遭遇丈夫的背叛,她将会以何种可怕的方式为自己讨回公道?
面对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倾轧和背弃,她们或是毫无反抗之力的牺牲品,或通过各种极端方式迎合男性价值准则重新得宠,又或者回过头来复仇,手刃深爱却背弃了自己的男人,并且干脆不再相信感情,认为“女人到头来也不过是倚仗自己”,靠得住的只有金钱。这其实是一种矫枉过正,是父权体制压迫下女性的过度反弹。这种反弹并不意味着女性独立自主意识的确立和被认同,反而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三
由文章前两部分可知,父权社会为女性设立的一切价值准则自女性出生开始就对她们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并逐渐渗透到女性生命的方方面面。然而,从父女间不伦关系和女性杀夫复仇的角度出发批判男权可谓是剑走偏锋,李碧华为何选取这样极端的视角对男权体制进行批判和揭露呢?归根究底,与她所处的时代、社会背景以及自身经历息息相关。
首先,“父女乱伦”和“女性杀夫”这两种极端批判视角的选取与香港当时的商业化文学环境密切相关。李碧华的创作集中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此时香港的服务业和商品经济迅速发展,文化上也产生了以商品化为特征的大众消费文化,通俗文学的势头蒸蒸日上,严肃文学反而退居边缘。众多作家处在这种商业化的文化大势下,便不得不根据市场的需求调整自己的创作,在商业价值和文学价值之间谋求一种平衡。都市男女、情爱纠葛的皮囊在香港商业文化环境下是不得不披的,这是作家吸引读者、维持生存的必要手段,而在皮囊下潜藏的批判男权体制的灵魂核心,则是作家对作品文学价值的追求。不过,雅俗兼具的原则既然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如何使自己的作品在纷繁驳杂的同类型小说中脱颖而出,是李碧华需要关注的问题。显然,“父女乱伦”和“女性复仇”无疑是一种不错的噱头,这种极端的写作角度可以作为小说的“商业卖点”之一。
其次,西方文学思潮的传入和女权主义运动的兴起也是影响作家选取批判角度的重要因素。一方面,作家对于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等思想有了更加清晰的认知,为自身的创作建立起强大的思想背景和理论支撑;另一方面,随着香港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女性的教育水平和就业率逐渐提高,这使她们的身份和角色发生重大转变,给了女性重新审视自我、评价自身生命价值的机会。同时,在逐步走向社会的过程中,女性时常遭遇着男权传统遗留的问题和商业环境下新的社会规则,如何运用新的写作角度批判新的社会矛盾是香港作家们亟待解决的问题。“父亲强奸女儿”的视角不仅是批判传统男权的一柄利器,也映照了商品经济繁荣下香港社会的价值混乱和道德沦丧。“女性杀夫”的批判角度不仅张扬了女性的主体精神,同时也对女性的人性进行了更深的开掘。因此,李碧华这两种批判视角的选取是西方文学思潮和香港女性运动合力影响下的大势所趋。
除了大的社会背景和文学思潮的影响,李碧华的家庭背景和生活经历也为其创作视角的选取奠定了基础。李碧华的祖父是广东人,有四个妻子,还有侍妾。封建大家庭的生活环境让李碧华对女人之间的勾心斗角、女人最终逃不脱的悲凉命运最熟悉不过了。这为她的作品积累下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也使她形成对中国传统文化糟粕、传统父权体制弊端的深刻认识。除此之外,李碧华从事的职业也为她选用这两种极端视角提供了便利。李碧华定居香港后,做过记者、编剧、专栏作家等职业,很明显,开放性、流动性、多样性是这几种职业的共通点,这无疑使她有机会接触更多、更复杂的社会现实和文学资源。记者的职业使她有更多的契机可以看到深埋在社会底层的阴暗面,从中窥见人性的罪恶与深刻。编剧和作家的身份又使她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运用妖媚凄艳的个人文字把搜集来的素材连缀成驳杂吊诡的小说文章。
四
总而言之,批判父权体制的思想一直是李碧华小说表现的重心,丑化和放逐男性形象、描绘以女性为中心的压抑人生的手法也不仅运用在“吃”系列小说中,在她其余的作品中也有体现。如《潘金莲之前世今生》中的潘金莲,《胭脂扣》中的如花等等。在李碧华的笔下,叙述的重心聚焦在了女性身上,通过彰显女性的感官意识、弱化男性角色地位的手段,有意识地打破男尊女卑的思想窠臼。又或者把男性角色刻意塑造成贪婪、猥琐、无能、兽欲泛滥的形象在文本中展览呈现,形成对男权权威更为直接的消解和颠覆。如薄情寡义的十二少,贪恋风月的许仙以及道心不坚的法海。这种批判视角的选取是李碧华个人写作特色与特定时代、社会环境融合的结果。
纵观内地对于李碧华的研究,总体上还处于一种相对薄弱的状态。在目前较为主流的几本文学史教材中,或是对李碧华根本无所涉及,或是简单地将其归入言情作家中一笔带过。近些年来对于李碧华的研究虽然有所改观,但仍存在着许多问题,如研究资料不足、研究角度过于陈旧等。而在港台及海外的李碧华研究中,则存在着较为鲜明的两级分化:或是简单地将其划入通俗言情之列,或是从文化角度将其作品定位为精英文学。笔者认为,李碧华小说所呈现的浅白、猎奇甚至吊诡的风格的确具有通俗文学的属性,但这些迎合市场的成分不应看作其创作上的巨大局限,这是独特的时代、社会环境对作家创作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影响,不但没有使她的作品“降格”,反而因此形成了小说中雅俗共赏,商业价值与文学价值兼具的特色,这是不同时代对于文学本身不同的馈赠。也正因如此,在通俗性的皮囊下,李碧华对性别的书写描绘、对男权意识形态的质疑否定、对西方文学理论的运用收编,更加值得学者们进行更深的开掘。
注释:
1.“吃”系列小说:《潮州巷·吃卤水鹅的女人》、《钥匙·吃燕窝糕的女人》、《寻找蛋挞·吃蛋挞的女人》、《猫柳春眠水子地藏·吃眼睛的女人》、《饺子·吃婴胎的女人》。
2.本文对小说原文的引用全部出自[1]李碧华.饺子[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此后出现不再做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