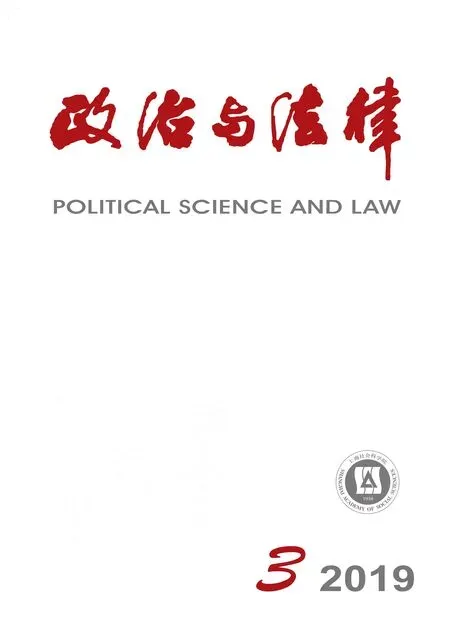敲诈勒索罪中“被害人处分必要说”之辨析
2019-01-26蔡桂生
蔡桂生
(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北京100872)
被害人处分,又称被害人交付,在我国刑法学中,经常被认为属于敲诈勒索罪成立的必要要素。王作富教授认为:“采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目的是迫使他人交付财物。亦即行为人的上述行为与他人交付财物之间,必须存在着直接因果关系。如果交付财物不是受到威胁或要挟的结果,不可能构成敲诈勒索罪。”①王作富:《侵犯财产罪》,载高铭暄主编:《新编中国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04页。赞同王作富教授观点的有刘明详、尹文建等,参见刘明祥:《财产罪比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97-298页;尹文健:《敲诈勒索罪》,载赵秉志主编:《侵犯财产罪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431页。张明楷教授认为:“敲诈勒索表现为使用……胁迫手段使对方……处分财产,使行为人或者第三者取得财产。处分财产的人必须是被胁迫者。”②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017页。劳东燕教授指出,正是处分行为的存在,使得敲诈勒索罪区别于违反被害人的意思而取得财物占有的盗窃、抢劫等夺取型犯罪。③参见劳东燕:《敲诈勒索罪》,载陈兴良主编:《刑法各论精释》(上),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578页。与劳东燕观点类似的学者有车浩、邹兵建、郭泽强等,参见车浩:《抢劫罪与敲诈勒索罪之界分:基于被害人的处分自由》,《中国法学》2017年第6期;邹兵建:《交通碰瓷行为之定性研究》,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判解》(第12卷),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100-101页;郭泽强:《敲诈勒索罪》,载马克昌主编:《百罪通论》(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74页。
这一要素是否真的必要呢?我国《刑法》第274条(敲诈勒索罪)规定:“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该法条中并没有“处分”或“交付”的明文表述。因此,“究竟需否以被害人处分作为敲诈勒索罪成立的必要要素”这一问题,仍需从理论上加以解答。以下,笔者将首先基于比较法的视角,在一般学理上对被害人处分是否必要进行研讨并作出判断,之后再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对此问题加以针对性的处理。
一、关于被害人处分是否必要的正反意见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刑法学界大量地引入了日本刑法的知识。在这种条件下,可以参考一下日本刑法学如何回答被害人处分是否必要这一问题。《日本刑法典》第249条(“恐吓罪”)(对应于我国的敲诈勒索罪)规定“恐吓他人使之交付财物的,处十年以下惩役”。该条中出现了“交付”的字眼,而此处的“交付”即为“处分”。由于法条中明确限定了以“处分”为必要,且恐吓罪与诈骗罪同列于该法第37章,在日本刑法学说上均要求恐吓罪的要件之一是被害人处分财物,没有争议。④参见[日]大塚仁:《刑法概说(各论)》,冯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08-309页。不过,自21世纪以来,除了日本刑法的知识,德国刑法的文献也逐步为我国学界所了解。与日本的情况不同,《德国刑法典》第253条规定的勒索罪则是以“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地获利,违法地使用暴力或以带有明显的害恶的威胁,强制他人为一定行为、忍受或不为一定行为,因此使得被强制者或他人遭受财产损失(处五年以下的自由刑或罚金刑)”为其内容。这种表述和我国《刑法》一样,都缺乏“交付”或者“处分”的字眼。这就使得德国(而非日本)的情况,成为我国研究者应当关注的对象。⑤车浩在相关论著中提到德国经验,但未对德国经验深入分析。参见前注③,车浩文。与德国类似,同样不以“交付”或“处分”作为敲诈勒索罪之要素的,还有《奥地利刑法典》第144条(参见《奥地利联邦共和国刑法典》,徐久生译,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60页)、《丹麦刑法典》第281条(《丹麦刑法典与丹麦刑事执行法》,谢望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1页、第214-215页)、《越南刑法典》第135条(《越南刑法典》,米良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7页)。
在法条没有规定“交付”或者“处分”的字眼的德国刑法中,被害人的任何行为(作为、忍受、不作为)皆可以成为强制的结果和勒索罪中财产损失的中介。有鉴于此,成立勒索是否需要被害人的处分行为呢?在德国,判例和多数观点认为,构成勒索不必以被害人处分为要;⑥Vgl.Kindhaeuser,Strafrecht Besonderer Teil II,2008,§17,Rn.23 ff.;LK-Vogel,2010,§253,Rn.13 ff.少数观点则主张,勒索以被害人处分为要。⑦Vgl.Wessels/Hillenkamp,Strafrecht Besonderer Teil II,2010,Rn.712 f.
这两种观点在德国司法实务中的区别,体现在暴力抢开他人汽车的案件之中。按照前一种观点,当被告人以暴力抢开被害人的汽车一阵子之后,又将车辆返还给他,直接成立抢劫性勒索(处罚较重)。⑧《德国刑法典》第255条(抢劫性勒索)规定:“如果勒索是用针对人的暴力或者在使用带有对身体或生命的现时危险的威胁之下实施的,对行为人处与抢劫者同样的刑罚(一年以上自由刑)。”Strafgesetzbuch,Beck-Texte im dtv,2009,S.127.根据后一种观点,抢开他人汽车的,由于缺乏交付或者处分,不构成抢劫性勒索,同时,因为缺乏非法占有的目的,也不构成抢劫,而只能构成强制罪和未经许可使用交通工具罪(处罚略轻)。⑨《德国刑法典》第240条(强制)规定:“非法用暴力或以明显的恶行相威胁,强制他人为一定行为、忍受或不为一定行为的,处3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刑。”第248条b(未经许可使用交通工具)规定:“违背权利人的意愿,擅自使用其汽车或自行车的,若该行为未在其他条款规定更为严厉的刑罚的,处三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刑。”Strafgesetzbuch,Beck-Texte im dtv,2009,S.123,126.德国的自由刑最短为一个月,这使得成立强制罪和未经许可使用交通工具罪通常而言比成立抢劫性勒索处罚更轻。除了实务上的这一区别外,在德国刑法学中,这两种观点还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讨论。
(一)“被害人处分不要说”的主张及其理由
在德国,主张被害人处分不是成立勒索罪的必要要素的,是判例和部分学说(多数观点),其理由如下。
第一,在德国刑法史上,勒索罪是从抢劫罪中发展起来的,其担负着填补抢劫罪的漏洞的任务,并且,在当今的《德国刑法典》中,勒索罪与抢劫罪被置于同一章,而不是与诈骗罪被归为一类。《德国刑法典》第255条规定的抢劫性勒索的处罚,也是指向抢劫而非其他罪名。可以说,德国刑法发展史说明,勒索与抢劫之间是补充法与基本法的竞合关系,而非互斥关系。⑩Vgl.SK-Sinn,2010,Vor§249,Rn.16.
第二,德国刑法不仅保护绝对权免受外界直接的侵害,而且也保护相对权免受外界直接的侵害,比如,《德国刑法典》第289条规定的抵押品的取回(“为了所有人的利益,而以违法的意图从用益权人、质权人、使用权人或留置权人处取回他自己的或他人的动产,处三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刑”),便是如此。⑪gl.Kindhaeuser,Strafrecht Besonderer Teil II,2008,§17,Rn.26.所以,那种认为“勒索罪由于保护的是(包括相对权在内的)整体财产,也就不能像绝对权所享受的免于自外向内之侵害的刑法保护那样,而只能通过阻止自内向外的处分来实现刑法保护”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第三,要求成立勒索以被害人处分为必要,是将勒索罪的犯罪结构理解成诈骗罪那种(类型化的)间接正犯结构。在诈骗罪的场合,被告人以间接正犯的形式对被骗者进行操纵,从而使得被骗者沦为被告人的行为媒介,基于此,操纵他人“自我损害”便应认定为“他人(即被告人)实施的损害”而受到诈骗罪条款规定的处罚。如果将勒索罪类比于间接正犯式的诈骗罪,那么被告人以轻微暴力的方式直接侵犯被害人财产,就会因为没有借助被害人之手间接侵犯其财产,进而缺乏被害人处分这一必要要素,而无法成立勒索罪了。并且,将勒索罪类比于诈骗罪是有问题的,因为诈骗只能以间接正犯的方式展开,以直接正犯的形式来欺骗对方,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告诉对方要侵犯其财产的真相,就无法诈骗了。这种间接正犯结构是诈骗这一犯罪行为所独有的,不是财产犯罪所共有的特性。强制罪既可以以间接正犯的方式(以暴力相威胁或者胁迫),也能以直接正犯的形式(“暴力”或“绝对的力量”,absolute Gewalt)实施,所以,没有理由如诈骗罪那样,将勒索罪限制在间接正犯式的行为之上。⑫Kindhaeuser,Strafrecht Besonderer Teil II,2008,§17,Rn.29 ff.
第四,《德国刑法典》勒索罪罪状中的“忍受”应解释为缺乏处分意思的情形。该法典第240条强制罪的结果,包括由暴力(即绝对的力量)所造成的“忍受”,而其第253条勒索罪由于使用了与第240条相一致的文字表述(“忍受”),也就应当采取前后一致的解释。“暴力”造成单纯的“忍受”是没有处分意思的。⑬这是赫德根(Herdegen)在《莱比锡刑法典评注》中的观点。Vgl.Kindhaeuser,Strafrecht Besonderer Teil II,2008,§17,Rn.24.“忍受”包括“忍受他人的拿走”之意,而“拿走”正意味着被害人没有交付的动作。⑭Vgl.BGHSt 25,228;LK-Vogel,2010,Vor§§249 ff.,Rn.57.
第五,如果勒索须以被害人处分为必要,就会导致在暴力强开汽车这种凭借“绝对的力量”侵害财产的案件中,既不成立抢劫(因为缺乏非法占有的目的),也不成立抢劫性勒索(由于缺乏财产处分),而如果被告人采取更缓和的手段,比如以暴力相威胁或者施加加重的胁迫,从而使得对方交付财物,那就可以依照《德国刑法典》第255条处以和抢劫罪一样的刑罚,严重之情形下甚至可以适用“严重的抢劫”(第250条)乃至“带有死亡结果的抢劫”(第251条)这些罪名的刑罚。⑮Kindhaeuser,Strafrecht Besonderer Teil II,2008,§17,Rn.28.这是对使用更为严重的暴力手段的行为判处轻刑,而对采用更为缓和的行为手段的情形判处重刑,属于罪刑失衡。
第六,若要求以被害人处分为必要,就会使得以“绝对的力量”(即“暴力”)撕毁债务凭证或乘坐出租车下车时不买单直接暴力夺路而走这种以暴力逃避债务的行为无法成立(处罚更重的)勒索罪,而只能论以《德国刑法典》第240条强制罪。⑯持枪拒付出租车费的案例,见BGHSt 25,224(227 f.)。
(二)“被害人处分必要说”的主张及其理由
在德国,主张成立勒索罪需要被害人处分的,主要是部分学说(少数观点),其理由如下。
第一,德国立法体例区分“针对物的犯罪”(Eigentumsdelikt)和“针对财产的犯罪”(Vermoegensdelikt)。前者如盗窃、抢劫,其对象只针对有体动产,这类有体动产可以呈现固态、液态和气态,但电力这类能量则不包括在内。后者如诈骗,针对的是有经济价值的财物及财产性利益。在“针对财产的犯罪”中,总是以进入到财产受损者的财产领域之内,从内部掏走其财产(即间接侵入财产)作为其表现形式的。被告人要么利用本属于被害人财产领域的某个犯罪工具(如在诈骗案件中),要么是自己就身处于被害人的财产领域之内(如在背信案件中)。刑法只在面对绝对权(对世权)时,以特定方式提供保护以免受到他人从外界直接入侵受损失者财产领域,⑰这是萨姆森(Samson)在其著述中提到的。Vgl.Kindhaeuser,Strafrecht Besonderer Teil II,2008,§17,Rn.36.而勒索乃是针对整体财产的犯罪,其侵犯对象包括相对权(对人权),所以其构成要件像诈骗罪一样,以财产处分这一形式的受害人加功为必要,并以从内部掏取受害人财产作为其构成要件的特征。
第二,要求勒索必须以财产处分为必要,并不意味着在《德国刑法典》第253条中采用与第240条强制罪中不同的“暴力”概念。要求勒索在构成要件上必须具备财产处分要素,不会影响到“暴力”的界定,不会(在理论上)导致产生一个限缩了的“暴力”概念,而只是会将施加暴力的特定情形,从勒索构成要件中排除出去,并且,在德国的普通法时代和德国以前多数的诸侯国法典中,“绝对的力量”(即“暴力”)并不是勒索的手段。⑱这是弗兰克(Frank)在其著述中提到的。Vgl.Kindhaeuser,Strafrecht Besonderer Teil II,2008,§17,Rn.25.
第三,要求勒索必须以处分为必要,是在勒索罪的成立上增添了一个构成要件要素,从而限缩了勒索罪的入罪范围,这在罪刑法定原则上是没有问题的。虽然“被害人处分不要说”的方案在刑事政策上可能更有助于抗击暴力犯罪,但“被害人处分必要说”的观点在理论上更为合适。⑲Vgl.Wessels/Hillenkamp,Strafrecht Besonderer Teil II,2010,Rn.712 f.
第四,《德国刑法典》第240条和第253条中的“忍受”(dulden),在字义上乃是一种“有意的举止”。如果要将它解释为“无意的举止”,那就逾越了文义的界限,因为在德文中,只有“任由”(erdulden)才是“无意的举止”。通过改变法条表述的文义,去解决解释上的难题,属于立法者(而非司法者)的任务。⑳SK-Sinn,2010,Vor§§249,Rn.15.
第五,要求勒索必须以被害人处分为必要,不会导致罪刑失衡。在暴力抢开汽车的场合,“被害人处分不要说”认为,暴力抢开汽车也应成立抢劫性勒索,否则就是重行为轻处罚了。然而,“暴力”(绝对的力量)也包括把车主骗出车外并将车主关在车外,从而夺路而逃的情形。此时的“暴力”,并不比拿枪逼迫车主转移汽车操纵权更为严重,所以,将暴力抢开他人汽车的行为,判定为符合未经许可使用交通工具罪和强制罪的构成要件,是合理的。㉑Wessels/Hillenkamp,Strafrecht Besonderer Teil II,2010,Rn.712.
(三)“被害人处分必要说”的芒刺与观点的选择
以上正反两方面的意见见仁见智、各有理由,这就需要在理论上对这两种意见作出适当的选择。值得注意的是,“被害人处分必要说”存在一处较严重的实务疑点:如果被告人采用普通的胁迫手段,例如以揭发犯罪相要挟,以阻止被害人对其采取反抗措施,从而自己将被害人的财物拿走(而不是由被害人交付)的情形,应当如何处理?
在德国刑法学中,该种情况称作“小抢劫”(kleiner Raub),由于其主流学说和判例主张勒索不以被害人处分为要,将这种案件作为《德国刑法典》第253条普通勒索罪来处理,没有疑义,而主张被害人处分为必要的观点,却认为此处应当成立强制罪和盗窃罪的想象竞合。㉒LK-Vogel,2010,Vor§§249 ff.,Rn.58.福格尔教授则认为,此处处分不处分的问题倒是其次,更重要的是这时被告人迫使对方放松管理,尚不构成财产损失,而之后的拿走则是盗窃,认定盗窃在德国法上处刑较之于勒索更轻。LK-Vogel,2010,Vor§§249 ff.,Rn.61.《德国刑法典》第242条(盗窃)规定:“意图盗窃他人动产,非法占为己有或使第三人占有的,处五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刑。”trafgesetzbuch,Beck-Texte im dtv,2009,S.124.
“小抢劫”案件中,被害人让被告人拿走财物时,被害人自己的行为状态,应当如何认识呢?此处被害人并无交付行为,不具备处分的表象,若要将其也视为处分,那就要从别的角度加以解释。有人提出,被害人的举止只要是有意识的就可以,反对的意见则认为,这会导致改变财产处分概念的含义。㉓这也是赫德根在《莱比锡刑法典评注》中的观点。Vgl.LK-Vogel,2010,Vor§§249 ff.,Rn.65.因此,更多人采取的是被害人还有无“选择自由”或者“采取其他举止的可能性”的方案来判定其有无处分:被胁迫者只要认为自己的加功,仍能造成财产损失结果或者使对方牟利,认为自己是这方面的关键环节(Schluesselstellung)(如知道财产藏匿处或保险箱密码),或者他仍有其他能阻止财产损失或对方实现牟利的举止,就是在处分。如果他认为他已经到了不管采取何种举止都于事无补的地步,已经没有选择的自由或没有采取其他举止的可能,因为不管被害人是否加功,被告人无论如何都会实现造成对方损失和牟利的目标,这时,就算被害人有交付的形式,也不能认定有处分,这种交付应当认定为“拿走”。反之,如果他认为还可以有选择或者采取其他举止的可能,比如,可以向他人求援以阻止拿走,但他觉得这样做会遭到对方伤害或者杀害,于是有意不选择求援等其他举止,则他忍受被告人拿走其财物,也应认定为“处分”。㉔Vgl.Lackner/Kuehl,2007,§255,Rn.2;S/S-Eser,2001,§249,Rn.2.
反对“选择自由”的意见认为,若有选择自由但忍受被告人拿走其财物,应认定为“处分”,会导致许多“抢劫”被认定为“抢劫性勒索”。在被害人认为损失无论怎样都会发生的时候,不应认定他没有采取其他可能举止的“选择自由”:他仍然可以出于自尊心的原因进行反抗,即使反抗在他眼里可能并无多大成功的希望。如果他放弃了这种反抗,以使得被告人在这方面省了力气,那么这个被害人在逃避胁迫压力这个问题上,与那些觉得有可能阻止损失的被害人,并无多大区别。所以,抢劫和抢劫性勒索的区分标准,还应该是行为的外观究竟是拿走还是交付。具体而言,也就是“拿走”(不排除有被害人的加功)的为抢劫,“交付”(不排除有被告人的加功)的为勒索。这个标准非常浅显,也是有操作意义的,它不仅合乎真实案件中常见的情形,而且符合法律文字的表述。㉕Vgl.LK-Vogel,2010,Vor§§249 ff.,Rn.66.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同样存在“小抢劫”成立敲诈勒索的案件,如(“顾某等人敲诈勒索案”)2000年8月的一天,被告人顾某、张某、鲁某等人在明知被告人崔力(已另案起诉)盗窃了摩托车的前提下,以送其至派出所相威胁,敲诈并夺走崔力盗窃得来的钱江125型摩托车1辆(价值人民币4000元)及人民币300元。法院认定顾某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张某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鲁某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拘役6个月,缓刑6个月。㉖参见刘中发主编:《刑事案例诉辩审评——敲诈勒索罪》,中国检察出版社2014年版,第267页以下。然而,与德国立法体例不同,我国《刑法》中并未规定所谓“抢劫性勒索”的罪名,故需要区分的不是(处罚上无异的)抢劫与抢劫性勒索,而是(处罚上有异的)抢劫罪与敲诈勒索罪。就被害人处分而言,笔者以为,被害人是否有处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关于财产的意思自由是否完全被取消。为了自尊心而反抗,并不能代表他有自由处分的意思,因为在经济社会中,“理性人”的标准并不会要求人为了单纯的自尊心去殊死反抗。由于许多抢劫案件中也存在被害人交付的现象,在德国,采用外观来区分抢劫与抢劫性勒索的办法,将这类抢劫案件认定为处罚上相同的抢劫性勒索,并无不可。然而,在我国,若运用该种方法将它们认定为处罚偏轻的敲诈勒索罪,则在处罚上未免有重行为轻处罚之嫌。所以,不适宜以外观方法作为我国刑法中区分抢劫和敲诈勒索的标准。由于意思自由乃是处分的前提,理论上关于“小抢劫”案件中是否存在被害人处分的争论,便可引出另一问题:能否以受害人意思形成的不自由作为认定是敲诈勒索行为还是抢劫行为的标准?
在回答该问题前,应明确的是,以受害人真实的事后心理反应,特别是其在案件中事后表现出的胆量,来判断被告人之前的行为是抢劫行为还是敲诈勒索行为,是不妥当的。因为究竟是抢劫行为还是勒索行为,需由司法者对其客观地予以评价,只有被告人着手犯罪之前所把握到的受害人的情况,才可以作为判定被告人之行为性质的辅助资料。在这一前提之下,被害人在接收到被告人的抢劫或敲诈勒索信息之时,会出现的不能自由形成自己意思的情况,才可以作为判断被告人行为性质的辅助材料。具体而言,在出现抢劫信息时,被害人的意思形成自由是被完全取消;在收到敲诈勒索信息时,被害人的意思形成自由只是受到限制。有鉴于此,在“小抢劫”的场合,只是限制了被害人的意思形成自由,即便缺乏被害人处分的动作(在前述“顾某等人敲诈勒索案”中,被告人夺走了摩托车),也应当认定为敲诈勒索罪而非抢劫罪。或许有人认为该种情形宜成立抢夺罪,但是,如果认定抢夺罪,就不适当地遗漏了对胁迫行为的评价。
二、我国法上的敲诈勒索罪应否以被害人处分为必要
在我国,任何国外的理论分析,都须结合我国实际的情况予以取舍。以下便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对敲诈勒索罪应否以被害人处分为必要作出研析。
(一)我国语境下采用“被害人处分不要说”的理由
在德国刑法学中,不管是主张不需要被害人处分作为必要要素的主流学说,还是主张被害人处分作为勒索罪要素的少数说,都给出了较细的论证,尽管结论可能未必符合我国的立法和司法路径,但是其论证过程是有启发性的。特别是其结合文义的方法论视角以及关于“小抢劫”案件的论述,对我国相关问题的讨论有参考价值。笔者认为,在我国刑法学中,也不应坚持将被害人处分作为敲诈勒索罪的要素,而只需被告人敲诈勒索行为侵犯财产的风险,体现在对方的财产损失之中即可。这与德国刑法学中该问题上的判例意见是相似的。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选择,理由如下。
第一,我国《刑法》中关于敲诈勒索罪的表述,既不同于《德国刑法典》,也不同于《日本刑法典》。我国《刑法》未像《日本刑法典》那样明文规定“交付”的字眼。这使得日本刑法学中以被害人处分作为构成要件要素的做法,难以直接套用于我国敲诈勒索罪的讨论。我国也没有像《德国刑法典》那样,规定“强制他人为一定行为、容忍或不为一定行为”,这使得“被害人处分必要说”的支持者所主张的“忍受”(dulden)不同于“任由”(erdulden),进而反对将“忍受”解释为“忍受他人拿走”的论据,在我国缺乏相应的实定法前提。
第二,“交付”还是“拿走”作为被告人行为的外观,只属于表面要素,它不能够决定犯罪的不法程度。在用“绝对的力量”(比如持枪抢劫)要求对方交出财物的场合,有交付的动作,但仍然无疑应当成立抢劫,而非敲诈勒索。“交付”或“处分”的动作,不是敲诈勒索罪特有的外在特征,在抢劫罪中同样可以有。我国立法部门也未要求以“处分”作为区分抢劫和敲诈勒索的标志。㉗参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491-492页。
第三,在“小抢劫”的场合,仍然应当成立敲诈勒索罪。如果坚持“被害人处分必要说”,就必须在此种场合中对“处分”作宽松化或者泛化的理解,即不再以被害人的实际交付为内容,而是主张被害人有“(被动)处分的意思”就足以认定“处分”:即使被告人亲手拿走了财物,也应认为被害人本人存在“默许”的处分意思。㉘参见前注③,劳东燕文,载前注③,陈兴良主编书,第579页。劳东燕教授认为被害人“单纯转移占有的意思”即已足够。可是,在笔者看来,这种“(刑法效力交谈上)无意义”的转移动作,只能算是案件中时而会有的表象,它无法充作需要犯罪含义的“构成要件要素”。劳东燕教授还反对将“小抢劫”认定为敲诈勒索既遂,而是主张定敲诈勒索未遂和抢夺(或盗窃)数罪。在笔者看来,这是将一个行为分成了两个行为来处理,例如,被告人看见被害人手机放在桌上,便对站在一旁的被害人说:“你不要过来,不然揭发你的犯罪。”被害人便保持原地不动,于是手机被对方拿走。这时被告人的行为明明侵犯了财产,应该是敲诈勒索既遂,而不是敲诈勒索未遂加盗窃罪的数罪。然而,作出此种理解会改变交付、处分概念的含义,在罪刑法定原则上存在缺陷,同时,也使得被告人行为的不法性质,不再取决于自己的行为,而要取决于被害人的主观意识,容易造成定罪量刑中的恣意。此外,在“小抢劫”的案件中,诉诸于被害人“处分意思”的做法,还会导致一处疑惑:“处分意思”是什么?在笔者看来,只有意思形成尚有自由的情况下,才有处分意思,意思形成不自由便没有处分意思;被告人的行为尚未达到取消被害人意思自由的程度,就意味着其行为没有压制性,对方还可以反抗。㉙至于对方实际上有没有加以反抗,则另当别论。该问题便由此进一步转化为:被告人的行为有无压制性?如此转化使得规范交往的对话者从被害人转换为被告人。刑事处罚以被告人而非被害人为谈话对象,才是刑罚法的真义所在。㉚参见潘星丞:《兼有欺诈与勒索因素的刑事案件之司法认定》,《政治与法律》2014年第6期。因此,在“小抢劫”的场合,借助“处分的宽松化”以贯彻“被害人处分必要说”是不合适的。
第四,采用“被害人处分不要说”并非德国法的特例,在东亚地区也存在相应的规定。《蒙古刑法典》第149.1条规定:“以暴力威胁被害人本人及其近亲属,或者以传播可以诋毁被害人本人及其近亲属的信息,以及以毁损被害人本人及其近亲属所有的或保管看守的财物相威胁,并有可能实际造成损害,要求转让财物或物权或履行任何具有财产性质的行动的,处以最低工资额251倍以上300倍以下罚金,并处3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监禁或3年以下徒刑。”㉛参见《蒙古国刑法典》(英文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1页。我国台湾地区有关规定中有所谓“恐吓得利”罪。依该规定,在行为人恐吓他人以免除债务的情形下,被害人并无处分行为,但这不妨碍恐吓者成立犯罪。例如,甲雇佣出租车旅行,因无力支付用车费用乃于车行至荒僻之地时,命令司机乙停车,诡称系逃犯,并将携带的小刀一把故意露出,声言欲索用车费用随同其上山取之,致乙心生畏惧,不敢索取用车费用,隐忍而归。㉜参见林山田:《刑法各罪论(上册)》,元照出版有限公司(台北)2006年版,第509页。依照我国《刑法》,该行为(在不考虑数额的情形下)属于“敲诈勒索财产性利益”的范畴,同样不妨碍敲诈勒索罪的成立。
第五,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由于抢劫、盗窃罪的对象“财物”在实际适用中已经脱离其表面文义,明显出现了将财产性利益等内容纳入其范围的现象。在这种情形下,不记名、不挂失的债权凭证等财产凭证已经成了抢劫、盗窃等罪的适格对象。㉝参见陈兴良:《规范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36-837页;前注②,张明楷书,第974-975页。以绝对力量撕毁被害人的债权凭证,以及暴力迫使出租车司机放弃出租车车费,均可能处以抢劫罪。换言之,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以抢劫罪、盗窃罪的方式对绝对权与相对权均进行刑法上的保护,以免其受外界直接的侵害。所以,如果以敲诈勒索和诈骗阻止的是整体财产、相对权的损失而非绝对权的丧失为由,进而主张敲诈勒索具备区别于抢劫、盗窃等罪的间接正犯结构和肯定敲诈勒索成立以被害人处分为必要,就没有注意到抢劫、盗窃等罪在我国同样可以针对相对权乃至整体财产而成立。这样,认为敲诈勒索由于可以针对相对权,就具有间接正犯结构和需要被害人处分的主张,便站不住脚了。
(二)采用“被害人处分不要说”的影响:抢劫与敲诈勒索之间成立竞合关系
采用“被害人处分不要说”,也有助于明确抢劫罪和敲诈勒索罪之间是属于竞合关系,还是互斥关系,从而合理地划定两罪的成立范围。我国有学者认为,如果低程度的行为能够成立甲罪(敲诈勒索罪),那么高程度的行为更能成立甲罪(敲诈勒索罪),所以,成立敲诈勒索罪只需要达到低程度即可,如果行为达到高程度,则另触犯抢劫罪。㉞参见张明楷:《犯罪之间的界限与竞合》,《中国法学》2008年第4期。按照这种观点,可以认为,抢劫罪与敲诈勒索罪之间存在法条竞合关系,前者是基本法,后者是补充法。㉟基本法与补充法,意味着两个法条的构成要件之间属于交叉关系,符合了前者的构成要件,未必符合后者的构成要件;特别法与一般法,则表明两法条的构成要件之间成立从属关系,符合了前者的构成要件,必定也符合后者的构成要件。当然,反对的观点认为,应当保持以被害人处分作为敲诈勒索罪的必要要素,抢劫与敲诈勒索罪之间并非竞合关系,而是互斥的关系。㊱参见前注③,车浩文。
在笔者看来,借助被害人处分来区分抢劫罪和敲诈勒索罪,并认为有被害人处分的是敲诈勒索罪,没有处分的是抢劫罪,两者呈现互斥关系的主张,是比较片面的。从现象上讲,在许多抢劫罪的案例中,被害人也存在交付财物的情形,这就使得它较难与敲诈勒索罪相区分。进一步而言,使用被害人处分作为区分标准,也有利用被害人的行为来决定被告人行为的犯罪性质的嫌疑:被害人事后有自主的处分,被告人的行为就成立敲诈勒索罪;被害人事后没有自主处分,则成立抢劫罪。这会使得被告人的罪责依附于作为个别情形的被害人的习性,而不是取决于被告人在刑法规范上对于自己的行为所应当承担的责任。抢劫与敲诈勒索之所以不同,决定性的因素还是在于其采取的究竟是抢劫行为,还是敲诈勒索行为。如果其采取的行为能够取消具体被害人为了保卫财物而加以反抗的意思自由,就是抢劫行为,自然,在这种场合,无论是被告人拿走还是让被害人交出财物,都不存在具有一定自主性的被害人处分。如果被告人采取的行为只是限制具体被害人为保卫财产而反抗的意思自由,则是敲诈勒索行为。这种场合下,被告人已经给被害人留出了自主处分的空间。所以,被害人处分与被害人意思自由是否被取消一样,均只是判断被告人行为之不法内容的辅助性材料,不能倒过来决定其行为本身的不法性质。
以被害人处分来作为互斥的标志,只是看到了犯罪结构这一方面,犯罪结构只是反映了犯罪行为的外观,虽然借助犯罪行为的外观在很多时候可以区分出不同犯罪的界限,但是,这仍然是一种不关心规范保护目的的本体论径路,进而可能会错失问题的关键点,导致耗费很多精力,却得不到应有的成效。在笔者看来,还是应把关注点放在规范的保护目的上,换言之,也就是要注意财产法益在敲诈勒索罪和抢劫罪这两个罪名上的体现。犯罪对象则是法益的现实载体,这样就有必要考察这两个罪犯罪对象的范围宽窄问题。马克昌教授从犯罪对象的角度提出敲诈勒索罪和抢劫罪之间存在对象上的区别:“……索取利益的性质不同。本罪(敲诈勒索罪——引者注)取得的可以是动产或不动产,也可以是财产性的利益;而抢劫罪获取的一般只能是动产”。㊲马克昌主编:《刑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29页。张明楷教授在论证敲诈勒索罪与抢劫罪之间是补充法与基本法的关系时,便针对该“对象上的区别”加以驳斥:“既然敲诈勒索取得的可以是动产,而抢劫罪获取的一般只能是动产,那么,一方面,当行为人获得的是动产时,上述……区别便没有意义。另一方面,既然抢劫罪获取的‘一般’只能是动产,那么,当特殊情况下行为人抢劫了动产以外的财产时,也可能成立抢劫罪,上述……区别也没有意义。”㊳同前注㉞,张明楷文。
张明楷教授可能是在试图将财产性利益也纳入抢劫的对象以批驳互斥论,但是,这似乎在论证理由上未能切中肯綮。按照德国刑法立法体例,抢劫罪属于“针对物的犯罪”,而非“针对财产的犯罪”。这使得抢劫了不值钱的亲人纪念照在德国只成立抢劫(对象只需要是“物”,而不需要是有经济价值的“财产”),而若勒索不值钱的纪念照却根本无法成立勒索罪,因此,德国的抢劫与勒索之间属于基本法和补充法的关系,而非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我国《刑法》中并不存在“针对物的犯罪”与“针对财产的犯罪”的二分法,故我国司法实践不会将抢劫了他人不值钱的亲人纪念照认定为抢劫罪,这也使得在我国不会由于被告人抢劫了无经济价值的物,而出现德国刑法中那种成立了抢劫罪却不成立勒索罪的现象,进而抢劫罪和敲诈勒索罪之间似乎也无法呈现基本法和补充法的关系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与德国的情形不同,虽然我国司法实践不会将抢劫了他人不值钱的亲人纪念照认定为抢劫罪,却会将抢劫毒品、假币、淫秽物品认定为抢劫罪。㊴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指出:“以毒品、假币、淫秽物品等违禁品为对象,实施抢劫的,以抢劫罪定罪;抢劫的违禁品数量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抢劫了违禁品,是依照司法解释成立抢劫罪的,而敲诈勒索违禁品是否入罪,则似乎缺乏相应的司法解释。倘若这无法成立敲诈勒索罪,那就意味着,实施了“高程度的抢劫行为”仍可以不符合“低程度的敲诈勒索行为”。由此可以推出的结论是:在我国,依照司法解释,通过在违禁品问题上成立犯罪的肯定与否,抢劫罪和敲诈勒索罪之间仍然可以呈现基本法与补充法的竞合关系。然而,若敲诈勒索违禁品、赃物,也成立敲诈勒索罪(如前述“顾某等人敲诈勒索案”),㊵理论上的观点,见前注③,劳东燕文,载前注③,陈兴良主编书,第576-577页、第581页。抢劫罪和敲诈勒索罪之间就成立特别法与一般法的竞合关系了。
综上所述,在实定法框架下,抢劫罪和敲诈勒索罪可以成立基本法与补充法、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不过,实然法上这种竞合关系的认识仍然存在说理弱点:第一,如果勒索了违禁品,意味着保护违禁品的占有免受勒索,这就与非法持有违禁品的犯罪在评价上产生了矛盾;第二,在我国司法解释上,尽管违禁品属于抢劫罪的对象,但是,在法律上还是没有承认违禁品的价值(认定盗窃违禁品的具体数额时,原来只是“参考”而非“采纳”违禁品非法交易的价格,现在是盗窃、抢劫“不计数额”)。㊶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毒品工作座谈会纪要》(2013年后失效)指出:“盗窃、抢劫毒品的,应当分别以盗窃罪或者抢劫罪定罪。认定盗窃犯罪数额,可以参考当地毒品非法交易的价格。认定抢劫罪的数额,即是抢劫毒品的实际数量。”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指出:“盗窃、抢夺、抢劫毒品的,应当分别以盗窃罪、抢夺罪或者抢劫罪定罪,但不计犯罪数额。”故而,在应然法上,抢劫违禁品和敲诈勒索违禁品,皆应当只以非法持有违禁品的犯罪加以处罚。基于此种认识,抢劫和敲诈勒索的对象均只是合法的整体财产,存在区别的只是抢劫的对象范围更为狭窄(比如不包括不动产),这样,抢劫罪与敲诈勒索罪之间,便不再是基本法与补充法关系,而只是特别法与一般法的竞合关系。
三、结 语
敲诈勒索罪构成要件的满足,是否以被害人处分为必要的问题,应当结合具体的立法体例展开讨论。日本和德国的刑法中,日本法在恐吓罪(相当于我国敲诈勒索罪)中规定了需以被害人处分作为犯罪成立的必要,德国法在勒索罪中没有规定要有“交付”或“处分”的要素,因此,应当参考法律规定与我国相似的德国法来研讨这一问题。在我国,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不宜坚持将被害人处分作为敲诈勒索罪的要素。敲诈勒索行为与被害人的财产损失之间,只需要被告人敲诈勒索行为侵犯财产的风险体现在对方的财产损失之中即可。敲诈勒索罪并不具有诈骗罪那样的间接正犯结构,故而,也就不需要被害人处分这一要素。在所谓“小抢劫”和“敲诈勒索财产性利益”的场合,只要造成了相应的财产损失,无需被害人处分,就可能认定敲诈勒索罪既遂。在“被害人处分不要说”的条件下,司法解释对抢劫违禁品成立抢劫罪进行了肯定,这使得抢劫罪可以凭借这一点在成立范围上大于敲诈勒索罪,由此,抢劫罪和敲诈勒索罪之间可以呈现基本法与补充法的关系。然而,敲诈勒索赃物也有成立敲诈勒索罪的,这使得抢劫罪和敲诈勒索罪的犯罪对象重叠,它们之间又属于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此外,从应然法上讲,抢劫违禁品和敲诈勒索违禁品,均应只以非法持有违禁品论处,在这种条件下,抢劫罪和敲诈勒索罪之间也是特别法与一般法的竞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