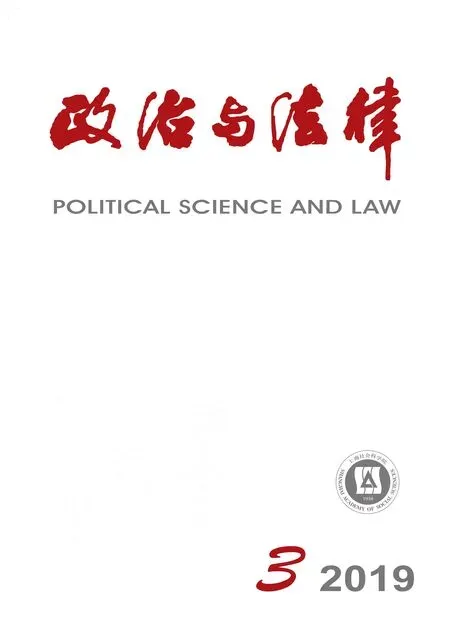被害人同意理论在医事领域刑事违法行为认定中的适用*
2019-01-26王永茜
王永茜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北京100191)
在现代医患关系中,患者的自主决定权与知情同意权受到重视。“知情同意权起源于自主决定权,其核心是确保患者获得充足的医疗信息、作出理智的医疗决定。”①马辉:《侵犯患者知情同意权责任纠纷的鉴定问题研究——兼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国卫生法制》2018年第4期。根据我国现行医疗法律制度,②我国《侵权责任法》第55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书面同意。”《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33条规定:“医疗机构施行手术、特殊检查或者特殊治疗时,必须征得患者同意,并应当取得其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另参见我国《执业医师法》第26条和第37条和我国《精神卫生法》第43条。医生实施手术等治疗行为时,应当尊重患者的自主决定和知情权利,并征得患者同意。如果医生未征得患者同意而对其实施治疗行为,即属于专断治疗。“在早期临床上,专断医疗并没有遭到反对,近来则是因为病人自主意识的抬头,专断医疗才受到质疑与禁止。专断医疗侵犯了病人的自主权,所以,基本上不被容许。”③张丽卿:《专断医疗行为的刑法容许性》,载《北大法律评论》2015年第16卷第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页。在刑法上,患者同意是被害人同意理论在医疗领域的具体应用。刑法在多大程度上重视患者同意,不仅关系到医疗行为是否构成正当的业务行为,而且关系到专断医疗是否具有刑事违法性。不当的医疗行为可能构成非法行医罪或者医疗事故罪,而专断治疗等违背了患者意志的医疗行为至少在保护了患者最大利益的场合应该被容许。本文将在刑法与医事法的交叉领域,探讨患者的自主决定和知情同意与被害人同意之间的合理界限。
一、患者自主决定权的减损
被害人同意理论被广泛适用于普通的刑事案件,影响着犯罪的构成与刑罚的适用。在一些专业领域,被害人同意可能与正当业务行为发生冲突,尤其是在医疗领域。在医疗领域,患者的自主决定权受到尊重,医生的专断医疗行为不符合正当业务行为的要求,从而可能进入刑事法的规制范围。然而,由于医疗行为的专业性,患者的自主决定权会受到一定的限制与减损,其不同于普通生活事务中的自主决定权。正是由于医疗目的与刑法规制目的的不同,被害人同意理论在医疗领域的适用与边界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
(一)人的自主决定权
从权利来源上看,人的自主决定(也称自我决定)在哲学、道德和法律上都具有坚实的基础,世界各国都将人的自主决定作为一项基本的道德原则和伦理准则,以权利的方式加以尊重,并在法律上予以保护。在哲学层面上,“自我决定就是主体基于对自由的普遍承认和尊重而通过行为来决定和实现自己的自由,它是意志自由的客观表现”。④冯军:《刑法中的自我答责》,《中国法学》2006年第3期。在道德理论上,“从自由主义角度出发,个人决定及知情同意两者均是个人自主性(personal autonomy)的体现”。⑤黄柏恒:《大数据时代下新的“个人决定”与“知情同意”》,《哲学分析》2017年第6期。在语义学上,“自主”(autonomy)这个词最早出现在17世纪,“古希腊语的autonomia演化为词根autonomos,意思是‘有其自身的法律’,其中,autos指的是‘自身’(self),nomos指的是‘法律’(law)”。⑥新牛津英汉双解大辞典编译委员会编译:《新牛津英汉双解大辞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30页。因此,“自主”在概念上包含了自我治理和自己决定的意思。
自主概念与权利基础论相结合,形成了个人对于自己身体的自主决定权,即作为个人自由的一部分,每个人都对自己的身体拥有自主决定的权利,作为私人支配的领域,个人的身体免受国家、社会以及他人的干涉或者侵犯。密尔认为:“任何人的行为,只有涉及他人的那部分才须对社会负责。在仅只涉及本人的那部分,他的独立性在权利上则是绝对的。对于本人自己,对于他自己的身和心,个人乃是最高主权者。”⑦[英]密尔:《论自由》,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1页。这种个人乃是自己的最高主权者的立场,确定了个人在道德上的自主地位,也赋予了个人对自己身体的绝对支配。
尽管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但我国现行宪法并没有明确规定个人的自主决定权。有学者指出,如果把自我决定权看作是对列举权利之外的一般性行为自由的概称,就可以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我国《宪法》第24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我国《宪法》第38条)这两个宪法条款看作是一种概括性条款,即把包括被宪法明文规定的基本权利在内的各种人权都涵盖其中,当然也包括公民处理自己事务的自我决定权。⑧参见车浩:《自我决定权与刑法家长主义》,《中国法学》2012年第1期。虽然我国宪法没有明文规定,但理论上一般都接受自主决定权的概念,并将其作为人格权的一部分。在刑法上,个人的自主决定权早已被立法者所接受(如性的自主决定权),并且通常与自由意志、个人责任原则联系在一起,成为被害人同意的理论基础。
(二)患者的自主决定权
具体到医疗领域,患者的自主决定权指的是每个人都有权决定与自身健康有关的事项。正如密尔所言:“每个人是其自身健康的适当监护人,不论是身体的健康,或者是智力的健康,或者是精神的健康。”⑨同前注⑦,密尔书,第14页。我国学者从人格权出发,将自主决定权作为一项重要的人格权,从而构建了医学领域的患者自主决定权。“患者自主决定权,指在医疗关系中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患者,经过自主思考,就关于自己疾病和健康问题所作出的合乎理性的决定及采取的行动。”⑩参见陈树鹏、石庆红:《关于患者人格权保护的几点思考》,《医学与法学》2018年第3期。
患者的自主决定权是其知情同意权的理论基础。“尊重个人人格权,就等于承认每个人都有权利和能力为自己的事务做出决定。知情同意权正是基于这一理念而出现的。对于患者的医疗措施由患者本身,而非精通医务知识的医疗人员决定,蕴含着对个人选择权的尊重,这也是传统医学理论转变的原因。”⑪唐芬:《患者知情同意权法理基础之重构》,《社会科学家》2011年第7期。可以说,征得患者同意,实质上就是尊重患者的自我决定权。因此,有学者指出:“知情同意法则是自我决定在医疗领域的体现。”⑫杨丹:《医疗刑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5页。我国台湾地区有判决指出:“医疗乃为高度专业及危险之行为,直接涉及病人之身体健康或生命,病人本人或其家属通常须赖医生之说明,方得明了医疗行为之必要、风险及效果,故医生为医疗行为时,应详细对病人本人或其亲属尽相当之说明义务,经病人或其家属同意后为之,以保障病人身体自主权。”⑬我国台湾地区“最高法院”94年台上字第2676号刑事判决。
患者对自己身体的支配权也是一项道德要求,这一道德要求得到了法律的确认和保护。例如,英国法律对于个人身体的自主决定权给予充分的尊重和保护,发展出一种个人主义的、身体自主优先的法律立场。在一起患者拒绝接受医疗案中,丹纳森勋爵(Lord Donaldson MR)指出,在选择医疗方案时,个人有权自主做出决定,“个人能够做出的选择并不仅限于他人同样认为是理性的选择,在个人做出的选择是基于合理理由、不合理理由、未知理由,甚至是没有理由的场合,个人的自主决定权仍然存在”。⑭Re T(Adult:Refusal of Treatment)[1992]4 All ER 649,pp.652-653.因此,英国法院对于患者身体的自主决定采取的是充分尊重的立场,患者有权做出接受或者拒绝医疗的决定,法律并不审查这种决定是否合理,也无权对这种决定进行否定。在患者的自主决定权与其医疗上的最大利益发生冲突的场合,医生必须尊重个人的自主决定。易言之,“如果一个成年患者已经做出决定,拒绝同意医院对其实施延长或者可能延长其生命的手术或者治疗,那么不管他的决定多么不合理,负责对他进行治疗的医生都要遵从他的决定,尽管医生不认为遵从他的决定将符合他的最大利益”。⑮R T(Airedale NHS Trust v Bland)[1993]AC 789,p.864.
(三)患者的自主决定权的“谦抑”
自主决定权是一个带有浓厚的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人格权利。如果将这一人格权直接引入我国医疗领域,那就意味着患者的自主决定具有绝对性,在患者的自主决定与其在医疗上的最大利益发生冲突的场合,医生不得违背患者意愿对其实施专断医疗。例如,在德国的“肌瘤案”中,⑯[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最高法院判例·刑法总论》,何庆仁、蔡桂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2页。该案的基本案情如下。被告人乃是一家医院的主任医师。他给附带起诉人做了一例手术。在先前的一次检查中,她被检查出了一个有两个拳头大的子宫肌瘤,他建议她实施手术切除。在手术过程中发现,这个肿瘤并不是长在子宫表面,而是和子宫牢牢地长在了一起。由于除了同时切除子宫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清除这个肿瘤,被告人就切除了整个子宫。对于这样大的手术,附带起诉人当时并不同意。联邦最高法院判定医生成立过失身体侵害罪。法院认为:“《基本法》第2条第2款第1句所保障的身体完整权,要求也需考虑到这样的情况:人们也可能拒绝放弃身体完整,即使这种放弃可以使他免于能危及性命的痛苦。对于在何种情况下,别人应当理智地愿意牺牲自己的身体完整,以求得康复,这个问题,没有任何人可以以法官自居。这个准则对医生同样有约束力。尽可能地治疗病人的肌瘤,虽是他的主要权利和本质性义务,但这种权利和义务的边界在于人们对于自己身体的基本的、自由的自我决定权。”⑰同上注,克劳斯·罗克辛书,第73页。在日本,未经患者同意的治疗行为可能构成故意伤害罪。“至少在日本,作为侵害意思决定的犯罪,不存在‘专断的治疗行为’这一构成要件,违反患者明确的意思切除其乳房的行为,无论在乳腺癌的治疗上多么合适,仍然构成伤害罪。”⑱[日]前田雅英:《刑法总论讲义》(第6版),曾文科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12页。
即便是在西方社会,患者的自主决定权也是一个直到近代才开始受到重视的权利。早在古希腊时代,“希波克拉底誓言”确立了医生的职责是治病救人,医生当“尽余之能力与判断力所及,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⑲百度百科“希波克拉底誓言”辞条,https://baike.baidu.com/item/希波克拉底誓言/213221,2018年11月10日访问。因此,为患者谋利益是整个医学伦理之根本,而医疗行为在本质上是“行善”,是维护患者的生命和健康。可以说,自医学产生之日起,“行善”原则就一直是医学的最高准则。在“行善”原则的指导下,人们普遍接受这一假定:既然医生是为患者谋福利的,而医生在医疗领域是专业的,那么,何种医疗行为更加符合患者的利益,就只有医生最了解。在“医生最了解”这一假定前提下,“患者的福利或者最大利益主要由医生来决定,医生相信哪一种选择或者治疗方式对患者最有利就采用哪一种,而不是由患者本人选择自己想要的那一种。在患者健康的改善和医疗行为的仁慈之间具有紧密的关联关系,但在医疗实践中,医疗行为的仁慈成了父权主义概念得以施行的主要的正当化根据”。⑳Sheila A.M.McLean,Autonomy,Consent and the Law,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Cavendish,2010,p.9.这种强调医生决定地位的“父权主义”医疗模式在西方运行了很长一段时期。医生一直维持着专业上的权威地位,患者也一直小心翼翼地谨遵医嘱。然而,这种医疗模式下的“医生—患者”关系是失衡的,医疗行为一旦失败,“医生—患者”关系就会发展成“医生—被害人”关系,患者的自主决定权和身体健康权均受其损。因此,“父权主义”医疗模式的合理性值得反思。
首先,这一模式的假设前提不成立。医生最了解医学,但医生不一定最了解患者,身体健康是患者本人的最大利益,医生并不能代替患者做出选择。其次,这一模式中对医生定位不准。在一般情况下,医生确实比一般患者具有更多的专业知识,但不能据此就认为医生拥有最终的医疗决定权。很多医生之所以认为他们可以凭借“知识权威”而获得“决定权威”,就是因为他们犯了一个基本的逻辑错误,“错将其肩负的更大的责任误认为是更高的权威,并错将他们的选择凌驾于患者对于自身生死的选择和偏好之上了”。㉑Maureen Kelley,Limits on Patient responsibility,Journal of Medicine and Philosophy,Volume 30,2005,p.197.最后,这一模式缺乏合理的正当化根据。医疗行为的仁慈是一个高尚的医学目的,体现了医疗行为的医学价值,但却没有反映患者自身的价值,而且,医生的高尚最终服务于医学目的,一旦将医学目的或者医学的仁慈置于最高地位,患者的权利和患者的利益必然会受损。因此,随着现代人权运动的兴起和患者的权利意识增强,患者的自主决定权越来越受重视,最终撼动了医生在医疗领域的决定性地位。
患者的自主决定权移植到我国之后,最初出现的是照搬西方的做法,倡导患者具有绝对的、个人的自主决定权,这在医疗领域和医务人员中引发了诸多困惑。与西方不同,我国具有浓厚的传统家庭主义文化。“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家庭是社会的细胞。‘齐家’是中国人的最高价值目标,甚至可以说个人的所有行为都带有家庭的烙印,这与西方强调个人与个性的文化传统具有天壤之别。”㉒余燕、黄胜开:《医疗自主权与患者家属决定权、医院特殊干预权的冲突与协调——以陕西榆林孕妇跳楼事件为视角》,《西部法学评论》2018年第1期。患者的自主决定权经过“家文化”、“功利论”、“简单化”等中华传统文化彻底改造过以后,浓缩成了手术前一味要求病人家属或者单位领导签字的行为模式。㉓参见张英涛、孙福川:《论知情同意的中国本土化——中国文化视野中的知情同意走向》,《医学与哲学》2004年第9期。这又在医疗领域和医务人员中造成了另外一种不理性的做法,即表面上尊重患者的自主决定权,形式上过分注重病人家属或者单位领导签字。2007年11月,在北京发生了“肖志军拒签案”。㉔关于这一案件的深度分析,参见苏力:《医疗的知情同意与个人自由和责任——从肖志军拒签事件切入》,《中国法学》2008年第2期;吕英杰:《“肖志军拒签案”医生的刑事责任分析》,《政治与法律》2008年第4期。2017年8月31日,在陕西省榆林市发生了“榆林产妇跳楼事件”。㉕关于这一案件的讨论,参见胡国梁:《患者知情同意权制度构造之反思——从榆林待产孕妇跳楼案切入》,《法学杂志》2018年第11期;王婷婷:《榆林产妇跳楼案中知情同意权行使问题》,《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在这两例案件中,医院均因患者家属未签字,没有取得患者及其家属的同意,从而未对患者实施专断治疗,由此引发了患者死亡的结果。
医疗机构意欲尊重患者的自主决定权,引发的却是患者死亡的不利结果,这是患者的自主决定权在我国医疗领域中出现的“悖论”。近来,医学界和法学界都在对这一问题进行反思,已有不少学者对患者的自主决定权提出了质疑。法学界有学者认为,自主决定权在进入医患关系之中时,其功能是被夸大了的,“自主决定虽然看上去对保障人的尊严和实现人的价值非常美妙,但要将其拓展到其他法律关系之中,尤其是以知情同意权的方式植入医患关系之中必须十分谨慎”。㉖同上注,胡国梁文。伦理学界也有学者认为,患者的自主决定权这样一种带有浓厚的自由主义思想特点的医学伦理原则,在引入我国的医疗实践领域之后面临着许多问题,“过度强调患者的自主权往往隐含着对于医务人员职业美德的怀疑,显示出人们已经不再相信充满利益冲突的现代医疗中的‘他者’,加剧了医患之间的信任危机”。㉗刘月树:《知情同意原则的中国化:一种生命伦理学视角的转换》,《伦理学研究》2013年第1期。
患者的自主决定权作为患者的知情同意权的理论基础,这一点不容置疑,但是,我们不能照搬西方的做法,将患者的自主决定作为最高的医疗准则。在患者的自主决定与医生的治病救人之间,需要寻找一个最佳的平衡点,用医生的治疗权对患者的自主决定权进行一定的“谦抑”。对患者的自主决定进行谦抑,是因为确立患者“自主”原则,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保障患者的最大利益,同时,这只是出于“理性人”的假设而相信患者可以基于自身理性而作出对自身利益最佳的选择。此外,从法律权利视角考察,患者“自主”原则的权利渊源是“人的生命健康权”,在所有的法律价值序列中,生命权一直是“法律保护的最高法益”,㉘参见董青梅:《中医哲学对现代法律的启示》,《河北法学》2017年第1期。所以,患者的生命权“优先”于其自主决定权,无疑具有法律上的适当性。由此可见,要在医学领域实现患者的自主决定,需要进行理论视角的转换,“在‘行善’原则的基础上重新定位知情同意,即在充分尊重患者自主决定的条件下,由医患双方以及患者家属的共同参与下来实现医学之善。这种‘行善’不是否定权利主义,而是不再将其放到至高的位置”。㉙同前注㉗,刘月树文。
二、被害人同意理论对患者知情同意原则的具体化
刑法上的被害人同意理论不能直接运用到医疗领域,因为“患者”的同意并不直接等同于“被害人”的同意。“患者同意的,是医生告知医疗方式、医疗风险、医疗后果,这种医疗行为才是患者接受和认可的对象,患者的同意表明了其对医疗行为及其风险的承担。也就是说,患者的这种医疗许可是‘告知后同意’而不是‘被害人同意’。有了患者告知后同意,才能启动或者推进医疗行为。”㉚章瑛:《医疗告知后同意法则的刑法适用性研究——基于被害人同意理论的分析》,《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因此,我们需要将刑法上的被害人同意具体化到医疗领域。
(一)被害人同意不等于患者同意
在刑法上,被害人同意是违法阻却事由。“得到承诺的行为不违法(Volenti non fit infuria;Scienti et con-sentienti non fit injuria)的法律格言,直译应为‘对意欲者不产生侵害’,‘对知情且同意者不产生侵害’,即行为人实施某种侵害行为时,如果该行为及其产生的结果正是被害人所意欲的行为与结果,那么,对被害人就不产生侵害问题。”㉛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04页。被害人同意的有效条件大致包括五个方面:一是同意主体对同意的内容、意义和后果能够正确认识;二是同意对象是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三是同意时间必须在结果发生时;四是同意表示只要在被害人的内心存在即足够;五是非基于被害人真实有效的同意无效。㉜参见黎宏:《刑法学总论》(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54-156页。具体到医疗领域中,患者是接受医疗行为的客体,也是自身医疗利益的主体,对于医生侵害自己身体的行为有权同意或拒绝。在这个意义上,被害人同意是患者行使自主决定权的表现,但是,被害人同意的有效条件不能直接适用于医疗领域,即被害人同意不直接等同于患者同意。
第一,关于同意的主体,在医疗上,患者的自主决定年龄放得更宽。在由于年少或者精神病而不能对同意的内容、意义和后果有正确认识的场合,虽然在医疗上不能成为自主决定的主体,医生只能征求其监护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的同意,但在未成年患者与其法定代理人的意见相左时,未成年患者的自主决定权可能优先。例如,“未成年人决定刺青、穿耳洞、肚皮或鼻梁穿洞,但是父母不许;或相反,父母决定代理承诺,让未成年子女刺青等等,但子女不愿意。这应该看未成年子女是否有充分的“自然的,认识能力与自我决定,依照‘自主原则(Autonomie-Prinzip)’处理”。㉝林东茂:《医疗上病患同意或承诺的刑法问题》,《中外法学》2008年第5期。未成年患者的自主决定能够优先的关键,在于其是否能够依照“自主原则”做出“自然的”自主决定。之所以放宽未成年患者的自主决定权,是因为医疗事项关系到个人的身体,而个人对于自己的身体拥有较一般事项更高的支配权。
第二,刑法上的同意,其对象是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但在医疗上,只有当治疗行为对患者的身体具有侵入性(伤害性)的场合,例如手术行为,才会涉及治疗行为是否构成故意伤害患者的问题,而很多不具有侵入性的治疗行为,在性质上并不属于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因此,无需根据刑法上的同意来阻却违法性。此外,否定生命的同意在刑法上是不被允许的,但在医疗领域,患者的同意加上优越的利益(如新药测试等),患者可能对关系到自己生命的情形做出同意。
第三,刑法上的同意必须在结果发生时做出,但医疗行为对于同意的时间要求并不是特别严格,为了患者的最大医疗利益,在符合了必要性、紧急性或者被害人意识模糊无法做出判断的情况下,可以推定患者存在着假定的同意。“假定的承诺(假定的同意),一般是指在治疗过程中,医生没有充分向患者履行告知说明义务,没有得到患者的承诺,便实施相关的治疗行为;但事后查明,即使医生向患者履行告知说明义务,患者也会同意该治疗行为。”㉞张明楷:《刑法学》(第五版),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227页。
第四,刑法上的同意表示只要在被害人的内心存在即足够,但在医疗过程中,患者的同意需要明示地以书面形式表现出来。例如,2006年7月1日施行的《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暂行规定》第24条规定:“实施人体器官移植前,医疗机构应当向患者和其家属告知手术目的、手术风险、术后注意事项、可能发生的并发症及预防措施等,并签署知情同意书。”因此,在医疗领域中,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责任范围扩大了,需要承担“告知义务”,患者基于“被告知”的医疗信息做出“书面”决定。
第五,在刑法上,非基于被害人真实有效的同意无效,在医疗领域,患者的自主决定是否有效需要根据“医生—患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假设在医生撒谎对患者说“你患的是癌症,剩下的日子不多了”之后,患者因绝望而选择自杀的场合,能否一概认定患者关于自杀的自主决定因为受医生的欺骗而无效?在医患关系的问题上,如果按照父权主义医疗模式,医生处于优越的“父权地位”,而患者处于弱势的被动地位,要认定医生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就不存在理论上的障碍。然而在患者自主决定模式下,要认定医生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就存在疑问了,毕竟自杀的决定是患者“自主”做出的,虽然医生实施了欺骗行为,但欺骗行为对患者的自杀不具有决定意义。
(二)被害人同意在医疗领域的修正
刑法上的被害人同意要具体化到医疗领域,必须进行一番修正。所谓修正,就是将刑法上的同意原则与患者的自主决定权相结合,确保医疗上的患者同意是自主的、有效的同意。这一修正不仅是刑法上的“被害人”与医疗上的“患者”的视角转换,更是从刑法上的“同意”(consent)到医疗上的“知情同意”(informed-consent)的内涵转变。
从构成要素上看,知情同意包含了两个基本要素:一是知情;二是同意。“知情要素,指的是披露信息和理解所披露的信息。同意要素,指的是自愿决定和授权进行。法学、管理学、哲学、医学和心理学文献往往将以下五个要素作为知情和同意这两个基本要素的成立条件:(1)能力;(2)披露;(3)理解;(4)自愿;(5)同意。”㉟Tom L.Beauchamp,Autonomy and Consent,in The Ethics of Consent,edited by FrankLin G.Miller and Alan Wertheimer,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56.在这五个要素中,能力是患者知情同意的前提条件,不属于知情同意的必备要素。披露并非需要在所有的场合都必备,有时,信息不需披露,患者已经理解;有时,信息虽然披露了,但患者并不理解。因此,在披露和理解这两个要素中,重要的是让患者理解。这样一来,上述五个要素,只有理解、自愿和同意这三个要素才是关键要素。理解,是“知情”的关键要素;自愿决定和授权进行是“同意”的关键要素。
1.理解
在医疗过程中,患者需要理解的是与其自身相关的医疗信息。在父权主义医疗模式下,医生(包括医疗机构)对患者往往采取“最小披露原则”,医生掌握了尽可能多的专业医疗知识,却不向患者透露,患者无法根据充分的医疗信息来做出自主决定。医疗信息的不对称导致了医疗行为的专断性,这是父权主义医疗模式被诟病的最主要原因。随着患者自主决定权的兴起,医生治疗的对象不再是单纯被治疗的“客体”,而是具有自主决定能力的“主体”。作为“主体”的患者自然会要求知晓更多的医疗信息,但医疗信息毕竟是专业的医学知识,要做到全部披露并不现实也不可能,因此,患者应该知道多少信息才符合知情同意原则的要求,需要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做出界定。
法律上的界定采取的是比较模糊的做法,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医疗信息披露的数量和质量取决于患者本人的需要。英国2005年《精神卫生法案》第3条第4款规定:“与患者做出(1)决定采取这种或那种治疗方式相关的信息;或者(2)不能做出治疗决定相关的信息,包括与合理可预见的治疗后果相关的信息,都是必须被披露的信息。”㊱S 3(4),The Mental Capacity Act 2005,UK.法律上的规定只是划定了信息披露的最低要求,根据这一要求,与患者做出治疗决定或者不做出治疗决定有关的信息,都是患者应当理解的信息;反之,与患者的自主决定及其后果无关的医疗信息,医生可以不提供。从这个角度来看,医生提供的医疗信息必须有利于患者理解自己的病情、自主做出决定,并且知道自己做出的决定所可能带来的后果。这无疑是“最小披露”和“全部披露”之间的第三条道路,是一种“折中披露”原则。
我国采取的大致也是“折中披露”原则。“知情同意原则并不要求医生向患者说明所有的医疗信息,对患者做出决定不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信息,不是医生说明的内容。具体而言,①属于一般医学常识并且没有危险的事情,例如,注射会产生轻微疼痛等,不需医生事先说明;②在反复治疗时,原则上不需要医生向患者说明患者曾经同意的内容,但是,反复治疗本身会因为多次累积而发生新的治疗效果时,医生应当告知患者实情,例如,胸腔积液患者住院期间多次穿刺抽液的,医生应当告知患者每次穿刺抽液后的不同效果;③基于对医生医术的完全信赖,患者自愿放弃接受医生说明的,医生可以不说明医疗的具体内容。”㊲冯军:《患者的知情同意与违法——兼与梁根林教授商榷》,《法学》2015年第8期。
虽然法律并未给医生设置较高的披露义务,但法律要求医生的披露能够帮助患者做出自主决定,并且确认患者理解其自主决定的性质及可能带来的结果。因此,在披露义务的规定上,法律并非一味给医疗机构或者医生强加义务,而是鼓励医生与患者之间进行“对话”或者“协商”。在临床实践中,医疗行业或者医生协会往往对医生提出更高的要求,以确保患者理解并做出决定。例如,英国医疗协会发布的《优质临床医疗指南》指出:“在经测试确定患者无自主决定能力之前,重要的是你要谨记,每个患者都要被给予尽可能多的帮助,以便做出他们自己的决定。你可以试着换种方式与患者交流信息,也可以帮助患者理解信息中涉及到的概念,但你要尽可能地提供帮助。为了做到这一点,你可能要思考你所使用的交流方式,将信息切分成若干小块,并考虑换一种描述事物的方式。”㊳Good Medical Practice,London:General Medical Council,Factsheet 460LP,2015.这是英国医疗协会提出的“尽可能多的披露”标准,体现了英国医疗行业的较高的医生职业道德水平,属于医疗行业的自律性规定,不可能成为法律上的一般规定。
当然,无论采取哪种披露原则,也不论医生披露多少医疗信息,在刑法上最为关键的是让患者理解与自身相关的医疗行为及其后果。例如,在德国联邦最高法院1978年裁决的“牙医案”中,证人(女)长年患重度头痛,所有的医生诊断都没有办法找到病因。在诊断未果后,她自认为是补过的牙齿导致了头痛,就要求作为被告的牙医拔光她所有补过的牙齿。作为被告的牙医及其助手进行检查、研究后,反复地告诉她,根据医生的诊断,补过牙齿和疼痛之间不存在什么联系,尽管如此,她基于她的外行和缺乏理解力,执意希望牙医大量拔除她的牙齿。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证人(女)所表示的拔牙同意无效,“至于被告人没有隐瞒缺乏医学上的征兆,在法律上则并不重要。决定性的仅是,他(不管采取什么手段),没有成功使得证人对现实的医疗诊断有正确的理解。仅仅这点,便足以在法律上使被告人放弃为证人拔牙”。㊴同前注⑯,克劳斯·罗克辛书,第70-71页。
2.自愿
无论从道德层面还是从哲学层面,自主决定的本意就是允许个人自愿选择。个人是否自愿选择涉及两个基本要素:一是自主的人(autonomous person)的判断;二是自主的行为(autonomous action)的判断。“在知情同意中,自主的人指的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即一个有能力做出同意的人。理论上通常假定一个独立的、有其自身价值和信念的人就是一个自主的人,但人在患病或者抑郁、疏忽大意、被强制或者其他限制性的条件下,并不能做出自主的行为,例如,一个自主的人,在没有理解文件、不同意文件条款的情况下,却在文件上签了字,这个自主的人就属于在特殊情况下没有做出自主的行为。”㊵Tom L.Beauchamp,Autonomy and Consent,in The Ethics of Consent,edited by FrankLin G.Miller and Alan Wertheimer,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61.如果单纯从程序上看,只要一个有自主能力的人在文件上签了字,签字行为所表示的授权同意就是这个人的自主行为,但是,这个授权同意是在行为人没有理解文件、不同意文件条款的情况下签订的,如果从实质上尊重个人的自我决定,就必须否定这种签字行为的自主性,这里的否定就是基于行为的不自愿。
自愿是知情同意的关键要素,但法律不可能无限制地保护个人的自愿决定。刑法上的同意原则对个人自主选择的保护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个人的内心决定必须是自愿做出的,自愿是自主决定的实质要素;二是个人的内心决定不能基于错误、被欺骗、被强制而做出,错误、欺骗和强制是自主决定的否定要素。
这样,刑法上的同意原则就使得医疗上的知情同意原则具有了两种不同层面的含义。“第一层含义,自主选择的概念是核心:知情同意是个人对于医疗干涉或者医学研究参与所做出的自主授权。个人不应只是做出明确同意或者遵从医嘱。他/她必须通过其知晓和自愿同意的行为做出授权。当且仅当一个患者或者主体,在不受他人实质控制的情况下,实质理解医疗行为,并有意授权一个医生对其实施该行为时,一个知情同意才会发生。这个定义是在界定知情同意的构成要素时更可取的。”㊶Tom L.Beauchamp,Autonomy and Consent,in The Ethics of Consent,edited by FrankLin G.Miller and Alan Wertheimer,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57.这一层含义是道德层面的,将个人的自主决定置于自主授权的权利地位,而授权行为是单方法律行为。“第二层含义,知情同意可以通过同意的社会规则来分析,这些规则决定了同意在法律上或者制度上有效。知情同意并非必然是自主行为。这个层面的知情同意指的是制度上或者法律上有效的授权,其效力由通行的社会规则决定。例如,一个心智成熟的未成年人不能在法律上授权或者同意对其实施医疗行为,但他/她依然可以做出自主授权,因此,一个患者或者主体可以自主授权对其实施医疗干涉,从而给出第一层含义上的知情同意,但其授权却没有法律上的效力,因而没有给出第二层含义上的知情同意。”㊷Tom L.Beauchamp,Autonomy and Consent,in The Ethics of Consent,edited by FrankLin G.Miller and Alan Wertheimer,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58.这一层含义是法律上或者制度上有效的知情同意,与道德层面的同意相比,法律上或者制度上的知情同意更具可行性和操作性。
因此,自愿性要素的加入具有两方面的效果:一是对医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医生在履行告知义务时必须确保患者不是在形式上收到了告知,而是在实质上理解了被告知的医疗信息,否则患者完全可能以“不自愿”为由,否定自己之前给出的知情同意;二是对患者做出了一定的限制,即患者给出的知情同意必须在制度上或法律上有效,至于是否在制度上或法律上有效,由通行的社会规则决定,不以患者的个人意愿为转移。
3.同意
知情同意原则的制度目的就是为了给患者提供自主决定的信息和机会,而患者自主决定的结果就是对医疗行为给出同意或者拒绝。在患者给出同意的场合,医生的披露和建议获得了最好的结果,医生与患者之间达成了一致的信任关系。在患者明确表示拒绝的场合,难题再次出现:一方面,我们不能否定患者的拒绝意思,既然尊重患者的知情同意权,那就意味着患者可以选择同意,也可以选择拒绝,患者的拒绝应该与其同意具有同等的效力,受到同样的尊重;另一方面,医生毕竟是专业人士,医生的治疗建议在医学上是符合患者的最大利益的,而患者是外行人士,且患者的自主决定会受到其自身、家庭、社会、文化、经济条件等各种外在因素的影响,这些影响因素可能会损害其在医疗上的最大利益。
在这个问题上,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安乐死。生命属于个人最高级别的法益,受到了法律最严格的保护。医学的发展有其局限性,并非所有疾病都能治愈,在患者身患绝症,医治无望的情况下,基于患者自主决定死亡的意志,要作具体判断和处理:(1)医生为了减轻患者痛苦,刻意终结其生命或者加速其死亡的情形,属于积极的直接安乐死,这种情况一般性地不被法律允许,因为存在着可能被滥用的危险;(2)医生为减轻患者痛苦,采用虽然符合医疗行业规范但却可能具有缩短生命之副作用的药物为之进行医疗镇痛的情形,属于积极的间接安乐死,这种情况虽然存在争议,但医生的目的和动机在于缓解患者的痛苦,只是以间接故意的心态容忍了加速患者死亡的后果,因此在刑法上不能被认定为故意杀人行为;(3)医生放弃或者中断可以延长其生命的治疗措施,从而使患者有尊严地自然死亡的情形,属于消极的安乐死,消极的安乐死常常被称为“听任死亡”,几乎在所有国家都不是犯罪。“在德国法律体系中,消极安乐死也是被允许的。其根据在于患者的自主决定权。早在1957年,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就已经判断,如果医生无视患者可能的反对意见擅自对其进行手术治疗,那么即便治疗行为本身符合医学行业规范,也因为侵犯患者的人性尊严而违法。这就意味着,只有患者自己才能决定是否接受治疗。当患者(即便是不理性地)拒绝治疗时,医护人员就必须尊重患者自主决定的权利,放弃对其采取治疗措施。”㊸王钢:《德国刑法中的安乐死——围绕联邦最高法院第二刑事审判庭2010年判决的展开》,《比较法研究》2015年第5期。
随着患者的自主决定权越来越受重视,安乐死出现了新的分类。“(1)自愿的主动安乐死(voluntary active euthanasia):根据患者的明确请求和患者完全的知情同意而有意地采取药物或其他的干预措施导致患者的死亡。(2)非自愿的主动安乐死(non-voluntary active euthanasia):对不具备明确请求能力的或者精神上不可能明确请求的患者(例如昏迷患者)有意地采取药物或其他干预措施导致患者死亡。(3)不自愿的主动安乐死(involuntary active euthanasia):没有得到有行为能力的患者的明确要求和/或完全的知情同意(并不意味着一定违反患者的意愿,例如可能并未征求患者对安乐死的意见),而有意地实施药物或其他的干预措施导致患者的死亡。”㊹[法]玛丽·德卢拜:《我选择,有尊严地死去》,孙敏、张怡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176-177页。如果绝对尊重患者的自主决定权,自愿的主动安乐死是可以被合法化的(荷兰、瑞士等国已经将其合法化),但由于安乐死涉及生命的最高价值,同时涉及道德、伦理、法律和医学等诸多方面的问题,目前在我国及世界很多国家都尚未被合法化。在安乐死尚未被合法化的国家,即便患者明确请求医生提前结束自己的生命,医生也不得基于患者的请求而提前结束其生命,否则构成故意杀人罪。
综上所述,患者同意之所以能够在医疗领域得到全面适用,得益于患者和医生这两方面的认可。一方面,同意原则保护了患者,可以使患者避免承受其不想要的或者未选择的医疗干涉;另一方面,同意原则保护了医生,可以使医生避免承担不必要的医疗风险,特别是在手术难度高且复杂,根据现有的技术不能保证百分之百成功的情况下,患者的同意在一定程度上分担了医生所冒的手术风险。至少在理论上,患者的自主决定权应该与医生的医疗干涉权相结合,两者应该在相互尊重与信任的基础上,共同寻求可能的、最好的解决方案。然而在临床医疗中,虽然医疗行为都是在医生先行告知,患者签字同意后实施的,但医生几乎无法做到理想状态的“完全披露”,“可是,如果他做不到这些,就意味着患者或接受实验者作出的同意决定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对他的信任而非对信息的理解,最终其自愿性就会受到怀疑。因此,在医疗领域里,知情同意往往是不可能的”。㊺[美]乔尔·范伯格:《刑法的道德界限(第三卷):对自己的损害》,方泉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336-337页。因此,虽然患者表示了同意,但这种同意是否是真正“理解”并足够“自愿”给出的同意,这种同意在刑法上是否属于阻却违法的有效同意,是需要讨论的问题。
三、有效的患者同意阻却犯罪构成
判断医疗行为属于刑法上的正当业务行为,除了要有治疗目的正当、治疗方法适当之外,还需要患者的有效同意,这是医疗行为正当化的“三根支柱”。以医疗手术为例,“如果患者在了解了手术的意义之后,表示了真实同意的话,就可以说,手术行为所针对的被害人的法益被放弃,手术行为不符合伤害罪的犯罪构成”。㊻黎宏:《刑法学总论》(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51页。反之,如果手术行为未取得患者的同意或者超越了患者同意的范围,即便治疗目的正当、治疗方法适当,也不属于正当业务行为,可以构成犯罪。因此,手术行为是否取得了患者同意或者取得的患者同意是否有效,关系到手术行为是否具有正当性。
(一)原则上无效的患者同意
患者同意必须真实、有效,才能阻却医疗行为的违法性。患者同意建立在患者自主决定的基础上,因此,在患者受到欺骗、胁迫或者本身行为能力不足(年少者或者精神病人)的情况下,同意无效。除了必须遵守基本的被害人同意理论之外,患者还必须遵守以下刑法的基本原则和规范,以确保自己有权给出有效的同意。
第一,遵守不损害原则。刑法不允许人们因其同意的行为而被他人不法侵害,尤其是,可能伤及生命的重伤害行为,世界范围内的刑法都否定被害人同意的有效性。如果尊重个人的自主决定权,个人是可以同意他人对自己进行不法侵害的,同意原则就应适用,但是,“若该被同意行为看来是如此公然地损害,以致没有任何理性的人竟会同意这样的损害,那么,可以合理地假定同意者并不理智,他的同意也因此是无效的。这使得我们能够依据经同意原则补足的损害原则,干涉他的自由。”㊼[美]乔尔·范伯格:《刑法的道德界限(第一卷):对他人的损害》,方泉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27页。因此,即使个人同意出卖自己的人体器官的,医生也不得为其实施器官摘除手术。器官买卖为法律所禁止,只有通过合法途径捐献器官时,捐献者的承诺才可能有效。
第二,遵守父权主义保护规范。刑法规范是强制规范,刑法上的同意原则并非完全是为了保护个人的自主决定权而设立的,在个人的自主决定可能危害到自己的或者他人的生命、身体和健康的场合,刑法转而否定了个人的自主决定权。例如,经患者一再请求而对其实施的安乐死,构成故意杀人罪。可以说,刑法规范既保护个人的自主决定,也对自主决定权的行使设定了一定的限制。刑法出于父权主义立场,有时会对个人做出的决定是否合理、是否应受到法律的优先尊重,以及是否符合个人的最大利益进行衡量,必要时会出于强制保护的目的而否定患者的自主决定。例如,“对于年少者、精神障碍者等,虽然要考虑监护人等的同意,但仅凭此还不能予以正当化”。㊽[日]前田雅英:《刑法总论讲义》(第6版),曾文科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12页。又如,对于自杀未遂者,虽然其本人拒绝接受医疗救助,但医生要基于父权主义立场和行善原则,尽可能挽救其生命。
第三,遵守公法强制规范。法律规定了不同类型的医患关系,例如,在患者是精神病人的场合,患者及其法定代理人不同意进行治疗,但患者符合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84条规定,即实施暴力行为、危及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的行为,经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可以予以强制医疗。㊾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二、三、四、五庭主办:《刑事审判参考》2013年第4集,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强制医疗专栏”发布的指导案例[第886号]朱某被强制医疗案、[第887号]宋某被强制医疗案、[第888号]荣某被强制医疗案和[第889号]高康球被强制医疗案。又如,在患者患上了法定传染病等特殊疾病时,医疗机构发现传染病病人,应当根据我国《传染病防治法》的相关规定以及患者本人所患病情,对其采取必要的强制治疗和控制传播措施。这种强制治疗属于行政强制处分行为,不论患者是否同意,都不得违反传染病防治的公法规范。
(二)无法获得的患者同意
在一般情况下,医生可以事先获得患者同意,但在强制治疗、紧急治疗和专断治疗等特殊情况下,医生无法获得患者同意。例如,患者昏迷而不能自主决定或者患者所做的决定危及其自身生命时,医生是否可以对其实施专断治疗?对此,刑法学界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是极度重视患者同意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患者的知情同意是最高医疗准则,未取得患者同意的专断治疗不仅是民事侵权行为,其严重情形也是犯罪行为。㊿参见前注㊲,冯军文。二是适当弱化患者同意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当其医疗目的、医疗适正性足以提供正当化基础时,患者的有效同意就显得不那么重要,尤其当某个医疗行为的医疗目的越强烈、医疗适正性越显著(如强制治疗、紧急治疗等)时,患者的有效同意就越应当保持‘谦抑’。”邵睿:《专断性医疗行为的刑罚界限》,《江西社会科学》2017年第7期。
尊重患者的自主决定也是为了保护患者的优越利益,没有必要在任何情况下都将患者的自主决定放在最高的位置。医学价值是医生必须遵守的医学伦理,以“行善”为原则。患者价值是个人自主决定的道德权利,以“自主”为原则。在一般情况下,患者价值“优先”,医生“行善”在后,医生不得违反患者意志对其实施治疗,但在特殊情况下,医生无法获得患者同意,不实施医疗行为可能危及患者生命,此时,医生不再是医疗行为的建议者,而是医疗行为的决策者,可以对患者实施专断医疗。如果我们担心医生会滥用治疗决定权,医事法律可以规定严格的专断治疗条件和程序,例如,借鉴美国关于紧急治疗权的规定,“可由3个以上主治医生会诊后对需要救治的患者实施诊疗措施,且只需把患者的病情和救治措施告知家属即可”。温天朗、汤优佳等:《患者自主决定权与医生医疗干涉权的博弈研究》,《中国社会医学杂志》2017年第3期。
专断医疗是医疗行为,具有治疗目的和治疗适当性。“如果将专断医疗作为犯罪处理,就是将治疗行为与刀刺身体的行为等而视之,忽视了医疗活动的社会价值,因此,不宜追究专断医疗的刑事责任。”甘添贵:《医疗纠纷与法律适用——论专断医疗行为的刑事责任》,《月旦法学杂志》(台北)2008年第6期。在无法获得患者同意的情况下,允许医生为了患者的最大利益而对其实施专断医疗,是为了解决患者的自主决定权在我国医疗领域中出现的“悖论”,即避免因为尊重患者的自主决定权而引发患者死亡的不利结果。在北京发生了“肖志军拒签案”之后,重庆又发生了“拒签门事件”。杨光友不顾其妻子谭芳菊产下一男婴后失血量达1000多毫升,需及时采取输血和介入手术,否则有生命危险,竟然在“同意书”上签下“不输血”的字样。重庆医院实施了专断医疗,通过输血和介入手术挽救了产妇的生命。
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虽然发生过上述专断医疗事件,但尚未出现因为专断治疗而将医生的行为认定为犯罪的案件,也未发生因为没有实施专断治疗而将医生的行为认定为(不作为的)犯罪的案件,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司法现象,即无论医生是否实施专断治疗,医生的行为都不是犯罪。有学者认为,“肖志军拒签案”中的医生虽然没有违反实定法的规定,“但是,医生在应然的意义上构成了诊疗义务的不作为,可能成立医疗事故罪;相反,在重庆的‘拒签门’事件中,医生强行输血符合了‘知情同意’的精神内涵,即使有违实定法的规定,但不必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代表了我国‘知情同意’制度未来发展的方向”。杨丹:《医疗行为的正当化研究》,《社会科学》2009年第12期。这是一种实质解释患者同意的观点,与现行相关医事法的有关规定不相符合,但符合人的生命权至上的原则和刑法对患者生命健康的保护精神。
未征得患者同意还有一种情形,即患者对于医疗行为的认识错误。如果我们对患者同意采取“谦抑”的态度,将医生的医疗干涉权与患者的最大利益结合起来,在医生无法获得患者同意时,容许医生的医疗干涉权补充患者的自主决定权,就可以解决患者的认识错误问题。例如,“只有接受治疗才能活命,病人却拒绝接受。治疗本身是有危险的,但不接受治疗危险更大。而病人拒绝的唯一理由是他固执地误以为治疗所用药物会使他性无能。……如果不进行治疗,形同允许病人自损,而一旦他得知真相,根本不会拒绝治疗。强制病人接受治疗正如阻止那个坚称自己茶杯里不是砷而是糖的饮茶者喝下毒茶。在这两种情形里,当事人都无意寻死,因此,干涉他并未侵犯他的个人自治”。[美]乔尔·范伯格:《刑法的道德界限(第三卷):对自己的损害》,方泉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343页。因此,(强制)医疗干涉行为是否侵犯了患者的自治,需要刑法对患者同意采取实质解释的立场,并需要就患者意志与患者的最大利益进行法益衡量。
(三)不阻却违法的患者同意
在通常情况下,患者同意与被害人同意一样,可以阻却医疗行为的违法性,但在特殊情况下,因为患者同意的理解要素或者自愿要素存在问题,即便形式上存在着患者同意,甚至患者自愿求医的,也不能阻却医疗行为成立犯罪。我国《刑法》第336条规定了非法行医罪。在非法行医案件中,患者可能是误认为行为人取得了医生执业资格而求医,也可能是明知行为人没有取得医生执业资格而求医,在患者主动求医的情况下,行为人对其实施医疗行为的,能否构成非法行医罪?这就涉及患者同意的有效性问题。
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刑事审判指导案例(第316号)“周某某非法行医案”中,被告人周某某在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和办理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情况下,在某市某区私设诊所擅自从事行医活动。2002年11月2日9时许,周某某应孕妇蒋某某亲属之邀出诊为蒋接生。23时许,周某某用手触摸检查后感到胎动,认为有生产迹象,遂给蒋肌肉注射催产素1支(1毫升)。至次日凌晨,蒋仍未生产且腹部疼痛加剧并直冒冷汗,周又给蒋注射病毒灵1支,安乃近半支。凌晨6时许,周某某用手触摸检查后告知蒋家胎儿孕妇均正常,可去医院做进一步检查并收取80元后离去。2002年11月4日上午,蒋某某去重庆市红十字会医院检查,被诊断为:胎儿已死于腹中。某市法医验伤所法医学尸体解剖鉴定结论认定,蒋某某的胎儿系在脐带、胎盘病变的基础上,因肌肉注射催产素1毫升引起强烈宫缩,导致胎儿在宫内窒息死亡。
在该案中,周某某是应孕妇的亲属之邀出诊,孕妇也同意周某某为其注射催产素,属于患者自愿、主动求医,其中关于周某某行为刑事性质的关键问题是,患者“自愿”求医的,能否阻却非法行医罪的成立。法院判决被告人周某某犯非法行医罪。其理由如下。第一,非法行医属于危害公共卫生的犯罪,侵害的是社会法益。任何人对社会法益都没有承诺权限,故患者的承诺是无效的。第二,对治疗行为的承诺,只能是一种具体的承诺,而且这种承诺只是对医疗行为本身的承诺,不包括对不当医疗行为致死致伤结果的承诺。第三,在许多情况下,患者是因为不了解非法行医者的内情才去求医的,这显然不能认为是患者的真实意志。由于患者求医是基于误解,因而其承诺也是无效的。第四,非法行医行为违反了法律秩序,即使非法行医行为取得了患者的同意,也是法律所禁止的。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二、三、四、五庭主办:《中国刑事审判指导案例(增订第3版):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第5卷),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285页。
在“周某某非法行医案”中,最高人民法院采取的也是一种实质解释的立场。对患者同意进行实质解释,是为了保护患者的最大利益。患者同意的制度设计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患者,这种保护既包括尊重患者的自主决定权和知情同意权(前者),也包括实现患者在医疗行为中的医疗利益(后者),而实现后者才是患者同意的最重要的制度目的,尊重前者只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后者,尤其是,我们不能过分注重形式,因为尊重前者,反而引发对患者不利的医疗结果。因此,刑法并不因为形式上存在着患者同意就放弃对患者的医疗利益进行保护:在患者没有认识到行为人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而自愿向其求医的场合,患者给出的同意因为存在认识错误而无效;在患者已经认识到行为人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而仍然自愿向其求医的场合,患者给出的同意仅对于医疗行为本身有效,对于医疗行为可能引起的伤亡结果无效;在患者已经认识到行为人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而仍然自愿向其求医并明确表示自愿承担医疗行为可能引起的伤亡结果的场合,患者给出的同意超越了被害人同意的范围(个人无权对社会法益作出承诺),仍然无效。
四、结 论
患者的自主决定和知情同意是整个医疗关系的核心,所有问题都绕不开它。刑法上的同意原则为患者同意提供了理论上的正当根据,同时也设定了患者同意的有效性的合理界限。知情同意原则通过法律的制度性安排(主要借助于刑法的强制)改变了医生与患者之间的地位不平等和信息不平等:一方面,这一原则提高了患者的地位,确保患者有权听取医疗信息和建议,并在理解这些信息和建议的基础上,自主决定对治疗行为是否同意;另一方面,这一原则降低了医生的权威,这表面上是给医生增加了披露义务,但实质上是解除了医生可能会对患者承担的医疗法律责任,降低了医生可能因为其医疗上的作为或者不作为而构成犯罪的执业风险。根据知情同意原则,只要医生尽职履行了充分的披露义务、取得了患者有效的知情同意,那么,只要其正常履行医疗行为,就不会构成可能涉及的故意犯罪(故意伤害罪、非法行医罪)或者过失犯罪(过失致人死亡罪、医疗事故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