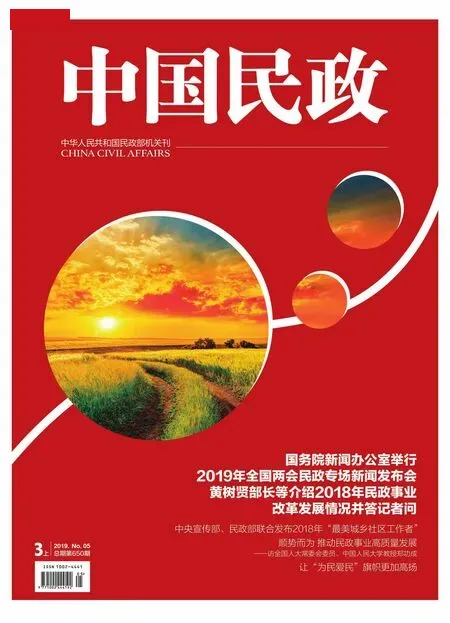学术前沿
2019-01-26
基层治理的十大痛点2017年底以来,新华社《半月谈》持续刊发来自基层一线的系列调研报道,聚焦基层治理十大痛点,刊发后引起强烈反响。一是监督检查频繁。各项督察检查过多过频,耗费基层干部大量时间精力,滋长了“脱实向虚”的不良风气。二是问责滥用。基层干部普遍反映,现在的问责状态是“下面一颗钉,上面千把锤”“上面千把刀,下面一颗头”,问责滥用成为基层干部的心病。三是压力“甩锅”。压力层层传导,原本是落实各项工作的必要之举,而不少地方却将其演变为“甩锅”,转发文件“甩锅”,分配任务也“甩锅”,“锅锅”砸向基层。四是处处留痕。“痕迹管理”日渐演变成一种督导方式,带歪了许多干部的工作观、政绩观。五是材料论英雄。日常工作被填表格、报材料等填满,而实际工作没时间去干,“穿靴戴帽”的“包装文章”应运而生。六是庸懒干部。有四类干部值得警惕:“推手式”干部信奉最好的办法就是拖,“摆拍式”干部撸起袖子不干活,“二传手”干部将责任推给下级,“等上岸”干部坐等安享人生。七是典型速成。基层改革试点轰轰烈烈开展,经验模式满天飞,简单以会议落实改革,用材料打造出“改革经验”“盆景典型”。八是政策打架。一些多部门交叉施政的领域存在决策“翻烧饼”现象,部门之间“神仙打架”,基层成了“角力场”,让基层干部做工作左右为难。九是上升“天花板”。基层干部管理机制仍然不够健全,许多干部认为“干好干坏一个样,反正都没有提拔的机会”。十是幸福感缺失。基层治理陷入“疲态治理”怪圈,在高强度的任务、高频次的督查、高压力的问责等因素影响下,紧绷运转、僵化管控、过关心态等现象凸显。
摘自:《2018,基层治理十大靶点》,《求是》,2019年第2、3、4期
互动式治理,国家治理体系创新的新方向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或公共治理体系的变革,是一个全球性的浪潮。这一浪潮的冲击力,在于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关系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互动式治理新范式的倡导者既超越了强调市场机制积极作用的新自由主义,也超越了强调行政机制积极作用的新国家主义,其重要的理论意义主要体现在超越新社群主义对社群机制自主运行的强调上。首先,互动式治理新范式并不贬斥政府的作用,也不再执着于市场机制的主导性,从而超越了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学、经济学和公共管理理念。互动式治理的新范式固然重视市场机制的作用,但在两个方面实现了对新公共管理和经理主义范式的扬弃和超越,即一方面凸显了社群机制的作用,另一方面在一个更具有包容性的框架中将行政机制的驾驭、控制和协调作用也纳入到公共治理之中。其次,互动式治理新范式在两个论述层次上超越了新国家主义。其一是在互动式治理中,政府不再是公共治理中唯一的、甚至是最重要的行动者,政府的单边主义行动不再可取。其二是在互动式治理的新分析框架之中,发展政治学和发展社会学中有关政府超越市场和社会特殊利益的国家自主性,也成为不切实际的理念。最后,互动式治理理论超越了政治学、社会学和公共管理学领域中各种强调社会行动者自主性积极作用的理论,笔者冠之为“新社群主义”。互动式治理范式的倡导者将新社群主义社会思潮的理论发展与互动式治理新范式加以有效整合,既能为新社群主义的公共政策分析开辟新的视角,也能为互动式治理的新范式提供充实的内容。
摘自:《走向互动式治理:国家治理体系创新中“国家-市场-社会关系”的变革》,顾昕,《学术月刊》,2019年第1期
贫困是动态的 贫困度量标准是可变的按照2011年调整后的新贫困线人均年纯收入2300元标准计算,到2020年按照这个标准估算,中国在统计意义上将不会存在贫困人口。这一变化意味着贫困县将成为历史,中国将进入一个没有“贫困”的时代。然而,按照农民人均收入2300元计算的贫困人口在统计上的消失绝对不意味着中国农村贫困的终结。这是原因,贫困线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不仅因为贫困是动态的,也因为度量贫困的标准是可变的,贫困线的每一次调整都会随之带来贫困人口规模和数量上的变动。贫困标准的调整包括以下两种情况:一是不同时期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采用更高的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贫困标准;二是保持生活水平不变的同一标准,用不同年度的物价水平进行调整,要保证其可比性。因此,国家在2020年宣布脱贫目标实现的同时,还需要客观指出2020年之后的贫困工作治理新目标和新特征。关于对2020年以后我国扶贫工作应该如何开展,谷树忠指出到2020年我国贫困问题也不再是单纯的经济现象,而是集经济、社会、自然等因素于一体的复合现象,需要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自然生境等多个维度,审视2020之后的贫困问题。张琦认为2020年后的减贫战略将随着由集中性减贫治理战略向常规性减贫治理战略的方向转型,由解决绝对贫困向解决相对贫困转变,由重点解决农村贫困转向城乡减贫融合推进转变,由重点解决国内贫困向国内减贫与国际减贫合作相结合方向转变,减贫发展国际化合作将会强化。左停提出应该积极借鉴国内外的相关经验,重点做好反贫困政策与社会救助政策的衔接,并要大力提倡“发展型社会救助”。
摘自:《2020年扶贫工作的若干思考》,李小云、许汉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
社会组织偏离“社会属性”必定衍生腐败非营利性是社会组织最本质的特征。然而,一些社会组织及其从业人员戴市场的帽子,拿政府的鞭子,坐行业的轿子,收企业的票子,图自己的乐子,腐败问题令人震惊。被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多次痛批的“红顶中介”最为典型。社会组织领域的腐败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偏离了“社会属性”。其一,社会组织的腐败行为,与对公共权力制约不够紧密相关。有的社会组织本身就是“二政府”,有的在人员、办公地点、职能等方面与一些政府机构交叉重复,有些事项只有有政府背景的社会组织才能办成。其二,管理体制滞后是社会组织发生腐败问题的根源。一些社会组织依附于政府部门,沿用行政方式管理,在资金来源、管理运作和社会服务等方面存在先天不足,成为政府行政权力的延伸。其三,有的行业协会利用与政府的“依附关系”或者协会领导与政府官员的私人关系,当起“掮客”。其四,很多行业协会虽然是社会组织,但背靠政府,拥有政府授权,本身掌握着一些隐形权力,比如制定行业规则、组织行业评比等,甚至权力滥用,通过向会员单位乱收费等方式获取非法利益。其五,社会组织内部“一言堂”的管理乱象也不可忽视。很多社会组织的负责人是由政府主管部门指定或任命的,选举流于形式,日常工作如何开展、资金如何分配使用等则多数由负责人说了算。其六,社会组织的外部监管机制、公开透明机制缺位也容易导致腐败。一方面,作为社会组织的主管部门,民政部门因人员和经费等制约,对社会组织的管理基本局限于登记、年检和执法查处等。另一方面,一些公益类社会组织缺少公开透明的运作方式,钱怎么收、怎么用,外界知之甚少。
摘自:《透析社会组织领域腐败问题》,陈金来,《中国纪检监察报》,2018年3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