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垮掉”的时代正名
2019-01-25谷立立
谷立立
提起盖伊·特立斯,不能忘记他的“新新闻主义”写作。所谓“新新闻主义”,旨在“和而不同”,具体说来,就是以文学的形式撰写新闻报道,将对话、场景铺叙、心理描写发挥到极致,而不在乎写下的究竟是小说,还是采访。特立斯自称是“参与观察者”,这意味着他永远不会站在远处,遥遥观察他的受访者。很多时候,他宁可忘记身份,卖力地与人物合为一体,想他们所想,做他们所做。在《被仰望与被遗忘的》一书中,他采访修建布鲁克林大桥的建筑工人,观察爬过帝国大厦顶端的蚂蚁,追踪格林尼治村的流浪猫,再次印证了他写作的宗旨:人物不分高低贵贱,大人物也好,小市民也罢,都有值得被书写、被牢记的闪光点。
于是,在《邻人之妻》一书的最后,我们看到了特立斯自己的身影。四十三岁的他形容自己“瘦而矫健,黑眼睛,一头棕发已经开始变灰”。随后,他笔锋一转,切入正题,告诉读者他正在创作一本书。这本书很幸运,又很不幸,尚在襁褓之中就受到了媒体的“过分”关注。这话不假,《邻人之妻》的确不是一本轻松写就的书。今时今日,恐怕已经很少有人会像特立斯那样,对非虚构文学抱有单纯的热情。从《王国与权力》《被仰望与被遗忘的》到《邻人之妻》,他的每一次写作都可以加上相似的定语:历时多年,厚重如砖头,书写的核心则是他所熟悉的美国。一部《邻人之妻》,他写了整整九年。九年的时间,可以是一场世界大战酝酿、爆发、转折、停战、审判,也可以是一本书搜证、采访、动笔、修改、成文。特立斯甚至没有想过要在惫懒的时候丢下笔记,重新开始另一个轻松愉快的玩意儿,反倒是排除杂念,一心沉浸在创作中。

盖伊·特立斯(Gay Talese)
当然,让《邻人之妻》成为热门话题的,不是他过于漫长的创作时间,而是颇具“爆炸性”的内容:性与道德。评论家莱斯利·费德勒曾说:“成为美国人与成为英国人、法国人不同,它意味着去想象一种命运,而非继承什么;因为美国人总是栖居于神话而非历史之中。”事实上,正是这些注定要“栖居于神话”的美国人,将历史的陋见牢牢地抓在手中:在经济、政治方面,旗帜鲜明地反叛英国,在性事上却与保守的维多利亚传统捆绑在一起。直到二十世纪,包括《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尤利西斯》《洛丽塔》在内的文学作品,都被当成“小黄书”大加禁止。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国内艺术摄影杂志并不少见。只是,这类杂志常常被标注上光圈、镜头、焦距等专业术语,伪装成人畜无害的“严肃”艺术品,在政治异见的边缘打着擦边球。模特仿佛刚刚从提香、马奈的画作中渡海而来,却要混迹于学术、政治、文学、黑人刊物当中,通过规模小、野心大、胆子肥的分销商偷偷运往街头报亭,“就像先前卖私酿威士忌一般小心”。似乎是要为三十年来的美国社会正名,特立斯下笔是克制的、冷静的。他的态度很明确:严肃,即使被曲解、被误读,也要一如既往地保持严肃。与其说他翻开的是普通美国人对性的接受史,倒不如说是诸多小人物的列传。我们看《邻人之妻》,就像在观看一部制作精良的纪录片。特立斯的面前就像放有一台摄像机,远远地,人们三三两两走上前来,对着镜头讲述自己的前半生。他们大多出生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或者来自移民家庭,或者生于保守乡间,“在对婚姻和忠贞的理想主义观念中长大”。成年后,无一例外都成了自己时代的“辍学生”,想要远离父母找到自己的幸福,却不知道等待他们的究竟是什么。
当然,仅仅用轻飘飘的“非虚构写作”来形容《邻人之妻》远远不够。如果说这是一部雄心勃勃的小说,特立斯应该不会反对。事实上,他大可以放弃对话,放弃场景铺叙,放弃心理描写,甚至不必对每个人物的出生、成长来一番追根溯源式的回顾。但他终究不愿成为热门话题的记录者,不愿靠名人八卦来提高声誉,更不愿写一些注定会“阅后即弃”的文章。就像大多数新闻报道,在事过境迁之后,很难被人提起,更别说会被反复阅读。特立斯的内心抱有宏愿,他要突破文体的局限,做越界的尝试。这表明从一开始,他就与他倾慕的作家菲茨杰拉德、菲利普·罗斯、约翰·厄普代克,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相互比拼。

《邻人之妻》 [美]盖伊·特立斯著 木 风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以休·海夫纳为例。世人都知道他一手创办了《花花公子》杂志,特立斯偏偏要将他与菲茨杰拉德画上等号。恰好,海夫纳最爱的作家正是大名鼎鼎的菲茨杰拉德。这是另一部“大亨小传”,或者不妨说是《了不起的海夫纳》。与迷恋码头绿光的盖茨比一样,海夫纳对湖畔豪华公寓里的女人投去了羡慕的一瞥。不过,這倒不是邪念,而是对沉闷生活的反叛。海夫纳的前半生,就像是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中产阶级生活的病理切片:出生在“节制、压抑、克己”的原生家庭,父母就像“维多利亚时代惹人怜爱的文物”,从不喝酒,从不抽烟,洁身自好,谨慎持家。
二战后,退伍老兵海夫纳本来有资格成为知名漫画家,不料与主编意见不合,多次尝试,多次失败,最终丢了到手的饭碗。婚前,未婚妻的背叛更让他对未来的婚姻失去信心。海夫纳当然可以像同辈人那样,要么压抑天性过着鸡毛蒜皮的郊区生活,要么敞开心扉放下一切背包上路。但他太自我,既不肯为自己套上紧箍咒,更不愿在平庸中未老先衰,“他想退回自身,重新开始人生,以自己独一无二的方式活着”。一九五三年,二十七岁的海夫纳在自家厨房里编辑出第一期《花花公子》,封面选用了玛丽莲·梦露的艳照。他当然知道他推崇的享乐主义,与盛行于美国国内的苦行主义距离十万八千里。不过,乐观的他深信,只有借助这场“金色的幻梦”,才能为这个死水一潭的国家撕开一条口子,把“健康”的观念输入进去。
事实证明,海夫纳成功了。到了下一个十年,《花花公子》已是名副其实的传媒巨头。时间到了一九六八年,观念革命席卷了整个美国。显然,望梅止渴式的观看已经不能满足颠覆传统、颠覆平庸的新一代。一八七八年,马萨诸塞州自由思想家E. H. 海伍德在考姆斯托克的围追堵截下,写出了他一生最重要的著作《丘比特之轭》。书中流露出他对自由恋爱的向往。九十年后,海伍德的构想终于在现实的美国落地生根。这是约翰·威廉森和他的砂岩俱乐部。和海夫纳一样,仪器工程师威廉森也是不折不扣的梦想家。他有令人艳羡的稳定工作,却很难克服沉闷、无聊的情绪,找到真正的自我。
于是,改变应运而生。特立斯的讲述开始于一次意外的偶遇。好比误入梦中仙境的小姑娘爱丽丝,貌合神离的布拉洛夫妇结识了砂岩的创办者威廉森,就此展开一场极致的感官冒险。不过,感官体验并不是重点,重点是如何改变成见。砂岩的存在刷新了当时美国人的观念。威廉森凭借一己之力,成功地“超越了幻想,创造出一种新的共同体”、一个自由的乌托邦。在威廉森这里,对邻人之妻(或邻人之夫)的觊觎,不过是夫妻背叛的恶果,与道德没有事实上的关联。如果爱与被爱不再保守、不再封闭,背叛与欺骗是不是会成为“历史”?那又何必非要苦苦觊觎邻人之妻的美貌?只管去爱她吧,“她的愛没有界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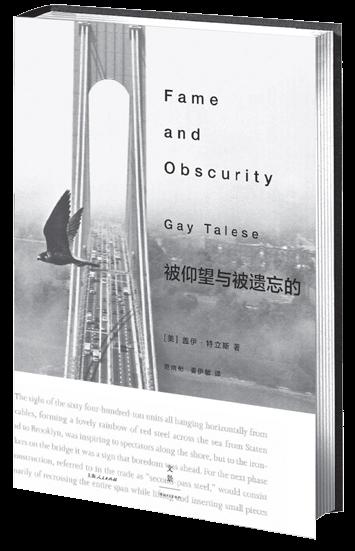
《被仰望与被遗忘的》 [美]盖伊·特立斯著范晓彬 姜尹敏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不过,特立斯很清楚,就算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性解放运动在社会、科学方面为这个国家带来了颠覆性的改变,他身边的美国人还是像上一辈、上上一辈一样笃信家庭,购买《读者文摘》。离婚率再高,似乎也阻止不了人们再婚的热情。甚至,就连敢于打破常规的叛逆者,也有坚守传统的一面:谨守法律、老实本分,静静地住在居民区里,公寓一尘不染,“客厅里的椅子和沙发比他祖母的年纪都要大”。尽管如此,特立斯仍然相信这个国家的“内里正在被重新思索和评价”。那么,海夫纳和威廉森呢?他们的一生所为,不过是“强烈地想要在他的时代留下他的印迹”。如果没有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他们的后半生也该是失败的:被工作左右,被婚姻套牢,期待改变却又无能为力,把打打闹闹当成家常便饭。多亏有了变革的时代,所有梦想才能成真。这一次,他们是时代的参与者,也是时代的书写者。当然,与特立斯钟爱的人物一样,他们既不需要被“仰望”,也不应该被“遗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