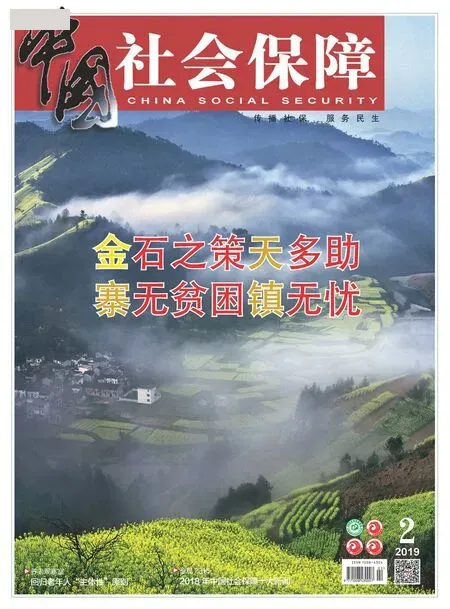回归老年人“主体性”原则
2019-01-25于建明
■文/于建明
步入老龄化社会,各级政府关于养老事业和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密集出台,市场和社会主体对于养老市场的参与跃跃欲试,独生子女一代面临的赡养重担也屡见媒体,但老龄化的主角——老年人本身却尚未在这一话语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反而是在关于老人倒地扶与不扶、公交车上让座与否引发争吵等现象的探讨与争论中常出现老年人的身影。为什么会出现老年人在应对老龄化的话语体系中相对缺席的现象呢?
老年人“主体性”缺失?
如何“恢复”老年人在积极应对老龄化中的“主语”作用,依赖于老年人“主体性”的发挥。这里“主体性”是指在进行制度设计时以老年人为中心,为老年人发挥自主性和能动性所进行的安排。在我国,提到应对老龄化时常用的“养老”一词,从词义看,老年人成为被动接受的角色,在英语、日语等语言中并不能找到直接对应的词,在这个领域,英语语系多用“elderly care”,日语用“介护”。从对象看,“养老”指向所有老年人,而“elderly care”与“介护”指向为需要照护的老年人,要以身体状况评估为依据,健康老年人则不在其列;从内容看,“养老”包含了老年人的方方面面,而“介护”与“elderly care”更侧重照护需求,更强调只在老年人有需要时介入。
从我国目前现有的政策体系看,自从2000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0%进入老龄化国家开始,特别是2013年《关于加快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出台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相关政策文件密集出台,但是在各个文件中反复出现的是政府、市场和社会,作为老龄化主角的老年人应该如何定位,应该发挥什么作用却几乎未被提及。这与政府投入大量的财力、物力和人力,老年人的获得感却依然不强密切相关。
老年人“主体性”缺失会带来一系列问题。首先是老龄化被过度问题化。每当提到老龄化问题,都会看到截至2017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2.41亿人,占总人口17.3%,65岁以上人口1.58亿人,占总人口11.4%这样的数据,俨然所有依年龄被划分为老年人的人都是问题,都需要被应对。而现实生活中我们能看到,很多低龄老年人精力充沛,正享受退休后的美好生活,甚至有些高龄老年人依然活跃在各个领域。老龄化会带来很多问题,但并不是说所有的老年人都是问题。老龄化之所以被过度问题化,与老年人自身自立意识不强,政策体系没有充分考虑老年人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忽略了老年人在老龄化应对过程中的主体性密不可分。
二是财政资金投入欠缺精准化。在社区调研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见到最多的是书画室、舞蹈室、棋牌室等为健康老年人设置的娱乐场所。政府购买的养老服务中也是经常看到组织老年人端午节包粽子,重阳节爬山,为舞蹈队、合唱队购买服装等以服务健康老年人为主要内容的项目;与失能失智老年人的照护相关的项目反倒少见。这一方面是由于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对于专业性有着较高要求,项目难度大,另一方面也是与政府职责的错位有关。从国际上看,失能失智老年人的照护是政府提供基本养老服务的主要内容,即使是发达国家提供基本养老服务已经让政府力不从心。就我国尚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来讲,将健康老年人的休闲娱乐纳入政府的职责范围不利于发挥老年人的能动性,容易形成“等、靠、要”的心理。
三是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与老年人需求的错位。截至2016年底,我国已建成养老服务床位730.2万张,每千名老年人31.6张(《2017中国民政统计年鉴》)。尽管如此,许多养老机构仍然是“一床难求”。与此同时,很多建于郊区的养老机构尽管有着高标准的硬件设施却“一客难求”。有数据显示,我国养老床位的空置率达到40%以上。由于我国对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财政投入主要集中在养老床位的建设补贴、床位补贴与运营补贴等方面,养老床位的空置意味着财政投入的巨大浪费。而养老机构建设对老年人需求缺乏精准把握的原因与以补贴供给方为主的财政投入方式有着最直接关系。也就是说财政投入上缺乏老年主体性的制度设计直接导致了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与老年人需求的错位。
如何才能最为精准地把握老年人的需求,关键在于让老年人的选择具有指挥棒作用,即充分发挥老年人的“主体性”原则。
多维度支持老年人“自立”
如何重新树立老年人在养老问题上的主体性地位,是政策制定者、养老服务提供方以及全社会范围要思考的问题。笔者有如下几点建议:
一是在全社会树立对老年及老年人的正确认知。对老年和老年人的认知既关乎如何面对现实社会的老年人,也与每个人如何思考和面对自己老年密切相关。“有尊严”地度过老年既是个人的人生目标,也应该是应对老龄化的政策目标。保持“自立”事关老年人的尊严,这意味着不要给老年和老年人贴上负面标签,要将老年看作人生的阶段之一,是人生阶段的自然延续。要在全社会加强人到老年并非只能成为社会负担,而是仍然可以发挥社会价值的共识。
二是培养老年人自身的“自立意识”。尊老、敬老是传统美德,老年人的“自立”与这两者并不矛盾,本应互为表里,老年人的自立自强是年轻人尊老敬老的前提。数据显示,我国的老龄化将会以更快的速度增长,未来30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将快速增长到30%左右(王广州,《中国人口预测方法及未来人口政策》;《财经智库》,2018年5月),如此大规模的老年人口如果都依靠政府和社会是完全没有可能的。这也意味着老年人的“自立”既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只有树立了自立意识,老年人才能在事关自己的政策选择上发挥主体性的作用。
三是支持老年人“自立”,回归老年人的“主体性”应作为应对老龄化的原则与手段。从政策框架来讲,需要重视老年人的医疗,在疾病急性期后重视康复与身体机能的恢复,在养老服务标准的制定上将老年人自理程度的恢复与保持作为重要目标。在具体的服务领域,将老年人的自理程度的恢复与维持作为最高原则。这一点,日本在老年人护理领域所遵循的“自立支援”原则是很好的示范。而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在认知与实践上尚有距离。
笔者在调研中接触到我国台湾地区从业者运营的山东省某养老机构,他们引入了日本“自立支援”的护理服务体系,老年人力所能及的事情要求老年人自己完成,即使是对于完全失能的老年人,也通过调整食物,尽可能地保持老年人自我咀嚼与吞咽的能力。不过,这种方式目前在我国“水土不服”,据说受到老年人子女的质疑,将其理解为照顾不周到的表现。这与社会现有认知不无关系。
四是在具体的政策体系中确立老年人的“主体性”原则。与老年人需求相匹配的服务体系应是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政策目标。如何才能最为精准地把握老年人的需求,关键在于让老年人的选择具有指挥棒作用,即充分发挥老年人的“主体性”原则。
如何才能体现这一原则,核心在于改变现有的以补贴供给方为主的财政投入方式为以补贴需方为主的补贴方式。这一转变将使围绕政府财政投入转的市场主体转变为围绕老年人的需求转,通过让老年人进行选择来调动市场满足老年人需求的动力。这一方式在国际上也已经成为了共识。我国如果采取财政补贴的方式,需要明确政府的职责定位,将兜底保障作为政府基本养老服务的内容,将兜底保障对象明确为经济困难老年人的经济支持及失能失智老年人的照护;如果采取长期护理保险这样的社会保险方式,则要明确个人和政府的责任和权利,确定个人缴费及政府财政投入方式及额度,同时对经济困难老年人采取减免缴费额度及自付比率的方式进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