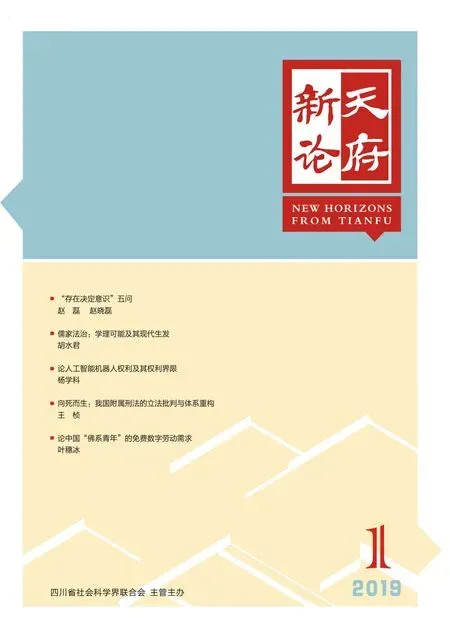论中国“佛系青年”的免费数字劳动需求
2019-01-21叶穗冰
叶穗冰
2017年底,继“70后”被称为“夹缝中的一代”、“80后”被称为“垮掉的一代”后,“90后”在媒体上有了新的代称——“佛系青年”。“佛系青年”代表了一种看淡一切、缺乏学习与工作的动力、每天只与手机为伴的人生态度,[注]叶穗冰:《当代中国青年“佛系青年”价值观初探》,《理论导刊》2018年第8期。他们的口头禅是“都行、可以、没关系”。其实并非所有的“90后”都是“佛系青年”,但“佛系青年”的主体是“90后”。
除“佛系青年”的代称外,“90后”还被称为“数字原住民”。我国从1994年开始接入互联网,之后出生的人都是“数字原住民”,即伴随着互联网成长、生活高度依赖互联网的人群。“90后”是我国第一代“数字原住民”。
由此观之,“90后”具有看似矛盾的两种身份:作为“佛系青年”,他们冷漠而慵懒,不愿参加现实社会劳动,不擅长与人合作;作为“数字原住民”,他们每天向互联网贡献数据,投身繁忙的义务劳动,从不计较报酬。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13年对7875名大学生的调查,24.4%的“90后”会在互联网上“有感而发,自己创作”,11.9%的“90后”会“对原作品再加工”,[注]施芸卿:《数字不平等的再生产——以大学生网络使用为例》,《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1期。两项相加,超过1/3的“90后”会在互联网上进行无偿劳动。不愿参加现实社会劳动的“90后”中有相当一部分乐于从事免费数字劳动。
一、免费数字劳动
“数字劳动”的概念肇始于意大利那不勒斯学者蒂齐亚纳·泰拉诺瓦。他在《免费劳动:为数字经济生产文化》一文中把“数字劳动”作为“免费劳动”的一种形式:“‘免费劳动’是自愿给予和零报酬并存,享受和剥削同在,具体包括:互联网用户自由浏览网页、自由聊天、回复评论、写博客、建网站、改造软件包、阅读和参与邮件列表、建构虚拟空间等。”[注]Tiziana Terranova, “Free Labour: Producing Culture for the Digital Economy”,Social Text, 2000,No.2,pp.33-58.免费数字劳动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生产数据的创造性劳动,一类是消费数据从而变相为媒体提供用户数据信息的非创造性劳动。本文的免费数字劳动指前者,即在互联网上进行原创性的、无偿的数字劳动。
与现实劳动一样,免费数字劳动也要消耗人的体力与智力。免费数字劳动者运用自己的知识技能,通过控制鼠标与键盘的活动在互联网上创造数据,付出了自己的时间成本与知识成本。免费数字劳动的创造产品——数据具有很大使用价值:问答类的数据直接为他人解惑;百科类的数据传播了知识;字幕类的数据帮助他人理解作品;分享类的数据启发他人的思想;等等。这些数据同样具有商品价值,可以用“在线劳动时间”和“发送数据量”等指标来度量。
然而,免费数字劳动的产品并没有转化成商品。笔者以为,“佛系青年”心甘情愿地在互联网上奉献自己的知识和精力、不图名利、不计报酬的免费数字劳动是出自他们自身的需求。
本文分析“佛系青年”的免费数字劳动需求重在探索“佛系青年”产生基本生产需求的心理动机,由此,主要参照了美国心理学家德西和瑞安提出的自我决定理论,即“如果环境能满足人类先天具有的三种基本心理需求:自主需求、能力需求和归属需求,个体的受控动机会向自主动机转化,自主动机会处于主导地位,对目标产生持续投入。反之,如果个体的三种基本心理需求被抑制,其自主动机会被减弱,行为积极性被减弱”[注]Patrick H, Knee C R, Canevello A, et al., “The Role of Need Fulfillment in Relationship Functioning and Well——Being a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Perspective”,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7,No.3,p.434.。
二、基本心理需求之自主需求
自主需求是人们自发、自主决定自己行为的心理需求。对长大成人的青年来说,“我的地盘我做主”是他们的强烈愿望。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权力需求:向成人世界夺权,自己做出行为选择。
为了完成这一过程,他们首先要获得必需的社会经验。“佛系青年”是推崇体验主义的一代。迈克·费瑟斯通把体验主义概括为“他们有冒险精神,敢于探索生活的各种选择机会以追求完善,他们都意识到生命只有一次,因此必须努力去享受、体验并加以表达”[注]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126页。。他们的体验既包括线下生活的体验,也包括线上生活的体验——网上问答、互动交流、传递信息、完成在线任务都是线上生活的体验。对信息时代的“佛系青年”来说,线上生活的体验比线下生活的体验更重要,而且线上生活体验的过程也是享受的过程,可以用“传播即快乐”来概括。
现实社会劳动很难与娱乐相结合,免费数字劳动却是一种“玩劳动”。泰博·肖尔茨指出:数字劳动为既是游乐场又是工厂的互联网上的劳动,除传统的工资劳动外还有无规律的自由免费劳动,是个体消耗在社交网络上的创造性工作。与传统的物质劳动不同,它们全然被感觉不到、看不到和闻不到。互联网上的“玩”和“劳动”紧密相连,从而产生了“玩劳动”。[注]Jonathan Burston, Nick Dyer, Witheford and Alison Hearn, “Digital Labour: Workers Authors Citizens”,Ephemera, 2010,No.3,p.214.
雅虎知识堂是一个在线问答十分活跃的虚拟社区。在用户给出的以健康为基础的在线回答问题的原因中,前十位是:享受、功效、学习、个人利益、帮助他人、社区利益、社会参与、同感、名誉和互惠。[注]Oh 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Motivations of Health Answerers in Social O&A”,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2,No.3,pp.543-557.这一享受的体验包括被他人需要的满足感和充分发挥才智完成任务的成功感。
百度百科是全球最大的中文百科全书。这一平台的首页显示,有超过660万的免费数字劳动者参与了平台的建设,他们奉献了超过1500万个词条。[注]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2018-10-15.这些免费数字劳动者的享受体验包括词条被采纳的愉悦感和网名在“最近更新”模块被标注出来的自豪感。
比网络问答和百科知识条目编撰更能激发人们免费数字劳动动机的是微信、微博等平台,因为这些平台不仅有知识的分享,更有及时的互动,劳动与娱乐达到了高度的融合。人们在上面展示自己丰富多彩的生活画面,以赢得关注者的赞赏;转发信息与传播知识,在人们的围观中满意地塑造自己智者的形象;进行文学创作或纵论时事,更能在别人的点赞与转发中获得成就感。互联网上的免费数字劳动既是一种劳动,更是一种享受体验。
在获得必需的社会经验之后,“佛系青年”迫切希望向成人世界夺权。每一代青年在成长的过程中都试图向成人世界夺权,“叛逆”也好,“垮掉”也罢,无非是青年对成人权力或积极或消极的抵抗。在传统社会,权力是一种知识,通过对知识的独占取得意识形态的控制权;在信息社会,“权力还是一种如福柯所说的那样与知识有强烈的联系,但信息性的知识正日渐取代叙述性的和论说性的知识”。[注]斯各特·拉什:《信息批判》,杨德睿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7页。“佛系青年”还没有足够的能力与成人争夺现实社会的权力,但他们通过发帖、发朋友圈、写微博等,不断在互联网上创造数据、获取数据控制权,一点一点地打破成人的权力垄断,获得虚拟社会的部分权力。与不合作行为相比,免费数字劳动更有通过创造性劳动获取权力的积极意义,同时也使得“佛系青年”免于被劳工化的命运。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被克里斯蒂安·富克斯这样解读:“如果商品形式暗含着不平等,那么一个真正公平、民主和公正的社会必然是一个以共享物为基础的社会。”[注]克里斯蒂安·富克斯:《信息时代重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曲轩译,《国外理论动态》2017年第12期。凯文·凯利则认为:“当众多拥有生产工具的人都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努力,共享他们的产品,不计较劳务报酬,乐于让他人免费享用其成果时,新社会主义的叫法也就不足为奇了。”[注]凯文·凯利:《必然》,周峰等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年,第56页。从这一点出发,“佛系青年”的免费数字劳动不仅具有通过创造性劳动获取权力的意义,更昭示了信息时代共产主义工作伦理的萌芽。
三、基本心理需求之能力需求
能力需求是人们相信自己具有一定能力、能完成相应任务的心理需求。长大成人的青年们要自主决定自己的行为,必须建立在充分了解自己能力的基础上。为此,青年们会有意识地接受一些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以确认自己的能力。免费数字劳动对“佛系青年”来说是一项既与世无争又能挑战自己能力的工作。
免费数字劳动首先是对“佛系青年”情绪自控力的挑战。对于相当一部分免费数字劳动,比如给外文影片配制中文字幕、进行文学创作等,“佛系青年”在着手之时并没有十足的把握。随着免费数字劳动的深入,困难增加,劳动者可能产生焦虑、困扰等负面情绪。要想继续完成工作,他们必须不断克服自己的负面情绪,他们的情绪自控力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不断加强。随着任务逐步完成,愉悦和满足感逐渐取代焦虑和困惑感,他们对自己的能力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免费数字劳动也是对“佛系青年”知识技能的挑战。在免费数字劳动过程中,劳动者通过线上实践,调动了自己的知识储备,查找了新的知识,重新整合了自己的认知体系,积累了解决问题的经验,提高了自身的知识技能,从而促进了免费数字劳动者自我价值的实现。免费数字劳动成果上传到互联网后,如果得到了其他数字劳动者或数字消费者的采纳或肯定,免费数字劳动者的社会价值也就得以实现。由此,“佛系青年”不仅实现了人生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而且透过价值标尺认识了自身的知识技能水平。
免费数字劳动还是对“佛系青年”领导能力、协调能力的挑战。免费数字劳动并不意味着个体劳动,恰恰相反,免费数字劳动很多时候是一种协同知识生产,即基于互联网平台、以大规模协作的方式完成复杂的任务。比如,雅虎知识堂、百度百科,一条有价值的信息往往由几十人甚至上百人共同编撰;大型网络游戏,一个任务的完成需要多名玩家分工合作,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任务,处于核心位置的角色要学会组织、分工与管理,处于边缘位置的角色要学会协调与配合。“佛系青年”可以通过任务完成的情况认识自己的领导能力、协调能力。
美国心理学家班杜拉的社会认知理论有个核心概念——自我效能感,是指“人们对于自己在特定情景中是否有能力操控行为的预期”[注]Bandura A., “Self-efficacy: Toward a Unifying Theory of Behavioral Change”, Psychological Review, 1997,No.3,pp.191-215.。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能力需求正是人们对自我效能感的需求。研究表明,对于参与知识共享的个体来说,自我效能感是个体对从事知识共享能力的一种判断,它直接影响知识共享行为或通过激发和维持知识共享意图甚至通过目标设置间接影响知识共享意图来影响知识共享。[注]Hsu M. H., Ju T. L., Yen C. H., et al., “Knowledge Sharing Behavior in Virtual Communit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ust, Self-efficacy, and outcome expectation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Computer Studies, 2007,No.2,pp.153-169.
从表面上看,“佛系青年”常常“看淡一切”。实际上,这是他们在现实社会中处于不利竞争地位的自我保护与伪装。如果他们提升自我效能感的需求在现实社会中得不到满足,那么他们就只能投身于虚拟社会,在免费数字劳动中挥洒自己的知识能力,体会到被重视、受赞扬的感觉,并因而认可自己的能力。虚拟社会自我效能感的提升往往伴随着现实社会自我效能感的提升,因为虚拟社会的免费数字劳动成果能够转化为有竞争力的资本,为“佛系青年”在现实社会找到更理想的工作。
四、基本心理需求之归属需求
归属需求是人们确信自己与他人有关联或从属于一定组织的心理需求。人是社会性动物,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存在。在考察“佛系青年”的免费数字劳动需求的时候,容易被忽略的是他们在免费数字劳动中对虚拟组织的依恋这种归属需求。
阿兰·德波顿说:“历史证明,社会保障了生活的基本需求之际,就是身份的焦虑滋生之时。”[注]阿兰·德波顿:《身份的焦虑》,陈广兴、南治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序言”。这种身份的焦虑实际上是对自己在社会中所处地位的担忧——一种因缺乏归属感而产生的焦虑。当代“佛系青年”正处于身份的焦虑之中:一方面,社会保障了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他们得以追求归属感等精神层面的东西;另一方面,集体主义的宏大叙事成为历史,现代社会的原子化倾向瓦解了社会凝聚力,他们正在丧失归属感。在虚拟社会,他们通过免费数字劳动结成兴趣圈,从而寻找自身的归属感。根据中国青年报对1982名青年的调查,91.0%的受访青年有自己的兴趣圈,56.9%的受访青年认为兴趣圈能让年轻人找到志趣相投的朋友,56.2%的受访青年认为兴趣圈可以帮助年轻人增长见识、获得新技能;49.1%的受访青年认为兴趣圈能丰富年轻人的生活,48.1%的受访青年认为能从中获得归属感和自我认同感。[注]王品芝,陈子祎:《考研、英语、动漫......超九成受访青年有自己的兴趣圈》,中青在线,http://news.cyol.com/content/2018-05/16/content_17195369.htm,2018-05-16.对“佛系青年”而言,与他人合作、成为某组织的一员的意义甚至可能超过了免费数字劳动本身的意义。
归属需求包含三个层面的需求:互动、互惠和认同。
(一)互动
查尔斯·库利提出了著名的“镜中自我”的概念:“在许多情况下,与他人的联系依赖较为确定的想象形式,即想象他的自我——他专有的所有意识——是如何出现在他人意识中的。这种自我感觉决定于对想象的他人的意识的态度。这种社会自我则可以被称作反射自我或镜中自我。”[注]查尔斯·霍顿·库利:《人类本性和社会秩序》,包凡一等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132页。库利的理论从静态角度分析人与他人的联系。根据这一理论,“佛系青年”在虚拟社会从事免费数字劳动,产生劳动痕迹,收获劳动成果,然后被他人所感知,产生他人对自己的评价,而“佛系青年”通过他人的评价来感知自己的社会形象和与他人的关系,整个过程就像照镜子一样。
米德进一步指出,自我是通过与他人的互动过程而得到发展的。他说:“‘主我’是有机体对他人态度的反应;‘客我’是有机体自己采取的一组有组织的他人态度。他人的态度构成了有组织的‘客我’,然后有机体作为一个‘主我’对之作出反应。”[注]乔治·H·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赵月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137页。米德的理论从动态角度分析人与他人的联系。自我与他人的互动在互联网上主要体现为数据的生产与消费,数据的生产就是一种数字劳动。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也就没有人与他人的互动,是互动的需求引发了免费数字劳动。
戈夫曼试图解释人们之间互动的基本过程和原理,提出了拟剧理论:人与人在社会生活中的相互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作一种表演。生活中的每个人或是个体表演者,或是剧班中的一员,总是在某种特定的场景,按照一定的要求,在观众的注视下进行角色呈现。[注]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冯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4页。免费数字劳动是一场在虚拟社会进行的表演,免费数字劳动者在观众的注视下进行创作,向他人展示自己的学识、能力和乐于助人的品性,赢得他人的喝彩与点赞,一个社会互动过程就此完成。
就像演员们在舞台上使用艺名一样,免费数字劳动者多使用网名而不是真实的名字,但这并不妨碍名称的标签化作用。由于身体缺场,人们的角色表演更随心所欲,因而更频繁地进行。这种表演为的是引起他人的注意、换来他人的互动,最终形成亲密的圈层,以满足归属感的需求。有学者研究发现,个体感知通过贡献知识行为能够显著提升在社区的地位和知名度,是知识贡献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注]Ye S., Chen H., Jin X., An Empirical Study of What Drives Users to Share Knowledge in Virtual Communities: From Knowledge Science,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 2006,pp.563-575.
(二) 互惠
“佛系青年”的数字劳动是一种免费劳动,免费劳动没有外在报酬,但有内在报酬。根据布劳的社会交换理论,内在报酬是指他人的承认、感激、关注、信任等能反映个人吸引力、可以给自身带来愉悦感受的报酬,而外在报酬则指代物质性的财富或者是预期能得到的工具性服务。参与交换的个人会基于互惠性的原则对预期报酬进行理性计算,以决定是否采取特定行动。[注]彼得·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李国武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65-175页。
人们有形成圈层的需求,潜意识是希望圈层内存在互惠,自己对圈层的贡献能够唤起他人对自己有利的行为。虽然在虚拟社会的圈层中有免费数字劳动者,也有“不劳而获”的数字消费者,但是只有免费数字劳动者是这个圈层的核心成员,纯粹的数字消费者游离于圈层边缘。要想真正进入圈层中心,就必须不断向圈层奉献自己的数字劳动成果,使自己成为圈层内一支不可缺少的建设力量。这些免费数字劳动者如果一开始就能够得到圈层内他人的积极反馈,对互惠的预期会上升,更乐意奉献数字劳动成果;如果他们一直得不到积极反馈,对互惠的预期会下降,下降到一定程度时就可能转投其他的圈层。在这一过程中,免费数字劳动者带着先施惠于人、后受惠于人的期待,同时期待不同的施惠水平对应不同的受惠水平。
在知识问答社区,免费数字劳动成果往往用虚拟的“财富值”呈现出来。上传独创性文档,回答别人的问题并被别人采纳,可以增加相应的“财富值”。这些“财富值”并不能兑换成货币,它更像是一种互惠承诺——当免费数字劳动者需要别人的帮助时,可以使用自己的“财富值”去换取别人的帮助,并在圈层内获得良好的声望和地位。
在字幕组圈子里,免费数字劳动成果同样可以兑换成虚拟货币。更重要的是,一旦被字幕组这个圈层接纳,就可以获得字幕组内部的匿名账号,借此观看大部分国外最新的影视剧。对于剧迷来说,这个账号是无价之宝,同时也是作为字幕组圈层的一员的荣耀象征。
免费数字劳动者的互惠不是一报还一报式的互惠,而是一种泛化的互惠期待。在广袤的网络空间,他们用自己辛勤的劳动,让施予成为日常行为,让所有人都能从中获利,在消费主义泛滥的时代创造了奉献与分享的机会。可以说,“佛系青年”的免费数字劳动正在默默地改变着整个社会。
(三) 认同
互动和互惠构成归属感的表层结构,认同则构成归属感的核心结构。亨利·泰菲尔将社会认同定义为“个体认识到他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同时也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的情感和价值意义”[注]Ainhoa de Federico de la Rúa., “Networks and Identifications: A Relational Approach to Social Identities”,International Sociology, 2007,No.6,pp.683-699.。
一个圈层能够形成,总有共同的兴趣或爱好,比如爱提问、爱艺术、爱创作、爱聊天、爱烹饪等。这些共同的兴趣或爱好形成一个纽带,把一个个陌生的个体联系起来。在此基础上,圈层内的个体会不断地举行仪式活动——在同一个场景内,围绕同一个主题,共同从事指定的活动,包括一起互动“爬楼梯”、一起编辑文档、一起打游戏、合作一项工作等,其中交织着圈层成员的免费数字劳动。仪式活动产生了共同体验,圈层内的成员因此具有了或苦或乐的集体记忆,以有别于圈层外的他人。这种圈层甚至能从线上移到线下,圈层内成员不时聚会以增进感情,结成更为牢固的群体。随着圈层内成员线上、线下亲密关系不断得到强化,他们产生了有建构性的共同愿景和价值取向,激发成员留驻共同体的承诺,并以其独特的愿景和价值取向吸引圈层外的注意力,使得圈层能够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
比如网络游戏,通过公会把免费数字劳动者深度卷入,建立特定的名称与标识,有严格的规章纪律与权责划分,有共同的目标和任务。再如微信群,群主往往是最积极的免费数字劳动者,通过时时更新线上的信息吸引成员,以线上和线下的双重勾连锁定特定的群体,群体内有共同的善恶标准和价值取向。
五、免费数字劳动创造新的不平等
“佛系青年”的免费数字劳动由自主需求、能力需求与归属需求产生。通过免费数字劳动,他们创造了一个由他们做主的虚拟世界,与仍未由他们做主的现实世界区分开来。“佛系青年”的免费数字劳动因而具有了推动社会平等的意义。但是,他们同时通过免费数字劳动创造了新的不平等:免费数字劳动成果被兑换为经验值,劳动成果较多者成为圈层的核心,与相应的操作权限、社群等级挂钩,而社群等级又与权力、地位、声望等隐性资本挂钩;数字消费者成为圈层的边缘人,只能使用价值不高的数字劳动产品,无权分享更高级别的数字劳动成果。
互联网世界本来是一个扁平化的世界,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主体。但通过免费数字劳动创设圈子,却使得这个扁平化的世界有了金字塔式的权力等级结构,不同的等级享受不同的权力、承担不同的义务。一些圈层用“VIP会员”、星标会员等头衔强化了等级结构。由此,有着“都行、可以、没关系”的“佛系三连”口头禅的青年不得不放下身段,从圈层的边缘地带奋力向中心地带挪动,通过拼命奉献免费数字劳动成果,来赚取虚拟社会的身份和地位,作为对现实社会地位的补偿。从这一点上看,免费数字劳动和现实社会劳动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佛系青年”在虚拟社会并没有真正实现平等自由,只是换了一种划分等级的方式而已。
无论如何,投身免费数字劳动的“佛系青年”达成了基本共识——珍视创造性劳动所带来的快感,推崇后物质主义时代人类的无私奉献精神。这是“佛系青年”的免费数字劳动的核心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