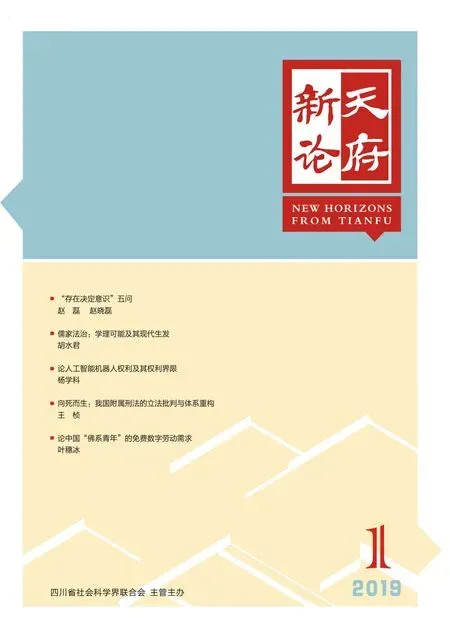数字平台时代的新帝国主义及其反思
2019-01-21王斌
王 斌
互联网技术的升级与更新,令“连接一切”的数字平台主导了网络世界。这些数字平台主要包括:社交媒体脸书(Facebook)和推特(Twitter)、搜索引擎谷歌(Google)、网络购物平台亚马逊(Amazon)以及安卓(Android)和“IOS”等智能系统及其终端。它们以信息中介的形式,串联起了全球绝大多数的数字资源和网络使用者。尤其是随着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的成熟,较之于传统的门户网站,数字平台更展现出了超强的资源汲取、数据收集和意识形态渗透等能力。事实上,数字平台在改变信息生产方式的同时,也催生了一种能够强化美国霸权地位的新型帝国主义。这种新帝国主义是数字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它持续巩固了全球经济社会的南北差距。正因如此,从社会理论的角度理解数字平台时代的新帝国主义及其产生的社会风险,不仅能提高我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水平,而且对建设“网上丝绸之路”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新帝国主义的研究范式及阶段化演进
帝国主义并不是一个陈旧的概念,它依然能十分有力地解释全球社会的新现象。有论者指出,透过帝国主义的视角,我们能清晰洞察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两大“支柱”:剥削与控制。帝国主义的剥削主要依靠国际贸易、对外投资和信贷业务,隐藏于其中的不对等关系造成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长期依附。[注]Ahmet Haim, Köse,Fikret enses et al (eds.), Neoliberal Globalization as New Imperialism, New York: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Inc., 2007, pp.1-2.而当数字化乃至平台化(platformization)的网络时代来临之后,帝国主义的盘剥仍未松动,相反却在数字平台的庇荫下不断得以再生和强化。
历史地看,帝国(empire)古已有之,但帝国主义却是相对晚近的资本主义现象。作为一个新兴概念,“帝国主义”一词首次出现在英语世界的时间是19世纪70年代;直到19世纪90年代后期,帝国主义才成为一个较为普及的词语。[注]王世宗:《新帝国主义与现代世界的兴起》,《历史》2000年第1期。1915年,列宁提出了“帝国主义时代”的概念。而后,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中做出了经典论述:“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以及“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就是垄断”。[注]《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50页、第660页。列宁的阐释成为学界研究帝国主义的主要范式,后继学人对各类新型帝国主义的分析,皆难以绕开“垄断”、“世界霸权”和“跨国集团”等关键词。只不过,现阶段我们对不同类型的新帝国主义的研究,更需将重点放到科技革新及其引发的社会结构变迁之上。
当前,学者们对帝国主义的认知可划分为三大基本类型。一是“帝国主义终结说”。这一流派坚信:帝国主义对有形疆域的过度依赖,是阻碍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完全成型的根源。所以,资本必须摧毁帝国主义,并通过和平的市场化方式操纵全球政治秩序。在此背景下,帝国主义势必被一类无中心、无疆界的国家或超国家机体所取代。[注]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17-218页。二是“帝国主义永恒论”。相关研究者指出:由于金融资本和军事力量仍集中在极少数国家手中,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本质依然未超越100多年前的帝国主义范畴。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就坚持认为,当前的帝国主义只是修正了传统的暴力掠夺手段,但仍旧以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为武器,试图通过重塑全球产业空间和经济地理来增强剥削,帝国主义一贯擅长的巧取豪夺从未改变。[注]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新”在何处?》,《国外理论动态》2017年第7期。三是“帝国主义更新论”。持此类观点的学者建构出了不同类型的“新帝国主义”概念,以调和前两种论点的矛盾。他们尝试向大众阐明帝国主义随全球经济发展而不断“进化”的现实,将帝国主义的新特征与其在20世纪初期形态之间的区别作具体说明。[注]Christian Fuchs, “Critical Globalization Studies: An Empirical and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the New Imperialism”, Science & Society, 2010,Vol.74, No.2, pp.215-247.我们基本赞同最后一类观点,即把当代新帝国主义视为一种不断再生和升级的世界霸权。特别是在20世纪中晚期以来,伴随交通设施、无线通讯和数字网络的大规模建设和全球性联通,新帝国主义的多媒体化和信息化趋势日益显著,学者们对这一演进过程也大致做出了三个阶段的划分与论证。
第一阶段是文化帝国主义(Culture Imperialism)。早在20世纪初期,资本就已经向文化领域延伸,这也引起了西方理论工作者的关注。在他们看来,文化帝国主义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利用自身文化产业优势,传播符合本国利益的信念、知识、价值观、行为规范及生活方式,从而实现对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控制。[注]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冯建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15页。法兰克福学派在20世纪30年代率先对文化工业展开了批评,这些论述间接地说明了文化帝国主义不仅是资本输出,更是一类操纵人类心智的精神控制。20世纪70年代,随着新左派激进主义浪潮的澎湃,文化帝国主义的相关讨论成为大众议题。学者们集中批判了发达国家利用大众媒体对他国实施的文化殖民,并揭露出美国企图借好莱坞和迪士尼等文化工业“驯服”全球的野心。
第二阶段是信息帝国主义(Information Imperialism)。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数字与通信技术的突飞猛进,英特网成为加强国际市场联接的信息架构基础,这令帝国主义形态呈现出了信息化趋势。互联网并未让全球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相反,掌握在美国手中的信息技术却进一步拉大了区域间的数字鸿沟。奥利弗·博伊德·巴雷特(Oliver Boyd-Barrett)指出:“基于微型处理器的电脑网络技术的发展以及美国对此技术的控制,在美国经济霸权和帝国主义推进中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注]Oliver Boyd-Barrett, “Cyberspace, Globalization and Empire”, 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2006,Vol.2, No.1, p.38.从这一层面上讲,信息帝国主义无疑是隐藏在数字化浪潮下的“毒瘤”。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尖锐地批评道:“21世纪的媒体和信息仍从属于金融资本,它们支撑了一种以美国为主导的、建基在高新数字技术产业的新帝国主义。”[注]Christian Fuchs, “New Imperialism: Information and Media Imperialism”, 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2010, Vol.6, No.1, p.34.
第三阶段是平台帝国主义(Platform Imperialism)。数字平台时代下的新帝国主义兴起于2010年前后,它是信息帝国主义的深化。2013年,韩裔学者金达永(Dal Yong Jin)在《三C》(tripleC:Communication,Capitalism&Critique)上发表了《全球化时代中平台帝国主义的建构》一文,率先提出了平台帝国主义的概念,并对此进行了极具前瞻性的探讨。2015年,金达永又出版了《数字化平台、帝国主义与政治文化》一书,他在该书开篇提到:当代信息权力的中心已从传统的万维网转向了新兴的数字平台,与传统网站不同,数字平台的主要任务就是为了促进Web2.0架构中的信息在全球范围内的实时收发。但国际间的信息交换和要素转移并不是完全对等的。比如,借由各类数字平台,美国互联网跨国集团成为数字技术开发和运营的实际操纵者,它们不仅隐秘地强化了发展中国家对美国的信息依赖与技术依附,更持续地通过社交媒体传递着自由主义价值,这也就构成了平台帝国主义数字化侵略的核心本质。[注]Dal Yong Jin, Digital Platforms, Imperialism and Political 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pp.3-4.接下来,笔者就将对数字平台的内涵以及由平台催生的新帝国主义之成因做进一步澄清。
二、数字平台的崛起及新帝国主义的成型
早在2010年,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就曾于全球知名杂志《连线》 (Wired)上,做出了“网站已死,互联网永生”的论断。他认为:发展了20年的网站已不复当年盛况,它愈益衰败且让位于更简单、更时髦的智能应用;由这些应用组成的数字平台,使得网民不再单一看重搜索效果,而是更偏爱直接、简易、快速的信息获取。[注]Chris Anderson, “The Web is Dead, Long Live the Internet”, http://www.wired.com/magazine/2010/08/ff_webrip/, 2010-08-17.这一转变引发了西方学界的集体关注。2011年5月,平台政治学术会议(Platform Politics Conference)在位于英国剑桥的安格里亚鲁斯金大学(Anglia Ruskin University)召开。虽然参会学者对数字平台的概念界定各有侧重,但他们都一致认为:数字平台不仅改变了全球商业的运作规律,更对世界政治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的衣食住行乃至喜怒哀乐,都被各类细分的数字平台引导、捕捉并监控,美国互联网跨国集团借此获得了海量的、极具分析价值的数据资源,大部分国家的信息安全都因此受到了严重威胁。
那么,数字平台与早先的网站相比,究竟具有哪些重要特征呢?我们对此可从三方面来认识:(1)数字平台是一个硬件和软件的复合体,它允许各类智能应用在平台自身的数字环境中运行,巨量的应用给用户创造了丰富的场景体验;(2)数字平台承担着交流和互动的任务,这加深了平台用户的参与感和相互间的粘性;(3)数字平台的设计并不是价值中立的,相反,平台的开发商和运营商能够通过界面、工具和操作系统来引导使用者的行为和感受。[注]③Dal Yong Jin, “The Construction of Platform Imperialism in the Globalisation Era”, In Christian Fuchs, Vincent Mosco (eds.), Marx in the Age of Digital Capitalism, Leiden: Brill, 2016, pp.332-333,p.332.正如乔丝·汉兹(Joss Hands)所言:“社交网络现今越来越多地变成了一个数字平台,这也意味着台式机已被平板电脑、智能手机和基于网络应用的界面及云计算所取代。同时,平台这一概念也明确地展示出,它具有一种能在相对密闭、商业化和可控的环境中捕捉网民数字生活的力量。”[注]Joss Hands, “Introduction: Politics, Power and Platformativity”, Culture Machine, 2013, Vol.14, No.2, p.1.
数字平台因掌握着海量的用户数据而获得了巨大的商业价值,这吸引了资本不断朝着平台开发和运营的方向聚拢,并催生了具有垄断性质的平台企业,美国的数字平台公司在此过程中取得了主导地位。截至2017年8月,全球企业市值最高的前五家公司都被美国的数字平台企业占据,其分别为苹果、“Alphabet”(谷歌重组后的伞形公司)、微软、脸书和亚马逊。这些互联网跨国集团的“寡头化”,也在本质上折射出数字平台的美国化,数字平台时代下新帝国主义的垄断属性暴露无遗。金达永就此做出了十分中肯的批判:“以往,美国控制非西方国家的手段是军事力量和资本,而后是文化产品;如今,平台似乎已成为了美国称霸全球的主要方式。得益于这些数字平台,美国完成了新一轮的资本积累。”③这种由平台化浪潮引发的新型数字垄断,让我们不得不提出疑问:数字平台是如何推动帝国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完成建构的呢?笔者认为,以下三点是我们理解此问题的关键线索。
一是,平台信息技术的升级为新帝国主义的成长创造了前提条件。移动智能终端的普及和更新,需要相应的操作系统和智能应用与之配套。但各类系统和应用不可能无限增长,日趋稳定的用户习惯会令少数公司掌握绝大多数网民热衷使用的产品。比如,脸书就在全球社交应用市场占据了绝对优势的份额,以脸书为代表的“超级应用”,实际上为平台帝国主义奠定了基础的数字生态环境。更为重要的是,各种“超级应用”无时无刻不在优化自身功能,以满足甚至是开发用户快速变更的需求,这就将数字平台的扩展与主体欲望的生产捆绑在了一起,数字平台时代的新帝国主义由此具备了不竭的动力支撑。
二是,资本市场的扩张需要数字平台充当全方位垄断的载体。用户生产内容是Web2.0时代的常态。因此,各互联网公司争相开发出功能更完整、覆盖面更广的综合性平台,以最大限度地“锁住”用户并占有其内容产出的价值。[注]José van Dijck, The Culture of Connectiv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6.另外,开发平台的互联网巨头为获取新的利润增长点,还大举兼并一些业务相关的网络公司,以期把平台扩充成“自足”的数字生态系统。以谷歌为例,该公司于2013年以125亿美元的巨额资金收购了摩托罗拉移动控股公司,其目的就在于为数字平台的建设提供智能终端的硬件设备支撑。近年来,谷歌还不断开发社交应用以期占领移动社交消费市场。事实上,谷歌在2010年还未涉入社交网络业务;而到了2013年,“Google+”则坐拥了5.4亿社交用户。说到底,以谷歌为代表的美国互联网跨国集团在各细分领域“开疆拓土”,就是为了做大数字平台而实现对用户信息的全面垄断,进而服务资本增殖,这无疑最为集中地折射出平台帝国主义的本质。
三是,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渗透方式的更新也得到了数字平台的支撑。当全球社会步入数字化阶段后,帝国主义也尝试创造一种新的合法性宣称,以粉饰自身的掠夺本质。特别是在Web2.0蔚然成风的当下,开发和运营平台的互联网公司正联手织就一类“平台意识形态”,它意欲让数字平台的用户深信:平台不仅以开放、联通、共享的姿态为网民铺设了通往新世界的坦途,更可以实现信息在不同时空传输的便捷性和高效性。这种“平台乌托邦”的话语建构,企图把以美国公司为主导的数字平台包装成通达世界的“电子桥梁”,让网民产生“越分享,越美好”的错觉,从而诱导各国政府和网民放松对信息技术的警惕,为平台帝国主义的通行大开方便之门。[注]John Nicholas, The Age of Sharing,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7, p.3.值得注意的是,在平台意识形态的形成过程中,数字平台寡头化程度随之提高,潜藏于平台之后的新帝国主义的危害性也愈益明显地体现出来。
三、数字平台时代的新帝国主义对全球治理的危害
现阶段,大型的数字平台虽然为全球网民提供了丰富的产品和服务,但也因其在技术、品牌和通道上的垄断而造就了平台帝国主义的盛行。这种数字平台时代的新帝国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利益、信息安全和社会稳定都带来了极为负面的影响,并严重威胁到了全球社会的有效治理。
首先,新帝国主义强化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掠夺和劳动力剥削。数字平台不能脱离硬件设备而单独存在,大多数数字平台跨国集团对硬件的需求量其实十分巨大,这也加重了它们在全球范围内对原材料供应国和加工地区的盘剥。具体来看,数字硬件设备的制造对稀有金属(特别是钽、钨、钼等矿物)有着极强的依赖性。再加上近年来各类移动终端更新换代提速,数字平台公司对发展中国家金属矿产需求愈益旺盛,这直接加剧了其对发展中国家矿产的侵夺。虽然苹果公司在2014年已承诺不再使用“冲突矿产”(Conflict Minerals),但由于数字产品的附加值依然被美国主要的数字平台公司掠取,落后国家所提供的原材料始终被压到最低价,低薪、无薪、童工、职业病等现象在这些矿石供应国里严重泛滥,采矿工人的生存环境甚至陷入了一种“非人化”生活境地。信息产业链里最底层的矿业工人承担了平台帝国主义最严酷的剥削,福克斯毫不客气地将这种不公义的全球分工斥之为“数字奴隶制”(Digital Slavery)。[注]Christian Fuchs, Digital Labor and Karl Marx,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pp.155-181.
受这种新帝国主义的影响,不仅采矿业具有明显的“奴隶制”特征,在加工和组装行业内,也同样存在相似的压迫。仍以苹果公司为例,该公司目前在全球拥有18家代工厂,其中14家位于中国,仅富士康就在我国内地占到了6家之多。为更快、更低价地承接苹果公司的代工业务,富士康在初期采用了半军事化的管理制度,它通过快速的流水线、密闭的宿舍和超长的工作时间,最大限度地获取了工人劳动的剩余价值。从这个角度上讲,苹果公司虽然创造了光鲜的“iphone”、“ipad”等大众科技产品,但同时也在发展中国家的代工厂内催生了大批深受苦难的“i奴”(iSlave)。换句话说,伴随数字产品的设计研发方案从美国向各代工厂的定向传输,硬件设备完成了最廉价的生产与组装,这在助推以苹果为首的美国高科技公司成为史上市值最高的数字平台时,也让发展中国家代工厂的劳工问题“返祖”到了奴隶制的黑暗之下。[注]邱林川:《告别i奴:富士康、数字资本主义与网络劳工抵抗》,《社会》2014年第4期。
还需要看到的是,平台帝国主义不仅在硬件生产中制造了新的数字奴隶制,更在软件开发的过程里加强了对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印度就是后者的典型。印度通过新自由主义的社会改革吸引了大量的国外资本,软件开发顺势成为该国的支柱产业。不过,软件开发所形成的大部分价值(75%以上)却重新回到了投资母国——美国。与美国相比,印度软件开发从业者的收入只有前者的7%~40%的水平。更为严重的是,印度软件开发从业者还面对着强制化的灵活性和流动性(compulsory flexibility and mobility),这造成了他们在承受无间歇、高强度的脑力劳动重负的同时,也面临着权利保障缺失和健康风险的陡增。[注]②Christian Fuchs, Digital Labor and Karl Marx,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p.210,p.245.总之,通过移动智能终端的制造以及相关应用的开发,数字平台时代的新帝国主义加强了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掠夺和劳动力盘剥,持续再生产了全球社会的不平等格局。
其次,新帝国主义加深了美国对全球数字信息的监控和盗猎。通过数字平台,美国互联网跨国集团获得了海量的、极具分析价值的数据资源,大部分国家的信息安全因此受到严重威胁。2013年初的一项调查显示,全球网民搜索的信息主要来自谷歌、脸书和优兔(YouTube),其占比分别达到46%、43%和32%。②用户对数字平台的依赖,不仅令平台可以决定网民接受信息的范围及理解信息的程度,更增强了平台的监控能力。当前,各大数字平台都鼓励用户自我生产内容,网民所产生的信息量大于以往任一时期。他们在各个平台上浏览的网页、点赞的倾向、观看的视频甚至是聊天记录,无一不成为平台公司可以轻易获取的数据资源。
平台帝国主义对用户数据的盗取,还深度损害了他国的国家信息安全。虽然全球各大互联网公司都声称对用户隐私进行了全面保护,但美国政府却依然可以利用数字平台实施广泛而深入的监控。《华盛顿邮报》曾指出,美国国家安全局(NSA)一直在把自己伪装成脸书的服务器,以此进入情报目标的电脑而获取信息。“棱镜门”事件的爆发,更说明了美国政府不仅毫无顾忌地践踏本国公民的隐私权,而且还借助数字平台和网络技术的优势,偷取他国政府的机要数据和机密信息,这令平台帝国主义再次挑动了全球社会在信息安全领域的敏感神经。从本质上看,数字平台时代的新帝国主义对其他国家数字信息的盗猎,证明了美国除了立于娱乐和商品来实现对全球的“软控制”之外,更在互联网领域中推进了一种相对强硬且隐藏度更高的数字化侵略。[注]⑤Eric M. Fattor, American Empire and the Arsenal of Entertainmen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p.166,p.171.
最后,新帝国主义便利了美国以网络民主为借口对他国内政的干预。以“网络民主”之名妄加批评他国,一直是美国推行帝国主义的传统。希拉里曾于2010年1月的一次演讲里说道:维护网络自由,既根植于美国建国之初的信念,又是保证公民平等获取知识和思想的基础;但突尼斯、乌兹别克斯坦和越南等国,却危及了信息的全球自由流动,美国对此必须予以制止和纠正。[注]Dal Yong Jin, “The Construction of Platform Imperialism in the Globalisation Era”, In Christian Fuchs, Vincent Mosco (eds.), Marx in the Age of Digital Capitalism, Leiden: Brill, 2016,pp.338-339.可见,美国政府常把自己标榜为全球网络民主的卫士,以“无条件网络自由”的普世价值干涉别国内政。这一行为的本质是将美国标准的网络自由凌驾于他国主权之上,进而毫无根据地把斗争矛头对准发展中国家,以期在全球范围内营造一种以美国精神为内核的虚假数字民主。此举也正应了艾瑞克·菲特尔(Eric M. Fattor)的论断:基于信息技术之上、无差别的网络民主,越来越充当了美国帝国主义“军火库”储备中的数字武器。⑤
近年来发生的全球抵抗运动也体现了数字平台作为美国“武器”的功能。有论者指出,社会抗争的发起和维持愈发依靠“文字、声音、图像在各种交错的社交平台中的流通”,数字平台正变成一个塑造社会运动的“超媒体空间”(hypermedia space)。[注]Esther Peeren, Robin Celikates et al (eds.), Global Cultures of Contestation: Mobility, Sustainability, Aesthetics & Connectivity,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p.20.特别是随着全球数字平台的建成,社交媒体开始成为美国宣扬网络自由的“扩音器”,被美国支配的网络民主依靠数字平台而获得了愈加广泛的传播。再加上这些平台缺乏基本的舆论“设置者”和“守门员”,盲目的民主“迷梦”更易掀起线上、线下共振的社会运动,这对各国政局稳定性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干扰。
“阿拉伯之春”便是这一负面效应的典型。在此次事件中,反政府力量利用脸书、推特等数字平台,将相关视频和图片在各社交网络里进行了实时直播。这些被网络民主情绪渲染的信息,不仅引发了大规模的社会动员和社会力量集结,而且催生了一类跨地区的、基于缺场互动的全球反政府社群。国外一些评论家甚至认为,“阿拉伯之春”实际上就是一场在美国支持下的“脸书革命”(Facebook Revolution):数字平台被潜在地改造成了散播美式民主的信息机器,这为美国意志的输出创造了新的媒介通道。[注]Miriyam Aouragh, “Social Media, Mediation and the Arab Revolutions”, In Christian Fuchs, Vincent Mosco (eds.), Marx in the Age of Digital Capitalism, Leiden: Brill, 2016, p.502.由此,数字平台时代的新帝国主义得以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巩固,美国政府也更能肆无忌惮地挥舞网络民主的大棒,在扰乱别国政局的基础上,精准打击与美国交恶的国家及地区。当前,面对这类帝国主义的恶劣影响,我们不得不对其进行更为深入的理论反思,提出相应的对策与措施。
四、结语:反思数字平台时代的新帝国主义
正如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一书中所言:“网络形态也是权力关系剧烈重组的来源。连接网络的开关机制是权力的特权工具。如此一来,掌握开关机制者成为权力掌握者。”[注]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弘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571页。卡斯特的论断洞悉了网络社会结构“分散式集中”的属性,数字平台的崛起更强化了这一特质。换言之,美国互联网跨国集团对数字平台开发和运营的垄断,不仅令美国政府控制了信息权力集散的“命门”,更便利了其向全球传送意识形态,甚至是输出革命。数字平台还强化了美国作为信息帝国的单极化世界霸权,美国凭此优势在多方面完成了对全球社会的实际掌控。非西方国家再一次面临来自美国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干预,积弊已深的南北差距势必继续恶化。这就造成了一幅极为吊诡的世界图景,即:当数字平台在强化全球关联的同时,一类新的帝国主义却得以继续扩张并愈益威胁到有效的全球治理。
事实上,自全球化进程启动以来,美国就一直未曾放弃推行帝国主义的霸权行为。约翰·厄里(John Urry)认为,一旦全球化变成美国企业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营利工具之时,它就注定会沦为“反乌托邦”(dystopia);比如,可口可乐、微软等全球企业都已跃升为重构世界政治经济版图的商业帝国,但它们却把世界重新带回到了黑暗的“新中世纪”(neo-medievalism)。[注]John Urry, Sociology beyond Societies: Mobilitie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ondon: Routledge, 2000, p.13.所以,伴随全球化进入更激进的网络化和数字化纵深阶段,我们也必须对网络技术和数字信息做全面的批判性反思。正如当代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奠基人达拉斯·斯迈思(Dallas Smythe)所言,“美国1945年以来在通讯和文化方面的外交奉行‘信息自由流动’政策,不过是其在世界范围内推行经济扩张政策的亲兄弟。”[注]达拉斯·斯迈思:《自行车之后是什么?——技术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属性》,《开放时代》2014年第4期。这一论断深刻指陈了数字技术的非中立性特征,数字平台背后输出的美国价值观也因之需要被进一步识别、揭露,网民群体则更需对此保持警惕且时刻坚定立场。
单一美化数字平台的观点无疑是错误的,但盲目否定信息技术也是亟需被打破的思维误区。我们对于数字平台的认识应放置于现实的政治经济环境中进行思考,这便要求我国学者坚守马克思主义立场,辩证地看待数字平台的二元属性。一方面,我们不可简单地认同新自由主义学者的预设,盲目将数字平台视为优化资源分配、实现共享经济的建设性力量。相反,现实已证明,数字平台进一步加剧了资本对市场的垄断,弱化了公众的社会权利和社会保障。[注]Frank Pasquale, “Two Narratives of Platform Capitalism”, Yale Law & Policy Review, 2016, Vol.35, p.311.一种体现美国意志的新型帝国主义正通过数字平台肆掠全球,它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利益和信息安全造成了巨大冲击。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认识到,数字平台本身其实蕴藏着潜在的解放维度。因为,数字媒体和社交网络不完全是虚拟的、群氓的存在,而是具有以集体化行动促进现实世界正义的巨大潜能。实际上,网民在基于平台的交往和互动中,已获得超越传统时空限制的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尤为重要的是,数字平台与各国网民事实上已形成了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所谓的物我合一的“行动者网络”。这种“技术赋权”的效能,提升了网民参与地区甚至全球社会治理的能力。网民因此不只简单地满足于平台为其提供的“虚假意识形态”,取而代之的是,他们会使用各种网络媒介和数字手段来推动现实变革。目前,全球各区域都已出现了从线上走向线下的群体、组织和社会运动,他们在公共空间中不断反思并揭露出当代帝国主义统治的丑恶面目。[注]Eric M. Fattor, American Empire and the Arsenal of Entertainmen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p.172.故此,破解技术问题的关键始终在于以社会建设的理念来引领技术发展,而非从抵制技术的层面去寻找答案,“见物不见人”的技术决定论更是应当极力规避的数字陷阱。
在数字平台对全球社会影响愈益加深的当下,我们应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提出的“四点原则”和“五项主张”为纲领,继续做好本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积极建构互联网的全球治理体系。[注]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2月17日,第2版。我们一方面要全力预防和回应平台帝国主义对中国隐蔽的经济掠夺及定向攻击;另一方面更要推动本土科技加速创新,建成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和共建共享理念的数字平台,向国际社会提供实现互联互通的中国技术和中国方案。尤为关键的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开展,我国数字平台必须成为联通“网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载体。总之,新时代的数字平台建设,不仅要持续发挥提升国际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功能,还需大力促进“一带一路”沿线网民乃至全球民众之间的互信互认,最终构筑起有益于全人类福祉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