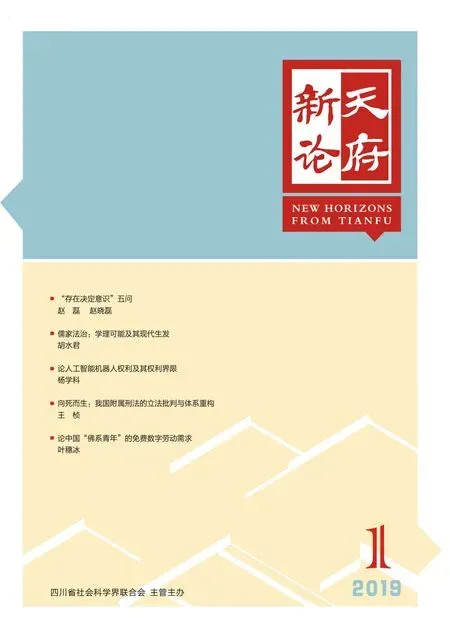暴力、文明与现代性
——埃利亚斯的暴力思想评述
2019-01-21周锦章
周锦章
尽管暴力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并以复杂的方式嵌入多元的社会文化历程之中,但却始终未成为社会理论的核心议题。纵观社会理论研究史,很少有学者将暴力作为研究的重心。多数人认为,现代性意味着人类普遍的理性化、经济增长、科技进步与社会和平。由于暴力既不是社会的常规状态也不是社会生活的内在特征,学者们往往将其视为非理性化的远古时代的遗留物,或无须深入分析的突发性异常,随着现代性的到来和扩张必将烟消云散。
有鉴于此,诺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对于暴力问题的探究显然为该议题涂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早在20世纪30年代,埃利亚斯就在代表作《文明的进程》一书中将暴力视为社会发展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他指出,随着外部社会控制的扩展以及自我约束的逐步内化,个人和集体暴力日趋消减。通过对礼仪的研究,埃利亚斯还审视了自我约束的发展对于个体暴力行为的抑制。而在《寻求刺激》一书中,他分析了橄榄球等暴力色彩浓厚的运动赛事以及英国的议会政治中对立双方学会通过信任而不是恐惧互相交涉和斗争。对埃利亚斯而言,暴力与文明水火不容,所以在人际关系和社会构型中摒弃暴力行为便成了文明进程(即现代国家形成过程中)的重要特征。具体而言,现代国家垄断了各种暴力的形式,社会调节较少依靠个体或群体的暴行,而越来越受到践行自我约束和相互克制的羞耻、厌恶和信任等情感的影响。总之,文明的进程从内外两方面对人类的攻击性和暴力行为施行约束。
本文试图检视埃利亚斯的暴力思想,一方面从心理生成和社会生成的角度对暴力与文明进程的关系进行解读;另一方面,则从现代性的暗面出发,对埃利亚斯的暴力研究进行批判性的反思。
一、暴力与文明的进程
被称为20世纪百科全书式人物的埃利亚斯,以研究西方文明的发展进程而享誉学界。他首屈一指地提出“文明”(或“文明化”)的进程,即欧洲在从中世纪到现代社会的变迁过程中,由于社会、文化和心理的复杂变化导致人际暴力的减少。这是因为现代国家垄断了暴力的工具,并通过控制、商业、城市化、财富和税收能力的发展维持疆域的和平。税收不仅扩展了军队实力和行政能力,而且形成了以非暴力方式处置冲突的相互依存和法律系统。随着越来越多的百姓安居乐业,劳动分工越来越复杂,人们相互依赖的集体意识逐步提升,社会控制也逐渐从外部他者的控制转变为自我控制。社会网络的复杂性和相互依存性的增加,导致个性的变化——广义而言,即情感从剧烈波动变成自我控制,时间感、事先筹划及自我算计和自律精神也与日俱增。宫廷社会礼仪方式的增加表明这些变化开始出现,随之扩展到社会各个角落,人们逐渐意识到围绕身体形成的羞耻感,并在日益明显的公私分化中越来越重视个体的私密感。相互依赖不仅是纵向上的也包括横向上的——上层阶级越来越依靠下层阶级,而处于上升中的阶层(城市资产阶级)开始复制宫廷社会的礼仪。没过多久,资产阶级渐渐地吸纳了这些贵族自律的标准,形成鲜明的禁欲道德观和情感;这些标准又从资产阶级向下层社会传递,最终成为整个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
埃利亚斯使用“文明”一词容易造成误导,毕竟它包含了殖民主义和自认优于其他民族的西方观念。一般而言,文明化意味着限制暴力且与军事社会截然相反的以德服人,即文明化是一个骑士阶层的权力和地位逐渐没落的过程。它同时包含了法治化的历程,如社会不满属于民事诉讼而非刑事案件。对埃利亚斯而言,关键之处在于对冲动和情感的自我控制。在辨析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文明历程时,埃利亚斯试图避免欧洲中心观,他认为所有社会都需要将社会成员进行社会化,并在“没有破坏、沮丧、卑微或以其他方式互相伤害”的情况下满足个体基本需求[注]Elias, The Germans, New York: University of Colombia Press, 1996, p.31.。所有社会都必须经历文明化的过程,这一进程从未完成且前途艰险。他指出,未来的历史学家在评价现在最发达的西方社会时,很可能将之视为“中世纪”的一部分,而他们的成员则是“晚期的野蛮人”。埃利亚斯始终认为文明的进程没有“起点”,即不存在人类尚未文明化和开始文明化的起点。
随后,为了驳斥工业化和城市化必将造成暴力上升的观点,埃利亚斯宣称,随着文明的社会互动方式的深入人心,人们对于暴力和虐待的容忍度越来越低。随着围绕身体形成的耻感和尴尬的增加(曾经大庭广众没羞没臊的行为,如排便和性交变得越来越私密化),人们越来越反感肢体暴力。同时,大多数人都摒弃自相残杀。在这种文化心理变迁的影响下,人们之间相互依赖的情感越来越宽广,埃利亚斯称之为“构型”。以个体利益为导向的多样化所形成的相互依赖的网络变动不羁且拥有自己的动力,但归根结底以有利于所有参与分工的、相互有密切关系的人群的最佳合作为依归[注]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王佩莉、袁志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340页。。构型不断地变化形式,国家内社会关系的现代性变迁也如出一辙。长此以往,武力的垄断、百姓的安居乐业、城市化及复杂的相互依赖逐渐成为新的惯习。
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第一卷《西方国家世俗上层行为的变化》中,对欧洲从中世纪至现代化时期的变化进行了全景的展示,认为欧洲的“社会惯习”发生了变迁。埃利亚斯宣称,在中世纪到现代社会的变迁中,文明礼仪首先出现在宫廷社会,随之扩展至整个社会。由于耻感和厌恶感渐入人心,原先占支配地位的习俗,如暴力、性行为、身体功能、餐桌礼仪和言谈方式也逐渐发生了变化。这些转变尤其要求人们根据与日俱增的社会复杂性和相互依赖性而将“自我限制”加以内化,这就涉及弗洛伊德所言的“超我”的力量。在第二卷《社会变迁文明论纲》中,埃利亚斯分析了文明进程的起源(特别是在国家权力的逐步中心化以及社会分化和现代社会相互依赖网络不断增强的背景下)的理论。与韦伯类似,埃利亚斯认为国家在疆域内对暴力合法性的垄断至关重要。
埃利亚斯提出,在中世纪社会,战争是常态,人们常常从虐待、破坏和折磨中寻找快感,例如虐待战俘、烧死异端分子及公开折磨和处决犯人等。然而,在现代社会中,暴力都集中在国家手中作为展示中央权威的手段,人们被迫互相生活在一个和平的环境里,情感模式和水准便会逐渐地发生变化[注]②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王佩莉、袁志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216页,第446-447页。。埃利亚斯认为,随着国家权力的中心化,社会对于个体节制和礼仪行为的认同日益增强,这种现象率先出现在宫廷社会,然后随着贸易、城市生活、更加复杂的劳动分工及“公民社会”的形成不断扩展。相互依赖的网络越持久和紧密,人们就越来越需要相互协调行为,互动中的暴力也越来越少。埃利亚斯以中世纪到现代时期人们旅行过程中的不同为例来阐述他的观点②。中世纪时期的旅行往往历尽艰难险阻,人们行走在泥泞的小道上,因为人烟稀少,相互冲突的可能性很小。然而,中世纪的旅行者必须时刻警惕动物、其他过客和土匪的袭击。时刻处于警惕状态容易使人们情绪不稳,稍微风吹草动就大打出手,因此个性较为冲动,遇事的第一反应就是求助暴力。现代旅行过程中的肢体暴力较为罕见,但冲突的风险大大提高。在这种情势下(现代社会典型的相互联系和复杂性),基于自律、高度警惕和先见之明的控制系统的形成至关重要。这要求现代人的个性不能冲动,而是要理性、精于算计和三思而行。
当然,现代社会的人们仍需要激情,主要由制度化和规范化的活动如体育运动加以满足,规则的限制减少了活动中的暴力和受伤的风险,但又能让观众体验到激情澎湃之感。体育的规则化使其过程中的暴力没有丧失自我克制,而观众却有机会在不用身体力行的情况下间接感受到打斗的激情,如格斗比赛。因此,“我们不再把观看绞刑、五马分尸和车裂当做星期天的娱乐活动。我们现在看足球比赛,而不是肉搏”[注]Elias, Quest for Excitement: Sport and Leisure in the Civilizing Process, Oxford: Blackwell, 1986, p.2.。当然,这一分析并没有提及观众之间发生的打斗行为,如今这一议题已经成为埃利亚斯的追随者邓宁(Dunning)的主攻方向。埃利亚斯描述了自我约束、先见之明以及结合了针对自身或他人行为的耻感、厌恶和尴尬等情感的个性结构的形成过程。在高度相互依赖的社会网络里,生存压力导致我们将他者或自身视为“危险区域”——我们对于他人的行为和自我内在本能的脆弱性感到焦虑。这些紧张的体验带来两种后果。首先,现代人类对外部世界直觉的“真实性”充满疑虑,自我和所谓的“他者”的界限泾渭分明;其次,人们因此容易将自我视为自由和独一无二的“主人翁”个体(埃利亚斯称之为“封闭的人”)。个体化和社会生活的私密性色彩越浓,羞耻感和自我控制的程度越深,导致人们认为自身“内在地”是某种完全自为、独自存在的个体,以至于掩盖了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彼此的依赖性[注]埃利亚斯:《个体的社会》,翟三江、陆兴华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33页。。
除了私密性之外,文明的进程还带来了非正式化,即随着社会距离、地位仪式和等级的弱化,人们彼此间的同情之心与日俱增且较不愿意诉诸暴力。非正式化则指社会关系的等级性开始松弛,规范行为的正式社会符号日渐消失。尤其是一战以后,这些变化不仅出现在相同社会等级的人们之间,而且在上层阶级和底层阶级之间也如出一辙。埃利亚斯以宫廷礼仪和德国大学生两性关系的变化来揭示这一社会转型。他对比了一战前后的仪式:一战前的仪式恪守历史悠久且十分严格的文化符号,如鞠躬、亲吻对方的手、使用正式的词汇“您”和“优雅高贵的女士”;到了20世纪晚期,当个体缔结社会关系时,往往只需要营造宽松的气氛即可[注]Elias, The Germans, New York: University of Colombia Press, 1996, pp.35-37.。因此,随着财富安全和社会角色分化的与日俱增,社会阶层间的距离日渐减少。后者意味着我们卷入多元角色的表演中,父母、情侣、公仆、教师、朋友或同事等社会关系中的正式化和等级情境逐渐淡化。齐美尔和戈夫曼等社会学家指出,竞争性社会互动需要管理千差万别的“自我呈现”。而正式化与非正式化之间梯度越小,我们在所有情境中的行为就越一致。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与之前相比,人们的行为举止越来越活泼,态度也越来越宽容,以至于“许多之前严令禁止的事现在畅通无阻了”[注]Mennell, Norbert Elias: An Introduction, Oxford: Blackwell, 1992, p.242.。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的交往越来越无拘无束,衣着也越来越随意,人们常常直呼其名而不是尊称。与过去相比,儿童的抚养方式亦较少权威化。20世纪早期以来,关于孩童抚育的文献开始谴责体罚、蔑视、吓唬小孩的童话故事以及情感距离和排斥等不当方式,鼓励家长培养孩子自治和自我控制的能力,尽量满足儿童的需求并采用正面鼓励的方式养成孩子的行为等。这带来了进一步的变化。在埃利亚斯看来,正式和僵化的社会互动意味着较高的羞耻风险(假如人们未能表现出预期的行为方式)和超我监督,而无拘无束和不按常理出牌的人则意味着更多的理性和自我规范行为的算计。这同时也包含了更高程度的自反性,即生活规划、自我创造以及萍水相逢的亲密关系等变化。然而,无拘无束意味着为了制造和维持边界,自我限制存在更多的张力,且带来更大的不安全感,毕竟由于缺乏正式规则,人们需要更多的随机应变。
埃利亚斯在晚年进一步提出(至少可以从他的著作中归纳出这一看法),非正式化和去等级化减少了人际暴力。因为社会距离和等级的松弛需要人们更多地进行自我限制,并在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们之间形成情感共鸣。由此可见,非正式化是文明进程的重要元素。当然,它也带来了相反的趋势。外在规范的缺失可能无法带来深谋远虑与娴熟的自反性行动者,反而会像拉什(Lasch)所言,造成人们的自恋、情感空虚和无视责任。基利敏斯特(Kiliminster)指出,新的愉悦可能来自对暴力场景的沉溺,而之前人们对此十分抵触[注]Kiliminster, “Narcissism or Informalization? Christopher Lasch, Norbert Elias and Social diagnosis, ”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008(3).。在商业化高度嵌入和“情感释放”的日常生活场景中,市场将迎合人们独特的口味。与之类似,沃特斯(Wouters)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平等理念渐入人心,人们只能在想象的王国里沉迷于危险的愉悦之中,典型的做法是通过“虚拟实境”建构暴力幻象,如电影《美国狂魔》 《天生杀人狂》和《低俗小说》[注]沃特斯:《非正式化:举止与情绪的探究》,张可婷译,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11年,第356-357页。。虽然非正式化带来自由表达和随心所欲,但最终这一过程增加了人们的相互依赖性,并因此形成社会纽带且减少了人际暴力。因此,媒体上的暴力影像并不会使观众对好勇斗狠无动于衷,反而使人们对其所造成的恶果更加一目了然且培养了陌生人之间相互关心的责任[注]Wilkinson, Suffering: A Sociological Introduction, Oxford: Polity Press, 2005.。
总而言之,通过解读埃利亚斯的著作可知,国家垄断暴力以及经济革命带来的安居乐业的复杂过程,使社会空间中人与人的相互依赖与日俱增。这意味着随着自我控制的内化程度逐渐提升,身体的耻感也日渐增强。伴随着社会功能的分化,民主化的程度越来越深,社会等级日渐松弛,非正式化意味着社会控制的增加和地位分化日渐模糊的人们之间拥有更强的情感共鸣,这反过来导致随意攻击的减少。当然,埃利亚斯并不认为暴力会因此减少甚至就此消失,而是提出人际互动中的情绪和冲动攻击将大大减少。
二、暴力与现代性的暗面
尽管埃利亚斯首次从社会学的角度探究暴力长期变迁的动态性、过程性和历史具体性,但其有关现代文明的愿景也存在不少张力和无法自圆其说之处。一方面,他所阐释的文明进程助长了殖民地开拓和大屠杀等暴力事件的发生。毫无疑问,西方人的“文明”优越感使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和法国等在开疆拓土中大开杀戒,所谓的“野蛮人”根本难以匹敌。在特定空间和语境中,“文明的进程”是一个日趋和平安宁的过程,但在世界的另一端或对于“文明的他者”而言又是极度暴力和血腥的。另一方面,文明的进程理论无法充分地解释战争的持久性和再生性。由于在定义上暴力和文明的历程呈反比,所以这一解释模型的逻辑推论一切暴力形式都将渐趋减少。这正是埃利亚斯所勾勒的欧洲社会的历史轨迹,与前现代世界“纯粹因为仇恨而置人死地”相比,在具有内在和平的“高度发达社会”中,个体通过平息“利益的矛盾”而和平共处。然而,暴力并没有日渐消逝,战争、革命、恐怖主义活动和其他暴力形式逐渐扩大化并越来越致命。单单20世纪就见证了超过250场的新战争,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死于非命。20世纪诞生了全面战争、大屠杀、毒气室、集中营、有组织的自杀式炸弹袭击和原子弹毁灭整个城市的惨剧。这表明了现代性与暴力之间的悖论,也是我们之所以反思埃利亚斯暴力社会学思想的主要原因之一。当然,笔者并不主张抛弃埃利亚斯的理论,毕竟它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文明与和平的起源,但为了全面审视现代性的另一面如何助长了暴力的社会动态机制,我们应该对这一理论进行反思。
20世纪50年代,汉娜·阿伦特在她著名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向读者介绍道:
一代人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其间一系列局部战争和革命从未间断过,其后被征服者未得到任何和平条约,胜利者也未得到休养生息,却以预料剩下的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能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而告终。这一等待的时刻就像丧失了所有的希望之后的平静。我们不再期望最终能恢复那种旧世界秩序及其一切旧传统,也不再祈望五大洲的人们重新统一团结;他们被扔进由战争和革命的暴力产生的混乱之中,而这一切的日益衰微仍被忽略了。我们看到同一种现象在不相同的条件下和全然相异的环境里发展——精神上的无家可归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漂流无根的心绪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
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依赖各种政治力量,我们无法相信它们会遵从尝试和自我利益的法则——如果根据本世纪以前的标准来判断,这些都像是疯狂的政治力量。人类似乎分裂成两种类型,一种人相信人无所不能(他们认为,只要懂得如何组织群众,那么一切都将是可能的),而另一种人则认为,它们生命中的主要经验是无力感。在历史眼光和政治思考的层次上,流行着一种含糊不清的共识,即一切文明的本质结构已经到了崩溃的临界点。尽管文明在世界的某些地方比其他地方保持得更好,但是它在任何地方都无法引导本世纪可能的前途,或对其中可怕的事件作出适当反应,绝望的希望和绝望的恐惧往往比起平稳的判断和审慎的洞悉未来,更接近上述事件的中心。比起那些鲁莽地一头钻进乐观主义的人来,那些全然相信世界将不可避免地毁灭的人会更善于忘却我们时代的各种中心事件。[注]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三联书店,2008年,第2-3页。
无独有偶,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的观点与阿伦特所见略同,他们也洞悉了现代文明的黑暗和绝望。在他们看来,法西斯主义和野蛮并非反常的疯狂,它们是“资产阶级文明”的结果:
我们本来的计划,实际上是要解释人类没有进入真正的人性状态,反而深深地陷入了野蛮状态,其原因究竟何在。
……在当代资产阶级文明崩溃过程中,值得追问的就不仅有科学的研究,也包括科学的意义。铁蹄的法西斯主义者虚伪颂扬的,以及狡猾的人文专家幼稚贯彻的,就是:启蒙的不断自我毁灭,迫使思想向习俗和时代精神贡献出最后一点天真。[注]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页。
彼时的知识分子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现代文明已经穷途末路。几个世纪以来,最文明的西方国家通过“殖民化”和“帝国主义”在地球的各个角落无恶不作。这一过程建立在破坏、强奸、抢劫、折磨和屠杀的基础上。为了追逐权力、威望和利润,非洲约有1000万人(包括男性、女性和儿童)惨遭不幸,被充当奴隶运往欧洲的殖民地。数以百万计的人在运输过程中、种植园、矿山或其他可怕之地由于恶劣的条件丧生。在澳大利亚和美洲,原住民被“文明”人不择手段痛下杀手。简言之,“文明人”非常暴力,正如法国政治家G. 克雷孟梭(G.Clémenceau)对J. 费里(J. Ferry)在1885年巴黎高度“文明”的国民大会上的发言的回应:
看看对于这些你们称之为野蛮人的征服史,我们将看到暴力,不受约束的犯罪、压迫和血流成河,弱者遭到践踏,胜利者作威作福!这就是我们文明的历史……多少令人发指的罪行以正义和文明的名义被实施。更别提欧洲人为他们带去的恶习:酗酒和鸦片。你们简直为所欲为。
“可怕!可怕!”这是J. 康拉德(J. Conrad)小说《黑暗之心》中的殖民统治者库尔兹(Kurtz)最后的临终遗言。这是所有他能记住的关于殖民者在非洲殖民地刚果所践行的“文明”活动。恐怖仍是我们“文明”的一部分。从欧洲殖民者在殖民地第一次杀戮、折磨或强奸,到巴黎或伦敦街头最近发生的恐怖行为,我们仍生活在现代性的暗面之中。除了埃利亚斯论述的相对和平的进程,在文明漫长的多元互动链条中还包括血腥的屠杀暴力,它们并非暂时的“去文明化”,而是现代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坚持文明化与暴力固有的不相容性,埃利亚斯误诊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在埃利亚斯的著作中,文明的历程被视为一体两面的现象,一方面通过这一过程个体学习如何约束自身“自然”的破坏性冲动,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秩序也变得越来越平和。然而,文明化与暴力行为不仅完全叠合,正如所有集体暴力都需要相当程度的自我约束一样,而且更重要的是,文明化是集体暴力的摇篮。早期文明正是通过战争和独特的文明所创建,并通过集体暴力加以扩张。欣策(Hintze)、奥本海默(Oppenheimer)和蒂利(Tilly)的研究清楚地表明,国家的形成与发动战争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注]蒂利:《集体暴力的政治》,谢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埃克哈特(Eckhardt)通过详细的数据也证明,文明化历程与集体暴力具有某种选择性亲和,即与早期文明相比,晚期的文明更容易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暴力并非文明的他者,而是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注]Eckhardt W., Civilizations, Empires and Wars: A Quantitative History of War, Jefferson, NC: McFarland, 1992, p.3.。
当然,埃利亚斯曾经强调文明的进程存在退回的可能,在这个意义上,类似大屠杀不过是漫长的“文明进程”中的暂时现象。他曾试图用“去文明化进程”的概念来修正解释模型。在分析纳粹和大屠杀时,埃利亚斯指出文明的历程偶尔会发生逆转,所以集中营、毒气室、折磨和种族清洗等行为可以被视为“最严重地退回野蛮主义”,即一切内在和外在约束以及个体都回归到“兽性自我”。但在笔者看来,“去文明化”概念自身也存在问题。即便对埃利亚斯的理论抱有同感的学者如平克(Pinker)也承认这一说法的局限性:
埃利亚斯的祖国德国在“二战”中的非文明行径,使他本人备受困扰,他颇费周折地解释了自己的理论框架内存在的“去文明化进程”。
如果说他的这些分析挽救了他的理论,实在有些勉强,他也许根本不应该做这些尝试。纳粹时期的恐怖不同于领主之间的烽火狼烟,更不同于市民在餐桌旁互捅几刀,其规模、性质和起因都完全不同。[注]平克:《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安雯译,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第99页。
实际上,这种超现实的暴力颇具现代“文明”欧洲的色彩。例如,鲍曼(Bauman)一针见血地指出大量文质彬彬的公务员、工程师和科学家卷入的大屠杀具有官僚主义的特点。从官僚主义的中立逻辑看,大屠杀是一项社会工程。受害者并不是惨遭霍布斯式处于自然状态下的“野蛮人”的毒手。它既不是“去文明化的勃发”或“崩溃”,也不是简单地源自德国具体的社会发展过程及对纳粹统治者的尊奉,即便这些现象在有组织的大屠杀过程中一目了然。大屠杀具有现代性的意味。出于各种理由,不管是从道德的角度还是担心其故态复萌的恐惧,我们当然愿意将大屠杀与文明相互剥离,因为这容易使社会普遍弥漫着也许我会像“文明”的德国人那样对无辜者持刀相向的恐慌。所以,更加严峻的挑战在于逐渐接受这样的观点,即我们的文明也存在暴力的一面,暴力有时不仅是一种社会荣耀,而且在文明进程中扮演着中心角色。
正如鲍曼所言,无数专家都认为“大屠杀是一系列独一无二却尚未完全明确的社会心理因素的特殊组合产物,这导致人们通常秉持的文明行为暂时停摆”。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将或多或少重蹈古典社会学的覆辙,即认为与“文明”不相符的暴力事件都被视作社会化失败的“反常”过程。然而大屠杀、种族灭绝以及两次世界大战绝非文明的倒退,而恰恰是迈向新时代的结构性“进步”。现代性为大屠杀提供了组织和意识形态工具。大屠杀并非现代性的异数,它只可能出现在现代时期和文明的进程中。启蒙的现代性遗产孕育了宏观且往往互不兼容的创造理想社会的意识形态蓝图,现代性提供了高效的官僚机构,科学和技术则为实现这些宏大远景提供了条件。因此,种族灭绝成了实现宏伟设计的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设计赋予了大屠杀以合法性;国家官僚体系赋予了它工具;社会的瘫痪则赋予了它“道路畅通”的信号。[注]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史建华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51页。正是文明化,而不是缺乏文明,成为数以百万计的人遭受有组织且持久的大规模屠杀的关键所在。
总之,埃利亚斯为我们理解某些社会生活领域的平和安乐提供了相应的解释。但他的观点也有缺陷和未尽如人意之处,毕竟他看不到现代性也从另一面导致暴力潜滋暗长。
三、余 论
综上所述,埃利亚斯的暴力思想主张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的相互依存,即暴力和攻击行为能够被国家等社会组织漫长的历史变迁和与日俱增的自我约束加以驯服。在这一背景下,埃利亚斯的过程社会学成功地超越宏观-微观/结构-能动性的理论模式,它强调结构和行动具有内在的动态性,并将人类社会的暴力构型视为处于不断波动和变化状态下依具体情况而定的过程。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埃利亚斯的观点更多的是针对现代和西方国家(如法国和英国)特定的“文明的进程”。与其他社会理论研究类似,只有将其视为具体社会过程中存在局限性和不完整性的阐释,这一理论才能更富有成效。实际上,社会学的文本和理论往往具有开放性,与具体的社会进程息息相关(远非放之四海而皆准),永远难以尽善尽美。在埃利亚斯看来,文明的进程试图克服的人类固有的野蛮和动物性,没有文明进程的制约作用,我们容易卷入野蛮的相互厮杀之中。由此可见,暴力并非社会组织或行动的产物,而是源于一成不变、与生俱来的、将他者视为满足原始欲望和需求之手段的渴求。由于埃利亚斯的社会本体论建立在黑盒子式的线性时间观的基础上,所以任何可能干扰或阻碍文明进程的事件都是历史的“倒退”。因此,埃利亚斯并没有意识到暴力实际上也是意识形态、社会认同和群体整合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埃利亚斯的和平、内敛和(潜在的)直线进化的准目的论乌托邦中,他始终无法直面暴力的纯粹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