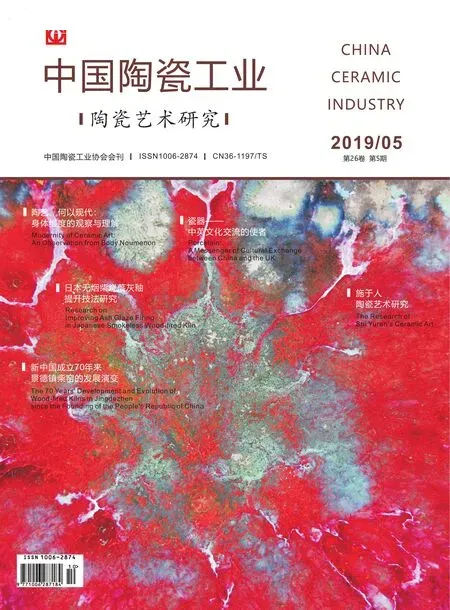陶土与神话
——“泥土造人”刍议
2019-01-21朱怡芳
朱怡芳
(江苏师范大学,江苏 徐州 221000)
1 有关人类起源的“泥土造人”说
纵观世界各地不同民族关于人类起源的神话传说,屡见“泥土造人”之说。特别是在中国本土,不仅汉族有女娲用泥土造人的溯源,各少数民族还有诸多关于人类起源的神话传说。当中虽然有卵生说、石生说、感生说、猿变说、精变说、果变说、葫芦变说、污垢变说等多种起源说,但是能够从丰富的少数民族文献和口述史资料[1]中统计发现,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中有三十二个民族都有与泥土相关的人类起源说,而且某些民族的人类起源有多个传说版本,比如蒙古族、回族、鄂温克族、塔吉克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撒拉族、土家族、傈僳族、独龙族、鄂伦春族、高山族、苗族、瑶族、黎族、彝族等。
泥土造人的造物主,既有天神、盘古、伏羲、女娲及特定名称的神,还有上帝、佛祖、玛祖、真主、造物主等宗教神,以及有神性的人物,比如祖先、巨人、神仙、人皇,甚至还有打柴郎。撒拉族有真主用泥土捏出人形阿丹的历史传说[2];哈萨克族有“上帝用土、水、火和风造人祖和人母夏娃”[3]的说法;广西的苗族流传着“纳罗引勾(半人半兽的巨人)用泥做男娃女娃”[4];仡佬族有“天神用泥造头曹人”[5]的故事;布朗族流传“天神布桑改沙和雅桑改西分别用泥土捏成男人和女人”[6];达斡尔有“天地开辟时天神用泥土捏造人类”[7]的说法;蒙古族有“当寰宇有微微曙光的时候天神用泥土造人”[8]的故事;青海的土族流传“山崩地裂后剩下的一个打柴郎捏泥人全都复活”[9];新疆的塔吉克族流传着“安拉命众天使下降到大地上,用泥土造人”[10]。
泥土造人说中通常涉及材料、方法、过程内容。尤其是泥土,在中国少数民族神话传说中出现的,主要包括有:用黄泥土造人,或是红土、白土、棕土,又或是五色土、七彩色土、多彩色土造人,甚至还有净土、泥垢、黏土、五方土、神土、山上的土、烂泥等特征的泥土造人。譬如,云南大理地区的白族流传着“人王公和人王婆是天地分开时用黄泥捏人和万物的祖师”[11];云南地区的怒族口传是“天神用红土沾泥造人”[12];云南红河州的彝族流传的是“天上的托罗神和沙罗神两个大神看见地面的山脚下,一边有黄土,一边有黑炭,还有一边是白泥。他们用这三种东西造人。”[13]由于有的民族因聚居地的变化和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发展,在泥土造人的同源历史中又出现各类版本,例如黑龙江牡丹江地区的回族中流传着“安拉用红、白、蓝、黄、黑五色土造出一个有特殊本领的人,起名叫阿丹,把他安排在伊甸园,叫他在园里耕种、看管”;[14]但是青海黄南州地区则流传着“天堂上的仙人们结伙到大地准备取土造人,但大地说‘真主没有命令,不能给五色土’,仙人们先后来了六次,没有取上五色土,每次相隔一千万年”;[15]宁夏中卫地区流传的是“真主命阿兹拉伊来(天仙名)用洁净的土造化人,天仙用净土造化出人祖阿丹”;[16]宁夏银川地区则流传着“天使按真主的指令,取红、黄、兰、白、黑五样土后带回天堂,真主用香水和五样土,造人”;[17]广西南宁地区流传的是“安拉用香灰拌泥造人”;[18]内蒙古的鄂温克族流传着“天神宝勒哈(天神,有时亦称“宝勒哈•巴格西”,“巴格西”为“佛师”之意)从五洲取来金土,从四海舀来银水和成泥团,用它塑造人类”。[19]
泥土造人的材料,除了泥土外,还会有使用其他元素的情况,比如用水、尿、奶与泥土混合而造人的方法最为常见。当然,泥土与其他要素一起化合变成人,不限于以上液体,从各民族的神话传说中还发现丰富的材料内容,像是汗、泥沙、砾石、肋骨、血、肉、尿、毛、光、灵魂、气、风、火、水、雨水、河水、海水、神水、银水、金土、黑炭、兽皮、香灰、兽骨,以及树木、荷叶、芦苇、葫芦等植物。黑龙江的鄂伦春族流传着“天神恩都里用野兽的肉和毛扎成10 男、用泥做成10 女”的故事;[20]新疆地区的哈萨克族流传“安拉为了使它具有生命活力,就把世界上的好东西混在土中,用水和成泥造人”。[21]
至于泥土的来源,有的从大地自然中来,有的从身上搓出泥、从岩石上搓出泥、从动物处获得,还有偷来、借来、受帮助得来的情况。新疆柯尔克孜族流传着“安拉要造人类时,便招来天神让他到大地上给取回一把泥土”的说法;[22]黑龙江地区的满族有“阿布卡恩都力(天神)用身上搓落的泥做成人”[23]的故事;独龙族流传着“天神嘎美和嘎莎用双手在岩石上搓出了泥土,用泥土揉成了泥巴团,又用泥巴团捏人”;[24]黑龙江地区的鄂温克族有“尼桑萨满帮保鲁恨巴格西佛师射龟取土造人”[25]的说法。
泥土变成人,有神吐出来的,有从土里直接生人,还有用光和泥造人、用泥土代替石头造人等情况,比如在维吾尔族关于女天神创世的神话中就讲“女天神吞进去的尘土都吐出来了,成了泥巴。这些泥巴星星点点从天上飞下来落在了地球上的各个地方,变成了许多矮小个子的人”。[26]有些情况下,泥做成的泥形还需要其他因素才能变成人,气息和灵魂则成为活起来的要素。给泥土吹气变成人的传说,比如福建宁德的畲族有“皇天爷与皇天姆用五色土造出的男女,吹灵气成活”的故事;[27]云南彝族流传“天上的托罗神和沙罗神两个大神用黄土、黑炭、白泥造出男人和女人太阳晒了7 天之后会动,但还不会呼吸,托罗神和沙罗神就朝男人和女人的嘴里吹了一口气,人就会呼吸了”;[28]傣族的《巴塔麻戛捧尚罗》经书中有“两个神用黄土做人,吹仙气变成活人,即人类祖先”;[29]蒙古族流传“母亲神用羊皮缝的人形中填塞泥土后,吹入灵魂形成了人类”。[30]
除了用捏泥、蘸泥、揉泥等方式造人,这些神话传说中还体现了采用窑火来烧制泥人的情况,也有用火烧干后、太阳晒后、日月和风雨洗礼后成活为人,以及泥人放在地上成活,埋在地里成活的情况。例如黎族流传着“很久以前,神仙把葫芦瓜开了个口,把用泥土捏成的哥妹两人放进去,洪水后经过日光和水的作用,成活”[31]的故事。此外,泥土作为无生命物能够生人,或是发生变化后变成人,比如云南德昂族的神话中:几个天神飞到地上吃香土后就不会飞了,只好留在地上,后来变成了人;[32]傈僳族的传说中“天神木布帕造地后,又用泥土捏了一对猕猴,猕猴慢慢长大变成人形,从此地上开始有了人”。[33]
用泥土造人也会遇到不成功的情况,泥人可能一开始不能呼吸、眨眼,不能活,有的因为失败结果反而变成了陶器,像是水缸和罐子之类的器皿。湖南土家族的神话里“李古老用泥巴做人,做了七天七夜,头有了,身子有了,脚手都有了,坐着不会出气,站起来不会走路,结果做人没有做成”;[34]广西瑶族流传着“密洛陀(创世者、女始祖)先用泥土来造人,没有造成人,却造出了水缸”。
在这些人类起源神话中,泥土造人或变成人的天数,比较常见的是7、9、12、49、81、360天等。例如,广西地区的壮族流传着“姆洛甲(女始祖)捏了很多泥人,用草盖起来,经过49 天,这些泥人活起来了”。[35]这些天数既能反映出客观的生产周期,也表明不同民族文化使用特殊数字的象征关系。
2 从造人形到造人性
中国古人将制陶工艺称为“陶埏”,这种概括精简贴切而寓意深刻。捶击、踩踏练泥为“埏揉”,喻意磨练人的脾性;和泥、陶冶制作为“埏埴”,也喻意后天的教化、培养。制陶是凝气精神的工艺,更是孕育培养、陶冶人性的艺术。它虽被喻为泥与火的艺术,但实则在土、水、火、气的融合中生成,心凝而形释。从不定形的泥土到定形的陶器,对应在人的文化结构中之人的规训和可塑性,神话传说中的泥土造人、制陶术、制陶人本质上正是揭示人性教化和人伦构建对社会存在和发展中起到的核心作用。
不仅在中国各民族的“泥土造人”母题神话中,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人类学家关注的生存在现代时期的土著文化中,也能发现“土-陶-人”之间的联系与文化隐喻。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克罗德·列维-斯特劳斯曾在《嫉妒的制陶女》中通过北美洲和南美洲的有关神话剖析了制陶的社会文化意义。他指出:“陶土首先呈现出的是一种不完全定型的状态,制陶人或制陶女的工作,就是使一种原本不具有一定形状的物质材料变得具有一定的形状”;[36]“制陶人或制陶女的技艺就是对一种没有固定形状的物质材料来加以限定、压缩、拿捏和塑型。”从美洲神话中,可以发现较多情况下都是女性作为制陶者。卡斯滕也曾强调过女性与陶器的等同性问题:“制造陶器和使用陶器的责任都交给了印第安女人,因为人们制陶用的黏土就像土地一样,是属阴的——换句话说,黏土具有女人的灵魂……制陶重任在身的女性与她们使用的土壤和黏土之间,有着一种有趣的连接。在印第安人的思维中,陶器就是一个女人。”[37]这种现象无独有偶,世界上有些地方的制陶多是专门由女性来负责的,有些地方的文化中陶器代表了女人又或是女性身体的一部分(具有生殖功能的部分),在有些原初文化中,女性怀孕时的身形甚至被称作“陶罐的形状”。
从定形到定性的限制和教化过程中,制陶术的传承文化中可见各种戒条和禁忌。不仅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将某些原料与神奇现象和宗教性的复现联系在一起,表述制造或使用陶器等器皿所含的意义,甚至对材料选取、工艺细节、规定制作者、烧造仪式等方面极度认真的态度,这都属于原初社会的“哲学”。例如,制陶过程中不能出声,受欢迎的女性所制陶艺高超,制陶者独管土地等等。
正如列维-斯特劳斯论说的,一切技艺都是将一种物质限定在一种形状之中。制陶的泥土外表粗糙、结构松散,视觉、触觉乃至知性都面临一片不定型的物体和一种蛮荒的原始状态。亦如《圣经》对创世之初的描述是大地没有一定形状而且是裸露的。由此,天地造物者的作品与制陶者的陶器在文化语义上有对应的结构。将某种物质限定在一种形状中,既有制服这种物质的隐喻,又意味着当人们将一种物质从无限的可能性的领域中取出利用的同时便是缩小了它的其他可能性,这种物质最后只能实现某几种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和限制性是相关的,从材料和技术上来看,几百种微小的变化都会给陶罐造成毁灭性的或无法实现使用功能的后果。具体来说,当人在选择陶土、釉料、涂料、焙烧温度、烧造方式时,任何微小的差池都会将一周乃至更久的制陶劳作化为乌有。因此,为了制成陶器,制陶者必须严格遵照经验总结而得的最能避免失败的方法,不可违背的经验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制陶匠人的保守精神,也反映出对那些会改变他们生活和生存可能性所抱有的戒心,比如世代的模仿和遵从,又如制陶技艺在家庭中的独门相传。[38]
在古埃及神话中,人类是由圣神哈奴姆在陶器作坊中用泥土塑成的。如果从造人形到塑人性的意义上去理解神话寓意的话,泥土就是人本身,形成的人性就是制陶术和成为器的过程及结果。
3 再造现代版的“泥土造人”神话
用泥土造人的神话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39]在人类文明与文化的发展历史中,泥土与人的关系似乎是先天性的,无法割裂。对泥土、大地的改造与加工,特别是制陶的造物遗迹证实着世界范围内曾有的人类文明历史。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是神话母题的“泥土造人”说还是远古的制陶业,都是必然的历史纽带,将人与土地在本质上统一起来。人类的共同经验证明土地能养育人类万物,正如《释名·释地》中界定:“地,底也,言其底下载万物也”,“土,吐也,吐生万物也”。土地是人类物种存在的根本,是人类繁衍生息之依赖,是人类的起源与归宿,对于农耕民族而言更甚。由此产生的土地膜拜、民间对土地神的祭祀风俗,在反映对土地敬畏、崇拜的同时,也暗示了人与自然互动的公平性与经济性。因为想要从经营的土地上得到丰饶的回报,就必须顶礼、供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皇天后土”、“社稷”都是关于这种伦理观念的体现。
神话在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伦理教化作用。它约束人并有教旨性,让人对大地、泥土保持敬畏之心,使人与土地、自然长期维系和谐共生的状态。泥土和大地是人类的来源也是归宿,如果对自己身体之源的泥土都不尊重和珍爱,就怕在工业化急速发展的今天乃至不远的将来,再也没有什么是人类不能改造的了。
各民族传统的“泥土造人”说在今天可能并不适用,但是这些文本和观念存在的意义,并非让人猎奇某些神话历史。其实,它在任何时代都有深刻的伦理意义,最基本的就是生态伦理观,这也是本文最后要提出的现代人也有必要书写再造现代版的“泥土造人”神话。
十七世纪以来科学的分野,促进科技超速发展的同时,人文和人伦也遭受着毁灭性的解构。现代文明过分强调人改造自然的能动性,将土地作为资源和资本利用开发的对象和无生命的形式进行贪婪的榨取,使得生态自然破坏加剧。不仅如此,人类与土地的冲突在自然、经济、政治多个方面恶化,导致人对土地的依赖和崇拜之情淡化疏远。在这种趋势下,如果换种方式思考,那么可以理解国家对振兴农村发展、传统工艺、乡土文化的政策,亦是试图唤起人们对土地自然的“原生”情感,正如大地伦理(Land Ethic)的倡导者、美国环境学家阿尔多·利奥波德所指出的“大地伦理将人类在共同体中的角色由征服者改为共同体的普通成员。这意味着人类要尊重共同体的其他成员,同时也尊重共同体本身”。从生态伦理角度,以及人伦的立场,他倡导人类在这个时代应该从土地的征服者转化为土地的共同体成员,呼吁人类对土地热爱、尊敬和赞美,这种现代社会人地关系中的情感诉求难道不是现代版的“泥土造人”神话吗?
利奥波德认为现代文明以来,人们对待大地就如同俄底修斯的女奴一样,大地只被当作人的财产,任何与土地自然的关系都演变成了以经济的个人利益为基础的单向性的索取,而人类在享受特权的同时却没有任何伦理约束及义务说明。他的理论特别强调将土壤、山川、大气层等地球的各个组成部分拟人化地看成是人的器官,只有整体协调运作才能良性存在,而且只有真正尊重了大地共同体(植物、动物、水、高山等)、履行对共同体的义务,人类才能在自然因果中长久和谐地生存下来。
综上所述,“泥土造人”已经成就的陶土神话,或者说人类文明历史的神话,不是一个过去时,“泥土造人”的伦理意义在今天仍然持续发酵,并由现代人书写着今时对未来的启示和寄语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