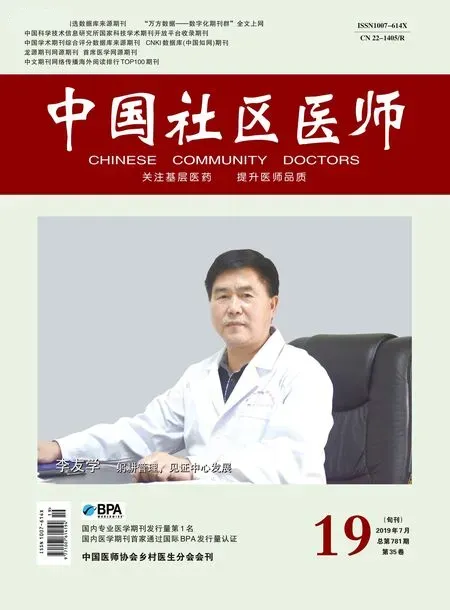类承法运用乌梅丸临床经验探讨
2019-01-17王功峰王言艳类承法
王功峰 王言艳 类承法
276023山东省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医院,山东临沂
类承法,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医院主任中医师、山东省五级中医药师承教育项目第四批指导老师。师承山东省名中医,国家第三批老中医学术经验继承指导老师刘启廷主任中医师,临床尤其擅用经方治疗内科杂病。近年来类承法主任医师应用乌梅丸治疗内、外、妇、皮肤等多种复杂病证,疗效显著,2016年笔者有幸被遴选为其学术继承人而侍诊左右,深得恩师教诲,受益颇丰。现将类老师运用乌梅丸的经验介绍如下,与同道共飨。
乌梅丸配伍分析
乌梅丸出自《伤寒论》338条[1],主治“蛔厥”“又主久利”。本方由乌梅、细辛、蜀椒、黄连、黄柏、附子、干姜、桂枝、当归、人参、苦酒、米饭、蜜组成。该方重用至酸乌梅、苦酒为君,姜、椒、辛、附、连、柏,大辛大苦者为臣,参、归为佐以调气血,桂枝以散风邪,米饭与蜜护中。结合药物性味与功效,分析乌梅丸的配伍特点如下:①刚柔相济,体用皆调:肝为“将军之官”体柔而用刚。乌梅丸重用酸柔之乌梅,并醋渍,“酸入肝”配伍甘温之人参、当归、蜂蜜、米饭,“酸甘化阴”合用则滋肝阴,补肝体。配伍辛温之附、桂、椒、辛,则补肝阳,助肝疏。如此甚合《内经》“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补之,酸泻之”之大法。以苦寒之连、柏佐制辛温之烈。乌梅一味,功兼补肝、敛肝、顺肝三用。全方配伍刚柔相济,体用皆调。②寒热并用,补泻兼施:乌梅丸既有辛热之附、桂、椒、辛温补阳,又有苦寒之连、柏泄热,寒温并用,温阳不化火、清热不助寒;配参、归、蜜、米饭,助温阳之功,防苦寒之弊;乌梅酸收,故本方具中和之性、和解之功。③辛开苦降,调畅气机:方中重用乌梅敛阴和里,以辛温发散之附、桂、辛、蜀、姜宣通阳气,甘温之参、归补气和血,伍苦寒沉降之连、柏清泄邪热。综观全方,配伍严谨周密,清上温下、调和气血,实为“治厥阴,防少阳,护阳明之全剂”[2]。毛进军认为[3],乌梅丸方中暗含《伤寒论》5个经方的方药及方义:四逆汤,大建中汤,当归四逆汤,黄连汤,干姜芩连人参汤,此方寒热药并用,有温阳通脉、清上温下等诸多功效,寒热表里气血同治和通治,是治疗厥阴病本证的代表方。
乌梅丸证治病机
《伤寒论》对乌梅丸主治病机的论述第326条:“厥阴之为病,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疼热,饥而不欲食,食则吐蛔。下之,利不止。”第338条“伤寒,脉微而厥,至七八日肤冷,其人躁无暂安时者,此为脏厥,非蛔厥也。蛔厥者,其人当吐蛔。今病者静,而复时烦者,此为脏寒,蛔上入其膈,故烦,须臾复止;得食而呕,又烦者,蛔闻食臭出,其人当自吐蛔。蛔厥者,乌梅丸主之,又主久利。”其中326条主要突出了肝经郁热的症状,而338条突出了脾肾虚寒的症状,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共同体现了厥阴病寒热错杂的复杂病机[4]。病至厥阴,两阴交尽,阴尽阳出,若阴阳之气不相顺接,则阳气难出,阴阳失调。阴尽则阳生,寒尽则热生,从而表现出寒热错杂之上热下寒证。《诸病源候论》曰:“阴阳各趋其极,阳并于上则热,阴并于下则寒。”刘渡舟先生说[5]:“其组方特点反映了厥阴病的基本病理变化,即由厥阴疏泄不利,气机失调,以致寒热格拒上下,上热下寒,阴阳之气不相顺接,并进而导致脾胃不和,升降失常。”此外,厥阴病多在丑时(凌晨1:00~3:00)发病或加重,“厥阴病,欲解时,从丑至卯上”,可知丑时当为足厥阴肝经所主,这与厥阴病寒热错杂、阴阳之气不相顺接的特点以及其欲解时证的发病规律相吻合[6]。蒲辅周先生曰[7]:“外感陷入厥阴,七情伤及厥阴,虽临床表现不一,谨守病机,皆可用乌梅丸或循其法而达异病同治。”
类老师经验总结
乌梅丸在《伤寒论》中主“蛔厥者”“又主久利。”清代以来,诸多医家认为,乌梅丸不但主治蛔厥、久利,更是作为厥阴病的主方治疗上热下寒证。清柯琴在《伤寒来苏集》中就指出:“乌梅丸为厥阴主方,非只为蛔厥之剂矣。”[8]历经现代医家的临床研究验证,其适应证涵盖了内、外、妇、儿各科疾病,成为多种疑难杂症的验方[9-10]。类老师精研岐黄,熟读经典,博采众术,兼收各家,尤其结合清代医家吴鞠通《温病条辨》中所载学术思想及当代伤寒大家刘渡舟教授的临证经验,在临床治疗内科杂病、妇科等疾病的过程中,类老师谨守病机,善抓主症,审因析机,病证结合,灵活加减,做到证治相应,方证一体,知常达变,举一反三,广泛运用乌梅丸[11]。凡辨为肝郁证而使用柴胡类方剂无效,寒热错杂、虚实相兼者均可应用乌梅丸治疗;若有部分病证在下半夜出现或加重时,亦可选用乌梅丸。类老师运用乌梅丸,第一重视抓病机,谨守乌梅丸证阴阳不通、寒热错杂的病机,掌握乌梅丸证的证候表现,凡属阴阳失调、寒热错杂、虚实相兼、肝风内动、气血不和之证者,见是证用是方,就可根据方证相应原则选择乌梅丸辨治。正如《素问·至真要大论》曰:“谨守病机,各司其属。”第二注意权病证,从八纲辨证来说,乌梅丸证涉及寒热虚实、表里阴阳。类老师遵循仲景“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的辨证论治大法,擅于根据患者体质、病情、兼夹证等不同,权衡气血阴阳盛衰变化,判断寒热虚实轻重缓急,灵活调整化裁乌梅丸。例如肾阳虚明显者,以肉桂代桂枝,或二者同用,并加大附子等温热药的比例;如热象甚者,则加重黄连、黄柏等寒凉药,缩减寒凉之品;风甚者,酌配防风、钩藤、木瓜、白芍等。第三强调“欲解时”抓时机。欲解时,是指有利于病邪解除的时机。《伤寒论》第328条曰[12]:“厥阴病欲解时,从丑至卯上。”这三个时辰中,寅、卯时与少阳病欲解时相重合,此时正处于阴尽阳生、极而复返的时段,若阳长而阴消,阳进则阴退,阴寒得阳生之气,阴阳之气交接顺利,则寒退而病解。顾植山教授对欲解时的独到见解为“相关时”,他认为,丑时至卯时正值阴气将尽,阳气初生,由阴出阳之时间节点,故厥阴病在丑时至卯时若“得天气之助”“值旺时而解”则病愈[13]。临证中但见疾病于下半夜丑时至卯时发作或症状加重者,即可选用乌梅丸,若症状出现口干、四肢厥冷等机体阴阳失调、寒热错杂之症,用之更可效如桴鼓[14]。
验案举例
患者,男,55岁,2018年10月8日初诊。失眠5年余,加重1周。患者于5年前因家中出现重大变故而失眠,入睡困难,睡后常于1:00~3:00左右易醒,醒后难以入睡,多梦。经多种中西药治疗,效果欠佳。后靠睡前间断服用阿普唑仑片1~2片方可睡3~4 h,烦躁,口苦,口干,双下肢发凉,夜尿2~4次,大便溏。舌淡红苔腻略黄,脉弦细。辨为上热下寒证,治当清上温下,治以乌梅丸原方,方药组成:乌梅30 g,桂枝10 g,附子6 g,干姜6 g,黄连6 g,黄柏10 g,蜀椒6 g,细辛3 g,党参10 g,当归10 g,7剂,水冲服,1剂/d。二诊:失眠有所好转,睡眠可达到5~6 h,间断服用阿普唑仑1片,心烦,舌淡红苔黄腻,脉弦。效不更方,7剂继续服用。三诊:疗效颇佳,睡眠良好,自诉“5年来从来没睡得如此舒服”,心情舒畅,舌淡苔薄白,脉稍弦,予以乌梅丸巩固治疗半个月。随访半年,一切良好。
按:类老师认为患者失眠多年,多方治疗效果不明显,伴口干、口苦,下肢发凉,大便溏,提示上热下寒,寒热错杂。阴阳之气不相顺接,阳不入阴,故失眠。此外,患者在丑时(凌晨1:00~3:00)发病或加重,符合“厥阴病,欲解时,从寅至卯上”的特点,治疗当以清上温下、调和阴阳为法,以乌梅丸治之,因方证对应,故收良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