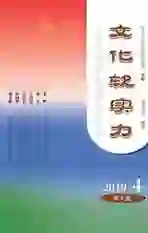甄别“四种思潮”,防止“四大陷阱”
2019-01-15彭国华
彭国华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就进一步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作出了新的顶层设计,强调要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并提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这一重大创新论断,强调要加强和改进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建立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的体制和机制,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注意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参见: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在京举行[N].人民日报,20191101(01).这些重要论述为我们推进新时代思想政治课改革创新提供了根本遵循。
下面我想谈谈怎样守阵,如何甄别“四种思潮”,防止“四大陷阱”。因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旗帜鲜明地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思想观点,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必须对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所出现的种种社会思潮进行深入的把握和科学的甄别。当前,无论是在网络的虚拟空间和现实的世界,有四种社会思潮值得特别关注,分别是新自由主义、宪政民主论、“普世价值”论和历史虚无主义。在这“四种思潮”中,新自由主义主要针对的是我国的经济体制和经济制度,宪政民主论主要针对的是我国的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普世价值”论和历史虚无主义主要针对的是我国的核心价值观以及历史文化。这四者相互勾连,对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形成合围的态势。这四种思潮泛滥的结果可能产生“四大陷阱”,即“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西化分化陷阱”和“塔西佗陷阱”。
一、新自由主义与“中等收入陷阱”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贫富分化、腐败多发、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等局面,难以实现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型升级。
如果在我国推行新自由主义,必然会使我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美国左翼经济学家大卫·科茨曾概括出新自由主义的七个主要特征:一是要清除商品、服务尤其是资本在全球经济系统内自由流动的障碍;二是政府不再扮演引导和调控经济的角色;三是国有企业和公共服务私有化;四是削减政府的社会福利计划;五是向累退的税收政策转变;六是从劳资合作转变为在政府帮助下的资本单方统治;七是以自由放任的竞争模式代替大企业间合作式竞争模式。由此不难看出,以美英为主要代表的新自由主义,主要目标是通过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干预、推行私有化、实现累退税、加强资方统治权等手段,最大限度地保护资本利益。
我国近年来由于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加大,实体经济发展出现困难,于是一些主张新自由主义的学者借机大力鼓吹相关主张。他们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解读为“彻底市场化”,否定国家宏观调控;将“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解读为公有制企业“私有化”;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读为对新自由主义供给学派的呼应,主张效仿美国,实行累退税政策;等等。这些主张是否可行?我们可以从基尼系数这个角度稍加分析。基尼系数是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本指标之一。我国基尼系数在2008年达到峰值0.491之后,近年来呈逐年下降之势,但仍然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这表明我国收入差距或者说贫富差距还是比较大。如果按新自由主义的主张搞私有化、市场化、累退税,最大限度限制政府宏观调控,中国势必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不但在经济上无法实现转型升级,而且可能会出现“富者累巨万,贫者食糟糠”的悲惨景象。
二、宪政民主论与“修昔底德陷阱”
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是指一个新兴大国必然要挑战守成大国,而守成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挑战,导致战争不可避免。这个说法源于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他认为一个崛起的大国与原有的统治霸主竞争时,双方面临的危险多数以战争告终。
如果在我国推行西式宪政民主,就有可能使我国落入“修昔底德陷阱”。这可以从宪政民主鼓吹者的主张中找到答案。他们认为,在中国实行宪政应包括如下要素或其中大部分要素:成文宪法、国民主权、代议民主、有限政府、权力依宪法划分、确认基本权利保障、司法(或审判)独立、宪法监督或违宪审查等。他们的核心主张是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主张军队国家化、实现三权分立和经济私有化。
由此可见,一些人主张的宪政民主,概括地说就是推翻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和军队的领导,搞美国式的“民主政治”。这些主张挑战了我国政治制度底线,企图“改旗易帜”,引起内乱,导致社会动荡。很显然,这些主张不会被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所容忍。这种思潮内部现在也在发生分化,有所谓“社会主义宪政派”与“自由主义宪政派”或“泛宪政派”之分,需要我们对其进行具体分析。
三、“普世价值”论与“西化分化陷阱”
“西化分化陷阱”的含义比较明显,也可以换一种提法,以前叫“和平演变”,后来叫“颜色革命”“茉莉花革命”等。其含义基本一致,都是指通过非暴力的手段推翻不奉行西方价值观的国家政权。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其暴力色彩一点也不弱。
所谓“普世价值”,实际上是西方价值观。“普世价值”与西方以基督教为中心的价值观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比如,1948年成立的世界基督教教会联合会就宣称“教会是超国家、超民族、超阶级的普世性实体”。正是基于这些因素,西方国家提出的所谓“普世价值”必然是以西方为中心的价值观,具有排他性、扩张性。它实际上也是西方推行新自由主义、宪政民主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支撑。关于这一点,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说得很清楚:“美国自建国以来笃信自己的理想具有普世价值,声称自己有义务传播这些理想。这一信念常常成为美国的驱动力。”
除了上面所说的新自由主义、宪政民主不适合我国国情外,一般意义上的自由、民主、人权等西方价值观是否适用于中国,从而具有“普世”意义呢?清华大学陈来教授从四个方面分析了中华文明核心价值与近代以来西方核心价值的区别:一是责任先于自由。中国文化的价值观强调個人对他人、对社群甚至对自然所负有的责任,体现出强烈的责任意识。二是义务先于权利。中国文化在人和人的关系中强调义务为先,互相承担义务是中国伦理的一个根本特色。三是群体高于个人。中国文化的主流思想认为个人价值不能高于社群价值,社会远比个人重要,因而强调个人与群体的交融、个人对群体的义务,强调社群整体利益的重要性。四是和谐高于冲突。中国文化注重以和为贵,强调多样性之间的和谐。很显然,中华文化的这些价值观与西方近代以来强调个人权利、个体自由优先,强调以自我为中心,克服非我、宰执他人的价值观存在着根本不同。如果简单移植西方个体本位的价值观,必然导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局面。
四、历史虚无主义与“塔西佗陷阱”
“塔西佗陷阱”得名于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其含义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指当执政党或政府部门失去公信力时,无论他们说真话还是说假话、做好事还是做坏事,都会被民众认为是在说假话、做坏事。
历史虚无主义者就是要通过所谓“反思”“新解”“人性论”“发现新大陆”等,否定中国近现代革命史,诋毁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和成就,抹黑正面历史人物、革命英模特别是党的领袖,为某些反面人物“翻案”,从而使我们党失去公信力、瓦解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合法性、正义性。历史虚无主义者善于利用一些历史节点和历史事件做文章,大造舆论声势。比如,在中国人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抛出“共产党歧视国民党抗战官兵,未给国民党将领应有荣誉”的观点,企图为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史实翻案;并且散布言论,“虚无”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史,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等。历史虚无主义者还调整策略,更多使用揶揄、影射、戏谑的手段诱导网民自我联想、自我推断,其手段更加隐蔽、策略更加复杂、诱导更加细微。除了这种“右”的历史虚无主义,还有一种历史虚无主义也值得警惕。比如,在一些抗日战争题材的影视剧中,出现了“手撕鬼子”等与史实根本不相符的情节和镜头。对于这种历史虚无主义,我们也不能听之任之,应该加以重视和警惕。
(本文作者系人民日报理论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