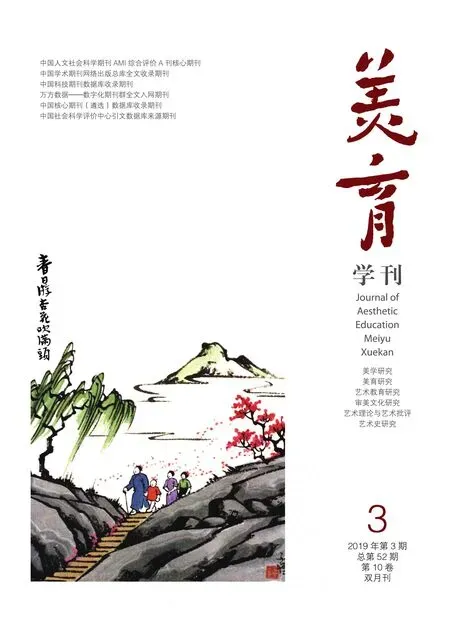艺术教育: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的“存在”之路
2019-01-15王煦
王 煦
(桂林理工大学 艺术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6)
艺术教育属于人文教育,以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为目标”。海德格尔存在论为本文提供了解读艺术教育目标的新视界。柏拉图在《智者篇》中说到:“当你们用到‘是’或‘存在’这样的词,显然你们早就很熟悉这些词的意思,不过,虽然我们也曾以为自己是懂得的,现在却感到困惑不安。”[1]1从希腊人开始,关于人的“存在”这个问题的解答就呈现出晦暗不明的镜像。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说:“我们用‘是’或‘存在着’意指什么?我们今天对这个问题有了答案吗?没有。所以现在要重新提出存在的意义的问题。”[1]13故而,海德格尔以“存在”为核心,展开对现代性生存境遇下人的存在及其意义的追问,创立了基础存在论哲学。从存在论视域思考被悬置起来的“人”,让“人”重返存在家园。海德格尔指出,“存在”是一个真理的“除蔽”过程,“存在地地道道是超越(transcendens)”[1]45,“存在”之境域是“人”“自然”“神”源始同一而共栖之境。基础存在论取向下的艺术教育以学生的精神成长与超越为追寻目标,实现这个目标就是走“存在”之路。即以超越日常生活为基础,在提升艺术精神内驱力的推动下,复归精神自由,实现“诗意生存”。对学生“存在”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在于,使其在物我同一的体验中,超越“自我”的有限性,从而在精神上得到一种自由和解放,一种欢乐和享受,因而觉得自己是一个真正的人。学生的审美和人文素养的提高是一个生成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显现“自我”,最终完成在艺术教育中成长的超越历程。现将实现艺术教育目标的“存在”之路具体阐释如下。
一、超越日常生活是艺术教育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的“存在”之路的基础
在青少年中,“人文教育十分薄弱,由此产生了许多社会弊害。有的青少年不知道怎样做人,也不知道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在什么地方。这是十分危险的倾向”[2]426,这是其一。其二,作为此在的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必须受制于‘自古皆然’、‘人皆如此’、‘一般都这样看’、‘习以为常’、‘固不待言’、‘已成定论’之类的社会的、历史的和世俗的观念,只有接受这些,他才能为自我(主体)争得一点存在的空间”[3]。因而“以非自立状态与非本真的方式而存在”[1]157,由“自己”而现实化为“常人”,“沉沦消散于世”。本真之性被遮蔽,失去了精神自由。
超越日常生活,可以使学生以本真状态归回世俗生活世界。如歌德所言:“要想逃避这个世界没有比艺术更可靠的途径;要想与世界结合,也没有比艺术更可靠的途径。”句中的“逃避”应作积极义,即超越。超越日常生活的琐碎局限性,以新的艺术视界再造世俗生活世界,进入审美的精神境界,从而升华个体、群体甚或人类的生存品味,实现内在生命价值,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
超越日常生活,学生须脱离“常人的桎梏”。通过艺术教育培养学生“自然”的审美心境和对“闲适”生活的情趣是其途径。
“自然”的审美心境,是一种自然适意的心态,是对自性的满足。海德格尔指出:“希腊本身就在大地和天空的闪现中,在把神掩蔽起来的神圣者中,在作诗着运诗着的人类本质中,走近人之本质,在一个唯一的位置那里达到人之本质,而在这个位置上,人诗意的漫游已经获得了宁静,为的是在这里把一切都包藏入追忆之中。”[4]海氏阐释了人的本性,“在作诗着运诗着的人类本质中,走近人之本质”。作为人本性的“存在”,通过作诗、运诗即诗教,由遮蔽走向澄明之境,并与人的“诗意的漫游”的审美理想联系起来。艺术教育可使学生真诚地面对自我生命体验与感受,强调自然本性,处己之真。如海氏所言:“只有当此在作为操劳……而操持的存在主要是把自身筹划到它的最本己的能在上去……此在才本真地作为它自己而存在。先行到无所关联的可能性中去,这一先行把先行着的存在者逼入一种可能性中,这种可能性即是:由它自己出发,主动把它的最本己的存在承担起来。”[1]302-303故使心灵达到“自然”的自由状态,如其所是地去生存于本真的澄明之中,将特殊的具有超越性的此在导向一个新的无限的世界。这就是“先行向此在揭露出丧失在常人自己中的情况,并把此在带到主要不依靠操劳操持而是去作为此在自己存在的可能性之前,而这个自己却就在热情的、解脱了常人的、幻想的、实际的、确知它自己而又畏着的向死的自由之中”[1]305-306。因而,体悟到自由自在自适的真乐境界。
超越日常生活,使学生正视忙碌的日常生活,学会养成并享受“闲适”生活的情趣。“闲适”可放松人的紧张心理,趋于平静心态,从容自适,能挤出更多的时间进行沉思,直觉体验和表现内心的真实感受,由此进入本真状态,成为让思想周游、精神自在的超越性的存在。由于“非本真的存在者不断丢失时间而后来没‘有’时间;而在决心中的本真生存从不丢失时间而‘总有时间’,这始终是本真生存时间性的独特标志因为决心的时间性的当前具有当下即是的性质”[1]463。这充分表明,作为学生的此在不再绽向他物而筹划着各种事务并操劳于其中,而是绽向自身;学生“当下”即掌握了他所有的“时间”,真正拥有闲暇。在闲暇中,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得以充分发挥,真正地为自在生命而生存;通过自在生命的自由体验而获得“高峰体验”。这是自我实现状态的典型感受,也是一种从容有度、安适自在的人生态度与生活方式,其中蕴含着“宽快悦适”的生命真乐。
二、复归“精神自由”是艺术教育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的“存在”之路的关键
人本来融身在万物之中,与万有相通,人在精神上无羁绊,是自由的。然而,是人有了主客关系的思维方式之后,才出现了人与万物之间的限隔,人被囿于“自我”限定的空间内,失去了精神家园,也失去了精神自由。
复归精神自由乃是通过艺术教育培养学生以审美的思维方式看待世界万物,重新找回自己的精神家园和精神自由。其途径就是超越。审美思维的整个活动是以“美”为价值趋向展开的,而美(意象世界)就是这种超越。“只有超越,才有真正的自由”[5]。其发生机制,以学生欣赏周杰伦演唱的《青花瓷》为例,《青花瓷》的诗意在于通过美感的感性直接性表达了歌者对心爱女子情思的情境。歌声伴随着各种乐器合奏而出的节律声,学生的情绪逐渐被带入了宛如烟雨蒙蒙的江南山水胜景:檀香、烟雨、炊烟和波动的水月等动态的“象”与歌者思念的愁情同构契合,学生就在与《青花瓷》的节律和用以青花瓷为中心的“象”,来寄托歌者对心爱女子情思的歌词构成“象”群组成的关系性存在中,生存与展开。对学生而言,歌曲《青花瓷》的节律和“象”群称得上是“上手的东西”,“上手的东西的存在性质就是因缘。在因缘中就包含着:因某种东西而缘,某种东西的结缘”[1]98。在欣赏活动中,学生与歌曲《青花瓷》和以其为中心的“象”群结缘。这就是审美性质的“象”,契合学生的“意”,当学生对其进行审美观照而达到了情景交融时,就形成了“意象”,这就是美。此时,学生和意象世界构成了一种融入和超越的内在状态。这里只有“关系”与“因缘”,人与世界的融合,而没有“分裂”与“对立”。因此,达到“游心之所在”,即灵犀相通的自由境界——主体的生命情调与客观的自然景象感应相通,成就一个“鸢鱼飞跃,活泼玲珑,渊然而深[6]”的生命的自由空间。
审美思维是一种源于人生的原初体验视野的开放性、展示性思维,是一种存在性思维。只有进行这种前思维状态的诗性之思,进行源始的存在之直观和领悟,此时,“让人从显现的东西本身那里,如它从其本身所显现的那样来看它”[1]41,“主体与客体同此在和世界不是一而二二而一的”[1]70。从整体的视角来考察世界存在者的本然存在与关联,体悟到真实的生命存在,体悟到精神生命的自由和解放。审美思维最终建构的意象世界,“美(意象世界)是情景合一,是对自我的有限性的超越,是对‘物’的实体性超越,是对主客二分的超越,因而照亮了一个本然的生活世界即回到万物一体的境域,这是对人生家园的复归,是对自由的复归。”[2]79
复归“精神自由”,使学生调适了自身失衡的人格心理结构,弥合了灵和肉、感性和理性分裂状态,使之趋向内在的丰富和完整,当下消解了主观与客观、能指与所指、物与我的界限,达至澄怀味象,乘物游心的境地。正如马克思主义美学所言,这是由于只有在源于深情和热爱的审美创造活动中,自我才突破了现实的束缚、理性的制约,自我才能由片面的、异化的单项人提升与超越为完整的自由人。这时的自我与世界主体之间相互欣赏、彼此交往、融合为一,从而进入自由王国的审美之境,完成了“解蔽”,建构了意义世界,实现了人的本真生存和“诗意地栖居”。
三、提升艺术精神是艺术教育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的“存在”之路的内驱力
艺术不仅能满足人的精神需求,而更重要、更基本的是一种生存方式,一种人生观,一种理想的人生境界。艺术的作用展现为艺术精神对人日常生活的塑造,对人精神的升华。林语堂认为,艺术精神如要普遍地深入社会各个角落,就必须将艺术看作游戏。席勒将艺术活动比拟为高级的游戏活动,认为在审美游戏活动中,人的感性与理性协调,人性达到完善的状态。斯宾塞认为艺术活动和审美活动在本质上都是相对高级的游戏活动,其产生是为了发泄剩余的精力。康拉德·朗格认为艺术是运用高级感官的幻觉游戏。伽达默尔则认为游戏是艺术活动的存在方式。游戏不止是一种生理现象与心理反应,游戏的力量颇大,在虚拟的游戏场中,参与者的情绪和精神被深深震撼,其心灵冲破了世俗的羁绊、自由自在、物我两忘。人在艺术活动中,保持着一颗“沉迷于游戏中的孩子的心灵”[7],使人的精神处于游戏状态且接近自由。真正的艺术精神主要是一种游戏的精神,而游戏是艺术精神的核心内涵。
游戏精神可述说为审美的无功利性。康德认为,艺术是自由游戏的产物。他说:“艺术也与手工艺区别着。前者唤作自由的,后者也能唤作雇佣的艺术。前者人看做好像只是游戏,这就是一种工作,它是对自身愉快的,能够合目的的成功。后者作为劳动,即作为对于自己是困苦而不愉快的,只是由于它的结果(例如工资)吸引着,因而能够是被逼迫负担的。”[8]康德将自由视为艺术的精髓。整个艺术活动自始至终都具有自由游戏的性质,审美状态就是人的自由游戏状态。当今社会,现代性将人们的日常生活压抑的支离破碎,人们在此机械性地存在着。种种实用功利的忖度将人们层层禁锢起来,遗忘了人与世界原本的游戏关系,压抑了人性,致使人性中的“童心”和“天真”近乎泯灭。面对这样的生活,既不是要摧毁它,也不是要用一种全新的生活取代它,而是要重新安排生活,使之成为人类的精神庇护所。因此,将日常生活变成自由快乐的“游戏场”,倡扬多一些游戏精神势在必行。游戏精神可以“使人脱离了日常生活的种种限制和陈规,舒展了自己的天性、情感和想象力。”[9]游戏的空间就是心灵的空间,艺术教育依托艺术激起受教育者的想象力。“想象力以一种我们完全不理解的方式,不仅善于偶尔地、哪怕是从久远的时间中唤回那些概念的标记;而且也善于从各种不同的乃至于同一种的数不清的对象中把对象的肖像和形象再生产出来;甚至如果一心想要比较的话,也善于根据各种猜测实际地、哪怕不是充分意识到地仿佛让一个肖像重叠在另一个肖像上,并通过同一种类的多个肖像的重合而得来一个平均值,把它用作一切肖像的共同标准。”[10]受教育者凭借想象力的游戏,不断地对现实进行否定,对即成进行摒弃,游戏状态所酝酿的超越精神使受教育者完全抛开利害考虑,即没有认识上的诉求,也没有伦理道德上的约束,“在审美意义上,孤身一人会意识到这个世界是他的世界,是一个将他孤立于形单影只境地的世界,在此它把这个世界的种种传统习俗抛在了一边。”[11]从而找回诗性的焕发状态。艺术教育正是凭借艺术的游戏性,来弱化与冰释人的功利心,提升人的游戏精神,使人脱离那种在追求目的的过程中所感到的紧张状态,整个身心都处于自然状态,林语堂说:“我主张各方面人士大有业余活动的习惯。……人人在客厅里欣赏他的朋友的业余魔术,比欣赏一个职业魔术家更来得有兴趣;作父母的欣赏子女的业余演剧,比欣赏莎士比亚的戏剧更来得有兴趣。我们知道这是自然发生的情感,而只有在自然发生的情感里才找到艺术的真精神。……艺术保持着游戏的精神时,才能够避免商业化的倾向。”[12]以游戏的态度对待人生,真正活在时间的现代维度中,最终让人真正地热爱生活本身,而不是随生活而来的其他事物。
游戏精神可述说为审美的创造性。艺术教育是通过审美活动的方式对受教育者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游戏有某种要成为美的倾向,这种审美的因素很可能就等同于那种创造有秩序的形式的冲动,它把生气灌注给游戏的各个方面。我们用以指称游戏因素的那些词汇,绝大多数都属于我们用以描述美的效果的词汇:紧张、均衡、平衡、冲突、变化、消融、解决等等。游戏迷住我们;游戏是使人‘入迷的’‘吸引人的’。游戏带有我们可在事物中窥见的最高特质:节奏与和谐。”[13]游戏与审美活动具有相通之处。受教育者在审美活动中,与日常世界处在一种游戏空灵的关系之中,精神处于游戏状态,此时的思维状态是发散型的思维状态,可以天马行空,浮想联翩,能够见他人之所未见,说不可言说之事,让世界回归到未被触碰的本真的陌生化的原初世界。“我们留恋于对美的观赏,因为这种观赏在自我加强和自我再生。”[10]58故每一次审美活动似乎永远都是一个全新的游戏的开始,而且不依靠任何固定的规则,只需想象力的活跃,“想象力可以自得地合目的地与之游戏的东西对于我们是永久长新,人们对它的观看不会感到厌倦”[10]80。因此,通过想象力的游戏,将现实中的既定抹平,再依据自己独有的方式设定秩序,使美在游戏中不断重生。审美活动的游戏性激活了受教育者“健康的儿童性”或“第二次天真”(马斯洛语),也激活人的感官,使人重新拥有自己的感受力;“培养了一种分散的、任意并列的,并且是开放的经验,而不是一个受到限制的统一的经验,因此,他令日常的东西变得不那么熟悉,以使它能够得到重新思考”[14]。人不再固守日常经验的预定型,一切处于待筹划的可能性之中,最大限度地还原了感受的本真性。只有这样,受教育者才能找到独特的创造视角,打碎影响的焦虑,形成有个性的自己。每一次审美活动都是一场全新的游戏,每一次游戏都开启一个全新的世界,游戏的这种重构世界的特点让受教育者体验到一种类似于上帝创世般的乐趣。游戏的乐趣拒绝一切逻辑、分析等思维,那么游戏的巨力就来自美,美成了游戏生发相续的动源。诚如康德所言,只有在爱与美的游戏中,人们才能快乐且自由地行动,才有道德的完美,才有生活的幸福。
海德格尔认为存在就是永恒游戏者,永恒的游戏让存在得以栖居并成其自在。他说:“大地和天空诸神和人终有一死者,这四方从自身而来统一起来,出于统一的四重整体的纯一性而共属一体。四方中的每一方都以它自己的方式映射着其余三方的现身本质。同时,每一方又都以它自己的方式映射着自身,进入它在四方的纯一性之内的本己之中。”[15]1180“映像游戏”不再表明为不同对象之间的关系,而是一种自身生成的游戏,在照亮四方中的每一方之际,获取其本己的现身本质:“本真存在”。它表明,游戏来源审美,故本真;游戏基于主体间性,故自由。人在本质上应该变成一个游戏的人,所仰仗的是游戏精神。人只要有了此精神,才能超越对“小我”的自视,对“大我”的关怀,达到“无我”境界,生命个体与天地万物契合为一,即天地境界,冯友兰说,天地境是用“负的方法”实现的一种超越了人与己、物与我、各种分别与计较的游戏世界。就会“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任物而不任于物”,可品味出超越日常生活态的意蕴;会入乡随俗而不仰人鼻息。
如是,艺术教育的效果,就能使学生抛弃用实用功利的态度思索问题,排除以专业化的观点对待现实生活,使游戏复归日常世界,将生活当成一场多维游戏,只去尝试、感受、创造。因而,把游戏精神引进教室和适宜的生活场所,致使刻板重复的日常生活得以松动与舒缓,从中体验到更多的美感愉悦,感悟到生活的真谛。
我们进行艺术教育,不能靠强制,或者特意地引入超越日常生活的游戏精神。而是使受教育者在游戏中不自觉地接受艺术教育,这才是广为认同的艺术教育经验。
四、实现“诗意生存”是艺术教育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的“存在”之路的必然
实现诗意化生存之路是“‘人以审美的人生态度居住在大地上’,‘是在人的层次上以一种积极乐观、诗意妙觉的态度应物、处事、待己的高妙化境’”[16]。实现诗意生存,应当以什么态度直面物对心淹没的当今世界,是关乎学生日后生存方式的选择问题。克尔凯郭尔认为,人们应“以审美的眼光看待生活,而不仅仅在诗情画意中享受审美”[17]。这就是要在艺术教育中培养审美态度,为人生态度与生活方式提供坐标。中国古典美学中,老庄的“涤除玄鉴”、“心斋坐忘”,宗炳的“澄怀观道”,郭熙的“林泉之心”,司空图的“素处以默,妙机其微”,刘勰的“物以情观”,邵雍的“以物观物”,王国维所说的“胸中洞然无物,而后其观也深,而其体物也切”,都在倡扬一种审美态度(审美眼光),“有审美的眼光才能见到美”(朱光潜语)。美之所以为美,是存在的敞开,是“作为无蔽的真理的一种现身方式”[18],与此在的趣味爱好无关。海氏指出:“为了感受某物是美的,我们必须让与我们照面的事物本身纯粹地作为它自身、以它本身的等级和地位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必须使与我们照面的事物本身在它所是的东西中开放出来,我们必须把它本身所含的东西和带给我们的东西让与和赐予给它。”[19]把现实的束缚与外在功利的计较放在从属于生命内在本性的地位,摈弃妄虑杂念,类似于现象学的“悬置”或“加括号”等“现象学的还原”方法。用海氏的思想来表达就是回到原初,回到人的存在,回到人的真正起点。这是一个由去蔽走向澄明之境的过程——审美态度的建立。因此,实现诗意生存要引导学生以审美的态度对待世界。持有审美态度的学生不是日常生活中与世界对立的片面主体,而是回归本源的主体,超越了处于非美状态的存在者,也是存在中的主体。根据海氏后期的思想,存在被理解为人与世界的共在,即天、地、神、人四方游戏。天、地、神、人之间没有主客体之分,我与世界之间的障碍得以解决。天、地、神、人平等相处,互相依存,自由得以实现,从而达到人存在的至境,即诗意生存,换用海氏的说法是“诗意地栖居”。它使生存突破了时空的桎梏,克服了我与世界之间的对立,“时间—游戏—空间”“为四个世界地带‘相互面对’开辟道路”[15]902。
超越现实生存,成为“绽出的生存”,在生命之外,再也没有异化生命的存在。万物即生命,生命即万物。明心见性,摒弃妄心,领悟并把握到本心,“我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我心”(陆九渊语),从而进入自由的生存状态和澄明之境,开始一种随缘任运,自然适宜的生活。在“充满劳绩”的情况下,拥有真正、自然、自在、自由的审美休闲空间。唯有如此,学生才能具有思诗合一的高层次的生命体验——休闲体验,包括对其生命本质的参悟,又有对所处世界的领会。这时,我们的生命是真切的,我们的世界是清静和神圣的——具有了存在意义上的人之为人,生命之为生命,世界之为世界的本质意义。
总之,实现诗意生存,要突破“技术地栖居”方式;须要爱护自然,尽拯救大地之责;超越“自我”,克服现实生存及其体验的局限,回归存在本体,成为本心澄明的存在。以审美的态度看待世界,朗照万物一体的生活世界,从中体味其蕴含的无穷意趣,达到自由的诗意生存状态,将审美与人生结合,进而从现实的物质世界跃入艺术人生境界。
应指出的是,本文的艺术教育是从广义上讲的;实施艺术教育不能单纯理解开设一门或几门艺术课,应使艺术教育寓于学校教育的各个环节,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学校而言,须要创造浓郁的文化与艺术氛围。对社会来说,须要有一种以人文精神为支撑社会教育环境。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的艺术教育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