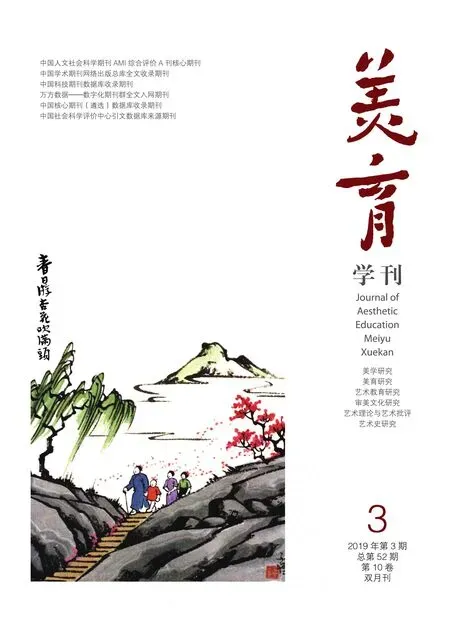艺术美育的生成及其在消费时代的作为
2019-01-15梁晓萍
梁晓萍
(山西大学 哲学社会学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艺术美育是一个合成词,它包含着“艺术”和“美育”两个维度的意旨,隐含着由艺术、美育而至“艺术美育”的生成性过程和特征,对艺术美育的研究与思考因此便至少应该探析两个层面的三个问题。两个层面是艺术美育为何与何为;三个问题为:艺术(实施美育的主体)是什么?艺术与美育因何、于何时结盟?消费与电子传媒合谋的时代,艺术美育的核心功能什么?
一、艺术是什么:从立法到阐释
“艺术,这一在今天为人们所广泛使用、似乎无需佐证的自明物,其实并不是先天的存在物,而是社会历史语境中的生成物,即有一个逐渐生成、发展,并被人们认知的过程。”[1]西方艺术由最初的包罗万象——甚至制作一张床、一艘船、丈量一块土地、统领一支军队都叫艺术——到成为建筑、雕塑、音乐等一类事物的专门指称,经历了非常漫长的辨识与讨论过程。中国直至近代,才在艺术理论转型的自我诉求与西方现代艺术观念的冲击与启发下,辗转从日本借鉴了“艺术”这一学术概念。然而有趣的是,人们大都承认有艺术,认可艺术的生成性,但对于什么是艺术,艺术内涵、艺术真理,却众说纷纭,直到今天依然没有停止争论。
关于“艺术是什么”这一问题的讨论,若从哲学的角度讲,主要有唯物与唯心两种立场,前者认为艺术是某种质素或形式,后者则强调艺术与意识的紧密相关性。从内涵的角度讲,也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强调“艺术”与“美”紧密相关,认为艺术是美的,具有包括审美在内的一种或多种功能价值,从创作主体的角度讲,认为艺术具有独创性;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艺术并非功能价值的体现物,而是某种规定或惯例的确证物,主体的创作不具有独创性。早在古希腊,柏拉图已经开始了对于“什么是美”和“什么是美的”的思考,为艺术与美搭起了关联之桥,开启了艺术与美互相言说的哲思之旅;1746年,巴托在《简化为单一原则的美之艺术》中第一次提出了“美的艺术”,稳固了“艺术”乃“美的领域”的身份归属。之后,康德、黑格尔以及诸多学人都在这一基本观点框定下、在审美的维度中探寻艺术之内涵。在“艺术是美的”相关理解中,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达·芬奇等从艺术是模仿的角度论证了艺术与美的各种勾连,克罗奇等则强调艺术对于艺术家主体情感的集中表现,什克洛夫斯基等形式主义者强调作品本身的张力与寓意,汉斯·罗伯特·尧斯却又从接受主体的角度阐释艺术的意义。以上对于艺术的诸种理解,尽管基于不同的审美活动元素,却有一个共同点,即都以“艺术是美的”为大前提。
然而时至20世纪,艺术与审美的关联却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衅:杜尚将在陶瓷店购买的小便器堂而皇之地送进博物馆,签上名便得到了主办方的认可;沃霍尔在自己的“工厂”复制着可口可乐瓶、美元和明星等现成的物品,将这些商业对象置于画布中央,或者直接将一些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罐头、烟灰缸和番茄、麦片、肥皂的包装盒等签上名展出,称之为艺术。在杜尚和沃霍尔的作品中,是否可以被称之为艺术的界线是“所签的名”与“所搁置的地方”,而有关艺术是否美、艺术技巧以及原创性的思考则被摒弃了。诚如丹尼尔·贝尔所言:“今天,现代主义已经消耗殆尽。紧张消失了。创造的冲动也逐渐松懈下来。现代主义只剩下一只空碗,反叛的激情被‘文化大众’加以制度化了。它的实验形式也变成了广告和流行时装的符号象征。”[2]
关于凡·高第255号作品《鞋》的“真理事件”非常有趣地历经了对于“什么是艺术”的代表性理解。海德格尔认为,那是一双保持着器具原样世界的农妇的鞋,聚积着“步履的坚韧和滞缓”,回响着大地无声的召唤、宁静的馈赠,也浸透着大地上人们的焦虑与喜悦。这是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式美学的解读,他从艺术作品本身出发,强调艺术作品自身“置入”的特性,强调其被揭示的“无蔽”状态,从而指出正是艺术作品让存在者的真理无阻地发生。艺术史家夏皮罗则在给海德格尔挖了一个陷阱后“揭示”了海氏难以自圆其说的症结,他认为,凡·高至少有三幅“磨损的内部那黑乎乎的敞口”的鞋子,它们都有针对哲学家的可能,而海德格尔只选择了第255号作品,从而基于自身进行“联想”,他“‘想象一切而后又将之投射到绘画之中’。在艺术品面前,他既体验太少又体验过度”[3],夏皮罗指出海德格尔犯有作品选择与解释方面的双重错误,没有意识到“作品中艺术家的在场”,强调这就是凡·高“以自画像的角度来描绘的”自己的鞋子,是凡·高自我的一部分,而艺术作品的“真理”就是艺术家自身,是其心灵世界的再次显现。詹姆逊不认可海德格尔艺术的真理在艺术自身的观点,也不赞同夏皮罗的观点,但他承认这是一双“农”鞋,强调艺术与对象之间的符合关系才是艺术的真正魅力,即艺术质量的高低缘于与现实真实的贴近度,凡·高的《鞋》与“农民苦累不堪的整个不完善的人类世界”相符,从而以“最灿烂的、纯油彩的形式”,为生活于“无生气的客体世界”的农民进行了乌托邦式的世界重构和精神补偿。可见,对于凡·高的《鞋》的理解,海德格尔坚持从作品本身出发,夏皮罗强调艺术家的精神力量,詹姆逊则更关注艺术对现实的反映,不过,倘若将分析的镜头再往回拉,我们发现,此三者的讨论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即都承认这是一双鞋,只不过对鞋的主人、《鞋》所含的意蕴及其来源的理解不同,德里达则迥然不同于前三位的理解,他反对为鞋子找主人的做法,因为这并非一定是“谁”的鞋,更何况这并不是一“双”鞋,甚至可能就不是“鞋”,既然无主人,亦并非海德格尔所说的承担过器具性的器具,那么,鞋子便成为飘浮的能指,或者仅成为一个符号,不确定性才是作品真正的意义。这样,作品的“真理”便成为一个伪问题,艺术与美便也各奔东西。既然如此,那么,杜尚、沃霍尔的作品为什么还会被称为艺术?或者说,在何种意义上我们认定杜尚、沃霍尔等人的作品为艺术品?若承认这一点,唯有转换论域,从关注“什么是艺术”转换为对“何时是艺术”的讨论;暂时搁置基于康德美学意义上的“艺术终结”问题,从为艺术“立法”转变为“阐释”艺术和为艺术重新划界;转变观念,从论析艺术之为艺术的内部因素转向对艺术品的外部语境的探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丹托和贝克尔的“艺术界”,贝克尔、迪基的“艺术惯例”等理论,都是这方面的有益探索。当“当代艺术抽离、掏空了审美价值。艺术不再是美术,不再是对审美体验的表现和沉思……而成为了一种由制度身份、娱乐价值和商业包装所定义的心理结构”[4]时,那么,艺术还能够进行“美育”的使命么?答案是肯定的。对于这一点,我们不妨参照人们对于“丑”这一审美形态的理解。近代以来渐次频仍且得到关注的“丑”,不仅折射出生活本来的丑,而且通过“不和谐”的形式,显示出历史的阴暗、人生的苦难以及艺术家的“悲愤”,通过取消时空、削平深度、打乱整体等蓄意的破坏,使价值沦为虚无,使传统的高潮、中心等亦全被覆灭,从而深刻反映了近代以来人们于生存中体验到的不安全感和不信任感,当观众沉浸于这些“丑”的艺术时,便也会感同身受,在精神的高度契合中体会到深刻的自由感,这也是美育,是基于对“丑”的深入理解的一种美育。
那么,艺术与美育是于何时、基于什么样的情形结缘的呢?
二、艺术与美育结缘
法国学者雅克·朗西埃一直致力于学科分工之藩篱的拆解,他从一个稳定的治安秩序必定辨别和选择出“需要”被看见和听见的声音(即一些声音虽然在社会中存在,却故意被忽略),从而推衍出,在美学领域亦存在“可感性的分配”,也有“什么是艺术”“什么不是艺术”的人为规定,并以此为理论依据区分出三种艺术体制(regimes of art)(即三种艺术类型):影像的伦理体制,以柏拉图“影子的影子”说为代表;艺术的诗学/再现体制,以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论及其后的再现论、反映论为代表;艺术的美学体制,以人性解放为主题的现代艺术诸潮流为代表。朗西埃历史视域中的美学体制论巧妙地揭示了一个事实:美并非天生即为艺术的本质特征,它只是在特定阶段的特定背景下、被历史赋予艺术的一种特殊品格,也即审美与艺术并不具有必然的联系,二者的结合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一种特殊现象。朗西埃对于艺术“审美”非原初性面纱的揭示启示我们,艺术与美育的结缘也是有条件的。
艺术美育的前提是承认艺术是美的,从而认定其具有以“美”而化人的功能,从“关系”的角度看,它实际上是对于艺术“他律”的一种关注。中国早在西周时期,礼乐教化观念已经达到充分自觉的程度,已开始自觉地对包括贵族子弟和国民在内的“人”进行艺术教育,古籍所传的周公“制礼作乐”可视为古代美育思想的早期表征。春秋战国时期,孔子进一步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教育思想,其弟子子游在武城为宰时,便曾以弦歌的形式来宣扬教化。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自西周、先秦诸子至明清时期的文人思考,音乐等艺术之所以受重视,主要在于它们能够承担为统治服务的社会化育功能,无论是通过“审声”而“知音”“知政”,还是对于“治世之音”“乱世之音”(《礼记·乐记》)的区分与辨识,都是基于“与政通”的理性前提,依托的是社会制度建设之核心的“礼”,突出的是艺术服务于社会秩序的“干政”功能,尚非真正的“美育”。以魏晋时嵇康“声无哀乐论”为代表的艺术“自律”理论,敏锐地发现了音的快慢、高低与单复等的变化与听者的情感变化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关联,从而对人的感性能力产生相应的影响,这一“先进”的思想尽管已经有了与现代艺术美育极为相近的思考,只可惜这种力量过于单薄。西方从早期滥觞于宗教中的艺术,到古希腊柏拉图的“影子的影子”说、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的净化与陶冶说、古罗马贺拉斯的寓教于乐说等,也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他律立场,更多地将艺术置于庞杂的上层建筑体系中,视其为宗教、政治或道德的陪衬物,而极少提及其对于个体感性体验能力的影响作用。
在人类艺术活动与艺术美育的历史上,伴随着由他律而自律、由自律而他律的艺术观念交相变化的过程,对于艺术功能的理解也发生着相应的变化。整体而言,西方自18世纪开始比较多地关注人的感性认识能力的完善问题,从而使艺术与美育真正结盟,在这一过程中,有两个事件不得不提。一是1750年,德国理性主义哲学家鲍姆嘉登鉴于“感性认识”研究的缺失而出版了《美学》一书,在宣告美学(Aesthetic)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正式成立的同时,将自古希腊以来一直被视为低级认识能力的“感性”这一“混乱和朦胧的”(莱布尼茨语)“自卑”者[注]鲍姆嘉登指出:“希腊哲学家和教父们已经仔细地区分了‘可感知的事物’和‘可理解的事物’。……‘可理解的事物’是通过高级认知能力作为逻辑学的对象去把握的;‘可感知的事物’是通过低级的认识能力作为知觉的科学或‘感性学’(美学)的对象来感知的。”又曰:“美学作为自由艺术的理论、低级认识论、美的思维的艺术和与理性类似的思维的艺术,是感性认识的科学。”鲍姆嘉登:《美学》,简明、王旭晓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第169、13页。,以学科研究对象的方式隆重地推介到人们的研究视域。鲍姆嘉登称“美学”为“美的思维的艺术”和“自由艺术的理论”,强调“美学”既需要总结“自由艺术”(《诗的哲学默想录》《美学》中主要指“诗”)的“艺术”(技能、规则),同时也要探究这种技能与规则所得以成立的形而上原因(理论、科学),从而使艺术成为美学的核心成员,使艺术与美育的有效联结成为可能或必然。二是1793年,德国古典文学与美学家席勒在其书信体著作《审美教育书简》中,第一次在美学与艺术史上提出了比较系统和全面的美育理论。席勒认为,近代社会严密的分工不仅造成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分裂,也使个体人性的分裂成为一种必然,从而在主与客、现实与理想等多个层面体现出矛盾与不和谐,为使近代人能够恢复到古希腊时期完美和谐的人性状态,席勒提出以“游戏冲动”弥合“感性冲动”与“理性冲动”之间的裂隙,通过艺术的审美教育,修缮因理性冲击而支离破碎的感性,使近代人的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席勒对于艺术美育的认识,有效突破了古希腊以来把美育仅作为道德教育之方式或补充手段的偏狭观点,使其成为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一种有效凭借。
中国古典典籍中的“美育”一词,最早见于“建安七子”之一徐干的《中论·艺纪》,其引今文经学《鲁诗》曰:“美育群材,其犹人之于艺乎。”此处“美育”一词尽管与今日“美育”之内涵有相通之处,徐干与汉儒已将“艺(诗、乐)”视为“美育人材”可依赖的重要途径[注]徐干曰:“先王之欲人之为君子也,故立保氏,掌教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教六仪:一曰祭祀之容,二曰宾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丧纪之容,五曰军旅之容,六曰车马之容。大胥掌学士之版,春入学舍,采合万舞,秋班学合声,讽诵讲习,不解于时。”又曰:“故诗曰:‘青青者我,在彼中阿;既见君子,乐且有仪!’美育群材,其犹人之于艺乎?”徐干:《中论·艺纪第七》,黄素标点,上海:泰东图书局,1929年,第28页。,并将其与智育、德育紧密相连,并举为协力培育古之贤才的有效依凭,然因古代美育的出发点乃政用,其终极目的是培养符合统治需要的“表里称而本末度也。故言貌称乎心志,艺能度乎德行。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纯粹内实,光辉外著”[5]的“君子”,而非个体人的全面完善,故而仍非现代意义的美育内涵。至20世纪初,蔡元培基于代替宗教的目的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著名美学思想和现代意义的美育,其曰:“美育的名词,是民国元年我从德文Asthetische Erziehung译出,为从前所未有。”[6]186在倡导“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中明确了“美感教育”的地位。他通过《教育独立议》等多篇文章不断阐释其现代美育观,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17年发表于《新青年》杂志、由在北京神州学会发表的演说内容整理而成的《以美育代宗教说》一文。蔡元培认为,与强制、保守、有界的宗教相比,美育具有自由、进步和普用的特性,以陶养感情为目的,可以使国人的感情勿受污染和刺激,使其受艺术熏陶而纯正。需要指出的是,蔡元培描绘的是一个“大美育”图景,包括“美术馆的设置,剧场与影戏院的管理,园林的点缀,公墓的经营,市乡的布置,个人的谈话与容止,社会的组织与演进”,以自然以及建筑、雕刻、图画、音乐等艺术进行美育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恰如其所言:“我以为现在的世界,一天天往科学路上跑,盲目地崇拜物质,似乎人活在世上的意义只为了吃面包,以致增进了贪欲的劣性,从竞争而变成了掠夺”,“……我的提倡美育,便是使人类能在音乐、雕刻、图画、文学里又找见他们遗失了的情感。”[6]214-215蔡元培大美育思想中的艺术美育观不仅具有宗教所具有的神圣性和精神高度,也使其成为近代中国建构国家与国民形象的有机组成部分,并昭示出一条将美学理论与艺术实践相结合的美育之路。
至此可知,西方自18世纪,中国自20世纪初始,现代意义的艺术美育观相继出现,与中国古代儒家以培养“君子”为目的故而将诗、乐纳入伦理道德体系的美育观不同,也与柏拉图为构筑充满理性的城邦故将“煽动人非理性欲望”的艺术家驱逐出理想国的美育观不同,现代美育的兴起,是对不断扩张的技术操控力与渐次弱化的文化影响力、高度丰赡的物质财富与普遍存在的精神困惑、容易获取的日常满足与精神自由的强烈受挫等多重矛盾思考的必然结果,欲望与生命意义的格格不入、理性与感性之间制衡关系的撕裂,促使艺术审美承担或部分承担起精神疗伤的重要功能,那么,在今天这个消费与电子共舞的时代,艺术美育对人的精神世界又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三、消费时代艺术美育的作为
人类美育的历史发展,大体可以分为不自觉的美育活动、自觉的美育活动、美育学科的建立、现代意义上的美育四个阶段[7]。上古“礼”“乐”混融而交织于“以舞降神”的祭祀活动之中,“先王乐教”的美育功能尚与政治、宗教、伦理等其他社会功能杂糅在一起,至迷信深重的商代,尚乏利用“乐”进行美育的自觉行为。周代人文精神跃动,周人敬畏天命的同时,有了“天命有常”的理性之思,“礼”“乐”随着“礼”观念的出现而渐次分化,乐舞的审美特征逐渐显现,尽管此时的“乐教”由于与宗教祭祀的原始联系尚未斩断而未充分显示出艺术自身的审美特征,但可以肯定的是,艺术美育在周代已端倪尽显。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的现实境遇促使孔子等有识之士开始思索“乐教”的重要作用。可以说,春秋末期的“艺术美育”解决的是培养君子以承担扭转时势、恢复周礼的任务。近代蔡元培以改造国民性和变革社会为旨归而提出“以美育代宗教”,体现了其“教育救国与启蒙民众”的理想。由上述跳跃式的梳理可见,以乐教为传统的中国艺术美育,自古至今有一条共同的主线,即沿着“人”及人性的养成而不断展开,其大致过程是强调艺术美育对个体人格的塑造,对个体情感的陶冶,从而使艺术美育与社会乃至人类的发展相互关联,在更深层次上体现出艺术美育的人文价值。艺术美育实施的基础是“个体”审美情感、人格与主体精神的完善,然而,消费时代尤其消费与电子传媒合谋的当下,这个基础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当代社会,财富、金钱、效率、增长、享乐等基本价值观念正愈来愈深刻地引导着人们的生活,诚信、正义、幸福感等生存和生活的信念与感受出现危机,甚至逼近人类精神的底线。经济的快速发展,财富的迅猛增长,的确提升了人们的生活质量,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条件,然而,物质的不断翻新并没有使现代人的幸福感明显提升,相反,生活在琳琅满目的色彩包围当中的现代人无法克服掉内心的焦虑,也不得不承受着盲目追求物质财富而带来的诸如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等的挑战,与艺术美育最直接关联的便是一系列审美问题的出现。
消费时代,曾经一直被指认为是边缘性的、派生性的、女性化的被动性“消费”本身,一跃成为一个“能动的”、能对周围集体和周围世界产生意义的“结构系统”,消费品反过来成为社会行为和社会群体的一种代码和标识[8]。西方在资本主义之前,中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艺术和审美属于极具自律性、由社会精英操控的高雅文化领域。而在消费时代,工业化的批量复制在日益精致的技术效应和大众媒介的陪同下,一方面拆解原来艺术家身上的神圣光环,消泯艺术创作中“个体精神”的独特魅力,一方面通过大量制造千篇一律的“艺术品”来假意慰藉消费者的心,实则诱使大众的审美情感体验不断标准化,使个性不断被共性所吞噬,从而导致了消费者——审美主体的审美感官迟钝化,审美趣味肤浅化,审美能力平面化,审美价值功利化。如此,则在欲望与金钱两面大旗的引领下,消费时代表面繁荣的审美之气象,孕育的实乃审美主体本能欲望的泛化和感性意识的沉沦,其结果则是急功近利心理的膨胀以及主体精神的丧失。
再者,由于鲍德里亚所说的“仿像”,即通过模拟而产生的影像或符号在电子传播媒介作用下的几何级增长和肆意扩张,符号远远大于其所指涉的内蕴,影像远远大于其可以阐释的涵义,形式与意义的比例变得极不相称,本应立体的生活因之而变得平面化,“泛艺术化”从而形成。有人或许会疑惑:人人都是艺术家,岂不美哉?人人重视真正的艺术确应当是好事,它象征着审美感受的充盈完善与精神生活的极大丰富,然而日常生活的“泛艺术化”却隐藏着极为严重的后果:包括政治、经济、商业、教育等一切社会活动将都成为艺术,整个社会都将被浸透在伪艺术之流中。曾几何时,“全民写诗”的浪漫主义式冲动并没有使大众的写作艺术水平整体提升,相反,大量涌现出的、今天已很难再想起的“诗歌”,倒更像是见证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闹剧;同样,今天打着艺术的旗号消费自然(如九寨沟、桂林山水)、历史(如关公故里)与艺术文本,商家盗用艺术之名,扩张自己的商业领地等现象已屡见不鲜。
综上可知,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消费时代的审美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美学发展中极为引人注目的现象,成为全球化语境下人类审美活动面临的新问题,因此,新世纪中国美学与艺术美育的发展,必须正视和思考消费文化语境下审美观念的新变化以及在审美活动中出现的新问题。面对消费时代审美创造与接受主体双双被功利裹胁而使人性再次分裂的状况,艺术美育需要积极面对,主动思考,争取有所作为。那么,艺术美育在哪些方面可以发挥其引领与修缮作用,或者说,艺术美育在当下消费时代需要强化哪些功能呢?
首先,淡化欲望,弱化功利思想。审视当下,人类的欲望系数逐年递增,人类甚而以过激行为谋求利益最大化,欲望不达则又心生怨恨,甚而绝望;由人的健康、社会地位、财富、政治权利、教养、尊严感、道德能力、人际关系等各种因素合力结果的幸福感,因片面追求财富等单一维度的发展而产生“短板效应”,凡此种种,诱发消费时代的诸多文化误区与审美变异,导致身心愉悦感严重缺失。而艺术通过体贴人心的形象塑造而作用于人的情感,通过艺术世界的营造而使人在对于现实世界的暂时忘记中放飞思想,继而又接通现实而进行沉思,从而放慢身心节奏,培养符合人性健康发展的心理质素。
其次,完善感性。艺术美育通过艺术教育实施美育,以各种艺术形态融入美育中,受众直接碰触到的是具体而特殊的媒介,跳动的音符、柔婉的歌喉、鲜活的文字、斑斓的色彩、多样的线条、优美的动作,激发的是丰富的想象、浓浓的情感、深邃的愿望和无限的精神徜徉,因此,它能够直接作用于人的气质、性格、感情、品位等精神品格,以一种丰沛超常的感性力量,提升人认识美、体验美、感受美、欣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有效协调感性与理性的平衡,最终促成当代人美的素养和美的理想。
第三,关注异项美感与标出性文化。一般而言,当人们位于文化正常状态中时总是能感受到一种愉悦,此即谓“正项美感”[9],譬如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一支抒写家和万事兴的歌曲、一幅表达延年益寿的画作、一出表达善获善报的戏剧等,或者通过异项文本如波德莱尔《恶之花》、艾略特《荒原》等艺术文本而获得正项美感,此亦谓艺术美育的传统功能。现当代社会,艺术越来越偏转于对异项文化的关注,作为对主流文化的不安和抵制以及补充,异项艺术也逐渐被文化中项逐渐认同,如朦胧诗歌、金庸武侠、装置艺术、行为艺术等。依托这种艺术欣赏实施艺术美育,不仅有益于培养敏锐的审美感知力、扩充大众的审美想象力,亦可以加强其对于“怪、险、奇、诡、异”等不寻常之美的关注,以及对于社会边缘人、多余人、小人物、底层等标出性人群生存命运的思考,从而使其在获得一种异质美感的同时增强其对标出性文化(异质于主流的文化)的理解。
第四,激励主体精神。对于人的主体精神的尊重既体现为强调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作用和目的地位,强调尊重人和为了人的尺度,也强调在人类社会中个体精神不受集(群)体意志的控制、压抑和排斥,消费时代则具体表现为主体不被消费鼓吹所诱惑和异化。关于前者,因其利益共通性而常常可以达成普遍共识,对于后二者,则由于利益分配的争夺以及人的需求的变化而成为一种精神乌托邦。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消费类型逐渐从中产阶级消费过渡至家庭消费,又至今天的个人化和全民消费,消费内容也发生了从物质到物质兼精神、从实物到实物兼符号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人们的主体精神渐渐被物质—符号所诱导乃至遮蔽,在不知不觉中沦为被动者,被异化为各种产品(包括文化产品)的奴隶。艺术美育的最终目的恰在于自觉剥离人身上“被动的”“集(群)体的”外衣,唤醒人们的主体精神,还原人为感性适度的(既不缺乏也不泛滥)、感性与理性兼具的完善的人。
我们已经不可避免地进入了消费时代这一特殊的文化语境,在当下的审美实践中,无论是审美创造中的功利性、技术追求大于内蕴追求、借助工业的机械复制和肤浅化制造等问题,还是审美传播中基于营利、借助电子媒体、鱼龙混杂的大众传播问题,抑或是审美接受中追求刺激性、肉身化、符号性、快捷性、平面性等问题,都成为美学和艺术美育亟待思考和积极回应的现实问题,这就要求艺术美育要密切关注当代人的日常生活和感性生存,并对这些问题进行及时分析与解决,唯有如此,消费时代的中国艺术美育,才能真正找到自身坚实可靠的价值根基与生存位置。蔡元培曾以可以传导的“神经”来比喻美育[注]蔡元培以人的生命机体比喻教育的方方面面:“军国民主义者(相当体育),筋骨也,用以自卫;实利主义者(即智育),胃肠也,用以营养;公民道德者,呼吸机循环机也,周贯全体;美育者,神经系也,所以传导;世界观者,心理作用也,附丽于神经系,而无迹象之可求。此即五者不可偏废之理也。”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二卷),高平叔编,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35页。,强调美育之于人格完善和人群化育的重要作用,作为美育最为重要的途径,艺术美育必将通过人类创造的、具有开放性特征的艺术这一符号群,通过色彩、旋律、文字、线条等直观符号、符号所张显的形象以及其中所包孕的意蕴等鲜活之材,有效接通审美实践,在感情的“传导”中完善当代人的审美情感,培育其更具人文关怀的审美价值观,使接受者跳脱有形和有限的现实生活的界线,抵达无限而诗意的精神自由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