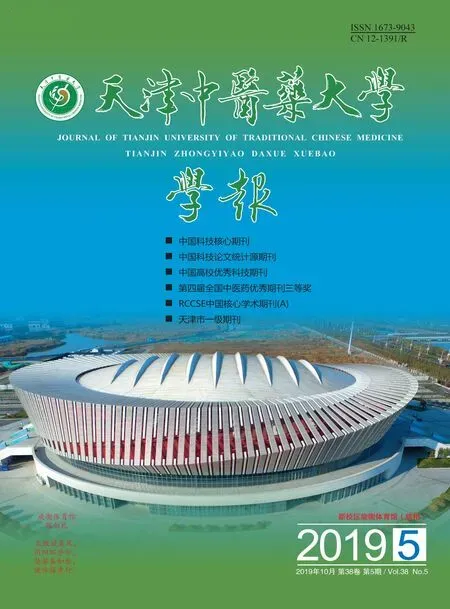再论《伤寒论》第131条*
2019-01-14王林东张国骏王东强
王林东,张国骏,王东强
(1.天津中医药大学,天津 301617;2.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天津 300192)
《伤寒论》词简义深,自古以来为其作注者颇多,但争议亦颇多。第131条:“病发于阳,而反下之,热入因作结胸;病发于阴,而反下之,因作痞也。所以成结胸者,以下之太早故也。结胸者,项亦强,如柔痉状,下之则和,宜大陷胸丸。”至今仍存在诸多争议:其一,对“病发于阳”“病发于阴”的争议;其二,对“痞”字的理解;其三,对结胸成因的理解。
1 各家对131条的阐释
张路玉认为表邪为阳,里邪为阴,病发于阳为太阳表证,病发于阴为内挟痰饮,外感风寒;认为痞即心下痞,方予泻心汤[1]。张隐庵认为病发于阳为发于太阳,病发于阴为发于少阴,少阴病误下,则邪入于胸膈之阴分,发为痞证;并未对痞的具体含义作出解释[2]。舒驰远[3]、黄元御[4]认为病发于阳为风伤卫,病发于阴为寒伤营;痞为心下痞;舒驰远[3]还认为并非是下之太早,而是不应下。柯琴[5]认为阳指人身之外,阴指人身之内,阴非指阴经亦非指阴证,发阴、发阳均有发热;痞为心下痞。钱潢[6]认为发于阳为邪在阳经,发于阴为邪在阴经;痞为心下痞。当代有学者[7]认为阳是指素体壮实且内有痰水的一类体质,阴是指素体不足且内无痰水的一类体质。也有学者认为[8]病发于阳为感受风热类邪气,病发于阴为感受寒邪。后世也大多在这几种说法中争论,但笔者认为这些说法大多考虑不够周全且存在值得商榷之处。对此,笔者冒然提出以下见解,不足之处还望同道斧正。
2 对于“病发于阳”“病发于阴”的理解
笔者认为“病发于阳”可以理解为发热重恶寒轻的太阳病,“病发于阴”可以理解为恶寒重无发热的太阳病。笔者认为原文7条中的“发于阳也”“发于阴也”及141条中的“病在阳”具有参考价值。
此条中“病发于阳”“病发于阴”为并列关系,故其中“病”字的含义应当一致,因为此条为太阳病篇中的条文,故“病”字理解为太阳病最为合适,且结合141条中“病在阳”的论述,其中“应以汗解之”及“其热被劫”提示“病在阳”应指以发热为主的太阳病。7条中“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亦提示“病发于阳”应为以发热为主的太阳病。结合“所以成结胸者,以下之太早故也”一句,其言外之意为晚用下法就不会发生结胸了,推断病邪有向阳明腑实证发展的趋势,故此时应有发热的症状,因此笔者认为“病发于阳”应解释为发热为主的太阳病。
和“病发于阳”相对应,原文7条中“病有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提示“病发于阴”应为恶寒严重而无发热的太阳病。发热、无热作为两个症状其实反映着正气的盛衰。正气盛,足以和邪气相争,故而发热,若此时误用下法,势必会使在表之邪热入里;若正气虚弱,不足以和邪气相争,则只见恶寒,误用下法,则会引寒邪入里,导致邪传三阴,甚至阴寒凝结于脏而发藏结。两者本质的区别在于正气的虚实,故而“阴”“阳”亦可以理解为“正虚之人”“无虚之人”。
3 对于“痞”的理解
大多学者认为“痞”就是“心下痞”即泻心汤证,而胡希恕先生认为[9]“痞”当指藏结,因为阴证用了下法不会发为病势更轻的心下痞证,且上一条讲的是结胸和藏结,所以胡教授认为痞就是痞块,即为藏结的意思。这是对“痞”的解释最充分的一种说法,也很具有说服力。但是胡教授把病发于阴理解为阴证,本身就是存在争议的,所以不能以此来排除痞为心下痞的可能。
3.1 “痞”不能理解为心下痞 《伤寒论》及《金匮要略》中含有“痞”的条文共29条,其中论述“心下痞”的条文有20条,论述“心中痞”的条文有3条,论述“胸中痞硬”的条文为第166条,论述“胁下痞”的条文有96和167条,论述“气痞”的条文为第151条,论述“少腹肿痞”的条文为大黄牡丹汤证1条,单独一个“痞”字的条文仅第131条1条。
“痞”字首见于《伤寒论》96条,意为胀满堵塞不通的感觉,对此并无争议。笔者认为131条中的“痞”字当同于此意,而不能理解为“心下痞”,依据有四:其一,按病位,痞可出现在心下、心中、胸中、胁下、少腹等部位。故“心下痞”只是“痞”的一种情况,不能等同,不能以偏概全,一概而论。其二,详前略后是张仲景的写作习惯,“心下痞”最早出现在142条,而本条在其之前,故不可能为“心下痞”的略语。其三,所有论述心下痞证的条文均明言病位在“心下”,并无省略现象,可见张仲景认为痞可出现的病位很多,这只是其中一种情况,故必明言病位。《伤寒杂病论》中不涉及“痞”之病位的条文只有2条,即151和131条。151条论述“气痞”,虽未言病位,但意在说明痞的性质,而不是痞在某部位的略语。故131条中的“痞”也应没有病位的省略,而只是作为病性的描述。其四,表证无论有无发热,下后都可能发为心下痞证,149条则提示有发热症时,下后既可发生结胸又可发生心下痞;154条则论述热痞的证治。故知心下痞证和结胸的区别不在于有无“热入”,而在于邪气有没有和水饮互结,若没有则发为气痞,若水饮与邪气互结则发结胸。而在原文中,结胸和“痞”显著的区别即在于有无“热入”,故“心下痞”在此于理不通。综上,第131条中的“痞”不能理解为心下痞。
3.2 “痞”可理解为“藏结” 笔者认为痞可深入理解为藏结,依据有二:其一,从条文结构及文意联系来看,第128条提出结胸、藏结的概念并论述了结胸的脉证;129条论述藏结的脉证;130条论述藏结的阴阳属性;131条言结胸及“痞”的成因;其后几条均言结胸的证治。149条至166条虽大多论述心下痞,但从149条“……而以他药下之……若心下满而硬痛者,此为结胸也……但满而不痛者,此为痞……宜半夏泻心汤”来看,心下痞和结胸可以是柴胡证误下后的两种不同转归,张仲景意在和结胸相鉴别,以防后学误当作结胸来治疗。直到167条复言藏结,“总—分”之行文结构明矣。故而,此处“痞”为藏结的可能性更大。其二,“痞”代指藏结在原文中有实例。167条“病胁下素有痞,连在脐旁,痛引少腹入阴筋者,此名藏结,死”。此处“痞”即为藏结之意,故知张仲景有时以痞来代藏结。因此,131条中的“痞”理解为藏结更为合适。对于藏结含义的论述主要在129、167两条,129条所述藏结似于结胸,“寸脉浮”提示邪从表而入[10],“时时下利”提示可能经过误下,应是新发的一类阴寒凝结于脏的疾病。若出现“舌上白胎滑”提示阳虚水泛,则难治。而167条则是长时间疾病发展的结果,因与129条具有相似症状即“如结胸状”,且具有内脏阳虚、阴寒凝结的相同病机,故亦命名为藏结,但此种藏结更加危重。两种藏结病机相同,症状相似,但病程不同。131条中“痞”所指藏结应为第一种类型。下述医案可以佐证此种观点,患者桑某素体娇弱,并非痰实壅盛之体,但经误下后仍可发为结胸,且服用大柴胡汤后症状加剧,大柴胡汤本可泄热,但症状却加重,盖因泻下之后损伤脾阳进一步加重了体内的痰水之邪,故而引起症状加重[11]。
4 对“而反下之,热入因作结胸”的理解
病邪在表,而用下法,导致邪热入里与水饮互结而发结胸,邪热和水饮是导致结胸缺一不可的两个病机,但是如此重要的病机却没有在原文中出现,那一定是隐藏在原文的第一或第二要素[12]中,“邪热”病机无疑隐藏在“病发于阳”中。而“水饮”的病机当隐藏在“病发于阳”或“而反下之”中,故而有的学者[13]认为病发于阳是指素体有痰水之实邪内结,国家规划教材《伤寒学》[14]亦认可此说法,其言外之意为素体没有痰水的人下后就不会发生结胸,其无疑缩小了结胸的可能发生人群,且下法之后的“热入”无从说起,这是以方测证,强行将病机加入其中的结果,缺乏实质依据,故此说法有待商榷。然而“水饮”也可能发生在“下之”这个环节,下法是可能产生水饮的,下法伤脾,脾失运化则生水饮,即下后发生一过性的脾伤饮停,水饮与入里的邪热相结而发生结胸。故笔者认为此处的水饮不应该是素有的而是下法伤脾新生的。此处有一则医案论述了此种"藏结"的证治,患者胸腹硬满疼痛而似结胸状,饮食尚可,大便稀,小便正常,苔白滑,脉沉细紧,诊断为阴寒极盛,脾肾阳气衰败之证,处以党参、附子、干姜之类,五剂即愈。5 总结
第131条在原文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其之前论述结胸和脏结,之后论述结胸证。故而理解此条时联系上下文十分重要。本条也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下半部分论述大陷胸丸证,争议较少;上半部分论述结胸和“痞”的成因,承接上文,争议颇多,对此部分笔者的理解为:太阳病发热较重,或伴有向阳明腑实发展的趋势,反用了下法,导致一过性的脾伤饮停,同时邪热入里与水饮互结,遂发结胸;恶寒严重而无发热的太阳病,其人素体虚,反用下法,遂发藏结;结胸是下法用的过早所致。笔者认为此说法较符合临床实际,且对临床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疾病向阳明腑实证发展的过程中,把握下法使用的时机十分重要,既不可过早又不可过晚;用下法应防止发生脾伤饮停的情况,可佐以健脾利水之品;虚人或表证未解时慎用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