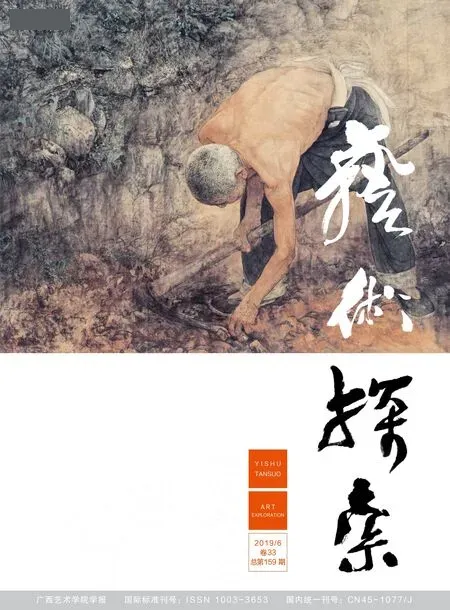新时期以来重庆舞蹈发展述论(1978—2018年)
2019-01-10王海涛
王海涛 李 匆
(1,2.重庆大学 艺术学院,重庆 401331)
新时期以来40年的重庆舞蹈可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第一,通过对“文革”前舞蹈的恢复重建,舞蹈题材也在思想解放后向现实主义转变,民族舞蹈开始挖掘本土舞蹈文化;第二,伴随着大众文化的兴起,以群众舞蹈为主流,重庆舞蹈在实践中确立了本土化舞蹈品牌,散落的巴渝舞蹈文化在这一时期得到抢救和整理;第三,进入新世纪后,随着舞蹈形式的丰富、高等舞蹈教育的发展、跨国际的艺术交流以及群众舞蹈主导地位的确立,重庆舞蹈进入了繁荣时期,也朝全国舞蹈话语权和主体地位的方向迈进。
一、历史回顾
抗战时期,舞蹈成为人民表现思想情感和挥洒爱国情怀的重要艺术形式。“重庆人民在内部条件不利的情况下, 高举爱国主义旗帜, 为挽救国家危亡而奋斗, 形成了重庆人文精神的又一特质——艰苦卓越的奋斗精神和反对专制、追求进步的科学民主精神。”[1]89一批批舞蹈人将舞蹈与爱国情感联系起来,形成了具有抗战文化色彩的新舞蹈风格。其中,《游击队之歌》《义勇军进行曲》《丑表功》《罂粟花》《饥火》等一大批现实题材舞蹈,是吴晓邦为重庆带来的振奋人心的作品。这些作品采用戏曲舞蹈与现实手法相结合的形式,开启了中国的新舞蹈艺术:“一方面从中国传统戏曲、武术、民间传统歌舞中汲取文化营养并借鉴舞蹈语汇,另一方面从现代中国民众的现实生活动态中积极提炼舞蹈语汇,同时借鉴西方现代舞的表现技法,并以表现中国社会现实生活为舞蹈表现内容的一种新舞蹈形式”[2]180,影响着中国舞蹈和舞台艺术的发展。作为抗战时期激励人心、鼓舞斗志的文化形式之一,舞蹈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人民的情感寄托。
抗战结束后,舞蹈又成为树立民族自信、宣扬民族大义的文艺形式。在这一时期,中国舞蹈开始迈进当代都市剧场。1946年3月6日,影响全国的“边疆音乐舞蹈大会”在重庆举办,大会汇集了新疆舞、藏族舞、苗族舞等各地民间舞蹈,这不仅为重庆人民带来了多民族舞蹈文化,更把中国民间舞蹈作为独立的艺术形式“搬”上了舞台,首次走进都市剧场中展演。冯双白评价说:“应该说,中国民间舞迈入当代都市剧场的步伐,起始于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尤其是以戴爱莲等人在四川重庆大会堂举行的‘边疆舞蹈大会’的表演为重要标志。”[3]490藏族舞蹈《巴安弦子》《春游》,苗族舞蹈《苗家月》,羌族舞蹈《端公驱鬼》,以及其他民族民间舞蹈在此汇集展演。“在1946年,它们却像是荒岛中的璞玉,首次被舞蹈家系统地挖掘、整理搬上了都市的舞台,以灿烂的光彩轰动山城,演出盛况空前,应邀一演再演。”[4]2抗日战争后,重庆舞蹈并没有因为战争带给人的不安和恐惧而停滞不前,相反,它更像是鼓励人心和宣扬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用独特的艺术表现方式抚慰着受伤的人们,也成为中国民族舞蹈发展进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二、开拓探索期(1978—1990年)
1978年5月,“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立了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形成了广泛而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也激发了艺术家的创作热情。新时期以来,思维的开阔和时代的特性,引导重庆舞蹈创作朝现实主义方向转变,并逐步探索本土舞蹈文化的构建。
舞蹈创作离不开文艺的总体导向。新时期以来,全国文学艺术都朝着写真事、说真话的现实主义前进。重庆舞蹈跟随时代创作思潮,创作出一系列现实主义题材的舞蹈作品。1983年6月,重庆市歌舞团首次进京演出,《小萝卜头》《燃烧吧,节日的火把》《葬花吟》《拉纤的人》《康定情歌》《乡音》《玩花灯》《钱迷》等作品呈现在首都舞台上。其中,由毕西园和杨昭信编创、题材选自《红岩》的《小萝卜头》,塑造了向往光明、渴望自由的人物形象,弘扬了真、善、美 ,宣扬了民族文化,也凸显了革命斗争精神。“从中可以看出舞蹈者已把创作触角深探到历史及现实生活等更多领域,表现出一种‘求新思变’的愿望和要求。”[5]35
这一时期,重庆舞蹈开始将传承民族文化,如巴渝文化、三峡文化、渝东南少数民族文化等,作为舞蹈发展的重要内容。这体现在舞蹈作品地域特征的凸显,也体现在本土文化和舞蹈专业课程建设的融合。1988年,重庆市艺术学校建立了舞蹈、曲艺、杂技、话剧、音乐剧等专业。其中,舞蹈专业开始尝试以中国舞和巴渝特色舞蹈的教育教学体系为主,将重庆民间舞蹈与学院教育相结合,并注重不同艺术学科之间的交叉。这一举措显示了重庆文艺办学模式向多元化的转变,还行之有效地保护、传承了非遗舞蹈和地域文化。此阶段对本土舞蹈文化的保护和探索,是重庆民间舞蹈发展的重要之举。
三、实践形成期(1991—1999年)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转型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大众文化的兴起,群众舞蹈在这一时期成为主流,引起了重庆舞蹈爱好者和退休舞蹈干部的关注。先是一两人在广场扭秧歌,到社区和团体的舞蹈组织,重庆群众舞蹈成为重庆和全国群众文化的代表。同时,重庆舞人对散落的巴渝舞蹈文化进行了整理,并编制成理论教材。这一时期,无论是群众舞蹈还是专业团体和舞蹈人,都向着发扬重庆地区舞蹈文化的中心聚焦。
在这种良好的形势下,随着全国群众舞蹈比赛的兴起,重庆群众舞蹈开始创作属于自己的舞蹈作品,并以舞蹈队和文化单位为代表,登上了全国群众舞蹈比赛的舞台。
这一时期,重庆群众舞蹈不仅成为大众娱乐的文化活动,更是向着专业化、民族化的趋势发展。1994年5月,全国首届中老年健身舞蹈汇演在北京圆满举办,为期一个星期的汇演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如社交舞、国际舞、太极拳、健身舞等。其中,重庆的作品《枫叶恰似二月花》在众多节目中脱颖而出。1996年在第六届全国“群星奖”首届舞蹈专场的比赛上,重庆代表作品《老天快下雨》《叶儿青青,菜花黄》取得了优异成绩,在全国舞台上展现了重庆群众舞蹈的专业水平。1997年,由文化部、国家民委、重庆市人民政府主办,重庆市文化局承办的第七届孔雀奖少数民族舞蹈比赛在重庆举行。全国各民族舞蹈家近300人相聚重庆,参赛作品70多部,这不仅为重庆舞蹈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也标志着重庆舞蹈在探索前进中走向独立。
“铜梁龙舞”“高台狮舞”“秀山花灯”“肉莲花”“花灯舞”“摆手舞”等是重庆民间舞蹈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民间舞蹈并非仅以单一的形态呈现于舞台,而是融入群众舞蹈的建设中。如铜梁龙舞,在群众的自发和舞龙队伍的带领下,形成了以铜梁龙舞为载体的群众性舞蹈作品。铜梁龙舞不仅参加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华诞的庆典,还代表“中国舞龙队”在国际龙狮邀请赛中为国夺得桂冠,使全国对重庆舞蹈给予了认可。也由此,重庆舞蹈逐渐形成了具有本土文化特色的群众舞蹈艺术。
巴渝舞是阆中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消散在历史长河中的舞蹈文化,巴渝舞抢救工程迫在眉睫。1992年1月19—21日,重庆市舞蹈家协会召开首届“巴渝舞讨论会”,参加讨论的有舞蹈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民俗学家、民族音乐学者及《中国民间舞蹈集成》编辑部研究人员等。会议注意了巴渝舞的尚武精神,从考古学、文献学等角度对巴渝舞进行了考证,并提交了11篇学术论文,为巴渝舞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字资料。“会议的主题是讨论研究历史名舞巴渝舞,但实际上研究与探索的范围已经超出了这个历史名舞的范畴,而是伸展到对巴渝地区历史传统舞蹈文化的研究。”[6]2一年后,王静主编的《巴渝舞论》出版,正是首届“巴渝舞讨论会”的学术成果整理。
四、繁荣发展期(2000—2018年)
设立直辖市后,“重庆文学艺术、群众文化、文物博物馆事业、文化设施、广播电视和新闻出版等重庆文化的各个领域,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使重庆文化呈现出较为繁荣的发展局面”[7]512。城市和文化的繁荣,打开了重庆舞蹈的市场。高等舞蹈教育的形成和发展,群众舞蹈的进一步普及和提高,舞蹈市场“引进来、走出去”的策略,国内外舞蹈文化的交流,等等,使这一时期重庆舞蹈呈现出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转变。
“科教兴渝”战略实施后,对文化教育的高度重视,为重庆舞蹈带来了广泛的教学资源和人才力量。随着一大批优秀舞蹈工作者的返乡和外来专家的陆续抵渝指导,重庆舞蹈开始向培养专业型、综合型人才的目标发展。2000年,中国汉唐古典舞奠基人孙颖受邀来到重庆大学任舞蹈系主任,随后在重庆大学创办了汉唐古典舞系,同年还在重庆与古典舞同仁一同编写了《中国古典舞(汉唐)基训教材大纲》,至今仍为重庆大学舞蹈系教学的重要指导。此外,西南大学、重庆师范大学、重庆文理学院、重庆人文科技学院等都陆续成立舞蹈专业,组建校园舞蹈队,并构建具有代表性的特色学科。重庆高等舞蹈教育一方面是重庆舞台表演的核心力量,为重庆市舞蹈比赛和重庆市大学生艺术展演带来饱满的作品,另一方面也将优秀传统文化跨越国界进行交流和展示。
舞蹈表演团体作为舞蹈传播、交流、创新的核心力量,在此时的重庆纷纷涌现。区别于以往表演团体的表演模式,重庆舞蹈团体不仅仅围绕本土文化展开创作,更以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成为联系全国舞蹈、世界舞蹈的重要形式。2013年,在刘军的带领下重庆市芭蕾舞团推出了原创现代芭蕾舞剧《追寻香格里拉》,编导将西方芭蕾舞与中国民族民间舞相结合,从题材到表演形式再到舞蹈语言,整部舞剧都给舞蹈界和观众以“新”的感受。作为中西部地区唯一的专业芭蕾舞团,重庆市芭蕾舞团在这一时期创作出大量的舞台作品,《追寻香格里拉》《山水重庆》《天鹅湖》《寒逐》《睡美人》《堂•吉诃德》《霓裳炫彩》等作品享誉全国。随着舞剧《杜甫》在全国舞台亮相并为重庆摘得首个中国舞蹈“荷花奖”舞剧奖,重庆舞蹈走向现代与传统相结合、求新思变的繁荣阶段。
同时,群众舞蹈依然是当下重庆舞蹈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就像山城高山中的密丛,郁郁葱葱,点缀着重庆舞蹈的繁荣。重庆群众舞蹈寓教于乐,艺融于民,百花齐放。一方面,它是承载区域文化的重要形式。在全国群众舞蹈比赛和展演中,铜梁的龙舞、渠县的高台狮舞、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秀山花灯、酉县的摆手舞等纷纷亮相,或以独立的舞蹈形式表演,或穿插于其他作品之中。另一方面,它是重庆人民自我愉悦和满足的需要。随着广场舞的兴起,“无论是在主城区如渝中区人民广场、沙区文化广场、九龙坡区九龙广场,还是在远郊区县合川塔尔门广场、铜梁龙都广场、黔江文化广场、涪陵体育广场等等,人们或自发地、或有组织地在这里开展各种体育、舞蹈、演出、展览等活动,以至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广场文化现象”[7]519。
新时期以来,重庆舞蹈呈现出若干不同的发展阶段。从将舞蹈作为抒情达意的手段到注重舞蹈作品中的民族关怀,从较少的舞蹈团体和稀缺的舞蹈人才到高等舞蹈教育和专业团体的发展,从广场上扭着秧歌自娱自乐到群众舞蹈在全国专业舞台上取得荣誉,重庆舞蹈跟随全国文艺发展热潮,逐渐打开了繁荣的局面,并形成了鲜明的地域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