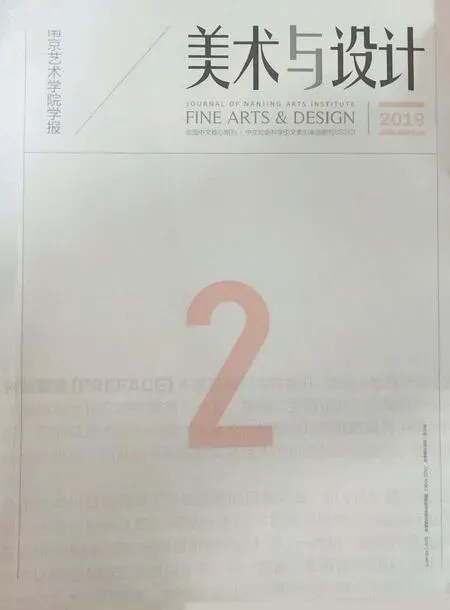包世臣碑学思想之渊源授受考述
——兼与“源自阮元”说商榷①
2019-01-09南京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23
安 生(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一、弁 言
书学史上,清代碑学不论在技法层面,还是书法史观、书法美学等观念层面,无不给予书坛以至深至巨的影响,其风流所被泽及当代。职是之故,书学界在进行理论谱系的界定与理析的过程中,一致认为,包世臣之碑学思想源自阮元,刘恒《中国书法史·清代卷》:“真正将阮元的碑学主张发扬、完善,并使之深入人心者,还应归功于包世臣的实践和宣传。”[1]191金丹承其说,明确指出包世臣书学思想“当然受到当时的学术权威阮元理论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2]62-70。姜宝平亦认为“包世臣完全承袭了阮元的尊碑观念。……将阮元中原古法的碑学观念落实到了实处”[3],等等②详见李宗纬解析《艺舟双楫》(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胡泊《清代碑学的兴起一个“范式”转换的研究》(南方出版社,2009年版)、邵敏智《清代书法理论之碑学审美意识研究》(中国美术学院,2010年,博士论文)、王民德《晚清碑学思潮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2014年,博士论文)、郭红全《当代北碑书法的审美自觉》(《中国书法》,2017年,第24期),等等。,而罕有异声。
这固然可以为碑论的缘起兴衰串联为一个完整的历史闭环,却并未符应历史的文献事实与本然逻辑——“一脉传承”的单线“影响/被影响”在传统“文人文化范畴”③罗思德定义的“文人文化范畴”是一种本体内在的综合因子。(罗思德《以文解画,以画解文:中国古代绘画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复旦学报》,二〇一五年,第四期,第二六页。)长泽规矩也认为,诗书画作为艺术的三种重要门类,其关系密不可分,溯其远祖为唐王维、元赵孟頫,近则明沈周、唐寅、祝允明、文征明等人而尤以董其昌兼擅三艺,至有清一代先后有王士祯的诗画同趣、金农、翁方纲、郑燮诸人的金石与书画诗文等。(参见长泽规矩也《中国学术文艺史讲话》(影印本),山西人民出版社,二〇一五年,第一九五页。)由此可知,立足诸文艺的现实实践,进行交叉综合的理论观照与建构方式已成为明清思潮。笔者以为,“文人文化范畴”还具有一种本体外在的社会关系因子,即以个体之间交游问学、切磋竞技为中心构成的一种群体性思潮。本文视域即涵盖内、外二者。的观照下,往往遮蔽了主体自在的多重身份层叠与多元知识受容的复杂生态语境。本文绾合艺术研究的外部视角——包世臣交游问学的社会关系网络,与内部视角——包世臣《艺舟双楫》之论文、论书表现出的综合文艺思想,缕析包世臣碑学思想之渊源授受,兼与“源自阮元”说商榷,以求教于方家。
二、圈内与圈外
在扒疏包世臣一生交游问学的社会关系网络之前,首先对书学界关于“包世臣碑学思想源自阮元”说的定论逻辑作一扼要阐述。阮元宦显仕达,名重清廷,在经史、天算、舆地、编纂、金石、校勘等方面皆有高深造诣,被尊为一代文宗,享寿八十又六,谥“文达”,入祠乡贤禂、浙江名宦祠。《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成为彰示阮氏书学思想的集大成之标识。缘其高位与专著之内外双重影响力,遂在其周围凝聚成一股强劲的士人文化群体,其“碑论之祖”的地位得以为当代书学界所建构。④详见刘恒《中国书法史》(清代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周斌《阮元书学思想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金丹《阮元书学研究》(荣宝斋出版社,2012年版)、姜宝平《清代碑学的定鼎与局限——从阮元、包世臣到康有为》(《中国书法》,2017年,第四期)等等。
所以强调阮氏“碑论之祖”的地位为当代书学界所建构,是因为这种历史谱系的重塑是随着新时期①新时期的时间界定,取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时间段。整个文艺的复苏才逐渐完善起来的。检校清及近现代的学人论述,尚未发现“包世臣碑学思想源自阮元”的说法。谢应芝《书安吴包君》:“君学书三十年,尽交天下能书之士,……遂称书家大宗。”[4]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包世臣》亦言:“其书法,得古人执笔、运锋、结体、分势之奇,推为书家正宗焉。”[5]康有为叙包氏碑学思想之渊源亦直言其受之于邓石如而不曾提及阮元,《广艺舟双楫·尊碑》:
泾县包氏以精敏之资,当金石之盛,传完白之法,独得蕴奥;大启秘藏,著为《安吴论书》。表新碑,宣笔法,于是此学如日中天。迄于咸、同,碑学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言北碑,写魏体,盖俗尚成矣。[6]8
以至有人将包世臣视为“碑学开山之祖”,祝嘉《艺舟双楫疏证》自序:
包世臣是清代碑学开山之祖,他于嘉庆七年二十八岁的时候,认识碑学祖师邓石如,受邓氏的影响,研究碑学,前后又结识当时不少书家,相与讨论,写成《艺舟双楫》的《论书一》《论书二》,碑学的兴盛,他是有很大的功劳的,称他做碑学开山之祖,是很恰当的。[7]2
清及近现代诸学人在体认包世臣碑学思想之渊源授受时概不涉及阮元,而独言邓石如。这与当代书学界“包世臣碑学思想源自阮元”的定论构成学理矛盾。金丹《包世臣书学批评》尽管将包世臣碑学理论的启示归于阮元,却也注意到这种结论与文献史实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包世臣小阮元12岁,尽管包世臣在文章中没有直接提到阮元的名字”并自注“包世臣和阮元多年同住扬州,却没有交往的记载,其原因不清,阮元和邓石如也没有交往,或是布衣和大学士的地位悬殊过大,或是其他原因。又包世臣在文章中多处不点名地批评阮元之流”[2]62。
金丹将邓石如、包世臣师徒无与阮元交往②在阮元与之交游的金石学人亦不与邓、包诸人相涉。参见张勇盛《阮元金石交游考》《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6年,第9期。的史实简单地概括为“布衣与大学士”悬殊的社会地位实不能成立。因为师徒二人皆与同为宦显的张惠言、张琦兄弟以及金榜、钱伯埛诸人等交好至密,包世臣女嫁于张琦子,两家结为姻亲。这恰恰反映了邓石如、包世臣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是将阮元排斥在外的,且共同指向了社会关系网络的内部成员构成——多为“桐城派”。
包世臣安徽泾县人,其业师邓石如安徽怀宁人,二地皆毗邻桐城,同属江南左布政使司安庆府。③《清史稿·地理志》:“安庆府,属江南左布政使司。……领县六。怀宁、桐城……”(赵尔巽等《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第2002页。)此时恰是桐城派昌大期,如刘师培《论近世文学之变迁》勾勒桐城派发展影响之轨辙:“望溪方氏,摹仿欧、曾,……桐城文士多宗之,海内人士亦震其名,至谓天下文章莫大乎桐城。厥后桐城古文传于阳湖、金陵,又数传至湘、赣、西粤。”[8]171师徒二人自幼的受学基础皆得益于诸长老、族辈之人的乡学(桐城学),李兆洛《石如邓君墓志铭》“君少以贫故,不能从学,逐村童,采樵,贩饼饵,负之转鬻,日以其赢给饘粥”故自幼“暇即从诸长老问经书句读。”[9]219包世臣《述书上》溯其书学经历“乾隆乙酉之岁,余年已十五。……余从问笔法,授以《书法通解》四册。”[10]367
邓石如与姚鼐为忘年交。姚鼐倡古文,主张“义理、考据、词章”三者并重,创“阴阳、刚柔”说,享誉海内。关于二人交往及姚鼐对邓石如的影响,穆孝天据现存有关姚、邓二人的题咏赠答析断:
邓石如的书法篆刻成就,固然是他勤奋学习的结果,特别是他的篆刻能融浙派与徽派的阴阳刚柔的风格于一炉,但在指导思想上,却得自姚鼐理论的启发……他们之间的频繁交往,不仅因为他们在书法上有着同样的酷爱,更重要的则是他们有着共同语言。在数十年的相处中,或相互题咏赠答,或相互作书谈艺,彼此融洽无间。[9]55
姚鼐长邓石如十一岁,曾先后在梅花、紫阳、钟山等书院任主讲,以其文学理论与实践、学术成就名重当朝,且姚鼐文论与邓石如书法实践多有契合处,经姚鼐,邓石如还得以与当时擅名书坛的王文治等人结缘。包世臣亦曾“以嘉庆壬申谒惜抱先生于白门钟山书院,请为学之要。”[10]354(《清故翰林院编修崇祀乡贤姚君墓碑》)
不宁唯是,邓石如师友弟子——梁巘、程瑶田、金榜、张惠言、包世臣等亦皆与桐城派——尤以刘大櫆的渊系甚深。④参见穆孝天、许佳琼《邓石如研究资料》(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王佳佳《刘大櫆交游考》(安徽大学,2015年,硕士论文)。包世臣更与文之“阳湖派”、词之“常州派”创始人张惠言、张琦等人及其后学殿军周济交往甚深。“阳湖派”虽对桐城派有所批评、修正,却仍是从桐城派起步且受益于刘大櫆特多,陈继辂《七家文钞序》:“乾隆间,钱伯坰鲁思亲受业于海峰之门,时时诵其师说于其友恽子居、张皋文。二子者,始尽弃其考据骈俪之学专志以治古文”[11],乃“桐城派之旁支”[12]526-540,吴育、左辅、李兆洛等皆与邓石如交往甚密且各有记文赞述其书艺成就。[9]52
包世臣与常州词派殿军周济的亦师亦友之切磋相学,成为晚清碑学“重拙大”理论成型的重要绾合点。“重拙大”作为晚清词学理论的经典概念,肇始于端木埰,经王鹏运而至况周颐明确揭橥为词学“三要”,以其丰富的内涵与浑雅的格调,充实、提升了词学理论批评的内容与高度,是晚清词学走向成熟的标志。[13]一般认为,“重拙大”与晚清词坛重“寄托”与“蕴藉”的思潮保持一致,它上承张惠言“意内言外”并直接受孕于周济“四家”说,是张惠言、周济学说在创作上的具体实践与理论上的体系建构。①相关论述主要有魏春吉《〈蕙风词话〉中的重拙大理论》(《河南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李旭《从附会求意到审美把握——常州派词学的理论升华历程》(《中国文学研究》,2002年,第4期)、苏利海《“重拙大”新议》(《文艺理论研究》,2011年,第4期)、彭玉平《晚清民国词学的明流与暗流——以“重拙大”说的源流与结构谱系为考察中心》(《文学遗产》,2017年,第6期)等。周济曾以己作诗求教于包世臣而被批评为“质美而未学”[14](《介存斋诗自序》),周氏遂将诗稿付之一炬并“益自淬厉,求之六经三史,以期实用”[15]361(魏源《荆溪周君保绪传》),包世臣经世致用思想与诗文词同质观皆对周济“以词存史”的词学观有着较深的影响。[16]
弥纶以上文献所载以邓石如、包世臣师徒为中心及其后学者的交游网络,刘大櫆与邓石如师梁巘、程瑶田交往密切;其弟子姚鼐、金榜、钱伯埛与二人互为知己,并影响着阳湖派、常州词派创始人张惠言、张琦、周济诸人;王鹏运、况周颐又受桐城派王拯督教,且艺术史界将况周颐、郑文焯等晚清词人归入以康有为为核心的遗老书家圈。[17]2042其核心身份共同构成了安徽籍的群体文化圈,《安徽通志稿·列传》卷十传安徽文化之盛:
有清二百七十余年,皖人才能以其天赋伟异之才施之学问,创开一代风气者,经学则有戴震,佛学则有杨文会,而书法则石如其尤也,其聪明才力足使千人皆废……[18]
这种聚内与排外的紧张关系,正牵扯着同时期文坛上骈、散之争的公讼——以桐城“三祖”为代表的古文家与以阮元为代表的骈文派彼此攻讦、对峙,成为清代汉学与宋学之争在文学领域的投影。[19]刘毓崧因循阮氏“文言说”而赞述扬州骈文派,《吴礼北竹西求友图序》:“况百年以来,扬郡名儒尤盛,自阮文达公而外,……其深于骈散体文之学者,奉《易·文言》为根柢,《诗·大序》为范围,《春秋》内外传为程式,以熔铸秦汉后之文;而非若诘屈以为新奇,空疏以为简洁也。”[20]而桐城派对阮氏此论批评甚烈,姚鼐《与石甫侄孙》表现出对骈文派的嗤之以鼻“吾昨得《凌仲子集》阅之,其所论多谬,漫无可取。而当局者以私交入之儒林,此宁足以信后世哉?……至于文章之事,诸君亦了未解。凌仲子至以《文选》为文家之正派,其可笑如此”[21]。阮元主持《国史儒林传》编撰,故姚氏所谓当局者以私交之入儒林,正对阮元而发。足见桐城派与骈文派之思想理念的对立。包世臣不仅向姚鼐求“为学之要”,更将其书法成就同其业师邓石如并誉,《论书十二绝句》(十二):“无端天遣怀宁老,上蔡中郎合继声。一任刘姚夸绝诣,偏师争与撼长城。”[10]387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包世臣《国朝书品》将姚鼐行草书推至“妙品下”,仅次于“神品”(一人)、“妙品上”(一人)的邓石如,而阮元竟不在其所选评清人书法“九品”九十一人之列。[10]387-394此诚为包世臣与阮元虽同居一城多年,却始终不曾与交往的深层原因。
三、书论与文论
外部社会关系的梳理不能构成包世臣碑学思想与桐城派渊系甚深的直接史实,好在双方所存的理论著作中保存了相对丰富的切近观点,可以互为关照与印证。
包世臣所著艺舟之双楫——“论文”“论书”,在历史上并不多见,足见其在文学、书学上有着共通交衍的理论自觉追求。[22]倘觇鉴包氏书学与桐城派文学的切近,不妨将包氏文学作为勾连二者的跳板。包世臣为文始终秉持“经世致用”的政用思想,故倡明道之古文而斥“利禄之途,人怀侥幸”之时文,《或问》:
古文言皆己意,八比则代人立言。……古文虽短章,取尽己意,故转换多变态,其墙壁宽而峻;八比虽长篇,取协题情,故推勘少回互,其墙壁隘而夷。……朝驾南辕,暮从北辙,前邪后许,谬种流传,隳风气而坏风俗,遂致世道人心愈趋愈下。[10]304-306
所谓时文“代人立言”乃陈陈相因,蹈袭形式,难以抒写性情,寄托经旨;“古文”则正“表露己意”,任性自然。包氏在与时文之“假、恶、丑”的比对中凸显古文之“真、美、善”。那么,如何作古文?包氏落实桐城派“言有物”“言有序”的文法规范,《扬州府志艺文类序》:
盖尝论词无古今,概为三则:诗文赋颂,异流同源,懿彼发伦类之淳漓,讽政治之得失,……言必有物,斯其上也。……于以发抒抑郁,陶写襟怀,程其格式,平险分焉。……气以柔厚而盛,势以壮密而健,……斯其次也。至若以形声求工,倍犯为巧,此则属对之余,酬酢之技。……风斯下矣。……然而详加披诵,则古厚今浇,古劲今孱,篇幅滋长,意义逾薄,则知文气之变,本自人心。[10]258
包氏将“懿讽得失”“陶写襟怀”“形声求工”依次置作上、次、下三等,意在言文有远近、高下之次弟;所贵文能“讽颂政治得失”,根柢在文有“世道人心”之义理,《或问》:“盖义理存乎人心,随所学为深浅,既明字义,又明文法,而必依人为说,从门入者,不是家珍,斯之谓矣。”[10]305包氏所言“义理”“文法”者,即姚鼐所倡“义理、考据、词章”也,故包氏特推誉近世桐城姚氏学派之文法造诣,《雩都宋月台古文钞序》“近世古文,推桐城姚氏,其造诣,实能别时古之界,所言信为有序。”[10]332
既然文法是古文创作的第一精义,《与杨子季论文书》:“天下之事,莫不有法,法之于文也尤精而严。”[10]262如何进一步落实桐城派所倡之“言有物”“言有序”的要则,《艺舟双楫·论文》首篇《文谱》开宗明义:
余尝以隐显、回互、激射说古文,然行文之法,又有奇偶、疾徐、垫拽、繁复、顺逆、集散,不明此六者,则于古人之文,无以测其意之所至,而第其诣之所极。……是故讨论体势,奇偶为先。凝重多出于偶,流美多出于奇。[10]249
垫拽、繁复与“回互之事”相对;顺逆、集散与“激射之事”相对;而奇偶、疾徐,则行于垫拽、繁复、顺逆、集散之中。故只有回互、激射之法完备,文义才能隐而复显。其后依次胪列“文法”之分目,并举例以致意,“次论气格,莫如疾徐”“垫之法有上有下”“拽之法有正有反”“至于繁复者,与垫拽相需而成”“然而文势之振,在于用逆;文气之厚,在于用顺。顺逆之于文,如阴阳之于五行”……若详加比较刘大櫆《论文偶记》所论文法,包氏所言文之“奇偶参差”的承袭之迹昭然,其《二五》:
文贵参差。天之生物,无一无偶,而无一齐者。故虽排比之文,亦以随势曲注为佳。好文字与俗下文字相反;如行道者,一东一西,愈远则愈善。一欲巧,一欲拙;一欲利,一欲钝;一欲柔,一欲硬;一欲肥,一欲瘦;一欲浓,一欲淡;一欲艳,一欲朴;一欲松,一欲坚;一欲轻,一欲重;一欲秀令,一欲苍莽;一欲偶俪,一欲参差。夫拙者,巧之至,非真拙也;钝者,利之至,非真钝也。[23]10
在粗陈包世臣古文思想后,反观其书论。包世臣论书与论文同,首重性情。《答熙载九问》:“书之形质,如人之五官四体;书之性情,如人之作止语默。……是故有形质而无情性,则不得为人,情性乖戾,又乌得为人乎?”[10]396
其二,书贵“气满”,《答熙载九问》:
先生常言左右牝牡相得,而近又改言气满,究竟其法是一是二?作者一法,观者两法。左右牝牡,固是精神中事,然尚有形势可言。气满则离形势而专说精神,故有左右牝牡皆相得而气尚不满者,气满则左右牝牡自无不相得者矣。[10]397
“气满”为精神本质,即“性情之正”,包氏论书再三致意“书以气为主”,刘大櫆《论文偶记》倡“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故神以气为主”[23]3(《其三》)或已开先声。“左右牝牡”之于“气满”,又与姚鼐“阴阳、刚柔”之于“义法”相酹,《复鲁絜非书》:“且夫阴阳刚柔,其本二端,造物者糅,而气有多寡进绌,则品次亿万,以至于不可穷,万物生焉。故曰:‘一阴一阳之为道。’夫文之多变,亦若是已。”[24]94其后,刘熙载《书概》有“书,阴阳刚柔不可偏颇,大抵以合于《虞书》九德为尚”[25]804之论。包氏区分作者与观者,着眼在作者创作的浑然天成而学者学习的渐次进阶,实践指导意义突显。
桐城文论影响悠久深远,最得力处在理论与实践的顾盼相长,也就是理论的实践品格得以贯之,刘大櫆《论文偶记·九》:“要知得气重,须便是字句下得重;此最上乘,非初学笨拙之谓也。”[23]5何谓“字句下得重”?即由字句反寻音节,由音节体会神气,自下而上贯通神会,“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故“音节者,神气之迹也;字句者,音节之矩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23]6此即传桐城文法者之不二法门。包世臣论书辄遵桐城可操作性极强的作文之法,多敷陈书法之双钩、悬腕、实指、掌虚、逆入、平出、峻落、反收等可具实践的技巧,《答熙载九问》:“汰之,避之,唯在练笔。笔中实,则积成字,累成行,缀成幅,而气皆满,气满则二弊去矣。”[10]400故包氏特重练笔与运指,《述书中》“东坡有言:‘执笔无定法,要使虚而宽。’善言此意已。……凡人引弓举重,筋必反纽,乃长劲得力,古人传诀,所以著悬腕也。”[10]370
四、余论与结语
文人问学交游是一种较高层次的学术交往。在这种活跃的氛围濡染下,不断拓展已有的学术视野、更新自在的思想观念,对创作实践、理论生成、学术争鸣等面向的创新,无疑构成集群效应。这种集群效应在不断吸纳新成员,扩大原交际圈的同时,又反过来为学术更新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这种互为因果的文化滋生机制正是促成桐城派与晚清碑学能够成为文学艺术史上并峙的两座高峰的重要原因。
尽管《艺舟双楫》的成书时间较阮元《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后出六载。①参见金丹《包世臣书学批评》(附录)《包世臣年表》(荣宝斋出版社,2007年版)与《阮元书学研究》(附录)《阮元金石书法年表》(荣宝斋出版社,2012年版)。然包世臣早期交游问学已频繁接触桐城派姚鼐、钱伯埛,阳湖派张惠言与张琦兄弟,邓石如、周济等诸师友,其碑学思想的酝酿已在其中。也就是说,包世臣碑学思想既得力于自少时起孜孜不倦的创作实践,又深受益于其交游问学之诸师友的切磋相长而卓然自立。包世臣一生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皆与桐城派的渊系甚深,从而将文坛中与之对立的阮元排斥在外。其碑学思想遂与其文学思想相观照,在桐城派古文大家之文论文法的沾溉下,融入书论,从而彰示出“文书观照,互为阐发”的综合形态,且一以贯之着对笔法、运锋、结体、分势等可操作性性极强、示范意义极大的具体创作技巧的形而下实践品格。这种实践品格非是对阮元碑学思想的具化,包世臣与阮元不存在踵继、阐扬的谱系传承线索。应该说,二人皆自觉地符应着乾嘉以来书坛欲以矫帖学之弊而倡碑学的时代风潮,将碑论谱系的建构单一地归置于阮元一人显然不符合文艺发展的多重交衍脉络历史实际。因此,二人碑学理论应呈“一水中分,二流并进”的峥嵘态势,并在各自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传承后学的发展中互衍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