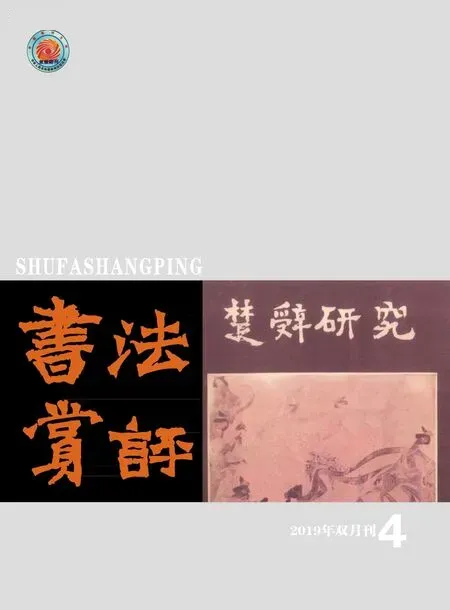博古颖传拓及其在当代艺术创作中的价值研究
2019-01-09王仁海
王仁海
“博古颖传拓”是在长期金石研究和传拓实践中形成的一种新技艺。《辞海》中对“博古”释义之一是指古器物、也指图绘古器物形状的中国画。博古颖传拓即为:“对古器物(包括各类金石碑刻)用颖拓与传拓相结合又加绘事等综合方法来再现的一种新传拓技艺。”[1]在多元文化发展的新时期,对当代艺术创作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一.传拓技艺的历史沿革与创新
(一)传拓技艺的起源与沿革
《中国传拓艺术图典》中对“传拓”释为:“传拓亦称椎拓,是中国特有的保存文献的传统方法,就是用纸、墨和传拓工具从金石器物上捶印其文字和图画的技法”。[2]其是中国传统的一种将事物以图像的形式归真到纸张上,可以说这对于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不可磨灭的意义。它是以湿纸紧覆于金石器物之上,用墨打拓,使器物铭文、纹饰、图形等特征真实复制到纸上的技法。据《隋书经籍志一》载:“其相承传拓之本,犹在秘府。”王国维说:“拓墨之法始于六朝,始用之以拓汉魏石经,继以拓秦刻石,至于唐代此法大行,宋初遂用之以拓古器文字。”[3]可见“传拓”一词早已有之。那么,传拓这种技术方法,至少应在隋代已经产生,甚至更早。唐代以后,传拓技术得到广泛发展。唐天宝四年的《石台孝经》后刻《李齐古表》,表内有“臣谨打本分为上下卷,于光顺门奉献以闻”。又唐元和八年,《那罗延经幢》后有“弟子那罗延尊胜碑,打本散施”。唐代诗人韦应物在其《石鼓歌》中写到,“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白黑分”,讲的是把湿的拓纸覆盖在石鼓的表面,通过击扫的过程而得到白黑分明的拓片。可以看出,唐代的人对传拓技法不仅已经熟练掌握,还能拓出白黑分明的拓本。在宋代的三百年间,传拓从未间断,对古代名碑大量再翻刻、拓制,几乎每个时期都有一批新帖出现,而刻帖内容形式多样,使刻石拓墨技术有了显著提高。同时,金石学的兴起,促进了收藏古物、记录古物和研究古物之风的形成。除了拓印石刻文字之外,政府还采用传拓术拓取青铜器的铭文。自宋开始,传拓技术的提高与金石学的发展紧密结合了起来。明代的传拓方法摹仿宋法。到了清代,金石学有了很大的发展,传拓也得到很大的提高。随着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产生和不断发展,金石学逐渐融入到考古学中,成为考古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使传拓工作有了更广泛的应用空间。因此,传拓在文物考古工作中被越来越广泛的运用。传拓的种类繁多,按拓法可分为擦拓和扑拓;按传拓用墨种类可分为松烟子拓、油烟子拓、蜡拓;按拓片墨色可分为墨拓、朱拓、彩色拓;按拓技可分为淡墨拓、浓墨拓、乌金拓、蝉翼拓、镶拓、隔麻拓、瓜皮拓、夹纱拓、打拓、扫拓、响拓、影拓。而从拓片内容的表现形式上看,最主要的可分为平面拓和全形拓。
传拓技术的形成可以说是不亚于西方文明创作出摄影技术,因为在西方的摄影技术还未形成之前,中国的传拓技术可以说是世界上唯一一种可以让事物以完整归真的图像形式保留在纸张之上的一种技术。同时,也可以让实物在破损的前提下能够完整的保存原来的面貌,对于文化研究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至今已成为明显的“中国元素”符号之一。
(二)颖拓技艺的起源与沿革
“颖拓”在周佩珠《传拓技艺概说》中释为:“‘颖拓’,由毛笔的别名‘毛颖公’引申得名。这种方法,多用笔尖对一些器物进行扑拓,如拓青铜器全形,就得用毛笔来扑拓不足之处。”[4]可见颖拓非拓即画,是画出的一种拓片形式。
邓见宽在《茫父颖拓》[5]一书的前言中述称,“颖拓”为民国初年姚华(茫父)所始创。姚华将自己的作品初称为“响拓”,后又称为“颖拓”。[6]而在姚华《许琴伯朱摹正光三年造象索赋》诗中,则又自述称“我昔为颖拓,闻之蘋萝翁(梁山舟学士),往往写佛像,仿佛出精铜”,[7]是亦有所本耳。姚华生于1876 年,清光绪三十年(1904)进士,曾留学日本,在民国初年,以诗文书画享誉旧京,其颖拓作品曾广受追捧。20 世纪50 年代,挚友陈叔通为了弘扬姚华的颖拓艺术,曾经编印姚华遗作,并广求学者题跋。1954 年至1957 年间,林志钧、邵裴之、马叙伦、郭沫若等人为姚华颖拓《泰山刻石》二十九字所作的题跋,均是应陈叔通所请而作。林跋称之为“临拓”、邵跋称之为“笔拓”、马跋亦称之为“笔拓”,郭跋称之为“颖拓”。[8]以郭沫若学术地位尊崇,遂成定论。
名曰拓,实为画,追求作品的形神、气韵如同拓的一样,以乱真为佳。近代郭沫若对姚华的“茫父颖拓”的学术地位大加推崇:“毡拓贵其真,颖拓贵其假,假则何足贵?君不见绘画,摄影术虽兴,画笔千金价。”[9]颖拓作品亦受到世人的认可和肯定。
世人常混淆椎拓、响拓、颖拓的差异。颖拓亦名笔拓,碑刻拓本与颖拓形式上相似,响拓与颖拓制作法相近。椎拓直接拓自碑刻,留下经捶打斑驳不平的痕迹;颖拓是临摹手写,两者较易辨析。响拓与颖拓同为摹写,故邵裴子(裴之)的跋语就此加以说明:“响拓、颖拓皆笔拓,双钩临摹(面临或背临)原碑帖,最后着墨;双钩后加墨于匡廓内是响拓,双钩后加墨于匡廓外是颖拓;响拓临摹效果若帖本,颖拓临摹效果若碑刻拓本。”邵裴之分别说明了响拓与颖拓的异同,但他通谓之笔拓,故云:“笔拓之法创自姚君,其法与响拓适反。”语意含糊易混。又一跋者林志钧引明代李日华《紫桃轩杂缀》记叙,说明唐人响拓在暗室中对光取映临摹,而林亲见茫父“其拓也,不在暗室中,无有穴牖映取。余曩过莲华龛,见茫父信手用秃笔或团絮染墨渖,对古刻临而拓之,施之纸或绢素无不可”;林“戏称茫父之绝技为临拓,以其与前人响拓殊科也”。
颖拓美的魅力。茫父自题颖拓《汉·满君颂》:颖拓“是书是画无能名之矣。”鉴赏者不乏从绘画角度评论颖拓,郭沫若跋语云:“茫父颖拓实古今来别开生面之奇画也。”宋千居跋语云:“茫翁善画,能以写意摹拓石刻,遂无描填之迹,而有自然之妙。此非深于金石者不易到也。”黄宾虹亦跋云:“叔通先生今来西泠出示茫父手写双钩响拓秦泰山石刻卷,固悟挽近敦煌莫高窟发显唐画粉本,用钻凿圆点作孔楮上,累累若贯珠,画者以粉垩柏黄楮,亦犹画。言起点,积点成线,有线条美,黑白二色是为真色。”茫父言:美“皆须从空处着眼。”他以画法作颖拓,着力于匡廓外,有纯用渴笔,或略加浅墨濡毫取润;有“用米家山(米芾)乱点写法,兼用元人古柏点万叶齐攒”法。郭沫若颇识颖拓三昧,颂颖拓之美:“传拓本之神,写拓本之照,有如水中皓月,镜底名花,玄妙空灵,令人油然而生清新之感。”以玄妙、空灵、神理等传统美学观念审视颖拓,基于想象,又启发进一层想象,以致无穷,以达理想境界。继姚茫之后,周一鹤、姚鋈、张海若、大康(康殷)等均有佳作留存于世。
(三)博古颖传拓技艺的实践与探索
多元文化发展的新时代,通过长期实践研究和探索,单纯的传拓和颖拓已不能满足时代对传承传拓技艺的要求。结合两拓之法并研究清末六舟达受及陈介祺之传拓法,并用现代的科技手法进行了创新形成“博古颖传拓”之新技艺,先要分析一下二人之“器外”与“器内”之不同拓法。
清末南屏净慈寺僧人达受开创了“器外拓”之先河,阮元跋六舟《焦山鼎全形拓本》:“此图所摹丝毫不差,细审之,盖六舟僧画图刻木而印鼎形,又以此纸大小之以拓其铭,再细审之,并铭亦是木刻。”徐珂《清稗类钞》亦道:“阮文达家庙藏器,有周虢叔大令钟、格伯簋、寰盘、汉双鱼洗皆无恙,惟全形锤拓不易,因而真迹甚稀。况夔笙求之经年,仅获一本。复本所见非一。石刻较优于木,然真赝相形,神味霄壤,可意会不可言传,不仅在花纹字画间也。”可见六舟为“绘图刻版,器外施拓”。[10]
清代著名的金石学家陈介祺对摹刻古文字要求丝毫不爽,力追得其神韵,这对刻工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故其常感叹无良工,以致虽富藏而终不得刻传。陈氏以传古为志,“遂屡为同志言之,鲜有合者,盖不知古文字之至足重”,认为“不摹其字而徒释其文,后之读者徒增感叹。古之遗者日就堙没,此学问之事岂玩好之奇耶噫”。其良苦用心诚可感矣。[11]陈介祺《陈簠斋笔记附手札》中道:“作图之法,以得其器之中之尺寸为主。以细竹筋丝穿于木片中,使其丝端抵器,则其尺寸可准……他人则以意绘,以纸背剪拟而已。”《簠斋传古别录》则进一步指明:“以纸褙挖出,后有花文、耳、足者,拓出补缀,多者去之使合。”可见陈介祺重在“器内施拓,绘图分拓”。[12]
在实践过程中,“博古颖传拓”吸收清末六舟达受的“器外拓”的原理,也结合陈介褀的“器内拓”之法,即现有的金石器物可采用器内拓,失传的金石器物(或国家重要不可手拓文物)采用器外拓,不足之处加以“颖拓”和其他绘事等方法辅助完成,特别是充分利用现代技术、新材料的辅助。这种二次创作的“拓品”再现范围较广,通过研究和实践可用于以下几类情况:
一类是原金石器物或碑刻已湮没无迹或剥泐漫漶,但有历史记载和相关拓片资料留世。如用博古颖传拓可再现秦泰山刻石宋拓全貌效果。
第二类是现存国家重要金石文器碑刻等,因保护文物已不允许拓印,便采取参照初拓本而做成器外版进行传拓,对不足之处进行“颖拓”补绘,使其拓色更加贴近原金石器物。
第三类是现存可拓的立体器具类,可采用器内拓与器外拓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博古颖传拓”,从而制作出全形拓。参用“焦点透视法”依据器物原大小尺寸做好器外版而传拓外形,在原器上传拓主要图案或铭文(即器内拓),最后根据视觉需要进行“颖拓”及绘事等补笔。
(四)传拓、颖拓、博古颖传拓技艺的比较与思考
“传拓”可从金石器物上捶印其文字和图案,真实复制图文,但失传的和剥泐漫漶的器物无法再现其面貌。
“颖拓”可参考可视资料基本再现拓片效果,但精细的和特大型的器物无法再现。
“博古颖传拓”利用先进科技与创新方法将器内拓与器外拓相结合,既可体现传拓和颖拓之优点,又可弥补颖拓和传拓的不足。
二.博古颖传拓之技艺特征
(一)博古颖传拓之“器外版”精准传真
博古颖传拓重在再现“文物金石”历史面貌而呈现的拓片效果,故要求其器外版(即绘图刻版)的制作精准和艺术性,所用材质需根据拓片形式效果要表现的精细情况而有所选择,以精准“拓片”博古传真。
(二)博古颖传拓之艺术再现“创作过程”技艺要点
博古颖传拓是结合传拓与颖拓之技艺优点于一体,再把先进科技方法融入其中,有一套较为系统而科学的技艺方法,可根据构图中虚实的需要而进行深浅及浓淡的艺术处理手法。
(三)博古颖传拓之“精拓作品”艺术标准
博古颖传拓作品贵在“与真正的金石拓片作品在观感上十分近似”,并有一定的艺术标准要求。其精品的产生,不离情、理、法三大要旨,其拓制过程包括观物取象、迁想妙得和借墨抒情三个阶段。简而言之,情是指器物图像信息与传拓者主观感受的融合;理是物理、艺理、哲理融为一体的境界;法是将情与理精妙地表达出来的恰当方法。法由心生,无法之法,是颖传拓艺术的至高境界。颖传拓过程由观物取象开始,经过对器物的历史、文化的分析和提炼,在诸多因素综合作用下完成对原物的加工与再创造。观物取象是对器物的形态特质、文化内涵、艺术特色进行全方位的把握;迁想妙得是在接受客体信息的过程中,通过联想的方法来激活创作者的艺术思维,借助个人修养达到主客合一、物我两忘的境界,寻找出合理达情的表述手段;借墨抒情是将这些感受程度以某种方式表达出来。也就是说,由观物取象而取其形,由迁想妙得而畅其神。观物取象是因,借墨抒情是果,从而最终形成高质量的博古颖传拓作品。
三.博古颖传拓作品之审美嬗变
博古颖传拓主要有“拓画”和“画拓”两种,其作品审美嬗变表述如下:
(一)重文物资料价值的“博古颖传拓作品”
随着时间的流失历代铸刻的金石器物和碑刻很多于今已不存在人间,有的剥泐漫漶,今人难睹其貌,通过查阅史料用“博古颖传拓”创作的该类作品,不能无中生有,尺寸如实,其重在金石文物资料价值的再现。
(二)具有文物资料价值与艺术审美价值相融合的金石类“博古颖传拓作品”
这类颖传拓作品再现的是以碑刻或青铜器为表现主体,并对金石器物或碑刻的考证文字运用书法题跋的形式来完成画面,使其形成独立审美价值的金石题跋类“博古颖传拓作品”。
(三)具有文物资料价值与艺术审美价值相融合的博古画类“博古颖传拓作品”
这类颖传拓再现作品多以青铜体或碑刻为表现主体,在此基础上补画花卉蔬果而相互配置构成画面,根据构图需要落款题跋后形成既具有金石文物资料价值、又具有审美价值的“博古颖传拓作品”。
(四)在国画作品中处于次要表现元素,有审美情趣而不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博古颖传拓作品”
这类作品多以国画其他题材为主体,为构图需要部分空间加“拓”的“博古颖传拓作品”,虽有一定的审美意趣,但非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
四.博古颖传拓在当代艺术创作中的价值
(一)“博古颖传拓”在当代审美文化中的尚古情怀
“博古颖传拓”再现的是“古”碑或“古”器具,这也正符合我中华民族审美文化心理,受传统文化影响,中国人崇“古”重“礼”的文人情怀传承至今,与时下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高涨热情是一致的。
(二)“博古颖传拓”在当代金石视野研究中的博古传真
“博古颖传拓”之技艺重现金石类作品,既保护了文物又重现金石拓片之面貌,从金石视角研究方面填补了一项技艺空白,再现的艺术作品可满足金石考证历史复原及题跋艺术的需求。
(三)“博古颖传拓”在当代绘画多元发展中的应用推广
在当代艺术多元发展创作中,用好民族传统文化元素符号,无疑“博古颖传拓”是较好的技艺之一,逼真的拓片效果会比线条手绘等表现的更具有“中国金石味”。
通过实践研究可知,“博古颖传拓”的每一幅作品:“都是作者参照原拓、文献资料或原器物,在忠于历史和原器物的基础上,进行二次创作的复合原创性作品,集捶拓、颖拓、书法、绘画艺术于一身,而不是简单的墨拓技艺的展示。[13]”“博古颖传拓”每一幅作品:“对墨色变化、构图形式以及书法题跋的内容和形式都有较高的艺术要求……只有精于书画创作、金石考古及碑帖鉴藏者,才能创作出优秀的‘博古颖传拓’作品。”[14]用此技艺可再现流失或残破的金石器物和碑刻,并拓宽了传拓技艺的范围,在传承的基础上又有了创新和发展,对文物保护有很大意义;其再现金石作品的技艺也是当代艺术创作绘画的一种新的技艺方法,对当代艺术多元化的创作、作品呈现丰富的中国元素符号是有一定的启迪意义,对讲好“中国故事”的当下文化传播更具有现实的时代价值。
注释
[1]王仁海《拓印技艺的传承与创新——以博古颖传拓为例》,《中国书法·书学》,2017 年第8 期,第132 页。
[2]国家图书馆编《中国传拓技艺图典》,故宫出版社,2013年,第15 页。
[3]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林文光编著《王国维文选》,四川文艺出版社,2009 年,第93 页。
[4]周佩珠《传拓技艺概说》,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 年,第68 页。
[5]邓见宽《茫父颖拓》,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4 页。
[6]徐传法《颖拓艺术研究》,《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5 期。
[7]姚华《弗堂类稿》诗丁,中华书局,1930 年,第23 页。
[8][9]邓见宽《茫父颖拓》,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4 页。
[10]郭玉海《金石传拓的审美与实践》,故宫出版社,2015 年,第63 页。
[11]陆明君《簠斋研究》,荣宝斋出版社,2005 年,第80 页。
[12]郭玉海《金石传拓的审美与实践》,故宫出版社,2015 年,第64 页。
[13][14]王仁海《基于欧阳中石先生书学理念的“传拓文化”研究》,首都师范大学编《弘文焕采——欧阳中石先生书法教育思想研究文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376、37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