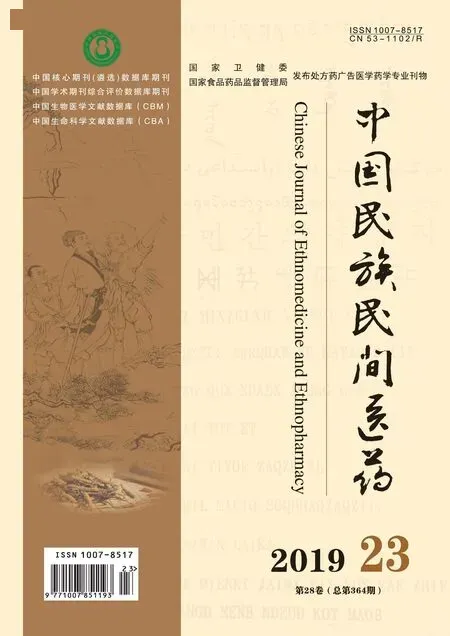陈乔林治疗外感热病验方“加味葛根芩连汤”与验案一则
2019-01-07
1.云南中医药大学,云南 昆明 650500;2.云南省中医医院,云南 昆明 650021
外感热病是因感受六淫邪毒或疫疠之气,正邪交争,以发热为主的一类病证。陈乔林主任医师为云南省名中医,全国第二、六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长期从事急诊医疗、教学、科研工作,治疗外感热病经验丰富。文章介绍陈乔林主任医师对外感热病的认识及其验方“加味葛根芩连汤”的临床运用。
1 病因病机
陈乔林主任医师认为,外感热病的基本病理机制是阳郁为病。《素问·热论》有云:“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1]”张志聪注释:“凡外淫之邪,始伤表阳,皆得阳气以化热,故曰:凡热病者,皆伤于寒之类也。[2]”张氏将“寒”释为多种外邪,皆得阳气以化热。这也正如王冰所注:“寒毒藏于肌肤,阳气不得散发而怫结,故伤寒者反为病热”[3],并解析说:“寒气外凝,阳气内郁,腠理紧致,元府闭封,致则气不通,封则湿气内结,中外相薄,寒盛内生,故人之伤于寒,转而为热,汗之则愈,则外凝内郁之理可知。[3]”韩祗和尤其注重阳气郁结,其云:“夫伤寒之病,医者多不审察病之本源,但只云病伤寒,即不知其始阳气郁结而后成热病矣……伤寒之病,本于内伏之阳为患也。[4]”刘河间赞同外凝内郁的观点,其总结说:“寒主闭藏而腠理闭密,阳气怫郁不能通畅,怫然而作,故身燥热而无汗”[5],“非谓伏其寒气而变为热也”[5]。感受六淫邪毒或疫疠之气,邪正激争对峙交困,正气欲拒邪外出而未能,这种态势可以一个“郁”字来概括,相争于表为表郁,相争于里为里郁,表里俱相争为表里皆郁。
2 临证经验
陈乔林主任医师认为,治疗外感热病,针对“郁”这一病证发展转变的重要环节,最重要的治疗方法就是透邪外达和泄越其热,以达到顺正祛邪、激浊扬清、破郁为通的目的。
加味葛根芩连汤是陈乔林主任医师治疗外感热病的常用经验方之一。方药组成:葛根30 g,黄芩12 g,黄连12 g,炙甘草10 g,僵蚕10 g,蝉蜕10 g,大黄10 g,瓜蒌壳10 g,瓜蒌仁10 g,法半夏 10 g,胆南星10 g,生姜汁一匙。该方主治外感热病,表里俱郁,临床症见壮热,有汗或无汗,咳喘痰阻,口气臭秽,腹胀便结或下利臭粪,舌尖边红或舌红,苔白或黄,脉浮数或滑数。其方以葛根芩连汤为主体,重用葛根解阳明肌热,黄芩、黄连清肃阳明里热,配以蝉蜕、僵蚕、大黄,寓升清逐秽之意。用于秽浊重者,口臭难闻,便结,昏沉,用瓜蒌、法夏、胆南星合黄芩、黄连成小陷胸汤,去胸膈痰热,喘咳痰漉。姜汁安胃降逆。热盛动风者,加龙胆草、地龙、钩藤。
陈乔林主任医师指出:“葛根芩连汤”出自《伤寒论》:“太阳病,桂枝证,医反下之,利遂不止,脉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葛根黄芩黄连甘草汤主之。[6]”因误下而变生利遂不止,当为协热下利,脉促只是邪陷,邪正互争,尚未酿成完全里陷,气乱还出于上所致。这是仲景救治误治的医案,表证误下,外邪入里化热,下迫上蒸,被称为阳明表里热病。此处之“表未解”,不是说尚存在桂枝汤证,而是说阳明经病之阳明表证(表象),而里热证,指的是阳明胃府热证。陆九芝是这样理解的:“……太阳之表病,因下而变为阳明之里热矣。而脉促喘汗则尚能为阳明表证,故凡阳明表证当以此方为主方,不必因乎误下,亦不必有下利证,但见脉促喘汗即可用此方耳。”葛根在本方中是解阳明肌热,不是如同麻、桂之解表,其与芩、连为伍则作用于阳明,与麻、桂为伍则作用于太阳。它与《伤寒论》所云:“太阳与阳明合病者,必自下利,葛根汤主之”[6]恰成对照,葛根汤之下利为风寒兼犯肠胃,粪不臭秽。《世补斋医术》陆九芝提出“病之始自阳明者为温,即始自太阳而已入阳明亦为温”[7],“质而言之,温病者,阳明也。[7]”所以陈乔林主任医师经验方“加味葛根芩连汤”是由葛根芩连汤加味而得。
3 验案举隅
患者马某某,男,2岁2月。2017年12月29日初诊。主诉:高热1天,惊厥1次。现病史:患儿于2017年12月28日晚受凉后出现发热,最高体温39.5℃,手脚凉,孩子自诉有害怕的感觉,易惊,无鼻塞流涕,无咳嗽咯痰,无腹痛腹胀,大便白天已解,色黄,成形软便,小便正常,给予中药汤剂口服(蝉蜕10 g,麻黄10 g,葛根18 g,炒黄芩15 g,白芍10 g,生石膏25 g,银花15 g,连翘15 g,浙贝母10 g,生甘草15 g,槟榔10 g)并间断(体温达39℃时)按药物说明给予布洛芬混悬液口服及物理降温,体温可稍降,但不能降到正常,整晚体温波动在38~39℃之间。29日早晨仍有发热,体温在38~39℃之间,于09∶00左右孩子发生惊厥,持续约20余秒,发作停止后其母立即给予“地西泮2.5 mg”口服,急送医院,给予“苯巴比妥55 mg”(5 mg/kg,11 kg)肌肉注射,并给予“安宫牛黄丸”1/4丸水研灌服,经治疗后孩子退烧,遂带孩子回家继续口服以上中药汤剂。到下午14∶00左右,患儿再次发热,体温逐渐升高,16∶00左右体温 39 ℃,再次带孩子到医院查血常规,提示:白细胞计数、中性粒细胞计数、淋巴细胞计数降低,超敏C反应蛋白正常,淀粉样蛋白升高。于18∶00请陈乔林主任医师诊治,患儿症见发热,体温 39 ℃,胸腹热,手脚凉,无汗出,孩子自觉害怕的感觉较昨天明显减轻,偶尔会感觉害怕,无鼻塞流涕,无咳嗽咯痰,无腹痛腹胀,精神差,由家长抱着,时醒时睡,时有哭闹,饮食差,进食少量白米粥,不会主动要水喝,大便未解,小便正常。既往史:有复杂性高热惊厥病史,足月顺产,混合喂养,按计划免疫接种。过敏史:否认药物及食物过敏史。体格检查:体温 39 ℃,精神差,由家长抱着,时醒时睡,时有哭闹,咽充血明显,扁桃体Ⅲ度肿大,无脓性分泌物,双肺呼吸音清晰,未闻及干湿啰音,心率134次/min,节律整齐,各瓣膜听诊区未闻及病理性杂音,腹软,按压时患儿无抵抗或特殊表现。触诊胸腹热,手脚凉,无汗出,舌尖稍红,苔根稍白腻,指纹紫,刚达风关。辅助检查:详见现病史。西医诊断:热性惊厥;中医诊断:外感高热并急惊风(表里俱郁,热盛动风,痰热互结。)治法:清热止痉,化痰祛风,辛凉解表;处方:加味葛根芩连汤加减:蝉蜕10 g,僵蚕10 g,葛根15 g,焦栀子8 g,淡豆豉10 g,炒黄芩12 g,炒黄连6 g,天竺黄6 g,瓜蒌仁6 g,胆南星6 g,生大黄6 g(中药汤液泡5 min),蜂蜜少许,黄酒3~5滴。1剂。嘱不再使用“安宫牛黄丸”,改用“紫雪丹”。(但当晚没有买到“紫雪丹”,故未能服用)。上方水煎,首煎,当晚灌服2次,每次约20~30 mL。服药后热退身凉,未再发热。
12月30日复诊,患儿未再发热,手脚仍凉,不再自觉害怕,开始咳嗽,咳嗽频繁,干咳无痰,无鼻塞流涕,精神好转,饮食有所增加,进食白米粥量增加,大便已解,溏,色褐,臭,小便正常。舌尖稍红,苔根稍白腻,指纹紫,刚达风关。方药:射干8 g,生麻黄5 g,蝉蜕8 g,桑白皮8 g,瓜蒌皮6 g,前胡8 g,胆南星6 g,化橘红8 g,银花10 g,连翘10 g,芦根20 g,生甘草10 g。1剂。
12月31日复诊,患儿咳嗽明显减轻,仍干咳无痰,无发热,无汗出,无鼻塞流涕,手足开始微温,精神明显好转,进食量基本恢复平素水平,大便溏,臭,小便正常。方药:上方麻黄减为3 g,加刺蒺藜5 g。2剂。服药后痊愈。
4 小结
该案为外感高热并急惊风,小儿脏腑娇嫩,形气未充,腠理不坚,在气候突变,寒暖失调时,六淫或疫疠之气,从口鼻或皮毛而入,使肺气郁闭,腠理郁滞,阳气不得宣泄,积阳生热,热极生风而发病。又因热邪煎津生痰,致使痰热互结,使病更甚。病机正如上文所述感受外邪,邪正激争对峙交困,表里俱相争,致表里皆郁,郁而化热,热盛动风。治疗的重点在透邪外达和泄越其热。选用陈乔林主任医师验方“加味葛根芩连汤”加入栀豉汤、大黄,尚有仲景小陷胸之义和杨栗山升降散之义在内,疗效较好。